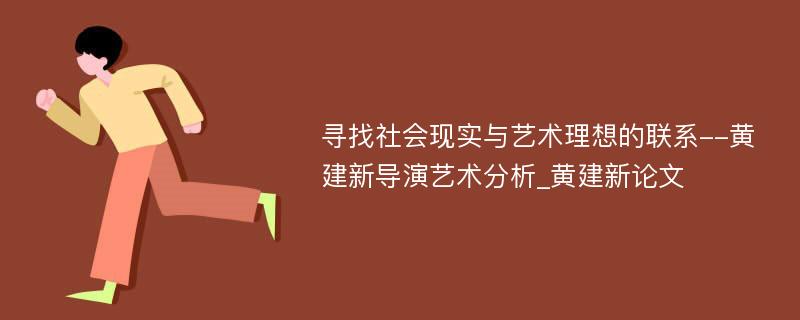
寻找社会现实和艺术理想的契合点——黄建新导演艺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导演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6-0064-09
中国电影很快将要面临进入WTO的考验,全球化的背景对中国电影的威胁已经日益临近,我们亟需加快研究对策。总结中国电影的历史成因与显在问题,探究如何发挥中国电影的特性,以建立自己的独有品格,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在跨世纪的关口,怎样把握艺术理想和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使艺术能和现实取得较好的呼应,这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问题。一些出色的导演在创作中逐渐摸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很好适应了时世变化,黄建新就是典型的一位。分析他的创作特点,有助于我们看清电影艺术是如何在创造中前进的,也有益于今后中国电影的进步。
一、风格与形态的圆熟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建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电影现实与电影理想相互关系的一种表征,即从对传统无所畏惧的反叛与创新开始,表现出努力实现个性理想的独特果决倾向,进而融合传统,面向现实社会的微细动向,挖掘俗人俗事中的微言大义,明显走向谐和、平和、调和,呈现出创作的圆熟状态。
“谐和”是在形式上寻求与现实内容相协调的不动声色的表现形式。事实上,黄建新的艺术轨迹就是中国电影从外在形式到内在蕴涵探索的一种缩影。在《黑炮事件》中形式的刻意追求是十分醒目的,大块的色彩设置(工地的橙色机械、会场的纯白、巨大挂钟的黑色等),明显的大物件和人的对比,情节的精心设计,细节的巧妙安排(如赵书信看孩子推多米诺砖阵等),都不惜以触目惊心来达到冲击视觉的效果,从而引人思考。而90年代的创作就明显不同,反朴归真的形态一目了然,如不好不坏的生活平民(《站直罗,别趴下》),觊觎官位的明争暗斗(《背靠背,脸对脸》),起哄装蒜卖乖讨好的各色人等(《红灯停,绿灯行》),尤其是《埋伏》的生活状态自然流畅,生活进程和人物的心绪情感共时呈现,事态就是情态,嬉笑怒骂都从声画中来,构成当代都市连绵不绝的人心民情的风俗画,到了《说出你的秘密》则更为谐和自然。
“平和”是指在人生态度上从尖刻嘲讽、犀利剖析的先锋状态(早期),转为平和看取生活的缺陷,把嘈杂纷乱的原生态现实视为正常,甚至默认含有不理想的生活情态才是合理的生活现实。这在《轮回》的内容中表现已然明显,到“城市百态三部曲”则根深蒂固了。在《背靠背,脸对脸》中,王双立曾狡黠机警应对上上下下的攻讦,但最终却“透视”了为官之道的无聊乏味,对升迁与否浑然无谓了。实际上,不管他是耍尽聪明的争夺由副转正的权利,还是无所谓的听凭世事纷争而自享其乐,电影表现出来的观世态度已不是愤世疾俗而多少含有冷静旁观的意味。“平和”可以更深入的玩味世事的奥妙,也有可能更好的展示人生剖析社会。在《说出你的秘密》中,都市人们现代形态的常态生活和意外导致的变异表现以不动声色的影像显示,深入到更为隐微的心理世界的内里,使他的电影继续保持相当的艺术水准。
“调和”表现为在政治主题的讽喻性和宽容性上趋近于调和,《黑炮事件》、《错位》矛头所指无疑是官僚习气、社会政治风习的弊端;《轮回》表面上玩世不恭,但对政治的直接抨击力已是隐藏了许多;“城市百态三部曲”中除《背靠背,脸对脸》外,都更加重视对世俗人心的展示与剖析,即或是《背靠背,脸对脸》对现实政治的表现,也被王馆长悟透人性而平和恬淡的处世态度所冲淡;而《埋伏》的处理则基本完成了这种调和,尽管英雄的行为纯属歪打正着,英雄的形象也是反传统的、多含卑琐私情,但影片宣扬的的确是主流政治所崇尚的正宗主题。黄建新的视角已经不是激烈外向的揭露表层生活,而是冷峻深细地剖析平常生活的深层蕴涵,需要观众细细琢磨和领悟,因而他的影片具有沉稳中显机智,调和间显犀利的风格。可以看出黄建新创作十余年的变化,证明它和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有某种程度的吻合。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黄建新的电影形态变化又是中国电影形态变化的一个缩影。
黄建新电影早期呈现出形式和艺术手法刻意求新的形式化明显特点,而后期的创作则形式比较自然,追求生活化的表现方式,这和我们所见的中国电影的逼近生活化的趋向是一致的。只要想想从《秋菊打官司》为明显标志的实景拍摄的贴近生活,到《民警的故事》的同期声、非群众演员表现的全生活化,中国电影变化趋势明显。黄建新都市题材的电影的落脚点,也相当典型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90年代中期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现代都市文明为背景的电影较多出现,不仅是题材变化的结果,其实也是生活现实的要求,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电影更加趋近现实的必然。复杂的城市生活现代化进程通过电影得以表现,也证明电影跳出以古老农村为对象来展示旧俗奇观、揭示传统弊端的窠臼,而更加与现实生活合拍。黄建新的电影牢牢抓住这一点,在追踪生活变化上眼光远大,立足点牢靠,因而总是不落后于时代潮流,受到观众的青睐也就在情理之中。
综观黄建新电影,呈现的是颇为独特的艺术世界:即既长于细致入微的个体把握,又具有广阔宏观的生活关照;既有丰富灵动的生活描述,又不乏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贴近并再现生活的原生态,又实为精心的艺术构思。换言之,黄建新是以艺术追求的独特性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因此,黄建新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伴随中国电影变化进程而始终把握独立品性的艺术家的追求过程——以稳健的创新和扎实的艺术发展形成创作的鲜明轨迹。
二、注重现实性的理性思考
黄建新被认为是长于理性思考的当代导演,他所走过的创作路程都是自觉主动的结果。我们从《黑炮事件》的选取与改编的思路,以及大胆取用超乎常理的表现手法来看,确实可以发现他的思考动机与目的。这种敏于思索的个性也使原名叫《浪漫的黑炮》的小说更加突出了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批判力度。而众说纷纭的《错位》则更是黄建新主观意识的现实产物,即或它不是大力褒扬的作品,但努力思索的印记是十分明显的。至于90年代标志黄建新电影突出成就的几部都市电影,则是黄建新对眼花缭乱的世道变化积极思忖后的主动选择的成功结果。
当然,上述尝试并非全盘成功。比如,单就《黑炮事件》而言,过分形式化的追求和十分明显的理念未必是人们所推崇的。但重要的是,这部片子的艺术构思和创新意识如此强烈,对电影语言的革新大胆果敢,和80年代中期影像美学的崛起合拍呼应,对中国电影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黄建新在此片里表现的现实批判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动人。就黄建新电影的贯穿线索而言,从《黑炮事件》开始,无论思想情态如何变化,他对社会的关注,对国运民生的思考是始终如一的。
而《错位》的成就就不那么可观,它的问题不是出在如一些作者或评论家所言的“太超前”,而是“太落伍”,即在转瞬即逝的形式探求热潮中固执的进行更为抽象的理念表现。《黑炮事件》把借鉴和创新已经处理得令人信服的新鲜到位,并有出人意外的花样翻新,而《错位》却并没有显现出独特的创造魅力。如果说人们为《黑炮事件》瞠目惊异的话,那么《错位》则已是惊奇满足过后,新鲜不再了!更重要的是,《错位》远不如《黑炮事件》内容扎实,虚无缥缈的故事也许更能显示创作者的思考理性,却难以引起中国百姓的感性共鸣。所以《错位》只能是黄建新的错位:形式的错位实为观念认识的某种错位,至少可以说,《错位》的不足是“虚”置情境,情“隔”大众,缺少鲜活气。
应当承认,黄建新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理论准备,它决定了黄建新电影创作所具有的优势,由此也可以理解黄建新创作思考的必然性。所以,当黄建新创作他的第一部影片《黑炮事件》时,让“摄制组的主创人员集中读了一些书籍,主要是一些有关方法论和艺术新学说的书籍”[1](p399)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当然,对导演创作而言,问题可能还不在是否具有思考——尽管当代导演真正具备理论素养的并不多,但黄建新的成就是和理性思考的现实关照相联系的。就是说,他不仅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质,而且具有和现实问题相关照的视野,从而使其创作具有宽阔的视野和踏实的基础。在1985年向古老文化反思的浪潮中,黄建新没有随同去投注于历史陈迹和农耕文化的大潮里,但他同样是在反思批判。《黑炮事件》的都市现代背景和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文化反思的深刻性,因为他的视点始终忠实于自己所生长的当代社会,从现实入手更能抓住传统的弊端。在现代化的工业文明背景下人们竟然保留着极不协调的悖时眼光,这揭示的本身就十分新颖,其思想深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黑炮事件》的不同凡响证明黄建新对社会现状的贴近和关注。
《轮回》的情况比较复杂,就号称“王朔电影年”的1988年来说,传统观念是颇为反感的,这牵扯到非主流人物、某种程度的反严肃政治的“痞子”思潮占据正统领地的问题,也牵扯到娱乐文化大肆进军曾被目为艺术神圣之殿的电影的如何评价的问题。此片是表现都市生活电影的较好之作,它保留王朔创作的基本倾向——尽管那不是令人高兴的现实内容,但作了许多改变:玩世不恭仍在,但社会批判加强了;表现的轻松性和展示城市生活中某一类青年心态神态的意义明显,但添加了一些表现善良(如石岜的结局所透视出来的东西)、苦恼(如刘华玲的富足却不满为钱的生活)、真挚友情的内容(如石岜和晶晶的情感),使王朔的调侃和世俗化减弱了,在艺术表现上也比较成熟,可以视为都市片中的好影片。从传统的观念来判断,石岜们的行为不应为社会所认可,津津乐道于边缘人物的出格犯忌,不免有损时代的正题,而且类似的故事和相近的表现对象在以后的都市电影中屡屡出现,这使得不少人很为担忧,但影片所表明的正视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某一类人及其存在现象的态度,无疑是应当的。在揭示都市青年无法回避的理想矛盾、情感困惑和行为误差方面,黄建新的敏锐和细致是值得赞许的,从跨世纪中国电影的开放姿态来看,这种表现也是时代的必然。
更为典型的表现是黄建新从澳大利亚回国后的创作实践。面对他2年未见、颇为“陌生”的中国社会,黄建新的反应是不知所措:“我一直被一种感受强烈地撼动着。那就是周围的巨大变化所形成的我未曾体会过的生存观念和信仰的大裂变,这包括与改革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我试图去掌握它而无从下手。”[1](P416)他没有闭门造车、空自思考,而是请假到各地去看看,对改革开放的大势和由此引起老百姓的心理变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的思考更加深入,“通过走走看看、说说谈谈,一个事实展现在我面前,这就是传统价值观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发生了动摇。”[1](P416)黄建新被这较过去远为复杂丰富的生活现象吸引住了,他的思考紧紧联系着活生生的现实,要去探究这里的文化现象。于是黄建新的新都市电影就诞生了。在那里,动态的现实和有内涵的文化思考集合在一起,构成都市百态众生相。颇为流行的老百姓口头禅“站直罗,别趴下”,就是个人思考和现实关照的最好说明。
无疑,《站直罗,别叭下》是当时表现都市生活的出色之作。它和1992同为现代都市背景的几部影片:《青春冲动》、《四十不惑》、《天堂回信》、《找乐》一起构成整齐的质量。黄建新在他这部作品中开始了他的一个新的时期,就是表现城市人的种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黄建新的目光定位于此,就开始再一次展现他的独特之处,并奠定了他作为现代都市电影的代表导演的地位。在此片中,黄建新十分准确的抓住了90年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人的巨大心理变化,通过相邻的三位不同地位、身份人物的矛盾冲突,相当准确的揭示了时代的特征:金钱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当高作家、刘干部、个体户张勇武在或明或暗的角逐争斗时,我们感到每个人的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是一个变动时期的必然现象。本片最有意义的就是不动声色描绘了变化的细致过程和心理机缘。以刘干部为例,他对传统是非“颠倒”愤愤不平而又不动声色的抗拒,尽力遏止扭转的世态,靠积极的舆论和纯熟的避开锋芒的策略对付发迹的对手,却不仅不能改变现状,反而被现状所改变。他从不满、失落、软磨硬抗到随波逐流、进而主动妥协的过程,其实就是从改革初期过来人们所经历的矛盾过程。张勇武的霸道蛮横固然遭人嫉恨,但他托时代之福而生活得以提高,在生存地位变化的同时情感也发生微妙变化,确实耐人寻味。他所代表的原本卑微,但生逢“运世”而发财致富的幸运儿的经历,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它恰恰证明了人的物质地位可以改变精神状态,和精神情状常常离不开物质基础制约的道理。我们当然不会因此认定张勇武是时代的标杆,他的粗俗无理仍然与他的发迹相伴随,他肯定要在深入的改革年代遇到新的人生困惑,但影片所展开的特定年代的生存情态和心理状态,确实是很真实动人的。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仿佛看到身边发生过的种种现象和各色人等。
有理由说,黄建新正是在重视现实性的思考上达到创作的不同凡响。
三、注重平民化的文化阐释
黄建新的电影是卖座的电影,但决不意味着哗众取宠、只为票房,他的电影是文化电影,只是黄建新极为聪明地抓取了中国老百姓的兴趣愿望而已。
所谓注重平民化的文化阐释,就是指黄建新电影的立足点在普通老百姓的通常关注的社会生活兴趣上。凡人小事,斗嘴下棋,妇姑勃谿,哪怕些微的官职升迁都会引发针尖对麦芒的计较攻讦,邻里间鸡毛蒜皮小事也都要牵涉到国政大事、都会引轩然大波。平民化的视角和普通人的情感体味,在黄建新电影中栩栩如生的展示着。在黄建新电影中,我们找不到恢宏的历史曲折斗争,也无法重温铁马金戈的战争烈火和呛人硝烟,一切如常、又出乎常态,从而产生动人的光彩。简言之,黄建新电影是平凡人的故事流程,是小人物的心态表露。(虽然其间不乏某种狡黠、也常常带出讽喻。)
黄建新电影表现的是十余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情态,它是透过最为平凡的人物和最为明了的动机来展现的。备受猜忌的知识分子、没有生活落脚点的无业青年、心存不平的失落干部、善良而怯懦的作家、无礼搅三分的个体户、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物等,都是“小人物”,他们的行为方式最为直接的代表社会大众,而他们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也无遮拦的表现着生存的赤裸裸目的,在这样真实情态的社会群体面前,人性的真善美丑毕露无遗。
这在《站直罗,别趴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引起我们兴趣的不仅仅是该片的生活原生态的生机勃勃(那份生活气息一半靠的是恰如其分的表演和演员选择),更主要是选取的角度和对此的评价。我们发现,惯常所用的正误好坏的价值标准在这里已根本转变,因为不是历史人物,也不是“大人物”(历史人物重在价值评判,“大人物”则必有政治分野——好坏优劣),所以表现不在甄别,而在剖析上。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牵连着社会人心,但小人物就没有必然的正反,小人物永远在世俗生活中争相表现着他们的优点缺点,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强行区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黄建新认为影片中的“这些人,人人有毛病,家家有苦衷;人人有优点,家家有真情。”[1](P419)因此,他一改过去拍摄的惯例,不去做导演阐述,而要求在拍摄中去发现去体会。这种不重人物政治分类,而重生活原生态的表现角度,是黄建新电影的独特之处。
《红灯停,绿灯行》的问题则明显增多。都市生活的变化莫测固然有了某种表现形式,但在这部片子里,黄建新的优点多少丢失了。首先,影片颇为虚空,没有实在的内容,明显是硬凑起各色人物,宛如太刻意的拼盘,令人怀疑其可信度,试图呈现生活的真实,却缺少合理的逻辑性。其次,影片有垃圾化生活之嫌:吃学员贡礼的教练、富得流油的大款学员、吸毒却孝顺至极的长发学员、憨直心善的女性学员等等凑在一起,试图表现生活中各种人的状况,复杂是复杂了,却很难让人舒服。实际上,本片还在延续黄建新对“典型化”生活人物的剖解方式,却走到了故意做作的程度。更为明显的不足,是对生活浮光掠影的匆忙表现,在看似多种职业多种性格人物的表现上,同样的调侃,貌别神同的话语,不约而同的行为举止,都使剧中人物缺少性格深度。影片与同一时期相似题材的一些电视剧和都市作品犯了同一病症,即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含蕴不足,而且,电影艺术表现也无甚突破,这使得该片远逊于作者此前的两部都市片。
《埋伏》回到黄建新表现人物的基点上,关注小人物的复杂心性,他们本质善良,又并非纯净得没有七情立欲。男主人公原本普普通通,有爱欲,有私利,嘴上不满世事,却依旧混同流俗。本片的优点是使个性人物的“七情六欲”充分展示,又使之阴差阳错的受尽磨难,而把非英雄的英雄化过程剖开给人看,相当真实。叶民主的反英雄化形象,是和黄建新对普通人的理解一致的。他们无甚大志,常怀幻想,虽期求不高,仍难免落魄,唯一不变的就是叶民主们心地颇好,感念别人,也被人感念(叶民主和田恭顺彼此之间最可佐证)。创作者高明之处是以细枝末节来剖解平凡人最隐秘的情感,在星星点点的表现中挖掘常人不经意但其实高尚美好的东西。整个故事的巧合是在显示普通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他们的闪光其实连自己也不见得意识到。本片突出表明黄建新观念中的英雄认识,他让平凡之躯在不能不为之工作的被动中取得精神的升华,叶民主即使成了破案功臣,也依旧是非英雄的普通人,(他痛打邱建国就是证明),但普通人的英雄化则更加动人。叶民主能抛开恋人,死死坚守水塔的动力,其实正是老田给予的榜样力量。认可平凡的英雄,承认英雄无处不在的观念,这正是黄建新创作始终或显或隐地存在的内涵。
黄建新电影的小人物表现是他的文化阐释的结果。黄建新电影的人物,都处于比较“尴尬”的处境,在世俗洪流中,他们没有纯净的避难所,恰恰因此,才格外显露艺术所容易忽略的“日常状态”。黄建新认为文化就在每一个人身上,就在朴实无华的现实生活里。所以,他要从文化的角度去看今天的人们在想什么,作什么,出了什么毛病。他对平民百姓的描述,既不是悲天悯人的同情和歌咏(那还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优势者的惯用伎俩),也不是毫不留情的鞭鞑谴责(那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批判),而是真实透现社会存在的问题。黄建新表现人物表面上是采取了间隔远离的态度,而实际上是折射社会世态人心。
我们可以这样评价黄建新:他固然不是宏大气象的表现者,没有浪漫激情的慷慨之态,却以隐藏在冷静背后的狡黠、冷眼旁观式的关注而赢得都市百姓的青睐,他以文化的阐释赋予平民生活以新的含义。
四、独特的艺术探求表现
黄建新电影艺术表现的形态是变化的,大体而言,经历了从形式探求、刻意求新到文质浑融、求诸自然的过程。正如人所共知的,化入了表现内容的无形之巧的“技巧”才是成熟之境。90年代,当黄建新得心应手的施展才华于都市题材时,他的电影表现的纯熟真正得以体现。这里着重概括其中的几个方面。
1,注重人物心理剖析。对人的关注必然从外在深入内在,优秀的艺术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把握应当准确而深刻。黄建新的视角显然和人的命运、人的心理世界的展示息息相关。早在《黑炮事件》中,对赵书信的内心感觉很大程度是通过他的无奈表情和似乎随意的行为来表露的。在《背靠背,脸对脸》中,人物的心理感觉更具微妙,是在副馆长似乎小视职位的潇洒和实则无奈中透露出来的。让观众细致入微的体味无奈人生和有苦难言的内心隐衷,是影片对人物命运思考的深入标志。及至最新的《说出你的秘密》,对人物心理的深入揭示更为内涵。从心理层面揭示人性的多样复杂性,证明黄建新对人的认识的特殊立足点。作为黄建新新一轮都市片的成熟之作,影片在稳重的结构和老练的叙述方式中深入到现实世界中人的内心深处进行探索,它的动人处是对人生思考的丰富性剖析。影片表现车祸后逃匿的犯罪心理的搏斗过程,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多面和复杂。影片展示的是现实中普通而和美的家庭生活发生的波澜:夫妻心眼都好,家庭气氛和谐,但面临秘密被揭破的恐惧而导致的猜忌、担忧、困惑。我们真切看到现实生活中常人完全可能遇到的心理危机,和人性如何挣扎、善良如何苏醒、美好怎样升华的真实过程。影片对人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剖析,深入到人性挖掘与心理拷问的层面。
中国电影的世纪末忧虑其实多半与观众疏离有关,除了大众化时代必然产生的艺术门类发展而导致的分流,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传媒对电影的冲击之外,电影停留在事件描述层面和粗浅的直接说教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除非屈从世俗,堕入打打杀杀和脱、透、露式的泥沼,否则就要在根本的人文精神上下硬功夫。中国电影的人文艺术味日渐消失是很值得忧虑的大事,人文电影的天地其实很大,而其要害是对人性和人的内在思想与心理世界的剖析。在这方面,黄建新的新片《说出你的秘密》是较为成功的例子。它揭示了我们常常不敢正视的心理现实,显示了创作者对人生探讨的认识深度。影片的揭密不仅在撞人逃逸者是谁的谜底上,而且落脚在常人面对这道难题时将如何正视的心理谜底上。在夫妻恩爱和怀疑猜忌之间,在良心谴责的道义感和惟恐罹难的恐惧感之间,影片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弱点、本能与人性良知之间的搏斗。丈夫执着寻找目击者的道德感和日益深重的犯罪感的痛苦心理、惟望不是事实的侥幸心理的角逐,把当代生活中一个清白家庭可能遇到的恐惧和抉择平铺在我们面前。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之后,将陷入怎样一个心理矛盾之中?这种不由自主的抉择和随之的痛苦又可能是常人刹那间都会遇到的,和美的家庭和谐和的夫妻关系在特殊状态中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又会如何处置?影片的现实主义表现与带人生哲理的思考,是从心理层面展开的。这种从现实简单事件推向心理承受极致的人性思考带相当残酷的成分,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在维系亲情和躲避危害时必须抉择的尴尬痛苦。所以,影片比起赤裸裸的表现现实人生多了思想的负重,警示人们思考,尽管这种影片优美荡然无存,但深刻成为可能。
2,意外的关节点构思。黄建新电影的文化性没有妨碍观赏的引人入胜,他对情节进展的关节点和变化的转折点的把握具有顽强的信念。故事核心的意义常常依靠转折的意外来显现。比如《黑炮事件》中一枚象棋卒子的构思成为影片物小意大的标志,同时也是始终吸引观众情态的物件,透过棋子,人生百态和政治炎凉,一一得以显现绾联。在《埋伏》中,主人公的遭际是建立在叶民主被缺少公德的人忘了通知的失误事件上的,这具有双重的揭示意义:官僚主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忽略和普通人对人生偶然的必然态度。影片给予我们的思考不是平面化的,牵连事件的事故中隐藏的价值判断丰富而深刻。在《背靠背,脸对脸》中,情节的转捩点是王双立到手的几次提拔却意外落空的挫折,仕途的升沉不定、人心的难测、做人的进取达观与消极退缩之间的态度全面亮相。《说出你的秘密》的关键就在车祸的偶然出现和人物的内疚,帮助受伤者却被误当作助人为乐者的情节点。前者引来家庭的悲欢异常,后者深刻显示了人生无可规避的尴尬。
《埋伏》的出现重新显示了黄建新的机敏和创造力。这部既表现主流题材内容,又表现颇有私心杂念的边缘化人物的电影,是黄建新才能的又一次体现。论故事,影片普通而又神奇,讲的是普通人,遇到的却是奇特事:一位并没有什么英雄相的小人物叶民主为了上级布置的监视任务,在水塔上呆了30余天,意外的使案子得以了结;而导致他呆在水塔上的竟是品性不好的邱建国玩忽职守造成的,这几乎使他丧失性命;本非英雄的叶民主之所以能监守岗位立下奇功,是因为一个无意中拨通的电话里充满哲理的老人的话语给他一次次的鼓励,而那位睿智老人其实是聋子,他只是并无目的的自说自语而已;水塔本只是一个监视点,却因为藏有杀人犯的大批钱物,从而既牵制了狡诈的敌手,又造就了英雄;于是,一个好看的警察抓匪的常见故事,有悬念的破案的疑难惊险情节,动人的人物命运的波折起伏等几个因素都聚集在一起,构成这部影片的吸引力。从中不难发现“巧合”、“偶然”等中国电影长期吸引观众的东西被黄建新加以利用,巧妙的组合,达到的效果很好,目的当然是在塑造人物。
3,淡化艺术技巧。黄建新电影的艺术技巧经历了自外在张扬而内在收敛的稳步成熟过程。从《黑炮事件》对色彩的过分夸张和形式感的热衷,《错位》过分荒诞化的显示,到《背靠背,脸对脸》较为隐蔽的暗示(如建筑格局与环境的压抑性暗示),再到《说出你的秘密》的生活常态的自然显示,这些变化过程形象揭示了黄建新电影对艺术技巧把握的深入走向。艺术追求的趋于平淡自然是和注重客观展示生活图景、生活情态的艺术观相联系的。从注重张扬个性意识,到隐藏自我、突出生活本有的色彩形态;从炫耀式的使用技巧,到遮蔽技巧而呈现生活质感和思想情态,及至他在具体镜头表现上也力戒技巧花样而突出表现对象的整体形态,这些变化使我们对一个对艺术真挚追求,并对艺术本质首先是艺术思想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创作者内心世界,有了完整的认识。
《背靠背,脸对脸》无疑是黄建新电影的又一个出色作品,成为都市电影的优秀代表。它对现实细致深刻的剖析,对人物复杂内在性格的表现,对仕途政治的某种揶揄,对现代人心的独特挖掘分析,以及融合他早期理性思考的优长、某种象征意味和生活实况的结合等,比较集中的表现了黄建新电影的特色,当之无愧的达到黄建新电影的上佳水准,也是中国电影的出色之作。本片就内涵而言,进一步发展了《站直罗,别趴下》的思考深度,在人物背景上也进一步延伸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困惑痛苦,其思考触角探入久远历史的痼疾与心理的浮尘,逼迫人们追索思考。这部影片突出显示黄建新擅长处理微细琐事和政治命题之间的呼应,让一个小小文化馆缩映转型期的社会生活,逼真而富有内涵力。影片特别把光彩投射在始终企盼由副转正的卑微小人物身上,通过王双立的几度沉浮,艺术化的凝缩了人的生命挣扎和精神负载的悲欢,展示悲喜交织的人物命运和在权利渴望与命运角逐中的恩恩怨怨。在这位沉浮于宦海的副科级小人物身上,集中了既有心计,也善于调度人际关系,但又不失良善和温存的复杂个性,流露出特定背景下人们常见的渴望、失落、尴尬与无可奈何的种种心理。论影片不动声色的机智讽喻和对时弊深入的剖解,是较黄建新其它影片更为高超的。精心的构思、精致的构图也给人深刻的印象。此外,对冲突处理的张弛有致,和造型的写意性手法等也是值得关注的艺术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