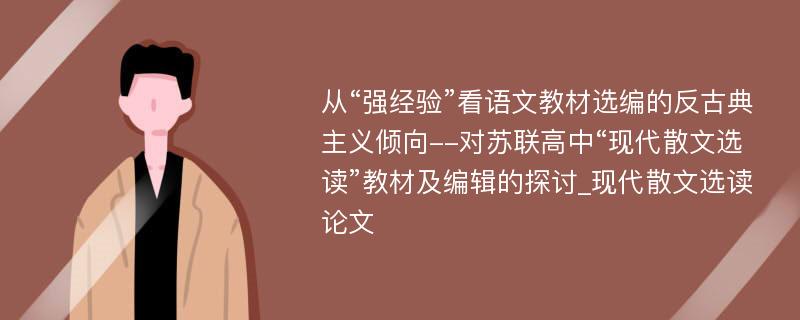
从“强体验”看语文教材选编的反经典倾向——就苏教版高中《现代散文选读》教材与编者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读论文,选编论文,编者论文,散文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教版高中《现代散文选读》(2007年7月第二版)共分六专题,分别从人、事、景、情、物、论六方面结构全册,共32篇散文。教读之前,笔者先让学生用一周时间把全册所有选文通读一遍,然后让他们选出最喜欢的和最讨厌的及没感觉的三类文章。
获得多数学生推荐票的是胡适的《我的母亲》、梁实秋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贾平凹的《画人记》、梁衡的《把栏杆拍遍》、丰子恺的《送考》、孙犁的《鞋的故事》、刘志成的《怀念红狐》、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林清玄的《可以预约的雪》、钱钟书的《论快乐》、俄国作品《女歌手》。余光中、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历来受学生喜欢,但此次未入选。而学生选出的最讨厌的选文是《寒风吹彻》《绝地之音》《云南冬天的树林》及几篇外国作品。其他作品大都是我们教师也不曾读过的,归入了没感觉一类。整体来看,就学生角度来说,“好文率”仅三分之一,再询问多位教师的看法,感觉很类似,虽喜好有差异,但好文的总数不多。笔者在教完全册书后,将这个调查又进行一次,调查结果与上一次基本相同。在教学中,针对首次调查中学生表示讨厌或表示没感觉的文章,笔者进行了更努力的导读与讲解,想把学生引入宝山而有所获,但结果是笔者教得很累,学生读得要睡。这对于语文教材来说,应该是说不过去的。诚然,教材选文不可能全照学生口味来作迁就,但教学的一切都绕不开“学情”,我们的选文作品如果让学生抱着读之无趣无味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失败。编者挖空心思选好文,学生和老师却不喜欢。问题在哪呢?笔者认为原因很可能是——编者的经验、作者的体悟与学生和老师的体验不在同一轨道上。也就是说,编者似乎是在用自己的体验或作者的体验来勉强学生,“逼”着学生感动,而学生却感动不了。
下面具体说说选文的两个倾向。
一、个人喜好与求异倾向
过去的教材选文因为时代原因,政治化和大主题倾向较重,一些无意义的篇目占据教材多年,好在这个“反人文”倾向得到了纠正。又因为是选修教材,编者有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编者的个人口味很明显,教材中过半篇幅的选文教师在中学、大学及任教职之后从没见过。该册书编者一为文学评论家汪政,一为成就突出的作家毕飞宇,评论家和当代著名作家的组合,使得编选之文不自觉地出现“深度体验”。对于汪政老师的评论和毕飞宇先生的小说,笔者一直推崇,然而,对于选编中学教材,笔者却不敢过于崇敬,因为文章好与适合学生读,且读来有收获,是两回事。
好选文应该是编选者的口味与学生口味的交集,即既要是好作品,也得是大部分学生能读、想读、读后能消化的有营养的作品。显然,如果承认前面所作的学生调查是实情的话,那我们的教材编者就有点拿自己口味代替学生口味的嫌疑了。其实本册教材中,两位名家所编选的文章,不仅仅是不适合学生口味,连教师口味也未顾及。那究竟是种什么口味呢?在笔者看来,是“年轻作家口味”或是“现代评论家”口味。这两种口味肯定比教师口味层次高,特点是“深刻”、“独特”、“体验化”。以《寒风吹彻》《绝地之音》《云南冬天的树林》为例,读者必须沿着文字的缝隙小心地钻进去,或是要如诗人所说“站在刀尖上跳舞”,一不小心就可能找不到路径或是滑下来。这个过程很累很紧张,但不这样就读不出东西来。这就有点为难学生了,悦读变成累苦之读或无味之读。在调查教师时还发现,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教师对这几篇文章的共鸣度,要远远超出二十几岁和五十岁以上的教师,这现象正说明了这几篇选文的个人口味很重,是阶段性口味,非大众性口味,只契合了中青年的人生阅历和阅读取向。作家写此类文字时正处于这个年纪,而读者中,年纪再大些的,会觉得此类文章不够纯净,情感缺少过滤;年纪小的又因无体验而觉晦涩。本来,要从浩瀚的现当代散文中选出32篇编成一本薄薄的《现代散文选读》,其难度应该是在太多的好文章中不知该用哪篇,但该教材选入的作品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好像无好文章可选而草草成集。连教师都不来电、读不懂、不想读的课文,要想学生来电来神,可真难。
再看全册的选文,“求异”的意图很明显——大家熟知的少选,公认的名篇少选。求新,这本来是个好品质,然而创新的本质不是求异,而是深刻把握本质规律。如果并未树立起一个求新的可靠目标与准则,往往就会只凭自己喜好来选文,结果是,选的是好文,但不是以学情为基础的好文。偏离学情,正是对规律的偏离,创新就成了一厢情愿的求异。
所以笔者的想法是,编教材,不能仅看作品本身,还要顾及教师与学生口味,就像当年叶圣陶、刘国正等前辈们编文章给学生读时,要按照“从学生中来”的标准反复无数次。所谓“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正是中学教材选文的原则。
二、反经典倾向
这本苏教版《现代散文选读》,有着很明显的“去经典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年轻作家作品多、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多、体验性作品多。符合上述三种特征其中一种的都有相应的几篇选文,而把这三个特征集中在一起的,则是让学生最头疼的《寒风吹彻》《绝地之音》《云南冬天的树林》三篇。笔者认为,教材,不管有多么深奥的编写理念,文章不管有多“深”,当它们呈现于学生读者眼前之时,应该好读、耐读。“深入而浅出”应该是选编教材的理念。否则,其价值会失落。
从作者角度看,此三文均出于青年作家(相对于作品成品时间)笔下,本来,我们绝无必要因作家年轻或名气不大而看轻其作品,但这几篇选文却不是作家的成熟作品。当时的作家本人正处于一个追求个性和文笔的张扬期,通篇流淌的是激烈的情绪和放大的感受,所谓一种“强体验”——故意用力的,勉强求深刻的。我们绝对应该为选非名家作品进教材叫好,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应该选真正的佳作。连作家刘亮程自己也说那篇《寒风吹彻》不算适合学生读的作品[1],笔者相信,这几位作家现在回头看它们,会把它们当作成长、探索的印迹,但不会把它们当成自己得意的作品。
从文学评论角度看,这几文也有话可说。
首先是篇幅问题,作家因为年轻,情感过滤不能自如,文笔放开后则收束不力,显得冗长。笔者试作过如此设想,把这几篇文章大砍大删一番之后,只留下一千多字,反而能尽显其志,而又精炼十分,且一点不削弱意思的表达。
其次就其内容和主题来说,《寒风吹彻》表达的是人生的苦难与生俱来。这本不是一个新鲜的立意,古今中外,此类作品很多,在宗教意义上,更是永恒的出发点。但如果把这种生命关怀放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年轻作家群体中来看,就显得有思想和“深刻”。所谓“触及到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人类生命觉知意义上的悲悯情怀”。问题是,这一个并不很出奇的主旨,实在不适合学生去领悟,要花季的学生去透彻体验生命的本质其实是宗教意义上的苦难,其难度可想而知。
《绝地之音》指向一个深奥的文化命题,说它表现的是原民的生命力量或是黄土地的生命力量,或是民族的力量,再或是文化的力量,都可以。该篇与《寒风吹彻》的共同之处是,都在诉说一种深刻的“体验”,文字的表达上也尽量用铺排的方式和欧化的意识流形式来突显这种体验的“强烈”。但问题是,这种体验的强烈,只在于作家本人身上,很难传达给学生,感动不了学生。费尽心机地导读和点拨,学生依然是为学而学,没感觉。在这个反衬的意义上来说,作家其实是矫情和故作呻吟了。
于坚是很有名的当代诗人,他的诗歌和散文都属于先锋意识下的实验性文本。“于坚总是尽量避免传统人文精神的干扰……而尽可能采用最简单的直接的描述来呈现自然的直观状态……去除语言的‘遮蔽’,避免主观的想象与夸张,力求客观地描绘事物的真实状态”[2](p212)。本来,看这些导读文字,就比读于坚的诗歌还要吃力了,《云南冬天的树林》恰恰又表现出语言的繁复和铺张,比诗中难懂的意象还多了语言文字的处处陷阱,这就更让普通学生读者一头雾水。究竟别家作品是如何表现为被人文干扰、主观、不真实的呢?而于坚又是如何在作品中表现其不受干扰、不主观、真实的?退一万步讲,如果导读中的评价真能算作于坚这篇散文的特色,那这个特色对于学生又有何意义?连评论家自己都说“选择这样的写作者作为自己的讨论对象是冒险的”[2](p231),那把这种“特色”选给高中生读就不仅是“冒险”了,简直是“逼学生在‘强体验’中感动”。
除了这几篇不适合学生读的作品之外,还有刘鸿伏的《父亲》,虽说感情真挚,但实在是个中学生腔一类的作品——“在那一刻,我分明看见父亲的两鬓已钻出丝丝白发……挺直的背,此时已显得佝偻了。望着青头巾、黑包袱、灰布衣的父亲,我的心一阵战栗。”此文与胡适的《母亲》对比颇能说明问题,胡文无煽情句,“母亲”身上的东西好像还不如“父亲”光辉,但我们却能感悟到一个特殊背景、环境、年代下的妇女极个性而又极典型的形象。与之相比,“父亲”个性不够,是个大众形象,所以说是“后中学生”作品。难道,在现代文学散文名篇中,真的找不出更好的写母亲父亲的作品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明明选了名家的作品,却又不选其最具代表性或是最好的作品,如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余光中的《假如我有九条命》,都不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不知是个人口味,还是故意要与别人不同。
教材选文的反经典、区别大众的意图是把双刃剑。如果取舍恰当的话,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可能是好事,但倘若只是为不同而不同,那就很可能失于偏激。若说经典千年不变,那不可能,特别是那些“时代的宠儿”,当然要抛弃,要淘汰。但毕竟还有不少超越时代的经典是经得起岁月打磨的。其实,经典是个开放系统,它的价值已不仅仅在于其作品本身,它所代表的时代特征与背景,后人多年以来的解读、研究、感悟,都已成为经典作品的附加值,已融为经典元素。而非经典作品虽然也可能有好的一面,但却只是单薄一文而已,没有足够丰富的文化传承积淀,不具备附加值。以此类作品代替经典作品其实是不划算的事情。我们过去所产生的对经典的质疑,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让我们选择了假经典、伪经典、伪神圣的东西,而不是因为“经典选文”的思路有错。所以,在教材选文上,曾经的假“经典”可以淘汰,但还是应以经典作品为主。我们有足够多的真经典可供选择,而不必因为要做出对经典说“不”的姿态,就大量选择没几个人读过的甚至是试验性的作品。也不必用“时代性”来作为抛弃经典的理由,经典的产生有时代背景,但成为经典后又超越了时代。我们让学生读散文,不是求职谋生,不是媚俗,并不要求经典作品适应当前。
真正的好作品,是作家体验极深但表达出来时却浅显又隽永之作,所谓深入浅出,读者才会越嚼越有味,越读越有感悟。其实很多成就卓然的老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如柯灵的、汪曾祺的、梁实秋的、丰子恺的……简直太多太多,其特点都是读来浅,想来却是隽永深致,而且很能让学生走进作家心灵深处。既然有如此多的经典可读可选,又何必非用那些“强体验”选文来逼着学生感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