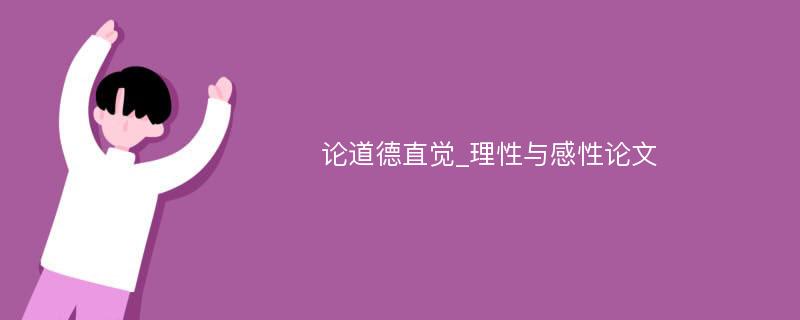
论道德直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提出道德直觉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道德认识方式和道德认知能力,阐述了道德直觉的特点及其在道德认识活动和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直觉 道德直觉 道德直觉的特点、道德直觉的作用
一、道德直觉的概念
对于直觉,哲学史上虽然论述颇多,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直觉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认知主体认知能力达到某种程度的表现。如理性直觉论者笛卡尔认为:“我所理解的直觉的意思,不是对不可靠的感性论据的信念,不是对混乱的想象之靠不住的判断,而是智慧之明确和细致的概念。”〔1〕在此, 笛卡尔实际上把直觉看作是一种与智慧齐名的理智方式和能力。又如,直觉主义者柏格森等人把直觉看成是一种先天的、神秘的、与逻辑思想不相容的非理性认识能力,并把它看作是一种最高级、最深刻的认识形式。柏格森说:“所谓直觉就是指感应(La sympathie),通过这种感应,我们可以把自己置身于对象内部,以便和对象具有独一无二的,并且是难以表达的东西相吻合。”〔2〕这实际上也就是说, 直觉是人的一种处于意识深处的特殊本能,可以“突然地看出处于对象里面的生命现象,从而把握难以言传的实在。”〔3〕
勿庸置疑,直觉是认识主体认知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同时也是认识主体在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认知能力。但由于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脱离实践来探究直觉,虽然看到了直觉的一些表面特征,却未能揭示出直觉作为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的本质,特别是直觉主义者把直觉看成是一种神秘的“领悟”、“顿悟”,不但没有揭示出直觉的真正本质,反而给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灵知世界”不在彼岸,而在此岸;“知性直观”并非神性,而是人性。“不仅五官的感觉,而且所谓精神的感觉,实践的感觉(意志、爱情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凭着相应的对象的存在,凭着入化了的自然才能产生。”〔4 〕马克思的这段话指出了直觉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不可言状、不可分析的先天认知方式的能力,而是象感觉一样可以在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社会实践中得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化、对象化的过程中,当人的理性精神实现对象化的同时,感觉也实现了感性感觉理性化,即对象化的实现,使自然与人、必然与自由、感情与理性的统一物历史地反映,积淀到人的感觉印象中来。对象化的成败,使感觉“看到”现象的真假;实践的反复,使感觉体验出自身的可靠性。然后,通过形象思维活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工组合成质、象一致的理性意象。由于理性意象虽然与理性概念一样,都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反映,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感觉印象个别性的品格,所以它能成为感性与理性、个别性与普遍性、物质和精神之间互相联系的中介。基于这一特性,人们对感觉映象的本质属性辨别、判断,就可以不必都经过思维活动复杂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抽象、概括等加工过程,而往往只须在感知活动中将储存在大脑中的理性意象与特征相应的某一事物的感觉映象比较一下,便能直接作出判别。这样,人类除了具有直观感受的认知方式和能力外,又发展出能够直接进行观照活动的直觉顿悟方式和能力。
由此可见,一方面,直觉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实质上是理性认识成果直接作用于感受活动的结果。与感知、学习、思考、直观等认知方式不同,在性质上,直觉包含理智之光对事物本质的觉察,它是感觉与思考、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概念熔于一炉的特殊产物;在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直觉是对外界事物的整体性质的直接的、非逻辑的把握。另一方面,直觉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能力,实质上是理性认识成果在直觉顿悟方式中,它已作为一种心理物取得了独立存在、独立活动的能力。这一变化,使直觉观照活动既有理性普遍性,又取得了压缩、省略思维操作过程的直接性,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性洞察力、透视力。
直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能力,必然存在于道德认识活动中,而且由于道德认识对象本身即伦理关系客体的特殊性,道德直觉的作用更加突出。列宁曾说过,道德没有“感性”的材料,即道德不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它具有不可感性直观的特征。道德只存在于人的各种活动和关系之中,并构成人的活动和关系的一种内在规定或内在必然。因此,“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看到道德现象,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构成人们的活动。”〔5〕道德存在方式的这一特性, 也就规定了人对道德的认知主要不是靠认知主体超然物外的经验确证和理性论证来把握,而主要是通过与认知主体的价值要求、价值期待相关的理性领悟和理性直觉等方式来把握。
道德直觉作为直觉的特殊形式,它也是价值理性认识成果直接作用于道德感受活动的结果,即也是通过道德意象的观照活动而形成的一种道德认知方式和能力。但道德意象的获取并非象科学意象、艺术意象那样简单,它是道德主体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不断进行道德体验和道德领悟的结果。因此,道德直觉的过程虽是突破的、瞬间的,但道德直觉能力的养成却远非朝夕之功,而是主体长期道德经验积淀的产物。
道德直觉的发生不仅以道德意象的形成为基础,而且以主体对道德意象的内化为前提。真正的道德活动既不是一种仿效,更不是一种服从,而是主体的自主自决活动。道德直觉虽说是一种下意识能力,本质上却是直觉主体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特征主要表现为直觉主体对道德意象、规范、律令的认同和内化,使道德直觉真正出于“我(类)”的活动,而不是消极、盲目或为达到某种外在目的而进行的认识活动。如果道德意象、规范、律令是主体难以认同的他律,那么他所获得的道德知识就难以成为价值真理,所进行的道德判断也可能是对道德本质的歪曲反映。而这种直接的、非逻辑的认识活动决不是道德直觉,只能说是一种道德感性直观。
当然,道德直觉并不仅仅是指“道德中的直觉”,即道德主体对现存的道德规范及其所反映的现实关系的直觉,而且它还包含着“直觉中的道德”的含义,即作为道德的人在直觉某客观事物或行为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融入道德的因素。如人们在决策某项工程时,就会“考虑”该工程对人类是否具有善恶价值意义,在道德上合理与否。道德直觉的第一层含义强调的是道德上的直觉判断,第二层含义强调的是道德上的直觉创造。两者缺一不可,忽视其一,必然会缩小道德直觉在道德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道德直觉可作如下界定:所谓道德直觉,是指主体在伦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主体对社会普遍的道德知识和规范的内化为基本前提,对人与世界的伦理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总体性质进行综合把握的道德认识方式和能力。
二、道德直觉的特点
道德直觉作为直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在以实践——精神的特殊方式掌握世界的过程中发生和进行的。因此,除了把握道德直觉与直觉一样所具有的对对象把握的直接性、整体性和非逻辑性等一般特征外,我们还必须揭示道德直觉的特殊规定性。
(一)道德直觉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认知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讲,道德直觉的特质就在于它的道德性。这就是说,道德直觉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认知形式,它既非象科学直觉那样去直觉对象的事实属性与客观规律,也不象艺术直觉那样去直觉对象的美与丑(不能否认善与美、恶与丑有相通之处),而是直觉对象对于主体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它提供的不是有关对象是什么的知识,而是“应当是什么”、“应当如何”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直觉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思维,在人类的理性思维系统中,它属于价值思维或“内我思维”的系列,是人的价值理性的较高表现。
应当指出,道德直觉作为人的价值理性的较高表现形式,在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它不只是按照“我的尺度”来把握现实世界,即不只是从自身的道德需要出发来把握特定“事实”的价值与意义。它所追求的也不只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方式,而是在“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是与应当、现有与应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统一的视角上来把握世界的。如果说,人的其它直觉的能动表现也内涵着一定的意义追求或价值追求,那么它是以“合规律性”的追求(真)为重心和根本指向的(艺术直觉以追求美为指向),而道德直觉对现实世界的能动把握,则是以“合目的性”的追求(善)为重心和根本指向的,而且它所追求的“合规律性”也主要是为实现“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服务的。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表明了道德直觉是一种应然思维(即价值思维),它是从应当的意义上,即从对象与人的需要(尤其是道德需要)的关系意义上来把握世界的。
(二)道德直觉是一种特殊的范型认知方式。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认知结构。这种认知结构对于进入大脑的感性经验材料起着“过滤”和选择的作用。道德直觉作为主体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性的统一物,内涵着人的本质、需要、意志、信念、理想,表现着主体的内在尺度,无疑也存在着影响直觉性质和过程的道德直觉主体的认知结构。不过道德直觉主体的认知结构有别于康德所提出的联系经验与知性的先验图式,它不是先验的,也不同于一般直觉主体的认知结构,而是建立在道德感性经验、道德知识基础之上的道德认知结构或道德文化心理结构。因此,这种价值认知结构虽可以改变和调整,但与一般认知结构相比却更加稳定,从而形成一种固定的价值范型或价值模式在道德直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影响着道德意象的直接构成,而且还制约着道德意象的观照活动:它不仅作为一种价值框架或模式对新的道德感性经验材料、新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观念起选择、同化和改造作用,而且也作为一种功能系统在主体直觉过程中起识别和判断善恶是非的作用。
道德直觉作为范型认知方式,表明了道德直觉对道德经验的依赖性。由上述可见,道德直觉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如下两大因素:一是内化于心的既有普遍品格特征、又有个别品格特征的道德意象;二是影响道德意象形成和观照的价值范型。而二者生成,归根结底都是以直觉主体的道德感性经验的积聚、沉积为基础的。因此,道德直觉成果的取得虽说既是主体超越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中间环节的结果,也是主体超越某种道德经验而进行自由道德思维的结果。但不管是认识环节的超越,还是道德经验的超越,离开了主体长期道德经验的积淀和知识的积累,都是无从谈起的。王阳明所说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6 〕实际上就是由于世代相传的感情结构积淀在个人身上,使人在一定的境遇中能省去一系列中间推理,摆脱某种道德必然和道德经验而超然物外地直接把握父子、兄弟关系的道德实质。
(三)道德直觉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判断力。道德直觉作为认知能力,是主体在长期的道德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分辨善恶的“是非人心”,是人作为道德主体所具有的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它是道德主体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认识达到普遍性、综合性、本质性的表现,也是主体价值理性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标志。因此,道德直觉作为主体在合目的思维(即价值思维)中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判断力,并不是“合个人目的性”或“合自我目的性”,而是“合类目的性”的判断力,也就是说,道德直觉是从我与他人的统一角度来进行的价值判断的,即它是一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理解力、洞察力。因此,道德直觉并不表现为个人投机钻营的明察秋毫和对行为利益得失的“下意识”判定力,而总是表现为对人我关系中不计利害得失的一种心理体悟,是对善与恶、是与非的高度灵敏性和敏锐性,对道德必然的超然性和深刻性,对决定善恶价值取舍和行为价值取向的明智性。
应该指出,道德直觉作为主体在超验思维中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判断力,并不意味着道德直觉是人先天固有的神秘的“良知”、“良能”,也并不意味着它是凌驾于人生经验之上的神秘“超人”智能。正如道德直觉作为特殊的认知方式离不开道德经验一样,道德直觉作为道德主体的一种判断能力,也是人类道德生活经验的文化心理“积淀”和道德认知主体自身人生经验的理性升华的结果,尤其是自身道德经验理性升华的“精品”和极至。直觉主义者W·D罗斯曾说过:“只有具有道德经验的人才能‘理解’基础道德原则的正确性、错误性或美德性。 ”〔7〕这也表明道德直觉不过是形下经验的超越,形上的领悟。道德直觉的这一特质决定了一个缺乏悲欢离合、胜败得失、毁誉荣辱等人生经验和人生体验的人,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天才,具有敏锐的科学直觉能力,在道德上却无法达到为人处世的睿智和明哲的高度。相反,科学知识并不渊博、道德经验丰富的人,就可能具有锐利的道德直觉判断力。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 〕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道德直觉判断力形成的过程性及其对道德经验的依赖性,道德直觉的这一特点表明:道德直觉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也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直觉能力。
三、道德直觉的作用
道德直觉作为道德认识的一种基本形式和人们的一种道德认知能力,不仅在人们的道德认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们的道德认知方式有多种,如感性直观、身心体验,以及理解、判断、推理等,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是感性认知;二是理性认知;三是融感性和理性为一体的综合判断或整体性认知,道德直觉便是整体性道德认知的基本形式。由于道德认识的对象即道德价值没有“感性”材料,它只存在于人的活动和关系之中,并且总是同主体的需要、利益、兴趣、情感和意愿等要素相联系。同时也由于人们对道德价值的认知把握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并服务于行为选择的,因而,道德直觉往往发挥着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的认知作用。
道德直觉的认知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价值知识的建构方面。道德直觉的知识建构是依托价值范型的选择、同化、改造和识别、判断作用来进行的。当主体处于创造思维的某种情境,直觉对象的原型对这种情境的解决具有启发性时,直觉主体便通过道德意象的观照活动,以好坏善恶等范畴对直觉对象进行鉴别、评价、选择、判断,凡符合主体价值范型或模式的,就迅速转化为“善”,得到主体的认同;凡与主体价值范型或模式不符甚至对立的东西,就会转化为“恶”,为主体所拒绝或排斥。主体将这些善恶知识纳入自己的价值范型之中,从而形成了“善恶是非”之识。
事实上,直觉主义者之所以推崇道德直觉,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道德直觉的认知作用。如穆尔认为,道德知识的基本概念不是复杂的综合的构成,而是简单的、自明的。因此,人们对道德的把握,既不能诉诸于经验事实或自然事实的简单规定,也不能靠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来获取,只有通过道德直觉才能把握道德的真与假、善与恶。穆尔的这一观点表明,道德直觉能够从具有“善性”的事物中直觉到“善”,因而具有认知功能。当然,道德直觉并非是判断伦理命题不真实的“唯一正当理由”和判断伦理命题真实的“根据”。〔9 〕直觉主义者把道德直觉看作把握道德的唯一方式,夸大了道德直觉的认知作用。其实,道德直觉所获得知识的真实与否,也是以逻辑知识和丰富的道德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强调,应当把直觉“放在整个认识过程的前后关系上加以考察,而不能使它与逻辑知识相分离,不能同直觉所指示的动作的正确性和不正确的实践经验相脱离。”〔10〕
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道德认知活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在于指导行为的价值选择。道德直觉无论是作为认知形式所提供的价值知识即直接的综合价值判断,还是作为人们作出直接的综合价值判断的能力,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选择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们日常的道德行为选择,如:尊老爱幼、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等,往往都不是基于道德推理作出的,而是基于道德直觉或直觉性的价值判断作出的。可以说,道德直觉是作为行为的根据和价值理性因素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中发挥作用的。
道德直觉作为主体的一种直接的综合价值判断,它是主体道德行为选择的前提或根据。道德行为选择不仅表现在行动之前的内心权衡上,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行动之中。但不管是道德行为动机和目标的确定,还是道德行为、手段或方式的抉择,每一个环节都反映和体现了主体对客观伦理关系的认识、体验和判断,并且由于伦理关系本身的特点,也由于道德行为选择中的多重道德要求、复杂道德情境,人们对它们的认识、识别和把握,主要依赖于道德直觉的直接综合价值判断来实现。因此,道德行为选择不是任性、偶然、盲目的,而主要是在直觉综合价值判断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具有直觉综合价值判断能力的主体对道德必然“理解”得越透彻,对善恶是非分辨得越明确,他所作出的道德行为选择就越符合道德的要求,从而也就越能造就自己的德性和价值。可见,道德行为选择离不开道德直觉的作用。
道德直觉作为主体作出直接综合价值判断的能力,即敏锐的价值洞察力和透视力,说到底,也就是一种价值选择力。因此,直觉主体不仅能够对对象作出综合价值判断,从而为道德行为选择提供前提或依据,而且也能够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作出行为选择。同时,由于它是一种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理解力、洞察力和选择力,使得主体所作出的行为选择更合理、更合乎道德的要求。可见,道德直觉作为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力,对于人们识别道德情境、明辨善恶是非、区分价值等级,进而作出价值取舍、确定正确的行为动机和方向、择定合适的行为方式或手段,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人在大多数情境下,正是凭着这种价值选择力作出行为选择的。
收稿日期:1996—06—16
注释:
〔1〕《笛卡尔哲学著作》,英国剑桥大学1911年英文版,第1卷第7页。
〔2〕〔3〕李德顺等编:《价值学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61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5〕阿尔汉格奈斯基著:《伦理学研究方法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1页。
〔6〕《王成文公全书》·《传习录》上。
〔7〕转引【美】汤姆·L·彼彻姆著,雷克勤等译:《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2页。
〔8〕《伦语·述而》。
〔9〕穆尔著:《伦理学原理》,商务印务馆1983年版,第153页。
〔10〕科洛瓦诺娃著《道德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