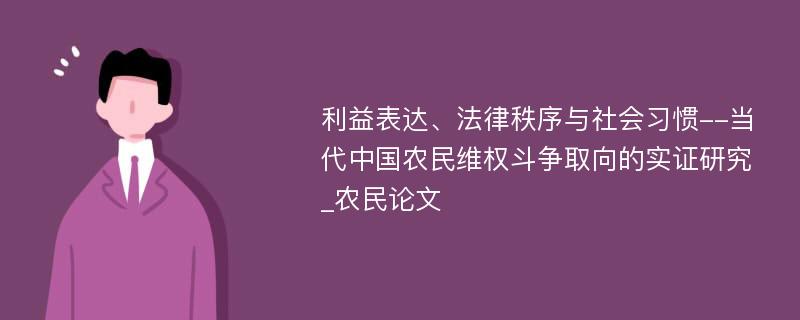
利益表达、法定秩序与社会习惯——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为取向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秩序论文,中国农民论文,当代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行动取向的意义
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理解有两种基本路径,即行动的逻辑和行动的结构。社会行动的逻辑研究是社会行动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动力学的意义;社会行动的结构则主要关注其内在的构成,它是界定社会行动性质的重要依据。而任何一个社会行动的内在结构都可以分为行为方式、行动技术、行动取向和行动特性等几个方面。这其中社会行动的取向不仅有关社会行动的规则体系,即行动者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标准;更多的则是关系到行动者为何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些有关行动根据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决定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取向的情况主要有“(1)目的合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伦理、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4)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①。简而言之,社会“行动取向的根据可以是:(a)惯例;(b)利益;或(c)合法的秩序”②。如果我们以此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就会发现,“利益”是他们行动取向的基础,“合法”是他们行动的特点,“习惯”是他们行动的路径。显然,这既有社会现代性的内容,也有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方面的习惯,更有农民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诉求。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习惯和诉求才能真正构筑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全景式图画。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衡阳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行动取向问题。湖南省衡阳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③。本文研究的资料主要是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
二、行动目标和利益表达
利益从来都是解释社会行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利益’这个范畴里,可以根据行动者们为了相似的预期而作出‘目的合理性’取向来理解他们行动的一致性”④。那么,在维权抗争的农民看来,什么才是他们的利益呢?也就是什么样的利益才可以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目标呢?
笔者对衡阳农民维权抗争的长期观察获得是这样一种经验事实,这就是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回避“利益”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他们自己的“利益”问题更是否定的。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彭荣俊就这样说:
政府那些当官的跟我说了好多好话,说给我利益。我表了这样的态,目前你跟我彭荣俊来讲这个利益,这是你政府给我的。你给我利益,没有解决农民的利益;我的利益是小事,你把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利益由群众来给我,给我什么利益呢,从言论上、评价上我就受到利益了,你要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我彭荣俊,我心里不得含糊⑤。
从彭荣俊在这里所说的,笔者看到了他对于“利益”的理解。也就是说,对彭荣俊这些维权抗争精英来说,他们行动的利益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群众的“言论”及“评价”才更是他们所追求的“利益”。更为重要的,他们一直坚持的是,他们的维权抗争行为没有私利,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村民们被基层政府和干部侵害了的利益。这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这里所谓的利益是中央和上级政府赋予的,是有政策依据的。这就决定,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只要是中央和上级政府赋予了的,就是他们的一种“利益”。其二,这些利益是被基层政府侵害了的,是需要采取行为进行保护的。在这里,利益是与侵害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不法侵害,利益才显现出来。其三,由于这是政策性和政府失范行为所产生的“利益”,也就关系到许多相同处境的村民,也就是大家的“利益”。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凌春伟曾经就这样说:
我要去维护农民的利益,我第一次上访的时候,也有些人比如那些律师为我维护利益,我想他为什么有这份心为我维护利益,我也有责任去维护这些人的利益⑥。
我们搞宣传就是要农民晓得哪些权益受到侵害。我告诉农民上面是什么政策,还把这些政策印刷出来、通过耍灯、通过高音喇叭宣传,让大家都晓得:政府又吃了我啊,老凌讲的有理啊,上面有文件啊,我们也应该去告啊,不合理的我也要拒交啊!你如果不发动起来,政府就懵了这里懵那些,干部的工作就好做。大家都晓得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干部就不敢乱来了⑦。
如果说,凌春伟最早的维权抗争活动是有关自己在税收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关系到自己直接的利益问题。那么,他在这里表达的则是“农民”这个群体的利益了。而且,这种“利益”是政策赋予的,是有“文件”依据的。只是由于“政府”不讲理“吃了”农民的“利益”,才需要有这些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出面来维权抗争。这不仅表明了农民维权抗争的合理性,而且也昭示了维权抗争精英行为的英雄主义色彩。另一位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凌学文就说:
我最初上访就不是为自己的家事,现在上访还是为了公事。我爱打抱不平,并不是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⑧。为了党的政策,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群众的政治权利,我们不会怕。我在省信访局局长那里也表明了,我宁愿死也不屈服投降⑨。
同为维权抗争精英刘德法有过更明确的解释。
去年衡阳县对我们搞农会下了个文件,他专门拿了文件给我,最后我参加了,民政局的副局长在我那里了解,衡阳县的副县长亲自到我那里,我跟他说原来抓着我打得头破血流,我现在不怕抓第二次啊,我不怕坐牢,我还要告诉你,我也不怕死!我为落实中央政策,要支持中央对农民的好政策,我死也不怕。我是为党做工作,我不是为个人。我个人的事如果来找你政府算帐,你起码还要找我一千多块钱。我从来不讲我个人的事。我在牢里坐七天,伙食我交了两百多块钱,这个是我出的;另外我在家里休息45天,动不得,我没找你政府讲半句,因为我是强烈要求你按党的政策办事,我没做亏心事,我不为我个人,我是为群众着想⑩。
可以说,刘德法在这里所说的“按党的政策办事”和“不为个人”及“为群众着想”,就是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对“利益”的最基本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没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曾因领导农民维权抗争而被判两年有期徒刑的洪吉发就曾明确表达过个人的目的。他说:
我作为人民群众,要求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把农民负担减下来,我就放心了。我个人的要求就是,我不图名也不图利,向群众都表过态,我洪吉发是主持正义,被冤枉判了三年刑。我要求衡阳县人民政府做朵红花让我戴上,四个乡镇四个责任区全部都到,我并不要他赔钱(11)。
洪吉发这里的“个人的要求”并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政治上的“平反”。事实上,在以后与基层政府的谈判过程中,县镇政府多次提出要给洪吉发一些补助费,其目的就是要他不要上访和组织农民搞宣传。但每一次都被洪吉发抵了回去,他认为,他的目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理清不清的问题”(12)。
上述的研究表明,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所指向的“利益”是以“合法赋予”为基础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会一直停留在这种“合法赋予”的“利益”上。衡阳县农民理论家陈标就这样明确地告诉笔者:
权利就是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法律不受他人非法侵扰,他非法侵扰农民的利益,一切都要由他指指派派,他说了算,把农民所有的权都剥夺过去了,变成奴隶。我现在有这种想法,人字总是两画,为什么等差有万万千千,一个人的权利,民生,民主,民权,应该要平等,为什么又不能平等?这个农民出的农产品,不能按成本核算来定价,要消费者来承担这个负担。工商品按成本核算来定价,要消费者来承担负担,如果工商品不按成本核算,那工资和税金由哪个来完成?那就没办法付工资和完成税金。所以我觉得呢,要把农民真正富起来,就要缩短这些差距。民富了国家才能强大,农不富,那国家还不能强大,那还是空的,如何使农民致富,那就要重视农业,要象其他兄弟一样,工农商要一视同仁,地位平等,共同上进(13)。
人的身价平等,民主民生平等,这就叫公道,不能由人说了算,卡个脑袋、卡个脖子,强迫农民接受他们的旨意,连本身的生命财产都卡在他们的手里,这些文件都是空的。受穷的根源就是,农产品根本历来没有实施具体成本核算的定价,农民不但没有报酬,连成本都赔上了,农民受穷的根源就在这里,要解决农民的根源问题(14)。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不但在生产生活以及税费等方面解决,真正使老百姓有自由,不受他们的束缚(15)。你对国家对人民有利,使国家强大起来,老百姓强大起来,那你农民起来造反是正义的;如果你不以国家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那你起来造反就是无理取闹(16)。
这是一个农民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的思考。它也许表述得并不完美,却代表了农民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到对权利追求的超越。可以肯定,这种根源于乡土社会的思想,其生命力要远远超越那些书斋学者们苦思出来的教条。
二、行动规则和合法秩序
从理论上来说,“合法秩序的概念则涉及到行动者们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作为规范的秩序之‘观念’的行动取向”(17)。“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而且特别是一种社会关系,可能以参加者的一种合法制度存在的观念为取向。这种事情真正发生的机会应该称之为有关制度的‘适用’”(18)。问题是,什么才是维权抗争农民所理解的“合法秩序”呢?
在衡阳县的维权精英看来,他们进行维权抗争行为的限度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他们无论开展宣传活动,还是上访报警,还是建立非正式的组织网络,都将自己的行动界定在“合法”这个边界内。但是,如果要更为深入追究的话,就会发现,衡阳县维权精英们所说的这个“合法”有着十分复杂的涵义。尽管有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农民对于“法律”的认定有着某些特定的意义,但却很少有研究者详细地剖析过这些具有某些特定意义的“法律”在农民那里是如何表达的。被称为农民法学家的凌春伟说:
宪法和法律是—个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与国内的被统治者,通过互相沟通、互相协调、互相妥协而达成的一种文书;它要求要互相遵守互相约束。也就是说:它是13亿多中国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由游戏的游戏规则。一旦法律失去它的约束力(大家都不遵守)即游戏规则被打破,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国家对人民就会失去控制,失去控制国家也就灭亡了。如果执政的政府对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不认真执行,使违法的人逍遥法外,使合法的权益屡遭侵犯或依照法律规定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人向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别人权益的人斗争对,这个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将表现出它是否诚信,对法律对人民的诚信将会使人民相信它是一个好政府,将会紧紧地团结在它的周围。由于人民的团结,它将形成一股强大的无坚不推的力量,任何顽固腐朽势力在它的面前都会被卷进历史的垃圾堆;反之则会被人民所唾失,被历史所淘汰(19)。
应该说,凌春伟这里对法律界定要超出我们许多专业的法律人士的理解。他对法律与政府关系的理解,正是他走向依法维权的根据所在吧。特别需要指出的,笔者在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收集的用于维权的“法律”中就发现,除了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正式法律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有关文件,甚至有关领导的讲话,他们都称之法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法律的表达和确认是有自己的方式和标准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则和标准就是利己原则,即他们采取和确认的法律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的,起码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他们在抵制地方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时,利用的是中央的政策和法律。洪吉发对法律的解释是很有意思的。
镇里下来乱收乱摊,群众就不肯出。我说,符合规定的那部分我们就出,那是中央和省市的文件原本规定的。党中央分地给我们种,我们就应该按中央的政策办事,把钱交好。但其余的部分我们就不能出,要加以制止,因为违背中央、省里和市里的政策就是违法的(20)。
显然,洪吉发所理解的法律,就是一切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规定。无论从中央到省里和市里的政策,只要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就是法律。这一点,在凌春伟的表达就更为明确了。他说:
法律肯定是站在老百姓一边。我是按中央政策办的,我走每一步都有法律依据,你要搞我几乎是不可能,他自己订的法律和政策,不可能说我错了(2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法律的“公正”和“正义”就是“站在老百姓一边”。那么,如果这些规则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呢?这一点,洪吉发因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而被判处了3年徒刑后,对法和律的理解就发生过一些变化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曾多次表示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所受冤屈,因为法律不会还给他公道。而对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彭荣俊有过这样的评述。
(洪吉发坐牢)出来气愤时就说要搞死某某。我说那搞不得,你是为了农友去坐牢,你就不能搞违法的事情。我就开导他,表了这样的态,老洪你搞什么都好,但不能违法,违法不要要把我姓彭的牵到里头,你若听我的就按我说的去做,正确的我会支持你,错误违法的我就要制止你;现在我要控制你的活动,如果你动机不对,我就会去上告公安局。所以他不敢乱来。他能为民众去办事,没有违法,我只能给他出点子(22)。
但是不是说,彭荣俊就完全理解了这个“法”呢?他的行为是否有过“失范”呢?李连江在研究中,曾指出,“依法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像他们最初宣示的那样,保证每个行动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法律”(23)。事实上,在一定情况下,维权精英还会采取用违法对待违法的办法。彭荣俊在2003年初就曾经用这“非法”的手段宋对待乱收了学费的学校。他说,
今年学费自愿部分偏高了,不把自愿部分算里面来,我们还没有偏高,整个衡阳县就是我们渣江的标准相对平稳一些,按照市里发的文件,财政局、物价局和教育局发的文件,不准把自愿部分加进去,底下就不那么搞,去年就把两本书合作一本,巧立名目,该发给学生的书他们扣押不发,寒假里做的寒假作业书在每个学生头上收了15元,按数目就收了几万。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我就去说要把盐田多收的这部分钱退给学生家长,他们不退,这样就发生了口头争执。我和他们说不清,就把他们学校老师的摩托车扣押在我这里,我这种做法也是违法的。我现在就是一句话,我当时就说了,你摩托车不是我扣押你的,你退给农民了,合理合法的,我就原原本本、毫无损伤地还给你。所以从那天到今天有接近10天了,我还没退给他。昨天派出所的人说也不好来,学校也违了法,你也违了法,怎么来处理呀,我和学校也和气,和你也和气。他说你最好把摩托还给他,我说那不行,你们出面,现在撇开学费,多收了撇在一边,但你们出面,要他们今年不要再乱收费了,我摩托车还给他。政府这边也递了报告,学区这边也没来找过我,你来找我,顶多也是扣押我15天,如果扣押我15天,出来我就和你一起告(24)。
如此说来,农民在利用法律作为维权抗争武器、确定行动边界时,有时会采取一种模糊的策略,即“打擦边球”或称为“走钢丝”。肖唐镖的研究就发现,“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这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他们对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念和看法,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为。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敌视性’行动”(25)。
应该说,这一分析是很有意义的,它为我们理解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一份清晰的图画。但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彭荣俊等的行动,还是可以说,衡阳县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以一种他们认可的“法定秩序”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一“法定秩序”,就是“中央规定的”,“站在老百姓一边的”,“对农民有利的”一切规则。这恰如凌学文所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越是镇压我越要反抗。因为政策是党中央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伪造的,我要用宪法和政策来保护自己,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容人家剥夺(26)。
四、行动路径和社会习惯
泰勒曾提出:农民之间在起义和暴动时的行为关系并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一次性的行为关系。恰恰相反,他们是乡村社区内世世代代连续关系中的一环。所以他们所面临的选择问题,必须作为“重复性博弈”(iterated game)的问题来分析。而农民在乡村社区内所进行的“重复性博弈”是一定会受到乡村社区本身的一些特点所影响的。在泰勒看来,“在一个相对封闭、人们世代交往、互相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村社区内,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来有往’这样的行为规范。这种社会行动规范是帮助农民克服‘搭便车’困境的有利因素:它可以在无形之中协调农民之间的行为。既然大家在暴动或起义之后还要互相见面、互相交往,那么,有事时最好大家都积极参加。任何投机取巧式的‘搭便车’行为,都会使人事后在村子里受到孤立,再也没法抬头做人”(27)。理论家的这些总结和解释,在衡阳县农民那里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证实。洪吉发就通过他那朴素的语言,表达过与之差不多的意思。他说:
我把要组织大家减轻农民负担的事告诉我老婆后,她就劝我,别搞了,减负又不是为你一个人,你把钱减下来了,分到你又没有份,你又没得到群众什么好处。我那时还没坐牢,我就说,不管是否得到群众好处,人不晓得天晓得,这就是讲迷信了。我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帮群众把负担减下来了,群众总会有个印象,一代传一代,子子孙孙都会记得。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我这么说,我老婆就讲,随你去搞吧,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讲了以后老婆也同意了,于是我就参加了彭荣俊的减负代表活动(28)。
我本人在牺牲一切利益,包括受到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上访?因为我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党中央、省市和各级政府都有这个精神,所以我要为大家主持公道,这是我们衡阳县人民的好传统啊(29)。
那么,什么是“衡阳人民的好传统”呢?这在衡阳县维权抗争精英们那里绝不是泛泛而谈的东西,它有非常明确的对象的。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衡阳籍烈士夏明瀚(30)。笔者多次从多位农民维权精英的口中听到过夏明瀚那首震撼人心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只是这中间的“夏明瀚”这个名字被换成了“彭荣俊”、“洪吉发”、“凌学文”等等。对笔者触动最大的是农民宣传家廖哲辉,他在讲述自己一次为了宣传党的减负政策被派出所找过去谈话时的情景时说:
派出所的就说:廖哲辉,你告乡政府,你以减负为名,你是反党为敌,乡政府奈你不何,我派出所能奈何你,你这个钉子我就要钉服你;你说减轻农民负担,减没有减下来,农民还凑了两块钱一个人给你了,你是加重农民负担;乡政府收这些钱是入国家财政,这些人凑钱给你是不义之财,那一户多少钱、哪个组是多少、全村是多少,你这个钱要报数给我,要分文不少。在路上就一直这么说。后来出了我哪个大队,派出所那个车子轮子的钢板一次就断了,走起来就挂得轰隆轰隆。他说怎么挂啊。我说是你黑了心,党的政策不落实,天地都不容许你的。他说:啊!你还讲这样的话啊!车后面有铁杆子,就将我滚到后面去,我外甥走了,就把我推到那后面去。他翻了文件看,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一下钢板断了,走台源没有钢板配,要到衡阳市才有钢板配,就把我在那里关半天。到下午天黑了,派出所给我两个苹果吃了。当时他到我那去就说,你这个组织,还有后台,你组织有哪些人,要把人员交给我。要按政策落实,拿你这些人搞死,要继续上,不停脚,要像河南省某乡一样。我当时讲,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廖哲辉,还有后来人。你拿我搞倒,还会有后来人。他说你就像夏明翰一样啊!你后来人怎么不来啊(31)!
廖哲辉在讲述这些故事时,语调是平静的。而却让我们感到有些迷茫和心痛,因为,当年夏明瀚烈士说这些话的是时候,面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今天衡阳农民维权精英们高呼这首诗时恰恰面对是夏明瀚烈士为之献身的政权。而且,他们赋予了这首诗基本相同的意义,这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传统”的政治价值,本身就赋予了他们行动的合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象衡阳县这样的“好传统”在中国的中部农村,特别是曾经的革命老区,是广泛存在的。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传统称之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表达更多的成为了一种行为标准的传承。这种传承在事实上成为了他们行动的一种重要的激励机制,是他们克服“搭便车”的力量所在。毫无疑问,把一种传统变成一种行为方式并将其转化成为行动者的责任,是需要许多中间环节和机制的。
五、结论:以法抗争与合法政治
笔者曾用“以法抗争”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在这一解释框架里,当前农民的维权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笔者这里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无论在“利益”、“秩序”还是“习惯”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应是“合法的政治”。其政治意义在于,他们维权抗争活动的对象是县、乡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权力机关;抗争目标是通过动员广大农民的参与来约束公共权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对象是县、乡党政机关及官员。在1990年以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民间纠纷型事件,一般是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发生的纠纷。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事件急剧下降,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基层党政机关(主要是乡、镇一级)这些公共权力机关以及基层党政机关在村庄的代理人作为集体行动诉诸的对象。因为在许多农民把自己的处境与中央及省市的文件进行对比后发现,县及县以下的公共权力组织和干部的行为与中央的政策要求有差距,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差距决定了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县乡党政机关和干部作为抗争的对象。这就决定,他们并没有把整个体制作为抗争的目标,是在认同并利用中央的合法性基础上的抗争行动,具有体制的合法性。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不仅是解读农民行动的语言体系,而且是理解农民动员机制的逻辑线索。第二,农民维权抗争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约束基层公共权力,以保障他们的权益。近10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议题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无论是有关农民税费、还是关于计划生育、还是有关学费或水费,都与基层政府的施政有关。这实际上是中部地区农民维权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农民们把中央及省、市有关农民利益的文件作为标杆,以此来衡量基层政府的行为,并从中找到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与中央规定的差距,然后通过上访、宣传等方式来进行抗争,试图通过上级的权威或动员广大农民的参与来约束基层公共权力的掠夺行动,以保障他们的“权益”。约束基层公共权力而不是取而代之,这是农民维权抗争与“造反夺权”的根本性区别。它一方面表明了农民维权抗争的目的,就是“约束干部,使他们不能乱来”;另一方面又界定了干部是否“乱来”的界线,这就是“违法”与否,而且法律还是约束那些乱来的干部的武器;更为重要的是,这也表明农民维权抗争只是工具性的,没有超越社会体制这一底线。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页。
②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页。
③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④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⑤彭荣俊访谈录(2003年2月27日)。
⑥凌春伟访谈录(2004年4月9日)。
⑦凌春伟访谈录(2004年4月9日)。
⑧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0日)。
⑨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0日)。
⑩刘德法访谈录(2004年4月12日)。
(11)洪吉发访谈录(2003年1月28日)。
(12)洪吉发访谈录(2004年4月9日)。
(13)(14)陈标访谈录(2004年4月10日)。
(15)陈标访谈录(2004年4月10日)。
(16)陈标访谈录(2004年4月10日)。
(17)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1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2页。
(19)凌春伟:“浅论教育乱收费的危害——救救孩子、救救法律”。
(20)洪吉发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1)凌春韦访谈录(2004年4月9日)。
(22)彭荣俊访谈录(2002年12月29日)。
(23)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24)彭荣俊访谈录(2003年2月27日)。
(25)肖唐镖:“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
(26)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7)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8)洪吉发访谈录(2003年1月28日)。
(29)洪吉发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30)夏明瀚,衡阳县礼梓乡人。1925年后出任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负责农运工作。1927年起,历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委员,平江、浏阳特委书记和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农历2月29日。在汉口余记里惨遭国民党杀害,时年28岁。
(31)廖哲辉访谈录(2003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