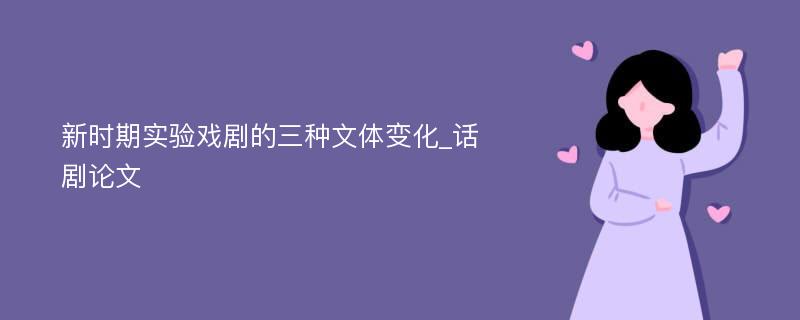
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三次文体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验性论文,话剧论文,新时期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相继涌现,为话剧的文体变革提供了种种鲜活生动的文化土壤,而旧有的东西又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决定了新时期实验性话剧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过渡性色彩,也留下了一些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和反思的缺憾。就新时期话剧文体内容和形式的融合而言,由于在文体建构中纳入的文体资源很多,一时来不及或没有能力消化,形意分离、为形式而形式的情况十分常见。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无疑是新时期实验性话剧文体变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西方戏剧在传入中国后的几十年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易卜生——斯坦尼式的稳性的亚文体形态。虽然丰富的审美形式结构滋养了风格各异的戏剧创作,但单调的布局形式结构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戏剧的创作自由。新时期伊始,西方的一些新的戏剧创作和观念被介绍进来,这些新的戏剧观念又激活了对被遮蔽的古典戏曲的重新认识。这样,新时期话剧的文体变革从一种内在需求中获得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稍后的对新时期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成为整个社会与整个文艺界共同的关注点。形式探索和社会问题构成了新时期初期戏剧界的两种巨大动力,于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探索介入剧,这也决定了新时期初期戏剧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形式和内容相互融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形式内容化,另一方面是内容审美形式化。形式内容化是指单纯的形式也获得了一种诗美的特质,这突出地表现在音乐、诗歌中,就戏剧而言,格洛托夫斯基(后期)和尤金尼奥·巴尔巴等人的实验戏剧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形式内容化的特征。朱栋霖认为:“戏剧的内涵是多层面的,诗本体充溢在各个层面,与每一层的内涵相融合。政治意识与社会问题的存在仅是一个基础,人性与文化的表现则是第二层意蕴”,而戏剧的第三层是“哲理、象征层面”。他认为,曹禺戏剧之所以“历经五十余载仍具有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社会问题剧达到了现实主义的诗化形态”。[1] (P17-23)诗性化是戏剧内容各层面之间、内容和形式之间相互转化与融合的有效途径。戏剧作为一种视听和时空的复合艺术,能够调动人物语言、人体动作、音响、灯光等多种手段来获得一种诗性化的效果。如果艺术同现实生活的距离太近,就容易丧失自身的审美品格,只有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超越表象的现实生活,才能营造出内在而深刻的诗性,进而达到揭示历史本质的目的。
新时期话剧文体变革初期,戏剧家们的主导性策略是对戏剧假定性本质的认同,这获得了戏剧时空的更大自由,大大强化了戏剧的叙事能力和表现能力。就表现手段而言,歌舞、音乐、电影,乃至民间艺术等都被新时期实验性话剧充分吸纳;就表现方法而言,写实的、写意的、两者兼容的,样式各异。然而,新时期实验性话剧在不同阶段,其内部的融合手法与程度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概括地将新时期实验性话剧的文体变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文体变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主要包括以高行健为代表的一批戏剧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反叛中国现代话剧中的传统形态戏剧结构体制即布局形式结构为目标,将完整形态的现实生活打碎进行重组,如《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车站》、《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路》等。这些戏剧大量采用回叙、想象、幻觉,乃至荒诞的手法,为戏剧脱离生活的现实性、实践性而走向一种主观化叙事创造了条件,而主观化叙事无疑为内容的审美形式化提供了契机。然而,人物、事件的非现实性同样也包含着概念化的可能。高鉴在分析《屋外有热流》时就指出,该剧时空色彩的多变是以人物的非现实性为前提的。(作者曾有这样的自白:“如大哥不是这样一个观念形态的反性格化的意念人物,他怎么能做到时空色彩的多变?”[2])
新时期初期实验性话剧形式和内容广泛不对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法的冗余,即有些表现手法纯属多余,为手法而手法,这些表现手法没有能够被充分地审美艺术化,同戏剧显得有些隔离。
第一次文体变革期间,话剧为了扩大舞台表现力而大量运用一些的新的手法,而这些手法很多是从功能意义的角度去考虑的。这一现象突出地体现在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如剧中歌队队员做出雷声、雨声以及飘动的雨丝,扮演电话机、电话亭、门、桌子等。一般而言,符号有两种,一种追求功能相同,一类追求形式相同。在戏剧中,两种不同符号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思想,在东方写意性戏剧中一般强调符号的功能性,如将木马当作真马;在西方写实性戏剧中一般强调符号的形式性,即运用真实的事物进行表演。东方戏剧中的功能性符号被融合到写意性美学思想之中,是美的戏剧意境的一部分,然而在新时期实验性话剧中,功能性符号基本上仅仅具有一种指称性功能,而无法给予观众充分的审美想象。戏剧家们通过这些符号的运用无疑增强了戏剧的叙事能力,然而却无法对它们进行审美整合。这也是这些手法只能偶尔为之(以新奇感取胜)而无法常用的原因。
《车站》中那象征着“沉默的人”的反复出现的音乐声,曾经招来种种非议,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概念化意味太强,乐音的穿插同戏剧没能很好融合,从而形成了表现手法的冗余现象。剧中反复出现的音乐声越到后来越激越,它是以同等车人相对立(对比)的面目出现的,这些音乐声实际上代表着作者的批评视点。该剧音乐声的运用是到位的,问题是出在“沉默的人”的设置上,他在剧中一言不发,他同等车人的对比姿态十分明显,作者的意图近乎直白,这个人物在剧中仅仅作为一个观念性意象出现,而没有作为戏剧人物所需要的基本质素。剧作者意欲将自己的批评意图实体化为“沉默的人”,而当“沉默的人”离去之后,就只好以音乐声来代替,音乐声是“沉默的人”的象征。“沉默的人”在《车站》中实属蛇足,如果将其去掉,仅以音乐声来体现剧作者的视点,效果反而会好得多。另外,作者追求一种诗意化的表达,希望能“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全剧情绪的起伏上”,[3] 但是《车站》中的“荒诞”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停留于概念上,该剧的荒诞性色彩是通过时间的飞逝来实现的,而这种荒诞的时间对剧中人的影响十分有限。戏剧开始时,剧中人给予观众的印象就是对时间和生活的麻木,如做母亲的要进城给家人洗衣做饭,愣小子要进城吃酸牛奶,大爷进城是要与人下一局棋等等。但是随着时间一年、十年地飞逝,这些人除了更忧伤一些外,荒诞的时间在他们身上似乎并无多大影响。事实上,如果真要设置“时间飞逝”这么一个荒诞意象,那么就应当注意它在剧中的戏剧性作用;如果仅仅表现人们对时间的麻木,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完全可以去掉这一荒诞意象。因而,“时间飞逝”这一荒诞意象最终还是一个“硬核”,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化。
第一次文体变革中的实验性话剧从一开始就因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而备受指责,尽管林兆华曾以形式即内容进行自辩,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明显的。造成内容和形式分离的主要原因是,形式过于新奇花哨,而内容却相对贫弱,正如徐晓钟所说:“形式的华丽掩盖不住形象、内容的贫瘠”。[4] (P65)新时期实验性话剧一反以往的生活化叙事,着力增强戏剧的叙事能力,大量采用一些新的表现手段。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我们这些实验性剧目的形式,尚缺乏与戏剧意蕴结合的有机性。某些‘创新’只是以虚妄的故事为支架,勾挂起各种表现手法的板块。”[2] 新时期实验性话剧最抢眼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形式革新,而纵观整个新时期戏剧批评,只要一提变革创新,几乎都只谈形式,似乎就可旁证这一点。这一时期实验性话剧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对人性有所涉及,却存在着相当缺憾,有些话剧或对西方现代戏剧的一些新手法理解不够深刻,运用起来还不够灵活舒展,比较生硬稚嫩,如《屋外有热流》中主题思想过于直露。而某些实验性话剧以新异的艺术形式表现的,只是一些内涵不够深刻的社会问题剧,如《绝对信号》探讨的是社会待业青年的出路问题,《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关注的是见义勇为问题,《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讨论的是社会离婚现象。这些社会问题剧更多地停留于社会道德层面,而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去更深入地挖掘。它们往往只讨论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而过分具体的问题很难被拓展升华,也就难于达到形式和内容在诗性的开掘中交融的境界。
新时期实验性话剧形式和内容融合的问题在第二次文体变革中得到了较好地解决。第二次话剧文体变革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文化寻根剧,其突出代表是黄佐临、徐晓钟等人导演的作品。这些话剧是在前一时期话剧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同时它们也创造出了较为丰盈完满的审美形式结构,能较好地将多种文体资源化合于一体,创造出了较为成熟的文体形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洒满月光的荒原》、《中国梦》等。这一时期戏剧艺术家们对戏剧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前一时期话剧实验的得失为话剧实验的成熟创造了条件,本时期实验性话剧充分吸收前一阶段的成果,即对戏剧的自由叙事性和自由的戏剧结构的继承,广泛吸纳各种手段以为我所用,同时也注意克服失误,努力使各种表现手段、形式和内容得到有机的化合,追求深层的诗性结构。
一般的日常性语言的指称是单一的,它只是单纯的表意工具,意思表达完,语言也就无关紧要了。而诗性化的语言尽管也具有指称性,但由于它凝聚着浓郁的主观情感,它既依托语言,又超越了语言,成为能指和所指、形式和内容的复合体。在谈到形式和内容结合问题时,徐晓钟认为:“依据剧本和演出所遵循的不同的演剧观念、处理原则,舞台美术的总体形象,可能是通过与导演的构思的总体形象(或叫演出的概括形象、演出的形象种子)相一致的隐喻形象暗示出来;可能是在有着浓厚的气氛与情调的典型环境中获得反映;在运用假定性原则、写意手法的舞台美术设计中,它的造型形式的形、色以及体积与线条的节奏,也应该有视觉形象的内在统一。”[4] (P67)这里,徐晓钟谈到了第二次文体变革的实验性话剧促使形式和内容融合的几种主要方法:隐喻象征、情调气氛、视觉形象的内在统一等,正是它们共同创造了戏剧的深层诗性。
意象是诗人内在情思与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复合物,是客观物象的主观化表现。意象是意与象有机交融体,意消融了象的“物”的清晰性、单一性,使其变得模糊多义,以传达主体的无限情思。第二次文体变革的实验性话剧中大量运用象征性意象,如《中国梦》“放排”的意象,《狗儿爷涅槃》中的“土地”与“门楼”,《死水微澜》与《浴血美人》中的“红绸子”,《风雪夜归人》中的“白围巾”等。在舞台意象的运用方面,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该剧运用了大量的舞台意象:“捉奸”、“杀牛”、“围猎”、“古井”、“黄土地”,就连“转台”这样一种道具也被予以提升,具有了某种意象化的意味。由于大量的舞台意象的多维运用,“整个戏剧情境所蕴涵的生命意义,尽皆囊括在意象的象征之中,它们把触摸不到的内在生命形象化了,把看不见的命运形象化了,把全剧的精神意蕴形象化了,化为可见、可听、可感、可触的动作形象和动作形象组合”。[5] (P156)舞台意象以其特殊的魅力,既提升了实验性话剧的诗性品格,丰富了其内涵,又增强了戏剧文体内在的凝聚力。
第二次文体变革中实验性话剧的深层诗性追求,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整体的诗性品格,即徐晓钟所说的“情调气氛”。戏剧能够调动人物语言、人体动作、音乐、音响、灯光等多种手段,或运用意境、意象等方式来渲染情绪,营建情调。它们共同为戏剧情调的生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它们在戏剧中不是独自运行的,而是一个整体的戏剧形象。
这一时期话剧的文体变革产生于喧嚣一时的文化寻根热期间。与肤浅的道德启蒙不同,文化寻根加强了实验性话剧的厚重感,浓郁的文化氛围弥漫全剧。《狗儿爷涅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国农民形象,并探讨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心理结构与命运,表现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以及因对土地偏执的眷念所带来的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等精神特征。《桑树坪纪事》以悲凉深沉的笔调描绘了黄土高坡农村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悲剧以及因生存困境而带来的人性扭曲。该剧对农民及其民族心理结构的剖析十分深刻,徐晓钟曾说,“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王晓鹰认为,这就意味着《桑树坪纪事》突破了环境时空表层的情节结构而达到了一种自由驰骋的、洋溢着诗情画意的心理时空。[6] 正如曹禺所说,该剧是一片生活,但“凝聚力和吸引力却非常强。散文式的剧本演起来并不散,给人以完整、圆满的感觉”。[7] 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深层的诗性结构的营造,如剧中的“‘围猎’——象征性的诗化意象,像一条无形的链条将全剧看来似乎可以相对独立的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起来,结构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艺术整体”。[8] (P211)如果说第一期实验性话剧重点还在于突破传统话剧的布局形式结构,其诗性还只是一种局部性存在的话,那么第二期实验性话剧则将诗性纳入到戏剧的内在肌理里,形成了一种深层的诗性结构,这些诗性因素和诗性结构对这些戏剧文体的内部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实验性话剧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第三次文体变革时期。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消失了,相反的却是在强大的商业文化冲击下产生了某种虚无主义。最典型地体现了第三次文体变革的戏剧家是牟森,孟京辉与林兆华等人的部分作品也体现了这种变革思潮。这些戏剧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戏剧艺术本身,强调戏剧的舞台性(含剧场性),极力消解戏剧的叙事功能,甚至也努力消解戏剧的话语表达方式——代言体与对话,注重戏剧对观众的冲击力,强化观众的感受。对于这一时期的实验性话剧,即使戏剧创作界内部评价差异都很大。孟京辉认为,80年代进行的是一种探索戏剧,“探索戏剧是不清楚戏剧该怎么办,只是把新发明、新手段和新的想法,片断地、只言片语地搬到舞台上……探索戏剧可能是这种不自觉的东西”,而“进入90年代,许多戏剧工作者做的不止是简单的探索了,它是一种实验,这种实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9] (P144)而林兆华则认为:“我觉得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没什么好戏出来,90年代的戏剧比80年代是一种退步,80年代人们还有那种创作的欲望、热情,出来的东西还有那么点激情,或者还带有点艺术生命力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90年代就特别缺了。”[10]
在讨论第三次文体变革中实验性话剧文体的内部融合之前,让我们先从它们文体上的独特性谈起。
首先,第三次文体变革中实验性话剧追求的是一种物性的感受表达。这种戏剧的典型代表是牟森,在他的《与艾滋有关》中,舞台上是日常的锅、肉,演员随意地谈论着一些生活琐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些原生态的寻常的日常生活,没有经过提炼,所不同的只是赋予了它们一种舞台形式。牟森认为:“你把生活中的东西,放到舞台这个环境里,实际上这种语言本身,已经有了另外的一种意义了。”“这种意义是需要观众赋予的,而事实上每一个看戏的观众赋予了它的意义都不一样,我想这个就是我对于戏剧审美的一个理想。我希望给观众提供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又绝对不止是这个东西,它肯定要使你产生联想。这种东西是不能够用语言去解释的,只能用感受去体会了。”[11] (P159)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一、舞台上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些物象,没有也无法上升为一种审美意象,它们甚至没有起到传统写实剧中环境的暗示作用,它们不代表什么,就是它们本身;二、这种戏剧要表达的是一种感受,至于是些什么感受,留待观众自己去赋予。创作者提供的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同时他们又确信“绝对不止是这个东西,它肯定要使你产生联想”。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具体的东西仅仅是它们自身,并没有形成审美意象,那么,“肯定使你产生联想”凭借的是什么呢?仅仅因为它们是在舞台上,被赋予了一种舞台形式吗?
第三次文体变革中实验性话剧的美学追求依托的是演员的表演,他们企图使舞台表演达到一种人类学的深度,这是这种实验性话剧的第二个特点。正如牟森自己所说,格洛托夫斯基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剧实验主要集中于探讨舞台表演的表现力,他认为“演员的个人表演技术是戏剧艺术的核心”。[12] (P5)尽管演员表演在传统话剧中也同样很受重视,那主要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表演去尽可能好地解释剧本,要求演员恰如其分地传达剧本意图。格洛托夫斯基发展出了表现派与体验派之外的第三种表演方法:让演员在表演时达到一种空无境界,在对空无的追求中更充分地调动演员的舞台表现力,进而探寻形体背后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人类心灵的隐秘。牟森也“特别想在戏剧里边切入、反映人更深一层的一种东西”,他认为,“戏剧的魅力就在于和人的表面与背后的这种东西作对抗”,[11] (P152-153)也就是要探寻形体背后的人类学意义。为此,他在戏剧中大量启用非职业演员,他认为,戏剧表演中人的身份比演员的身份重要得多,而职业演员身份的一些成规观念会妨碍他们对追寻人类学意义的深入。同时他又说:“我希望演员在舞台上是一种被迫的反应,所以在我的舞台上,道具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作为一个物体,除了它自身的含义,它都能跟演员的身体发生联系。”[11] (P160)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三次文体变革中的实验性话剧具有其理论合理性,对人类学意义的深入挖掘具有将各文体要素统摄起来的凝聚力。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戏剧的日常的具体性与物性太重,它将走出具体性以便深入挖掘意义的重任完全寄托在演员和观众身上,而演员所受的专门形体训练又十分有限,同时人物对话对人的隐私的攻击究竟能取得多大效果也十分值得怀疑。在谈到《与艾滋有关》时,牟森说:“这个戏我最不满意的就是人物的说话,我希望的是更琐碎更无聊的谈话,可事实上那里面还是谈到了性,谈到了艾滋,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控制,因为现场上它是自由的。”[13] (P153)创作者的本意是通过在随意宽松的环境中对人的隐私的攻击,更琐碎更无聊的谈话,去直逼人的意识中更深层次的东西,事实上在创作中这是很难奏效的。同时由于没有确定的剧本,也较难确保戏剧的完整性。每次演出不一样,具有一定的剧场性魅力,但是正如牟森自己所说“现场上它是自由的”,创作者的意图难于完整统一地得到贯彻。汪继芳曾记录了她观看的一次《与艾滋有关》的演出情况,演出开始部分没有秩序,大家都抢着说话,结果不知听谁的好。
牟森反对职业演员身上因袭的成分完全是合理的,运用格洛托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排戏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于,在强调演员的技术性的同时,他似乎对如何从技术性走向心灵,如何褪掉日常生活的具体物性而走向精神性这一最为关键的过程重视得还不够,这就使话剧的形意是否能够成功融合成为一个让人十分怀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