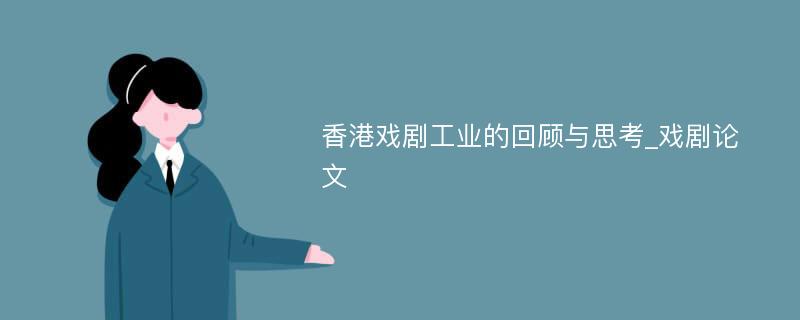
香港剧坛的追忆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坛论文,香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我生于香港,成长于香港,退休于香港,又曾在港从事话剧工作五十五年,自问未能熟悉香港发展的情况。这次执笔,顺谈社会及市民观感的演变,只因话剧发展不能离开社会与市民。所写的是个人所知和推想,错误自所难免。
Ⅰ.追忆
为了方便介绍,首先分期。我不按年代划分话剧发展的阶段,而以重大的转变作分界。
第一期:二十年代到香港沦陷;第二期:一九四六到一九六五,即香港光复到年青人接班;第三期: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即专上学联戏剧节开始到定目剧团(repertory theatre)成立前;第四期: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九,戏剧专业化时期。
今后的发展是否一幅风顺到九七呢?过渡期会有什么事件影响剧坛发展呢?谁也不会知道。
(一)二十年代到香港沦陷期
根据我所保存的资料,一九一一年已有“镜非台”及“清平乐剧社”。“清平乐”含有“乐清平”或“清平则乐”的含义,可见当时港人的心境。二十年代“琳郎幻境剧社”上演《梁天来》,我曾随先父母看过。我第一次看到文明剧——港人称为白话戏,与粤剧的《梁天来告御状》有别。依稀记得:一个青年向少女的父亲提出婚事要求,老人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拒绝,接着走到台前向观众说一番话。我觉得没有《梁天来》那么好看;现在想来,觉得它有颇浓厚的“反封建”意识。
不记得是一九三四还是三五年,我到广州石牌国立中山大学读书,当时洪深先生在中山大学教授戏剧,我旁听他的课程和参观他排演《五奎桥》。《五奎桥》开始的几场戏是相当沉闷的,洪深先生说:不能期望观众全神贯注地去看完全戏,只望有几个场面使他们念念不忘。果然,地主与官僚勾结,威逼利诱农民的几场戏,到今天我还有很深刻的印象。
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三八年广州沦陷,我投入香港的救亡工作里。我曾在《戏剧艺术》谈及抗战期香港救亡团体的戏剧活动,该文未完,现简述及补充如下:
当时的剧团有三种:一是本港团体,二是来自国内的,三是不公开而经常上演创作剧的救亡团体。
先谈本港剧团。约每月演出一次的有青年会剧社、女青年会戏剧组。文员协会、香港政府华员会的华员剧团、春秋剧社、远东剧社等亦常有演出。学校如香港大学、罗富国师范学院、中业学院、岭南大学及附中、培英、培正、真光、梅芳、华仁、华侨、仿林、知用等校亦成立剧团。有人统计,剧团总数(不公开的救亡团体除外)达一百五十,而最瞩目的该是“时代剧团。”
“时代剧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由香港影剧界卢敦、胡蝶、李月清、张瑛、赵如琳等组成。过去,他们曾组“华南戏剧组”,重视艺术;这次重组,修正过去的主张。这可从他们发表《我们的工作态度》一文可见。该文说:“我们没有忘掉我们底使命……既然没拿着枪杆跑上前线去,在后方……也得站好自己的岗位。…”。第一次公演的是阳翰生的《前夜》,主题是大义灭亲;接着是马彦祥从法人萨都名著改成的《古城的怒吼》。不久,沉寂了一段时期,欧阳予倩来港后再排新戏,后在港澳两地演出。
一九三八年,厦门沦陷,“厦门儿童剧团”二十七人,由七岁到十七岁,在林云涛带领下于同年十月到香港,为本港难民演剧筹款,两月后重踏征途,到南洋各地宣传抗战。离港前,“香港学赈会儿童团”假孔圣堂欢送。“厦门儿童剧团”演出《神州血债》,“儿童保养院”演默剧《复活》,“学赈会儿童团”演出《流亡》。
写到这里,我不期然想起上海的“孩子剧团”。该团二十二人,由八岁到十五六岁,在上海沦陷后分批逃生,有些扮作小伙计,有些给人家当儿女带走。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剧,这些孩子推动着我们。
本港的儿童受到“厦门儿童剧团”的感染,于三九年儿童节公演“蚂蚁儿童剧团”集体创作的《儿童万岁》,参加演出的有“学赈会儿童团”、“先锋儿童剧团”等多个团体。接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倡议成立“儿童剧场”,培英、培正、协恩、真光、兹理罗士、培道、华英等校均有参加,先后演出十多次,如《小英雄》、《三江好》、《死里求生》、《警觉性》等剧,一方面是响应抗战,另一方面是寓教育于戏剧之中。
接着谈的是来自国内的剧团。
最负盛名的是“三中”——“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中国艺术剧团”(简称“中艺”)和“中国救亡剧团”(简称“中救”)。
“中旅”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当时只有唐槐秋,女儿若青等六人,在华北等地演出,人数渐增。三八年七月抵港,公演阿英的《青风秋雨》、曹禺的《日出》、《雷雨》及尤竞的《夜光杯》等剧,极受欢迎。
很不幸,“中旅”闹分裂,原因是组织不健全和团员待遇不平等。据说团员除住食外每月只得港币五元,而主持者却过着浪漫的生活。各方调解无效,好些团员退出。其后唐槐秋得到张雪峰等协助重组“中旅”,三九年五月再公演《凤凰城》,为难民筹款。唐槐秋的生活较严肃了,但家庭纠纷没有解决,若菁、若英姊妹同情母亲,不肯参加演出。不久,唐槐秋便带领一些团员回国。
“中艺”是姜明等退出“中旅”后组成的。三八年十二月成立,三九年公演陈白尘的《得意忘形》、胡春冰的《中国男儿》等剧,又特为港人用粤语演出于伶的《花溅泪》,劝喻过着灯红酒绿的人们切勿重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覆辙。欧阳予倩宣称:“‘中艺’在香港成立,工作从香港做起。”他们吸收“中旅”的教训,财政公开,薪酬一致,生活严肃;又设立读书会、座谈会,可惜四○年便解散。
“中救”由金山领导,于三九年抵港,公演《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保卫祖国》等剧。《保》剧由四个拉幕剧合成,内有一个是《逃难到香港》。两月后“中救”改名为“新中国剧团”,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演出,筹得赈款一百万元(当地货币)。不幸被勒令离境,但已给当地侨胞留下深刻印象了。
除了“三中”外,还要谈谈“红白剧团”和“广东剧协”。前者是东莞的一群青年剧人组成的,三九年来港,也是筹款赈灾。首演日发表“我们的态度”:“自由解放需要经过斗争得来的,……用血红的代价,才能达到洁白的将来,……我们以‘红白’自勉”。他们曾公演陈白尘的《群魔乱舞》,演出时改名《狗》,并解释易名的原因。据他们说:剧中人物,与其说是“魔”,更贴切的应说是“狗”。“魔”虽然值得诅咒,却有点不凡。剧中人是混混沌沌的失了人的本性,也庸庸碌碌缺了人的本能,简直与禽兽无异,该称为“狗”。是不是借剧中人来讽刺或警惕港人呢?当时确有不少狗辈在港。
广东剧协的成员于三九年重组“广东戏剧协会第一剧团”,后以职业剧团出现,上演《自由魂》、《海上风云》、《烽烟万里》三部曲等剧。他们自称为“摇旗呐喊的后来者”,曾掀起一度热潮。
我想,留意本港剧坛发展的人们不会忘记三九年多个团体联合公演的《黄花岗》,有人提到“港督莅临参观,盛况空前”。港督确实很少屈驾欣赏我们的话剧,而事实上当时确是热闹非常。该剧原是“广东剧协”集体创作,参与编写的有夏衍、胡春冰等二十二人,在港演出时由胡春冰重新整理,全剧分四幕六场,导演团有胡春冰、李景波、欧阳予倩、黄凝霖、钟启南、卢敦、谭国始七位,演员过八十,加上前后台工作者达二百多人,比起一九七五年由三十四个剧团,超过二百个工作人员公演的“曹禺戏剧节”还热闹。
以上所谈的戏剧演出均是公开的,现略谈演出不公开的救亡团体。由于不公开,故鲜为人知。
救亡团体演出地点在私校,放学后把相连的课室改作舞台及观众席。观众是团员的亲友,人数很少超过一百;不售入场券,演后由观众自动捐款,交给报社作劳军或救济难民用途。我不时看到女士们解下颈上的金链,腕上的金链及其他首饰如戒指、耳环等放在捐款箱里。由于演出频密,筹得款项不少。又因演员与观众接近,感染力强。此外他们偶而到球场,在球赛间场时演出短剧,又不时到新界,在街上或搭棚演出。
我和家兄及表侄也时有参与上述的表演,当时我们未看过布莱希特的剧本或理论,却会在自觉的要求下运用“离间效果”。还记得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在演出中突然辩论时局,观众却不以为怪。
那时演出条件很差,没有舞台灯光,演员多不化装,必要时用红纸抹脸与墨笔画眉。由于赶戏,加上团体间要互相帮忙,有些人要参与几个救亡团体的工作,差不多每晚都要排练或演出,而且身兼数职,深夜还得赶写剧本或演讲稿。写的多是二十至三十分钟的短剧,现成剧本用不着:一方面要配合集会的时间分配,因为歌咏与分析时事更为重要;另一方面要反映时局的变化与社会上突发的事件。(例如当时的中华书局罢工。)因此,很少回家吃晚饭,经常以面包充饥。
工作忙与艰苦不算什么问题,性命的安危却非常重要。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英、日两国仍保持友好的邦交,活跃的团友不得不提防日本特务和香港政府的密探,无故失踪的事间有发生。及至香港沦于日手,团员纷纷逃亡,有些到国内后方,有些走上战场。我有约十个朋友都牺牲了,往事并不如烟。
(二)一九四六到一九六五——香港光复到年青人接班
沦陷期的剧坛情况,我不清楚。听说留港剧人会上演哥尔多尼(C Goldoni)的《女店主》(La Iocondiera)及曹禺的《雷雨》。
战后归来,剧坛已渐复原。救亡剧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有三种演出。其一是“天台戏”;其二是游乐场内的戏剧表演;其三是在戏院的正规演出。
“天台戏”是工人们利用天台演出的创作剧,我没有去看过。广东剧协的李门曾给我颇详细的资料,我无暇翻阅作介绍了。凭想像,演出是反映工友的心声。(当时国共内战。)写到这里,我想起港九邮差工人会在战时响应献机抗敌,演出自编的《流亡之歌》。无论演出者与剧本内容,都与战后的“天台戏”截然不同。
游乐场内的演出有苏园、东区游乐场及月园几个地方。我常到月园看戏,演出的是国语话剧:程刚芳会在那里主持。我亦常参观在戏院的正规演出,最负盛名的是“中原剧社”,上演的是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现成剧本,很受欢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原”、“建国剧社”的重要成员离港,不少工人亦回国,东区游乐社与月园拆卸,以上三种演出便停止了。
但剧场并没有沉寂。学院、学校与若干业余剧社恢复演出;我当时在罗富国教育学院任教,同学们要演戏,我只好再为冯妇了。罗富国教育学院在战时已演出两次,一是校内,一是公演,战后四八年恢复演出,后因校友会筹备夜校经费及建立日校,公演筹款更多了。
四九年,教育署举办学校戏剧比赛,大受欢迎。第一届由马鉴与容宜燕任正副主席,第二届胡春冰代替马鉴,容宜燕继续主持到第九届,第十届由谭国始接办是最后的一届。
五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时代,在这情况下兴办戏剧比赛实在难得。这敏感不一定来自教署,可能来自参与工作的人士。当时的比赛,教师可以协助,并可请外界帮忙。皇仁中学有柳存仁,英皇中学杨晏华,圣士提反女校有黄蕙芬,培正中学有关存英。钟景辉就读培正,当时已显露表演才华。香岛、培侨、劳校亦可请影艺界人士指导,于是问题发生了:如果左倾学校演出最优秀,应否给予冠军呢?表面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便成了问题。有一次,某剧在演出时曾下幕一次,有位评判认为这是违反独幕剧规则,有人反驳,引起剧烈争论。又记得每次到左倾学校评戏,务必集体准时到位,入座便演,演后勿勿离去,遇见旧朋友也不招呼。我当时亲历其境,因为我也是评判之一。因此,有人认为学校戏剧比赛的停办,与政治敏感不无关系。我曾查问学校戏剧比赛停办的原因,没有人给我答复,但敏感还是存在的。
五二年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成立,马鉴、容宜燕当正、副主席。翌年胡春冰代了马鉴,接着容宜燕当主席多年,其后是鲍汉琳、高浮生、郑璇、朱瑞棠等。五六年底周年大会,几位资深组员退出,其后另组剧社。“中英”的分家显然与战时“中旅”的分家不同,我听到好些传说,但不报道了。
五二年有件大事:本港剧人联合演出《黄花岗》,没有战时那次的热闹。五五年是第一届艺术节,并举行独幕剧创作比赛,但参加人奇少。五六年第二届艺术节,同年,剧人举办戏剧展览,连办三届,六零年学办马鉴纪念戏剧奖金创作比赛,参加的人亦不多。六一年大会堂落成;同年,业余话剧社成立,它与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成为本期最有影响力的业余团体。六五年,电影界组团上演《人间地狱》,这是从高尔基(M.Gorky)的《底层》(The Lower Depths)改编而成。
这一期的剧坛由成年人当主力,不能说青年学生不想演戏,否则学校戏剧比赛不会这样蓬勃;也不能说当局没有鼓励,否则没有艺术节和比赛。然而学生的自动、自觉还不强。这期上演的剧本多是现成剧、翻译剧。翻译剧以鲍汉琳最多,例如《妙想天开》(Her Husband's Wife)、《并无虚言》(Nothing But the Truth)等,其他如吴健生的《倩影》及拙译(英雄)(Arms and the Man)、《社会栋梁》(Pillar of Society)。创作剧较少而以古装居多,例如胡春冰的《李太白》、《美人计》、《红楼梦》、《锦扇缘》,熊式一的《王宝钏》、《西厢记》、黎觉奔的《红楼梦》、《赵氏孤儿》,姚克的《秦始皇帝》、《清宫秘史》,柳存仁的《红拂》,吴健生的《四面楚歌》,庞德新的《赎》,我也凑趣写了《昭君出塞》、《孟丽君》。社会剧不是没有,我不讳言以我最好。我在这期写了十个剧本如《风雨同舟》、《通灵有术》、《菩提树下》,柳存仁写了《我爱夏日长》。反映低下层人物的新作有朱瑞棠的《毒海余生》及姚克《陋巷》。我以为本期最成功的创作剧是《陋巷》。它在六二年的首演是剧坛盛事,演员有郑子敦、袁报华、张清、陈有后、梁舜燕、庞焯林、鲍汉琳、黄蕙芬、黄宗保、陈劲秀等。
为何有这么多的古装戏?可能是吸引观众吧。有人说古装戏和翻译剧易于通过,当时演剧是要送检的。我更要通过教育署检阅的一关,幸而没有不批准,极其量是建议修改若干句。但我仍然觉得与送检无关,主要是风气和投观众之所好。这期的演戏很多是为了筹款,例如罗师的建校及街坊福利会的筹募经费;其次是为了兴趣,“发烧”。很少人提到剧本的内涵,战时剧本的时代使命感已消失了。
(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专上学联戏剧节到定目戏团成立前
我以六六年作为第三期的开始,原因是该年有几个新现象出现。一是年青人活跃而成年人淡出,专上学联戏剧节的诞生标志着这一转变;二是西方新派剧的兴起,它与存在主义流行于专上学院,影响到剧本的内容与演出的形式;三是公演多了,正是剧坛蓬勃的先兆。
专上学联戏剧节开始于六六年二月,该届的冠军剧是罗富国的《惊梦》。《惊梦》是我的新作,但我不是学生,同学们还未开始创作。同年三月,大专公社举办独幕剧创作比赛,凌礎基以《皮大衣》夺魁。当然,本港与五六年与六零年均有创作剧比赛,但六六年后,青年剧作更多了。
六六年上演的外国新派剧有影人组成“香港话剧团”的《绞刑架下的中锋》(Centre Forward),港大的《犀牛》(Rhinoceros)、《四川贤妇》(The GoodWoman of Szechwan),浸会的《快乐旅程》(Happy Journey)、《动物园的故事》(Zoo Story)。以前有没有人导演新派剧,我不知道。新派剧的兴起,钟景辉、黄清霞、黎翠珍、卢景文、朱克均作出贡献,其后有袁立动、陈载沣等人。谈到演出,记忆所及,有七十余场,加上我不知道的,可能近百数,是比以前多了。因此,我认为是剧坛蓬勃的先兆。
六七年五月来了一个逆转。新蒲岗工厂劳资料纠纷引发的“五月风暴”使“香港的安宁受到骚扰”(见专上学联的《香港学生运动回顾》),对剧坛有颇大影响。十二个剧团联合公演《陋巷》不得不延期,我在港大教外课程部的“戏剧理论与实践”,完成廿四讲后不得不结束。六八年,元气还未恢复。黎觉奔写了“一九六八年的回顾”,提出五点总结:①演剧困难没有改善,一是大会堂加租,二是场地难找;②一年来青年朋友站在前哨;③成名作家不努力,除李援华有新作外,其他剧作家没有作品产生,今年公演的都是老剧本。④十二个剧社共同排演《陋巷》是一喜事。⑤专上学联会及各院校的努力可嘉。剧评人寒连在同年的回顾指出:量颇可观,质未有突破表现。
六九年八月,中学生组成的校协戏剧社成立,上演拙作《天涯何处无芳草》。校协与学联成了本港最有影响力的学界剧社,且于七三年举办中学中文剧本创作比赛。其后不断努力,到八九年十月已出版《青年创作剧选》两集了。学联停办戏剧节后,校协仍活跃于剧坛。
六八年,十二个剧社成功地演出姚克的《陋巷》,六九年,天青、世界、勇毅、佛青组成普及戏剧会,其后参加的有天一剧社。同年,市政局举办青年戏剧节,共演九天,分日夜场。该年度演出剧目约一百。七零年,致群剧社成立,上演《魔鬼门徒》(Devil's Disciple),其后该社常有演出,直到今天,仍是业余剧团的中坚。七二年,朱克改编和导演的《七十二家房客》掀起了一度热潮。七四年,市政局与罗富国校友会、致群剧社举办“中国话剧发展”讲座,共二十次,每次三小时,参加者超过二百人,暑假过后仍近一百。七五年,市政局举办“曹禺戏剧节”,公演五剧,参加者有二十四个团体,工作人员超过二百。这些都有力说明这一期的剧坛比从前蓬勃了。
这期又可说是剧本内容的转变期。以学联的演出为例:初期学联同学的创作,可以六六年第一届雷浣茜的创作奖《梦幻曲》及六八年第三届龙梦凝的冠军奖《山远天高》说明。前者通过爱情的抉择来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剧里的情人代表理想,丈夫代表现实,女主角在梦里与情人相恋,醒后随夫归去。后者亦接触理想和现实的问题,作者在场刊写着:“女主角是徘徊在现实与幻想的个人,律师代表现实,诗人代表理想,他们都自私,表示现实和理想随时想吞没个人。”作者着重于个人的独立。我觉得,这阶段的专上同学编剧是从内心出发,写出个人内心感受,但未注意到社会阶层。
学联第二阶段的创作,从六九到七二年,我认为是受外国思潮与剧坛的影响。六九年第四届冠军剧是黄韵薇的《等待》,内容讲述男主角患上绝症,等待死亡。最佳创作是梁凤仪的《夜别》,也是谈绝症、死亡。七零年演出后,一位剧评写着:“本港剧坛陷入迷惘阶段了。”其实迷惘、灰色已从六九年开始,该届加上神秘感而已。最佳演出是李志昂的《奔》,一开始用新手法。七一年,新亚艺术系演出《※》,一位剧评家写着:“我只能靠估,要我说什么好呢?我只好说他们演得《※》一般美好就是了。”那届的冠军剧是港大的《五十万年》。七二年有两度演出,一月是第七届,浸会演出《围墙外》,剧里的角色全是死人。冠军剧是中大的《蟒》,场刊说:“我在我所开的玩笑中迷失了,……我在玩笑中丧失自己。”最佳剧本是港大的《冬眠》,两个人谈感受:“我们是蛇虫鼠蚁,我们是自欺欺人,……我们从无知到觉醒,觉醒而后行动,然后失败、失望,没办法!只有冬眠等待。”十二月是第八届,冠军剧是中大的《市外》,场刊说:“为我们哭笑实在不值得,……逃出市外,枯死于市外。”当年的评判发表意见,一位说:“技巧相当好,只是调子有点灰色。思想空洞。”另一位说:“同学们受外国影响过大,且多接受形式与消极思想。……如果我们再看几次,可以到城隍庙解梦啦!”另一位说:“毛病是只把思想、讨论说出来而没有运用戏剧形式。”这几年的剧本与演出,不能说不好,只是失落、迷惘、绝望、灰色的调子很浓,加上形式主义与神秘感。看来同学们传达的是外国思潮,未必全是内心的感受。
使我惊奇的是:七十年代初期,同学们到维园集会,保卫钓鱼台,七一年到日本领事馆抗议,七二入高潮,五月十三日举行保钓大游行。但刚在这个时候,另一些同学却在写失落、迷惘的剧本,成了强烈的对比。
七三年专上学联没有举办戏剧节。七四年是第九届,该年学联举办“中国周”,发表文章:“放眼世界,认识祖国,改革社会,是学联今年第十六届周年大会向同学们发出的号召,也是学联对近年香港学生运动发展方向的总结。”该年的演出有港大《雾散云开》,中大的《日出日落》,虽然两者的观点不同,认识和关心中国则一。葛师的《谁之过》反映社会,而浸会的《劝君莫作男子汉》抨击当时警察的贪污,台词通俗而精警,例如:“金牌烂仔帮有牌烂仔”、“唔理有牌有派,有派有牌,通通拉。”引起哄堂大笑。七五年第十届有五个集体创作,有谈帮忙劳苦大众修桥的《桥》,有学生参加社会运动的《炼》,有学生参与政治的《急流》,“认中关社”成为这期的主流了。
校协的步伐与学联互相呼应。校协从七一年上演的《麈》到七四年的《会考一九七四》,也是从迷惘、灰色到“关社”的。
(四)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九——戏剧专业化时期
我以七七年市政局香港话剧团的成立作为本期的开始,并把它称为定目剧团而不叫职业剧团,因为职业剧团已出现多次,香港话剧团的称号也有人用过。市政局香港话剧团的诞生,标志着剧坛开始用“两条腿走路”。过去没有官方剧团,而政府对业余剧团的资助奇少。剧团只以一条不健全的腿维持多年,七七年后,情况有所改变。
香港话剧团开始时,演员只有十位,现增至二十四。演出大型、小型及巡回演出。政府的资助,据八七年八八年的统计,款项达六百七十万元。全年观众五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人次,平均每张票要资助九十四元。
八二年二月演艺发展局成立,历来受益者有职业的中英剧团,(这与“中英学会中文戏剧组”及其后的中英剧社有别)及几十个业余剧社。演艺团体获得资助的来源,除演艺发展局外,还可以从市政局及区市政局、各区议会。政府肯拔款资助是构成剧坛蓬勃的一个原因,得不到资助的剧团当然困难重重。关于这点,留在以后再谈。
除了香港话剧团,七九年有中英剧团与海豹剧团的成立(前者是职业剧团,后者是半职业剧团),八七年又有中天制作公司成立,它与浩采制作公司均是民间的职业剧团。于是,四个职业剧团,政府全力资助和民间组成的各占一半。我不知中天与浩采怎样维持他们的动作?但无可置疑的是这四个职业剧团有助于推动戏剧走上专业化的道路。演艺学院于八二年二月成立,更能培养戏剧专业人才。八五年七月,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招生,名额二十五名,报名者达八百之多。这实使我惊奇,对剧坛来说是一个好现象,戏剧专业化更明确了。
这时期的演出更多元化,编剧、导演、舞台技术的水平提高,观众数字也有所增加。有人说编剧未如理想,但不能说没有提高。剧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古典剧、实验剧和一些商业性的演出。这和场地的推广也有关系,演出从剧院到学校、到广场,于是表演可以从对着一面观众以至三面、四面观众。
能够得到资助的剧团是幸运,没有资助的剧团却惨了。他们要面对种种困难,而最重要的是财政困难。不少业余剧团倒闭了,闻说“进念·二十面体”也面临厄运。进念有前行剧团的称号,打破传统的手法,不重视逻辑关系的情节,用语言、动作的重复或其他的手法来表演,即使有些观众不接受,也不能低估他们的贡献。
这时期话剧艺术交流多了。外国剧团来港演出是众所周知的,国内剧团来港也比前多,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王昭君》、《推销员之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原野》、《风雪夜归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家》及广东话剧剧院喜剧团的《七十二家房客》、《三姐妹》,而到国内演出的有致群剧社的《武士英魂》,香港话剧团的《不可儿戏》。
然而,使人担心的是创作剧虽增,而出版奇少,造成这情况的是:话剧观众仍是少数,欣赏演出的观众以至剧人也不爱阅读剧本。有些人得到某些机构的资助,自资印行例必赔本。这一方面局限了交流,且使本港话剧中缺少纪录。
最后,我想略谈每年一度的市政局戏剧汇演,我觉得它像本港剧坛的缩影,反映了剧坛的情况和剧作的多样化。
汇演开始于七八年,由致群剧社、罗富国校友会戏剧组、香港青年话剧组、高风剧社及实验室剧艺社组成汇演筹委会,与市政局合办“业余剧社汇演”。翌年,由市政局主办,参赛亦只有五个单位(罗师退出,大学实验剧团加入),创作剧由一个增至两个。参加单位每年递增:七九年五个,八零年八个,八一年五十九个,到八八年增至九十三个。创作剧从一个开始,到八八年增至二十九个,占决赛的三十单位的96.7%。比赛分公开组与中学组,前者专为业余剧社而设。历来中学组的创作都比公开组多。八八年,中学组全是剧作,其中不少是集体创作。
从创作剧的内容看。公开组写的,多是普遍性的题材,比如爱情、自我、沟通、疏离,……谈现实的社会问题较少,但并不是没有。七八年,香港青年话剧社以当时一个妇人因劝丈夫戒赌不遂而斩去自己和儿女的手为题材,写出赌的危害;七九年写神女生涯。港九机缝制衣业职工总会亦写下层市民的辛酸。但这两个团体都解散了。后来致群剧社及少数业余团体亦有些反映时代的社会剧出现,比如“致群”的《末段旅程》谈老人问题,《档案——SG三七》探讨学生性行为的背景、成因。
谈到性问题,某年有个得奖剧本写得坦白,比如在台上除裤小解,不是面对观众而是背台;亦有描写女主角与丈夫欢叙时口中不停叫着“发仔”,幻想力丰富,只不知观众有何感想。中学生的剧作,不会出现那种作品,可能缺乏经验而不易通过老师那一关。
还有一个现象,公开组不少写人生的灰暗、失落、虚无。八八年有一个剧本名叫《虚无的人》(Nowhere Man),该角色只有过去而不生存于现在。某剧社在场刊写上几句话:“前提: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死了。’结论:如果尼采说对了,以后我们只好相信自己;如果上帝说对了,我们注定永世不赦。”我觉得很精彩,即使未敢苟同。
回头谈中学组的剧本。多年来的题材都是以描写学生生活居多,比如考试压力,代沟,失败学生,父母不许参加课外活动和做义工,电视对青少年的影响,青少年的同性恋及幻觉,暗恋异性师长,从大陆来的学生面对的困难,由歧视到谅解等等。亦有谈释囚问题,被奸少女难于摆脱阴影,伤残问题,老人问题,孤儿问题,九七问题。颇奇怪的现象是:中学生谈“九七”比业余剧社为多,而且观点有异。公开组谈“九七”多是暗示,不加评论;中学生却直接指明“九七”困扰,强调人有移居外国与返回本土的自由,又表明自己的志愿:“生于斯,长于斯,贡献于斯”,《阿恩的来信》高唱“我愿意以香港为家”作结。
两者比较,谁较好呢?“见仁见智”,难下结论,但有一宗值得高兴的事:几年前,中学组的佛教善德英文中学演出《朱秀才》,反映会考失败的学生自杀,却为曾因科学失败自杀的朱秀才救。题旨指出自杀的不可取,生存该有目标,全剧轻松惹笑,后被某电影公司拍成《开心鬼》。
谈到技巧和形式,真是各有千秋,篇幅所限,恕不叙述了。我当了戏剧汇演评判多年,目睹业余剧社与中学组的进步,非常兴奋,我不讳言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Ⅱ.反思
(一)剧坛的路向
首先感到的是:话剧观众很少,大概是两、三万人吧,那是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市民生活忙,辛劳一天后回家,第一宗事是亮灯,第二是开电视机,第三是换衣服,第四是弄饭或等饭吃。有人说:反应快,少用脑的玩意最受港人欢迎,于是人们乐于玩电子游戏机与看电视。看话剧要想像,要理解,毋怪许多人不入剧院。港人又喜欢走短线,快收成;话剧要经过多次排练才能演出,又要演出多次才有根基,所以香港的土壤不宜发展话剧。可是,“不宜”并不等于“不能”,问题的解决还在我们的手里。有位朋友说:巡回演出不多,戏剧教育在学校未能推广,市民看话剧的兴趣尚待提高。是不是可以举办多些戏剧欣赏的讲座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值得我们考虑吗?具体办法是怎样呢?
第二个问题是使命感。中国剧人刚开始便有使命感的,其后也负着这个包袱,并因此而受到逼害,甚至牺牲。王钟声的被杀、陆镜若的毁家推动剧运,便是例子。香港剧人没有受到逼害,但在战前与战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战后,我觉得没有使命了,但被人推动再作冯妇后,在工作中又感到另一种使命的存在。这成了我的缺点,有人劝我:“放弃使命的包袱吧,那会使你成绩好些。”他也许是对的,我想了一会后回答:“那么,我玩桥牌好了!”朋友说:“对,你爱玩桥牌,何不写本玩牌的书呢?那也是对人有贡献的。”我确实喜欢玩桥牌,现在每天都是自己和自己较量,或者和电脑比高下。我同意人们在演出中力求“搅笑”,给观众带来欢乐的好事。可是,我依然服务于剧坛,或者是过于执着吧!
我又认为过渡期的使命感更重。与市民生活有关的,除了通胀、治安,还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制衡、监督、信心、培训与吸引人才等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到戏剧的艺术性和局限性。有人认为艺术性可与普遍性、永恒性共存,但与时代性不大调和。高尔基说:“文艺写的是人。”基本上这是对的,单纯描写动物、风景和花草树木的是少数。但写人是不是只写人性中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呢?我的观点是:人不能超越时空而存在,人性更不能不带有时代性和空间性(环境影响)。毫无疑问,抗战剧是不受欢迎了,也没有人上演,但是不是改编后会受欢迎呢?提起改编,香港话剧团曾上演过两个改编的戏。一个是《七十二家房客》,未演前我予以赞成,看后很失望,一位朋友看过以前朱克导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后对我说:“我不反对旧瓶装新酒,但不要把前人的心血糟踏啊!”我说:“你不予好感,是吗?”他说:“可能迎合今天的观众,我觉得不伦不类。”另一个是莎剧的改编,我看后确实觉得不伦不类,写了意见也不敢交出。我觉得这是改编的问题,有些人编剧是很好的,我很想改编于伶的《七月流火》,我以为那时上海的动荡与市民的心态,有点像香港人,并可暗示前景。
有人认为戏剧只适宜写小问题,谈大问题便不中听,甚至流于说教,我不大同意。我以为普遍性、永恒性可以和时代性结合,艺术性可以带出时代感。问题是怎样编写,且要边排演边改动。任何艺术都有其局限性,但局限并非不能打破的。我期望有些演出一方面有艺术价值,另一方面能反映过渡期,不是轻描淡写的反映,也不必用暗示性的反映,而是直接地既反映市民的心态,亦使市民知道前景在我们手中,虽有困难,不会绝望,天也不会塌下来的。
第四个问题谈到反传统的演出。我说的反传统,并非指技巧、内容、形式的革新,而是令好些文人,尤其是工道之士,摇头兴叹的演出。其中有些涉及是粗言秽语,有人看后说没法“顶得住”,不得不中途退出。但大部分观众却觉得非常“过瘾”,把所受的抑压宣泄出来了。他们找到代言人,看来让他们上台表演“讲粗口”,像卡拉OK一样,更受欢迎,我对这类演出不生反感。我未退休前,学生们已掌握三种言语:一是用来和家长交谈的,二是应付师长,尤其是女教师,三是同学间的沟通,言语间不加上助语词既“不够劲”,亦不能畅所欲言。我看今天他们该已掌握五六种言语了。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在桌球室、在卡拉OK,难道还说出在操场里、课室里、家里同样的语言么?
不要以为剧院是学习语言的地方。学生和市民不去剧院,难道不会听到更坦率、更粗暴的污言秽语吗?如果这样想,简直是掩耳盗铃,更正确地说,是像驼鸟埋头于沙堆里。
另外,对于一些被指为色情的演出(例如几年前的《看见你——灰飞烟灭》),我接受,但不会写。“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有很多题材要写哩!
第五个问题谈到中国话剧的路向,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中国话剧是由西方传来的,开始时不无中国戏曲的遗留及东洋剧的轻微影响。到二十年代文明戏消失后全部西化了。我在六十年AI写作的《昭君出塞》,把元曲、话剧、旧诗朗诵、哑剧、影象造型,放在同一剧里;题材连贯,每个单元都在谈昭君,看来是不同艺术的组合,但每个单元保留个别的特色。七八年,我为“香港话剧团”写了《窦娥冤》,把话剧与戏曲表演揉合一起,当时的想法仍是个别独立的。导演袁立动在话剧表演中加插若干戏曲动作,我不以为然。过了几年,我觉得袁兄的处理是对的,即使当时觉得不调和,甚至不伦不类,实是一项有建设性的尝试。我觉得袁兄比我走远一步。八二年,我到新加坡戏剧营谈《中国话剧发展的路向》。未到新加坡之前,我细心考虑,中国话剧应否在形式上与西方相同,只在内容上有分别呢?我阅读有关梅兰芳的书(他没有留下著作,但讨论他的艺术和纪录的作品却不少),我又翻阅布莱希特的作品及研究布莱希特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籍。我觉得“写实”和“写意”是可以结合的,“梅”、“史”、“布”三大体系的融和可以成为中国话剧的风格,使中国的话剧有中国的特色。我又想到中外的舞剧、歌剧、音乐、绘画、书法。中国的舞蹈也用脚尖,和芭蕾舞相似,但它常配上中国的武功,整体形式和西方舞不同。中西歌剧当然不相似。绘画,虽然有些书法家在中国书法中采取西方绘画及东洋画的技巧,但不会失去中国画的特色。音乐与书法也是一样,中西两方的分别很清楚,于是我以为上述三大体系的融和及写实、写意的结合,便是中国话剧的路向了。不久我读到国内黄佐临的“戏剧观”,和我的意见没有什么矛盾。随着,国内剧坛讨论黄老先生的“戏剧观”,但不久便沉寂了。
我现在还思索这问题,有位朋友说:“为什么要有中国特色呢?哪样好便照做,不必负上‘民族包袱’。譬如,西方音乐的‘壮美’显然比我们的文人音乐动人,古琴的清雅不会像交响乐产生强烈的共鸣。”我智力不高,不禁茫然了。
我仍在想:如要创造一种中国话剧特有的风格,必须有重大的突破。首先要有突破性的剧本,再由编、导想到揉合的设计。这必然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最后,我写出下列几点期望:
(一)期望本港年青剧作家、导演、演员、后台工作者抽出一些时间学习中国文化。
(二)期望多些剧本出版。我不明白政府肯资助演出而不肯资助出版。市政局只出版过八三年汇演《优异创作剧集》,因为销量不如理想便不继续。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出版了几本和他们有关的书,而演艺发展局似乎没有资助出版的打算。为什么呢?香港话剧团的演出也不是全受欢迎,演出可以大量拨款,却不肯拿出万多元出版汇演得奖剧本,是不是我们毋须在剧坛留下创作剧的纪录呢?
(三)期望剧协发挥力量,出版刊物,又把本港剧团团结起来。
(四)期望出现对过渡期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剧本与演出,这是我对年青剧作和演出团体的厚望。
(五)期望有中国特色的风格出现。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中外剧团常到本地演戏。即使我们的梦想永不实现,也希望香港剧坛有突破,能推动国内话剧的进展,这不会是梦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