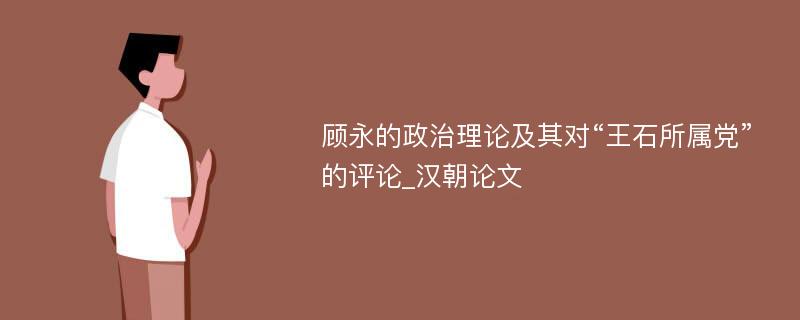
谷永政论及其“党附王氏”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论论文,王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谷永,字子云,西汉后期著名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政论,敢于指斥皇帝的失德行为,其切直与当时的宗室忠臣刘向相比,毫不逊色。但前人每以谷永“党附”外戚王氏,对他评价甚低。班固断言谷永“专攻上身与后宫”,是由于“党于王氏”,“自知有内应”[①],已属贬讥。而常作惊人之语的明代学者李贽更斥之为“该杀”、“一派畜生”[②]。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谷永的评介,较为宽容,肯定了他的政论有救世之效,但对“谷永之心”仍严词苛责[③]。流风所及,谷永一直被罩于道德史论的贬责之中。
然而,历史上,每当国政衰败之时,心理负荷最重的,莫过于士大夫中政治见解最敏感者。汉末的谷永,就是这样一位卓识之士。他不愿浑浑噩噩,也不想明哲保身;他要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就必须对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势力,有所选择。所以,谷永的言行,实际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乱世临近之际,急于用世的功利之士,往往需要托庇于某一权贵集团,借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本文虽致力于重新检讨谷永的历史定位,但着眼点却不仅限于对一位古人的重新评说。
一 谷永政论的特点
汉末政论中,不乏真见卓识。刘向的宗室孤忠,鲍宣的直言下情,都各有其价值。就在这些充满警世谠言的名篇佳作之中,谷永的政论,亦有其光彩独具之处。
1、从“民本”思想谈国家兴衰
“以民为本”,是先秦政治思想中极可宝贵的精华。但随着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君主独尊的意识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除陆贾、贾谊曾利用汉初总结秦亡教训之机,高标过“民本”思想外,其已很少见之于汉人言论了。成帝元延元年,时任北地太守的谷永,在奏对灾异时,郑重其事地以民本思想来开导、告诫最高统治者:“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④]并率直指出,统治者地位的确立,是上天“为民”择贤而立,统治权力不会永远属于某一姓所专有。君主行道,自可得到天地福佑,百姓拥戴;如果君主无道,残害百姓,上天就会“更命有德”,政权易手。在这篇著名的奏对中,他提出的消灾止祸之法,实际上是以减轻赋税、赈济流民、劝民耕桑为中心的。
论史者往往对刘向的政论多加褒赞,但将其与谷永鲜明的“民本”立场比较,刘向政论的立足点是为维持刘氏家天下,其最著明者为“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⑤]的警句。刘向的宗室情结,固然可以理解,但立论却显然不及谷永高远。
2、借谈灾异切谏成帝
自西汉中期以降,借谈灾异而讥评时政者,所在多有,但像谷永那样把批评的矛头专指皇帝者,并不多见。
早在尚未与王氏深相结交之前,谷永即开始了对成帝的坦诚规谏。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刘庆忌举荐谷永。在谷永第一次奏对论政时,他即针对成帝湎于酒色、不理朝政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措,屡失中与?”劝诫成帝“留意于正身,勉强于力行,损燕私之间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并断然指出,“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⑥]这篇奏对,确立了谷永政论的基本模式,其中无投机之念,只有匡君救弊的一腔忠贞,故成帝深受感动,特赐召见,以示勉励。
成帝永始二年,星陨如雨。谷永再次借天变以责皇帝:“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于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他指出:三代毁于“妇人群小,湛湎于酒”;秦朝亡于“养生大奢,奉终大厚”,这两种亡国祸根“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⑦]同年,又有“黑龙见东莱”之异,时迁任凉州刺史的谷永,再次上书切谏:“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岁矣。”他痛陈汉家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他认为成帝之前的七位皇帝,都是“承天顺道”的明君,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于成帝自身:“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⑧]显然,成帝已被指控为灾异之根源、乱国之罪人。对此,平常对谏言每多优容的成帝无法忍受,盛怒之下指令御史收捕谷永。幸得卫将军王商暗通信息,谷永提前离京,才幸免牢狱之灾。就进谏无所顾忌而言,成帝时期,当推谷永为第一人。
仔细品味这几次奏对,不难发现,灾异不过是谷永讥评时政的契机,或称之为借口,议论的重心,总不离朝政缺失与百姓疾苦。其良苦用心,实应为读史者所深察。
汉代儒生侈谈之“灾异”学说,因带有神秘、附会的色彩,曾被当代学者鄙弃。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作法,近年来已有所纠正,肯定灾异学说有其积极意义的论著,时有所见。在此,还应补充指出的是:西汉谈说灾异者,大都是关心时政、志在救世的志士,而批评灾异之说不足凭信者,却不乏大奸大恶之徒。与谷永同时的张禹,即是其中之一。张禹以成帝师傅之尊,官至丞相。年老致仕后,仍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当时臣民上书,多把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归咎于外戚王氏专权所致,成帝一度颇以为然。但当他车驾亲临张禹府第、询问致灾根由、并把臣民归罪王氏的奏章出示给张禹看时,张禹不敢得罪王氏,竟答称:“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⑨]由此打消了成帝的疑忌之念。张禹的话表面上冠冕堂皇,似乎对灾异之说独持理性思考,其实却是为了结交王氏,自谋私利。与那些大谈灾异以求补救时弊者相比较,张禹的话实无可取之处。所以,直臣朱云指张禹是天下第一“佞臣”,欲请尚方剑而断其首[⑩]。稍后,又有杜业斥张禹为“奸人之雄”[(11)]。皆为知人之快论。西汉的阴阳灾异学说,为覆盖一世的时代思潮,用其说以议政如谷永者,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拒其说以售其奸如张禹者,则难逃佞臣之定谳。
尤其可贵的是,谷永虽以善谈阴阳灾异而著名,但对于祭祀鬼神的虚幻无益,却言之凿凿。“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为乞求生子,凡上书自称能祭祀鬼神、擅长方术的人,都以“待诏”的身份,宣召入京,“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谷永则劝告成帝,不可轻信此种骗人之术:“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并说,凡是“盛称奇怪鬼神”、有升仙不死诸般方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他进而历数周灵王、楚怀王、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妄信邪说,重用方士,盛行祭祀,耗资无数,却只落得“旷日持久,靡有毫厘之验”的事例,强调指出,察于前车之鉴,足知今日祭祀求福之举,不仅无补于事,还将开启奸人窥视朝廷之路。谷永的话,入情入理,使得沉浸于巫鬼氛围中的成帝,略有觉醒[(12)]。
上述奏对表明,谷永本人并未陷入“迷信”的泥沼,相反,他对世俗迷信的态度是相当理智的,而在当时,能具此种卓识者,堪称凤毛麟角。由此,似可推测,谷永对成帝侈谈灾异,是一种类似于“神道设教”的策略,目的在于增强进谏的警诫力度。
不论是大谈阴阳灾异之灵验,还是力驳祭祀求福之愚妄,谷永谏君匡失的志向,是始终如一的。
3、尊功尚能 翼辅汉室
西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功利之士,与那些尸位素餐、苟且求容的儒宗重臣相比,他们的个人品行,或许有不足称道之处,但他们所建立的功业,却为西汉后期的历史平添了诸多生机。谷永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深知功利之士对维持西汉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尊功尚能”就成了他政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为陈汤辨白及力荐薛宣的两次奏对,便集中体现了这一政论特色。
汉元帝时,“多策谋,喜奇功”的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袭杀与汉廷公开对立的匈奴郅支单于,建立了西汉经营西域以来最辉煌的功业。当时控制朝政的宦官石显及儒相匡衡,刻意贬抑立功异域的陈汤等人,甚至欲以“矫制”重罪惩治陈汤。幸有刘向上疏,盛赞陈汤“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才得以赦罪不究。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旧事重提,以“专命”和贪污之罪,奏免陈汤官职。后来陈汤又因上书言事不实之罪,被捕下狱并判处死刑。时任太中大夫的谷永,立即上疏,奏保陈汤:“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他把陈汤类比为前代身系国家安危的名将,力言其功不可没,“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指出以言事之罪,诛杀陈汤,将使将士寒心,不利于激励群臣为国赴难[(13)]。成帝准其奏,赦免陈汤。此后,陈汤仍有参议边事、为国效力之举。
尽管陈汤先后得到了王凤、王音的赏识和重用[(14)],但不能把谷永奏保陈汤的动机,解释为党附王氏,因为,反对王氏擅权最激烈的刘向,就曾最早为陈汤辩护。事实上,这件事集中体现了“事功派”与“守文派”的政见分岐[(15)]。谷永援救陈汤,还有两个动机:其一,谷永之父谷吉早年出使西域,为郅支单于所杀;陈汤矫制起兵袭杀郅支,对谷永有复仇雪耻之恩德,谷永代鸣不平,实为人之常情。其二,谷永钦佩陈汤的才干,服膺他的事功,有保全国家栋梁的愿望。此外,谷永致段会宗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重才惜能的情怀。“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与谷永相友善”,早年间曾任西域都护,甚有威信。后来,成帝应西域诸国之请,再次任命段会宗为西域都护。谷永感伤段会宗暮年远行,致书劝诫:“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万里之外以身为本。”[(16)]这里所流露的不仅是挚友之情,也有为国惜才之念。
薛宣,西汉后期的能吏之一。谷永上疏荐薛宣出任御史大夫,是薛宣步入政治中枢的关键因素。在疏文中,谷永开宗明义地指出,帝王之道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能在位;又分析御史大夫“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接着力荐薛宣“材茂行絜,达于从政”,有多年任职的阅历和考课中名列前茅的政绩,赞誉他“法律任廷尉有余,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表白唯恐朝廷用人“舍公实之臣,任华虚之誉”,故而越职举荐的用心[(17)],使成帝深为所动,遂任命薛宣为御史大夫,不久升薛任丞相。而这篇举贤疏,亦充分吐露谷永尚贤举能、忧国忧民之心声。
此外,谷永主张信守与匈奴首领达成的友善协议[(18)],以及从宽处置被控有罪的宗室诸侯王[(19)],都表现了他希望稳定政局、避免战争的审慎态度,很有老成谋国的政治家风范。
对谷永的政论,可以评定为:规谏无讳,切中时弊;立意高远,议论广博;秉忠谋国,情真意切。
二、谷永“党附王氏”无可厚非
谷永因党附外戚王氏而蒙受千古贬辱,已见开篇所述。本文无意于否定谷永党附王氏的事实,但认为,客观地分析当时政治派系的状况,谷永的选择并非堕落,他攀结王氏为奥援并非全出于一己私利。质言之,谷永虽有“结党”之事,并无误国害民之迹,实有匡君纠弊之行,故不可仿效古人,横加贬斥。
谷永攀交王氏,史有明文,尤以二事为甚。其一,成帝即位之初,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朝臣中多有讥议,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上疏称赞王凤等人“有申伯之忠”、“小心畏忌”,明言“不可归咎于诸舅”。由此得到了大将军王凤的赏识。其二,谷永得王凤之助擢任光禄大夫后,致书拜谢王凤,其中有“虽齐桓晋文用士笃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之句,又引豫让吞炭毁形以报智伯知遇之恩的典故,以喻自己甘作王门“死士”之志[(20)]。若以道德论史者角度看,此直可视作谷永卖身投靠权贵而人品卑下的表现而大张挞伐。然而,谷永本非道德家,而是一位急于用世的利禄之士,所以评价他主要应看他从政的行为,而不应囿于他攀交王氏的不体面言论。
下面两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和研究。
1、对成帝时期王氏外戚的地位与作用,应予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氏外戚在成帝时始得秉政,权倾一时。并且,它确实为后来王莽的代汉自立,提供了一定条件。所以,王凤及王氏五侯,历来为人所贬斥。但后有王莽之代汉,并不意味着成帝时的王氏就已是汉政权的心腹大患。细按史籍,王氏虽有专权与奢侈之弊,却不无善政可陈,至少,有匡君纠失方面,王氏的积极作用,是不该被抹煞的。
王凤的专权,主要表现为:阻止成帝任用刘歆为中常侍,排挤定陶共王出京,胁迫成帝罢免丞相王商及诛杀京兆尹王章,抑制素有贤能之名的外戚冯野王入朝辅政等五端。其中尤以杀害刚直敢言的王章最不得人心。王章弹劾王凤专权之语:“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以及王章被杀后“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21)]的史官综述之言,铸成王凤专横欺君之定论。然而,王氏与成帝的关系,不是没有可讨论之处。
西汉政制,本有以外戚辅政的传统;其间,虽迭生巨变,但这一习惯作法却终西汉而未改。“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22)]班固此语,即道出汉人认可外戚辅政之局的认识根源。综观西汉历代辅政外戚,多获“专权”之恶名,唯王商(丞相王商,而非王凤之弟)、史丹、傅喜三人幸免此讥。然而,此三人立朝辅政时间很短,其政治建树亦少。这实际上印证了令道德之士沮丧的常例: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辅政的外戚,欲有所作为,必须以专权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则外戚专权实为外戚辅政体制的自然伴生物。王凤的专权应是一种可被理解的政治行为。
况且,王凤的专权程度,比此前的吕氏、上官氏、霍氏稍逊一筹,且无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图谋,在皇帝面前表现亦有谨慎从命的表现。如,辅政之初,有黄雾终日之异,言事者归咎于王氏骤贵。王凤惧罪,上书自责,请求辞职。辅政七年之后,王章向成帝面奏王凤专权,王凤也未直接以铁血手段惩治王章,而是上书求退,自言有“三当退”之过,史称“辞指甚哀”[(23)]。只是由于成帝之母王政君的出面干扰,再加上成帝的出尔反尔,才使王章成了牺牲品。王凤的请罪求退之举,亦不必全以“权术”相诋;即便是以退求进、要挟皇帝的一种表示,至少也可证明,他的专权程度与霍光凌架于皇帝之上相比,仍有霄壤之别。王凤死后,王氏擅权更为减退。成帝发觉王氏五侯奢侈僭越,下书责问,王氏诸人立即束手请罪,“皆负斧质谢”[(24)]。此时,成帝若欲黜退甚至诛杀王氏,并非难事。由此可见,王氏的专横,并未超出恃宠而骄的正常范围。
王氏辅政可称述者,首推勇于谏正成帝之失。这是前人所忽略、而今人应给以标揭的。成帝以荒淫无道而著称于史,他既爱女色,又有男宠,不仅宣淫于宫闱,而且出宫微行,秽恶之声溢于民间。这些行为,大多发生于王凤死后不久。由此可以反证,王凤在位时,成帝心中有所忌惮,行为尚属谨慎。王凤死后,从弟王音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立朝辅政,其威权逊于王凤,故成帝始得自行其事,即表现为失德之事愈多。王音本以谨慎周详而知名,但在昏君面前,却不明哲保身,他冒着被贬辱的风险,直言劝谏。在集中记载王氏事迹的《元后传》中,班固给王音六字定评“数谏正,有忠节”。只因过于简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幸在《五行志》中保留了一段王音切谏成帝的奏对,才使读史者可以领略王音的忠直风范。鸿嘉二年,有大批飞雉群集于朝廷宫阙及重要官署,朝野惊怪连日。王音等人乘机上言,解释为天地“谴告人君”,奏请皇帝痛改前失,以求转祸为福。成帝却厚颜为自己辩解,王音当即加以驳论:“陛下安得亡国之语!……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泆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25)]此谏义正词严,忠君忧国之至诚,发于肺腑,感人至深。在汉代谏章中,亦足为上上之选。
前人论史,囿于“正统”之见,凡权臣与皇帝争权,往往对皇帝寄于同情,而对权臣加以贬抑。如果权臣又具外戚身份,则贬抑更甚。如果打破这种成见,重新审视王氏外戚与汉成帝的关系,我认为王氏对成帝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具有理性和公正的色彩,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谏正匡救的作用,它维持了西汉政权的正常运行,而未曾构成威胁。至于后来王莽利用了王氏辅政所建立的声威,废汉自立,自当另作别论。
2、谷永攀交王氏有忠公之益而无利己之实
结党,本是汉律所严禁、士林所不齿的行为,精明的谷永,何故主动攀交王氏,且有意张扬这种“私党”关系呢?以常情常理推断,谷永本为进取之士,依投王氏,必有其利己的图谋;身在宦海,追求腾达,当是他的原始动机。但从谷永的仕宦生涯看,投依王氏,并未给他带来官运亨通。即使在王凤辅政期间、谷永最受赏识时也不过官居光禄大夫,后又出为安定太守。王凤死后,谷永因挑起了王谭与已居辅臣高位的王音之间的内讧,为王音所忌恨,一度被迫告病免官。后虽致书王音谢罪求容,仍被抑为闲职。王音死、王商辅政后,谷永才迁任凉州刺史,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后又外放为北地太守。晚年,在王根的推荐之下,征入为大司农。但身居卿位仅一年有余,即因病免官。谷永不仅长于论政,而且临事治民,亦非庸材,“所居任职”[(26)],实非虚誉;但他一生中,居朝任官未获实权之位,反而长期出任边远地区的太守、刺史,以其才干而言,实难言得获重用。实际上,由于谷永“党王”色彩过于明显,反而引起了成帝的反感,这正是他不可能获得重用的真正原因。史称:“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最明显的例子是,谷永任职大司农岁余患病,“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27)]。成帝打破对患病的公卿给以在位养病之恩的惯例,将谷永免职,其厌恶之情,毫不掩饰。由此可见,谷永党附王氏,并未给他带来仕官荣耀。结交权贵,总以谋取权势利益为目的。而谷永攀交王氏的后果,却与常情相背。是事与愿违?还是谷永另有所求?我认为大有探求之必要。
谷永结交王氏,主要目的当不在于追求仕途腾达,而在于寻求一个庇护者,以使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谏正皇帝,做一个名垂青史的谏臣。以下事实当有助于我们遥体谷永的心态。
谷永在上书中,曾自言其志:“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28)]他不仅在任言事之官时,尽忠切谏;出守边陲,也曾几次越职言事,隐然把忠谏弼君视为自己仕宦中的首要责任。
谷永与王氏似有一种默契:王氏为谷永提供一层庇护屏障,而谷永则利用敢于直谏的名声,言王氏所不便言,从而起到谏正皇帝的作用。故史籍有载:成帝诸多失德,“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29)]谷永与王氏、成帝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三方都是灵犀相通的。谷永真正受益于王氏的,只有一事:当谷永因切谏激怒成帝、成帝令御史捕之下狱时,幸得卫将军王商暗通消息,始得免祸。这一事实,正可说明王氏借重谷永,意在谏正皇帝,而谷永也乐此不疲。
展读谷永政论,不得不钦佩其中所表现的浩然正气和敢言之勇。此种文心侠胆,倘发生在以道德立身的古之君子身上,自可称源于方寸丹田;而谷永显然不足以当此。然而,对于一个注重名利的进取者来说,只有有所恃凭,才能使刻意营造出来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常盛不衰。如则,则谷永攀交王氏,不能全视为谋取私利的投机行为,至少从其客观效果而言,实多有可取之处。
综上所论,谷永的政论具备独特的价值;历来对谷永“党附王氏”的贬议,影响了对谷永及其政论的正确评价。汉成帝时期的王氏外戚,虽有专权的一面,但因其制约成帝,对维持汉政权的生存,有其积极的作用;谷永虽有投依王氏的言论,但他在成为王氏私党后,仍不失直谏忠臣的风范。在政治动荡之秋,不能要求每个功利之士,都恪守道德信条而行无瑕疵。对于那些随世变通,甚至不惜降辱人格俯就世俗,以求施展自身抱负、匡世救弊的特殊志士,后人理应给予理解和同情。
注释:
① ④ ⑥ ⑧ (20) (26) (27) (28) (29)《汉书·谷永传》
②李贽:《史纲评要》卷九《汉纪·孝成皇帝·建初四年》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成帝·七》
⑤《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⑦《汉书·五行志下之下》
⑨《汉书·张禹传》
⑩《汉书·朱云传》
(11)《汉书·杜周传附杜业传》
(12)《汉书·郊祀志下》
(13)《汉书·陈汤传》
(14)《汉书·陈汤传》载,大将军王凤在陈汤失势之后,“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又据《汉书·陈咸传》载,“车骑将军王音辅政,信用陈汤。”
(15)关于西汉“矫制”行为及其文化内涵,详见本人与李宜春合写的《西汉“矫制”考论》一文。(近期内将在《中国史研究》刊载)
(16)《汉书·段会宗传》
(17)《汉书·薛宣传》
(18)《汉书·匈奴传下》
(19)《汉书·文三王传·梁怀王刘揖附刘立传》
(21) (23) (24)《汉书·元后传》
(22)《汉书·外戚传序》
(25)《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标签:汉朝论文; 西汉皇帝论文; 谷永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西汉论文; 汉书论文; 王凤论文; 陈汤论文; 王氏集团论文; 王姓论文; 东汉论文; 秦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