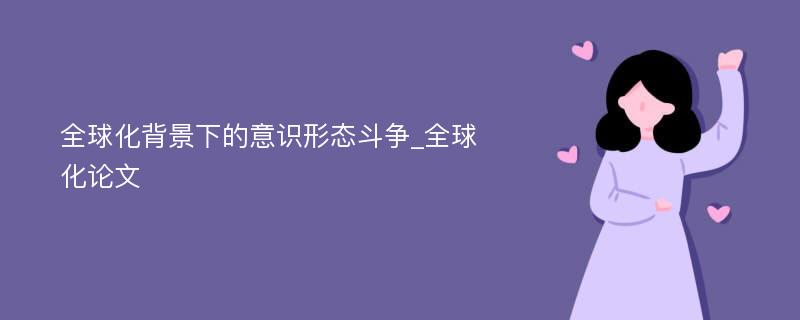
全球化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问题是当今世界瞩目的一个问题。它决非单纯的学理探究,而是切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全球化意味着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关联使人类活动突破原有的时空限制,在时空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这个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本文试图就全球化引发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一些探讨。
一
一般认为,全球化肇始于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是全球化的开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壮大,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使得资本冲破国界,闯荡世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将把全世界联系在一起。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缩小了人们的时空距离。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经济分工的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九十年代,除了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这两个特点更显著外,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也引人瞩目。现代的通讯,如国际互联网,使“地球村”变得比以往更加狭小。正是在九十年代,人们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并进而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
所以,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有两个前提:经济上的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如果从十五世纪算起,全球化的历程已有了500年。这个时间概念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化迄今给我们的是些什么东西: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种族灭绝、世界大战、少数国家对财富的掠夺和大多数国家的被盘剥、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等。如果说,这500年的全球化有什么样功绩的话,就是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还有就是使少数国家聚集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财富。而全球化对绝大多数国家则是一场大灾难。奇怪的是,今天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很少提及这段人类已走过的全球化路程,他们往往热衷于就九十年代出现的新情况提出新的概念、新的理论,西方的学者自不必说,就是我国学者,包括那些对全球化问题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其实,历史往往比学理更能说明问题。
人类迄今的全球化过程,其本质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对全球的大举入侵。这个入侵是全方位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从殖民化时代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西方列强主要是用所谓的“文明”对“野蛮”的优越地位来为它们的罪恶行径进行意识形态辩护。欧洲列强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和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相比,其他的文化和民族都处于蛮荒状态。所以欧洲人有义务去开化他们,他们也有义务接受白种人的摆布。于是,殖民统治变得合情合理,把非洲黑人象牲口一样贩卖也心安理得,对其他民族进行文化灭绝成了“白种人的负担”,“欧洲中心论”也因此出笼。这样的一套意识形态说辞为西方列强的罪恶行径罩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与此相对应,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的压迫和剥削的主要意识形态武器就是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不同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必然引发交流和碰撞,但从已经走过的全球化的历程看,全球化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由于少数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颠覆所引起的。今天全球化的形式和表现和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全球化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以往有什么变化吗?没有。
二
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人们在不自觉中把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混同起来。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同时提出的,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即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其为人们广泛承认的客观标志:国际分工、跨国公司、资金的全球大规模流动,而且这样的一些特征仍在深化中。那么,全球化这个概念有什么客观标志呢?全球化不仅仅指全球经济一体化,还包括了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国家主权的逐渐消失和全球文化的形成。但国家主权的消失和全球文化的形成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他们的确凿标志,它们只是人们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客观过程,而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一种预估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和全球化这个概念同时提出的原因。(作者倾向于使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但考虑到全球化概念被广泛使用,为讨论的方便,仍多处使用这个概念。)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客观过程和全球化这样一个仍处于纸上谈兵的主观概念混为一谈,利用了全球化概念的主观性,把他们心目中未来的世界模式说成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把它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强加于世界,从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所以,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斗争首先就表现为对全球化的理解上。
对人类大同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的天性。东、西方文化都有许多这方面的表述,因为民族—国家是有局限性的。而统一可以使人类避免战争、隔阂与敌视,更好地交往,这是人类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所以当许多人一听到全球化这一说法时,便不由自主地以一种浪漫的想法来思考全球化,把全球化的过程和结局描绘得花团锦簇,以至于无法想像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了危险性的进程,甚至看不到那已开展的全球化给第三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在这里,我们应该分清三个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的浪漫想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际过程,西方国家将它的全球化模式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如果说全球化有什么意识形态陷阱的话,最大的陷阱就是广大第三世界人民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失去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觉,将自己的民族利益拱手相让。世界上并不是所有都那么善良,有些邪恶的势力就利用世界广大人民的这种浪漫的情致,来达到它们的险恶目的。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社会结构、国际政治、民族文化带来诸多变化,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平等对话也是应该的。但全球化毕竟是个很模糊的概念,人们应该对此抱一种谨慎的态度。我们应注意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经历了500年,人们才首次自觉地认识到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刚刚开始。那么,要全面全球化,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遥远的将来。但西方国家却宣称“国家主权”已经过时,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将普照人间。它们利用经济、军事的优势地位,强行推行其全球化模式,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科索沃战争)来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要拨开西方国家散布关于全球化的种种迷雾,厘清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持正确的方向。
三
全球化的另一个意识形态争论便是如何看待“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问题。西方的舆论将民族主义看成是当今世界的大敌,更是全球化的大敌,如《经济学人》警告说:民族主义会妨碍在亚洲的自由贸易,而且民族主义对“全球公司”扩展的威胁比暂时的资本短暂更甚。(注:“全球化·市民社会·民族主义”,载《哲学研究》1999.12。)
民族主义作为人的基本情感有其存在的合理根据。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必然存在。我们反对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一种族主义。但既然民族—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为什么一种合情合理的人类基本情感却遭到横加指责呢?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西方学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的描述也承认,全球化并不凭借这种优势消灭国家,只是国家与资本将处于互惠关系之中。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难道不会对国家的某些主权产生影响,从而削弱主权国家的某些权力吗?这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设置的一个意识形态陷阱。这些被削弱的权力交给谁呢?交给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警察自居,它们把自己当成国际社会的代名词,对不符合它们意愿的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成了世界的恶霸。全球经济一体化根本不可能对主权概念提出挑战,即使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有超出本国政府控制的可能,但当它们对国家主权产生威胁时,一国政府还是有能力控制它们的,所以这些活动没有对国家主权概念提出挑战。(注:如马来西亚对进出资金的管制。)所谓民族—国家已开始过时,民族主义成了世界的威胁不过是西方国家捏造出来的谎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恰好是在地理大发现,即全球化开端以后,即使我们不能说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全球化完全可以和民族—国家并行不悖。
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对自身的意识,是民族存在的客观反映。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其霸权主义,就要对这样的意识进行瓦解和消灭,所以,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入侵和反入侵。
不同文化在空间上的接触和交流,其结果总会使原有文化产生一些变化。但西方国家却有着深深的文化优越感,它们对于异质文化采取了连根拔起的态度,企图在全世界实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化。他们的主要策略就是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各种文化的在空间频繁接触这个现象,为它们的文化侵略寻找借口。它们鼓吹所谓的“普遍的价值观”和全球文化,声称民族意识已经不合时宜。文化是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它要比国家更有生命力。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仅仅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比以往频繁这个现象,对于这样的不同文化的接触,正确的态度应是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怎么能够轻易断言“普遍的价值观”和全球文化的存在呢?应该看到,这种说法有极大的迷惑性。它似乎不象过去西方列强在文化观上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论调,而是用全球文化、普遍的价值观这样一些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说辞,但本质是一样的。西方国家毫不掩饰地说,这种所谓的全球文化便是西方的文化,而其它的民族文化都将溶入到西方文化中。他们正利用经济上优势地位以及文化上暂时的优势地位进行这样的文化侵略。教皇保罗二世11月在印度召开的亚洲主教会议上宣称:下一世纪天主教的重点在亚洲。目地就是要用西方基督教文化征服整个亚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所谓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大敌,不过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撒的弥天大谎。其目地是要消除其它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而乖乖地听它们摆布,因为这些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削弱它们自己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文化,相反,它们正拼命把它们的国家意志和文化、社会模式强加给世界。
全球化的概念在九十年代被正式提出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上面所说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冷战结束的原因。冷战时期,虽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但意识形态的对立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使西方国家觉得,他们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征服整个世界,从而将世界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已经到了。九十年代初,美国所鼓吹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都是这方面企图的体现。但他们很快意识到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在世界各地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对实现他们的企图造成了威胁。他们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围绕着全球化概念,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不顾民族国家存在的客观事实,打着批判“民族主义”的旗号,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以达到他们称霸世界,从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的目地。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方面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同时又公开主张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非西方文明采取敌视和围剿的态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四
围绕着全球化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其本质就是西方国家企图将它们的民族利益凌驾于其它国家民族之上,这不仅为人类已走过的全球化过程所证实,而且也为西方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各项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所证实。所以,全球化下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是两种意识形态为了证明自身模式的正确,或者说,为了证明自身关于全球化模式的正确而展开的斗争。冷战结束后,围绕着全球化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少数国家企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控制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的霸主,从而为自己攫取最大的经济、政治利益。绝不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力图在这个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以,全球化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之争。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斗争;而全球化下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南北之间,即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间的斗争。冷战结束后,西方列强企图继续这500年不公正的全球化过程,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一个更公正、平等的交流对话环境,从而避免弱肉强食那悲惨一幕的重演。
五
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客观的进程混同于主观的意愿。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不落入西方国家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要把它们严格区分。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客观进程,在这样的世界洪流面前,中国不能置身之外,应该积极地参加到这个进程中,同时在这个进程中趋利避害,为自己争得最大的民族利益。对待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和文化交流问题,我们也应该把因经济全球化而导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区分开来。同时,我们也要把仅具可能性的世界政府和全球文化,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没有恰当的区分,把它们混为一谈,就容易陷入要么全部拒绝,要么全盘接受的两极,既不利于我国的发展壮大,也不利于我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德里达新近指出,全球资本主义和传媒大一统的“新国际”是用前所未有的战争手段来谋取世界霸权。霸权与暴政的根淅并不在于强大的军事或邪恶的政治制度,而是始于言语。(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载《现代哲学》1999年.2)这种“言语”就是意识形态渗透。我们不仅要积极地投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且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化理论,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全球化问题是切关我们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我们应该让国民知晓这个问题,尤其是针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增强广大国民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意识形态的警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