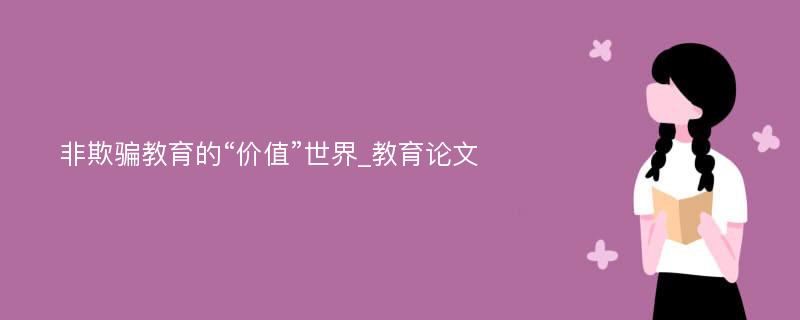
解蔽教育的“价值”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8)09-0011-04
一、教育的原点追问:人为什么需要价值规范
教育学是迷恋人的“成长”的学问,教育是教人“成人”的实践。《荀子·劝学》中释曰:“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静),能定然后能应(应变)。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依笔者看来,“定”是用以反映个体面诸于己的“自在”状态,而“应”则用以反映个体对诸于外的“自为”境界。而“定”(自在)与“应”(自为)又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自在的定,个体的自为无以找到内在发起的根基;没有自为的应,个体的自在无以彰显其生命的本性实在。故此,教育所追求的“成人”实践,就是要把人送达“能定能应”或“自在自为”的道德或伦理境界。
那么,什么是道德或伦理呢?如果伦理学是一套人们借以进行选择和行动的价值规范,那么,要确定、判断或接受任何特定伦理规范体系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为什么需要一套价值规范?换言之,教育学所遭遇的伦理问题,首先不应当是“接受何种特定的价值规范”而是“人类是否真的需要价值?”或者说,人类对于“善”和“恶”的价值概念是否可以任意创造而无需由此引申或者确证什么:我们究竟是基于事物本性实在来行动,还是必须按照一定的准则和规范来行动呢?伦理学究竟是个人主观奢侈的情感幻想关系呢,还是一种客观必须的理智的领域?显然,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尚未有一个哲学家对这一前提性问题做出一种理性的、客观的论证和科学的回答。亚氏的伦理学基于观察试图回答:高贵者和智者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却仍未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选择这样的行动?如果说“善”是超越任何社会伦理学的规范之上的源泉、基础和标准,那么,“善”又如何成为被社会所选择和声称的福祉呢?这种循环论证无异于说“善的标准是对社会的善”,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恐怕没有人能够确证“善”的价值是什么,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价值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回到人类的特殊性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具体而言,无生命物的“自在”是无条件的,它只能改变其存在形式,却不能停止或者消灭其存在;而有生命体的“自在”则面临着不断的选择,因为生命本身首先就意味着自我保存和自我创造的“自为”过程,否则它就亡化为无生命的化学元素存在了,而其生命却无以“自在”(即被异化)了。于是,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是其目的本身,而不是其他目的或他人利益的手段,正如生命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一样。而价值和德性成为人借以保持自尊和选择理性的终极手段,而此时,“幸福是个人达到自我价值的意识状态”[1],而这种幸福源自生命目的和价值生存的需要,而由选择所确认的价值有可能成为一种人们借以进行选择和行动的价值规范或道德规范,毋宁说是实践的内在规定或逻辑。
进一步而言,人对于价值的需要究竟又是如何成为个体对于“善”、“恶”规范的需要呢?半个多世纪前,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2] 教育系师生的这种尴尬遭遇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考的路向:价值规范或者道德规范为何“值得”个体的内化与外化?这不仅是教育系师生的尊严所在,也是教育学的生命根基所在一教育不是在孤岛上或闭室里进行的,也无法去除人所寄居的文化家园赢得“秩序”。换言之,作为多元个体(同质异态群体)中的独特价值的人,其价值的行使(选择和行动)决定着他生命的目的和进程。
二、教育的个体盲域:价值规范何以转化为科学实践
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所言,“教育学不仅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种技能”,“教育学是某种介于教育技能和教育科学之间的事物”,“教育学是教育理论之总和”[3]。那么,教育学何以成为介于教育技能和教育科学之间的“桥梁”呢?教育学又何以成为教育理论的“上属”呢?对此,涂尔干明确地区分了“教育”(education),“教育学”(pedagogie)和“教育科学”(lasciences de l'education),认为教育是一种“行动”或“实践”,而教育学和教育科学是以教育为主题的“理论”[4]。这样看来,教育学在经历了“科学”(正题)与“技能”(反题)的对决之后,走向“合题”一教育学作为沟通教育技能和教育科学的“桥梁”,要求探寻指导教育实践规则的教育技能(策略)与追求符合教育事实规律的教育科学(知识)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而教育学自身肩负着两种资源之间能量转化的使命。这种双向贯通的教育学不仅意味着“教育理论之总和”,同时也意味着“教育技能之总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总和”不等于说是将两者“混同”或者“混合”,而是通过教育学的“间性”立场使得教育科学和教育技能更好地为成就“教育”服务。惟其如此,教育学才能够将生命个体的价值规范转化为教育的科学实践:它不仅是教育学学者把教育实践向教育理论的转化,它同时意味着教育理论向教育实践的转化;而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正是通过教育学这一中介才达成彼此间的“对话”、“理解”与“相遇”。
那么,个体在面临教育世界的多重价值规范时应当如何确证一种合己的价值规范呢?换言之,个体如何让自身的行动,从充满了可能陷阱的教育价值域中恰当地运用符号解构和迅速重建其一种合己的“产生式”呢?显然,这一恰当的合己行为不能够建构在纯粹的“假设”之上,而必须首先退回到生命体的“自在”原点上来问诊自身的价值取向,而在确诊的“自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自为”性的实践逻辑建构。《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笔者按:由诚而明,得之天性;由明而诚,学而知之,得之于教。)教育学“成人”使命的坚守,不在乎学习者已经被导人于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而对这此行为的正确性却毫无理解的“道德训练”,而在于学习者能够理解道德原则,并执著于此,所以能够依据这些原则来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向的“道德教育”。这就是说,价值规范要真正转化为“教育”影响力,它必须被个体转化为其所理解并据以思考其行为的原则,换言之,成就“教育”的关键并不在于把某种价值规范从外在“植入”个体,而在于个体从内在理解和接纳它成为其“自为”品质。否则,那种所谓的道德不是停留于“训练”就是外在于“模式”,而不能够被有生命的个体所理解和据以思考其行为方向。这也正是古今中外教育学史上讨论最多的教育的“内在目的”问题。事实上,不论是教育者还是学习者,他们都是不断追求并展示其生命“自在—自为”性的个体,都是不断地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满,他们通过“自在”的思想与“自为”的行动,不断地实践着生命的创造性存在,而在教育的场域中他们需要尊重彼此的生命“自在—自为”本性,这就要求个体在“成己”的同时还须有所“克己”。诚如王守仁在其《传习录上》中所言:“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张载则在其《经学理窟》中释曰:“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那么,王守仁的“克己—成己”和张载的“合内外、平物我”在人的价值实践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王国维在康德把人的能力分为“纯粹理性”(即“理论理性”,指向物质现象领域的知识力)、“实践理性”(指向道德实践的意志力)和“判断力”(指向审美情感的感受力)的基础上认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种: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5] 事实上,当今的学校教育多数只是为了“为己”、“成己”的生(educating for his life),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合内外—平物我”的教育(educating in everyday life)。笔者认为,工业社会要将真善美“三德”的教育理想实现,首先必须使得每一生命个体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即,洞识“自在—自为”的生命本性和教育使命,把价值规范转化为个体科学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是时,即为“学习社会”的成就日。
三、价值澄清:教育实践的“解蔽”潜则
关于对于生命个体本性的洞识,荀子早就在其《解蔽》篇中揭示了人们认知上的“蔽塞”问题:“故(何)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好恶不同)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思想方法的共同弊病)。……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焉(把一切事物摊开而以道衡量之),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何谓衡?曰:道。”[7] 老子在其《道德经》中也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天之道,损有徐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徐以奉天下?惟有道者。”[8] 可见,教育之道既不在乎纯粹奉天下的“道”也不在于其所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或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而是个体在对“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事实尊重的前提下,要求个体的“成人”实践经由一种“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的价值规范上的衡量。那么,教育实践的价值规范的衡量究竟经由何道呢?
笔者以为,既然“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9],那么,我们对于“成人”理想的追求,既不能像“实用主义”那样一味地强调教育者所施的教育措施的效能和实绩表现的有无,也不能像“功利主义”那样一味地强调外在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差额大小,而是要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人的改变,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活动,文化世界的本体就是人的自为的生命存在”[10]。我们应当把教育学场域中的文化生态建设当作教育的使命,我们应当把个体生命在教育文化之中的寄居式互动所生成的体验与成就当作教育的生命,我们应当把个体的人的自为的生命存在当作教育文化的活的本质和存在形式。这是笔者所理解的教育之道。循此推演,教育学的科学与技能的坚持必然走向个体的实践的价值秩序追寻:这一实践逻辑如何在教育文化生态之中得以显露?个体又何以把握这种实践逻辑来借以思考自身的实践方向?董仲舒在《深查名号》中所揭示的个体之间的道德价值真义曰:“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也就是说,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与人之间如果相同则求在理路上的通达,而若要有所行动则务求互利,而如要有所授受则要顺其性质。对于这种合道德的教育,朱熹在其《答顾东桥书》言:“其教之大端……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语出《古文尚书·大禹漠》)”即说,人若是体会到这种微妙的和惟一合己的道德准则之理,就会使自己的行动和措施合乎中庸的要求。而这种“中庸”既是柏拉图理性灵魂界分中被称为“正义”的用以保持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的恰当比例的“至高无上的善”,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期望的合于美德的“最好的生活”[11]。
进一步而言,教育实践层面上的解蔽,有待于教育中人对教育的内在价值以及作为有生命之人在这一共同价值愿景中各自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规范进行澄清,这种价值上的澄清将直接决定着教育之道的尊重与遵循,并最大程度地影响到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效度。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教育在现当代社会变迁和知识转型的过程中长久未能得到澄清,致使中国教育学的争论一直滞留在外围的模式和形式范畴的认识论领域不能自拔,而要真正迎来中国原创的本土的教育学的新生,必须命中教育学的价值命题进行有深度的解蔽并在这种解蔽中澄清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实践逻辑,使得教育学的成长真正成为教育科学和教育技能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成就所由。
四、逻辑超越:中国原创教育学的当代出路
教育实践独特的对象性和时代性决定了教育学研究的生态面貌,决定着教育文化富有人文底蕴的交际气质,同时决定着教育变革的生理结构。大海对贝壳的定义或许是珍珠,时间对煤炭的定义或许是钻石;教育对个体的定义或许是命运,成长对生命的定义或许是自然。回望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教育遗产,我们常想自问:历史的教育传统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的发展意味着财富还是包袱?它实际地发挥了、发挥着和应发挥怎样的一种作用?我们不能撇开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不能撇开以宗法制为本位的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不能撇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德治、仁政、礼教统治思想和文教方针以及忠恕、中庸、中和等特有的思维认知方式来思考传统教育;我们同样不能撇开它们来思考中国现当代的教育使命,我们也不能撇开中国现当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征来思考当代教育使命与传统的内在联系,我们更不能在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地去做一时一地的断代定点的教育实验和实践。这是我们对于原创教育学的期待与呼唤的“飞白”之际,这是我们对于逻辑超越的教育学生成方式的“失重”之根。正是在这种一样上,教育通过创造人的文化创造了人,而人在教育文化中所获得的价值“在训练儿童的过程的不断应用之中,一直承担着对实践的普遍修正”[12]。
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有生命价值的人无法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教育世界分割开来,因为“教育”或者“受教育”在价值或者意义的生成中发生,而个体的成长在价值或意义的交往中进行,面对教育世界,人“‘在世界中’来‘看’这个‘世界’,世界就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交往’的一个‘环节’。”事实上,正是“人的生活本身提供了人‘认识自己’的这种权利,而不断地打破概念知识所给出的各种‘定义’框框。‘人’的‘意义’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中。‘人’生活在‘世界’之中,自从‘人’‘有’了这个‘世界’之后,‘人’就有了‘意义’,所以‘人’的‘意义’……是从生活、从‘世界’体会领悟出来的”[13]。教育实践就是人与人的交往,就是价值与价值、意义与意义的关联,就是生命在生活世界中的更新与生长,就是个体视界与经验的扩大与丰富,就是人性与个性的丰满与完善。在这一交集中,个体存在对于价值的必然需要促动着教育与学习理解的成就与超越,而对于这种成就与超越的衡量需要实践逻辑的自觉与关联,因为学习与教育的通达与默契所指向的首先就是这种结构范畴的秩序关联,将这种结构关联上升到实践逻辑的层面上意味着个体的价值和意义的融合与交互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运行机制和擅变理路。基于这种机制和理路,个体对于教育的摄取和重建就赢得了一个开放的扩展空间,从而为人的欲动提供了一种富有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经验体系,个体在这种智慧的澄清中变得“勇敢”,生命在这种精神的建构中实现“站立”,而教育在这种逻辑上的接洽中成就“到达”。于是,面对这种逻辑性和历史性的实践逻辑,教育世界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需要不断地解蔽对主体生命业已构成遮蔽的先验标签,从而在不断地重识和重构中进行创造性的教育性交往。
诚如怀特在《街角社会》中所述:我们也许承认任何局外人无法真正充分地了解某一文化,不过,我们接着还应该问一声,是否任何局内人都能充分了解他或她的文化呢?在强调局内人的知识是一个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局外人也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摘掉标签的可能性总是少于贴上标签的可能性,而且在许多时候社会并不情愿为他们摘下标签,是因为谁也不愿意为摘掉标签沾上‘同情恶人’的恶名。于是,许多人始终处于被‘隔离状态’之中,而那些‘标签’和‘烙印’却要伴随他们一生。”[14] 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小学课堂教学中,10%左右的所谓差生被提问次数只及班级平均次数的一半,只及优等生的1/4;教师为了维持课堂活跃气氛,往往将课内80%的问题请约占学生总数20%的思维灵活者来回答,约有30%的学生没有被提问机会[15]。这样课堂教育中就发生了学生在教师眼中的“显在”和“潜在”差别,恰如书法笔画中的“飞白”现象。而这种教育实践上的“飞白”既是事实性的(实然也是表达性的应然):说它是事实性的,因为它是对教育内在生成关系的直观揭示,而不是笔者的主观臆造;说它是表达性的,是因为主体交往的表达(肢体的、言语的或者气质的)注定要“遮蔽”部分处于“盲点”里的学生,问题的关键是主体(即包括教育者也包括学习者)要有这种“自在”之态的有所自觉,从而引发为了教育具体达成的双向“解蔽”——去除“随大流”意识而真实地从群体的遮蔽中敞露个体的独特,真正地去体验和欣赏遭遇到的每一个对象人的实践逻辑,不去占有和钳制它,而是在实践逻辑的尊重与欣赏中各自“像罗各斯说话一样说话……通过对它的反应,通过成为它的回声(echoes)和真的对等陈述(counterstatement),与罗各斯保持一致”[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