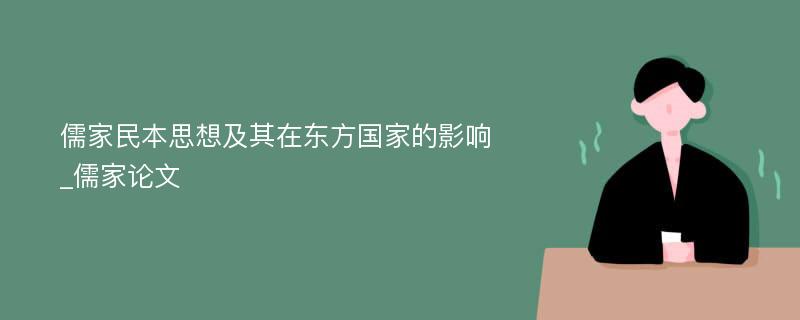
古典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在东方国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民本论文,古典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方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愈来愈重要。90年代被喻为“亚洲时代”[1]。“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亚洲在崛起”[2]。世界银行宣布:“东亚的发展经历是一个经济奇迹”[3]。中国“已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中心”[4]。“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5]。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背景”[6],即所谓的“亚洲价值观”,[7]或亚洲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本文并非意在探讨整个亚洲的传统“价值”,而只想就与“亚洲法律价值观”和“亚洲法律文化”有关的“古典儒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在东方国家的影响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古典儒家的民本思想
这里的古典儒家,主要指孔孟儒家。孔孟是否有“民本思想”,这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分歧源于对《孟子·尽心上》中的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民贵君轻”说[8],是孟轲对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高度发展”[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就是“民本”思想[10]。上述两种观点,一种主张“民贵”,一种主张“民本”。“贵”和“本”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贵”表明“贵重”、“重要”、“本”则有“根本”之意,也即是说,主张“民贵”观点者认为孟子主张“民是重要的”,而主张“民本”观点者则认为孟子主张“民是根本”或“民是最重要的”。
其实,对于孟子“民本”思想,其提出者也许应当首推朱熹,他在其《四书集注》中为上述孟子那句话作注时讲:“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应坛遗以视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11]可见,朱熹就已认为孟子上述那句话中包含民本思想。再看看孟子本人的论述,在前引的那句话后孟子紧接着继续讲:“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神稷,则变置。”[12]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得到百姓的欢心便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欢心便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欢心便可做大夫。诸侯危害国家,那就改立一位贤君。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孟子以为,诸侯比大夫重要,天子比诸侯重要,百姓则比天子还重要。在大夫、诸侯、天子、百姓这几类人物之中,“民”即百姓是最重要的,因而,它是“根本”。再结合孔孟在其它地方的论述,[13]应该说孔孟是有民本思想的。
孔孟对民本思想的阐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孔孟对“民”的“关注”、“重视”,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德”和“贤”的要求。如上所述,孟子主张,得到百姓的欢心便可以做天子。而天子怎样才能得到百姓的欢心呢?答案是:做天子的唯有达到“德”和“贤”的标准才能得到百姓的欢心。所以,孔孟对民本思想的阐述表现“上”和“下”两个方面:对“下”,表现在对“民”的看法上,对“上”,表现在对统治者的要求上。
孔孟对“民”的重视表现在,从孔子到孟子均主张,以平民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以惠民的社会政治作为最高目的。它在孔子那里还只是很温和、很模糊地表现于“民无信不立”这样的命题中,例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4]
而在孟子那里,则不仅鲜明地表现于民贵君轻、坏君可废等相当大胆的主张中,而且还激烈表现在“闻诛一夫纣”等颇有抗逆意味的看法中。[15]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6]
很显然,孟子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那么,怎样才能赢得民心呢?根据孔孟的逻辑,统治者必须实行“德治”、“仁政”。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对下应慎刑罚,薄赋敛[17],为政以德,实行“王道”;另一方面,对上来说,统治阶层必须能达到“贤”(有才能)、“德”(品德高尚)这样的标准。所以,在孔孟那里,“德治”、“仁政”和“德化”、“礼教”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通过“教育”、“考试”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到统治阶层中来。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的。孔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实行“德治”,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8]。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重视“德治”。孟子反对无德的旧贵族,而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19]他是先秦“贤人政治”的倡导者,即主张“人存政举,人亡政息”[20],实行“仁政”。否则,即使有“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21]如果“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22]
由此可见,古典孔孟儒家是有“民本”思想的,其“民本”思想的两根支柱:一是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二是主张实行“德治”、“仁政”。
二、孔孟民本思想的涵义
要弄清孔孟民本思想的涵义,我们觉得必须弄清下面两个问题:一是“民本”与西方“民主”的关系,另一是“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已有许多论述。不少人认为孔孟有民主思想,意即民本思想就是民主思想。胡适认为近代的正统思想“没有把握住古典儒家的民主精神”[23]。孙中山说:“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和舜的话,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世袭所有。虽然他们的政府名义上是君主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制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24]美国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孔子的民主思想及其对西方的影响。[25]韩国金大中认为,民主思想其实是亚洲文化的要旨。“早于洛克2000年,中国哲学家孟子就已提出类似观点。倘若君王举措失当,百姓有权替天行道,起而推翻之……中国古老的‘民本政治’宣扬‘民意即天意’,一个人必须‘尊民如天’……没有任何思想比孔子、佛教和韩国的东学教思想更合乎民主真谛的了。显然,亚洲的民主思想正如西方的一般深厚……儒家学者以进谏昏君为天职”。[26]
当然,也有许多人反对这种主张。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差异,正包含着“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的思想岐异。认为“为民作主”属中古民本思想,其政治背景是专制的;“由民作主”属近代平民意识,其政治背景是民主的。[27]
事实上,尽管孔孟提倡爱民、重民、以民为本,提倡贤人政治、仁政、德治,认为百姓在君王举措失当时可以替天行道,但其民本思想也不可以等同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我们认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孔孟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认真论证过作为统治者的权力的来源问题或者说权力的产生方式问题,而这正是每个民主主义者所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他们也提到百姓在某些时候可以替天行道,但这并不是一种理性化的权力产生方式,就好象后来中国历代统治王朝末期都会有一些人替天行道推翻一个王朝的统治,但接下来他们建立的王朝却并非民主的制度一样。所以,孔孟的民本思想还是与民主思想有原则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包含着“为民作主”的涵义,后者则是“由民作主”的思想。
另一问题是“民本”与“人本”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差异的。在中国古代,“民”是一个集合概念。这种概念的特征是,把同类对象集合为群作为一个整体来反映。它只适用于该整体,不适用于构成该整体的个体。[28]而在西方,“人本”中的“人”首先表示的是单个的个体,然后才从每个个体中抽象出“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更象马克思所讲的作为人的本质的那个“人”的概念,即“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9]要理解“民”,首先得理解构成它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古代,“民”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家”。有人认为,在儒家学说中,父亲的地位优于统治者,家的地位优于国。[30]《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一只羊,而这个人的儿子非常正直,因而向官府告发了他父亲偷别人的羊这件事。对此,孔子评论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31]说明孔子认为与国相比,家的地位更重要。新加坡的李光耀认为:“西方国家与东亚国家对于社会和政府有个基本的观念岐异……也就是说,东方人认为,个人是家庭中的一员”。[32]有人甚至把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改为“家庭、社稷至上,个人次之”。[33]《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福山指出:“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绝非表现在政治方面,而表现在浓厚的家庭主义上,家庭观念超越一切,包括与政权的关系。也就是说,儒家是由下而上建立了秩序井然的社会,而非由上而下,家庭的道德责任成为社会的基石,甚至超过对当权者的义务”。[34]
在儒家思想中,家或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体的价值只能通过家来体现。生儿育女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家或家族的繁荣和延续。“孝”是维护家族秩序的最主要的行为准则,是“德”的根本。[35]国家成为国君之“一家天下”。在这个社会中,由子孝、妇从、父慈观念和规范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推广到社会之中变成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组织原理,官僚成了“父母官”,君主成了“最高家长”。
因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的“人本”思想。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的“民”首先是指由个体构成的集团,是“家民”而非“公民”,而“人本”思想中的“人”则是指人类的个体。
三、民本思想对东方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整个儒家思想对东方各国特别是对典型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越南等)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当然,作为儒家思想之一部分的民本思想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更是丝毫不能否认的。
首先是“家庭”观念的影响。“家庭是亚洲社会的基石。无论在社会、经济或情感方面,家庭——而非政府——成为个人与整个家族本身的支柱。即使所说的自力更生或个人责任,也都是在家庭的范围内孕育的”[36]。李光耀认为,东西方的差异在于:“东方社会认为个人是家庭的成员……至于西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民认为政府的强大足以承担许多义务,而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这些义务往往是由家庭承担的”[37]。“西方对于现代化的典型观点主要是围绕民权、言论自由与民主展开的,但现在这些观点已受到亚洲的挑战。亚洲人把家庭放到第一位,并期望创造平等、和谐、公正的发展环境”[38]。韩国人典型的集团主义意识就表现为家族本位主义。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也是联结个体和社会的主要纽带。家的稳定和有序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有序[39]。在韩国,“集团的创业史便是家族的发家史。董事长即家长”[40]。在日本,集团是家族的延伸。其表现之一是村落社会中集团组织的多样化。同族集团和各种组织纵横交织。……其表现之二是个人生活的集团化。……其表现之三是行动的一致化。个人从属于集团,集团的意志往往决定个人的意志。……在家族和集团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人们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并严格按此行事”[41]。“以忠孝为中心的家族主义集团意识更是(日本)国民凝聚力的一个核心”[42]。
与这种家庭和家族主义意识相联系,东方国家很少有个人的“主观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民法很不发达,而民法主要是权利法。所以,在中国古代法律中,规定义务的东西多,而规定权利的东西少。“日本的等级制度并无主观权利的概念”[43]。日本人厌恶主观权利的概念,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是感情而不是理性”[44]。在日本,“除不具人性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外,没有人会为了行使法典规定的权利而诉之于法院。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自愿而又乐意地履行约定的义务以免使债权人陷于为难的处境,意外事故的受害者宁愿自认倒霉而自发地放弃行使权利”[45]。其它东方国家也大致相同。不重视个人的“主观权利”是与家庭和家族主义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后者存在的情况下,个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而也不能要求什么权利。所以说不重视个人的“主观权利”也是民本思想影响的表现之一。
与儒家民本思想所要求的“贤人政治”、“仁政”、“德治”相联系,东方国家强调最高领导层的才能和品德的重要性。新加坡的“精英主义”、“专家治国”即是最典型的表现[46]。这是新加坡领导人所推崇和奉行的一条治国路线。精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为政在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治国者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并且又能网罗天下英才为国家所用,那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能兴盛繁荣。这部分精英必须既才华出众,又品德高尚。中国的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也是民本思想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其它东方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与上述情况相联系,民本思想在东方国家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教育的重视。很显然,教育是选拔第一流人才的最重要的途径。在中国古代,通过教育并进行科举考试是中国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非常重要的途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近代,孙中山创立五权宪法,设立考试院专门负责教育与考试。孙中山认为,他建立这一制度的基础是孔子打下的,因为他一再主张“举直”和把政府机构交给有德有才者手中的必要性。他主张,这种人,通过适宜的教育而具有了必备的治国责任心,应被挑选到政府官位上,并且除了品格和能力外不论其它条件[47]。现代东方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如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主要是通过建立精英主义教育体制来培养人才[48]。在日本,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49]。在韩国,其人口为4100万,每年却有30万名学生进入大学,这是韩国经济腾飞的秘诀之一[50]。
除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之外,民本思想还推崇廉政,所以,东方国家着力推行其廉政政策。廉政是民本思想的必然逻辑。原始儒家对此已有许多论述,如:“见小利则大事不成”[51];君子谋道不谋财,“放于利而行,多怨”[52];不与民争利,财聚则民散;节用爱人等。廉政思想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影响,在新加坡和韩国比较突出。新加坡政府为了保证为政廉洁,除制定了一套缜密严厉的条例外,还设有一独立的强有力的治贪机构——贪污调查局。它直属总理办公室,局长由总统任命,向总统负责。这个局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构,权重效高,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者职位多高,调查局也无所顾忌。韩国金泳三认为,“要想发财,就应当去做商人,而不是当官”[53]。1993年2月他就任总统后,为了有效惩治腐败,采取了严肃纲纪法规、公布官员财产和金融实名制等廉政措施,“廉政风暴”横扫韩国社会各层面,受到国民赞扬。
民本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影响,表现在东方国家实行的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1955年,新加坡设立中央公积金制度[54],其初衷是为就业者建立一笔养老储蓄金,但是经过近40年的发展,它已成为可提供养老、购房、医疗保健、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我国推出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也与公积金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民本思想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东方国家对民心向背的重视。对此,毛泽东有过许多论述。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思想,其中有一条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据介绍,《中国日报》在宣传新加坡出版《邓小平文选》时论述到,在“制定各项目标与政策时,出发点和目的都在于人民是否支持,是否乐意,是否点头同意这些目标与政策”[55]。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日本、韩国等通过教育选拔高级优秀人才的作法,以及推行的其他各项政策,都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可见,人民支持与否是东方国家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标准,也是立法的基本原则。
总之,民本思想在东方国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强烈的家庭、家族及集团主义意识,不重视个人的“主观权利”;重视领导者的“德”和“才”;重视通过教育选拔人才;推行廉政建设;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关注民心向背等等,这些都是古典儒家民本思想对东方国家的重要影响。研究古典儒家民本思想及其在东方国家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这些国家的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的特点是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如将法律视作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现象,那就应该了解它萌生的特定民族灵魂深处并在那些经过长期发展而孕育成长的历史过程。[56]
注释:
[1][2][3]〔美〕约翰·奈斯比特著 蔚文译:《亚洲大趋势》,外文、经济日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联合出版,第2页。
[4][5][6][7]同上,第10页,第7页,第40页,第48页。
[8]见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03页;张国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74页。
[9]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第103页。
[10]赵士林著:《心学与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0~111页。
[11]〔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1版,第525页。
[12]《孟子·尽心下》。
[13]见《论语·宪问》、《论语·雍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公孙丑上》等。
[14]《论语·颜渊》。
[15]《孟子·梁惠王下》。
[16]《孟子·离娄上》。
[17]张国华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第51页。
[18]《论语·为政》。
[19]《孟子·公孙丑上》。
[20]《礼记·中庸》。
[21]《孟子·离娄上》。
[22]同上注[21]。
[23][24][25]转引自〔美〕顾立雅著、高专诚译:《孔子与中国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95页、第396页,第十五、十六章。
[26]同注[1],第63页。
[27]同注[10],第142页。
[28]《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43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30]〔美〕D·布迪、C·莫里斯苦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8页。
[31]《论语·子路》。
[32]转引自注[1],第43页。
[33]见注[1],第51页。
[34]转引自注[1],第52页。
[35]赵炜编著:《韩国现代政治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21页。
[36]同注[1],第74页。
[37]转引自注[1],第75页。
[38]同注[1],第252页。
[39]赵炜编著:《韩国现代政治论》第120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亚太资料》1992年第14期,第4页。
[41]同上,第2至3页。
[42]同上,第3页。
[43]〔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03页。
[44]同上,第508页。
[45]同上,第508页。
[46]《亚太资料》,1994年第4期,第1页。
[47]《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98页。
[48]《亚太资料》1994年第4期,第5页。
[49][50]《亚太资料》1992年第14期,第6页,第8页。
[51]《论语·子路》。
[52]《论语·里仁》。
[53]宴真著:《儒家思想与东亚经济现代化》,载《传统与现代化》,第52页。
[54]高兴民、叶宝琳著:《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载《传统与现代化》第57页。
[55]转引自注[1],第63页。
[56]〔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等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66页、258页。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孔子论文; 家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