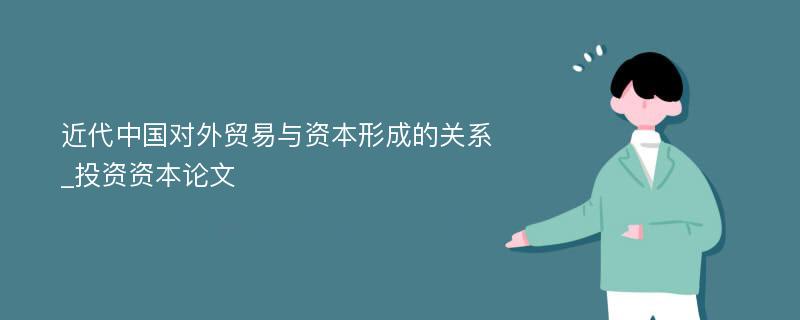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资本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04)01-0115-04
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形成的快慢,往往是经济发展初期促进和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中国近代时期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突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太大[1](PP.291~312),但它却对中国的资本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一、对外贸易行为利得向资本的转化
近代中国早期的资本形成极为困难,民生艰难导致的低储蓄率不足以积累起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基本资本量,富裕的绅士阶层将其剥削所得用于奢华的生活消费,剩余部分则热衷于投资土地以收取地租或拆放高利贷以收取高额利息。但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初始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官办企业)、外资(包括国际资本流动、政府对外借款的即时资本化、外商企业赢利的再投资等)、华侨汇款(除去用于消费的部分)、对外贸易行为利得(同对外贸易直接相联系的国内贸易所获得的利润也包括在内,它有时甚至占整个对外贸易利润的大部分,并主要集中在买办手中)、其它社会资金(来源于地租和高利贷利息而不再继续投资于土地和高利贷的部分)。下面评述一下对外贸易对资本形成的作用。
对外贸易对资本形成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买办收入的资本化。前人关于买办的研究早成荦荦大端,国内的黄逸峰、国外的郝延平都是其代表人物。与本文有关的内容兹举买办收入一项。买办收入到底有多少,因为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为依据,前人根据买办业务量所做的估计有以下几种,详见表1。
表1关于近代买办收入的几种估计(注:作为白银的计价单位“两”,全国各地制衡标准稍微有差异。括号内的数字是本文按1关两=1.114上海两折算的,汪熙的数字另需折算比率为:1元=0.29712美元(1936年币值)、1关两=1.558元。)
估计者 时间(年)买办总收入 来源
黄逸峰 1860~1894 4亿两
《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
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
郝延平 1842~18945.3亿两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1970
河北大学
1840~1894 2.3亿关两(2.56亿上海两)《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严中平 1890~1913 6.2亿关两(6.9亿上海两) 《中国棉纺织史稿》
汪熙
1868~193615.29亿美元(36.8亿上海两)《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
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黄逸平 1840~18944.5亿关两(5亿上海两) 《近代中国经济变迁》
《中资史》 1840~1894
5亿两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资料来源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168、173页;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149页。
上述六种估计的时限除汪熙的估计较长外其他基本相同;买办收入的估计数除河北大学的估计数偏低外,其他四种估计相差不多。我们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估计为准,以1840~1894年买办收入5亿两计,这笔资金的数目确实可观。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相比较,清政府1843年岁入为3700万两,1868年岁入为6100万两[2](P173)。也就是说买办50年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全国近10年的国库收入,足见买办收入数量之巨。
当然,5亿两的买办收入并非全部直接从对外贸易的买办行为中所得,其来源结构如表2。
表21840~1894年买办收入的来源
项目
收入(万关两)占总收入(%)
1.洋行买办薪金 8800
17.6
2.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它收益18400 36.8
3.出口商品货价差额 8400
16.8
4.鸦片贸易收入 9700
19.4
5.外资工厂买办收入 19003.8
6.银行买办收入 600 1.2
7.轮船、保险业买办收入 10002.0
8.经手外债、军火所得收入12002.4
总计
50000 100.0
资料来源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173页。
从表2看,第1~4项和第8项中的经手军火收入毫无疑问都属于对外贸易行为所得,第5~7项和第8项中的经手外债收入并非直接得自于对外贸易活动。但这时期工厂加工业、航运业、银行业、保险业的主要业务是以对外贸易活动为服务对象的,它们随着对外贸易的发生而发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后四项所占的比重也极小,累计不足10%。因此可以把5亿两的买办收入全部视为对外贸易行为利得。
这笔庞大的资金干什么用了呢?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粗疏估计,买办的消费支出大约占到总收入的50~70%,按平均60%计算,亦即有40%的积累率,约合2亿两[2](P175)。对这2亿两资金的去向,则如表3所示。
表31840~1894年买办积累的投资去向
项目
投资额(千两)
占总数(%)
交存外商企业保证金10000050.0
附股于外商企业12000 6.0
投资城市房地产30000 15.0
投资商业、银钱业 53000 26.5
投资近代工业、航运业
5000 2.5
合计 200000100.0
资料来源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181页。
本文认为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甲午战争以前的情况。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工业尚处在发育阶段,第三产业却获得了超前发展,这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上表中买办积累的投资去向中除买办交存外商企业保证金占了一半以外,有1/4是投向商业和金融业领域的。
甲午战争后,尤其是经过维新运动的冲击、清政府“新政”对实业政策的促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外商企业数增加了,对外贸易额增长了,买办人数和买办收入随之增加。仍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所估计,到1920年,买办总人数将近4万人,是甲午战前买办人数的4倍;1895~1920年间,买办总收入估计达到了10亿两以上,比1894年前买办总收入增加一倍[2](P756)。与表1中严中平所估计1890~1913年买办收入为6.9亿上海两相印证,上述数字基本可信。这笔庞大资金若仍按60%用于奢侈消费计算,40%的剩余积累就合4亿两,再加上退休买办在甲午战争前支存外商企业的保证金的返还(或以入股形式与外商合营),尽管这时其转化为投资的具体数字不得其详,但对于近代中国这个资本市场的极端稀缺性而言,这笔资金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它有效地缓解了资本形成的压力。
二、买办资本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
简单地说,买办资本的投资方式有附股于外商企业、与洋务派官僚合办民用企业(即通常所说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最常见的是自营企业。而买办资本的投资领域则广泛涉及工矿、商业、金融、航运、房地产等诸多方面。
附股于外商企业是买办早期的一种重要投资方式。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一些空头的冒险家来到中国(多数集中在上海),他们依持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惯靠吸收华人资金去开办企业,而当时因清政府尚未对国人开弛设厂兴业之禁囿,不少华商为追逐优厚利润,也只有将资本以附股形式投入外资企业。根据汪敬虞先生的估计,在整个19世纪,有华商附股的外资企业共62家,实收资本4000万关两以上,其中有的企业华商附股比例高达60~80%之多。而这其中主要就是买办的投资,在已查实身份的47名华人股东中,洋行买办28人[3](PP.528~529)。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旗昌轮船公司,1862年成立时额定资本100万两中至少有1/3是买办附股的资本[4](PP.29~30)。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买办资本也加入进了官督商办民用工业、矿业和航运业的行列。兹各举一典型列之。例一,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洋务派为了稍分洋商之利并解决清政府财政困难而设立的,最初由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主持,但50万两股本无从着落,彭只好辞职,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接手后,初订募股40万两,但因为郑观应、徐润、唐汝霖、卓培芳等买办的踊跃纳股,很快就募集到了50万两,织布局随得以建成[5](PP.287~292)。例二,开平煤矿的兴建资本总计100万两,徐润投入15万两,其它大部分由唐廷枢、唐茂枝这一对买办兄弟奔走募集,这就是唐氏后人唐绍仪所称的“唐氏家族拥有最大数量的开平股份”[6]。例三,轮船招商局最初由沙船商人朱其昂筹建,但朱募资乏策,李鸿章委请唐廷枢、徐润加入,招徕股金的局面随之顺利,在第1期的100万两股本中,徐润一人干脆认购24万两,唐廷枢10万两,另外还有买办郑观应、陈树棠、刘绍京的投资[7](PP.148~149)。
对于官督商办这种形式,有人认为它具有封建主义胎记的落后性,但它却符合那段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现实。郑观应这番见解或许不无道理。“全恃宫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两弊具去。”[8](P704)
也有的买办资本独自投资于企业。甲午战争后,这条投资渠道逐渐成为主流。在工业领域,如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1888年就开设了源昌缫丝厂。20世纪后,除源昌缫丝厂的50万元外,祝又投资20万元兴设源昌碾米厂,投资20万元兴设华兴面粉厂,投资67万元兴设公益纱厂,投资14万元兴设恰和源机器打包厂,合计191万元。此外,他还在上海龙章造纸厂、苏州振兴电灯厂、扬州振扬电灯厂、无锡源康缫丝厂、无锡惠元面粉厂拥有股本,使其投资总额达到306万元[9(P39)。又如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朱志尧,1897~1910年间投资上海大德油厂21万元,通昌榨油厂13万元,求新船厂69.9万元,申大面粉厂27.9万元,北京利呢革厂60万元,另外加上在同昌纱厂、大达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的股本,投资总额达到365万元[10](PP.164~165)。
在商业领域。商业本是买办的本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能查明身份的买办112名,出身商人的就有75名,占67%[11]。买办资本在早期也最主要是投资于商业,许多买办在洋行任职时差不多都经营着自设的行栈、钱庄、当铺、揽载行等。徐润在宝顺洋行充任买办,除了各种工矿投资外,还先后创设有绍祥字号、润利生茶号、宝沅丝茶土号经营丝茶、鸦片等生意,又开设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烟叶、白蜡、黄白麻和桐油等。胡梅平,沙逊洋行买办,在天津设有鸦片行、糖行及堆栈,在张家口设有羊毛收购站。
也有不少买办出身于钱庄。旧中国的商业领域,历来就与钱庄关系密切,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商业需要钱庄资金的融通,买办自设钱庄既可获信于洋行,又便于向外国银行拆借款项。因此买办资本广泛地投放于金融业领域,敦裕洋行买办严兰卿在上海、苏州就经营了七、八家钱庄。20世纪以来,买办资本不仅大量投资钱庄,更大量投资新式银行,严信厚、朱葆三、叶揆初、虞洽卿、陈光甫等人都为“江浙财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航运业继轮船招商局以后,私人航运也逐渐发展。著名的荷兰银行买办虞洽卿除了倡设四明储蓄银行、三北机器厂外,还经营着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以及仓库码头的储蓄、装运业等。
洋行往往与租界相联系,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投机有其得天独厚之便利,买办遂厕身其间相谋其利。立兴洋行和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刘人祥,在汉口租界外收买大片土地,使沼泽之地“整理为繁盛之街地,用致巨万之富”[12](P962)。徐润在房地产方面下的赌注更大,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他在上海广置房产,遍及外滩四马路直至十六铺一带,造架房屋3800余间,每月收租2万余两;另外置地3000多亩,共合成本223万两,到1883年,他的地产估值1500多万两,增值7倍[2](P178)。笼统估计,20世纪以前,全国用于房地产的投资约4000万元,合3000万两白银[2](P178)。
从1920年开始,随着买办制度的革新,买办势力逐渐衰弱了。但这时,买办资本作为民族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买办收入作为对外贸易行为利得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前期资本形成阶段的使命,从此以后,日益增大的国有和民营的现代金融势力开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担纲起中国经济发展资本形成的首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