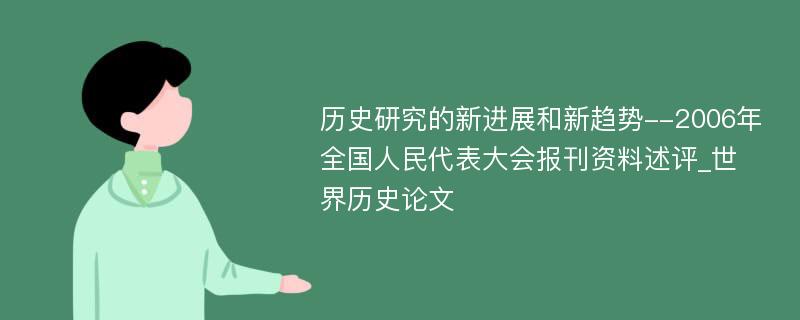
历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动向——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历史学论文,报刊论文,新进展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以下简称《历史学》)是一个反映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动向、提供史学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2006年,《历史学》共全文转载各类论文146篇(含7组笔谈和专题讨论)。这些论文分别被编入“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史研究”、“学术史”、“专史研究”、“比较研究”、“文献学研究”、“史学家研究”、“访谈录”、“史学动态”、“考古学动态”、“史学动态”等栏目之中。如果加上“史学百家”栏目中的论文摘要,有将近230篇的容量。从这些论文来看,在过去一年中,史学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进展和新动向值得关注:
一、坚持唯物史观,批评历史虚无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在实践中逐渐确立起来,这种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但一个时期以来,有些研究者在认识上对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产生怀疑,在实践上则漠视、轻视唯物史观,甚至对唯物史观进行超越理性的批判。这“不仅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的否定上,而且表现在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和对中国近代当代历史的肆意丑化、歪曲、颠倒上。”①这种情况使得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唯物史观要不要坚持,怎样才能坚持好,成为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史学界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看法。
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一般认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性理论进行运用,是一代中国人的自觉的理性选择,并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制性要求的结果,这种选择既因文化整合机制而起作用,也因社会需求机制而发生作用。”②因此,坚持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是一个基本原则,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当前形势下坚持好、发展好唯物史观,推动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对此,有研究者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继承和发展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③。有研究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条件下,要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④。有研究者指出了在《史学概论》教材中贯彻唯物史观、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⑤。有研究者从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素养的角度,认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史学工作者加强自己素养的必然途径”⑥。这样的看法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胪列。还有一些研究者针对那些认为唯物史观存在理论缺陷的看法,着力于从基本理论和重大问题上去发掘、阐释、丰富唯物史观的内涵。如有研究者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等理论问题的由来、发展和意义⑦。有研究者对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道路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思考,分析了马克思本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并对后人的误解进行了辨析⑧。还有研究者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时代条件、思想渊源、历史理论、某些流派和代表人物,丰富了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⑨。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具体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歪曲”,推动中国史学和唯物史观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史学界自觉承担的时代任务。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表现,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就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田居俭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了一个总体概括:“这种倾向,从形式上看有虚有实,虚是理论拼凑,实是历史解读;从内容上看有整有零,整是总体否定,零是分体曲解。”他认为以“中国文明西来说”来否定中华民族的起源和中国历史的独立性,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⑩。黄凯峰则指出,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需要注意:一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二是以“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为代表的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三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而贯穿这三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观点,一是片面强调历史认识和著述的主体性,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将历史直接归结为文本和叙事;二是否认历史有所谓的规律,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三是否定历史的连续性,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以分割的片断,并对片断作出符合自己当下需要的评价。同时,各种不同层次的虚无主义还否认历史的实践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历史教育领域。对于各种各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思想根源,作者甚至把它提到了“与和平演变交相作用、相互裹挟”的高度,认为在批评、纠正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历史教育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性,改进和提高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11)。
当然,批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是为正常的学术争鸣设限。相反,正常的学术争鸣是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是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的。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应当给予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有些分歧则应允许其长期存在。即便是有些错误的观点,也应当通过学术而非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文革史学”的悲剧不能重演。对此,史学界也是有共识的。
二、加强史学交流,注重比较研究,中国史学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无论在范围、层次,还是在密度、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史学正在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而如何使中国史学更好地了解世界并为世界所了解,也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前提就是要提高自身的品格。在当前来说,要提高中国史学的品格,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二是要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遗产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三是必须认真地对待和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建立了这样的前提,还必须明确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路径。他提出的路径包括:一要推进中外史家的对话;二要加强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要提高对比较研究的认识,不断摸索和总结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作者还提出了几种比较研究的模式);三是要促进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走出”国门,切实改变中外史学交流中的不对称现象,而这需要从筹划、遴选、出版等各个方面进行操作,也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12)。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所作的一个总纲性思考,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者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行动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外国史学有益成果的借鉴与中外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
在借鉴外国史学成果方面,有对外国史学发展趋向的介绍和研究,如《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13);有对外国著名史家的研究,如《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14)、《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15)等;有对外国历史观念的研究,如《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16);有对外国史学不同学派和思潮的研究,如《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17);有外国史家对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如《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18)、《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19);有对外国历史专门领域的研究,如《西方思想史研究笔谈》(20);还有研究者提出要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21),反映出中外史学交流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总结与进一步提升的程度。而2006年8月20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对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一次深刻反思。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方法,使用的范围当然不限于中外历史和史学的比较,有些研究者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提出比较问题的。瞿林东对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作了初步梳理,首次提出了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这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创见,有利于比较对象和主题的系统与分类,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的具体与深入。他还对中国古代史家运用比较方法总结历史经验、评价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编撰和史学批评等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古代史家在比较研究方面的认识和方法(22)。马克垚、庞卓恒都是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和实践的名家,对他们的历史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既是经验的总结,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23)。当然,随着中外史学交流的加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逐渐成为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有研究者指出,文明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国际史学研究的新潮之一(24)。而国内学者关于中外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既有宏观的,如关于中西古代文明问题的比较研究(25),也有具体的,如关于中西封建专制政治的差异(26),还有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的总结(27)。2005年10月25日至27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了“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从理论与方法上对比较研究作了一次总结。这些情况说明,中外历史和史学的比较研究正方兴未艾,向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迅猛挺进。而这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中外史学交流一直存在着“输入”多而“输出”少的不对称现象。可喜的是,中国史学名著正在加快“走出国门”的步伐。《新五代史》出版英文版就是一个代表。戴仁柱在《新五代史英文版序言》中对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的背景,欧阳修的“春秋笔法”和批判精神,《新五代史》在内容、方法和评论等方面的特点,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这是一个值得充分肯定的努力方向(28)。
三、全球化、全球史和环境史学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加速,全球化、全球史和环境史学日益成为中外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分别在奥斯陆和悉尼举行的第19、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化、全球史及相关问题列为大会的主题之一(29),反映出国际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国内学者也开始探讨全球化给中国史学带来的机遇和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对全球史的追求,首先使得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发生了转变,即由以前的“民族”或“国家”转变为“全球”。其次,追求全球史使史家们尤其是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调越来越不满,即便是一些西方史家也开始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比较深刻的反思,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思想和实践越来越丰富,中国史家如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都有突出的贡献。
但是,理想化的全球史能够达到吗?目前来说,可能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全球史是一个历史范畴,有着具体的社会内容,它受着全球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些人简单地将“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这是有问题的(30)。事实证明,明确全球史观是认识全球历史的一种新的“方法”,而不是以西方主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念,是完全必要的。从这样一种方法出发,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会作出不同的历史价值判断,形成不同的全球史观。也就是说,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也不应当、不可能中断每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我们应当努力构建的全球史,是属于中国史学的全球史,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31)。
在全球史的主题关照下,国际史学界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关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史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由生态史研究拓展到环境史研究,反映出人们开始突破只注重自然环境研究的局限,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如人的环境观念、社会运动、政府政策、经济活动等。这样一来,对于环境的重视,又可以与常态的历史研究接轨,使环境史学进入历史研究主流有了可能(32)。
国际环境史学研究的发展动向也被国内学者敏锐地感觉到了,并开始了自觉的思考。有研究者直接提出了环境史学如何在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同时做到本学科的自觉的问题。指出,“一方面,环境史研究需要从历史学外部继续做好学习和借鉴工作,但是,在借鉴与环境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理论与方法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环境教条’,惟环境而谈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史研究需要在历史学内部自觉地做好继承工作,但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自己的研究单位,丰富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33)还有研究者对环境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环境史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它的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而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更为深刻明显(34)。这种思考,反映出国内学者开始构筑中国自己的环境史学科的努力和环境史学科的成熟程度。除了总体性和理论性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关于环境史的具体研究,如吴晓军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解读了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35)。这样的具体研究丰富了中国环境史学的内容。
四、努力构筑和丰富中国现当代史学史
中国现当代史学史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热点,在过去的一年里,研究者们继续努力构筑和丰富其细节与内容。他们主要是从学术体制、教育和研究机构、史学流派、史学家及其学术成就等角度来描绘中国现当代史学史的图景的。
现代学术体制不仅是中国学术和史学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现当代史学史得以顺利发展的制度支撑,因此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比如王建伟就以《史学年报》为例,论述了专门性的史学期刊在中国现代史学体制建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史学期刊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现代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大量出现,使历史知识有了新的传播方式与渠道,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也有了稳定的园地,改变了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机制。同时,以往个人的单独研究方式渐渐消失,大量学人开始涌入高校或专门研究机构,学术群体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强(但也带来了开放度不够的问题)。它表明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化建设有了新的内容,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出现了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36)。
现代历史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及史学流派是中国现当代史学史的重要内容。其中,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师生也不多,但他们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学术队伍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江山,其人文传统、学术风格、治学理念、教育模式和方针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视为中国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新阶段的标志,并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称为“清华学派”,认为他们的研究水准直逼当时的“国际前沿”。当年身处其间的学子的回忆也颇真切感人,而对清华史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特色之总结,不但精当,而且让后人追慕不已(37)。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史学、清华学派的研究,是当前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生动个案。其他还有关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大史学系等研究和教育机构的研究。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史学史是一座房屋,一个个史学家则是支撑这所房屋的一根根支柱。对于这些支柱,研究者们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仅2006年《历史学》“史学家研究”和“访谈录”栏目中就收录了16位史家(38)。这些史家当中,有享誉史林的前辈学者,也有引领风骚的当代名家。他们的学术道路、治史旨趣、史学贡献、学术交游、人生取舍,既是宝贵的学术财产,也给后辈以极大的启迪。值得肯定的是,以“访谈录”的形式将当代著名史家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思想保留下来,既可以使时人受其思想的润泽,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活材料”。
当然,现当代史家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张剑平梳理了童书业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研究,指出童书业采取中外历史比较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了西周封建论,丰富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推进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深入探讨(39)。这样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现当代史学史的内容。
以上是过去一年中史学界比较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动向。当然,史学界关注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比如,关于中国史学的创新与发展问题,有研究者提出要以“新史学”作为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也有研究者指出了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创新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史学创新的思路(40)。比如,关于历史教育问题,有研究者分析了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关系,指出历史教育要借助于历史剧,但历史剧必须尊重历史的逻辑,历史学和历史剧可以而且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41)。再如,关于史学方法问题,除了对口述史学、“以诗证史”等方法的探讨之外,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受到重视。有研究者将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和趋向,探讨了它与人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并反思了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42)。也有研究者将人类学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认为这个视角的引入,可以帮助历史学更新观念、改变方法、扩展研究领域(43)。还有研究者将“原生态”概念引入历史研究,阐释了“原生态史料”与“原生态历史”、“原创性理解或解释”之间的依赖关系,突出了历史研究的原创性问题(44)。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史学界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展现了开阔的视野,有些方面的研究正与国际史学接轨。对于中国史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史学界总体上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研究也在顺利地展开。这些都表明中国史学正在健康发展,并将继续保持这种健康发展的趋势。
注释:
① 朱佳木:《史学理论三题》,《历史学》2006年第3期
② 李杰:《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问题》,《历史学》2006年第10期
③ 朱佳木:《史学理论三题》,《历史学》2006年第3期
④ 胡逢祥、张耕华:《当代中国史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学》2006年第3期
⑤ 张岂之:《关于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情况与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8期
⑥ 陈祖武:《谈谈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素养》,《历史学》2006年第8期
⑦ 曹守亮:《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历史学》2006年第9期
⑧ 于沛:《关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研究的再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10期
⑨ 张广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世纪40年代前后)》,《历史学》2006年第5期;梁民愫:《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重理论渊源和文化研究传统的双重考察》,姜芃:《霍布斯鲍姆和佩里·安德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历史学》2006年第10期
⑩ 田居俭:《必须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历史学》2006年第4期
(11) 黄凯峰:《以科学的历史观指导历史评价——兼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学》2006年第6期
(12) 瞿林东:《前提与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12期
(13)(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张爱红译:《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历史学》2006年第1期
(14) 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历史学》2006年第2期
(15) 吴道如:《贝克尔的相对主义史学》,《历史学》2006年第4期
(16) 张国刚:《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历史学》2006年第6期
(17) 梁民愫:《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历史学》2006年第5期
(18) 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11期
(19) (美)马克·塞尔登:《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的再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3期
(20) 张文杰等:《西方思想史研究笔谈》,《历史学》2006年第7期
(21) 张广智:《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历史学》2006年第8期
(22)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历史学》2006年第4期
(23) 侯树栋:《庞卓恒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历史学》2006年第8期;邹兆辰:《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比较观》,《历史学》2006年第4期
(24)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历史学》2006年第4期
(25) 刘家和等:《中西古代文明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8期
(26) 孙永芬:《中西封建专制政治差异》,《历史学》2006年第3期
(27) 刘林海:《从二分到跨文化比较——西方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述论》,《历史学》2006年第11期
(28) 戴仁柱著、马佳译:《新五代史英文版序言》,《历史学》2006年第12期
(29)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历史学》2006年第4期
(30) 王晓德:《关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几点思考》,《历史学》2006年第10期
(31) 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历史学》2006年第4期
(32) 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历史学》2006年第4期
(33) 梅雪芹:《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历史学》2006年第6期
(34) 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历史学》2006年第2期
(35) 吴晓军:《生态环境影响:解读西部历史变迁的新视野》,《历史学》2006年第2期
(36) 王建伟:《史学年报及其学术史意义》,《历史学》2006年第12期
(37) 何炳棣等:《“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1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笔谈》,《历史学》2006年第1期;李伯重:《20 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历史学》2006年第2期
(38) 他们是苏秉琦、谷霁光、张舜徽、陈垣、谢国桢、史念海、白寿彝、陈寅恪、罗荣渠、童书业、朱绍侯、杜维运、瞿林东、仓修良、廖学盛、许苏民
(39) 张剑平:《论童书业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探讨》,《历史学》2006年第12期
(40) 周祥森:《新史学:历史学者的永恒追求》,《历史学》2006年第1期;吴怀祺:《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历史学》2006年第10期
(41) 邢贲思:《历史·历史学·历史剧》,《历史学》2006年第4期
(42)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历史学》2006年第12期
(43) 卢卫红、刘兵:《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学》2006年第8期
(44) 章开沅等:《历史研究中的“原生态”问题》,《历史学》2006年第9期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历史虚无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