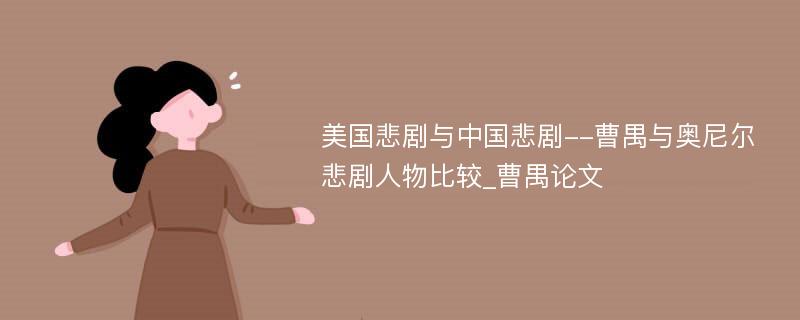
美国的悲剧与中国的悲剧——曹禺与奥尼尔的悲剧人物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奥尼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已经有数不清的文章谈论曹禺与奥尼尔的关系和对他们的接受,但大多停留在具体影响的描述上,所注意的中心是曹禺对于奥尼尔的戏剧技巧(主要是表现主义)的借鉴和超越。另有一些文章注意到曹禺的剧作无论在情节、人物还是场景技巧上都有许多可与奥尼尔的剧作相对照的地方,而且进一步作了许多较细的对比。但这样总给人支离破碎之感,而且,曹禺的剧作似乎变得“无一处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了。那么剧作家的创造性呢?为什么曹禺与奥尼尔会有这么多可以类比的特点呢?本文再来作曹禺与奥尼尔的比较,是因为笔者认为曹禺之所以接受奥尼尔的影响,奥、曹剧作中有如此多的可类比的方面,是因为曹禺与奥尼尔在基本的戏剧美学观上有相近的看法,在悲剧观念、悲剧人物、戏剧手法上都有相近的追求,也就是这种大方向上的趋同才使曹、奥产生了更加细节化的相似。
奥尼尔与曹禺从气质上讲都是典型的悲剧诗人,他们都生性敏感、情感丰富。或许因为天赋或许因为挫折,情感上都偏于阴郁。他们从小都饱尝到家庭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这些创伤终其一生都无法愈合,而且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他们对父亲都又爱又恨,他们都终生向往母亲的爱。曹禺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便去世了。他由继母抚养长大,这种创伤他一生都感觉得到。直到七十多岁了,他还热泪盈眶地呼唤母亲〔1〕。而对于奥尼尔, 母亲的吸毒成瘾和对他的忽视是他心灵创伤的根源。他就是《更庄严的大厦》中那个母亲讲的童话里面被放逐的王子,他是他母亲放逐的,永远无法打开那扇心灵的大门。奥尼尔感到自己永远是精神上的被放逐者,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精神的归宿。于是,“母亲”成为曹禺与奥尼尔一生的向往,“家”成为他们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精神的自由与归宿成为曹禺与奥尼尔最终的共同追求。
曹禺与奥尼尔都是古希腊悲剧的爱好者。这与他们天性中的敏感神秘的倾向相结合,使他们不停地追问那些永恒的命运和神秘,关照那些原始的爱与恨,崇尚那些不屈不挠的精神英雄。此外,他们更是戏剧大师易卜生的门徒。易卜生前期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相信意志能挽救人类。但当他发现人与社会的矛盾已经过于尖锐时,他退守到内在的精神领域、家庭的主题,退向神秘主义,观照人的内心的斗争和痛苦。永恒的精神冲突和具有吞噬力量的爱情成为他中后期剧作的主题。易卜生的转变标志着整个戏剧观念向现代的转变。
劳逊清楚地指出这种转变,这种转变为现代戏剧指明了方向,圈定了主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对性爱的强调;爱情是‘超出于善恶之外的’,它救人,它也杀人;三角恋爱变成中心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被忽略了,而被强调的是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情感上的需要。”〔2 〕“三角恋爱被当作一个心理问题而不是一个情况来处理了炽烈的情欲被部分地美化;家庭生活的冷酷无味;被削弱了的意志,凶兆的感觉;具有特殊情感和特殊力量的超人观念,神秘的解决方法——丧生以保生……所有这些概念在今天的戏剧中仍在永无休止地重复出现着。”〔3〕易卜生的示范再加上现代精神分析学对于恋母情结、 性欲及与之相系的家庭关系的强调奠定了现代戏剧的基本观念。
曹禺〔4〕和奥尼尔是易卜生的门徒, 他们分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和美国现代戏剧的开创者。他们代表了一种共同的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禺与奥尼尔成为中美现代悲剧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剧作显示出如此多的可比之处。
(二)
戏剧是写人的,是由人来演的。现代悲剧其不同于古典传统的不单在于它的悲剧观念、悲剧主题等方面,我认为更明显地体现在其悲剧人物的现代审美性上。而具体到曹禺和奥尼尔这两位悲剧作家,促使他们写出一部部现代悲剧的毋宁说主要源于悲剧形象的诱惑和对孕育于头脑中的悲剧人物的爱憎。本文就曹禺、奥尼尔的悲剧人物作一些粗浅的比较。
曹禺说:“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5 〕“《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此苦痛与欣慰……”〔6〕而对于奥尼尔来讲, 他剧中的悲剧形象如果深挖下去的话,实际上几乎都是他自己、他的父母和兄长的精神传记。他对父母、兄长的真实的爱恨是他写作戏剧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奥尼尔还是曹禺,当他们创作时恐怕都“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7〕但他们对于对之爱恨的悲剧人物的深刻挖掘, 正深刻地反映出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他们的悲剧性的挣扎和毁灭。
曹禺与奥尼尔著名的悲剧人物在审美特性上迥异于古典悲剧〔8 〕,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曹禺悲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女性形象。但这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造成多大冲击的女性形象!她们要爱,要恨。对于男人来讲,她们是夏娃,既是一种诱惑,又是一种挑战。做一些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作为曹禺的悲剧主角的女性不是青春少女(如四凤),不是半老徐娘(如侍萍),也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尽管曹禺对她们寄以深厚的同情,如翠喜和小东西),而是具有“雷雨般”性格、阴鸷的繁漪,虽不那么疯狂却同样任性的陈白露和妖冶强悍的花金子。他们都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情热烧疯了她们的心。”〔9〕如果追溯一下曹禺创作的潜意识的话,她们或许正代表了曹禺对母亲形象更宽泛一点——地母形象的追寻。繁漪、陈白露〔10〕(她们多少经过了文明化)和花金子,不正是野性的自由生命力的象征吗?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男性对于女性的向往是兼有母亲和“荡妇”型的——夏娃型或是地母型。
曹禺对繁漪的描写:“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人。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在那静静的长长的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是一个中国旧式的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明莫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当她见着她所爱的……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人……(但)她会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她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狺狺地,不,多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的。”而金子则完全脱去了“旧式女人”的文弱、哀静和明慧,她“眉头藏着泼野,耳上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长得很妖冶,乌黑的头发,厚嘴唇,长长的眉毛,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她的声音很低,甚至于有些哑,然而十分入耳,诱惑。”
但值得注意的是曹禺后来的审美观逐渐回归了传统。他的剧作逐渐消退了火气。郁热、狂野的气氛逐渐消失,终于进入了他创作的清秋季节——以《北京人》和《家》为代表——剧作的中心仍是女性,但已不复是夏娃型的了,而变成了为爱而忍耐和牺牲的空谷幽兰愫芳和春夜杜鹃瑞珏了。作者正回归于传统的审美观。愫芳甘心呆在生命的囚笼中,为了文清胆怯而无生气的爱而默默牺牲,她是整部《北京人》中的诗,但是一首最凄婉的诗。作者不忍她的灭亡,安排了她的出走。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愫芳出走之后又会如何呢?”而《家》中的瑞珏呢?她“虽只有十七岁的年龄,却举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小孩子的稚气。黑的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柔和的脸上浮泛着一脉淡淡的愁怨。”这样一个集纯真、端庄、妩媚、温婉、厚道,还有一点哀愁于一身的瑞珏真是符合传统审美观的最完善的女性。但她(们)与繁漪、金子相比有多大的不同啊!
奥尼尔剧作的女性形象在审美特点上与曹禺前期塑造的形象有很大的可比之处。
奥尼尔理想中的女性形象体现在其剧本中是典型的地母型。她的大多粗俗肉感(这一类女性中许多是妓女),有的虽不粗俗却也身高体壮,这类女性实际上就是妓女与母亲的混合。《大神布朗》中的妓女西比尔(Cybel)的名字就来源于安纳托利亚的大地之母Cybele。象征着异教酒神精神与基督教圣安东尼禁欲精神永恒冲突的戴昂、安东尼和其继承者比利·布朗都是最后在西比尔——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得到精神上永恒安宁的。突出的例子还有《榆树下的欲望》中的阿碧。阿碧粗俗而肉感,就是在她(他的继母)身上伊本找到了情人和母亲。作者描写两人在住有伊本母亲幽灵的客厅里第一次作爱时,阿碧感觉到幽灵:“对她变得和蔼了,”伊本的母亲让出了自己的位子。而也只有当阿碧对伊本流露出“真诚的母爱”时他才对她的热情有所反应。作者写道:“阿碧摆出一副非常富有母性的姿态,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他的母亲。她不断亲吻他,弄得他糊里糊涂,搞不清她和自己的身份。”伊本“感到通过她,也重新找到了母亲。”
再一个突出的形象是奥氏最后一个剧本——描写他哥哥的悲剧与救赎的《月照不幸人》中的乔西·霍根。杰米在母亲死后,绝望中他像母亲逃避到毒品中一样逃避到酒精和最下三滥的妓院里。乔西是蒂龙家佃农的女儿,她被描写为“个子特别大,几乎像个畸形的人,体重一百八十磅光景。”同阿碧、西比尔一样,她被赋予奥尼尔理想中的女性外形形象:结实的大乳房、细腰和丰满的屁股、大腿。她装出一副淫荡女人的样子,其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处女。在整整第三幕中,再次酒醉的杰米向乔西诉说了他对母亲的依恋和母亲的死给他带来的绝望。乔西在月光下把吉米抱在怀中,杰米在她怀中似乎重新找到了母亲,沉沉睡去。这个悲伤的大个子女人把一个面貌憔悴的中年酒鬼搂在怀里,好像她是刚从十字架上被解下来的。他们构成了一幅圣母哀悼基督那样圣洁而又悲剧性的画面。
这一类女性除了以上分析的三位之外,已形成了一个系列。再比如《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中的萨拉·梅洛迪,《发电机》中的梅·法伊夫和《安娜·克里斯蒂》中的安娜。这类妓女与母性混合的女性形象同花金子有极为相似的审美特点,共同体现了剧作家的理想。
除了这种地母型的女性之外,奥尼尔剧作中另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就是奥尼尔的母亲玛丽的真实的传记形象。她们大部分是母亲,但都敏感、高傲、神经质,近乎歇斯底里而自身又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如果说男主人公在上一类地母型女性身上找到归宿和安慰的话,那么这一类女性则是男主人公精神痛苦产生的根源,而这正是奥尼尔本人的真实情况。或许正是母亲对儿子的精神放逐,奥尼尔才创造出上一类妓女——母亲混合型的女性,希望受到伤害的心灵在理想化的女性形象身上找到安慰。
这一类女性形象主要有《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中的埃拉、《悲悼》中的克莉斯丁、《更庄严的大厦》中的黛博拉,当然——《长日入夜行》中的玛丽·蒂龙。这一类女性形象同繁漪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特别是《悲悼》中的克莉斯丁,简直像是繁漪的孪生姐妹。她同繁漪一样处于精神和欲望的完全压抑中,她们都有火一样的热情又都“秉性高贵”(曹禺语)。繁漪爱的是继子周萍,而克莉斯丁爱的是亲生儿子奥林。在奥林参战期间她疯狂地爱上了丈夫的堂弟、复仇者布兰特。布兰特在她心目中正好替代了不在眼前的奥林。像繁漪宁愿舍弃一切也要死咬住最后的爱情不放一样,克莉斯丁为了这绝望的爱情而毒死了丈夫。繁漪的绝望挣扎是推动《雷雨》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克莉斯丁的杀夫成为整个家庭血缘悲剧的开端。结局是繁漪面对自己造成的后果只有发疯,克莉斯丁面对儿子杀死情夫的事实只有自杀。克莉斯丁与繁漪在冲突的情感的性质上、高贵的气质、绝望的挣扎、甚至外貌上都有极大的相似的审美特性。
这组母亲形象是造成儿子精神痛苦的根源、而又对儿子有强烈的占有欲。最明显的代表是《更庄严的大厦》中的黛博拉。在这一点上她与《原野》中的焦母形象有较大的可比性。焦母与金子对于大星的争夺简直就像是黛博拉与萨对西蒙的争夺的翻版(无涉“影响”)。焦母对大星强烈的占有欲和她的阴狠(后者与黛博拉等没有相似性)使她成为《原野》中与仇虎、金子同样鲜明的形象,一起辉映。
(三)
在奥尼尔的悲剧人物中除了上述两类女性形象,同样重要而引人注目的就是儿子的形象。如果说上述两类女性形象代表了真实的母亲和理想的母亲的形象的话,那么儿子形象就是他本人精神的自画像。儿子形象是剧本的悲剧主人公,他们都有恋母情结,敏感而有诗人气质,他们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又受到母亲精神上的放逐(或者是背叛母亲或者是被母亲背叛),他们的精神极度痛苦。寻找母亲,寻找精神的归宿是他们终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儿子的形象纵贯了奥尼尔一生的创作。从《天边外》的罗伯特、《榆树下的欲望》中的伊本、《大神布朗》中的戴昂、安东尼、《发电机》中的鲁本到《悲悼》中的奥林,《无穷的岁月》中的约翰·洛文、《诗人的气质》和《更庄严的大厦》中的西蒙,直至最后的代表作《长日入夜行》和《月照不幸人》中的爱德蒙和杰米。
奥尼尔在谈到《发电机》的主题时说,“看来没人懂得这个真正的写人际关系的故事。就是说小伙子的母亲对他干的事情,以及导致他最后把那个姑娘——他母亲所憎恨并妒忌的姑娘——奉献给一个母性的神的经过,这一切是那个小伙子同上帝的真正的斗争,或者说激起了这种斗争。这一切符合隐藏在剧本后面的美国生活的主题,而美国正是具有恋母情结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他们对普通的宗教主题热中得要命,所以看不到人的心理斗争了。”〔11〕
在儿子系列形象的塑造上奥尼尔达到了他心理刻画的最高境界。他们是真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心理的深度、精神的痛苦和人格的分裂是这一类形象的共性。奥氏悲剧的命运感、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这类人物身上,对观众心灵的巨大冲击力也主要来自于他们。罗伯特代表了作者早年对天边外的美好理想的向往,戴昂、安东尼和约翰、洛文集中表现了现代人精神和人格的分裂,而伊本和奥林则集中表现了俄底浦斯情结,西蒙除了表现出恋母情结外还表现了物质贪欲对诗人气质的戕害。这类人物成为整个美国剧坛内涵最为丰富、复杂而又深刻的形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反观曹禺剧作中的儿子形象将是很有意思的。曹剧中的儿子形象与奥剧有些基本点上的类似,但曹禺在很多情况下并未充分展开(这不单是相对于奥尼尔而言的)。他的态度极为傲妙,对于儿子的形象他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即使相同的特征在两人笔下也会显出不同的审美效果。曹禺最著名的儿子(或者说男性)形象是周萍、周冲、方达生、仇虎、大星、文清和觉新等。实际上比较深地揭示了其内心冲突的人物只有周萍、仇虎、大星、文清。在审美特点上周萍和大星是最符合奥氏笔下儿子形象的(这当然并非衡量高低的标准)。周萍和大星都敏感而脆弱,大星对母亲的依恋、周萍与繁漪甚至与四凤的乱伦关系完全可以解释为恋母情结。周萍最像《悲悼》中的奥林,奥林先是依恋母亲而对父亲则深为反感,后来又依恋取代了母亲地位的姐姐。周萍在《雷雨》中可以算得精神最为痛苦、人格分裂最为严重的人物。作者如果再深挖下去的话,周萍完全可以成为最有心理深度的形象〔12〕。即使是现有的周萍形象也已具有了相当的心理深度和审美内涵。只是作者对他总有些蔑视(称之为“阉鸡式的男人”),这在创作中免不了就已经将他一定程度地简单化了。作者另外写了一个周冲(作者自称最喜爱这个角色),将诗人气质和对美好东西的向往赋予他。但实际效果却是周冲在剧中只是一个简单的平面人物,没有心理深度〔13〕。而事实上如果将周冲与周萍合并的话其结果就是奥林、伊本或爱德蒙。
被简单化得更严重的二个形象是焦大星。大星的心理冲突也绝对大于仇虎、金子和焦母。他处于母亲、妻子、朋友(又是仇敌)三种强大精神的夹攻下,他应该是最有心理分析意义的。而实际上他不单被简单化甚至被丑化了。作者为了表示对他的蔑视,甚至特意给他戴上了一个耳环。在剧中他只有受到嫌弃和至多一点同情的份。同时,仇虎在开幕时虽然是生命力的象征,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反成为精神分裂的人物。仇虎是这个剧中最有心理深度的人物。透过他坚硬的外壳,他内在的分裂和斗争才是作者着意刻划的。他本来就不单是什么“农村青年”,他产生的幻像更不是因为什么“封建迷信的毒害”,透过他反映出的正是现代人人格的分裂。在这一层面上他与奥氏的儿子形象有其一致性。
文清和觉新是作者审美观有了较大转变之后的人物形象,他们仍然精神软弱而痛苦,但已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的、历史的内涵,已不再与奥尼尔的儿子形象的精神痛苦处于同一层面。
(四)
奥、曹剧作中除了以上主要的人物形象之外,还有一类所谓的“不自知的坏人”。如《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老卡伯特、《长日入夜行》中的老蒂隆和《雷雨》中的周朴园、《北京人》中的曾皓等。这类人物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他们有丰富的心理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一种悲剧感,如果还不值得尊敬的话,起码值得人怜悯和同情。
老卡伯特是清教的忠实信徒,他有强烈的物质占有欲,而根本不顾妻儿的死活。但整个壮丽的农庄是他一手辛苦创下的。他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永不动摇。他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老蒂隆虽然吝啬,是造成妻子嗜毒和儿子不幸的重要原因,但他的吝啬是因为他出身贫寒,十岁就开始挣钱养家。他曾依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最优秀的莎剧演员。但出于对金钱的贪欲他却演出惊险剧《基督山伯爵》三十几年。他的贪吝也毁了他自己的前程。晚年面对妻子和儿子的不幸,面对自己一无成就的现实,他的内心是同他的亲人们一样痛苦的。
曾皓虽极其自私,但更多地则是显出他是个软弱的可怜的老人。晚辈的不肖使他伤透了心,还要时刻提防大奶奶的暗算。最后他唯一的寄托——棺材也给人抢走了。曹禺对曾皓的心理开掘较深。
同样,周朴园也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几十年来对侍萍的怀念绝不是作假(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只是他怀念的侍萍已不是那老得连他也认不得的真实的侍萍罢了。像卡伯特一样,他有一套恪守的行为准则,他贯彻如一。他不知道他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压抑和痛苦。他逼繁漪喝药并不是存心跟她过不去,他从他的原则出发要她“作个服从的榜样”,他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模范家庭。周萍就佩服他,甚至他的冷酷。但在最后一幕,他对自己确信的准则产生了怀疑,他说:“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太冒险,太——太荒唐。”作者对周朴园也并无太大的恶感,说他色厉内苒,把他比作自己的父亲〔14〕。周朴园是复杂的,他有他真实复杂的人性,在这种性质上他与卡伯特、蒂龙是相似的。
在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作为一个历尽沧桑、白发苍苍的老人的形象出现,照看着两个他曾伤害过的女性,在宗教中忏悔。他的亲人死的死、疯的疯,只有他一个人清醒地咀嚼着过去的痛苦。他没有选择死,他的活比死和疯更为艰难。“还是为虐待意志而不断地寻求不愉快的事情。为折磨自己而拒绝快乐,甘愿过着赎罪的生活;也就是故意地破坏意志。”〔15〕他的选择同《悲悼》中的莱维尼娅的选择性质一致。她选择了活着,守着那些死人,“让他们折磨我,直到偿清孽债,孟南家最后一个人咽气为止!”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两个罪人竟都有很强的悲剧感。
总体来说,曹禺与奥尼尔的悲剧形象在审美特点上有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都共同体现出现代性的审美特点,都共同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分裂,他们的人物都是丰满而深刻的创造。他们在戏剧中永远地活着。
(完)
注释:
〔1 〕曹禺的传记资料见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2〕〔3〕J、H、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PP103 —104、中国电影出版社1978.
〔4〕国内也有许多文章谈论曹禺对于易卜生的接受。 但着眼点仍在技巧的借鉴或者将接受只限于易卜生前期探讨人与社会关系的剧作。这是因为将曹禺和易卜生的剧作都有意解释为社会剧的原因。
〔5〕〔6〕〔7〕〔9〕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 卷P211,P214,P211,P215。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
〔8〕曹禺中、 后期剧作的悲剧人物在审美特点上有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10〕陈白露的形象没有繁漪和金子来得鲜明、深刻,主要因为作者写《日出》一部分转向了社会剧,是要塑造一组群像。
〔11〕Virginia Floyd:The Plays of Eugene O'Nell:a NewAssessment (Frederick Ungar Co.,Inc.1987) P356
〔12〕繁漪是《雷雨》中最为深刻和鲜明的形象。但实际上她的内心冲突远不如周萍来得复杂。她认准了一条路就一路走下去,而周萍却始终是矛盾的、分裂的。
〔13〕周冲或许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却的确没有写活。他甚至没有能进入戏剧冲突的漩涡,更别提心理深度了。李健吾很早就在《雷雨》一文中写道,“抹掉他在戏里的位置,毫无纠纷发生,未免使人失望。”“所以同样的性格,作者就把周冲写失败了。”(《咀华集》第94页作者注②,花城出版社,1984)
〔14〕田本相:《曹禺传》P16.
〔15〕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