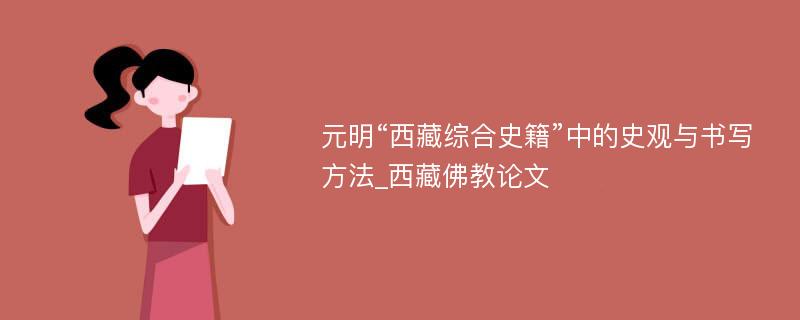
元明时期西藏的综合体史书的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综合体论文,笔法论文,西藏论文,史书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06)01-0043-07
一、布敦·仁钦珠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以及作者的纵向世界史观
布敦·仁钦珠(1290——1364年),藏历第五饶迥金虎年出生于后藏莫布霞,少年聪颖,出家为僧,为噶举派大译师卓浦的再传弟子。不过布敦并不满足一家之学,他还曾广泛游历各地,学习和深入钻研了西藏各派的教法和经典,对于萨迦派、嘎当派的理论也颇有研究,因其善于博闻强记、论辩圆通、修学兼优、无所不知,因而被人们冠以“一切遍知者”的美誉。布敦在年轻时就扬名全藏区,很快受到在日喀则东南的夏鲁地方的封建领主的注意,被邀请到此地主持夏鲁寺,布敦在夏鲁寺设坛讲法、著书立说,很快使夏鲁寺名气大振,他所传之教法后被其弟子和其他人称为夏鲁派,他本人也成为夏鲁派的奠基人。布敦生前著述丰富,其文集有26函,论著计有200多种,内容广泛,五明之学皆有涉及。《佛教史大宝藏论》完成于公元1322年(第五饶迥水狗年),当时布敦仅33岁。该书完成后不久,他又应蔡巴万户贡嘎多吉之邀请,为蔡巴辑录的《甘珠尔》校订目录,由于布敦熟悉各类藏文文献,因而其所编目录两部(《蔡巴目录》与《语宝目录》)在当时较为完善,为世人称赞。
《佛教史大宝藏论》在内容编排上,据作者自己的分类,共有四卷:
第一卷 讲说与听闻之理
第二卷 总说佛法出现于世的情况
第三卷 正法传到西藏的情况
第四卷 佛教法典分类目录
不过,布敦在该书的“序言”中又认为本书包括了如下四个“总纲”:
第一总纲 明闻、说正法的功德
第二总纲 明所闻、说之法
第三总纲 如何闻、说及修学法
第四总纲 所修之法如何而来的情况
前三个总纲基本与第一卷一致,第四总纲与后三卷相一致。
从总体来看,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佛教理论、教法、重要名词术语的介绍和解释,这些是构成第一卷的主要部分;第二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佛教在印度的产生以及后来在西藏的传播,其叙述方式与一般宗教史没有特别之处,主要围绕佛陀释迦摩尼的生平、创立佛教等重大事件来叙述,佛陀的十二功行自然是作者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在叙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时,作者采用较为简洁的笔法,叙事明晰、用词单纯,文笔简练,对于西藏佛教史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涉及。不过,本书有关历史的记叙相对《红史》、《西藏王统记》则显得较简略,与《彰所知论》倒有相似之处。在这一部分之后,作者又附有两个名录:一个是于吐蕃传法的93位班智达大师的名录,另一个是西藏著名的192位译经师名录。本书第三部分内容是将西藏当时传流于世的佛经和论典进行详细考析与编目,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佛教文献目录。
《佛教史大宝藏论》在结构上与一般史书不同,这是因为作者要叙述的内容并非纯粹的历史,而是试图从一种较高的视角来诠释藏传佛教的有关知识,因此,该书的第一部分先将与佛教相关的核心性概念以及作者对于这些概念、术语的理解进行讲说。对于历史的叙述,作者的历史观念总体上持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历史发生目的论”的看法,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佛教的产生是必然的,佛祖释迦摩尼的佛教是随同宇宙同时产生发展的,所谓前世佛、未来佛主理整个宇宙世界。在西藏,佛教的传入也是由其命运所决定,因为在神佛之光遍照世界各地之际,西藏这样一个雪域高原还处于蒙昧、黑暗的状态,连人类都不存在,最初的人类来自于神佛对猕猴与罗刹的点化,他们结合繁衍出众多后代,是为赭面黑头食肉者,品性存在善恶的分化的问题,雪域的境况只有佛教才能使之逐渐朝向有利于善的方面发展。所以,佛教在西藏的流传既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布敦的这种历史观并非他个人的发明,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提示的,在吐蕃王朝的后期,藏族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从宗教的立场上来看待西藏历史,将宗教对于历史的作用进行人为的夸大,以宗教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准。分裂时期,《玛尼全集》等伏藏著作也基本以宗教思想作为学术的主体,历史变成了宗教教理的具体诠释或补充。《佛教史大宝藏论》具有这种思想是毫不奇怪的,从藏族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布敦大师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试图创新的打算,这部著作在整体构思上类似《玛尼全集》,即将宗教学理、历史知识、核心经典融为一炉,形成“三位一体”的体系。这种安排的基本用意应该是:在开篇部分以宗教理论的阐释为主线,然后再以历史简述为补充,最后附录所有的藏文佛教经典、论著的目录,由此形成一种“宗教学”形式的,能够包容宗教全部知识的体系框架,读者(后学者)就可以从这部书中领略佛教知识的要义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布敦大师在这部著作中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他的“历史发生目的论”试图将历史的时间性进行整体的包容和概括,所以西藏的佛教史在他看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佛教的整体历史密切相关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眼里是解释宗教发生和传播的合理性的注脚。布敦的著作之所以既要阐述历史,又要包容宗教理论和相关的知识,盖取决于他的这种世界观。由于布敦本人在佛教方面具有较深的功底,这使本书对于佛教概念、名词的解释精当、透彻,对于藏文佛教论著的考证全面,故自其完成之日起,就一直为学人所看重。
二、蔡巴·贡嘎多吉的《红史》的“世界史”笔法
蔡巴·贡嘎多吉(1309年——?),生于藏历第五饶迥土鸡年,是蔡巴万户长仲钦·门朗多吉的长子。自小聪慧非凡,5岁就能识文断字,15岁时(1323年,水猪年)继任为蔡巴万户长,并娶妻结婚。16岁时,进京朝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得到册封蔡巴万户长的诏书和银印、银锭、黄金、绸缎等等。在他担任万户长的28年中,除了对贡塘寺、大昭寺、布达拉山上的庙宇予以适当的管理与修缮外,还对当时较流行的纳塘版《甘珠尔》进行校对,组织人力用金银汁缮写出260函的《甘珠尔》,使之成为当时一套标准范本。为使其工作保证质量和水准,他在编《甘珠尔目录》(原书名为《佛之甘珠尔珍宝新编目录,白册》)时,专门迎请当时的大学者布敦·仁钦珠来对该目录进行校订。后来布敦本人在对其目录加以增补、说明之后又编成《语宝目录》,此目录与蔡巴的目录齐名于藏区宗教界。在第六饶迥火狗年(1346年),蔡巴开始撰写《红史》,至水兔年(1363年)完成。这期间蔡巴万户与帕竹万户间发生矛盾与冲突,蔡巴·贡嘎多吉于水龙年(1352年)去职,将权力交给其弟扎巴西饶,自己则跟从堪钦顿夏巴·桑结仁钦出家,法名格微洛追,从此潜心于佛法和学术。蔡巴的著作除了《红史》、《甘珠尔目录》外,还有《花史》、《贡塘喇嘛传记》、《先父门兰多结传记》、《红史续集——贤者喜乐》等。《红史》写成后,很快被学人所重视,广泛传抄、刊印,流行至今。
《红史》,藏文为deb-ther-dmar-po-rnams-kyi-dang-po,意为《红色史册第一部》简称为tshal-bavi-deb-dmar,本书还有一个蒙古书名,叫hu-lan-deb-ther,其意思就是“红色史书”,与藏文意思一样。作为一部“史册”(deb-ther),这部著作在体裁上与以前单纯的王统史、教法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基本是综合性的史书,结合了王统史与教法史所能囊括的内容,也即是说,《红史》的写法是在内容上既有专门叙述王统世系传承的,又有对于西藏各个教派发展历史的概述,尤其难得的是该书在叙述历史时,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上,总揽全局,将当时所能了解的“世界”进行了专门的叙述,除了西藏卫藏历史外,还有阿里、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这种叙述方式无疑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从这部史书开始,藏族史学著作逐渐将叙述的对象从西藏扩展向周围地区,表明藏族的历史观与境域观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红史》全书分为26章,每章都设定了题目。其中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有关印度众敬王世系、薄伽梵(释迦摩尼)的历史、佛祖寂灭后三次集结、印度王统和释迦摩尼灭寂的年代算法等内容。第四至第六章分别对汉地的从周代到唐朝、从梁至南宋的历史进行概述,尤其是第五章专门把《唐书·吐蕃传》的藏译文进行全文的引用,并记下译者的身份与翻译的时间,颇为难得。第七章是对西夏史的简述;第八章是对蒙古历史的简述;第九章简述吐蕃王统历史;第十章是关于佛教后弘期开始的概述;第十一章简述了阿里王统及佛教弘传情况。第十二到二十五章,主要对藏传佛教各派尤其是萨迦派、嘎当派、噶举派的历史加以系统的叙述。第二十六章把元成宗赏赐给西藏僧人的著名的《优礼僧人诏书》全文收录,全书跋尾亦紧接此章而作结束。
《红史》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广收藏区周围各地历史并将之列在吐蕃历史之前加以系统叙述,从史书结构而言,这种由外到内的构成与叙述方式是颇为独特的,并且还反映出作者与众不同的境域观。如果与汉地史书的结构相比较,这种特点就意味深长。汉地史学自古以来一直就很发达,司马迁著《史记》,开一代新风,因为此书不仅在体例、体裁上颇有创新意识,而且《史记》还将汉地周边其他民族的历史加以关注和记录,且司马迁下笔严谨,所记录的内容可信度高。自《史记》以后,汉地官私史书对于周围异国异民族的历史的记录形成了传统,代不绝书。不过,汉地史学家在记叙历史时常常沿用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也表现出汉地史学家固有的境域观,即认为周秦汉唐,属于礼仪之邦,教化之地,此为世界中心,为“中国”,“中国”之外,基本都属于需要进行礼仪教化之地。因此,在叙述世界历史时,汉地的史学家基本上是先内而后外,即一般先讲述中原地区的历史,再叙述其他地区的历史。对于异邦民族的历史,中原史学家在叙述方式和结构上与中原历史叙述不相对等(往往列入传记之列,如《史记》的《大宛列传》,《唐书·吐蕃传》等等),而且将之置于全书后面的部分。这种结构无疑反映了汉族史学家一贯遵守的文化内向的特点。《红史》的叙述层次和重点明显不以吐蕃为中心,不以吐蕃历史为重点,而是多线并重,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等的历史所化费的笔墨大致差不多。这表明作者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与方式与汉族历史学家已经有一定的差异,作者对于外民族的文化怀有尊敬之心和学习之念,其文化外向性十分明显。自《红史》以后的各史书,但凡叙述吐蕃王统历史,一般都要对吐蕃以外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进行概述,这基本形成一个传统。同时,《红史》所摘录的《唐书·吐蕃传》藏译文也常为诸家史书所引用。
就史学史的意义而言,《红史》可以说在藏族历代的各类历史著作中较为彰显,带有“专门的世界史”(或民族史)意味。藏文史著中,《彰所知论》是最早开始记述藏人之外民族历史的著作。与《彰所知论》相比,《红史》除了记述中国其他民族的历史源流外,全书所表达出来的作者的历史眼光还更具有“专业的性质”,毕竟《彰所知论》的成书原因是八思巴出于教学需要(为真金太子讲学),因此八思巴的这部论著的基本构思是以传授佛教整体的学问为主,历史仅属于这个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布敦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在著述的出发点上也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作者主要立足于对佛教知识体系的建立上,显然,与这些著作相比,《红史》是作者经过多年准备,专门写成的历史著作,作者的构思完全是以阐述历史为中心出发点,这在史学史的学术价值上自然是有高低区别的。
而且,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蔡巴在《红史》中表达了一种新的民族观,他那个时代,元朝统一中国,将各民族容纳于同一个政治体系之下,形成密切的多民族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在撰写历史著作时,自然将眼光放开,而不限于吐蕃一隅。作者着力对汉地、蒙古、西夏等地的王统进行阐述,无疑也表现出一种统一共同体意识。这方面还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在藏族史学史上,《红史》开创了藏族历史著作的一个新的体裁,即史册,从这部著作开始,但凡涉及教法、王统、家族世系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内容的史书往往都以“史册”作为书名,后世这方面的典型著作就有《青史》、《朗氏家族史》、《西藏王臣记》等[1]。
三、释迦仁钦德的《雅隆尊者教法史》的特色
释迦仁钦德是吐蕃王族的后裔,其所在家族来自朗达玛之后的欧松的支系,吐蕃王朝灭亡后该族在西藏山南雅隆一带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形成雅隆王族世系。据有的研究者考证,作者雅隆尊者释迦仁钦德为雅隆王系释迦扎西(1250——1286年)的孙子,扎巴仁钦的儿子,扎巴仁钦曾经担任八思巴的侍者,到过内地,受元世祖忽必烈的诰封,后修建扎喀等宫堡。其幼子释迦仁钦德很小就被送往帕木竹巴处出家,出家后法名为拉尊·崔呈桑波,拉尊后来写下的这部著作,这部书在稍晚的《西藏王统记》中又被称为《大王统史》。[2]
本书在对历史的叙述上简明扼要,作者参照了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些史书及著作如《布敦佛教史》、《彰所知论》、《王统如意树史》、《唐书·吐蕃传》(藏译本)等,还有大量的各教派的传记、文献,所以本书应该具有其相应的史学价值。从结构上说,全书在章节上分得并不是特别严密,仅有几个大标题,如,汉地五王朝、吐蕃唐朝交往及甥舅史、吐蕃王统世系源流、蒙古王统及其版图扩展史、俄译师之讲经传教、上师大主宰桑波贝之子嗣、大皇帝之喇嘛帝师次第、吉祥萨迦寺之座主住持次第、康萨钦波之传承、萨迦本钦次第等。但实际上本书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这些,由于作者明确说明此书主要属于“佛教概要”,所以看起来作者对于全书的结构并不专门用心,这也可以从书后面的跋语中了解这一点,作者说:“若愿列出目录,则摘其红字部分即可,而王统世系与历代上师均能自成篇章。又,若另行摘出吐蕃王统等,亦可辑成史书。”[3] 他说的“红字”部分其实也较为简单,主要包括上面那些大标题(并不是全部)及开篇颂赞词等,再就是行文中的一些名称、词汇,并不能真正做标题使用。本书有特色的地方还包括作者在阐述历史时,较注意其引文的出处,常常在页下加以注释,或在文中说明其引用的原本名称,反映出作者的所具有的学术修养和品性。对于历史的叙述的方式,作者基本采用类似《红史》的顺序,先叙述世界的形成,再叙述印度众敬王、释迦世系及佛陀的生平事迹;然后再分别叙述汉地、弥药、吐蕃、蒙古等王统世系;最后对于萨迦历史进行相对较细致的解说,总体上讲,层次是清晰的。另外,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作者在引用材料时有很清楚的分类概念,他很注意把材料分成文献材料与口述材料,而且作者对这两类材料的引用都给予清晰的说明,这无疑可以反映作者以及当时的有关史学的学术水平发展状况。
四、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
索南坚赞(1312——1375年),据研究出生于第五饶迥水鼠年,为萨迦派僧人,曾任萨迦四大喇章之一的仁钦岗喇章的主持,1344年又兼任萨迦大寺的座主(时间不长)[5]。由于他本人学问高深、待人公正,加上他还师从过布敦大师,系出名门,因而生前就被民众尊称为“贤德大师”(班丹喇嘛当巴)。《西藏王统记》(rgyal-rab-gsal-bavi-me-long)是作者一部史学力作,本书在作者生前可能没有写完,据刘立千先生考证,本书成书的年代据各家版本的后记记载,基本一致记录为土龙年(1388年)完成,这一年代距离作者去世已经有13年了,因此此书应为作者生前尚未完成,后由其他人补续而成的。《西藏王统记》藏文书名为《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正法源流》,原书分为18章,按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天竺法王的出现、释迦摩尼降临人世间以及佛教在各地的传播;第二部分主要讲述吐蕃王统以及松赞干布的主要业绩;第三部分主要包括松赞干布以后诸赞普的事迹,记有从芒松芒赞到朗达玛10位赞普、朗达玛之后的吐蕃后裔王系(欧松、永丹、亚泽、亚隆觉沃等支系)的历史记略。刘立千在将此书翻译成汉文时,因藏文原书最后一章内容过于繁杂,故而将该章又细分为16章,合计33章,每章均配上标题,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
《西藏王统记》在写作中明显参照了《玛尼全集》、《柱间史》等伏藏著作。在内容上侧重于对历史上所说的“法王祖孙三代”,即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的历史事迹的记叙,对于松赞干布尤为重视,关于他的业绩,本书花费了9章的篇幅。作者对于文成公主入藏完婚的事迹也很重视,有专门的篇章对这次唐蕃联姻的盛事加以记录,并且作者在对待该历史事件时显然兴趣浓厚,因为在书中,作者基本不拘泥于历史的严谨,反而热情洋溢地把民间传说完全照搬,把历史事件作了文学的加工。比如“五难婚使”、“勘查吐蕃地域”、“修建大小昭寺”等等。这类传说在《玛尼全集》、《柱间史》中就已经存在,《西藏王统记》又将其系统收录,因而文成公主进藏的事迹基本就以这种传说或逸史的面目呈现在后来的藏族史书中,并且后期各史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叙差不多都以《西藏王统记》为参照。
在叙述方式上,《西藏王统记》的层次较为清晰,其体例基本属于编年史。同时,该书也有类似《红史》的结构,即叙述西藏历史时也注意照顾到周边民族的历史情况,本书第三章就专门记叙了汉地和霍尔(蒙古)两地的王统历史。不过,与蔡巴不同的是,本书作者索南坚赞的兴趣和热情更集中于佛教的传播和吐蕃王朝全盛时期的历史,因而对于西藏之外的地区、民族的记叙相比《红史》而少。当然,《红史》在对于吐蕃王朝历史的记叙上又比《西藏王统记》而简单的多。
《西藏王统记》的史学价值无疑是很高的,首先,本书是14世纪出现的首部对于吐蕃王朝历史进行全面、系统地加以叙述的历史著作,对于藏族史学史来说,意义深远。作者能够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同时合理吸收民间的逸史、传说,将吐蕃王朝的历史从远古的“猕猴变人”繁衍吐蕃六大部族开始,直到王朝灭亡后存留的吐蕃王系加以连续的记录,形成较完备的时代序列,这是十分难得的。
其次,《西藏王统记》的作者在年代上较为注重,在第一章就对佛陀生年进行考证,对于布敦大师的年代换算十分赞同。后面的各章作者也尽量要求准确,尽管在今天看来,本书的一些年代计算仍然有错误,但以当时西藏的学术水平而言,也是较为难得的。更值得赞扬的是,作者已经注意到汉文史料的年代记录与西藏的记载的不同体系问题,并且力图将汉文史料加以运用,对中原历代王朝历史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概述,并且注明其史料来源,这种做法也使其叙述显得扎实、可靠。
第三,《西藏王统记》对于吐蕃王朝历史的叙述由于作者注意广采博取,兼容各类传说,加上文笔生动,可以说基本达到当时藏族史学的最高水平,因而该书历来为藏族史学家所重视,在20世纪敦煌吐蕃文献被发现之前,本书是有关西藏王统历史的核心史书。
第四,作为一部在14世纪产生的王统史著作,本书更显其在藏族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当时的学术趋向是重宗教史而轻世俗历史,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从吐蕃王朝传流下来的古代文献还有一些,如本书作者引用的《大盟誓文》和《王统如意宝树史》就是对于吐蕃王统和历代赞普生平叙述十分详尽的史书,但作者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仅重视与佛法有缘之王,所以那些与佛教无关的赞普,如自聂赤到拉脱脱日年赞的27代王,合计时间约500年的历史,就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了。虽然本书在对于王统历史叙述上没有免俗(仍然只重视与佛教有关的王统历史),但作者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自然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作者对于自聂赤赞普到拉脱脱日年赞的27代王的历史尽力加以补充,比如其有关这27代王时产生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当时人们的一些发明的记载就较为精彩,其有关王陵墓葬的历史变迁的的说法应该来自古老的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传说,也具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五、索南扎巴的《新红史》所表现的民族史观
如果说蔡巴的《红史》所表达的“世界史”、“民族史”是一种宽线条的历史著作,那么班钦,索南扎巴的《新红史》则带有宽细兼备的特征,并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统一认识。
《新红史》藏文原名为rgyal-rabs-vphrul-gyi-lde-mig-gam-deb-ther-dmar-puvi-deb-gsar-ma,《王统幻化之钥——红色史册新书》,简称deb-ther-dmar-puvi-deb-gsar-ma,《新红史》。本书成书于明朝时期,1538年,作者班钦·索南扎巴也叫泽塘巴·夏孜班钦索南扎巴。1478年出生于泽塘。少年出家,由其师钦波索南扎西为其取法名为索南扎巴。他先后到桑普寺和色拉寺等求学,并于泽塘巡回辩经,于拉萨上密院学密法,取得格西学位,渐成一位大学者。曾任哲蚌寺塞洛林的听讲法台、甘丹寺夏孜扎仓法台、第十五任甘丹赤巴,还有色拉寺太清林、觉幕隆、帕姆寺、尼定、约纳、仁钦林寺等寺院的主管,还曾为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授戒。在他77岁时,也即1554年去世,其银质灵骨塔安置于哲蚌寺。[5]
《新红史》作为史册类著作,文字记叙简略,但包括的范围则比较细致,全书分五个部分,分别叙述印度、香巴拉、西藏、汉地和蒙古王统以及汉地蒙古佛教出现于西藏情况。与《红史》相比,《新红史》增加了香巴拉王统部分,对于元朝时期汉蒙在西藏的统治部分则将包括元朝确立的西藏十三万户在内的主要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和家族的历史情况,其中关于约卡、查嘎、琼结、桑岱、贡噶希佐巴、恰巴、仁蚌巴、内邬巴、聂等地方豪族的记载在《红史》中少见,是为比较难得的综合记录。元朝时期的十三万户在元明交替时代发生不少变化,如拉堆洛、拉堆绛万户的合并、帕竹的强盛、帕竹用兵雅桑、止贡、蔡巴、萨迦等,还有帕竹的衰落等《新红史》都作了交代。至于仁蚌巴等新兴家族历史,作者也给以相应的重视。
《红史》比较重视教法史,与之相比,《新红史》虽然也记载宗教活动,但更侧重地方家族豪强和政治势力的历史,这是其具有特色的地方。这种写法应该说有一定的创新,并且更符合其作为deb-ther即史册的体裁特点。另外,本书在写作方面还有几个优点。一是作者曾经编订过《佛历年表》,在年代学方面比较注意,一般大事均有清楚的年代、时间记载。二是作者对于所记历史进行过考证,并不简单地引用前人的说法,人云亦云。比如,他对于《西藏王统记》就指出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更正。[6] 第三是在历史著作结构和对史料的选择上有自己的特点,不拘泥于前人的形式,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表现出作者的眼光和勇气。他的这种历史叙述结构和方式对于后人还是有影响的,比如清代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基本就参照了这部著作。[7]
《新红史》在历史叙述的结构上有其专门构思,其前二部分主要叙述与西藏宗教有密切关系的印度王统和香巴拉王统。第三部分记叙吐蕃王统,第四部分记叙汉地与蒙古王统,其中主要对汉地、西夏、蒙古王统进行简略记载。第五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其标题为“关于汉蒙在西藏的统治情况”,这里面主要对元明时期的西藏政治历史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进行记载。这种章目安排显示作者对于元明时期天下统一、蒙汉藏各民族结成统一的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认识,显示作者的民族观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民族观是一致的。
六、小结
以上几部著作从总的方面来说上都很注重对事实描述的客观、真实性,但各书内容各有侧重与偏好,《红史》、《佛教史大宝藏论》、《彰所知论》、《新红史》在文字叙述方面注意文字描述与历史的结合,那种夸张、想象的描述比较少。《西藏王统记》则对于历史在总体符合具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性的叙述,相对前几种著作,比较注重文笔的优美和著述的可读性。当然,《西藏王统记》的文学类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对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修建大、小昭寺等事件上,这类事件在民间早就成为广泛流传的轶闻故事,作者在书中对民间故事加以完全的照搬,也有其相应的学术价值。
在历史观上,这几部史书作者均能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在他们的眼里,西藏与中央王朝、还有周边各个地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元朝统一中国以后,西藏作为大元帝国治理下的一个地区,更是直接的上下属关系,因而对于汉地、蒙古历史是十分重视的,尽管当时西藏的文献条件先天不足,可参考的资料少,译自汉文的文献材料严重缺乏,但这些著作都力图克服这些困难,展现中央王朝的自古以来的历史情况,并在叙述与作者时代相接近的“近代”、“现代”历史时,能够充分反映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的各种治理政策和关系,比如《红史》专门在书后全文收录元成宗赐西藏僧人的《优礼僧诏书》,并且在结束语中从全方位的角度声称:“此乌兰史册(红史),聪明的青年阅读后即熟悉典故,成为学者。以前上古尧帝时定国号为‘唐’,‘唐’之意为‘国土胜乐’。此后在虞王时,定国号为‘舜’,‘舜’之意为‘具有治理国政之大智能’。汤王时,定国号为‘殷’,‘殷’之意义为‘办一切事情秉公正直’。此后各小朝代未有命名。成吉思汗之时,定国号为‘大元’,‘大元’之意义,在《周易》一书中有‘乾元’二字,意为‘宽广辽阔、牢固之土地’。”[8] 显然,蔡巴在这里解释中央王朝名号的用意是将《红史》与有着悠久传承的中原历史学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且提示历史著作具有为后人提供治理国政的经验的意义。《西藏王统记》对于汉藏关系也十分注意,在叙述吐蕃王朝历史时,除了一再强调汉藏的甥舅关系外,还对于汉藏和好历史进行专门的解释,说:“以上概述(汉藏和好历史),若欲知藏汉媾和盟文,请阅拉萨石碑之文字。其后蒙古大将又来西藏,杀大臣穹夏,以此之故,汉藏又复失和。此汉藏史事之记录,乃出自汉主太宗皇帝时史家宋祈所编著史鉴,其后又略有修改,与及近时所出汉地译人胡降祖在新固德钦译成之藏文,其年代稍有不符,当时之人名,亦各自有译音不同,晚近国师仁钦扎大师住锡内地时,始将此汉藏和好史实,加以核对,于阴木鸡年(公元1345年)始在新固德钦付之枣梨,广为流布也。兹乃简略叙述,若欲知汉藏和好之情,及甥舅史事,则请阅彼碑文可也。”[9]《彰所知论》、《佛教史大宝藏论》《新红史》对于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在其叙述中也都给以专门的说明。《新红史》的作者还提出历史著作对于安定社会的作用,我们发现,作者眼中的王统史是基于一个汉藏蒙等民族的统一共同体之上的王统史,也是宗教和政治结合完美的王统史,作者说:“对于善业,凡今日之一切地方首脑人士,均应按佛法而行,如是则广阔之王土即可求享安乐;如果蹈循邪恶之友的欺骗、引诱行事,则势必导致连绵战乱,勿庸说见到此类之事,即使听到亦可将耳弄聋。应以刚毅、英勇及智慧使属民步入慈悲境域。如是,政教完美之事将如圆月普照,一切众生则可平安矣!”[10] 这里作者所说的“广阔王土”按照其全书的意指,无疑是指整个中国在内,这显示作者的具有开阔的历史眼光和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