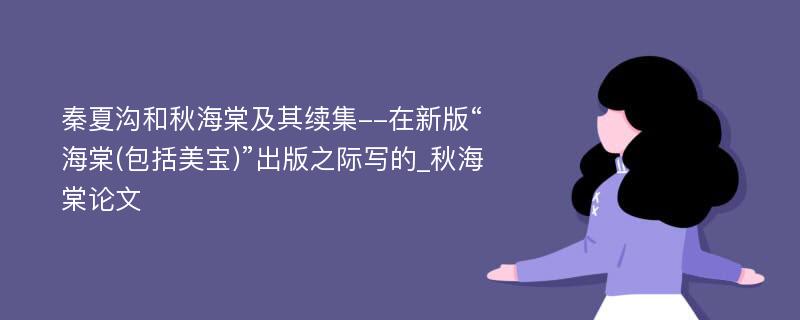
秦瘦鸥与《秋海棠》及其续书——写在新版《秋海棠》(含《梅宝》)出版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海棠论文,写在论文,新版论文,秦瘦鸥论文,梅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言情小说是民国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它发端于本世纪初中国现代都市形成发展之时。至二十年代中后期,虽然北方创作仍较沉寂,但在南方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却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曾经产生了包天笑、张春帆、李涵秋、毕倚虹等一批著名作家。
然而到了1929年,这种南盛北衰的格局却发生了变化。此时身居北京的张恨水悄悄将一部《啼笑因缘》送到上海,甫一面世,便石破天惊;翌年,刘云若的长篇处女作《春风回梦记》在天津一炮打响,旋即风靡全国。
张恨水与刘云若的出现,为北方文坛带来了生机,同时也标志着民国社会言情小说创作的重心已由南方转向北方。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南派社会言情小说虽不乏其作,但却反响平平,佳构难觅。直至1941年初,上海《申报》上一部小说的连载,方才使南方文坛重现转机,终于有了一部能与张恨水、刘云若等北派名家相抗衡的佳作。此书便是当年颇为轰动,至今仍被出版界看好的《秋海棠》,而其作者则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秦瘦鸥先生。
上篇:秦瘦鸥的生平与创作
秦瘦鸥原名秦浩,曾以刘白帆、万千、宁远、陈新等笔名发表作品。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上海嘉定县,自幼饱读诗书,古典文学根基极好,同时受祖父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曲艺术。年稍长,又与故乡草台班戏曲艺人多有往来,深谙个中三味。
学生时代,秦氏曾有过经商之念,因此先后于上海澄衷中学商科、中华职业学校商科、上海商科大学等校攻读经济学七八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曾说“在念中学和大学期间,戏瘾愈大,昆曲、话剧、电影,及至芭蕾舞剧等,有机会都要看,以致大大影响了我的学业,几乎每年都有一二门主课不及格,必须再补考一次,才能勉强过关。”毕业后,曾在工矿、铁道部门任职,但由于自幼喜好文学,又曾博览大量中外名著,故对写作兴趣日浓。在未出校门时,他便在《时事新报》学作记者,后又经友人之荐,先后任《大英晚报》《译报》《新闻报》等报刊记者、编辑、主笔等职,并兼任上海持志学院中文系、大夏大学文学院讲师,专授中国古典文学。工作之余,除从事文学创作与翻译外,仍醉心于戏曲艺术,结交了许多戏曲界朋友。
从目前所掌握资料看,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颇早,自1926年起就在上海《福尔摩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其时不过18岁。翌年,他便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大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发表短篇小说或散文随笔,同时于《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连载长篇社会言情小说《孽海涛》,这时他已使用了“秦瘦鸥”之笔名。但这个名字引起人们注意,则是在三十年代他翻译了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之后。
该书作者德龄为满族人,十余岁便负芨巴黎,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归国后曾入清宫两年,充任慈禧舌人(翻译),故对晚清宫内秘闻多有掌握。辛亥革命后,她在上海与当时美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怀德结为伉俪,几年后随夫返美专事英文写作,所述内容均为晚清宫闱琐事,《御香缥缈录》即是其中之一。此书于1933年初由美国纽约陶德·曼图书公司出版,不久,秦之好友倪哲存便从美国邮寄一本给他。秦氏在猎奇心理的驱使下,便着手翻译,并通过周瘦鹃之荐,于1934年4月中旬起,连载于《申报》副刊《春秋》版上。在翻译过程中,秦氏发现德龄由于不谙晚清历史,误笔甚多,于是他便依据《清史稿》、《慈禧传信录》等数十种旧书,进行校订,以期对原著进行缀补和弥缝。由于该书所述均为清宫轶闻琐事的亲闻录,故而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连载甫毕,即由《申报》馆印行单行本,再版七八次,累计印数超过五万册。此后,秦氏又用这个办法改译了德龄的《瀛台泣血记》。除以上两书外,秦氏还翻译了《茶花女》、《华雷斯探案》(九本)等域外小说。
虽然外国文学的翻译使秦氏载誉文坛,颇获好评,但真正使他声名雀起,名播遐迩,则是在1941年他创作了长篇社会言情小说《秋海棠》之后。此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可以说是在张恨水《啼笑因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盛况,对此下文将有详述。继《秋海棠》之后,秦氏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危城记》。但因《秋海棠》珠玉在前,此书终难望其项背,故而反响甚微。抗战爆发,他作为重庆《新民报》老作者,写了大量杂文随笔,谴责日寇行径,并参加了发起于桂林、重庆等地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
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并受政府指派到香港工作,担任香港《文汇报》副刊组组长、集文出版社总编辑。五十年代末返回上海,历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等职。这期间,他写的以手工业工人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刘瞎子开眼》于1951年在《新民晚报》连载后,翌年由新文化书局出版单行本。接着,反映劳动人民同封建把头斗争的《患难夫妻》、宣传新婚姻法的《婚姻大事》以及描写治淮工程的《江淮稻粱记》等电影剧本相继问世。其中前二部曾由上海惠昌公司电影部拍成故事片在全国上映。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笔记类文章,在上海、香港等地报刊发表。如1960年在香港《大公报》以宁远笔名发表的《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由于秉公而论,褒贬得当,受到人们关注。此后,又于1961年至1962年间,于该报连载读书札记《小说新话》;于1964年至1966年间在香港《文汇报》连载《晨读杂记》,并均有单行本面世。
文革十年,他备受折磨,曾遭到隔离囚禁,但仍然心系文学,不废创作。1969年至1973年间,在“牛棚”受审、挨斗间隙,仍以日记体形式写下了反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的小说《劫收日记》。新时期到来,他先后任职于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并欲为著名京剧女艺人新艳秋写文学传记,后因发现患有早期肺癌入院治疗而未如愿。八十年代初,应《解放日报》之约,开始了《秋海棠》续书《梅宝》的写作。此书于1982年底开始连载,随写随刊,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使《秋海棠》于四十年后终于有了作者本人亲撰之续书。此后,他又多方搜集素材,欲再以梅宝后人为主角,写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学校毕业新人从艺之故事,从而完成写定《梨园世家》三部曲的夙愿。然而天不假年,就在此书酝酿构思之时,却不幸于1993年秋天病逝,享年85岁。
下篇:《秋海棠》及其续书
1926年底,上海新舞台的两名年轻京剧艺人刘汉臣与高三奎搭班到天津献艺,得与天津直隶督办褚玉璞某姨太太相识,并发生恋情。此事被褚获知时,刘、高二人已赴北京唱戏。褚玉璞遂派兵进京将二人抓回。戏班方面托出奉系首领张学良从中斡旋,但由于褚乃山东土匪,虽然后来随张宗昌投靠奉系李景林部,组成直鲁联军,但并非张作霖嫡系,遂置张学良劝说于不顾,以“假演戏之名,宣传赤化”之罪,于1927年1月18日在天津将刘、高二人枪决,行刑前还极其残酷地用刀在二人脸上乱划一气。此事轰动津门,迅速传往全国,各种传媒更是争相报道事情经过,引起国人极大愤慨。
此时身处上海的秦瘦鸥闻知受到极大震撼,立刻产生了欲以此事为背景,写成一部小说的想法。为此他多方搜集有关事件的报道,并于三十年代初,利用客居北平之便,多次到天津实地采访。他后来回忆说,天津旧城里的大户宅门和石板路对他印象极深,并将所见一位妙龄淑女的容貌与气质暗记于心,欲当作模特儿来塑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但以上这些只是创作前的准备,真正将这个事件演为一部小说则是14年以后的事了。因为他不想走当时一些文人借着故事背景的轰动率而操觚之路,他想将故事的主题开掘得深些,这便需要时间。
1940年秋,周瘦鹃在上海主持《申报》长篇小说连载,为了发掘新人新作,特地登报悬赏佳构。一时应征作品多达一二百部,但适用者寥寥。此时他想起老友秦瘦鸥手头正有三部小说要写,于是便向其约稿。不久,秦氏便将三部小说提纲奉上,周瘦鹃慧眼识货,立刻决定刊发其中一部,这便是作者酝酿准备了十年有余,以刘、高被杀事件为素材的社会言情小说《秋海棠》。关于选中这部小说的原因,秦瘦鸥曾有过如下解释:“一则因为那故事曲折动人,描写男女之爱与骨肉之情,有深入浅出之妙;二则因为我生平爱花,苏州故园中紫罗兰庵的窗下,与紫罗兰并植着的,正是这别号断肠花的秋海棠,用这凄艳的花名来作书名,自是正中下怀的。”为了顺应读者当时的阅读心理,他又向秦氏建议:“该添上一个侠客型的人物;瘦鸥深以为然,就替我创造了那个好酒行侠行动飘忽的赵玉昆。”
该书于1941年初亮相于《申报》副刊,连载未半,便引起轰动,其在当时风靡程度大有“开口不谈秋海棠,读尽诗书亦枉然”之势。一些影剧界人士纷纷找到报社与作者,欲将其搬上舞台与银幕。1942年,秦瘦鸥应上海苦干剧团导演黄佐临之约,亲自执笔将其改为三幕话剧。后由当时话剧界大蔓费穆、顾仲彝、黄佐监各导一幕,边排边改,于同年12月24日公演于上海卡尔登戏院,再次引起轰动。连演五个多月,盛况不衰,打破历来卖座记录。特别是石挥饰演的秋海棠,凄婉动人,更为该剧锦上添花。如果说话剧的轰动仅限于上海,那么随后由马徐维邦导演,吕玉昆、李丽华主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是将这阵“秋风”刮往全国。不久,沪剧、越剧等地方戏曲也争相排演此剧,终使这场由文坛波及到演艺界的《秋海棠》旋风愈刮愈烈,其轰动效应直追十年前张恨水之《啼笑因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戏剧与电影的轰动反过来又使小说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种盗版书迭出的同时,坊间也出现了多种该书的续本。这其中在读者中影响最大,并被秦氏承认者,便是周瘦鹃的《新秋海棠》。周氏身兼此书策划与编辑双职,深谙书中三味。当该书在《申报》“一年刊完一部小说”的原则下,匆匆结束时,读者大哗。人们在为主人公的不幸唏嘘慨叹之余,纷纷向报馆及作者提出,此书“哀感太过,虽铁石人也将为之下泪,最好能使剧中人苦尽甘来,给大家乐一下子。”其中要求最甚者,便是周氏子女。于是周瘦鹃经过反复构思,“因了儿女们的一再纵恿;因了紫罗兰复活而鼓起我的勇气;因了秦瘦鸥兄和上艺诸艺人给予我的‘烟土披里纯’,我终于大胆地写这部《新秋海棠》了。”(周瘦鹃《新秋海棠》弁言)
周氏的续作虽于四十年代风行一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人们始终难得一见。直至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在编辑“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小说选”时,方才将其收入。但我们在读过此书之后便会发现:该书的开头与原书的结尾是接不上的。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出版,1980年已第6次印刷的《秋海棠》之结尾,是写女主人公罗湘绮历尽磨难,与亲生女儿梅宝相认后,同去找秋海棠。此时已隐姓埋名,沦为“筋斗虫”的秋正在后台侯场,看到她们母女后,由于精神错乱,竟一头撞在舞台假山上,旋即死去。而周续《新秋海棠》的开头则是秋海棠为躲避罗湘绮而从他居住的小客栈楼上摔下去,由于被窗外的梧桐树挡了一下,虽落地昏死过去,但立刻被人们送往医院。罗湘绮又赶到医院,出重金打点医生将秋救活。于是一家三口团圆,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续书开头与原书结尾之抵牾显而易见。
那么这种矛盾之处缘何而来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新中国成立后,秦瘦鸥为了使该书适应新时代的读者,曾于1956年对《秋海棠》作了较大修改。其中最明显处,便是结尾的变化。1980年作者在《读书》杂志上曾撰文提到:“万想不到有一家出版社竟一反常规,未经和我联系协商,突然宣布要出《秋海棠》了。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们所用的竟是解放前某私营书店留下的旧版本!最后由于我的力争,这个本子才限制了发行范围。”然而就是这个依据1942年7月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底本印行的旧本《秋海棠》,却使我们看到了该书结尾的原貌:罗湘绮与梅宝母女相认后,一同乘车去找秋海棠。但已经迟了,车子开到秋所住的小客栈时,秋海棠为躲避罗湘绮不幸坠楼而亡。此结尾与周续的开头恰如合榫接缝,顺理成章。新旧两种版本结尾比较,虽然新本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要高出旧本一筹,但却为读者设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或许秦瘦鸥对这个“谜”早有觉察,而且多年来一直想将“谜底”亮出,因此当《解放日报》于1979年向作者约写连载小说时,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放弃了几个新选题的写作,而决定亲自续写《秋海棠》。并且一反以前几种续本“大团圆”的写法,没让秋海棠,“死而复生”,而是以秋之女梅宝为主人公展开情节。对此他曾有过如下解释:“我想既然同样使用解放前京剧界的题材,那么与其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还不如驾轻就熟,以秋海棠之死为起点,让故事继续发展,可能更有把握。早年也有别人给《秋海棠》写过续篇,但都失败了。我认为第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第二是他们硬把秋海棠救活过来,再当主角,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感,所以读者也接受不了。”可见解放前包括周续在内的诸多续本,作者都是不满意的。秋海棠之死恰是全书高潮所在,此后故事戛然而止,从而产生余韵无尽的悲剧效果正是作者的刻意追求。而续书中无论是怎样让秋海棠复活,均属“续貂”之笔,是有违作者之初衷的。秦氏心目中的续书应是以梅宝为主角的下一代京剧艺人的生活故事。为了阐明自己这一观点,于是他亲自开始了续书的写作。这便是连载于1982年《解放日报》上的《梅宝》。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明白看出:《秋海棠》一书自1941年杀青至今,社会上流行的实际是两套版本。一套是以未经作者修改的初版本加上周瘦鹃《新秋海棠》为系列,我们姑且称之为“旧版”;另一套则是以作者解放后修订的新版本与《梅宝》为系列,此为“新版”。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这部《秋海棠》(含《梅宝》)便是以“新版”为底本,并在取得作者家属授权的情况下推出的,这无疑是符合作者遗愿并理应作为作者的代表作而存在的。至于“旧版”,虽然作为研究资料尚有一定价值,但重新出版显然有违作者意愿。然而遗憾的是,就在百花“新版”即将付梓笔者握管之际,一部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署名“哀情二圣秦瘦鸥周瘦鹃”所著以“旧版”为底本并且未经作者家属同意的《秋海棠·新秋海棠》却正在书店流行,这无论是对作者生前意愿(对“旧版”明确否定)抑或是作者著作权和作者家属的继承权(未经作者或作者家属授权)都是一种极大伤害,我想秦瘦老在天之灵如知此事,也将会再次“吃惊”且要表示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