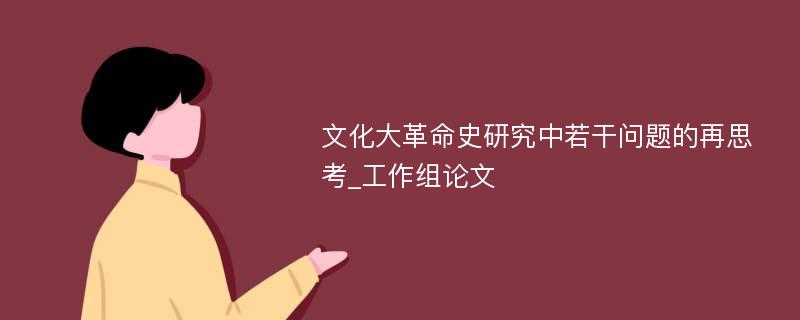
关于“文革”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史学界和学术界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笔者认为,对如下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一、关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不在“文化大革命”的范畴之内,但却和“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关联。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些话表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其之后,毛泽东对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成员已经产生了误解,随着他们关于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建设主张分歧的日益加深,毛泽东最终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清除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导致毛泽东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起点。
但是,关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评价,不少著述认为: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并对所犯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了民主,统一了认识,为经济工作的调整和动员全党战胜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毋庸置疑,大会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大会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统一了认识”两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大跃进”期间各级党组织存在的个人专断而导致的“一言堂”和瞎指挥现象格外关注,他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都对此作了严厉的批评。他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的党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党委会内部关系的原则否定了。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1](p75)。报告实质上批评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所推祟的“书记挂帅”的观点。
为克服上述现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2](p119)。会议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要求各级党委“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3](p164)。
如果仅从上述现象分析,大会对因党内个人专断所造成的危害认识是比较深刻的,所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诚恳的,由此也可以得出大会统一了思想的逻辑结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毛泽东虽然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其内心并不赞同刘少奇的讲话,而倾向于林彪在这次大会讲话中所提的“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2](p64)。会后,毛泽东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此件(指林彪的讲话)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2](p62)在4月29日他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罗:“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回答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水平差的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3](p830)
在毛泽东内心认同并赞誉林彪这篇充满个人崇拜讲话的情况下,七年人大会上的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值得深思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恢复,始终潜伏着个人专断随时泛起的暗流。
如果说当时的自我批评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则说明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原因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党内仍然存在着思想分歧。因为,在刘少奇看来,造成当时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7]。而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主要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虽然在会上也承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并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主要在于省、市、县三级党委负责人,没有认识到中央领导层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事实上,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首先来自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958年春对“反冒进”的批评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毛泽东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他甚至还说:“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1](p119)特别是他对林彪讲话的肯定则进一步表明,在对造成困难原因的认识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仍然存在着分歧,并没有统一认识,并从此埋下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种子。
二、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的问题
在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时,国内和国外的不少学者认为,“大权旁落”是促使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外如美国学者Simon Legs在其著作“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部分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国内一位学者也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5](93)。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认为毛泽东“大权旁落”的最有力论椐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和同外国一位友人的一次谈话。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17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出现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有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6](p143-144)。在同国外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全国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7]从上述内容看,毛泽东似乎真的“大权旁落”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主要证据有两点。
首先,从中央高层决策的实践活动观察,毛泽东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导地位。中国人格化的权力结构赋予了毛泽东超脱各权力精英群体之上,并能主宰事物发展进程的独特地位。只有当精英群体之间的张力严重失衡,一派精英群体的力量绝对高于另一派时,才有可能对最高领袖的权威构成挑战。纵观6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权力发展的格局,精英群体之间的张力始终处于紧张状况。如果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成员看作代表正确方向的精英群体的话,那么,以林彪、江青、康生等为主反对中央一线领导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并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成员则代表了错误走向的极左派精英群体。两个群体的斗争虽此消彼长,但在“文革”发动前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派精英群体的力量已绝对地超过了另一派。在精英群体势均力敌且存在紧张张力的条件下,毛泽东的权威不可能受到任何一派精英群体的威胁。相反,他向任何一方精英群体的倾斜都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失利,毛泽东仍然处于完全能够主宰中共决策发展进程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作为全面发动“文化大文革”标志之一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并没有到会。他只是会前在杭州召集常委会作了一些安排,然后将政治局扩大会议交给刘少奇主持。而会议的结果是一切按毛泽东的布置进行,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顺利地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开展了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批判,改组了北京市委;酝酿成立了实际上由江青控制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等。试想,如果毛泽东已经“大权旁落”,失去了对党内的控制权,这一切如何能够做到呢?
其次,如果上述实践活动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并未“大权旁落”的话,那么,1966年10月24日,他在中央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则给予了进一步的证明。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当康生说“大权旁落”时,毛泽东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该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8]从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内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毛泽东的“大权旁落”只是表面上的,他超然于各精英群体的独特地位,他洞察复杂政治生活的敏锐力,他娴熟驾驭精英群体的领导能力,他炉火纯青的党内斗争艺术,使他始终静观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发展趋向,并时时把握着扭转乾坤的主动权。第二,他的“故意大权旁落”,是他出于反修防修、永葆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的良好初衷的一次政治试探,并不是真正的实质的大权旁落。美国出版的《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其实毛谓的“大权旁落”,只是他为大树特树个人权威,进一步发展个人迷信的一种“师出有名”、“哀兵必胜”的策略手段。
三、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是否抵制的问题
目前,无论是国内抑或是国外,大部分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面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决策,在当时个人专断的情况下,虽想抵制而不可能,只好采取了消极接受的态度,跟着毛泽东的步调走,完全没有任何主动的反对和抵制。其主要论椐是刘少奇在196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检讨中说:“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19](p651)
如果仅从此段检讨的内容分析,可以得出刘少奇等人由于对开展“文革”方式的理解不同,而不是由于反对或抵制“文革”才犯“路线错误”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刘少奇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决策并非完全的消极接受,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必要的抵制,只是这种抵制在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面前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最后被“左”倾错误势力所压倒。其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消极的抵制。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刘少奇从内心来说是不满意的。《通知》中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是他在1964年至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反对的,也是他和毛泽东关于“四清”运动对象的重要分歧焦点。《通知》中所指出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14]。当时他应该清楚所指的对象正是他本人,既使他没有意识到指向自己,就当时中央的情况而言,只能联想到彭真。而彭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长期在刘少奇手下工作,他是十分清楚彭真是否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所以,无论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何种解释和联想,他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在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之下他又不得不予以接受,这种违心的接受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进发出与“文革”运动并不和谐的声符。1966年7月29日,在由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万人大会上,面对一些红卫兵提出的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少奇说:“我是党中央工作人员之一,……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就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诚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11]这段讲话与其说是将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分歧公开化,不如说是刘少奇将毛泽东个人决断发动“文革”的真相公开化。因为“党中央许多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实质上向群众宣布:发动“文革”的决策并非代表党中央许多集体领导成员的意志。可以说这是刘少奇在当时情况下对发动“文革”决策的无奈的消极抵制。
其二,主动的抵制。在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五一六通知》作些修改时,遭到了康生、陈伯达的一一拒绝。此时,刘少奇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康生、陈伯达之所以如此专断,是有毛泽东支持的。在刘少奇、邓小平根据常委会决定向北京某些高校派出工作组后,康生、陈伯达很快提出了要求立即撤消工作组的意见。在1966年7月18日的中央工作汇报会议上,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康生、陈伯达要求撤消工作组的建议。指出,“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11]。其意思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的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但康生居然也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在会上也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力主撤消工作组。陈伯达的讲话立即受到了邓小平的批驳:“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领导?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17]力主保留工作组。整个会议形成了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顶邓小平的局面。应该说,有过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验的刘少奇是十分清楚康生、陈伯达此时要求撤消工作组并不是他们两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站在他们背后的毛泽东的主张。但历史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党性原则使他们在会上没有屈服于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坚决地维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出的派工作组的决定。此外,刘少奇在1966年7月29日的大会还针对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说:“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并主张对写出标语的人“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11]。上述言行可以说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发动“文革”决策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主动抵制。
标签:工作组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刘少奇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论文; 陈伯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