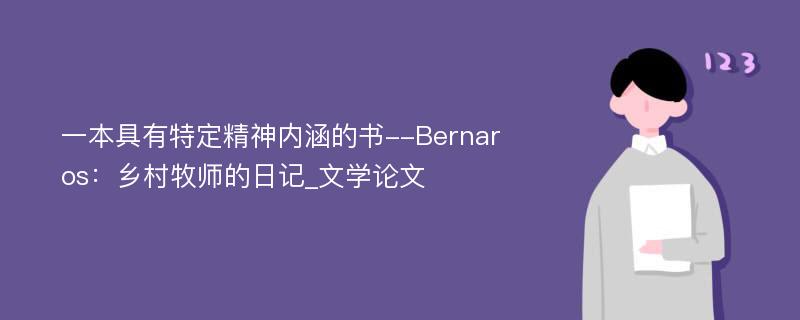
一部有特定精神内涵的书——贝尔纳诺斯:《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诺论文,贝尔论文,的书论文,教士论文,乡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本自叙体小说。
自叙体小说与一般自叙性作品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以第一人称自我的形式叙述某一经过了不同程度艺术加工的现实生活,后者则是作者叙述自我实际经过的某一现实生活。两种不同的作品,从文本上来看,都有相同的特点,即在叙述上的第一人称方式,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各自所叙述的现实生活内容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一个并非实际生活中原原本本的现实内容,而是经过一定程度的艺术想像,掺杂了若干虚构成份,另一个则是原原本本的现实内容,是实际生活中确曾发生过的真实历史。自传、回忆录、自叙性的诗歌与散文都属于此一大类。
小说就是小说。由于在古老的历史中,小说是从讲故事演变而来,最初小说的叙述方式一直都是旁叙,旁叙的方式对讲故事、对全面表现某一个事件的多方面与全过程无疑是再方便不过的,因为在这种叙述方式中,旁叙者被赋予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叙述上帝”的方便与特权。
小说领域中旁叙方式占绝对统治地位,至少继续到了十八世纪,这个时期,由于要适应更多、更真切地表现人物自我精神世界、心理变化的需要,小说中出现了第一人称自我叙述的新方式,这就是书信体小说,日记体、自述体小说的产生,这种变化是在欧洲各国文学中同步发生的,各个国度,几乎都推出了自己在世界文学享有重要地位的名著,在英国,有《鲁滨逊飘流记》;在德国,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法国有《新爱洛伊丝》、《危险的关系》、《吉尔·布拉斯》,及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小说中的自叙方式几乎已经占有“半壁江山”,而自叙体小说名著杰作已经是多得不胜枚举了。
虽然只是叙述方式问题,但与叙述的内容题材也不无关系,自叙体小说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或心理经验有关,在法国文学中的这类名著,夏多布里盎的《勒内》,龚斯旦的《阿尔道夫》,柯莱特的《流浪女伶》,拉迪盖的《魔鬼附身》,等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或成份。正因为多少是以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或心理经验为基础,作者才采用了自叙体的形式,以求自己的作品在人物的生活感受与心理活动上达到更深切自然的程度,反之,如果作者自己与他所描写的主人公在时空与状态上相距很远,他一般是不会采取自述体形式的,当然,也有特别“艺高人胆大”的例外者,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大师尤瑟纳尔写《阿德里安回忆录》(1951)就是著名的一例。
《阿德里安回忆录》以自述体形式写出了公元117年至138年的古罗马皇帝的生平与事迹。阿德里安是罗马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一生在内政外交方面颇多建树,要写出这样一个人物真实的生平与史绩,经得起历史学家的考核与推敲,这已经殊非易事,何况作者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高难度的标准,既非写一部“史记”,更非写一部“传奇”、“野史”或“戏说”,而是要虚拟、揣摩人物自己的思想写出一部“回忆录”,不仅是符合历史实际、有“信史”价值的回忆录,而且是历史人物合情合理的内心世界与思想轨迹的“笔录”,这就几乎是难于“上青天”了,这样艰巨的创作只有像尤瑟纳尔这样对古代历史与文化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型作家才敢于从事,才能够完成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此作的难度与成功,无疑成了尤瑟纳尔于198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院士的主要基石之一。
贝尔纳诺斯的《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也有类似的难度,其难度就在于贝尔纳诺斯不是教士,他却要写出一个教士的日记,也就是说,他不仅要熟悉乡村教士的生活,而且要洞悉乡村教士的内心,要虚拟出这种内心世界的状况、轨迹以及隐秘。既然是一本日记,总得有一些不为常人所知、不为常人所有的私事。
教士,这是法国文学中出现得最多的人物中的一种,大概是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教士属于特权阶级,教会不仅占有巨大的资产。而且拥有极大的权势,所以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教士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面目可憎的。在中世纪的小故事中,教士个个嘴馋、贪欲、吝啬、好剥削人,在十六世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教士被称为“可怕的猛兽”,十七世纪莫里哀著名的世态讽刺喜剧《达尔杜弗》中,天主教士号称“良心导师”,实际上是破坏平民家庭、骗取掠夺市民家财的恶棍,在十八世纪文学中,教士更是普遍地遭到了鞭挞,在几个启蒙思想大师的笔下,教士个个可恶,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中的教士不是上层社会淫乱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特务活动中的为害甚烈的鹰犬,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中,教士有的是为贵族淫荡的生活服务的皮条客,有的是阴险无比、玩弄权术诡计的阴谋家,在卢梭的《忏悔录》中,教士之下流简直不堪入目。显然是因为处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前夜,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教士作为特权阶级在社会上已动众怒,即使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与政治目的的文学作品,也对教士很不容情,产生于这个世纪的第一部法国性小说《好家伙修士无行录》中,教会修道院被描写成为了乱交、群交的大淫窟,各种稀奇古怪、扭曲变态的淫行,都来自教士的发明。
到了十九世纪,宗教与教会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没有了,文学中的教士形象也大有改善,除了像《巴黎圣母院》这样以暴露封建专制社会为目的的作品外,反映十九世纪生活的作品对教士也变得心平气和了,不再把教士都描写成魔鬼,倒是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通情达理,难能可贵,甚至德行高尚,人们熟悉的几部文学名著都是如此,在巴尔扎克的《乡村教士》里,主人公是一个心怀社会理想,为社稷人伦呕心沥血的改革家,而在《杜尔的本堂神甫》中,也有一个忠良憨厚、老实善良的皮罗多神甫,在斯丹达尔的《红与黑》中,彼拉神父与谢朗神父都是“最好的教士,德行完善的君子”,他们学识渊博,洞悉世态人心而又悲天悯人,忠于宗教的原则而又宽厚大度,严于教旨而又通情达理,惜才爱才,主人公于连正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帮助,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卡汝福神父更是一个集所有人道主义高尚精神于一身的人物,慈祥、仁爱、宽宏、善良、克己、磊落、高尚、廉洁、公正、有正义感、充满了睿智……,几乎所有的美德他都应有尽有。
应该说,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中,教士形象的情理化基本已经完成,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种特定身份与特定职业的人物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以及他们所显示出来的人性特征与水准。当然,对他们的描写与展示,都是作者从他们的外部,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去进行的,人们所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客观状态,即使作者也结合他们的客观状态,掀开他们内心世界的一角帷幔,但也是非常有限的,加以在身份与职业上的特殊,这种人物往往具有更为复杂、更为幽深、甚至带有神秘主义成分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一直是一个陌生而隐秘的领域,展示这种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特别是钻进这种人物的内心,从内而出,采取“自我说法”的表现形式,对文学来说,似乎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一片有待开垦的园地,但这样一个新鲜的园地,偏偏几乎无人进入,其原因不外是,当过教士的作家毕竟很少,即使当过也不见得就愿意“现身说法”,而没有当过教士的作家,也由于难以猜透、揣摩这种特定人物的特殊内心生活故望而却步。
因此,当贝尔纳诺斯作为一个非教士出身的作家,决定钻进一个教士的内心世界,以第一人称自叙体来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他无疑是给自己揽了一件“瓷器活”,一椿并非易事的任务,现在就看他是否有“金钢钻”、是否能用“金钢钻”把这件“瓷器活”好好地完成,是否可以真实地表现出一个教士的实际生活与内心世界。
贝尔纳诺斯没有当过教士,对他写教士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先天不足”,不过,没有当过教士,也可以对教士有相当了解,巴尔扎克在他《杜尔的本堂神甫》中就证明了这一点,何况贝尔纳诺斯还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对宗教是体知甚深、虔诚信奉的,这至少使他在两个方面具有揽下这桩“瓷器活”的条件,一是与教士比较接近,对教士的生活比较关注,比较熟悉,二是对宗教世界观、对教士的复杂的精神生活、幽深的内心世界比较容易理解,容易体察,容易透析,容易揣摩。
在《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中,首先可以感到作者对乡村教士实际生活厚实的了解,可以看到一个乡村教士现实的存在状况。
正如在几乎所有对教会人物进行过描写的文学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乡村教士原本都是出身于农村贫寒家庭,为了糊口与生计才进入修道院或神学院接受教育与培训,以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乡村本堂神甫或其他基层神职人员的职务,谋求终生就吃上这碗饭。即使是在封建专制、教会享有特权的时代,这种乡村教士从其出身与实际地位而言,都属于社会的下层,虽然肩负一方教化、众生引导、公共慈善的责任,他们仍属于社会上的小人物之列。
贝尔纳诺斯这部“日记”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他自称“出身穷人世家”,“也是个农民”,祖上都是包身工、卖苦力的,或者是当女佣的,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贫雇农”,十二岁就出家来到了修道院,结业后当上了一个可怜巴巴的村庄的本堂神甫。薪俸有限,日子过得很寒伧,饮水都没有着落,只好忍痛花钱请人到泉边去打水,膳食费付不起,也只好不用女佣了事,至于穿着,内衣的褴褛使他甚感惭愧,缝补过多次、渍痕斑斑的外衣更是显出一付穷困潦倒相,经济上甚至还偷偷接受有钱的同事的施舍。他年纪轻轻,胃部就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常为此而受折磨,但他仍极为忠于职守,每天都奔波在自己的教区,路上步行的时间实在花费够多,以致他自己也哀叹“我一生的全部精力将耗尽在这片沙路上”。其实,他这样辛劳的奔波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他所面对的是“精疲力竭”的农村,是充满了“多脏的秽物”的世界,“堂区是很脏”,“基督教国家还要更脏”,他就陷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琐事中忙忙碌碌,进行他无济于事的修修补补……。他并不就因此而心安理得,他常为自己涉世不深、不熟谙农村经济事务以及实际生活的某些基本情况而战战兢兢,对于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种种专业知识,他也准备“顽强地去进行钻研”,因为他认为所有这些经济事务、实际生活与专业知识都是他的职务要求,自己必须了解与精通的。虽然他严于克己,非礼不为,非礼不视,品行端正,但却经常碰见带有性意味的诱惑、含着邪意的骚扰以及含沙射影的恶意讥讽……
这一幅特定的乡村教士的完整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图景,作者既不是通过戏剧性的故事与事件,也不是通过完整的“自述”展现出来的,而是通过“日记”中的只言片语,零星记述编织而成的,其精到细致,真有如“勇晴雯巧补孔雀裘”。尽管是丝缕线索,但最终却构成了统一的意境与象征,以这个青年乡村教士操持之努力与有恒,来观照其实际效应之徒劳与无效,两相对照,显然形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意象,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比喻来说,简直就像西西弗在推石上山。看来,这个悲剧性的意象是贝尔纳诺斯有意造成的,这种悲怆性的意境是他有意构设的。
更重要的是,贝尔纳诺斯在法国文学中第一次打开了一个教士的心扉,这里不是弗罗洛式的充满了灵与肉、混杂着邪恶、承诺与罪恶的内心世界,也不是脱罗倍式的充满了世俗功利心、权术与算计的内心世界,而是一个从少年时候就置身在宗教教义的“染缸”中浸泡了十几年,因而宗教行为规范与天真自然感性在身上占有主导地位的教士的内心世界。这里所记载的,不是某个以功利与情欲为内容,困扰着、折腾着灵魂的戏剧性故事,也不是绘声绘色的日常见闻,甚至也不是鲁迅日记式的每天大大小小事务的流水帐,而是严肃性十足的思考,正经性十足的内心感受。
他具有十分真诚的敬业精神,热爱他的工作,认定自己并非供职于一个“虚设的行政机构,而是精神道德机制中一个不朽的活动细胞,深信自己的职责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教区视为安身立命的所在,没有视为继续升造的跳板,更没有视为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势力范围,而是当作一个与自己生命同在、为自己深深挚爱的对象,虽然它只是一个“宛如精疲力竭的牲口,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之上”的小村庄,请看他这种深情激动的呼唤:“我可怜的堂区,也许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堂区……,我希望我能死在这里。我的堂区啊,这是我叫它时不能不激动,不能不产生一阵爱的冲动的一个字眼呀!”
他对自己职责的艰难性有充分的认识与感受,对上,他感到上帝是他“怎么也说不清楚的”,而对下,对他面前需要领牧的芸芸众生,他又深感其人性的复杂与难办,“畜生的需要甚微,总是一模一样,而人则远非如此”,“人人都愿意谈论乡下人的单纯朴实,而我倒觉得他们复杂得可怕”,即使是面对堂区那些少女的夏娃式的狡黠,他都不止一次不知所措,事后总是一整夜一整夜地“由灵魂受苦”……他毕竟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轻人……
他颇具思想家的品格,很关心一些社稷人伦的历史、现状与可能的未来,经常思考国家、社会、道德等等大课题,特别是贫富问题,他把这个问题与历史、宗教、制度、世态、人心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很有若干深刻的见解,并且还包含了对社会前途的憧憬与设想,他无疑带有理想主义的倾向:“任何社会没有理由存在贫穷”,怎样改变“上帝的合法继承人穷人”的状况呢?怎样才能做到“恢复穷人的权利又不安排他们的权力?”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当政者所操心的这些大问题,居然缭绕在辖区仅一小村庄的这个乡村教士的小脑袋里。
他虽然只管理本堂区里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但他在精神上颇有点期望变革的倾向:“我钦佩革命者,为了用炸药炸毁一垛垛高墙堡垒,他们费尽了心思,要是思想正统的人那一串钥匙能为他们提供方便,以便他们能从从容容从大门进去而又不惊扰他们,那该多好。”
他当然没有少考虑宗教问题,他深知宗教与教会的力量与恒久性,他认识到:“教会是一种拥有自己的律法、自己的官员、自己的军队的主权国家……它正朝着跨越时空的方向发展,它要依靠各种连续的制度和社会生存下去”,他道出了宗教教会与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制度之间的依存关系,他悲叹,也许正是在这种依存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走了样”,“在日渐堕落”,“修道院院长们的乐观主义已寿终正寝”。他看到世风日下,“许多特别操心维持社会秩序的教徒,说穿了是维护他们自己”,他提醒自己“倘若我事事顺从这些人都乐意我扮演的角色,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颇有点自我操持的气节。
当然,他在跟教会的同道的交往与关系中有不少体验,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不少自省,他对周围的世态人心也有不少观感,如果如他自己所说:“修士们真是了不起的内心世界生活的主人”的话,那末,所有这些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心生活的内容固然都是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但最令人感动的,可能还是这个乡村教士心灵深处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与他自己对人之存在的悲怆感,他把人世概括为“人们眼睁睁看着烦恼横行无忌”的苦海,在这里,“烦恼是一种尘埃,您在来往之中不会看到它,但您在呼吸它,您在吞吃它,您在吮吸它。它是那样的细小,那样的纤薄,以至在牙齿下甚至没有声响。可是您停片刻,它就盖满了您的脸庞,盖满了您的双手,您必须不停地晃动才能抖去这种尘埃细雨”。他把自己视为这个烦恼世界上一个匆匆的过客,当人们读到以下这样的段落时,是很难不被深深感动的:“我只不过是小教堂门前的过往行人,而远在修建小教堂前的15世纪,这座村庄就在这里,耐心地忍受酷暑严寒,雨打风吹,它曾几度兴衰,几度沧桑,它牢牢地抓着这块贫瘠的土地,吮吸着它的精华,又把它的亡灵归还黄泉。它的生命历程该是怎样的神秘,怎样的深沉!它如同带走别人一样将把我带走,而且我比别人肯定走得更快。”
应该说,贝尔纳诺斯所打开的这个内心世界,理性的内容显然大大多于感性的内容,而且教士本来就是思想幽深,甚至多少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人,这个乡村教士又是一个爱好思辩的人,加以他写这部日记的唯一目的“就是自己对自己交谈”,他写下来的东西也就只求自己看得明白,而并不求别人看得明白,因此,其中的思想有时不免晦涩,现实关系与人际交往线索过于隐蔽,人物面目有失鲜明,某些意味过于微妙含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本并不容易读的书,是一部爱好思考、有研究兴趣的读者才愿意一读的书,它不是一本可提供消遣乐趣的书,而是一部有思想深度与心理深度的书。
当然,这本书的一切一切都是贝尔纳诺斯有意安排,一手造就的,显然,他只想表述自己的思想与见解,展示出一种人生态度、人生哲理,他并不想把自己的书写得“好看”,他本来就是一个安于清贫、淡泊名利的人,甚至在1927年就拒绝了接受荣誉勋章,他怎么会在1934年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投合通俗小说的趣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