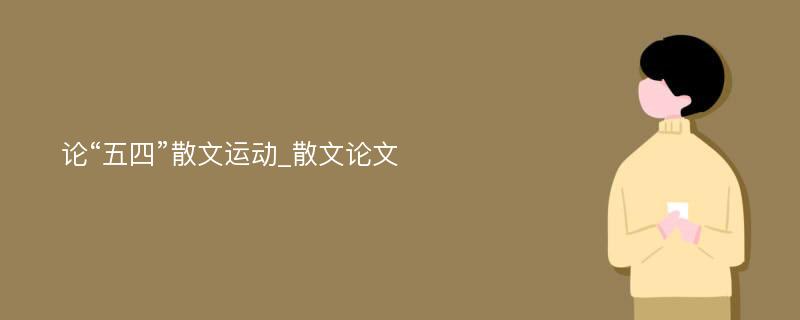
论五四散文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五四文学革命初创期10年的散文倡导和创作,是一场有承传关系、有领袖人物、有外来影响、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绩且影响深远的散文运动。其源头是清末“文界革命”,领袖人物为鲁迅、周作人。它挣脱旧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束缚,主张“言志”和张扬个性,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它重视白话散文的文学性,强调既要学习生动口语,更要研究语言的逻辑次序、结构关系、美感意味。五四散文运动作者多、报刊上散文栏目多、散文作品集多,各种散文流派已然形成。
【关键词】 议论纵横 汪洋恣肆 犀利泼辣 锐气逼人 雄壮气势 革新之举
五四文学革命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前空千古、下开百代的文学大变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大融和的背景上,这次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均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在新文学的辉煌成果中,散文(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和以记叙为主的散文)的收获是极其令人鼓舞的。巡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成就之大,水平之高,实不让于其他三类体裁的作品。对此,胡适、朱自清、鲁迅、曾朴诸先生在二三十年代都作出过相当明确而肯定的评价,像鲁迅所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就是人们很熟悉也很有代表性的见解。特别是1931年,曹聚仁先生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更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由五四运动带来文学革命的大潮流,……弥天满地,都是新的旗帜,白话文代替古文站在散文的壁垒中了。就当时的情形看,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散文运动较为妥切。代表文学的,只有幼稚的新诗,幼稚的翻译,说不上什么创作;其他盈篇累牍的都是议论文字。[①]
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简直就是一场“散文运动”。虽然我们还不能认同曹先生这段话中对新诗、翻译以及其他文学品类成就的某种轻视意味,但他提出的五四“散文运动”的观点还是相当犀利而富于启发性的。顺着这一指点,沿着散文历史发展的路径寻觅,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五四文学革命初创期10年间的散文倡导与写作,在实际上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有承传关系、有领袖人物、有外来影响、有理论主张、有创作实绩且影响深远的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运动。
1
五四散文运动的源头是清末的“文界革命”。约一个世纪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面对衰颓的国运奋起图存,开展了变法维新运动。为了配合政治上的革新活动并宣传扩大其影响,他们在文学界也发动了全面的改良运动,而“文界革命”就是散文领域的革新之举。
梁启超是清末文学革新运动的中坚,“文界革命”就是他提出来的。面对当时僵死的八股文、凝固的桐城文和奢糜的骈体文在散文界的泛滥,他大声喊出了“夫文界宜革命久矣”的宏壮声音,给人们以极大震动。他声言“文界革命”的终极功利性目的就是要“觉世,觉天下”[②],表现出磊落的襟怀与气魄。作为一位遍读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文坛精英,他不是像很多腐儒那样将自己禁锢其中,而是以相当开放的心态看待外国文学的长处。他说:“余……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谈》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之,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③]梁氏立足于中国的散文界,又借来“欧西文思”的武器,便开始了他的“文界革命”。
梁启超和他的同道者极力提倡的是一种区别于八股文、桐城文和骈文的“新文体”散文,它要具备“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④]的特点。这些主张正是吸收了白话口语与外国文学营养的结果,影响既深且远。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等就是一批“新文体”的示范性文章。这些文章以其“魔力”征服了知识界文化界,对旧思想旧文学形成了巨大冲击,在散文领域内造成了文体大解放的趋势,为10多年后的五四散文运动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因此,钱玄同充满感佩之情地由衷赞叹道:“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⑤]
2
鲁迅曾经说过:“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⑥]这段话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实际的。伴随五四文学革命而来的散文运动,便是清末“文界革命”遗产的直接承继者。这是这场散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承认的。但五四散文运动又不是“文界革命”的简单重复,实际上后者只是对旧散文的“改良”,所以同是钱玄同,他在赞扬梁启超时也坦率地指出了其不足:“梁任公的文章,颇为一班笃旧者所不喜;据我看来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晰耳。”[⑦]而五四散文运动则是从一开始便带着彻底冲破封建时代旧散文的樊篱,使自己迅速现代化的决心和力量登上20世纪文坛的。
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们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⑧]的文学进化观念出发,以旧文学语言形式上最严重的缺憾——文言为突破口,力主以白话代之,进而彻底否定整个封建文学。胡适提出了“八事”、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义”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惊世骇俗的变革主张,高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高一涵等纷纷起而应和胡、陈的振臂一呼,声势汹涌,经过与守旧派的激烈论战,在当时中国文化大变动的背景下,文学革命终于成功了。
五四文学革命从它发轫那一刻起,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推动和实行散文界的变革。这变革的发动者就是上述一班人。他们的很多变革主张,尽是针对旧散文而发的。他们尖锐地指斥长期居于文界正统地位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这些“妖魔”及其文章“尊古蔑今,咬文嚼字”,“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字,……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⑨]“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⑩]在近乎摧枯拉朽般猛烈的攻战中,旧散文的圣殿迅速地坍塌了。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五四散文运动的滥觞者们一面做着旧营垒的破坏工作,同时也就构建着自己的新殿堂。周作人说:“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11)]前驱者们那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文字,很多便是议论散文,只不过有些还暂时穿着“文言”那套过了时的服装。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散文出现在1918年。这年4卷4号《新青年》上刊登了7则“随感录”,它们都是短小尖锐的议论时政的文字,6则是白话文。它标志着现代议论散文中“杂文”的诞生,这是五四散文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随后,各类报刊竞相开辟专栏登载杂文,渐使杂文写作蔚成风气,1924年《语丝》的问世,更推动杂文发育成熟,成为文坛不可小视的景观。而鲁迅则对此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用毕生精力写作和提倡杂文,他的杂文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在他的推动下,杂文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体。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之父,是五四散文运动中逐渐形成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
以记叙为主的白话艺术散文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1919年李大钊写的《五峰游记》,此后到1921年初尚有包括冰心的《笑》在内的少数篇什出现,但影响都不大。使这类散文获得迅速发展的动力,应归功于周作人的倡导。1921年5月,周作人在《美文》中号召同道者们都来“试试”写一写那种真实简明的、以叙事与抒情为主的“美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周作人的一声召唤,似乎提醒了朋友们,使他们纷纷拿起了笔;而他自己则很快写出《山中杂信》等作品,仿佛兼有垂范之意。这样,白话艺术散文很快“热”了起来,作者与作品相继涌现,且佳作迭出,与议论散文特别是杂文成辉映之势。到20年代中期,其收获便斐然可观。周作人从此时起,便逐渐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对现代艺术散文的提倡与写作方面来,他的理论观点和创作实绩都颇有建树,身后也熙熙然跟着一批追随者。应当说,周作人是五四散文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1928年,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里说:“……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胡、朱两先生的话连起来,恰好总结了从五四散文运动的发生到20年代中期草创成功的这段历史。他们的总结当是最具权威性的结论了。
3
与以往历史上的历次散文运动不同,五四散文运动的发生发展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呈两个层次:一是西方文化、文学思潮对我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总体影响,一是我国现代散文对外国散文的直接借鉴。
五四散文运动中的弄潮者们众口一辞地承认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
周作人指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12)]周氏所说“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即我们所谓总体影响,它对中国新文学造成的是全方位的根本性的影响。自19世纪中叶起,我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走出国门,主动去寻找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武器,以便为自己的祖国服务。19—20世纪之交,严复、林纾、梁启超等的翻译事业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清末大批留学生的出国深造,更使年轻一代亲沐欧风美雨的洗礼,使他们成为有知识修养、有民主意识、有宏大抱负、有责任感与魄力的一代精英。“民国五六年的新文学运动,多半是由这个时期的留洋生所提倡的,并且他们至今仍然是文坛上的宿将,……他们在本国既已有充足的学问,出洋后又复受欧美学术思想的陶熏,比较之下,就能看出中国文学之缺点,他们提倡新文学运动是洞察中外的潮流而积极提倡的,故能一举成功。”[(13)]这里所说的“他们”,即指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郭沫苦、郁达夫等。
谈到现代散文对外国的具体借鉴,朱自清明确认为:“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他还特别举出散文写作已取得卓著成就的周作人、鲁迅、徐志摩等人作为典型,说明他们从外国散文接受的影响要比从中国接受的多。[(14)]郁达夫甚至“臆断”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气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15)]郁达夫的上述提法有的未必十分准确,但他认为中国散文受到了外来影响的说法是毫无疑问的。
周作人提倡“美文”,除了参照“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以外,便是借鉴“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的小品随笔(即郁达夫所说的Essay),向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以及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等“美文的好手”[(16)]学习。
除上述三位中国现代散文大家的论述外,还有不少现代作家也都谈到过外国散文对我国现代散文的影响。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五四散文运动正是充分吸收了外国文化与文学的有益营养,正是由于置身当时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转折时代,才令文学革命的开创者们视野更开阔,思路更开放,在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能超越前人,从而创造出崭新意义上的现代散文来。
4
五四散文运动的理论建设相对于创作来说是滞后的。1920年以前,几乎没有专论散文的理论文章出现,倡导者们的理论主张,大都较分散地杂厕于对文学革命问题的阐述及论争文字中。这不奇怪,陈独秀、胡适等人本来也并不是专以改革旧散文、提倡新散文为提倡文学革命的唯一指归的。他们当时是以文学为突破口,去从事新文化启蒙工作的。几年后,他们就各自转换方向,离文学便愈来愈远了。但陈、胡诸人毕竟都曾深受古代散文的浸润,也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对旧文学的优劣之处有着透彻的了解认识。他们的最可贵之处,便是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从旧文化、旧文学的营垒中走出来并发动文学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重点对象之一便是旧散文。所以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散文理论家,也还是对初期的现代散文理论发表了很多重要见解。到了1921年周作人选定了散文作为“自己的园地”去竭力加以开垦经营,才开始较系统地提出了他的一系列散文主张。他是最早专心致志弄散文的五四作家。在他和别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年代中期五四散文运动初创成功时,现代散文理论便有了最初的轮廓。
大致说来,五四散文运动时期的理论贡献有如下几方面:
1.白话散文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文体地位。在前驱者们看来,散体文章并非全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陈独秀主张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区分为二”。[(17)]刘半农认为文章应分为“文字之文”和“文学之文”,前者包括文牍告示、判案文书等类,它们“为无精神之物”;后者包括描写人情风俗、抒发情感怀抱的文章,为“有精神之物”。[(18)]钱玄同也有相似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现代散文应向西洋文的款式学习,学习其词法、句法、章法、语法。傅斯年说得最为干脆:“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19)]但这“文学之文”的概念仍嫌朦胧,直到《美文》出来才说得较可把捉,就是指区别于学术性文章的真实简明的文字,它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这一概括标志着现代散文作为独立文体的地位的确立。[(20)]
2.挣脱旧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束缚,强调“言志”和个性。封建时代的散文具有顽固的“载道”正统属性,因而成了拘囚个性的牢笼。五四散文运动的前驱者们从反封建的立场出发,坚决否定旧散文的这一传统,也就是否定用散文来阐扬封建正统思想的为文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极力突出散文的“言志”价值取向,张扬个性和自我表现。这是与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
周作人在《文艺上的宽容》中说:“文艺以自我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刘半农提出:“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而后所为之文,始有真正之价值。”[(21)]这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所以后来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是‘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22)]当然,强调个性、言志和自我并不等于忽视散文的思想内容,相反,现代散文从一开始其实便是“载道”之文,只不过所载是反封建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之道。周作人说“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23)],就是这个意思,也是要补救他先前过份强调“言志”而否定载道的缺失。在五四时期,前驱者们出于反封建的需要,否定“载道”说时有些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
3.极为重视白话散文的文学性。这是关乎现代散文能否被社会承认的根本问题。俞平伯明确地指出:“单就文艺而论文艺,技工在创作时之重要初不亚于灵感。文艺和非文艺之区别间,技工正是一重要的属性。”[(24)]这里的“技工”,当然是指形成散文文学性的艺术手法。陈独秀则谈得更为具体:“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25)]他在《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中一再强调散文要有“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美的体裁、艺术的结构”,以及想像、情感、趣味、艺术性之类;他特别指出:“‘白描’是真美,是人人心中普遍的美,‘百战不许持寸铁’是白话文的特性。”这些观点都是对于现代散文艺术美特质的相当精到的观点。1926年出版的夏丐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更系统阐述了散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与技法,说明人们对现代散文文学性的理论认识已相当深入了。
4.语言。五四散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对语言问题格外重视。翻开那些年的《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可以找到不少专门讨论语言和语法问题的文章。不消说,文言作为半死的文字很快就退位于正统,前驱者们同时也就开始刻意经营白话。对白话来说,做到言文合一首先必须明了通俗,但这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胡适提出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6)];傅斯年也提出了“精纯的国语”的概念,即既要学习“说话”式的生动口语,更要讲究语言的逻辑次序、结构关系、美感意味,从而“造前人所未造的句调,发前人所未发的词法”[(27)],在这里,傅斯年的见解显然要比他的老师胡适的提法具体得多;沈雁冰认为语言“要有光明活泼的气象”,文章“要用语体来做”,还应注重与内容的关系[(28)];周作人早年主要从内容与气质上去评价文言和白话,后来则多注意语言的“本色、简单、涩”等特点,他在《燕知草·跋》中说:
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上述作家们的观点,只是五四散文运动时期人们的论述的一部分,应当说,现代散文的语言问题,始终是在不断探索完善之中。
5
五四散文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宏富的成果。一般人论到文学革命的实绩,往往首先想到小说和诗歌,其实公平地说,散文比小说诗歌出现得不但早,而且数量也多。甚至在“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写的《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青春》、《爱国心与自觉心》、《新青年》等文章便可以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了:虽然形式上仍是文言,但内容是宣传社会改造、民主思想、人道主义、文化更新之类的,与五四启蒙运动的宗旨完全一致,且文学性很强。这些文章连同1917年后的《文学革命论》等一批议论文字,套用胡适当初谈自己白话新诗的一个比喻,可以称之为“后放脚式”的散文:文言文的语言外壳,全新的议政论文、抒情写世的现实内容。它们是文言散文向白话散文的过渡。关于这一点,当初曾激烈地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他的火气平息下去后有过颇为中肯的说明:
今日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有三种来源。第一是做惯古文的人改做白话,往往不能脱胎换骨,所以弄成半古半今的文体。梁任公先生的白话文属于这一类,我的白话文有时候也不能免这种现状。缠小了的脚,骨头断了,不容易改成天足,只好塞上棉花,总算是提倡大脚的一番苦心,这是大家应该原谅的。……[(29)]
这“后放脚式”的散文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18年,傅斯年、胡适都提出应以白话为文[(30)],钱玄同在一封信里说得最具号召力:“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31)]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散文遂渐次粉墨登场。从这时起到1927年的约10年间,白话散文大量刊登于各种报章杂志上,长篇的议论纵横,汪洋恣肆,短篇的犀利泼辣,锐气逼人,几乎造成了散文写作的爆发之势,实实在在地显示了五四散文运动的雄壮气势。
具体来说,五四散文运动的实绩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考查:
首先是作者多。除了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和鲁迅、周作人等人外,像陶孟和、瞿秋白、瞿世英、邵力子、曹聚仁、林语堂、刘大白、陈望道、沈玄庐、吴稚晖、叶圣陶、朱自清、孙伏园、章廷谦、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振铎、许地山、陈西滢、俞平伯、谢冰心等都是一时名家,而且我们还可以一口气再说出几十位来。那时的散文界,真可以说是群星璀灿,相映生辉。
其次是报刊多,栏目多。仅从当时作为全国思想文化中心的北京来看,几乎没有一份报纸刊物不登散文或者不设散文栏目的。《新青年》不必说了,它几乎就是专登议论散文的刊物,很多栏目也是由它创制的;就说《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努力》、《语丝》、《现代评论》、《晨报副镌》、《星期评论》等十几家报刊,也无一例外地用很大版面来发表散文。而刊登散文,特别是杂文的栏目,据有人统计就有“随感录、杂谭、杂感、杂文、杂评、杂著、随想录、乱谈、随便谈、评坛、批评、闲谈、小言、补白、读者论坛、通信、什么话”之类繁多的名目,[(32)]这些也构成了五四时期北京散文界的一道颇有意味的风景。
另外,结集成书的散文作品集也有相当数量。这方面同样有人作过不算完整的统计,1923年到1927年,散文专集约有30部问世,[(33)]这其中著名的有鲁迅的《热风》、《坟》、《华盖集》及其续编,许地山的《空山灵雨》,陈西滢的《西滢闲话》,钟敬文的《荔枝小品》,陈学昭的《倦旅》,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等。
最后,也是格外令人欣喜的一点,就是五色斑谰、风格各异的散文流派已然各逞风流,各展华彩,正如朱自清所说,其中“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它们“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34)],溢彩流光,令人目不暇接。现代散文可以说已渐渐脱去稚气,走向成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散文运动带着前所未有的超越意识,从我国古代散文的跑道上起飞,经历了10年的艰苦航程,终于胜利降落于20世纪的现代中国。它的成功造成了我国散文史上的又一次辉煌,同时也影响和鼓励着后来者,去攀登中国散文风光无限的新高峰。
On Prose Movement of the May 4th.
Huo Xiuquan
Abstract:During ten years of the initial period of May 4th written language revolution,the advocacy and creation of prose,in fact was a prose movement which had inheritances,leading personages,theory proposi-tion,foreign impact,solid result an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The"revolution in literatic circle"at end of qing dynasty was it's orign Lu Xun and Zhou Zuoren became the Leading personages,if stood for"express-ing aspiration~and"spreading out individuality",opposed the writ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advocated the writings in the vernacular.It paid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character of vernacular prose and put the emphasis on that not only the lively spoken language but also the logic sequence,the structure relations and the aes-thetic flavour of language must be studied.In the movement,the prose author,the prose specialcolumn and the prose collected works had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prose had been formed too.
Key Words:discussing the matter with great ease,on a boundless ocean taking a full swimming (itmeans taking action unconventionally and unresttainedly)(or it means casting off restrictious),in cisiveness and daringness (style),momentum pressing people,majestic momentum,innovational writing.
注释:
①曹聚仁:《笔端·现代中国散文——在复旦大学讲演》,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1月出版。
②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转引自《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③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出处同注②。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出处同注②。 ⑤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1卷2号。
⑥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⑦钱玄同:《通信》,《新青年》4卷1号。
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9月版。
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
⑩(18)(21)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
(11)(12)(16)(2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现代散文导论·上》,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9月版。
(13)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版。
(14)(3④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1982年8月版。
(1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现代散文导论·下》,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
(17)陈独秀:《致胡适》,出处同注⑨。 (19)②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卷2号,1919年2月出版。
(20)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也持这一观点,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1989年6月出版。
(24)俞平伯:《文学的游离及其独在》,《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25)陈独秀:《答曾毅》出处同注⑨。
(2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处国注⑧。
(28)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29)章士钊:《整理国故与打鬼》,《现代评论》119期。
(30)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新青年》4卷1号;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31)转引自蔡元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出版。
(32)评见张华主编《中国现代杂文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33)李宁:《小品文艺术谈》。
标签:散文论文; 周作人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杂文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文学革命论文; 钱玄同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