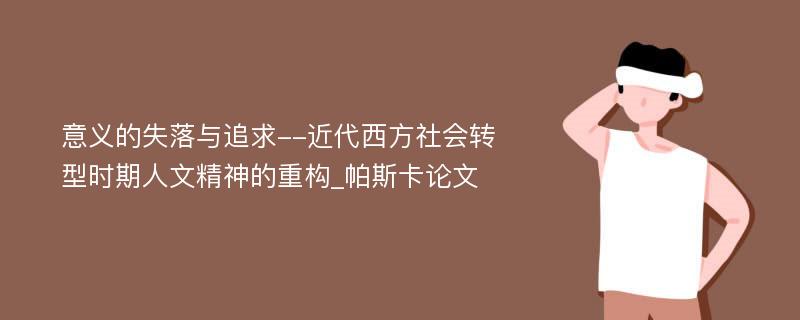
意义的失落与追寻——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人文精神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近代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意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人文精神的危机和重建成了备受学界牵挂的焦点问题。但细究起来,这个问题既非中国独有,亦非今天才有。在近代西方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个问题就以尖锐的形式被一些人本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提出来。考察和反思西方思想家当初为重建人文精神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人觉醒了以后
人文精神的危机通常表现为意义的失落,这种意义的失落往往和社会转型时期剧烈的生活震荡密不可分。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现代文明,中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但缺乏自由的个人并不感到孤独。这不仅因为宗教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而且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种族、民族、家族、社团等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社会母体。这种给人以安全感和相属感的社会母体当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惟因如此,资本主义瓦解僵死的封建结构,造成个人的自主独立和积极的社会流动,才被看成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问题在于,“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在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所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相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因此,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市场竞争给每一个人赐予成功的希望,也给每一个人强加了被淹死的威胁。生活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个人孤零零地面对苍茫的世界,无依无靠。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样两种相反的情绪。莎士比亚借哈姆莱特之口说: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
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在这段著名的文字中,莎士比亚坦露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情结。这种赞美和厌恶所昭示的问题,正是人觉醒了以后的问题。帕斯卡指出,按照基督教信仰,上帝绝对肯定地给出了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可是人一经觉悟,脱离了上帝,则谛听这种解答便成为一件“稀罕事了”。结果就是价值的倒错:“真正的本性既经丧失,一切都变成了它的本性;正如真正的美好既经丧失,一切就都变成了它的真正的美好。”(《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6页)但假如抛开对信仰权威的优先接受,把凡人的情欲看作人的自然本性,再把自然本性的公开释放所带来的福乐和荣誉看作人的真正的美好,那么,这种美好将势必扫荡人的羞耻感,从而带来沉醉于欲焰的狂肆、浪荡和残酷的纷争打斗。
对人的如此这般的厌恶是人的发现的合乎逻辑的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合乎逻辑地表明,人的发现不仅是人挣脱上帝怀抱的觉醒,而且是人在另一水平上或另一景观下的迷惘。帕斯卡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症结:“上帝的行动是以慈祥处置一切事物的,它以理智把宗教置于精神之中,又以神恩把宗教置于内心之中。然而,想要以强力和威胁来把它置于精神和内心之中,那就不是把宗教而是把恐怖置于其中了。”(同上书,第87页)首先是中世纪教会把宗教变成了以强力和威胁为特征的恐怖,所以才有了人文主义者对宗教的反叛;而反叛的基本目的,就是掰开教会的死手,救活神圣的价值理想。但是问题在于,在中世纪宗教系统中,价值理想表现为超世俗的神性的光照,因此,当对宗教的反叛不仅指向专断的教规,而且进一步从根本上危及超验信仰的时候,世俗化的自主人格能否获得如此崇高的尊严和伟大的力量,以致可以独立地承担起原本由上帝肩负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类带向自由幸福的光明境界呢?帕斯卡表示怀疑。他向那些自由勇士提出质问:摆脱上帝的监视而把自己提升为自己的唯一主宰,“难道这是一件说来可乐的事吗?恰好相反,它难道不是一桩说来可哀的事吗?不是世界上最可哀的事了吗?”(同上书,第95页)
哀莫大于心死。在发现人的渺小、可哀与兽性之后,人对万物灵长所寄予的信仰轰然倒塌。人的觉醒仿佛是一场错误。可是,人既觉醒,成为根本,则神本就不再成立;而神本不再成立,则向上帝祈祷便不能给自主独立又病入膏肓的人提供缓解焦虑的信心和依托,因为那里有一个忏悔的力量所达不到的盲区。在这样两难的处境里被扯来扯去,再坚强的神经也会被崩断,更何况那些想救活价值理想的人本主义者对世态炎凉是那样的敏感,那样的不能容忍!
帕斯卡认为,摆脱这一精神困境,必须来一场赌博。这场赌博是一大胆而惊险的跳跃。它需要勇气和毅力,也需要谦逊和虔诚,而且一定得赢回一个确定性的东西。根本说来,这就是在新的水平上重建信仰。
“谛听上帝吧”
所谓在新水平上重建信仰,也就是在人觉醒了以后重建信仰。帕斯卡强调,作为允诺真正美好的指路明灯,宗教信仰本质上应当是可敬的和可爱的。它以神恩唤起人的自由自觉的倾心,而不是煽动盲目崇拜。更不是诉诸强力恐吓。“维护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那就是毁坏虔诚。”(《思想录》,第123页)这意味着,新时代条件下信仰的重建,必须对承认人的理性自觉为前提。帕斯卡称,人作为一个生物存在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但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凭借思想他可以囊括整个宇宙。因此,思想形成了人的伟大与尊严。倘否认人的这种伟大与尊严,则信仰就会蜕变为蒙昧。
从形式上看,由于叹服思想的力量,叹服人类理性在探究宇宙运行规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明晰、精确和严谨,帕斯卡似乎接受了笛卡尔主义和近代科学的一切前提。这使他有别于奥古斯丁。但卡西尔评论说,思想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又在于,正是这位堪称当时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的帕斯卡,“变成了中世纪哲学人类学的殿军”(《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按照近代理性主义者的乐观成见,哥白尼日心说为代表的新宇宙学,打破传统的神学-形而上学所设立的天国领域的虚构界限,使人穿越太空,经天纬地,获得了理性得以自由飞举的无限空间。但是,深受中世纪哲学人类学影响的帕斯卡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茫茫宇宙向人无限制地开放以后呢?这开放真的就等同于解放吗?
帕斯卡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脱离上帝的监护,冲决羁约理性的狭隘围墙而驾雾腾云,它同时也是一次放逐。当人在无限的时空中颠沛流离的时候,他实际上显得既渺小又可怜。帕斯卡正告那些新宇宙学体系的乐观而盲目的崇拜者,近代科学世界已不再是光辉晶莹的圣宇,而是冷漠荒凉的黑洞。双手合十,仰首太空,再看不见高悬的神性明灯,再听不到天使的欢乐歌唱,只有一片对人的最深沉的情感要求缄默不语的无声空虚。于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和焦虑在帕斯卡心底油然而生:“我们是驾驶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在不定地漂流着,从一头被推到另一头。……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能建立起一座能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思想录》,第33页)
只要把这个荒芜的宇宙景象同哥白尼、伽里略那数学化了的条理井然的乾坤作一对照,就不难体会,帕斯卡是如何背离了由科学发展推波逐浪的理性主义洪流。笛卡尔自称他“顶喜欢数学”,因为数学的美感和单纯及其推理的清楚明白和绝对精确,提供了一个至为“稳固”、“坚牢”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可以建立起一座巍然的知识大厦。倘就帕斯卡杰出的数学贡献而论,他似乎有理由也完全有资格讲同样的话;关键在于,他不仅作为科学家思考各类数学难题,而且作为哲学家试图弄清数学理性的适用范围与合理限度。这使他作出了“几何学精神”和“敏感性精神”的原则区分。在帕斯卡看来,几何学精神具有原理的明晰性和演绎的必然性等优点,但惟其如此,它只适用于那些可以精确分析的、可以将其还原为原始要素的同质对象,而不能用来处理人的心灵。因为在人身上我们找不到科学逻辑所要求的那种齐一性、单纯性、可还原性和可计算性,而只能发现一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微妙性、丰富性、多样性、模糊性和矛盾性。因此,那种按几何学体系建立道德学的尝试,从开始就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臆想。
这样,帕斯卡便严格地遵循笛卡尔主义的分析逻辑,把近代科学精神锻造成了反对近代科学精神的有力武器。按照他的新思维,关于理性能力之伟大的证明,反过来看,恰恰就是理性能力之卑下的证据。“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同上书,第164页)伟大,在于它开启了无限的时空,在于它以清晰严谨的逻辑把握了宇宙运行的恒常律则;卑贱,则在于它把人变成无限时空中渺小的尤物,在于它那探究外物的逻辑格式无法在人痛苦的时候安慰人在道德方面的愚昧无知,在于它这个跛脚的精神挡不住感性欲望、财富荣誉对人的致命诱惑,挡不住人向腐化放纵、空虚无聊和烦恼绝望的无底深渊的沦落与沉坠。由于清醒地意识到人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来回撕扯、满怀不安而又毫无结果地东窜西撞的荒诞境遇,帕斯卡一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和李尔,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困惑。“瞻望四方,我到处都只看到幽晦不明。”(同上书,第106页)但与哈姆莱特和李尔不同,帕斯卡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毁灭一切的价值虚无。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走出幽晦、奔向光明的坚定信念。“一定要有一个定点,才好做出判断。港岸可以判断坐在船里的人;可是我们在道德方面又以那里为岸呢?”(同上书,第170-171页)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收敛愚妄,保持沉默,去倾听一个更高更真的声音,谛听上帝吧!
借用舍斯托夫的说法,谛听上帝需要的不是走,而是飞。所谓飞也就是摆脱情欲的羁绊,冲破规律之网的束缚,重新返回人因堕落而丧失了原本的神性生命。(参见《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4页)但与中世纪神学家不同,执着于这种重返的帕斯卡实际上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不是别的。正是近代那两股幸福主义和理性主义浪潮以人的解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超验神圣的全面袤渎。这种解放与袤渎的矛盾交织在帕斯卡身上打上了两个烙印。从否定的意义来看,它使帕斯卡获得了中古神学家体会不到而且可能将其指控为病态的孤独、忧郁、焦虑等情绪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帕斯卡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判断,他所发展出的寂静得令人恐惧的宇宙意象,以及那种被抛到这个世界,不知何来,不知何往,脆弱不定而孤独焦虑的感觉,根本就是一个走出中世纪以后的现代人的心态。倘着眼于此,有人把帕斯卡说成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先驱,似乎也不无缘由。另一方面,从肯定的意义上说,帕斯卡作为一个富有近代精神气质的思想家,对科学理性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不仅在于承认,科学理性展示了人“析万物之理”的主体能力的伟大,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科学理性在自身的知识框架内,其逻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就此而言,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用三段论逻辑证明上帝存在的理由,远没有近代科学认识论穷究人的认识能力时所提供的证明上帝不存在的理由来得有力,更何况科学家手里还拿着一架能看清天体真面目的望远镜呢!由此可以理解,帕斯卡为什么把谛听上帝看作是一个惊险的跳跃。他的勇气、他的虔诚、他的深思熟虑的严谨全部都体现在这样一句警世格言之中:“赌上帝存在吧。”
深入追究下去,我们可以从这里引伸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就上帝的存在打赌?关于这个问题,悲观主义者,像哈姆莱特和李尔,都作了消极的回答,或至少是把它悬置了起来。他们眼里揉不下肮脏的砂子,因此对人生价值产生怀疑。但他们被怀疑牵着走,始终没有摆脱绝望的阴影。与他们相比,帕斯卡既是后退,又是前进:后退到最原初的神秘,却也因而显现了穿透黑暗的神性亮光。换句话说,人在矛盾两极来回撕扯的尴尬荒诞的生存境遇,不是放弃信仰的理由,而恰恰是重建信仰的理由。“所有这些对立,看来仿佛是最使我远离对宗教的认识的,却是最足以把我引向真正宗教的东西。”
既然赌上帝的存在成为非作不可的选择,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场打赌最终能赢吗?倘以作为绝对实体的上帝的存在打赌,肯定要输给以实证科学为根据怀疑上帝存在的理性主义者。但帕斯卡说,他吁求的不是学者和逻辑学家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的上帝。于是局面便整个倒转了过来。一方面,指责宗教信仰缺乏严格的理性证明,变成了对宗教信仰的最高褒奖。因为假如基督徒给出这种证明,他们就是不守约言了:“唯其由于缺乏证明,他们才不缺乏意义。”另一方面,赞扬科学理性的清晰严谨,又不啻是对科学理性的致命诘难,因为逻辑的必然性压根儿就无法解决知识论范围以外的终极价值意义问题。“感觉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因此,可以追问,而且必须追问:当科学根据自己的合理要求,在正当地排除那些把上帝实体化的虚妄观念的时候,是否也有权利和根据把原本不属于它权限范围的价值信仰一并加以排除呢?反过来说,凭什么就能断定,出自信仰的情感激荡没有冷漠的理性推论来得可靠呢?一旦面对这些问题,近代理性主义浪潮的弄潮儿便会在帕斯卡那里发现一个最强大的敌手。
历史理性的盲区
帕斯卡逝世之后的下一个世纪是辉煌的启蒙世纪。在这个世纪,科学的令人目眩的成就使理智的优越性成为不可移易的信条。人们觉得,凭借理性的力量,不仅可以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精确认识和有效控制,而且可以改进社会,最终达至人性的完善。在一种乐观主义占上风的文化氛围里,帕斯卡的沉思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响,以致伏尔泰把向这位“卓绝的愤世者”发出的挑战,提到了“为人类辩护”的思想高度。按照伏尔泰的辩护辞,令帕斯卡感到迷惘的人性矛盾,不是人的荒谬和软弱的证据,而是人的力量的实际表现形式。因为矛盾性、多面性之举,意味着人是一个永远历险于新的可能的不定形的存在物。正是通过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外放显示和自由发展,人才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自己。没有理由为此感到悲哀。
但这样一个善恶混合的矛盾主体能否承载起推动文明进步的历史重负?假如一定得由它来承载,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当然不可能一切皆好。伏尔泰说,面对历史中随处可见的苦难,闭上眼睛无疑是愚蠢的自欺欺人。我们既不可能避免恶,也不可能根除恶。然而可以为之辩解的是,恶乃人性中固有的因素,且可以使历史显得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理性进步给人类显示了一种未来的希望,应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这种思想逻辑或可称为历史理性主义逻辑。
当伏尔泰用历史理性主义向帕斯卡挑战的时候,他表现出了能言善辩的机智幽默以及启蒙思想家那种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从理论上说,帕斯卡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理性既不能免除道德罪恶,它就不能充分疗治人因意识到这种罪恶而产生的心灵伤痛。而假如把对罪恶的解释权从上帝手中剥夺过来,转交历史,又会导致一个新的难题:倘说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而且作为某种调味品可以克服历史的枯燥与贫乏,那这是否意味着,根据历史理性的法则,历史的混乱、世界的灾难本身都有意义?伏尔泰似乎不愿接受这一结局。他的意思是,文明进步总要付出代价,应该对这种代价作好心理准备。同罪恶作斗争是必须的,只是不要把这种斗争的必要性扩展为厌恶人类进而向人类复仇的非理性的消极态度。但问题在于,如果把历史理性提升为评判文明进程的至上的和唯一的标准,将很容易得出现实即合理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既会妨碍对历史进步的代价作彻底的反省,也无法为反抗客观存在的人间苦难提供充分的价值依据。解决这些问题的强烈冲动,使卢梭游离于启蒙运动的主流之外,焊接了一个新的链环——伦理、政治与美学的链环。
可以说,在18世纪,卢梭是第一位严肃地看待帕斯卡对人的批判、并感受到这种批判的全部力量的思想家。他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获奖征文以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几乎是重现了帕斯卡在《思想录》中对人的伟大与可悲的描述。同帕斯卡一样。卢梭认为,文明社会用以装点人生的那种耀眼的光辉。只是一层浮华的外表。在这层外表下,隐藏着哗众取宠的虚荣和利己主义的物质欲望。前者使人丧失自我,只能从他人的意见去判断自己生存的意义;后者使人泯灭道德良知,沉醉于卑劣的功利谋划而不能自拔。
很明显,按照卢梭的这一评判,伏尔泰对文明进程所抱持的乐观信心显得过于轻率。当伏尔泰讥讽卢梭:“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卢梭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如果你观察到使我们憔悴的精神痛苦、使我们疯狂而疲惫的无度贪欲;如果你想一想人为了利益怎样在表面上相互帮助,而骨子里又如何相互欺骗、相互忌恨、相互残害;如果你考虑一下世间那“好像狼一样,尝过一次人肉以后,便厌弃一切别的食物,而只想吃人”的统治、奴役、暴力和掠夺……你将如何评估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伏尔泰回答说,无论代价多大,我们都不好苛求完美,而只能“让世界就这样继续下去”。这种回答相当有力,因为它理智地看到了支配历史进程的客观法则。但也正因如此,它遗留了一个价值空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抬举历史理性的铁的权威,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从价值论角度看,都是对鲜血和眼泪的某种程度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难道罪恶、混乱和灾难的不可避免,就成了顺从无常的历史命运、勾销对阴暗现实的批判谴责的正当理由?历史理性像一块石头,是不是意味着人也必须变成一块石头?假如人变成石头,麻木不仁地“让世界就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将如何索求自由、平等、正义和幸福?以这种方式追问的卢梭,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反叛而打中了启蒙理性不愿正视的道德真空。
一如帕斯卡,强烈感受到近代世俗化进程所造成的人们精神生活的神性匮乏和价值饥渴,并试图给予补救,是卢梭全部理论探讨的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卢梭把这一主题纳入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根据帕斯卡的宗教-形而上学,人的罪孽源于人的原始堕落,因此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固有特征。与此不同,卢梭虽承认人的堕落的异化现实,却不承认人的原罪的正当可靠。在他看来,“自然人”的原始冲动天真善良,纵会表现为“自爱”,也决不是什么“自私自利的爱”。由“自爱”到“自私自利的爱”的蜕变是文明进步的副产品。因此,是社会而不是个人才构成了罪恶的真正承担者:“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爱弥尔》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页)
于是就有另外一个重要差别。在帕斯卡,人类生存状态的荒诞由人的原始堕落所致。由于堕落,人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人生的完满,所以必须回归信仰。而这种信仰,一方面要求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产生由衷的负疚感;另一方面也要求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保持渴慕救赎、祈求新生的谦卑与虔诚。但在卢梭那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被引到了一个新方向。就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批判反省来说,由于社会被判定为罪恶的渊薮,因此意识到罪恶,将不仅导致人的内在紧张,而且会使这种内在紧张演化为人与社会的外在紧张。在这种紧张中,具有自主人格的独立个性,时刻体验到社会对他的压迫、抑制和伤害。他由此产生强烈的屈辱感,并为捍卫自尊而向社会、向习俗、向传统发动愤怒攻击。与此相联系,就对未来理想的设计谋划来说,由于原罪教义的有效性被否定,生存之价值意义的赎回,便不能指望上帝的恩典,而只能依靠自己的奋斗争取。这样,政治就取代神学,承担起了救赎的功能。但是这种政治并非形而下层面的务实的利益协调和规范安排,莫若讲,伦理关怀才是它首要的关怀,形而上的价值追求才是它统率一切的根本追求。这种追求所呼唤的,不是自惭和谦卑,而是激情和热血;不是循规蹈距的科层官僚,而是惊世骇俗的革命斗士,——他博击风浪,卓尔不凡,富于挑战精神,充满人格魅力。从气质上说,这是帕斯卡未曾见识过,而且见识了也会感到恐惧的新潮而激进的道德英雄和文化英雄。
我感觉,故我在
这种激进的道德英雄和文化英雄,很容易在大危机和大动荡时期走红;而一当它走红,作为某种理想化身被卷入政治洪流,进而为革命加速助燃,强化以正克邪的力度,则其结果往往是伟业与狂暴并举。此乃道德化政治实践的吊诡。雅各宾专政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暂且把它撇开,而集中考虑一下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落脚于人生后会培育怎样一种生活风范和存在方式。如果说,卢梭本人即其人生哲学的典型体现者,那么,他用《忏悔录》来为他的自传命名,似乎有些让人迷惑不解。因为,就传统的宗教道德含义而论,忏悔即悔过自新,但卢梭的《忏悔录》虽无意为自己遮丑,却充满受挫的怨恨与怒火。他那不留情份的自我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表现为否定形式的自我辩护和自我张扬,他通过审判自我而建立了一个审判社会的最高法庭: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的我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这是卢梭《忏悔录》中一段纲领性的文字。通常认为这段文字表达了卢梭的坦率。这个看法虽然不错,但尚不足以充分展示其个性。因为在传统思想家,譬如在奥古斯丁那里,坦率也是忏悔的合乎逻辑的要求。但是,为领受圣爱而将自己和盘托出的奥古斯丁,决没有坦率到像后来卢梭那样对自己的隐秘心理感受作细致入微的刻划描述的地步。这不是一个美学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性的精神品格问题。也就是说,奥古斯丁不是因为缺乏某种艺术修养而不会这样做,而是出于一种道德恐惧而不敢这样做。奥古斯丁的忏悔表达了一种自惭形秽的负疚感和羞耻感,而卢梭的忏悔则表现了一种狂肆不羁的唯我独大。当他反问:谁比我好?实际上已作出回答:没有人比我好!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仅使他不把袒露自己的缺点过错视为一种苦刑,倒深信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在他眼里,这实际上是一种向无聊世界的挑战,一种弃绝平庸的超拔,一种遗世独立、不同凡俗的孤傲。他对此深为自豪:“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忏悔录》,第3页)
丹尼尔·贝尔评论说,切不可把卢梭的自我崇拜等同于单纯的顾影自怜,也不好用裸露癖来简单地打发卢梭那近乎处心积虑地制造轰动效应的坦率。问题的要害在于,卢梭在这里确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新文化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生存意义的阐释,与习俗成规、与传统的连续性巨链无关,而仅仅与自我的个性、与自我经验的奇特性有关。(参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2页)此乃卢梭式精神品格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它的座右铭,用西方哲学的典型术语来表达,就是:“我感觉,故我在。”
对卢梭而言,“我感觉故我在”当然不是“我信仰故我在”。因为“我信仰故我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表现为对神性权威的优先接受,而卢梭作为一个生活于个性解放时代的新潮思想家,则始终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但与以“我思故我在”为基本信条的理性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不同,卢梭在理性化潮流,特别是理性化潮流和功利化潮流汇合形成的历史巨浪的冲击下,又感到六神无主。他觉得人不应当成为逻辑符号,成为机器零件,成为既阴毒贪婪又卑贱下作的冷血动物。假如人已经异化为或正在异化为这样的动物,在卢梭看来,那就必须以反潮流的形式向沉沦的芸芸众生展示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理想。他从激昂炽热、圣洁单纯、自由奔放的生命情感那里,找到了支撑这一生存理想的原始基础。“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情感之链。”(《忏悔录》,第348页)“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而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真理。”(《爱弥尔》,第338页)按照卢梭的看法,追随这一真理,人生将不再是异化沉沦,而会成为无拘无束的自由表演和自我实现。因此,跟着感觉走,跟着本能走,就是跟着良心走,跟着光明走:
“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味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善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照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同上书,第417页)
这就是卢梭在强烈感受到近代理性化和世俗化过程导致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神性匮乏和价值饥渴以后,所开出的疗救药方。药方的关键是褒激情,贬理智;扬直率,抑反思;重灵性,轻功利。卢梭试图以这种方式对人生意义重新加以解说,以填补传统信仰衰微后遗留下来的精神空白,延续和传递那颗形而上的人类价值火种。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坚持以个人为本位,卢梭的思想努力从本质上讲不仅与本来意义的宗教信仰无关,而且可以说截然相反。丹尼尔·贝尔认为,“凡是宗教失败的地方,崇拜就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20页)卢梭的精神取向正是宗教失败后应运而生的崇拜。对他来说,忏悔仅仅是一种形式包装,其背后隐含的,实际上是坦率的正当性,以及由坦率的正当性所确认的对自我情感的狂纵不法的张扬玩味。他越是把自发的生命冲动界说为圣洁的良心,则接受良心的指引也就越是演化为对道德禁忌,广而言之,对所有社会规范和文明准则的义无返顾的破坏与叛逆。因此,倘用一句话来概括,卢梭所走的道路,本质上乃是一条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以英雄代替上帝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崇拜之路。
正如舍勒分析的那样,卢梭式的文化英雄在蔑视世俗的浅薄的时候,发展出了一种极有深度的骄傲。那是一种唯我独尊且不加收敛的骄傲,骄傲者只围绕自我不停地旋转,而且越转越小,最终割断自己与社会、与传统相联结的一切纽带,成了和世界格格不入的“尘寰逃兵”。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衰微后的世界,在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蔓延后确实显得有些刻板和平庸,做“尘寰逃兵”无疑有它的文化魅力,因为它的神奇,因为它的不平凡。为了追求这种神奇和不平凡,卢梭把揭露自我的阴暗面当作一种向庸俗示威的特殊方式,孤傲得不要伪装,也无力伪装。可是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不要伪装一旦流行起来,成为时尚,就会演变为一种新的虚荣。不仅如此,卢梭所引发的更大的文化震荡,在于他那跟着感觉走的狂放的自我表现,在反理性、反功利、反文明规范的过程中,彻底清除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极力强调的那种对不加约束的自发本能和感性趣味的恐惧,从而开辟了一条寻觅新奇、不断探索经验边疆的宽敞大道。沿着这条大道迅跑,很快涌现出一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他们跟卢梭学会了蔑视习俗束缚,不过已不再像卢梭那样体会到痛苦,而是以极其轻松得意的神态去接受刺激,堂而皇之地将自我经验的怪诞新奇当作了创造性的源泉。时至今日,风俗蛋糕已被打得稀烂,声言要叛逆传统好比是奋力进攻敞开的大门。丹尼尔·贝尔于是提出了他的问题:谁来约束自大狂呢?就像无度开发自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一样,对自我经验边疆的无度开发也会导致道德生态危机。这一点在今天似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以上,我们简略地考察了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重建人文精神的一种努力,一种虽非涵盖全部却很有典型性的努力。但透过这种努力,我们似乎难以就什么是人文精神的问题作正面回答。恰当的提问方式也许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人文精神不应是什么来为人文精神应该是什么划定一个合理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从近代西方文化谈迁中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或可称作“边界意识”或“限度意识”。
1、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意义阐释”,那么这种意义阐释在价值层面应当是普遍主义的。缺乏具有普遍品格的道德律则,一个社会就缺乏将人们持久地聚合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但中世纪宗教传统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即使一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也不能被凝固为组织全社会的唯一模式而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强制推广。否则就是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
2、确认现世感性幸福追求的价值正当性,并通过个人的自主判断来为道德立法确定一个可靠的理性基础,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取得并传诸后人的一项伟大成就。这一成就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人摆脱依附性的不成熟状态,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人的典型品格。但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道德的实在性大多是而且永远是基于习俗和传统的有效性。“道德是在自由中被接受的,但决不是被自身的见解所创造,或者被自身所证明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这意味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组织包括真善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唯一原则和唯一方法并不充分,就像单纯的传统权威作为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和组织方法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一样。倘缺乏这种“边界意识”,则世俗化和理性化进程,便会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狭隘形式上伤害乃至泯灭人的灵性与德性。
3、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危机,一方面与价值理想的意识形态化有关,另一方面更与社会生活的功利化、实用化及所谓“解除魔咒”的理性化趋向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努力,常常采取以个性独立对抗传统权威、以生命情感对抗功用理性的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所谓人文精神的重建,主要就是以这种形式得到理念的表达,并展示其社会批判力量的。但是,一如传统主义和功用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也有它的合理边界。如果逾越这一合理边界,那么它的无度膨胀在政治上就会助长雅各宾专政那样激进的暴力主义;在文化上则会演变为极端反传统、反社会、反文明规范的自恋主义、虚无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恋主义、虚无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在后现代胜利凯旋的大众文化中,已慢慢丧失其表达价值关怀的批判向度,徒留一个反叛的外壳,从而与商业逻辑所支持的消费道德观逐日合流了。这大略是我们今天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所面对并须认真考虑的一个新的生活现实。
标签:帕斯卡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忏悔录论文; 哲学家论文; 思想录论文; 卢梭论文; 伏尔泰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