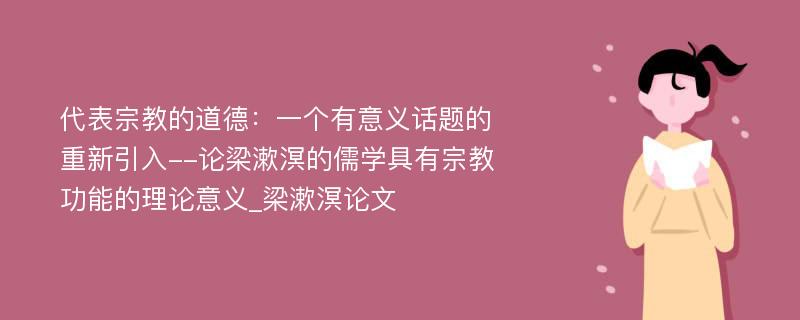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儒学论文,有意义论文,学说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5;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057-06
历史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自己。尽管近来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非常热闹,但严格讲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事实上,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梁漱溟就明确提出了道德代宗教的观点,认为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却具有宗教的作用。本文今天重提这个陈年的话题,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梁漱溟早年提出的这个重要题目。从这一特定视角出发,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于当前这场争论的理解,而且对于儒学的内在价值和重要作用也将会有新的体认。
一
道德代宗教的问题,是梁漱溟在研究中国文化特点时提出来的。
梁漱溟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对各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大致可分为家族本位的社会、个人本位的社会、社会本位的社会和伦理本位的社会。如果说,上古时代宗法社会是家族本位的社会,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本位的社会的话,那么,古代西方则是超越家族的集团社会,而中国则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在进行具体比较的过程中,梁漱溟非常看重宗教的作用,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说:“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由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1](P52-53)这即是说,宗教是文化的精神源头,中西文化差异如此巨大,一个十分重要的起因就是宗教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虽然西方社会自古希腊罗马之后就属于集团生活的社会,但西方社会大的集团生活是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产生后才形成的。这是因为,基督教与旧的宗教精神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从前有多少家邦就有多少神,现在神绝对惟一;第二,基督教主张兼爱同仁,人人以上帝为父,彼此如兄弟;第三,旧的宗教政教不分,而基督教超脱世俗,追求灵魂自由,使政教分离。基督教不仅与旧的宗教有如此多的不同,而且教会势力还特别强大,无论何人均属于教会,都不得叛离教会。教会不仅拥有众多土地,还享有教税,凡教徒均有纳税之义务。因此,中古时期的教会无异于国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和监狱,有定人终身监禁之罪之权,不但执行国家之职务,而且有国家之组织[1](P66)。虽然集团生活在西方的巩固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如需要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需要近代自治城市的兴起,但主要还是依赖教会的作用。教会实为西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由于教会的存在,西方社会成了典型的集团生活的社会。
中国文化自有另外一番情景。梁漱溟指出,中国自先秦周孔教化之后,宗教就失去了主要的市场,因此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明显缺乏集团生活。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在宗教组织中,而中国人的国家也不像国家,国家已经融于社会[1](P72)。虽然中国也有类似于西方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那样的团体组织,但那些组织都没有西方团体那样强烈的团体精神。因此,中西社会之不同,可以说是“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正是分向两方走去,由此开出两种相反的文化”[1](P76)。
中国特别重视家庭,这是梁漱溟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梁漱溟指出,在中国,人一生下来,便与父母、兄弟等相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始终不能离开这种关系。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他写道:“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平素多往返,遇事相扶持,则有乡邻朋友。随一个人年龄与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P81)他进一步解释说,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1](P81-8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认定中国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既有经济上的功能,又有政治上的功能,其在经济上的功能主要是指伦理中的财产共同关系。夫妇、父子、兄弟、亲族之间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遇到困难主要依赖其伦理关系寻求帮助,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总向政府申请救济。其在政治上的功能则表现为家国同构,治国的方案与齐家的方式相同。在中国,人民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间的伦理义务,而没有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团体意识。政治的理想在西方社会主要指社会的福利与进步,在中国则主要指天下太平,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还有宗教的功能,即所谓道德代宗教。梁漱溟认为,伦理并不是宗教。因为任何宗教都是以超越常识为背景的,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追求出世,一心探讨的只是人生的实在问题。诚如梁漱溟所说:“请问:这是什么?这是道德,不是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1](P107-108)但另一方面,周孔教化又具有宗教的功能。在梁漱溟看来,家为中国人生活之源泉,又为其归宿地,其作用相当于宗教。中国人可以从家庭伦理生活中得到一种“人生趣味”。如孟子就提出,人生之乐在于“事亲”、“从兄”等具体的伦理关系中。这也就是俗话所讲的“居家自有天伦之乐”。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天伦之乐,就会感受到莫大的痛苦。
梁漱溟特别强调指出,在中国,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升降,能给予家庭伦理以极大的鼓励作用。一家人(包括成年的儿子和兄弟),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就从这里,人生的意义好像被他们寻得了。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是在共同的努力中,熙熙融融,协力合作,最能使人心境开豁,纵然处境艰难,也会因乐而忘苦。第二,所努力者,不是一己之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或者是光大门庭,显扬父母;或者是继志述事,无坠家声;或者各德各财,以遗子孙。这其中可能意味着严肃、隆重、崇高、正大,随各人学养深浅不同,但至少,在他们都有一种神圣的义务感。第三,同时,在他们面前都有一远景,常常在鼓励他们的工作。当其厌倦于人生之时,总是在这里面(义务感与远景)重新取得活力,而又奋勉下去。每每在家贫业薄、寡母孤儿的境遇,愈自觉他们对于祖宗责任之重,而要努力光复他们的家[1](P87-88)。
总之,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因此具有了宗教的作用,取代了宗教的位置。“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如我夙昔所说,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那么,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1](P88)显然,梁漱溟提出道德代宗教,主要是为了指明儒学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起的宗教性质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梁漱溟看来,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作用是靠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这种作用是由道德承担的。由于这个不同,才导致了中西文化及其社会的根本性差异,即团体精神与伦理本位的对立。
二
梁漱溟提出道德代宗教的问题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它的意义并没有因为时同的久远而消失,反倒越发显得珍贵,在进行中西伦理思想比较,探讨如何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更加突出。
近现代以来,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休谟伦理难题。如所周知,所谓休谟伦理难题即所谓“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休谟指出,他在考察各种道德理论时发现,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判断的系词为“是”与“不是”,道德判断的系词为“应该”与“不应该”,可是人们在按照常规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总是不知不觉改变判断系词的性质,“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2](P509-510)
休谟伦理难题提出之后,哲学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难题,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让哲学界普遍认可的方案。麦金太尔在这个领域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将休谟伦理难题置于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断定休谟伦理难题之所以能够产生,是西方伦理思想拒斥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世纪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家所从事的运动必定要失败。麦金太尔指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一个目的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3](P67)。伦理学就是一门使人们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状态的科学。在这个重要对照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未受教化偶然形成的人性;二是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三是作为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合理的伦理戒律。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要素都必须参照其他要素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其中,第二个要素更是如此,没有它就没有办法保证由第一个要素过渡到第三个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中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被置于神学信仰的框架之中。伦理戒律不仅是理性的要求,同时还上升为神的禁令。在当时“说某人应该做某事也就是说这种行为在这些环境中将导致人的真实目的,同时还是说,这一行为是与神规定的及理性所理解的律法的命令相一致”[3](P69)。在这样一种框架中,神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共同在第二个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教和天主教出现后,理性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怀疑。人们普遍认为,理性只能用来计算,虽然可以确定事实,可以看到数学关系,但在实践领域作用甚微,对于人生的目的无能为力,必须保持沉默。这种变化使神性的地位更加上升了。尽管有了这个变化,但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基本框架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神的力量承担起了由第一要素向第三要素过渡的“教导者”[3](P69)。
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时代之后,人们既放弃了新教和天主教,也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取消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第二个要素,使得三大要素不再完整:一方面是一组光秃秃的道德禁令,另一方面是未受教化的人性,其间没有任何的“教导者”。这种改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道德哲学家们既放弃了原先较为完整的人性理论,又要为道德律令寻找合理的基础,使他们的人性观念与他们所追求的道德律令“从产生之时起就预先注定不相符合”[3](P71)。
这种理论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哲学家们往往看不到由于第二要素缺失所造成的理论困难。当然也有例外,狄德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狄德罗去世后发表的《拉摩的侄儿》来看,他对18世纪道德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力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康德则更进了一步,他一方面批评将道德置于人性基础上,希望以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一个尾巴,承认没有一个目的论的构架,整个道德就无法理解,并把这种框架表述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决条件”。过去人们总是以为,这个尾巴是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但实际上这里隐藏着重大的理论玄机。18世纪的道德确实是以神、自由、幸福为内容的目的论体系为前提条件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将道德与这一构架分开,你就失去了道德;至少也得说,你就极大地改变了道德的特性。”[3](P72)对于康德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第二要素在道德理论体系中是多么的重要。
理论的这种缺失直接导致了“是”与“应该”的分裂。人们开始相信,从纯粹事实性的前提中得不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休谟开始表述这一观点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和缓。到了康德那里,则断然否定从任何关于人的幸福或上帝意志的陈述中可以推出关于道德律法的命令。其后的哲学家走得更远,坚持认定在一个正确有效的论证中、结论中不能出现任何前提中没有包含的东西,任何企图从事实前提出推出道德或评价性结论的论证,必然是虚假的,不成功的。这个转化是致命性的,因为一旦接受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便会成为他们整个运动的墓志铭”[3](P72)。
通过简要回顾麦金太尔关于休谟伦理难题的论述,我们不难了解到,麦金太尔看待休谟伦理难题的方法,是非常有特点的。他不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将其置于西方伦理思想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通过对前亚里士多德传统到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世纪传统、理性主义传统发展历程的考察,人们发现,无论是在前亚里士多德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还是中世纪传统中,所谓“是”与“应该”的矛盾并不存在。理性主义之后,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理性主义拒斥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体系中原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这个内容不管是以神性的形式还是以理性的形式出现,都是不可或缺的,是保证第一要素向第三要素过渡的重要力量。但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放弃了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这个重要内容,使第一要素无法过渡到第三要素。正是这个变化,宣告了他们从事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休谟提出“是”无法过渡到“应该”的难题,不过是这种失败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麦金太尔的论述对今人有很大的启发,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完整的伦理学说必须有一个形上的根据。这个形上的根据在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目的论的体系,在中世纪是一个宗教神学的体系。不管是目的论的体系,还是宗教神学的体系,或者是以宗教神学代替目的论的体系,这个根据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发展,这个形上根据逐渐失去它的地位,理论家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理性之上。然而理性,不管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不是最后的,都无法代替那个最后的形上根据,没有这个形上的根据,也就无法解决人为什么必须行善,以及认识到道德法则后为什么必须依此而行的问题。休谟伦理难题就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休谟看到理性没有任何兴发力,不能直接产生一个善,所以,才将道德的根据置于情感之上。康德在伦理学上完成了由他律到自律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仍然无法回答人为何对道德法则感兴趣一类的问题,所以不得不为上帝保留了一席之地。康德的这个思想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由于人们不能理解康德的苦衷,同时,也是由于康德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康德的理性主义受到了后人的扬弃,纷纷由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于是,非理性主义之风大盛,成为近代伦理学的根本特点。但是,由于非理性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否定了道德的最后根据,使道德完全归属于情感,所以也不能解决体谟伦理难题,只能沿着这个方面走得更远。
三
再将视线转向中国。对此我们不难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休谟伦理难题在中国不存在呢?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回答:一是中国哲学远没有西方哲学发达,所以还提不出此类的问题;二是中国哲学中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使这类问题不可能存在。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答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在中国哲学中不曾提出来,是两条不同的思路使然,不存在何者发达何者落后的问题。而西方哲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市场,引不起共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特质,使其具有了天然的免疫力的缘故。
在这方面,梁漱溟关于道德代宗教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路。按照梁漱溟的看法,中西文化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路子,西方文化中宗教的作用极为重要,直接决定了其文化的性质,而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发挥作用的是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虽然梁漱溟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对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比较,但他也告诉我们,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是以道德来代替的,所以,在西方哲学中依靠宗教才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直接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解决了。换句话说,中国并不需要一个宗教的神学体系也能够使它的伦理学说达致圆满。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是因为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特别重视理性。理性是梁漱溟非常看重的一个概念。如所周知,梁漱溟所谓的理性,“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1](P123)。这与学术界通常的含义不同。在此基础上,梁漱溟专门把理性与理智区分开来。他说:“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日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数目算错了,不容自昧,就是一极有力的感情,这一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什么生活问题。分析、计算、假设、推理……理智之用无穷,而独不作主张,作主张的是理性。理性之取舍不一,而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1](P125-126)又说:“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1](P128)显然,在梁漱溟看来,理智与理性完全不同,理性高于理智,是人类的特征所在,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以理智为人类的特征,未若以理性当之之深切着明,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1](P126)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理性,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向上心特别强烈。梁漱溟这样写道:“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1](P132-133)何谓向上心?他进一步解释说:“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1](P133)“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1](P134)“唯此所谓‘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其理存在于我与人世相关系之上,‘看到’即看到我在此应如何;‘向上实践’即看到而力行之。念念不离当下,唯义所在,无所取求。”[1](P134-135)梁漱溟的这一思想是大有深意的。“理存在于我与人世相关系之上”,是说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看到’即看到我在此应如何”,是说我认识到了这个理,就应当如此行为;“‘向上实践’即看到而力行之”,是说依理而行,是一种自觉的向上实践活动,有了这种自觉的向上实践活动便能够知行为一了。在中国,从来不存在西方哲学中诸如人为什么向善,人认识到了善的事物之后为什么必须依此而行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说明问题,笔者不妨举一个例子。麦金太尔认为,西方哲学存在“是”与“应该”的分裂,一个重要原因是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功能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功能性概念是很重要的。说某物或某人是好的,也就是意味着这种物或这种人符合其特有的功能。这种理论在现实中是很好理解的。比如,从“这块表走得不准且不稳定”和“这块表重得不好携带”这类事实前提中,可以正确地得出“这是一块坏表”的结论。这种理论对于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生活好,做一个好人,如果这个基点确立不下来,整个道德理论就无从谈起了。“这种用法实际上植根于古典的传统理论家们所要表述的社会生活形式。这是因为,根据这一传统,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扮演一组角色,其中每一个角色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目的:家庭成员、公民、战士、哲学家、上帝的仆人等等。只有在把人视为先于和分离于这全部角色的独立个体时,才可能不再把‘人’作为功能性概念。”[3](P75)古典传统道德理论之所以较为健全,之所以没有产生“是”与“应该”的分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基点是牢不可破的。
这种理论与儒家哲学非常相似。儒家哲学的主旨是教导人如何做人。正如梁漱溟所说,“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作人’”[1](P119)。而在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一个完满的人格,就是“孝子”、“慈父”。“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何谓好父亲?常以儿子为重的,就是好父亲。何谓好儿子,常以父亲为重的,就是好儿子。”[1](P90)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做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根本不存在我明知好父亲、好儿子的标准,却不依此而行,反倒质问“我为什么非要如此”等一类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完全在于其重视理性。梁漱溟以下论述是值得深刻理解的。他说:“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唯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外是而求之,无有也已!”[1](P137)由此可知,理性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大体相当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虽然由理性开出的是道德,由宗教开出的是神学,但二者的作用却是一样的,即所谓“宗教道德二者,对个人,都是要人向上迁善”[1](P108)。中国人将理性视为“天之所与我者”,意即这是最后的,是完成道德的最终根据。由于具有这个根据,尽管宗教在中国文化中没有重要位置,却也不会出现如西方那种“是”与“应该”分裂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梁漱溟所说的理性在道德代宗教的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道德代宗教,其实就是梁漱溟意义上的“理性”代宗教。理性是人类的特征,每个人都属于人类的一员,都具有理性。有了理性,人们就具有了一种自然“向上实践”的动力,通过理智“看到”即认识到客观存在之理之后而“力行之”。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自然的向上动力,凡是认识到正确的事物,都必须自觉去实行。在西方,这种向上的动力是在目的论体系,或神学体系,或两者兼而有之,以神学体系代替的目的论体系中存在的。当这种体系由于种种原因被打破后,必然产生休谟伦理难题,产生“是”与“应该”的分裂。而在中国,这种理性是自周孔教化而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国哲学从来不存在休谟伦理难题,相反总是认为,凡是认识到的正确的事物就必须自觉去做,由“是”必须上升到“应该”,甚至“是”本身就是“应该”,道理就在于此。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是本文对梁漱溟所说而作的一点儿借题发挥。事实上,梁漱溟所关心的主要是文化比较的问题,休谟伦理难题完全是在其视野之外的。不仅如此,梁漱溟还把理性完全解释为一种道德情感,没有能够真正回答理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环极为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道德如何能够代替宗教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些显然都是梁漱溟的不足。但是,梁漱溟毕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完全可能开辟一个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笔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这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与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理论结构不同,儒家道德哲学可分为欲性、智性、仁性三个层面,其中欲性大致相当于(并非完全等同)西方哲学的感性,智性大致相当于(同样并非完全等同)西方哲学的理性,中国哲学最特殊、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多了一个仁性。所谓仁性,就是孔子的仁,就是孟子的良心,就是陆王的心学。由于有了仁性,人们就有了一种自然向上的力量。凡是认识到正确的自然就会行,凡是认识到错误的自然就会止,而不会出现知之不行的情况,否则就会有愧于心。欲性、智性、仁性虽然是笔者的一种新提法[4][5],但一些重要的要素,前人早已提出来了。其中,梁漱溟特别强调的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大致即相当于笔者所说的仁性。梁漱溟所说的道德代宗教,其实就是理性代宗教,而理性代宗教,其实就是仁性代宗教。有了作为理性的仁性,中国人不需要西方哲学的目的论体系或神学体系,本身就有一种自然向上实践的不懈动力,就有一种知之必行的力量。这种动力和力量,远比康德将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归之于“敬重”有力得多,深刻得多。这正是休谟伦理难题在中国没有市场,儒学家很少提出“理性本身如何是实践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3-03-26
标签:梁漱溟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宗教论文; 道德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休谟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目的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