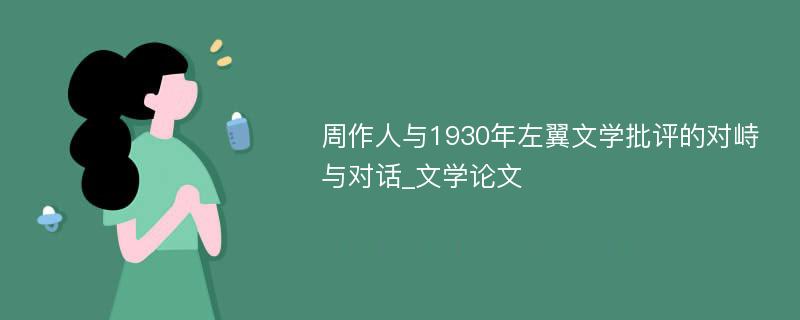
周作人与1930年左翼文学批评的对峙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左翼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0年3月的北平《新晨报副刊》上,刊登了黎锦明的一封信《致周作人先生函》①,过了不久,周作人的回信也在该刊发表。②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两封信由此引发了长达两个多月③对周作人“环而攻之”④的文坛“波澜”⑤,这让人不禁好奇黎锦明那封“肇端”④惹祸的信究竟说了些什么。原来,他向周作人抱怨了对革命文学独霸文坛的不满,他认为一些革命文学家们只要头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便可以让人仰视敬畏,而文坛中的其他人只好陷入“无意义的沉默”,他盼望周作人能够出来“主持”、“打破”这种众人缄口而革命文学独行其道的局面。
应当说,黎锦明的看法其实也是当时文坛中许多人的普遍观感,进入30年代后,左翼文学以其凌厉的攻势、霸道的话语权,占据了文坛的大小阵地,几乎对所有人都构成了“惘惘的威胁”⑦。一度的潮流中人郁达夫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文艺界“简直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⑧,“百鬼夜行,无恶不作”⑨。而置身事外的张爱玲也曾批评左翼文学“有太多的偏见和小心眼”以及“单调的洋八股”⑩,指出的也正是左翼文学在观念与手法上的种种偏颇。左翼文学的异峰突起,无疑带给30年代文坛的其他势力很大压力,然而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这种压力最终又产生怎样的结果,还需引起我们更多关注。
事实上,周氏兄弟与左翼文学的相遇历程均不顺当:有关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已被学界公认为一个复杂的命题;而关于周作人与左翼话语的对峙与对话,却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由此,重新思索黎锦明向周作人抛出的这一话题便很有意思,黎锦明无意之中是将周作人推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风口浪尖。更值得深究的是,在周作人此后的散文创作和文学思想中,可以捕捉到这场批评留下的潜在痕迹。两明(11)通信所引发的争端及其对于周作人的影响,实际上正是解读左翼文学与1930年代文学关系的一个颇具价值的个案,因此值得详加探讨。
一 “大黑狼”与“中山狼”
面对黎锦明的提问,周作人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他将回信题目标为“半封回信”,即只对黎锦明所提的译法问题作答,而对革命文学话题则宣布“告假”:因为觉得“自己不是文士”,“不配”对这个问题多嘴。尽管宣告抽身事外,却又在寥寥数语中流露出一种冷眼旁观的简傲姿态,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左翼文学青年的不快。然而,招致这些青年更大反感的是,宣布“告假”之后的周作人仍然不吐不快,又将对当时文坛的“许多意见”概括成三点:
(1)文学有言志与载道两派,互相反动,永远没有正统。(2)文学没有什么煽动的能力。(3)文士的职业是资本主义的私生儿,在合理的社会人人应有正当的职业,而以文学为其表现情意之具,有如写信谈话一样,这就是说至少要与利得离开。现今文学的堕落和危机,无论是革命的或非革命的,都在于他的营业化,这是落到了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了,再也爬不上来。(12)
这里,已然呈现出周作人两年后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核心论点:言志与载道为文学史上互相起伏的两大潮流。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现代作家的个性,比从前任何时代的作品都更加强烈,(13)那么相对于这种以个性化“言志”为特征的“五四”文学来说,左翼文学无疑是“载道”的。左翼文学的狂飙突起,在周作人看来与历史上任何一次载道文学的兴起一样,仅仅是潮起潮落的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浪花,随时有可能被淹没。这一点表面看来是在谈论文学史的潮流更替,实际上是隐晦地批评了左翼文学的显赫地位不过与历史上任何一种暂时占据主潮的文学样式一样,不值得惊异与瞩目。如果说第一点的讽刺意味还相当隐晦的话,那么第二、三点则直接针对左翼文学将文学工具化、宣传化提出了批评。周作人强调文学是超功利的,不具备“煽动”性,这便与当时左翼文学着力凸显的文学具有煽动力的观点俨然唱成反调。他进而批评左翼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指出其中媚俗、吸引大众眼球的因素,而这也正揭示一些靠商业因素立足的左翼作品的畅销奥秘。
周作人从文学史的长时段脉络和纯文学视角评点左翼文学的是与非,其观点可圈可点、具有丰富的探讨价值,然而却不幸成为左翼文学批评的众矢之的——《半封回信》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成为左翼青年的批评对象。事实上,“意气用事”(14)和抓住“枝节问题”(15)大做文章的方式正是这些攻击文字的重要特点(16)。这一点就连后来继承了这一批评周作人话题的日报《民言》也有所反省,认为这种现象是“为半句话打好几篇的无味笔墨官司”(17)。此时,曾经“五四”时期的 “岂明我师”已然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青年的开火对象。
曾有论者将当时的文坛情形比喻成民初政局:就好像戊戌时被守旧派目为洪水猛兽的康梁,民国后则被斥为昏庸腐朽,现今“十年前文学革命运动时代的健将”如今也被当做攻击鹄的,攻击者们也就此一笔抹去了他们“光荣的历史”。现今左翼文学有意无意地忽视贬低“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以实现自我标榜的潜在目的,在让人感叹“时代奔跑得竟如此的快”(18)之时,也昭示出这种批评本身便带有明显的“文坛政治”的话语背景。借助着革命文学已然降临的风云际会,左翼文学者们大胆宣布“在这个旧的时代还未毁灭以前”,“绝对不让反革命的著作者站在文坛上”(19),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他们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对周作人的社会属性进行剖析,将周作人与鲁迅一道视做“旧文坛的权威者”(20),其地位在时代洪流冲击下产生根本动摇是势所必然。他们甚至用居高临下,让人很难接受的口吻,宣布周作人“必然被新的机构所否定,所遗弃,似不幸又似命定的趋于死亡的没落”(21),这类用语自然引起了周作人与其苦雨斋弟子的强烈反感。即便是持有温和论调批评者,一方面认为不宜全盘否定周作人,另一方面也提出周作人确也“不配作革命潮流中的新文艺中的威权者”(22),因为“文艺的时代性”要求,周作人那种充满“闲情逸致地逍遥在‘象牙之塔’的苦雨斋里说趣话”的姿态,无法为时代潮流所“激荡”,更无法代表一时代之文学。
在这些攻击中,以一位名叫谷万川的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批评最为激烈。谷万川与周作人绝非素不相识:早在1925年,谷万川便深受周作人民俗学研究兴趣的影响,《语丝》上曾刊有二人关于搜集整理大黑狼民间故事的通信。(23)后来谷万川的《大黑狼的故事》经周作人推荐由北新书局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说谷万川蒙受过周作人的提携实不为过。
其实,在周作人的《大黑狼的故事序》中,可见周作人曾对具有整理民间文学兴趣的谷万川寄予希望:虽然看到了谷万川从南方参加革命归来后,对文学的感情明显变淡,却仍然劝其下定决心来“干这不革命的文学或其他学问”,“回转来弄那不革命的文学”(24)。然而,一厢情愿的周作人并不知晓,自己一再宣布“文学本来是不革命”(25)的观点,早已与昔日爱徒嫌隙渐生。此篇序言中流露出的这种对革命文学的调侃态度,或许也正埋下了与这位左翼文学青年的结怨伏笔。1930年初革命文学狂飙突起的锋锐势头,与谷万川自身的愤激性格相结合,他决定抓住这位“五四”文学元老在《半封回信》中对革命文学不够恭敬的“弱点”进行攻击。4月15号,《新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谷万川第一篇批评周作人的文章《文学果无“煽动能力”耶?》(26),讥讽周作人自取其辱:“如果不坐在象牙塔尖的棉花包上懒洋洋地说风凉话,谁也不来惹你。”(27)但是真正刺激谷万川的,恐怕还是黎锦明《致周作人先生函》中希望周作人能出来“主持”文坛局面的提议,他由此尖酸地讽刺道:“在你‘周某’尚未被选为‘中国读书界全权代表之先’”,所谓文学没有煽动力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在他看来,周作人一边拿着版税,一边却又批评左翼文学的营业化,这本身是充满悖论与讽刺意味的。
对于恩将仇报的后生晚辈,周作人的态度有可能是翻脸无情的。人们会油然想到40年代“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攻击周作人时,周作人曾经公开发表“破门声明”将其逐出师门。直至1961年,周作人还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将沈启无称为:“十足之‘中山狼’”(28),似乎犹未解恨。相比较而言,周作人对谷万川的态度显得相当和缓,甚至一直避让三分。同样是“中山狼”式的行为,周作人为何采取截然有别的处理方式呢?当然,对于类似左翼视角的批评,周作人将其一律视为“谩骂”(29)文字而不予理睬,似乎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然而事情仅仅就这样简单吗?
可以看到,周作人很早就理解谷万川对自己的攻击,并非简单的“中山狼”式的个人恩怨,而是其所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对“五四”文坛权威的非议与否定。如果不借助左翼思潮异军突起的力量,谷万川等人恐怕还只是跟随周作人的学术趣味、继续搜集“大黑狼”民间故事的无名小卒。然而崭新文学时代既已大幕开启,谷万川这样的文学青年就必须抓紧机遇,利用革命文学的话语锋芒,毫不留情地批驳并放大周作人的种种“落伍”言论,用一轮新日照射并显出前朝文坛耆宿的老迈身影,抢占文坛的新锐地位。因此,看到这一点的周作人对于谷万川个人的发难采取避让态度;但是,对于这种攻击背后所体现的两个文学时代的交接与交锋,周作人却是有话要说的。实际上,周作人的回应方式正是相当高明、隐晦而又耐人捉摸的。
二 “草木虫鱼”:被误解的“讥嘲”
4月17日的天津《益世报副刊》上,人们读到了周作人一篇风格独特的散文《金鱼》(30),其中的戏拟手法与讽刺笔调引起了左翼文学青年们的更大愤怒。此文妙趣横生,充分展现了周作人的幽默才华,然而形容叭儿狗“鼻子尤其耸得难过”,鹦鹉则“身上穿着大红大绿,满口怪声,很有野蛮气”等处,虽然感染得读者会心而笑,却又难免惹人猜想背后是否确有所指。让人心生疑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鱼》篇末未署写作日期,从发表日期上来看,《金鱼》的浮现,正好是针对谷万川在4月15日《新晨报副刊》上《文学果无“煽动能力”耶?》的反唇相讥。于是,谷万川立即写了《答复周岂明先生》(31)给予回击,将《金鱼》当做一则爱罗先珂式的童话寓言来解读(32),斥责周作人为“鱼缸文学的权威者”,竭力丑化周作人的形象,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33)
但仔细追究,却会发现谷万川与周作人在论点上存在着扞格不通的隔膜:即在文章用语、意象寓意等枝节问题上,谷万川保持了高度的敏锐,但对于《金鱼》中真正想要表达的精粹主旨却漠然视之。实际上,《金鱼》主要是借金鱼类似小脚女子的外形来批判丑陋野蛮的缠足现象,呼应了周作人一贯的“天足”观。如果联系1921年的《天足》中周作人讲述过的一个“文明古国的新青年”每每因为缠足女子的存在,而“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的离奇故事,便会发现几乎十年后,《金鱼》对于“缠足”的反感和反思,仿佛正是一席谈话的上下篇。(34)然而看到这一点的谷万川却用“倒觉得无关紧要”(35)将其轻轻掠过,这其实是颇为遗憾的。
读到了谷万川的《答复周岂明先生》之后,周作人很快发表声明,表示《金鱼》作于3月11日,并非是“答复贵刊批评”,而如果“有人误会系答复贵刊批评而作,与事实不合”(36)。不难看出,周作人始终否认《金鱼》是对于左翼文学批评的回应之作,结合其中的反缠足意旨,可以说自有其道理。然而客观上,此文笔法却又存在着让人想象的索隐空间。作者有意识地将金鱼与缠足女子合而为一,甚至是故意混同化、模糊化,把缠足现象化身金鱼实物,将沉重命题变幻为生物百态,抓住喻体来尽情舒展其生花妙笔,在一种轻灵而不胶着的气氛中嬉笑讽刺。这或许正是《金鱼》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金鱼云云都是虚化,其间隐喻浮现的世相百态才是实景。正是由于能将“草木虫鱼”之类拟人化,又将人情世景拟物化,才使得文章在一种举重若轻的氛围中实现话题流转。然而,也恰好是这种拟人与拟物的交相叠加,使读者往往能从喻体背后读解出超乎文本“所指”之外的图景。就周作人的本意,是试图通过众多喻体来指向所要表达的命题,但喻体的择取本身却又让人产生遐想。因为这些喻体本身往往具有约定俗成的含义,而这些含义足以对左翼批评者们构成挑战。然而周作人所看重的又恰恰不是这些寻常意蕴,而是自出机杼地在其间附加了崭新含义,以至于左翼批评家们的解读与周作人的指向之间终成南辕北辙。至于周作人是否同时也看到了喻体本身具有的讽刺意义,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让周作人招致谤声的深层原因,也正在于他在喻体双重含义(本义与周作人式的引申义)把握上的某种自信,他自认为在喻体本义上稍稍滑过而略涉讽刺不至于引来如此麻烦,读者自然会被引入文章的真正主题,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对于这一点,周作人本来已经心存警惕。例如《金鱼》中不乏那种不时冒出的自我调侃,而这正透露出作者是时时意识到阅读对象存在的,而自己的言说随时存在被曲解、被误读的可能。但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左翼批评者的敏感与误读程度均出人意表。
由《金鱼》而引发一场风波,其深层背景更源自1930年左翼文学青年周作人观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进入30年代,左翼青年开始对周作人持续思考的“五四”命题渐渐隔膜。有论者就曾对周作人的时事观感中所得出的历史循环论和悲凉感表示不屑,认为这不过是周作人“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无稽的谣言”而“引为不平”;对周氏的反封建命题更是存在巨大的理解误差,把周作人独特而犀利的女性论题视作“谈谈‘女裤心理’”(37)的消闲之举,认为根本不足为道。虽然在普遍的误读中,不乏有人看到了周作人“清淡的小品文”正蕴涵着“反抗精神”,“悠闲”外表之下藏着“讥嘲的话头”,借用周作人自己的话,便是虽然“富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38)但相对而言,真正的知音解人太过稀少,占据左翼文学周作人观主流的,仍是与批评对象不在一个对手级别上的随心指责。
例如当有论者提出像《达生编》《戒淫宝训》《太上感应篇》这类地摊书根本不该被购入北大图书馆时,周作人便写了《拥护达生编等》一文(39)故意与其唱起了反调:主张这类书不但应该购买,而且还应“尽量地多收,留作特种重要研究的资料”(40)。尽管是唱反调,但此文却体现了周作人观照中国文化时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从代表的最高成绩看去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从全体的平均成绩著眼,所见应比较地更近于真相”,《达生编》等因浓缩了“种种民间的思想与习惯”,从而更能“得到国民思想的真相”。这一观点,虽然令反对者也不得不赞赏其见解独到,但其深刻之处却很难为时人充分领会。
瑶君很快便做了一篇驳论文字,认为周作人是以“廿世纪思想界崭新的人物”而“拥护二千年前善恶报应”,明显曲解了周作人立论的出发点;他更径直言明周作人所谓考察中国文化的方法其实早已过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早已“人心大变”,这类书“几乎全打倒了,除了乡窝里的老太婆,及借此化缘的游方道士而外,谁也不看”(41)。这其实是贬低或忽视了周作人历史观中“恒常性”的独特价值,而这正是对瑶君那种直线演进的历史观的清醒反思,相形之下,瑶君的肤浅之处显而易见。其实,就在瑶君斥责周作人的过程中,更多表现的反倒是作者本人的困惑不解:在他看来,专讲产科分娩的《达生编》、宣扬禁欲的《文昌帝君戒淫宝训》与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不可能兼而提倡,殊不知这些表面看来甚为驳杂的读物在周作人那里都有可能被转化为探讨国民心理的上佳素材,瑶君所谓“觉得有点矛盾”的观感,实际上正暴露出左翼青年在批评周作人时的生涩与怯场。尽管观点上无法势均力敌,但言语间的冷嘲热讽却程度不弱。然而明嘲暗讽之间,种种误会与偏见背后的深厚隔膜均令人感叹。
可以说从《金鱼》开始,周作人的许多文章均引起左翼文学青年的一片哗然。5月12日《骆驼草》上刊载的《水里的东西》(42),周作人声明旨在“讲河水鬼的信仰”(43),引起读者对民俗学的兴趣,而谭丕谟却将其解读为一篇“充满冷箭暗刃”的讽刺之文,认定河水鬼背后确有所指;并从艺术“观念形态”上,宣判了这种“离大众太远”的作品不是“大众所能鉴赏”、是十分“错误”的。(44)周作人对此的反应自然相当不快:
先生们大约有时候求之过深,以为里边一定有什么讽刺,反而觉得看不明白了。我如要骂人,也会明白地骂,何必那样地指桑骂槐,借了什么金鱼啦河水鬼啦来胡说一番,不但气闷,也实在拙笨卑劣,乡曲自好者不为,我也何至于此呢?(45)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金鱼》还是《水里的东西》,虽然不乏意识到言说对象存在的紧张感与淡淡讽刺,但究其本意,却并非简单“指桑骂槐”、仓促应战的急就章,反倒是篇篇收集的精工之作。周作人自认不屑采用如此拙笨手段却频遭误解,但为自己辩解时却又必须保持“其温如玉”的君子风度,但其内心却很难波澜不起。
其实,就在抨击周作人的同时,左翼青年们也不得不承认周作人文章的“美妙与自然”,“一样的意思,经过他的笔底,总是分外有味”(46)。可以说,无论在学识涵养、语言技巧还是表达方式上,双方均不在同一层次。因此,这场一开始便不在同一水平线的交锋与对话,注定会呈现一方优势渐显的局面。左翼批评尽可能抓住了周作人不合时宜之处进行挖苦嘲弄,但在周作人却恰恰是一种明知故犯:他往往有意制造一些乖违常理的话题,预料会引发争议却并无畏惧,理由正是因此招来的指责刚好更充分暴露出对手弱点。
三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5月19日周作人发表《论八股文》(47),这是一篇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但却是真正“回敬”左翼批评的文章。或许正如周作人所料,左翼批评家对此文的反应完全不得要领:先是纳闷“《论八股文》做甚”,进而含糊其词地斥其为“一个复古的废物老人”所提出的“复古”(48)主张,对其中明显有意为之的逻辑混乱既无法视而不见、也无力做出解释。倒是《骆驼草》周刊的普通读者直言此文让人“难于捉摸”(49),恳请周作人能做些解释。对此,周作人故意模仿左翼文学中流行的新文艺腔回答说:“我真忧愁,我的文章使读者闷损,特别是诚恳如先生的也觉得意思不明。”(50)用游戏笔调婉讽左翼文学的同时,也流露出知音稀寡的喟叹。
也难怪各派读者感叹《论八股文》“好教人闷煞哉”(51),每当周作人郑重其事宣布“八股文的势力配天地而贯古今”(52)、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四时,就难免让人咀嚼这一说法背后的“反话和讽刺”(54)究竟占几成。实际上,周作人突如其来论起了八股,其针对当下文坛的批评意味其实要大于历史梳理的兴趣。他对于中国人奴隶根性的解析“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其实是暗指左翼文学大量生搬外来理论术语、借此横加讨伐文坛前辈的现象。所谓八股文“就是在今日也还完全支配着中国的人心”,八股精神甚至“在那些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心里还是活着”,中国的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夺舍投胎地复活着”,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左翼青年所秉承的精神遗传与历史渊源,而理论皈依则又指向其独特的历史循环论思想。
尽管周作人在对左翼文学的婉转批评中,采取了一种正反相参的言说策略:即在表面一再声明不过就事论事、“岂敢另有他意”(55),实质却用考镜历史的方式顾左右而言他,剖析左翼文学里浸濡的八股气息;但相形之下,“四大弟子”中的俞平伯表达方式要痛快得多。就在周作人对《论八股文》进行说明后不久,俞平伯便对“普罗文学家”的周作人批评做了正面回应。(56)俞平伯深知此文作于“多事之秋”,一定会引起更多责难,但仍然勇敢站出来回护本师。在俞平伯看来,当时理论大于作品、“只管搬弄‘某基’‘某夫’苏式人名,和布尔乔普罗利他等等空名词,来朦混人嚇唬人”的左翼文学与批评,本身便充斥着八股旧痕。针对傅非白的《鲁迅与周作人》(57),俞平伯特意指出“恕我又要不敬,做什么哥哥弟弟的截搭题,正是老牌的宗法和封建,正应该是八股文研究中的一种”(58),这等于是明白宣告了周作人《论八股文》背后确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俞平伯的论述中充满了“我们”与“你们”的对峙感,隐约显露出后来以周作人为首的京派文人与左翼文学间的畛域分明。
这篇《论八股文》后来被作为附录收入周作人两年后的著名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此篇演讲有专章涉及八股文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便再次启人思索周作人究竟是基于何种语境来叙述新文学的源与流。而联系1930年左翼文学对周作人的批评,就会看到周氏讲史原来有着丰厚的话题背景。事实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感与对话动机,左翼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很大程度刺激了周作人探索现代中国的八股余脉。虽然此篇演讲呈现出的核心观点乃是新文学的源头须得追溯明末小品,但就周作人的讲述动机来说却恰好本末倒置。所谓“言志”与“载道”此消彼长的文学史线索,并将八股文列为“五四”文学革命前夕的“反动”之一,实际上是在叙写一个有关30年代文坛的史前故事。身处1932年的周作人,虽然浓墨重彩地敷衍出新文学之“源”而未及其“流”,但他对于当下文坛变迁的观照却浓缩在这篇包裹在历史叙述外表下的《论八股文》中。(59)在当时背景下重提八股文,并非是从明末以来的文学史中清点出新文学的道路,而是为1930年的左翼文学寻根问祖、找寻其“载道”源头,就这一点来说其目光不可谓不深邃。在给胡适信的中周作人曾说:
春间在辅仁讲演,学生录稿付刊,不久可成,当呈请教正,题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大旨是表彰公安竟陵派,“但恨多谬误”,尚望叱正者也。(60)
他引用陶潜《饮酒》组诗最末一首中的句子:“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是诗人借酒抒怀,以酒中写诗难免会说醉话、恳请听者多加宽容的总结句。周作人这里借陶诗自明心迹,表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表彰公安竟陵而贬低八股,实际上有着以讲史为契机,批评左翼文学的八股气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拨的潜在意图。酒之于陶渊明与讲史之于周作人一样,均不乏借题发挥的成分,由此反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氏的褒贬抑扬,或许更能贴合论者原意。
事实上,追踪现代文坛的八股遗风,一直被周作人当做一个颇为得意的发现,在其后的多篇文章中,他均以此为视角或显或隐地对左翼文学进行解剖,《骆驼草》也由此成为周作人集中抒发此类婉讽的空间。例如《介绍政治工作》(61)便是一篇表面几乎看不到破绽(62)、实际上却异常尖锐的文章。此文中周作人将何容所著的《政治工作大纲》一书奉为“近来少有的好书”,并说自己是“一拿到手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一行跳过不读”,理由则是周作人自己曾有过编纂类似读物的打算:
老实说,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计画,想编一部完全的“宣传大全”,内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等门,人物门中按照百家姓,以人为纲,划分拥护打倒两目,将某人的同一事件,依照拥打两种场合,拟成适当文句,分别登录,以备临时应用。这部大全如能编印成功,生意一定不会差,只可惜工程浩大,而且泄尽人天奥妙,恐遭造物之忌,也不很好,所以就搁下了。现在何君《大纲》出来,略可补此缺恨,自然是很好的……(63)
这让人自然联想到左翼文学横扫现代文坛时那种“为文造辞”的批评套路,即预先定好批评论调,对于同一人事的臧否,不过是依据相应格式的填词造句。拥护与打倒的具体理由并不重要,事先设定的基调态度便决定一切。《政治工作大纲》共分“标语”、“口号”、“传单”等十章,这与一位青年批评黎锦明时提出的“革命文学不外是宣传,毋须具有真实的生命”(64)的观点异曲同工。过了没多久,周作人便对此有了补充说明:“中国人之善于做应制文诗,章奏状词,传单揭帖等,截至民国十九年止,至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了。”(65)从而明明白白将以“宣传”为重要特征的左翼文学归人了“古以有之”的载道文学一脉。
进而,周作人又揭示出八股文老妖不死的奥秘缘于汉字的特殊性(66),格外提出“文字在中国”别有“一种魔力”(67)。这一对东方文化中注重文字魔力的重要发现,使得周作人将左翼思潮对于口号、标语、命令的重视,视做“近于符咒”的“东方文化的把戏”(68)。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使他能够用一种更为洒脱的态度应对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之词:“我用了耳朵眼睛看见听见人家口头或纸上费尽心血地相骂,好像是见了道士身穿八卦衣手执七星木剑划破纸糊的酆都城,或是老太婆替失恋的女郎作法,孥了七支绣花针去刺草人的五官四体,常觉得有点忍俊不禁。”(69)一度被卷入波澜中的周作人,在怒波渐息之时,更多获得的却是因祸得福的从容不迫与难得启示。
结语:闯祸“得来的益处”
其实早在《金鱼》中,周作人由金鱼微物而钩连出缠足话题,采取了信手拈题、作赋得文字的方式,无疑是一种富有试验意味的创制。虽然文末提出这种“少言志而多载道”近于帖括之文,语含对左翼文学的讥刺意味,被未能辨明此中真意的谷万川斥作这种“口口声声”的强调“像个穿大红大绿的‘鹦鹉’”般让人生厌。(70)然而,正是这种对“赋得”文字的戏仿本身,却使周作人在这个“不是写字的年头儿”(71)、言说空间渐次逼仄之际,意外挖掘到了丰厚的写作源泉。他后来曾庆幸地说:《金鱼》使他“几乎闯了祸,这固然是晦气,但是从这里得来的益处却也并不是没有”。(72)事实上,进入30年代以后周作人开始反思胡适文学革命时期的著名观点:“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73)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大压力,早早就被宣判“没落”的周作人陷入了“实在无从说起”的困扰中。然而“草木虫鱼”的题材实验,却使其从“无一可言”(74)的表述困境走入“无一不可言” 的海阔天空。以《金鱼》为起点,1930年的周作人接连写作了《虱子》《水里的东西》《关于蝙蝠》《小引》《案山子》《苋菜梗》《两株树》等七篇文章,这便是收入《看云集》时的一组总题为《草木虫鱼》的散文。到了40年代,周作人还有“续草木虫鱼”的打算,又写了《蚯蚓》《萤火》《关于红姑娘》,可谓乐此不疲。直至晚年,周作人始终对“草木虫鱼”之类的题材保持浓厚兴趣。可以说,从《金鱼》开始,周作人不仅是找到了一类素材,更是寻觅到了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任何微小普通的题材都可以被周作人延展、钩连,进入其一贯的启蒙命题中来,从而做到无论写什么都有周作人式的独特观照。难怪后来曾有论者指出这种“从平凡的小事物里寻出新意义”(75)的写作方式对于中学生作文特别具有示范意义,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周作人散文琐屑题材的深入人心,虽然现象本身与其缘起早已判若云泥。
注释:
①(64)黎锦明:《致周作人先生函》,载《新晨报副刊》1930年3月24日第551号。
②周作人(署“岂明”):《半封回信》,载《新晨报副刊》1930年4月7日第565号。
③自1930年3月24日黎锦明发表《致周作人先生函》开始,到6月4、5号傅非白发表《鲁迅与周作人》为止,《新晨报副刊》共刊出针对周作人的批评四十余篇。
④(15)谨公:《关于周氏兄弟批评的枝节问题——对霜峰君略答一二》,载1930年5月15日《民言》日报。
⑤借用芸影《因为半封信》中的说法:“因为半封信引出许多整篇的文章来,这也算文坛上的一个波澜。”载1930年5月13号《新晨报副刊》第601号。
⑥(18)(38)霜峰:《我所见的鲁迅与岂明两先生》,载1930年5月6号《新晨报副刊》第594号。
⑦借用张爱玲《〈传奇〉再版序》里的著名用语,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⑧⑨郁达夫1929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信,载《郁达夫全集》(第11卷书信),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第179页。
⑩张爱玲:《银宫就学记》,载《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83页。
(11)借用刘松塘《致两明的一封信》标题的说法,此文将周作人(笔名“岂明”)与黎锦明合称“两明”,载1930年4月14日《新晨报副刊》第572号。
(12)(71)周作人:《半封回信》。
(13)参见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4)(17)《批评鲁迅周作人》,载1930年5月18《民言》“本刊特别澂文”。
(16)例如吴曼秋的《致岂明先生》(载1930年4月10号《新晨报副刊》),便“在纸上唱个无礼喏”,抓住了《半封回信》中的字眼不放,对其极尽讽刺之能事。侯凝在《周作人与黎锦明》(载1930年4月18号《新晨报副刊》)中,同样在周作人回信字句上反复纠缠。刘松塘《致两明的一封信》(载1930年4月14日《新晨报副刊》)对周作人为回答黎锦明时查阅字典的细节持一种吹毛求疵的苛责态度。
(19)刘松塘:《致两明的一封信》,载《新晨报副刊》1930年4月14日第572号。
(20)(57)傅非白(署“非白”):《鲁迅与周作人》,载1930年6月4日《新晨报副刊》第622号。
(21)同上,载6月5日《新晨报副刊》第623号。
(22)次丰:《鲁迅周作人文艺的时代价值》,载1930年5月22日《民言》日报。
(23)谷万川、周作人:《大黑狼的消息》,载《语丝》1925年11月9日第52期。
(24)(25)周作人:《大黑狼的故事序》,载《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第85页。
(26)谷万川(署“半林”):《文学果无“煽动力”耶?——质周作人》,载1930年4月15日《新晨报副刊》头条。从此文起,至5月31日《向岂明先生道歉》止,谷万川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周作人的文字七篇:即《文学果无“煽动能力”耶?》《答复周岂明先生》《“误会”欤?“世故”欤?》《十洲先生的疑误半打》《所谓“某君也者”》《我的总答复》《向岂明先生道歉》。
(27)左翼青年作者往往用“象牙塔”来形容周作人的地位,例如侯凝在《周作人与黎锦明》中,也将周作人与大众的关系概括为“象牙塔”与“铁塔”的对立意象,表明周作人从生存方式到文学主张均与当时文坛思潮存在距离,而这也是引发左翼青年反感的重要原因。
(28)周作人1961年7月31日致鲍耀明信,载鲍耀明编《周作人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9)周作人1966年3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有“陶明志编之《周作人论》中,除苏雪林文最有内容之外,馀悉阿谀与漫骂的文章”(载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十·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页),而在这本赵景深编的《周作人论》中,正录有许杰运用左翼分析方法犀利解剖周作人的著名文章《周作人论》,可见此类左翼批评在周作人眼中几同于谩骂文字。
(30)周作人:《金鱼》,载1930年4月17日天津《益世报副刊》第107期。后来周作人又将《水里的东西》《小引》等总题为“草木虫鱼”收入《看云集》。
(31)(35)(70)谷万川(署“半林”):《答复周岂明先生》,载1930年4月21日《新晨报副刊》第579号,文末署写作时间为4月18日,即读到《金鱼》后立即写作此文。
(32)在《答复周岂明先生》中,谷万川引用了爱罗先珂的《狭的笼》中的老虎与鱼缸中的金鱼这一情节,对周作人进行讽刺。
(33)在《答复周岂明先生》中,谷万川称周作人如同“坐在一个‘三块豆腐高’的古砖上,在他身边正有一道高耸云霄的铜墙身壁矗立着,他才看见了这世界的半面,便像小孩子骑竹马似的,觉得自己已经身驾云霄,可以去‘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所以对于别人的话一概瞧不起”。
(34)参见拙作《读周作人散文〈金鱼〉》,载《名作欣赏》(中学版)2006年第12期。
(36)周作人:《写〈金鱼〉的月日》,1930年4月23号《新晨报副刊》第581号。
(37)侯凝:《周作人与黎锦明》。
(39)(40)周作人(署“岂明”):《拥护达生编等》,载1930年6月16号《骆驼草》第6期。
(41)瑶君:《岂明先生与达生编等》,载1930年6月23日《新晨报副刊》第641号。
(42)周作人(署“岂明”):《水里的东西》,载1990年5月12日《骆驼草》第1期。
(43)(45)周作人回信,载1930年6月9号《骆驼草》第5期“邮筒”栏。
(44)(48)谭丕模(署“干因”):《谈“骆驼草”上的几篇东西》,载6月3日《新晨报副刊》第621号。
(46)次丰:《鲁迅周作人之文艺的时代价值》,载1930年5月22日《民言》。
(47)(53)周作人(署“岂明”):《论八股文》,载《骆驼草》1930年5月19日第2期。
(49)(51)(52)廖翰庠来信,载1930年6月9日《骆驼草》第5期“邮筒”栏。
(50)(55)周作人回信。
(54)郁达夫1930年6月23日致周作人信,《郁达夫全集》(第11卷书信),第180页。
(56)(58)俞平伯(署“平伯”):《又是没落》,载1930年6月23日《骆驼草》第7期。
(59)诚如高恒文先生所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周作人的文学观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是批判左翼文学观和回击左翼对他的批判的一篇特殊的文学批评。”见高恒文著《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注:第151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0)周作人1932年8月2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4页。
(61)(63)(68)周作人(署“岂明”):《介绍政治工作》,载1930年6月23日《骆驼草》第7期。
(62)例如《周作人年谱》中,就认为此文是周作人“介绍并推荐了何容著的《政治工作大纲》”(第400页),即可视做周氏讽刺笔法深藏不露、容易混淆耳目之一例。
(65)(67)周作人(署“岂明”):《专斋随笔二·文字的魔力》,载1930年7月7日《骆驼草》第9期。
(66)关于这一点,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三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8页。
(69)周作人:《专斋随笔八·骂人论》,载1930年11月3日《骆驼草》第26期。
(72)周作人:《专斋随笔之三·杨柳风》,载1930年8月18日《骆驼草》第15期。
(7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74)周作人:《专斋随笔六·草木虫鱼小引》。
(75)章锡琛:《周作人散文钞·章序》,章锡琛编著《周作人散文钞》,开明书店1932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周作人论文; 1930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黎锦明论文; 达生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