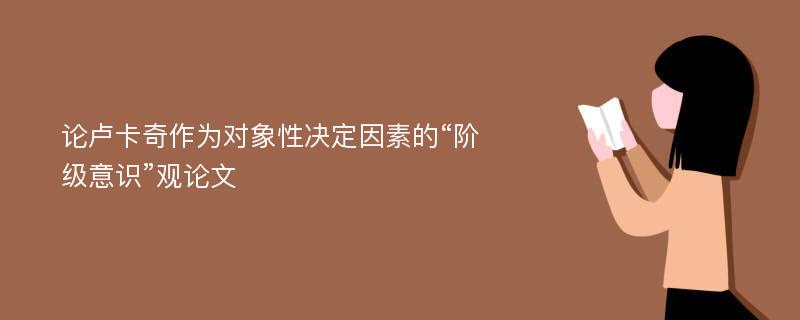
论卢卡奇作为对象性决定因素的“阶级意识”观
张秀琴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其早期准备性探索做了肯定和梳理,更为具体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并将这种悖论认定为物化意识。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是现代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基于商品的对象性结构形式的意识表现,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遮蔽了对象性活动的赋形功能,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离散。他最终引入辩证法来尝试重建主体的统一性,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成就一种新的、不被绝对客体化的对象性活动意识,成为主客体统一的现实承担者。
关键词: 卢卡奇;对象性;物化意识;阶级意识
1920年代(特别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卢卡奇,曾多次强调对象性形式(Geganstandlichkeitsformen)的决定性因素,是阶级意识——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二重性及其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1)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虽然从早期的文艺形式转到20年代的商品形式,但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更加贴近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了,实际却还是以超验的方式来对待经验问题。 。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资产阶级辩护士们(特别是哲学家们)的二律背反意识称之为物化(Verdinglichung)意识(其典型特征是直接性,即非中介的绝对客体性——在稍后的《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中,卢卡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前耶拿时期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的),并同时将超越物化意识(即现代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交付给无产阶级,即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成就一种新的、不被绝对客体化(Objektivierung)的对象性活动意识,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这样,卢卡奇就把阶级意识视为对象性形式的决定因素了。所谓对象性形式,即社会交往的一般形式(沿用黑格尔的做法,卢卡奇也称此为“中介”),一定的对象性形式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一定的主体性形式,并因此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因此,把阶级意识视为对象性的决定因素,就意味着把它视为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的主导因素。于是,如何理解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就成了人们判断他是否属于唯心主义论者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了(实际上,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很多论者指责为一个骨子里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即阶级意识不过是绝对精神的翻版)。当然,如卢卡奇自己所“辩护”的,1920年代的他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学徒”,并深受《资本论》等马克思著述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拜物教理论的影响,并因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重点论述了类似于拜物教概念的“物化”概念,且尝试着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将商品视为市民社会(即现代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形式,而物化则是基于这种商品对象性形式之上的一种被绝对客体化的对象性活动。这种以商品为基础的绝对客体化的对象性形式在思想上的反应,必然是物化意识。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是现代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基于商品的对象性结构形式的意识表现,是资产阶级在追求主体理性(自由)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悖论,即二律背反在思想上的表达。
一、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特别是《物化与阶级意识》的第二部分),卢卡奇开始具体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近代批判哲学(2) 卢卡奇在这里特意将希腊哲学排除在外(“只有希腊哲学是某种例外”,虽然希腊也有物化,但因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所以“古代哲学提出的问题和答案同近代哲学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7页),这与他在《小说理论》、《心灵与形式》和《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对希腊哲学时代的肯定(即认为在那里形式还是与生活统一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的二律背反,并将这种悖论认定为物化结构的意识表现,即物化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在1920年代前(特别是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划分了古代(希腊)的形式概念和近代(即现代市民社会)的形式概念一样,卢卡奇在这里区分了古代(希腊)的物化概念和近代(即现代市民社会)的物化概念(3)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认为可以用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来表征现代市民社会的这种客体性。 ;并以相类似的方式指出只有近代(即现代)物化概念才是建立在主客体离散(即建立在对于一个“对我们来说”是“异在的既定性”(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1页。卢卡奇称此为“独断主义”前提假设,这恰是客体化原则——它既是指引我们前行的“路标”,又是不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对立的“鬼火”(参见同上书,第192页),这样的(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式或形式理性主义)批判,非常类似于先前在《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中(以“渴望”、“姿态”和“瞬间”概念呈现出来的)对客体化原则的批判。 ——这个异在可以是绝对的主体,也可以是绝对的客体(5) 前者如费希特的自我,后者如自然主义者眼中的自然。卢卡奇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能令人满意,都是物化原则的体现。 )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表现为“理性的形式主义”(6)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认为这是一种逃离理性的对象性,即实证性。 ——然而,卢卡奇非常清醒地指出,作为一种认识方式,它是我们现代人“唯一可能”的把握现实的方式,虽然它从来不允许我们找到真正的对立和真正的统一。可见,这里的“物化”概念与稍后(1930年代)的《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对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的理解有很多相似之处,至少它们都标示着与古代社会截然不同的现代社会属性,并因此表征着一种现代性内涵。这种现代性内涵,也即主体性内涵,是理性主义的决觉,相对于混沌同一的古代来说,它代表的是主客体离散(即分离,或客体作为异己的东西的出现,并在这一意义上让主体得以真正呈现),然而这种离散却因为分离开来的主体或客体及其中介(即各种对象性活动)的再次绝对化(从主体视角来看,一般被视为绝对客体化)而成为虚假的理性主义,即卢卡奇所说的“理性的形式主义”。
本次试验中采用PE为皮层材料,在复合纤维中主要起热熔黏合作用,同时赋予PE/PA6复合纤维爽滑的手感,采用PA6为芯层材料,主导纤维的力学性能。本试验改变纤维的复合比例,其他纺丝条件保持不变,纺丝效果如表2所示。
于是,和古近之变、特别是理性主义原则密切相关的主客体同一(identische Subjekti-Object)问题(就像在前1920年代文艺青年卢卡奇时期一样),再次浮现出来。只不过这一次,卢卡奇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中介即对象性活动本身被绝对化的做法,所以他指出,任何一种客体化原则(形式主义)都将对象性水平任意拔高到如此之程度,以至于主客体二分性“被消除了”——要知道,古典哲学“不会看不到经验中主体和客体的这种二分性;而且,他们正是在这一分裂的结构中看到了经验的对象性的基本结构的”,所以他们会从“同一的主体-客体”出发,“把每一种既定性把握为同一的主客体的产物,把每一个二分性把握为对这种原初统一中派生出来的特殊情况”[1]193。一句话,在古典哲学中,主客体虽然是分离的,但却是离而不散的(7)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将此称之为“无客体的客体性社会”。 ——就像心灵和生活在希腊哲学时代中的关系一样。实际上,如同在《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和形式》、《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史诗时代、希腊时代和现代小说时代并在这一框架下来探讨文艺形式的具体历史发展和社会功能一样,他现在以同样的方法论来探讨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人的生存状况即思维和存在问题,也是自由问题。和青年黑格尔对古代社会的美好愿望一样,卢卡奇也把古代社会设想为美好社会。只不过,卢卡奇在这里更多的是在讨论古代哲学的视角中来进行的,所以他认为,希腊以来,所有关于思维和存在问题的探讨,都不过是主客体二分性结构的一个“特例”[1]193。换言之,我们对于存在(物、事、或事实)的探讨,都是在主客体二分框架之下来进行的。卢卡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进行了评析。在他看来,虽然近代哲学一直在主客体非同一性(或分散)结构中来对存在问题进行探讨,但他们却一直奢望以独断论(表现为宿命论或唯意志论)来对此分散进行统合(卢卡奇以康德的物自体问题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这恰是近代思想二律背反,这也是物化意识在哲学上的表现(8) 对于哲学史的这一梳理,与《青年黑格尔》中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分析,有诸多类似之处,只不过在那里,物化表现为实证性概念。 。
中介的范畴作为克服经验的纯直接性的方法论杠杆不是什么从外部(主观地)被放到对象(Geganstand)里去的东西,不是价值判断,或和它们的存在相对立的应该,而是它们自己的客体(Objektiven)对象(Gegenstandlichen)结构本身的显现。但这一结构只有在资产阶级思想放弃了对对象(Geganstand)的错误观点时,才能显现出来,并被意识到。因为如果对象(Geganstand)的经验存在本身不是早已是一个被中介存在的话,中介也许就是不可能的,这个存在一方面只有在缺乏中介意识时,另一方面只有在对象(Geganstand)(正因此)被从它们的真正规定性的联系中拉出来,被置于一种人为的孤立中时,才能获得直接性的外表[2]346。
正是这种不可解决的(因分散和分离而造成的)二元性,导致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上的二律背反现象。而其根源则是源自于其“生活基础”的二律背反,即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失去了它们的人的彼岸性”,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人却日益被孤立、被个体化和原子化,人们的活动和认识也表现为这一原子化意识的结果,人的社会活动行为特性也因此被“取消了”[1]209。在前一个方面的视域中,世界是人创造的,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即市民社会的人所面临的环境都是自己“创造”的“现实”(即自然的人化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关于“自然”、“价值”等概念就会变得混乱和错综复杂了),因为市民社会的人(的活动和意识)是依据自己所创造的“环境”(“规律”)来界定主客体等概念和关系的,这样,他们所说的客体,是与主体离散的客体:其本质是表现为绝对他者的自我创造物。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后一个视域中,创造者已经(有意无意)遗忘了创造的过程(即对象性活动本身),就这样,市民社会的人将对象性活动绝对化了(也即客体化了——自然的内在化过程,即成为所谓“第二自然”)。在卢卡奇看来,这样的客体化原则,是建立在对对象性活动进行消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们借以打开主动性、积极性的通向真正的生活之门(因为根据他先前的研究成果,对象性活动就是赋形,是创造或创生,而它被绝对客体化,仅仅表现为在“规律”面前的接受、甚至是跪拜的话,就意味着它丧失了自己固有的创造功能了),就被再次关闭了(如果说它在近代早期曾被打开过的话)。所以卢卡奇非常清晰地表述道:“对象的结构(Gegenstandsstruktur):自然内在化的这个表面的顶点恰恰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对它的理解。作为内容的形式和自然规律一样,也是以未被理解和不能理解的客体(自在之物)为前提的”[1]211注释1。所以当卢卡奇说“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问题,即自在之物的问题”的时候,他正是在强调该思想的最大缺陷,即客体化原则——也就是说,他赞成康德式的坦诚面对二分,但却不主张将其中的任何一方予以绝对化(当然在他看来,黑格尔没有这样做的)。为此,卢卡奇既反对唯意志论、又反对宿命论(如同他早期对抒情诗派和田园诗派的双反一样),因此他也反对与上述两种倾向相应的自然观,而是主张一种新的自然观(即他所谓“第三种自然概念”):自然“意味着真正的人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摆脱了社会的错误的令人机械化的形式的本质”,也即人需要理性原则,但这种理性(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种具体的总体(Konkreten Totaltat)原则”[1]229,211,212。
然而,无产阶级何以就能成为这一主客体统一(即历史辩证法)的现实承担者呢?援引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异化”(Entfremdung)的相关分析,卢卡奇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同样的直接现实性(Umittlelbarkeit Wirklichkeit),但因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相同的直接现实性的理解却是不同的:在资产阶级那里,那就是一个先验的、不可理解的自在之物(表现为规律、科学或理性),而在无产阶级那里,它却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产物(归根到底是创造物)(13) 卢卡奇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机器问题的论述为例,对比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并指出前者因为“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对象性(Wirklich Geganstandlichkeit)”而把“被考察的历史对象(Geganstand)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3页; 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Georg Lukacs Werke ,Band 2,Fruhschriften II , Darmstadt:Herman Luchterhand Verlag GambH & Co. KG, 1977, S.335-6)。 。也即,在无产阶级那里,物化(或异化)只是中介(对象性活动),而资产阶级却把它们视为直接给定的事实(客体化的铁定事实)。如此明显的态度和立场(理解事物的方式)的不同,在卢卡奇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结构形式(如物化)来与周围世界发生关系的,历史的本质正是这些结构形式(Strukturform)的变化,而正是这些结构形式决定了人的内外部生活(即兼具本真的生活与经验的生活之属性的心灵)的对象性(Gegentandlichkeit)。但这些结构形式并不直接地呈现自身,而是需要我们寻找和发现。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哲学辩护士们却满足于一种“直接性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对象的直接的物的形式(Dingformen)”要优于它们之间的关系(Beziehungen),这样他们就把握不了变化,所以“为了能从根本上把握住变化,思维必须不再把对象视为是相互绝对排斥的,必须把它们相互的关系,这些‘关系’和‘物’的相互作用都一样看作是现实的”[1]234。这样,现实就呈现出不同的层次:(1)原始的直接的物;(2)原始的直接的物在思维中的呈现;(3)因物和物在思维中的呈现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的认识(意识)。可以说,从最初直接的物出发(甚至对它的回溯式最终认识),“关系”就一直存在,所以物(Ding)一直是物象(Sache),即包含了关系的事物,而不仅仅(甚至从来都不)是直接既定的物本身(即物自体),而是表现为物形(Dingforme)的物象或事物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形式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没有这一中介,关系就无法想象。而中介越强大(即距离纯直接性越“远”),关系网就越大,物就“越是彻底地进入这些关系体系”,并因而变得更容易“被把握”。不过,卢卡奇强调,只有当这种对直接性的超越“沿着使对象更加具体化的方向前进”,“当这样达到的中介概念体系”“成了‘经验的总体’时”[1]234-235,上述目标才可能实现——注意,在卢卡奇这里,对直接性的超越,并不意味不要直接性,虽然他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直接性意识形态,但却认为“直接性和中介”不仅是“对待现实的对象所采取的相互隶属、相互补充的方式”,而且还同时是“辩证地相关的规定”[1]236-237。换言之,直接性和中介(Vermittlung)之间也遵循辩证法原则,所以他引述黑格尔的话说,“中介的东西必须是两个方面在其中的合一的东西”(14) 黑格尔:《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75页,转引自﹝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7页。 ,这样的合一当然包括对其他者(即直接性)的勾连。所以辩证法意味着,既不能将对象性活动抽象化为与主体对立的绝对的客体,也不能将对象性活动形式化为全部的社会现实而予以直接接受。中介就是中介,应该把它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视为一个变化的历史的过程。可见,卢卡奇反对将中介(对象性活动)直接现实化与他反对将中介客体化的原则是相一致的——直接现实化不过是客体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15) 他也在这个意义上对齐美尔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中的物化论再次提出了批评。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8页。 。
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认识活动)都是已经被中介了的、因而是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中介即是对象性活动。取消中介,就是取消对象性活动的创造性。其结果就是产生客体主义(客体化原则)和直接性意识形态——如资产阶级思想所做的那样。因此,卢卡奇说,这种将对象化予以孤立的过程“不是偶然的或随心所欲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且资产阶级本身“在理论上必然囿于直接性之中”),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可以超越这种因孤立对象性活动而造成的思维的直接性。而无产阶级要想这样做,就必须首先形成正确的认识,即消除那种把对象错误地分离开来的做法,并提供新的对象性形式,即引入中介,因为“中介范畴的方法论作用在于借助于它们,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必然具有的,但在资产阶级思想中必然没有得到反映的那种内在意义,在客观上发挥作用,并因而能提高为无产阶级的意识”[2]346-347。置言之,无产阶级意识就是新形式的对象性活动意识。
二、无产阶级意识是新的对象性活动意识
在新的克服虚假的或形式主义的对象化形式基础之上的物化逻辑中,要想祛除物化,就必须“要由‘行动’来证明和指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但是要理解这种统一,就必须指出历史是方法论上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场所,而且具体地指出这个历史主体的‘我们’,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1]223-224(12) 在此,卢卡奇反对黑格尔将“我们”等同为“世界精神”,所以黑格尔哲学也是神话,亦即遵循的客体化原则。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23-224页。 。在卢卡奇看来,可借以解决近代哲学遗留下来的二元论悖论(即二律背反)的辩证法,要想被当作历史的方法,就首先要靠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228。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主客体统一的历史承担者和代理人。
由上文可见,不恰当的对象化形式(卢卡奇常常承接先前的文学话语称之为赋形活动——虽然他已在这里通过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了商品作为对象化形式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但他依然过多地依赖于自己的文艺研究术语来表达这种新的对象性形式),只会给主客体的真正统一制造障碍,因为它实际割裂并分别绝对化或神话了主体、客体及其中介,造成了主体作为创造者的不可理解性。他把这种不可理解的僵硬性称之为“物化”。在他看来,正是物化撕碎了主体的统一性,因此现在需要重新发现统一的主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必须引入“辩证法”。换言之,引入辩证法是为了重建主体的统一性(通过超越分散),并使得对客体的理解成为可能(祛神秘化)——因而这也是一个重建人的努力。换言之,“溶化”主体和客体(以及与之相应的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一成不变的“僵硬对立”[1]219。不难发现,这恰是《心灵与形式》中“形式”所要做的事,后来在《小说理论》中被进一步交给了对象性活动(因为形式本身也日渐被神秘化或客体化了——如在形式主义那里那样)。这样卢卡奇就完成了从“形式”、“对象性活动”到“辩证法”的概念(作为对“总体”的理解)上的转型——与此相应的,就是他的从客体化原则经对象化原则到物化逻辑的思想演进路线图。
我们知道,这种具体的总体的理性原则,不是别的,正是辩证理性原则。这是一种新的对象化原则,探求的是形式背后的内容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其实他在先前的文学的对象化原则(即赋形功能)探讨中,已经以特定的方式谈到了这一点,且已启用相关概念:即他早在《现代戏剧发展史》、《小说理论》等中就已用过“总体”、甚至是具体的历史总体、“世界观”等概念,并强调了艺术作品的“社会历史根源”——实际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早期的准备性探索作了再次较为积极的肯定和梳理,只不过,他现在更加强调造成二元论的社会历史根源如何“赋与美学,即关于艺术的意识,以一种世界观性质的意义”,并主张新的赋形(对象性活动)要“以关于其物质基础的具体内容为目标”,而不要停留在“对艺术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1]211-212①(11) ①且卢卡奇通过对近代哲学的梳理(含普列汉诺夫的)指出,将美学原则(Asthetische Prinzip)提高成为客观现实(Objektiven Wirklichkeit)赋形的原则(Gestaltungsprinzip),依然是“回避真正的问题”,是“幼稚地停留在物化的思想形式中”,或至多“被驱赶着走向客体矛盾”,其结果只能是“被迫在思想上相应地也把主体撕成碎片”。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5、214、216页;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Georg Lukacs Werke ,Band 2,Fruhschriften II , Darmstadt:Herman Luchterhand Verlag GambH & Co. KG, 1977, S.320-1。 。换言之,要祛除掩盖在对象化之上的神秘面纱,恢复对象性活动的赋形功能、创造功能即真正的中介功能,而非仅仅充当心灵与生活之间的“显影剂”。卢卡奇力图以此来反对绝对客体化原则(即物化逻辑)。而他借以反对的最主要的武器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新的对象性活动意识。
当然,这并不影响卢卡奇对中介(作为对象性活动,具有赋形功能)的高度重视。相反,他正是为强调中介(及其功能),才努力把中介从它的错误应用(也即从客体化原则)中解救出来。在他看来,“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面临的世界呈现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决不会保持在一种”“纯直接性上”[1]238。因为:
主客体关系中的分离(主客体同一)和分散(主客体非同一)之间的古今对比,以及后者力图以独断论的方式回归到古代(即统合)的努力,就成了卢卡奇考察近代哲学的核心线索,当然他把这一线索理解为二律背反的悖论。在他看来,为解决这一悖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做了令人满意的努力,即黑格尔区分了不同层次的现实(即存在)概念(此在、存在和实在等)(9) 在《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认为这也是黑格尔的“实证性”后来所力图涵盖的诸存在范畴,因此实证性概念在内涵上也具有双重性,并因此成为“外化”概念的雏形和走向辩证法的“不自觉的第一步”。 ,马克思则“比黑格尔更具体、更坚决地实现了从存在问题及其意义的层次问题向历史的现实的领域,向具体实践的领域的过渡”[1]199。可见,对主客体及其中介关系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对存在(或现实)概念的不同界定。换言之,不同的主客体关系论(特别是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中介论)就决定了不同的现实观(体现在对存在的概念化上:如存在是“物”、是“精神”,还是“实践”)。显然,卢卡奇更倾向于将对象性活动从纯粹抽象的客体化原则拉回经验现实一维,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卢卡奇又同时反对那种将实践直观化的做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恩格斯的实践定义持保留意见(10) “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其实,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而工业在根本的意义上,“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6页)。 ),即指出了“批判哲学用转向实践以图解决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理论上已被论证了的二律背反,而是相反,使其永恒化了”。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表扬康德“在哲学上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不是随心所欲地、独断主义地决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而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1]207,208。这样,卢卡奇似乎又倾向于承认分离、乃至分散的不可避免性,以便为他的对象性中介活动以及最终的总体统合提供依据(也即黑格尔式的努力只能出现在康德之后)。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数学学科,有其很强的应用背景,所以要求老师不仅要把学科里面涉及的公式定理给同学们讲透彻,还要结合具体的实际例子,这样课堂效果才会更有效。
不过,上世纪50年代前后,“史诗”这种传自西方的文学类型,被一些熟悉文学,从事文艺工作的学者、诗人、作家运用到了少数民族的民歌整理中,并随着50年代民族文化工作的深入,催生了大量的作品。
这种新型的对象性活动,是中介性的,而不是直接性的。当然,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也会面临这种直接性的障碍,它对无产阶级来说,构成了“内在的障碍”,无产阶级因此“明确地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随着问题的提出,解答问题的途径和可能性也就出现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直接性,资产阶级会禁锢在其中,而无产阶级却有可能超越它呢?卢卡奇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两个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利益的不同(其实是对立)。也即对工人来说,“内心里是没有”“虚假活动的余地的”,他被迫成了“过程的客体,忍受着他的商品化和被简化为纯粹的量”,正因此,“他就被迫力求超越上述状况的直接性”[1]247,250。也就是说,被资本家当做量来计算的,恰是工人的“肉体、精神和道德”等质的存在。卢卡奇再次以劳动时间为例,认为“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上的物化着的已物化了的外衣”,“它只有在主体和客体处于直观的或(看来是)实践的关系,并对对象的本质不感兴趣时,才能被认为是对象性的客体形式”[2]350-351。也即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元对立的直接性(也即客体化)现实观,使得他们看到的工人都是作为客体的(以数量化的呈现方式——比如将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无差异地换算成抽象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不是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主体性存在。而无产阶级作为肉身的体验,必然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种被客体化的苦难,并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来试图有所改变——首先就是要改变自己的 “真正的对象性”和“真正的对象形式”被“歪曲”、被淹没、被直接客体化的状况[1]250。这样,卢卡奇以无产阶级经验的对象性活动的力量力图破解资产阶级社会的超验的对象性活动即客体化原则迷局。当然,要想破局成功,既不能只停留在纯粹的经验的对象性形式世界,也不能重复资产阶级的超验的或思维的直接性也即客体化对象性形式世界,所以,卢卡奇也提醒说,“超越直接性的运动不是僵化为停滞,僵化为一种新的直接性”;也不能是纯粹认识的活动,因为对纯粹认识的认识只会“导致对这些形式的重新肯定”[1]255,263。
然而,这又如何能做到呢?特别是面对同样物化深重的世界:正如卢卡奇所描述的,在这个世界里,除了时间,在劳动被转化为商品的发展过程中,一切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都被排除在社会形式之外,好像它们已经不是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主动者),人只有通过客观性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性。然而,正是在这里,在这个似乎“罪孽深重的时代”,卢卡奇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因为“恰恰是在一切社会关系的这种客体化(Objektivierung),这种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之中,社会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才第一次清楚地表现了出来”(16) 显然,卢卡奇在这里,将物象化与客体化并列使用,而且还和合理化(即作为形式主义的理性或理性的形式主义)概念并列。或许这是受韦伯的影响所致,因为韦伯在1920年代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就曾多次使用物象化概念(就更不用提合理化概念了)。但更有可能的是,卢卡奇也把物象化概念视为他自己的物化概念,所以才会在引述马克思使用物象化概念和异化概念的地方来说明自己的物化概念。换言之,至此为止,卢卡奇一直都是在别人的术语库中,偶然将物象化概念捡拾过来为自己的概念解释服务,因此,他对物象化概念的使用一直是不自觉的。多数情况下,都将之视为一种反过来伤害主体的客体化。而这也恰与他反对资产阶级直接性(即客体化)原则的旨趣相一致。 参见: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Georg Lukacs Werke ,Band 2,Fruhschriften II , Darmstadt:Herman Luchterhand Verlag GambH & Co. KG, 1977, S.361. 。也就是说问题暴露得越是明显,越是激化,距离解决问题的时刻也就更近些了,即正是绝对的客体化(合理化或物象化),才使得非客体化的相反趋势即主体(也即人格的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维度有可能得到恢复。当然,卢卡奇提醒我们说,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时还是依赖于物(Dinge)和作为物而出现的,是被“生产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中介了的关系”,是非人的关系,而“作为物象化(versachlichen)关系的核心和基础的人,只有在消除了这种关系的直接性之后才能被发现”。第二,“这种表现形式决不是思想的形式,而是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andlichkeitsformen)”,对它们的消除也只能实际地消除“社会生活形式”来实现[2]362。换言之,不能在纯粹认识的领域将其消除。第三,“这种实践不能脱离认识”。第四,“这一意识过程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表现为“历史辩证法的固有结果”(17) 卢卡奇在这里指出,“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要依靠历史来解释的(而黑格尔就常常这样做)。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64页。 。所以无产阶级意识的辩证法就是无产阶级的辩证法,因为“这时的意识不是关于它所面对的对象的意识,而是对象的自我意识,意识的这一行为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Gegenstandlichkeitsformen seines objekts)”[2]363。这样,先前的“形式”概念、以及这里和稍早探讨的“对象性”概念,都不过是作为“中介”概念预先上演的辩证法的大戏。所以卢卡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辩证过程把对象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1]264②(18) ②卢卡奇认为社会民主党思想的“资产阶级化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它对辩证方法的背离上”(以伯恩施坦等为例),认为是“马克思把辩证法变成了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70页、第278页。 。只有从辩证法出发,“历史才真正地变为人的历史”,人的世界的结构就“表现为动态变化着的关系形态的体系”,即“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最自我(对自然和对其他人)的关系就在这一连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1]274-275。这样,历史就消解了一切僵化的直接性,在它那里,“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不过是“对象性形式、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1]275③(19) 这大约也是卢卡奇一直强调的“社会性”的旨趣所在。所以在这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人的社会历史存在属性的强调。参见: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Georg Lukacs Werke ,Band 2,Fruhschriften II , Darmstadt:Herman Luchterhand Verlag GambH & Co. KG, 1977, S.372. 。卢卡奇承认,因为马克思的贡献,我们现在认识到,历史是包含客体性的历史,但更主要的表现为“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因此,“真理只能具有一种与各个阶级的立场及其相应的对象性形式有关的‘客观性’”[1]278。这就把阶级立场和利益与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加以探讨,并试图重建一种新的对象性形式的可能性,即成就一种具体的和历史的总体辩证法的理论与实践。
何睿祺解读了合作在“工业4.0”时代的意义,例如西门子与惠普企业(HPE)旗下安移通(Aruba)近日在通讯网络领域达成合作,就一体化通讯网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依托互补的产品组合优势,帮助客户构建从工厂车间到公司办公室的一体化通迅网络。何睿祺还提到了西门子与Bentley Systems的长期合作。双方近期宣布,将基于高度互补的软件产品组合,联合开发PlantSight云服务,以帮助用户通过简单的门户网络界面随时访问1D/2D/3D数据,从而为所有用户提供不断更新的“数字化双胞胎”工厂。由于过程工厂和持续投资项目的服务时间较长,这项云服务将为工厂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Georg Luka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Georg Lukacs Werke,Band 2,Fruhschriften II[M].Darmstadt:Herman Luchterhand Verlag GambH & Co.KG,1977.
On Luk ács 'View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s the Determinant of Objectivity
ZHANG Xiu-q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his book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ukács affirmed and analyzed his early preparatory exploration, criticized the antinomy of bourgeois thought more concretely, and regarded this paradox as the reified consciousness. Lukács believed that the reified consciousness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objective structure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also as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modity economics. And this bourgeois ideology obscured the formative function of object-oriented activiti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disper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Eventually he introduced dialectics to reconstruct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 pointing out that only the proletariat can achieve a new sense of objectivity, which is not absolutely objectified, and become the real undertaker of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Key words :Lukács; Gegentandlichkeit; the reified consciousness; class consciousness
DOI :10.16614/j.gznuj.skb.2019.04.001
收稿日期: 2019-02-27
基金项目: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秀琴(1970—),女,安徽合肥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概念、理论与实践专题。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9)04-0001-09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卢卡奇论文; 对象性论文; 物化意识论文; 阶级意识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