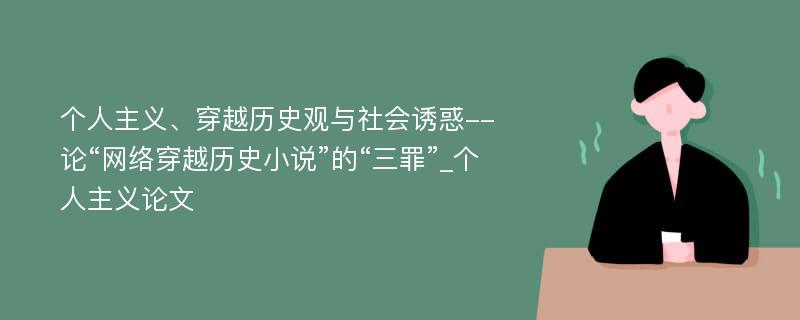
个人主义、穿越史观与共同体诱惑——论“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三宗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体论文,个人主义论文,历史小说论文,网络论文,三宗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穿越”题材是中国网络小说中非常“怪异”的亚类型。“玄幻”可追溯到民国的还珠楼主,“惊悚”有蒲松龄的狐鬼花妖,二者又可共同追溯到古典志怪小说传统,言情、校园、科幻、武侠、黑社会等题材也早已出现。它们借着网络平台,又有了类型化发展。“穿越”比较奇怪。虽然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明代董说的小说《西游补》,也曾出现“时空穿梭”情节,但它其实源于清末民初“乌托邦政治小说”,在西方则有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这些小说由于现代性时空的植入,使现代与前现代逻辑发生碰撞,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等。作为类型而言,它既是通俗历史小说的“亚类型”变种,又与言情等类型发生交叉关系。然而,作为普遍的历史消费与现代想象,穿越历史小说又是中国网络文学“独有”的。当下世界文学范围内,恐怕再也难找出像中国这样的“穿越”热情:无数作者和数量更庞大的男女读者,期待逃离现实,在令人咋舌的时空疆域,苦苦地进行“意淫”。女性回到古代成为成功男人追逐的“女神”,男性则改写历史,四方争霸,抵抗外辱,建设现代化强国。正统文学批评家往往嘲笑它的“荒诞不经”,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这么荒诞的东西,为何被大众广泛认可?从个人主义、穿越历史观与共同体想象三个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发生机制、潜在文化逻辑和精神困境。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文学?表面上看,这些穿越历史小说,都属于消费文化发展的产物,反映了类型化的社会接受心理需要,是“感受一下80后、90后所背负的巨大压力,学业、升职、房价、婚姻等,每一样都无法轻松对待,我们应该可以理解这些女孩为什么在面对《步步惊心》时倍感轻松”。①有的学者认为,穿越历史的文化心理,反映了“使人类在文学想象中实现了对自身既定时空规定性局限的超越,体味到最大的精神自由与快乐”。②而从深层次而言,我们却发现,这些穿越历史的小说,实际表现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诱惑、历史观念的纠葛。 首先,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表现出怪异的“个人主义气质”。汉学家普实克认为,个人主义、主观性与悲观主义,是中国新文学的三个基本特征③,个人主义的“发明”,通过第一人称运用、大量心理描写、主体意识来建构,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狂人日记》。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提出“内面的人”的概念。然而,个人主义并非仅通过“内面”的自我告白来实现,个人主体与世界的“征服”关系构建的外在主体意识,也是个人主义的表征。考察西方早期现代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有很强的第一人称意识,却没有普实克说的“悲观性”,或柄谷行人的“内面告白”,其主体的外在扩张性非常强。小说有“不断扩展”的世界时空观,“荒岛”成为野蛮世界的象征,与文明世界形成“对峙性”关系,闪烁着经典现实主义清教徒冷静务实的态度、资本扩张的野心与顽强主体意志。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者谱系,还有伏脱冷、拉斯蒂涅、于连、卡刚都亚等。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子夜》的吴荪蒲、《雷雨》的周朴园等才有类似特点。进入20世纪,当小说走入自身趣味的反动,从通俗文艺上升为高雅艺术,当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强者观念被怀疑与悲观所笼罩,荒诞意识、意识流、后现代符号狂欢等概念才流行起来。 新时期以来,个人从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宏大概念挣脱,表达自我建构与认同,然而总体基调阴暗悲观、或阴柔和美。20世纪90年代,当个体的人,在市场与政治规训结合前提下,被抛入资本、个体身份的全球化流动,以个体的内倾化压抑为代价,获得物质财富与存在感,其个体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就只能以“反讽”的姿态存在,如王朔。这种“反讽式”个人姿态,其基本倾向是回避“内面”,几乎没有“自我”的“告白”④。然而,王朔式的个人主义以虚无的激愤外表,掩盖宏大叙事冲动,其个人主义面目,既无“内在性”,又无外在“强悍气质”,就流于“痞子式”的模糊。纵观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这种以歌颂强者、具资本意味的个人主义,始终被放在“道德批判”的纬度,如王刚的《月亮背面》。“新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暴发户与私企老板,无不贪财好色、愚蠢丑陋,个人素质低下,如《分享艰难》的高大肚子。1990年代个人主义还借助“欲望叙事”取得话语合法权,如《上海宝贝》的倪可,但这类欲望叙事必须有“纯文学”语言外壳,才能模糊意识形态性。有的批评家将这类“欲望个人”,称为在“个体性”与“人民记忆”之间,以“无主体的主体”的虚无面孔⑤。陈染式的“私语个人主义”,则表现为对隐私和身体领域的执拗关注,以此表达对群体参与性的恐惧。“新编革命历史小说”如《亮剑》《历史的天空》,也有“曲折”的个人主义诉求:“如果说,革命英雄传奇仍重视书写革命传奇,那么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则是个人的传奇。如果说前者的革命英雄是人民战争中涌现出的优异代表,后者则是靠着个人天赋从底层通过个人奋斗终于出人头地的个人。”⑥(也有积极尝试,如关仁山《麦河》的资本家曹双羊)直到新世纪,“纯文学作家们”依然无法完美地处理“个人主义”问题。“个人主义”在新世纪“被分裂”了,一些作家热衷描写“失败个人”,将“内面性”推向极致,如贾平凹的《秦腔》以傻子引生为叙事主体,讲述中国乡土消失的现代化进程;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英雄,被抽象为金钱或权力符号,如阎连科《炸裂志》的孔明亮;或被夸张为成功的粗鄙代言人,如余华《兄弟》的李光头。纯文学小说家写尽“个人主义者”的粗鄙、丑陋与狠毒,却无法写出他们反抗现实的强悍意志,实现自我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精神。特别是中国扩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语境下,纯文学作家们对个人主义的表述效果与真实性,显然非常欠缺——对普通人的阅读而言,这些对个人主义的处理方式,并未对他们形成强大的心灵共鸣与情感信赖。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敬明的《小时代》,尽管肤浅庸俗,却也带来了一些别样的,却有“中国本土特质”的个人主义想象——尽管是片面的物质性。 所有文本想象,必定有现实的欲望焦虑。当考量那些网络穿越历史小说,就会发现,那些通俗又荒诞的穿越故事,却都有着“鲁滨逊”气质的男性或女性的“个人主义者”,如《梦回大清》的都市白领小薇,《传奇》的女编辑苏雪奇,《篡清》的公务员徐一凡,古龙岗《发迹》的何贵,有时糊涂《民国投机者》的楚明秋。他们有时也是某些“附身”历史名人的穿越者,如酒徒《指南录》穿越版“文天祥”,鲟鱼《我成为崇祯以后》穿越版“崇祯”,或附身于平凡小人物,如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的杨凌;或名人平凡亲属,如李小明《隋唐英雄芳名谱》穿越版的宇文士及私生子“李勒”。这些个人主义者,甚至是被“中国灵魂”附身的“外国古人”或“原始人”,如实心熊《征服天国》的欧洲中世纪少年伦格,老酒里的熊《回到原始部落当村长》的原始部落酋长赵飞。然而,这些男女穿越者有一些共性,现实中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人:小公务员、失败杀手、女白领、妓女、小职员、退伍兵、破产商贩、小工程师、厨师、穷学生、下岗工人(“穿越前”的文化身份,没有一个是农民,这也暴露出网络穿越历史小说“非乡土”的都市现代性特质);而穿越时空,他们也只是历史“失败者”:意外闯入者、奴隶、盐民、流民、土匪、士兵、赘婿、被废太子、末代君王、失宠妃子、家族弃子。然而,当代与历史之间,却存在约定俗成的“叙事反转”,即普通人穿越到历史时空,就会改变“个人”命运,取得人生成功,甚至改变历史,以“蝴蝶效应”影响当下现实。“穿越”的心理暗示,让读者无视故事情节漏洞和人物延续性,在对历史的改造中,完成了个人主义“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无论成为明君霸主、赫赫战神,或宫廷宠妃、古代女主,抑或绝世良医、商业大鳄、武林高手、风流文豪、考试学霸。这些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者,依靠现代人的知识、眼光,思维模式,及对历史缺陷的“未卜先知”,不仅拥有金钱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实现马斯洛说的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超越的需要。他们建功立业,开疆拓土,建设现代制度,发展现代文明,成就现代强国,或成为男性仰视的女强人。在穿越者身上,那些被中国文学遮蔽的个人主义强者气质,被展现了出来。历史与现实形成尖锐对立,这些穿越者们,充满了“征服”的幻想,征服前现代,征服历史,征服异族,征服世界,进而塑造真正强大的“现代自我”。 同时,这也是一个“传统伦理崩溃和重生”的过程,那些曾束缚个人意志的意识形态,都在穿越历史、改造历史过程被重审——无论五四式启蒙,还是革命叙事、儒家意识。这些穿越者,赤裸裸地谈论利益,在后宫淋漓尽致地钩心斗角,或在商场与政界“扮猪吃老虎”。任何宏大话语的“责任体系”,都必须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被重塑,而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使得这些穿越者充满了“资本的魅力”。如古龙岗的《发迹》,穿越大学生何贵,借助创意学和经济学知识,在清代建立商业帝国。阿菩的《东海屠》,穿越者东门庆,凭借野心和计谋,虚构了明末的大航海时代与殖民浪潮。老白牛的《明末边军一小兵》,穿越者王斗只是明末边军火路墩的小兵,他奋力杀敌,加上现代军事知识,成为一方枭雄。这些个人主义气质,在女性穿越小说中表现得更曲折隐晦,然而,那些在现实中灰暗压抑的女性,却在历史的穿越中,曲折地实现了“女尊”的个人理想。如浅绿的《错嫁良缘之洗冤录》,把现代的法医素质与方法放到古代时空中,让原本平凡的女子运用现代法医的手段屡破奇案,声名远扬。桐华的《步步惊心》,穿越小白领若曦,倔强任性,和阿哥斗嘴、和格格打架,却让众多优秀男士为她倾倒,而她也不自觉地卷入了九王夺嫡的历史风潮。 史蒂芬·卢克什曾区分两种现代特征的“个人主义”:“一种是个体与其角色,与其目标和决心相关的独特画面。个体显示其角色距离,勇敢面对所有可能的角色,原则上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接受、扮演或放弃任何一个角色。作为独立自主的选择者,他在行动、良好的观念、生活计划之间做出决定。具有这些本质特征的个体作为一个自治的、自我指导的、独立的代理人思考和行动;而另一种则是个体很大程度上和角色认同,被角色界定,他与目标和意愿的关系,较少由个人选择来决定,而是通过知识和发现来决定。自我发现、相互理解、权威、传统和美德在此至关重要。我是谁?这个问题由我所继承的历史,我所占有的社会地位以及我被装载的职业道德来回答的”⑦。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书写,“个人主义”话语主题,主要描述卢克什说的“第二种个人主义”,无论具宏大色彩的伤痕、反思小说,还是王朔式的痞子写作、激进的先锋小说、身体写作,新历史主义书写,“个人主义”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对稳定价值观缺失的关注”“对自我与社会角色差异性的体验”“对成为某个群体部分的强烈渴望”⑧。怪异的是,如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这样的“通俗文本”,个体作为“自主的人性自我”,反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那些穿越者,不但表达了对自由、民主、尊严的进步渴望,且充满了从“自我内部”发现意义的能力。他们不再是群体边缘人,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主体的英雄。他们在历史中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和意愿。邹邹的《清朝经济适用男》虽也写穿越女工程监理与皇子的纠葛,但描述重点却在齐粟娘的女性主体选择:她有非凡才华,也深爱老实厚道的小官员陈演,拒绝成为十四阿哥、漕帮大当家连震云等男性的玩物。天使奥斯卡的《篡清》,穿越者徐一凡铁血改革清末军事,他嘲弄维新变法的虚伪与革命者的天真,赤裸裸地割据朝鲜,防止甲午民族悲剧重演,也实现了“对抗贼老天”的理想。欧阳锋的《云的抗日》,穿越者欧阳云,回到抗战的热血岁月,凭借浑身功夫与报国之心,带领同胞,成就了“伟大的抗战胜利”。 然而,我们可以将这些个人主义气质的通俗小说文本,简单看作鲁滨逊式的个人英雄的中国穿越版本吗?这些主体自我想象背后,也表现出对“共同体”的热切参与与主动建构的热情。这些共同体诱惑,不再以宏大叙事名义(如革命、现代化),压制“个人主义”,而呈现出在此基础上的新民族国家叙事姿态。王绍光认为,发轫于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使市场原则侵入非经济领域,成为整合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的机制,从而导致1949年之后建立的“伦理型经济”的全面崩溃⑨。其实,这也是“重建伦理”的过程,不过这个伦理不是革命和家庭伦理,而是“个人主义”新伦理,即保障个人自由、尊严和生存发展权,支持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鼓励个人责任义务与物质回报相结合。正如张旭东所说:“目前的挑战正是:要在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中寻找一种重新想象民族的方式。这种话语将建立在复兴的乌托邦期待之上——后革命时期世俗化过程并不只是撕下了一个半农业和半斯大林政体的规范和禁忌,同时也将历史悠久的市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留待历史检验。世俗化不仅蔑视传统的政治,几乎无私地追求一种新的,在社会经济方面得到界定的自我:它还在其庸碌的俗常生产、消费、交际、实验和想象中创造了新的可能的共同体,创作出参与、文化与民主。”⑩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的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促进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新民族主义”要求。这种复兴的乌托邦期待,包含着新的想象和民主自由的要求——既不完全同于西方的民族历史过程,也不同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规定性。 同时,民族国家想象,又是个人主义“无法选择”的共同体诱惑。合理的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民族主体必须首先是他或她的个人的利益主体。中国和欧美社会的一个不同在于,中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冲动。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正在发展之中,现代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富裕的民众生活,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高度发达的民主自由、公正的政治体制和开放自由的公民话语空间,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发展内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作为重要口号,被执政党提出来。然而,现实生活中巨大的两极分化,强大的生存压力,腐败、炫富和文化体制的相对不自由,都使民族国家想象一方面似乎成了唯一能被官方和大众双向接受的合法想象;另一方面,却又存在严重偏颇性,五四以来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无不是在巨大的意识形态符号束缚之下,以牺牲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有“压倒了启蒙”的救亡,也有“领导一切”的革命。只在1980年代后,当革命化的均质社会趋向解体,个人主义浪潮再次出现,并以欲望叙事等特征,成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个人主义话语才在社会公共空间中逐步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这种“个人主义呼唤”,并未在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形成相应伦理权威和制度保障,从1990年代的主旋律文艺到新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抗战剧,就可看出端倪。民族国家叙事,是当前“最大的”合法性话语,无论何种个人主义话语,在历史领域的书写,如果不借助民族国家叙事,就很难在潜在文化心理认同上取得成功,也很难取得主流默许,进而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对这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意识,张旭东认为:“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或职业白领阶层没有对抗政府的自由,但他们还是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半自主社会和文化空间,结果,在一个初生的中国公共空间里就出现了新一代的民族主义者:正是市场蓬勃而普遍的发展以及国家力量不断撤退和去中心化,创造出了这个巨大的话语空间。换言之,如果他们是集体归属感的因素,他们既有世界主义的渴望,也几乎宿命般地认识都了世界主义的局限,他们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对欧美在早先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民族主义的理性效仿,也希望在认同已变得均等而单调的时代里维持某种中国性。”(11)尽管张旭东夸大了市场社会作用,并忽视政府的动员和意识控制能力,但他还是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问题,那些《中国可以说不》等粗浅通俗民族国家政治读物,其实正透露出“新公共空间”对“重建共同体”的诱惑与焦虑。随着大量城市自由流动的职业者的出现,原有计划体制的国家宏大话语失效后,都市自由民和主流意识形态其实都急切地需要某种宏大共同体理念,进行归属感的认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红色资源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在主旋律式的杂糅与整合下,逐渐形成了新权威表述方式,而那些发自都市文化空间,一开始是报纸、出版物和影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新世纪后,逐渐转变为网络为平台的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新共同体诉求,网络穿越小说,恰有这些“新共同体诉求”的言说痕迹。 与官方塑造的认同方式有差异,民间自发的民族国家意识,展现出了更为宽阔的包容意识,在穿越历史的过程中,大量的作者呈现出了熔铸他者,再造自我的勇气和魄力。这些小说不仅体现为现代性对前现代的征服,也同时表现为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不同文明形态、文明阶段概念的“尊重”。各种文明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在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去除偏见与强制,保留激情和理想,重新熔铸一炉。在小说叙事形式上,则表现为更宽广的叙事时空与宽松的心态,一切风花雪月的爱情,如同一切金戈铁马的征服,都在个人主义的基础被重新立法,并赋予了民族国家以新的想象。路易·加迪在谈及中国人的历史观时,认为“宽广的历史全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法”是其独特内涵,不同于欧洲史家“专注一国”的态度(12)。而网络穿越小说中,我们在现代性基础上,重新恢复那些全景式和内观法的史观建构。“世界史”正在变成“中国史”想象(13)。实心熊的《征服天国》,中国少年穿越中世纪,在圣城耶路撒冷,重现了骑士精神的骄傲与荣耀。红场唐人的《燃烧的莫斯科》续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表达了对苏联红色理想主义的怀旧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很多小说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如衣山尽的《大学士》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细节的描述,从琴棋书画,到漆器和木器的制作,从文采诗歌,到典章制度,甚至对八股文,也没有彻底否定,而是以精彩的考试制度,写出中国传统文人历史感非常强的生活场景。愤怒的香蕉的《赘婿》则表现了对儒学活用与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性思考。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利用清秀流畅的语言,写活了魏晋风物想象。文人雅士的诗画琴笛,宴饮交游,道家修仙与医家救人,魏晋的风评人物制,都被细腻呈现出来。而他的另一部作品《雅骚》则让穿越者张原来到万历朝,逼真地为我们描述了明代的文人趣味。 我们甚至看到很多历史“另类想象”,原有的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似乎都能在这些新“包容性想象”得到新的解决办法。而这些包容性想象,有的是更宽泛的民族主义,如龙德施泰特的《另一种历史》,重新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在抗战胜利的历史关头,让国共继续合作,对抗苏联入侵,直至建立两党制的,美国式现代文明强国。有的则表现为对革命理想主义的留恋与反思的双重情绪,如豫西山人的《重生之红星传奇》以红军湘江惨败为背景,描述了刘一民从红军战士成长为军长的经历,既写出了对革命叙事的怀念,也写出了对“左倾”专制主义的痛恨;有的则试图在大中华议会制度下实现民族的和解与共同繁荣,实现以商业立国的理想,如阿菩的《边戎》,写了一群穿越者,在疑似北宋末年的朝代,建立民族现代国家的努力。也有些小说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性征服模式的反思,酒徒的《家园》没有将草原民族和汉族对立,而是写出了各自的文化魅力和内涵,而长城上矗立的那把威武不屈的大槊,最终让李旭拼死守卫战场,也让幽州大总管罗艺放弃了让异族进长城的念头。《家园》表现出的守望家园的和平意识、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交流的开放姿态,无疑是穿越小说的新民族国家叙事最好的注脚。在这种新的民族国家意识之下,很多穿越历史小说,也出现了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审视,特别是那些经过五四启蒙和革命意识形态双重改写后的历史人物。例如,庚新的《刑徒》,将汉高祖刘邦塑造成了无能的混混,而将吕雉描述为深明大义、聪慧善良的女人。大爆炸的《窃明》质疑袁崇焕的民族英雄身份,以民族国家意识,对袁擅杀毛文龙,与后金私自媾和等行为进行了谴责。天使奥斯卡的《篡清》,对晚清著名历史人物的“重审”,颠覆了中国近代史对戊戌变法的“启蒙进步”描述,光绪的无能软弱,慈禧的阴毒自私,康有为狂热的名利欲望,翁同龢的首鼠两端,都被作者写得淋漓尽致。 灰熊猫的《伐清》则是这类以民间民族国家想象,“重新设计中国现代道路”穿越历史小说的代表。穿越者邓名来到了清朝初年的四川,在他的帮助下,反清复明的力量大大增强。然而,和一般的穿越历史小说不同,该小说的重点并不在民族复仇上,而是试图在民族和解、双赢的思路下,通过互惠的双边贸易,海外殖民贸易,配合强大的科技创新,实现一种类似“欧盟”的民族国家联合体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这个思路下,邓名既重视发展军事,更重视发展商业和科技,注重现代法律和议会制度建设,甚至主动给自己的权力套上枷锁,容忍不同派别和政治思想的存在,兼容并包,共同发展。在他的带领下,贸易联盟不断扩大,这种经贸和政治合作的方式,团结了周培公等江南各省总督、李定国等各类反清势力,甚至清政府和吴三桂。而联合政府的立国思想,正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每个人才能的“个人主义”。当书院的学生询问邓名的做法的原因,邓名回答: “你们中有的人有农业的才能,会培育出高产的作物;有的人有工业的才能,能设计制造出精巧的机器;有的人有文学的才能,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有的人有绘画的才能,可以描绘壮丽的山河……如果没有机会学习,你们的才能就会被埋没,太阳日复一日的起落。但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有你们的才能施展出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永远不受到野蛮人的威胁,让我们的子孙享受到他们祖先无法想象的生活。因此你们要学习,当你们找到了你们的才能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有了光辉的未来。” 在灰熊猫的民族国家想象中,“邓名的中国”,摆脱了中国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血腥杀戮立国的权力更迭,既是一个现代国家,有着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又符合中国的国情,有着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独特的人性化魅力: “我的志向?”邓名哈哈一笑:“我希望驱逐鞑虏后,院会里坐满了来自全国的议员,他们代表着全天下的百姓……”说到这里邓名突然停住了,他本想说希望议员们会在他进门时全体起立鼓掌,出门时议长会说“我们代表全体国民,感谢您多年的为国效劳”。 从中国文学的历史问题入手,我们也可看到网络历史穿越小说的“独特微妙”之处。如果说,惊悚、玄幻等网络小说类型,利用网络消费平台,完成通俗文学的市场化发育,那么,穿越历史小说则充分地利用了历史想象的政治性。假如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也有很强的消费性,也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焦虑基础上的历史消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我们能发现从“戏仿”和“戏说”到“穿越”的逻辑变化轨迹。 “戏仿”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理论语汇,在1990年代的小说中,戏仿是我们理解小说与历史关系的切入点,王小波的《红拂夜奔》,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刘震云的《故乡到处流传》,李冯的《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孔子》,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都有“戏仿”的特征。华莱士·马丁认为:“戏仿本质上是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体裁的种种形式特定的夸张性的模仿,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的不符。戏仿夸大种种特征以使之显而易见,它把不同的文体并置在一起,使用一种体裁的技巧去表现通常与另一种体裁相联系的内容。”(14)无论是作为文体的互文性,还是作为修辞性,戏仿所要表达的历史观,往往是对权威的历史观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挑战和道德嘲弄,它们要表达的,往往是更个人化的,颠覆性的,甚至有几分狂欢化虚无色彩的文本。因此,王小波将“风尘三侠”的故事,变成了数学流氓、神经歌姬与变态杀手的情感纠葛;刘震云笔下,曹操变成了满嘴河南脏话,喜欢玩女人和大铁球的败类;李冯的笔下,武松变成了胆小鬼;苏童的帝王则变成了玩命的走索艺人;阎连科的视野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高爱军的性爱狂欢。可以说,戏仿有强烈的消解历史宏大叙事的效果,无论启蒙还是革命,在戏仿的参照下,都被剥夺了宏大的权威性。 然而,和戏仿这样纯文学色彩强的语汇相比,还有些适合影视传媒的,更软性的,商业化历史的处理方式,比如常用在电视剧的所谓“戏说”,如《康熙微服私访记》《戏说乾隆》,这些“戏说”有传统说唱艺术的残留痕迹,评书、京剧等传统艺术,就有戏说的传统。历史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在戏说之中,往往更温情,调侃,但“敬畏”依然存在。可以“游戏”着说,但不可“仿”,因为“说”有客体的,旁观者的位置,而“仿”则有主体性的模拟行为。在影视剧这些商业行为更浓厚的文本形式,历史往往因历史人物的世俗化拉近和平民百姓的距离,历史人物也往往能更多地展现出人性化和日常化面貌。如《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皇帝访问民间疾苦,不惜装扮成叫花子、矿工和饭店老板,既让民众因为身份差距变化,带来观看趣味,又让百姓认同清官思维。当然,戏说的过程,由于夸张的修辞,也有可能变成荒诞的搞笑,如周星驰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鹿鼎记》。 “穿越”历史小说,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变得更加暧昧。《穿越时空的爱恋》(席绢)与《寻秦记》(黄易)是两部早期的穿越小说,它们关注的还是“穿越情节”所引发的浪漫情愫和“历史错位拼贴”所引发的知识乐趣,“戏说”和“戏仿”的味道还很重。然而,2005年后,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阿越的《新宋》、桐华的《步步惊心》等网络穿越小说再次勃兴,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含量、意识形态意味和叙事特征,却变得更复杂,读者对此的接受心理,也变得更加丰富。个人主义的诉求,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诱惑,在历史的解构中,又透露出了极强的历史建构性。历史穿越小说,空间感是不断开拓的,而时间感却表现为历史意识本身的模糊,或者说,更强的当下性,无论穿越到何时空,我们总是以现代人眼光来看待并改造历史——我们明知这是假的,但偏要把它当作真,并在其中收获心理快乐。这种心理愉悦,并不仅是叙事预先反转导致的张力,已知历史结局与主人公奋斗之间的对立,而且是“过去”对“现实”的刺激,现实失去历史感的疼痛,身在“过去”找到了历史存在感,而现在则无从选择,当下生活是逃离的,痛苦的。这种双向的心理张力,其实将叙事者角色一分为二,一个古代的,一个现代的;而且,读者的眼光也由此被一分为二,一个古代的视角,考虑真实性问题,二是从现代的角度,考虑是否满足共同体想象和个人主义主体性。 然而,尽管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表现了当下中国对个人主义和新共同体理想的呼唤,但穿越与戏仿、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穿越并不能真正形成文本内部“可逆性”和“互文性”,却可以形成叙事声音和眼光的“虚拟占有性”。这也是双重的占有性,是对真实性和虚拟性的双重占有。戏仿的可逆性中,反思是存在的,借着过去反思现在,借着现在反思历史。然而,穿越历史中,前提被假设为“真”,又是真的“假”。历史本质论意义的真实被完全取消,而沦为某种游戏的兴奋点。真和假的界限模糊了。历史也就变成了“不可知”的事物,这些不可知的历史残留物不是从颓败废墟爬出的亡灵,而是“当下现实”所腐变成的僵尸。它既是死亡之物,又是在当下的活物。它“非生非死”,却对生和死同样贪婪而执着;它拥有“死亡”的终极不朽性,也拥有“生”的行动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极端心理刺激性(半死),它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在个人主义和集体性之间,求得某种致命的诱惑。然而,它又只能成为当下社会中国现代性“无法完成”的某种症候性表象。 很多文艺理论家认为,“短暂的20世纪”(霍布斯鲍姆语)的“最后十年”至关重要,1990年代后,是多元代替一元,大历史观念走向终结的时代,大历史观念既指中国现代以来形成的革命历史观,也是新时期新启蒙历史观。1990年代后,又是后现代来临的“非政治化”年代。汪晖称为“去政治化”:“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15)。这些去历史化的小说,集中体现在从王朔到王小波、朱文等很多持边缘化姿态的个人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家身份也在90年代开始摆脱集体束缚,以自由撰稿人,独立小说家、甚至网络写手的身份认同,不断地在标识着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的时代的带来。 网络生存的状态,也部分改变了阅读和共享文化空间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变得更“个人主义”——这首先让我们更少参与公共性普遍伦理和事务,而是“守在电脑前”,靠网络虚拟空间形成的社交网络,进行虚拟想象活动。这种网络的文学生产、阅读、传播和评价体系,由于网络虚拟性质,带有更大的个人性。后现代社会的重大形态转变就在于,原有民族国家想象这类集体性宏大概念都已失效,而弥散的个体主义导致社会呈现出原子化状态:“后现代性的进程进一步地促进了个人的自由与选择,这使得维持持久的或永久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后传统时期,我们更容易摆脱那些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因此平添了对于其他人是否可以信任的疑虑。于是,某些社会资源就会受到削弱,而这些社会资源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16)有的说法是,互联网让交往回到部落式地方性认同状态,而“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指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向不特定大多数或特定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总称。自媒体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的出现,让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认,具有更大的民主性和个人主义特征。 但是,“去历史化”只是新时期以来的一种历史思维倾向,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育,城市化进程加快,人际流动性的增强,出走于革命、新启蒙等宏大叙事的中国社会,也在悄悄地增长着对于个人尊严、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性建构热情。所谓网络“个人主义”,无疑具有很大虚拟性和现实制约性,也有理论家乐观的“理论预设性”。中国的网络文化传播,与西方相比,虽处于全球化过程,但无论“脱历史”,还是“自媒体”式个人主义,与中国现代性本身发育还有很大差距。在主流政治依然具权威性和执行力的中国,在依然存在巨大发展动力与现代化建设可能性的中国,任何脱历史的幻象与虚拟个人主义表征,都无法掩盖现实中“建构自我”的诉求。不但高度自治和民享基础上的网络个人主义并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境,即便传统自由民主体制建设,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也就是说,媒体方式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不过是将其变得更模糊与不可控。由此,那些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中共同体诱惑与个人主义气质,与其说是新媒体时代造成了虚拟认同形态,不如说是网络释放了那些被传统文学和官方意识压抑的现代性渴望,而表现出的对个人权力、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和民间化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激情。陈晓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历史化进程不一样,西方是由个人力比多推演出了伟大历史,而我们由于民族国家和道德的理念过于强大,则由集体性观念推导出大历史。即便我们拆解历史惯性,但大历史逻辑却制约着我们时刻身处历史幽灵之中。”(17)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些荒诞不经的穿越历史奢求,这些反“纯文学”的通俗文本,潜藏着“个人”的现实批判和建构渴望? 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要表现的“个人主义”,恰不是理论家归纳的后现代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以虚拟方式书写的,更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诱惑”。因为“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外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与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建立”(18)。这种诱惑,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定义,表现出某些民族国家想象发生之初的表征,如主体的人,对物质欲望的肯定,对资本契约精神的推崇,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等。这些东西恰又不是“戏说”和“戏仿”,而充满了建构的热情和自信——也许,这恰是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中国特色”,也符合詹姆逊“永恒的历史化”的判断。詹姆逊认为:“依据表现性因果律或寓言的宏大叙事进行阐释,如果仍然是一种持续不变的诱惑,那么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本身已经刻写在了文本和我们关于文本的思考中了,这些寓言的叙事所指构成了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持续不断的范畴,恰恰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有关历史与现实的集体思考和集体幻象的基本范畴。”(19)在中国逃离红色教堂,狂奔于现代化旗帜的道路上,“穿越历史”似乎并不是为“留恋过去”,而是宣告那些“集体思考和集体幻象”:那些铁血金戈、或资本兴起的世界征服故事,“男卑女尊”的爱情征服故事,为当下个人奋斗梦想和共同体所诱惑,写下了曲折隐晦的“寓言”。 也许,这些寓言的“荒诞”在于,“最真实”的穿越,就是“最完美”的罪行。高精度的历史仿真游戏,代替历史真实渴求,恰说明了当下历史建构的被压抑遮蔽的缺失状态。由逃离现实和批判现实所组装而成的“穿越历史”征服快感,同样蕴藏着深刻的脆弱和冷漠。然而,正是这些荒诞不经的“穿越”故事,组成了一个仅仅是“表象”,而缺乏“实践能力”的世界。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且由于无痕迹,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20)也许,正是个人主义、共同体诱惑、穿越史观,构成了穿越历史小说的“三宗罪”,让一切试图缔造“伟大复兴”的官方宏大叙事主流企图遭遇了尴尬的背叛。 注释: ①龙柳萍:《接受美学视域下的网络穿越小说——以桐华〈步步惊心〉为例》,《柳州师专学报》2012年第4期。 ②李玉萍:《论网络穿越小说的基本特性》,《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普实克著,李燕乔等译:《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黄平:《反讽、共同体和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的〈顽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7期。 ⑤张颐武:《在边缘处求索》,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⑥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观——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⑦⑧贺美德、鲁纳编著,许烨芳等译:《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第204页。 ⑨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1页。 ⑩(11)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28页、第107页。 (12)路易·加迪著,郑乐平、胡建平译:《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13)房伟:《穿越的悖论与暧昧的征服——从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谈起》,《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14)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5)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9页。 (16)保罗·霍普著,沈毅译:《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17)陈晓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8)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19)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0)让·鲍德里亚著,王为民译:《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