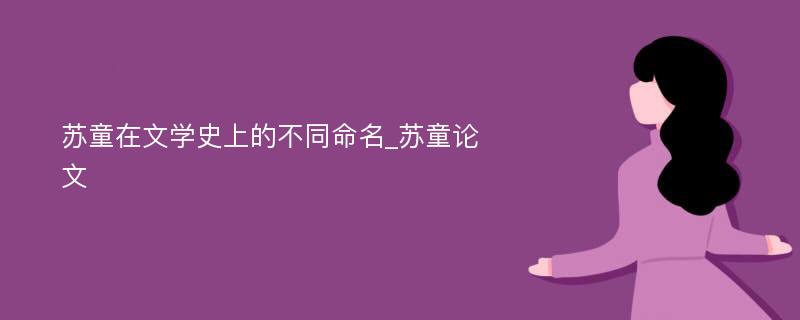
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众多先锋小说家中,文学史对苏童的命名应该说是最繁杂的,似乎他很难在当代文学史上“认祖归宗”。在孟繁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罗列了根据辽宁大学王春荣老师的统计,60年代至今出版的60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1) 本文从中选取了几部书写苏童的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大致根据时间的顺序,苏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别有如下的命名: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另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处理。其他先锋小说家,例如马原、余华、格非,在文学史中是很少有争议的,是“根正苗红”的先锋文学的代表,而苏童的头上却被扣上了太多顶帽子。诚然,“文学史不是孜孜以求一个想象之中完美无瑕的‘定论’——无论这样的‘定论’是叫做‘科学评价’、‘历史真相’还是别的什么;相反,文学史写成了一种效应史,一种注定要在时尚、趣味和不同时期的风格之中不断修改的文学史”(2),那么,苏童为什么在这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的修改,拥有了不同的命名,这其中的渊源在哪里。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以苏童的代表作《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为中心,探讨苏童在被建构的过程中,文学史对其的书写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而这种权力的实施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一概念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文学语境在不断变化中,所以在不同时期对苏童的理解自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一、“后现代性”的开端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是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集,此书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给予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对西方理论发展的总体情况作了评述,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登陆还是比较早的,可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融合还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中,苏童被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小说,这是写得比较早的文学史。“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思潮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与中国现实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只限于极少数的作者和读者,因而只是孤寂而非普泛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小说是以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3)。的确是这样,“当80年代先锋小说集中出现的时候,我们感到了现实主义批评的无力,只能给它冠之于一个‘形式实验’的名称。接着,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的加深,批评界又发现,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它进行阐释是非常得心应手的”(4),正是由于批评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运用,才导致了文学史中对苏童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命名。“在文学史上,总是有些批评家与一些作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不管他们是同舟共济还是反目为仇”(5),在1989年,即先锋文学“谨慎的撤退”(6) 的一年,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有一篇王干与陈晓明之间的重要对话,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在这里,强调了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并且说“可能是出于某种巧合吧。1934年正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语中的年代”,“这种巧合倒可以印证分解主义的一个观点:并不是人在驾驭语言,而是人的表达受制于语言的力量”(7),应该说,这篇文章的批评对文学史的写作一定会有影响的。这本文学史选取并概述了苏童的代表作《1934年的逃亡》与《罂粟之家》,文学史中认为《1934年的逃亡》“带有一种种族寻根意味和神秘氛围,作家是要在小说中实现一种形而上的神秘感和形而下的历史感的相悖组合,以求把握和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动因和原生真实”(8),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以一种本体论为核心的观察世界的观念取代了现代派的主体论观念,并且形成了一种无选择性、断片式或精神分裂式文本结构为特征的叙事风格。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解除了绝对信仰和终极价值之后的,破坏性的、表演性的文学”。(9)《罂粟之家》“尚带有《1934年的逃亡》的流风余韵”(10),它主要书写的是“一个地主家族兴盛、衰亡的过程。这个家族颓败的故事内涵相当丰富:历史与生殖、压迫与报复、血缘与阶级、革命与宿命等等,或对立或统一”(11)。如果说金汉等人的处理是由于他站在当时的话语语境之中来命名苏童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性,或者说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他是不会不知道的,只不过这是他所在的角度而已。
当然,后现代性与先锋性是不矛盾的,后现代性在文学上,表现“寻求超越性的精神信仰,表达反社会的抗议情绪,沉迷于神秘性的生存体验,广泛运用象征和隐喻来表现不可言喻的精神深度等等,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12),而80年代后期的情况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在逃离“新时期”构造的主流意识形态,格非说,“我所向往的自由并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争取某种权力的空洞口号,而是在写作过程中的随心所欲”,他指的主要是语言和形式,这一批先锋小说家都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13)。所以,他们“发明”了自己的“先锋”写法,这种“先锋”写法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艺术规范之中的,所以说,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不过,还是各有侧重的。
可以看出,这些概念之间的缠绕,“‘先锋派’或‘后现代性’,都不过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在80年代后期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一点生气(生动)”(14)。那么,金汉等人对苏童的命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先锋文学”的正名
“先锋文学”也许是苏童最正式的命名,“在先锋文学概念里,包括的代表作家大体有较早的马原、洪峰和稍后的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等”,“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冲击也最大”,“比较刘索拉、叶兆言、刘震云等人,他们在先锋的跨度和实质远远胜之,创新和前卫意识也更强,是最能承担‘先锋’称谓的一部分”,(15) 有许多文学史是这样处理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史,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等,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苏童是先锋文学的杰出代表,并呈现了坚实的理由。
客观地讲,苏童在文学史中曾经有过“无名”的状态,那就是在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的目录中,苏童被收录的那一节的题目只有“小说”两个字,至于是什么类型的小说,并没有被交代出来,或者说作者也感到很为难,于是用最简洁的“小说”两字,一笔带过,只是在具体的篇目中略微地提到:“自80年代中后期突起的先锋小说家是一个不小的创作群体,其中引领潮流的有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人”(16)。王庆生的这本文学史写于1999年,可能在当时写作时,作者也感到了将其归类、命名的棘手,既然如此,索性不做这样冒险的工作,但又不能不将其收录进来,毕竟这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也许是作者本着这样的想法,把它命名为“小说”当然是万无一失的。
在贺桂梅的《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归纳了目前通行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和文学史写作中,有三种对先锋文学的描述:一种是认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新潮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这样一个“后浪推前浪”式的文学思潮展开(同时也是“进化”)过程的环节,这种文学史强调的是70年代至80年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性,而先锋小说正是文坛持续创新的一个结果;另一种认为所谓“新时期文学”并不是开始于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1985年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到1985年寻根文学,到1987年实验小说这样一条线索去考察,直到出现余华、苏童、格非、马原这批作家,这时候文学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或者说革命,这种文学史叙述,强调的则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叙述成规的突破,并将先锋小说视为新时期文学真正开端的标志;第三种文学史叙述,就是在90年代初期有关“后新时期”的讨论中,论述者尽管在开启时间是1985年、1987年还是1989年上存在着争议,但倾向于将“先锋小说”视为另一时期——“后新时期”——的开端。(17) 不管文学史对先锋文学如何描述,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先锋文学的特质:“先锋小说的‘语言革命’或‘形式革命’,事实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革命’”(18)。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的写作距先锋文学活跃的1987年、1988年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文学史家们似乎更认可先锋文学在语言与形式上的革命来颠覆现实主义话语的统治地位的说法,于是对苏童作了先锋小说的命名,因为《1934年的逃亡》在《收获》1987年第5期的发表,使苏童成为“突然的先锋派”(19),“作为先锋作家,苏童的文体实验和操作更令人着迷”,“小说中叙事者具有‘多功能性’,他的小说通常都用第一人称‘我’,给人一种直接切入感。这个‘我’是一个与作家本我脱离了的叙述者,在对作者的‘背叛’中,‘我’获得了一个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在《1934年的逃亡》中作者提醒读者:‘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19) 这里与先锋派的第一人马原的“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当然,信不信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是不能要人强信的”是多么的相像。《1934年的逃亡》是确定苏童成为先锋派的标志,还依稀可以看到他模仿的痕迹,而接下来的《罂粟之家》,则更感到苏童先锋性的完善,“则真正显示了苏童的风格,这个家族颓败的故事内涵相当丰富:历史与生殖、压迫与报复、血腥与阶级、革命与宿命”(21),这正是先锋文学惯于表现的题材。这两部作品均为中篇,苏童很少有长篇的作品,这不仅仅是作者的兴趣使然,而是,先锋文学注重形式与语言的革命,而这种形式决定了只适合写成中短篇,而不是长篇,因为它并不十分注重内容。
文学史家在写作的时候,会受到当下历史情境的影响,会受到文学评论的牵制,“文学史并不是恰当的历史,因为它是关于现存的、无所不在的和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22),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在文学史家命名苏童为先锋小说的代表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批评界对先锋文学的关注程度。关于先锋文学,比较著名的理论论著有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洪治纲的《守望先锋》等,而学术论文则是铺天盖地,例如谢有顺的《绝望:存在的深渊处境——先锋文学中的一个现代主义主题研究》,吴亮的《回顾先锋文学》,赵卫东的《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张学昕的《想象与意识架设的心灵浮桥——苏童小说创作论》,葛红兵的《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等等。这些批评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苏童写作的早期作品,最重要的是《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最明显的姿态是先锋的,在语言与形式上是很下工夫的,而后的《平静如水》,“这个象征性的题目表明苏童迅速结束了他的先锋派生涯,他后来写下的《妻妾成群》这种作品,不过是他更上一层楼后回归故里”(23),与其他的先锋小说作家一样,都是昙花一现,先锋文学是转瞬即逝的流派,那么,它最灿烂的特质便是它语言与形式的先锋性,正是因为他的先锋性,而使得他被文坛关注,当先锋派不再适合时代的潮流,那么,作家的流变也是顺理成章,但人们更深的印象,也许就是在最初留下的,就是因为《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是苏童最早被关注的先锋文学意味很浓的作品,而后来的作品不再有先锋特质,但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仍喜欢用这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来概括整个作家的命名。其实文学史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的问题,比如“与作品有更多可读性和传统文人小说风味的苏童不同,格非更具有浓厚的先锋性”(24),言外之意,苏童是不太先锋的,还有苏童“虽被列入‘先锋小说’,但较受人们注意的还是描写清末民初‘家族兴衰史’”(25) 等等,都表明了文学史家的分寸与明确。
三、“新历史小说”的分歧
在后现代性与先锋性的缠绕中,新历史小说的命名似乎显得特殊一些,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中认为,“在众多的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中,苏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26)。是的,张清华在新历史主义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位学者,他也坚持苏童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在所有先锋小说作家中,要数‘历史叙事’的数量和在此方面表现出最浓厚兴趣的,无疑也要首推苏童”(27)。那么“之所以把一些先锋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典型例证,是因为它们在总体上呈现了类似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的一些特点”(28)。这区别于旧历史者确信历史的某种主流文化的存在,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关注历史与当下的内在联系;不把历史看成一个遥远的过去,而是与现实密切相连的过去,强调主体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在历史空间中的创造;把历史当做一种重新被书写的个人化话语”(29)。苏童有许多作品都是这样的写作方式,例如,《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又名《紫檀木球》)等,苏童自己也说:“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所说的方式勾兑的历史故事,年代总是处于不详状态,人物似真似幻”,“人与历史的距离亦近亦远,我看历史是墙外笙歌雨夜惊梦,历史看我或许就是井底之蛙了”(30)。正是由于这样的写作观念支撑的写作,导致了苏童在文学史上又多了一个“新历史小说”的命名。
张清华则认为,“从1987年前后持续到90年代前期的先锋小说运动,在其核心和总体上也许就可以视为是一个‘新历史主义运动’”(31)。那么,在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概念问题,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与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同1987年之后的先锋新历史小说,相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种种惊人的契合之处”,我们知道,80年代是西方文艺潮流大量涌入的时期,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和哲学基础正是这些所谓的结构—后结构主义,以福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在80年代进入中国的时候,当然会冲击和更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观。因为像苏童这样的一批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思想以及西方作品的影响,贺桂梅在《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探讨了先锋作家的知识谱系,其中着重论述了先锋小说家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手法的反叛和对西方作家的模仿与借鉴。那么,也就可以说是在这样大的文学环境中催生了一批新历史小说,是由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的影响,那是否就可以把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与中国的新历史小说等同起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新历史小说除了借鉴西方新历史主义以外,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苏童的新历史小说中依稀可以找到传统故事的影子,比如《妻妾成群》,不能不承认《红楼梦》、甚至《金瓶梅》的母题的影响。苏童的新历史小说是在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之间,在作家的自我的形式中搭建起来的。
80年代后期的文学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先锋小说家以其崭新的形式与语言区别于现实主义主流文学,或者说是对主流文学的反叛,而新历史小说与先锋文学是不矛盾的,甚至是它的接续,当先锋意味变淡而注重故事性时,并没有完全放弃艺术上的创新,那就是对历史小说的反叛,出现了我们见到的新历史小说。实际上,苏童的新历史小说除了具备较强的“新历史主义”的倾向或性质外,还有接近中国传统小说的一面,张清华认为“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其实包含了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念相通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的神髓’也使他对历史的叙述元素化了——把历史抽象为某种文化结构,这也是新历史主义的应有之义。而苏童是最擅长这一点的”(32)。《妻妾成群》是明显的例证。
批评家们看到了这种对历史的另种搭建,《米》的历史叙事是具有寓言性的,“‘米’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全部生存的根本保障,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不过都是围绕着关于‘米’的生存斗争与搏杀。在这样的一场无止境的游戏中,一切罩在历史真相之上的伦理、道德、温情等等社会学意义上的东西,都显得可疑和无关紧要”(33)。另外一部被张清华称为“游戏历史主义小说”(仍旧是新历史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苏童也同样是“对少年帝王的描述没有停留在顾念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而是沉浸在个人奇幻故事的虚构之中”,表现了他“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的强烈愿望”。(34)《妻妾成群》《米》和《我的帝王生涯》这三部作品在苏童的创作年表上是排在稍后的,除了《妻妾成群》发表在1989年,其他两部已经是在90年代发表的,而1989年也是特殊的一年,是先锋小说即将结束的一年,先锋小说家们纷纷转向,苏童也不例外,实际上先锋小说只存在了1987年、1988年、1989年三年的时间。而1989年之后,苏童并没有停止创作,只是不再先锋意味十足罢了,而是在新历史小说中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很好的成效。显然,在先锋文学已经撤退了的时候,再把苏童命名成先锋文学,是不合适的,而苏童作品中的这种浓重的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对于批评家们来说,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并且在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中,苏童是很突出的一位作家,所以文学史家作这样的处理,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苏童除了上述命名以外,还有一个个案值得关注,那就是在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有关苏童的介绍,没有出现在“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这一章中,只是在这一章的概述中简单提了一下苏童的名字,而苏童的出现是在“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这一章的独立一节中,即“从小说到电影:《妻妾成群》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作者认为“《妻妾成群》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35),并且用了不短的篇幅详尽地比较了作品与电影之间的差异,认为“在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中必然会丧失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同时也必然包括了商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36),其实,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交叉的地方。虽然作者在先锋一节中没有重点介绍苏童,但也会在概述中提到,虽然把苏童的作品作为专节处理,却又要冠之以“新历史主义”,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学史家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侧重,其实,陈思和这本文学史是很个人化的。在1988年8月11日至1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牡丹江师院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古、现、当代)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了“必须显现出个人对文学史的独特看法”,“应该允许个人有自己的标准、视角和价值观念,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才有可能出现真正多元化的局面”(37)。这种情况表明,“90年代中期后,一些具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取代‘集体’特征的文学史著作成为热门读本。这种‘个人’眼光的文学史都在试图摆脱历史叙述的约束,而有关80年代‘主流文学’的叙述于是出现了一些可以想见的变化。‘个人’叙述要求寻求新的观察方式,在方法论上放弃单一价值倾向”(38)。
上述围绕苏童而展开的文学史表述,表明对一个作家的文学史认同并不是一次完成的,纠缠在周边、差异明显的评论,既显示出人们在进行文学史定位工作时对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同时也暗含着对“正宗文学史”的强烈期待——没有一个治文学史的人愿意甘守“边缘化”地位。与此同时也说明,迄今为止“先锋文学”还难以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史概念,当人们对苏童创作的解释呈现出多种理论维度的时候,正好印证了苏童和其他作家所代表的“先锋文学”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研究对象,它与各种文学语境和解释模式的结合,都会生发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如果这样去看,“先锋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事实上还处在一种暧昧不明的不确定状态,它的“资源”正在被新的话语所整合、所利用,从而塑造成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先锋面孔”。这样一来,不少文学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因此都面临着“被推翻”的可能,而作为具有活力的“文学史重写”,恰恰可能在这里找到了它研究的新起点。
注释:
(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南帆:《隐蔽的成规》,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第8页,第18页。
(5)(10)(12)(1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原版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第6页,第320页,第14页,第7页。
(3)(8)(9)(11)金汉、冯云青、李新宇:《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92页,第594页,第592页,第594页。
(4)(15)丁帆、许志英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99页,第1272页。
(6)(19)(21)(23)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第91页,第94页,第91页。
(7)王干、陈晓明:《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
(13)格非:《十年一日》
(16)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17)(18)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10月。
(20)李赣、熊家良、蒋淑娴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2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2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25)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26)(29)田中阳、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第425页。
(27)(31)(32)(33)张清华:《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第59页,第113~114页,第129页。
(28)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
(30)苏童:《苏童文集后宫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34)张学昕:《想象与意识架设的心灵浮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1期。
(35)(3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第334页。
(37)陈思和:《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
(38)程光炜:《文学史与80年代“主流文学”》,《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标签:苏童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我的帝王生涯论文; 罂粟之家论文; 新历史主义论文; 逃亡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