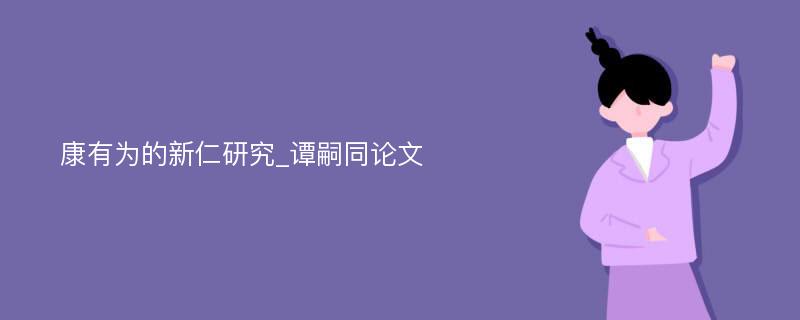
康有为谭嗣同的新仁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谭嗣同论文,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中华民族历代思想家对人际关系的沉思和伦理道德的调适。从“孔子贵仁”,到孟子“仁政”,再到朱子“仁统四端”,直到近代康有为、谭嗣同论仁,都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追踪时代的脉动,不断更新其内容。从发展形式上观察,中华仁学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新陈代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孔孟儒家的仁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仁,而康有为论仁尤其是谭嗣同著《仁学》一书则是把儒学近代化,用近代价值观念对古代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建,把儒学的思想核心仁从传统引入现代。从仁思想发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判断,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新解说,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的形成。本文把康有为谭嗣同的仁思想称之为“新仁学”,以区别于前此的中世纪“旧仁学”,并从本质与特征上进行必要的归纳与演绎,以便从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审视它推动中华民族价值观念进步的意义。
一、康有为是新仁学的奠基人
关于仁的概念,自古以来论者纷纷。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焉。”董仲舒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古圣先贤大体上没有把仁的概念越出人我关系的设计,为人亦即为我,所谓仁至义尽也;而康有为则把仁的概念扩充为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的总和。他说:“自黄帝、尧、舜开物成务,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学立教,以迪来士,皆以为仁也。旁及异教,佛氏之普度,皆为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为人者也。”①康氏不仅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趋势上论仁,而且提出“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的论旨,从横向的社会层面辐射仁的光谱,认为孝弟于家是仁之本,睦姻于族是仁之充,任恤于乡是仁之广,流惠于邑是仁之大,推恩于国是仁之远,若能赐类于天下,则仁之至矣。康氏把仁看成是充塞于天地宇宙之间人类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是他一生学术立论、改造中国、追求美好未来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用毕生精力写了对全人类充满“爱愿”的《大同书》,也可以说是康氏奉献给全人类的一部新仁学的教科书。那么,康有为对中华仁学有哪些新的发明和创意呢?
首先,仁为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是仁的根源。康氏在《孟子·微》中说:
“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②
“不忍人之心”一语源于《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标举人有四端譬有四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把仁定位在四端之一,而康有为则认为“不忍人之心”即仁为一切文明进化的动力,世上真善美的源泉。他说:“仁,忍也;又不忍也。”③他从人皆有同情心即恻隐之心出发,指出凡人之情,见有同貌同形同声者,必有相爱之心,以人行仁,人人有相爱之心,人人有相为之事,所以“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虽有内外体用之殊,其为道则一,亦曰仁而已矣。”④康氏把不忍人之心即仁心构建为最美好的道德原则,把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描绘为最完善的政治制度。认为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不忍人之心衍生出来,从而突破了孟子扩充四端只能“保四海”、“事父母”的藩篱,更富有近代理论的色泽。
基于这种“不忍人之心”,康有为在撰写《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绪言时,即首标《人有不忍之心》题目,依次列出人类社会的38种苦,发愿要为人类“去苦求乐”而献身,其出发点也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只有这种高尚的不忍人之心,才能明确对家庭的责任:“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才能明确对国家的责任:“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才能明确对全人类的责任:“生于大地,则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之异体也,既与有知,则与有亲”。⑤正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康氏目睹民国初年国家的混乱、人民的涂炭,所以在上海创办了《不忍》杂志,并在《不忍杂志序》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爱大地而亲中国,不忍之心磅礴而相袭的情绪。他说:
“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窥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⑥
康氏这篇阐明创办《不忍》杂志原委的序言,写于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壬子十一月冬至日,即公元1912年12月22日,距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已9个月又12天,换言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牺牲奋斗创建的民国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已三个季度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提出这“十不忍”,既是他“不忍人之心”仁的理论的感情爆炸,也是极具针对性的救国救民的呼喊。他喊出的每一个“不忍”,都是指斥袁世凯祸国殃民的实录,例如,是年3月29日袁世凯指使曹锟的第三镇制造“北京兵变”,波及天津、保定地区,民生能不多艰?英俄觊觎外蒙与西藏,袁记政府熟视无睹,国土能不沦丧?康氏痛心疾首,又有《蒙藏哀词》⑦⑧之作,惊呼“蒙藏失矣,瓜分今真到眼前矣,五千年文明之中国末日矣!”⑨其言哀伤,动人心魄!
对于康有为这种不忍之心爱国之志,长期为学者所误读,有人责问道,“究竟是什么使他这样不忍呢?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旧的反动的东西必将覆灭。”⑩这种不实的历史研究和惊人判语,信乎成了康有为反对社会进步甚至反动的铁证,其影响至广至深,庶乎成了某些历史著作展转相袭不容怀疑的信条。其实,只要我们冷静地读懂康氏这段话的本意,并和民初的政局和民情对照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康氏提出的这“十不忍”是对袁世凯北洋政府黑暗统治和腐败政治的揭露与抨击。
其次,仁为爱同类,去类界直至爱众生。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说:
“孔子之道,最重仁。人者,仁也。然则,天下何者为大仁,何者为小仁?鸟兽昆虫无不爱,上上也;凡吾同类,大小远近若一,上中也;爱及四夷,上下也;爱诸夏,中上也;爱其国,中中也;爱其乡,中下也*爱旁侧,下上也;爱独身,下中也;爱身之一体,下下也。”(11)
我国古代仁学侧重一个爱字。孔子曰:“泛爱众”,墨子主“兼爱”,孟子曰:“仁者无所不爱”,韩愈更言“博爱之谓仁”。林林总总无非条贯孔子“仁者爱人”的教说。康有为发挥董仲舒“仁者爱人,不在爱我”,“仁者所以爱人类”的微言大义,把仁爱发展成一个爱肢体、爱独身、爱旁侧、爱乡党、爱国家、爱诸夏、爱四夷、爱同类、爱生物的“爱分九等”又包揽宇宙众生的爱的系统。
康有为精心建筑的爱之大厦,至少有三层结构:(1)爱是感情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心路过程,从爱自己出发,然后爱他人、爱家乡、爱国家、爱本民族、爱少数民族、爱全人类、直到爱一切生物,达到至仁的境界;(2)爱是个历史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爱的表现形式不同,他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曰亲亲,次曰仁民,终曰爱物,“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12)(3)爱是天人合一,仁之美者在于天,康氏指出老子以天地为不仁,孔子以天地为仁,二者宗旨迥异,取仁于天而仁,此为道本。他向往仁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之治,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则仁参天矣。”(13)
康有为把古代儒家仁学重在爱的要旨,推进到不止言爱而且言类,不止言类而且爱及众生,让世界宇宙都充满着仁爱。他说生民之初,人们为求生存只知自私爱其类,苟非其类则杀绝之,“故以爱类为大义,号于天下,能爱类者谓之仁,不爱类者谓之不仁,若杀异类者,则以除害防患,亦号之为仁。”(14)所以他认为:“尽古今诸圣聪明才力之所营者,不过以爱其人类,保其人类,私其人类而止。”(15)康氏从人类发展史角度观察,认为爱同类固然是仁的重要阶段,但不是仁的尽头,到了大同之世,全地皆为人居,毒蛇猛兽已扫除净尽,只有鸟翔天空,牛羊遍野,物质极大丰富,有代肉妙品可以供食,因此杀生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他颇为动情地说:“何必日杀鸟兽,令其痛苦呼号以博我之一饱哉!以一饱之故而熟视鸟兽之痛苦呼号,上背天理,下种杀根,其不仁莫大矣。”(16)因为所有的生物都有天生之仁,故同类相爱乃是生命的根本法则,而且此一爱力必须普及众生,所以康氏力主戒杀:“先戒杀牛马犬,以其灵而有用也;次戒杀鸡豕鹅鸭,以其无用也;终戒及鱼,以其知少也。是故食肉杀生,大同之据乱世也,电机杀兽,大同之升平世也,禁杀绝欲,大同之太平世也,进化之渐也。”(17)质言之,大同之世,是至仁之世,应当戒杀,也就实现了康氏设计的仁从爱同类到达爱众生的境域。
第三,仁为以太,仁为互相吸引之力。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
“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孔子曰:‘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全神分神,惟元惟人。微乎妙哉,其神之有触哉!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故仁智同藏而智为先,仁智同用而仁为贵矣。”(18)
这一段话是康有为关于天地人神关系提要钩元式的哲学展示,他用传统的“元气”说,赋予天地人神以物质性的解释。物质是电的源泉,物质是神的灵明,神是精神世界的总名词,天地人神之间存在着一个“磁石”般互相吸摄的力量,这就是西方人说的“以太”(ether),东方人说的“仁爱”。“以太”即十七世纪西欧科学家所设想的传播光的媒质以及电磁和引力相互作用的现象。康氏企图用“元气”和“磁场”来说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天地人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带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有些学者不察,只在“神鬼神帝”字面上做文章,把这段话判为唯心主义的典型,神秘主义的范式,这显然是望文而生义。其实,康有为只是力图用所学得的西方科学知识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作一中国式的解释,使古老的仁学具有更多的近代科学魅力。萧公权说:“康氏在建立乌托邦之初,为道德作了世界化的解释。他对‘仁’或‘不忍’性质和渊源的理论颇带唯物的色彩。”(19)这是一种公允而实事求是的评论。
同时,康有为又继承和发扬了汉儒训仁为相人偶的评估,把西欧万有引力说引进人际关系,说明人和人之间的爱产生一种吸引力。他说:“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人具此爱力,故仁即人也;苟无此爱力,即不得为人矣。”(20)“仁”从“二”从“人”,从“仁”字构成上说明人生于地球之上立于天地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团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因而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一种崇高的爱力,是一种通达的电力,促使人类形成了共生的群体。人人都具有这种爱力,故人与仁合而为一,爱他人,爱家乡,爱民族,爱国家,爱人类,爱众生,达到至仁的境界,实现世界大同。假如一个人缺乏此种爱力,他既不能爱人,也无由获得别人对他的爱,就不可能被爱力吸摄于人类友爱的共同体中,而被摈于人类群体之外,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和生存空间。康氏运用相人偶说,把仁描绘成无处不在的把人类吸引在一起的电力,把仁演绎为无时不在的维系人类共生的最高道德准则,而且这种仁的吸引力是永无止境的,就是号称至仁的大同之世,“其为仁不过大海之涓滴也夫!”(21)仁的爱力和吸力,浩浩荡荡,无涯无际,是存在于宇宙人间的永恒的凝聚力。
第四,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康有为在《中庸注》中说:
“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人取仁于天而仁也,故有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文理灿然而厚,智广大而博。”(22)
康有为确认世界宇宙万物都是天生的,天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本源。他说:“天为生之本,故万物皆出于天,皆直隶于天,与人同气一体。”(23)天既生人,人与人之间又产生互相吸引的爱力,“则人己不隔,万物一体,慈悯生心,即为求仁之近路。”(24)康氏既指认仁是从天而生,所以爱及一切天生之物,祖宗者类之本,故知尊祖者,则爱同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天地者生之本,故知尊天者,则爱同生,我受天之气而生,众生亦受天之气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爱之理?
同时,他又用进化论的观念解释世有进化、仁有轨道,仁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拨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这时侯,既然人人皆生于天,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达到仁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则是至善至美至仁的时代。
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观念,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先秦时期的孔孟和老庄两家都以考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然而老庄崇尚自然,从天道出发考究天人之关系,提倡人类生活应当效法天道;孔孟以人类为中心阐释天人之关系,强调天人和谐的价值旨归在于人类道德之完善。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著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25)康有为仁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就具有中国传统主客和谐的文化精神特征。
但是,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门户洞开,社会风云激荡。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近代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天人合一”观念不特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受到了新观念的挑战。在康氏关于仁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论述中,我们就听到了西方自然观的回声。冯友兰先生批评说:“此实即程明道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而以当时人所闻西洋物理学中之新说附之。生吞活剥,自不能免。”(26)而陈荣捷先生认为冯氏对康南海之批评有失偏颇:“然此中有三项新元素:一为合为一体乃力之运用;二为合为一体乃互相吸引之成果;三为合为一体乃一自然现象。冯氏并皆失之。”(27)冯氏只注目传统而未察新仁之鸿蒙,陈氏既观照传统更瞩目创新,则独具眼识。我认为,对传统文化,后起者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发展的一面,而批判的继承才是科学的态度。康有为以吞吐中西文化的气魄,既承绪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又以学得的西方科学知识推陈出新,肩负起更新中华仁学的文化哲学使命,无愧是新仁学理论的奠基人。
二、谭嗣同是新仁学的集大成者
由于撰著论旨集中的《仁学》一书,谭嗣同以仁学为格致之学与中心的真知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用儒家、墨家、道家、基督教、佛教构建的以仁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8)谭氏仁思想的来源看似非常杂博,实则基调是明确的,无非调动自己的一切中西学知识,证明天地间唯仁而已,企图用一个仁字概括和解释世界,盖欲以之包罗当时人的新知识、新事物和新观念。诚如冯友兰先生说:“谭嗣同之思想,盖杂取诸方面而糅合之。其中虽不免有不能融贯之处,然要不失为其时思想界之一最高代表也。”(29)谭嗣同的思想走在当时时代的前列,为一般思想家所不敢想所不敢道,其在政治思想上和学术理论上最高成就,是全面地重新解释了儒家的仁,把仁学的主体工程重建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框架上,从而有力地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不妨说,谭嗣同的仁学就是中国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学。
民主,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中国封建社会延绵长达两千余年,是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中国历代思想家,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黄宗羲、王夫之斥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都孕涵有朴素的民主思想,但都未能动摇封建君主专制的一统天下。谭嗣同亲沐中国民本思想的雨露,吸取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精华,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新一轮的挑战,锋芒直指清朝封建统治阶级。
谭嗣同在《仁学》中,以愤怒的笔触抨击中国封建专制之酷烈,为世界所罕见。他揭露封建统治者利用“三纲五常”行愚民之术,其中“君为臣纲”尤其昏黑不道,而且“今兹”愈演愈烈,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30)他斥责说:“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亦得从容靦颜,挟持素所不识之孔教,以压制素所不知之中国矣,而中国犹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31)接着他历数清朝统治者罪行,指斥他们起于游牧部落,竟将全中国视为牧场,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所谓文字之狱,用尽一切刑名,惨酷压制榨取中国人民。因此欲行民主首先必须剥掉君主头上的神圣光圈。
近代西方人民主权论从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所以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谭嗣同站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运用西方契约论的思想对君统重新进行了解释。他肯定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王夫之的《船山遗书》皆是伸民权抑君权之作,并从君主产生的过程以及君民关系上界定民有举君之权亦有废君之权,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侪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32)
在这一段集中论述君民关系的文字中,谭嗣同强调民主是人民总体意志的表现,把几千年来颠倒的君民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君民关系的真实内容,即民是主人,君是仆人。是君食民之税,而不是民食君之禄。因此人们对君主可以共举之,也可以共废之,实行真正的民主。谭氏关于君民关系之说,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的学说,因为他不了解君臣和一切国家机关是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产生的,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这些观点,明显的是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严复1895年发表的《辟韩》一文的影响,而颇接近于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33)。应该承认,谭嗣同在宣传民主时最大的贡献是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
谭嗣同从君是民“共举”的观点出发,极力反对“忠君”意识,提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34)据他看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35)所以他对那些为家天下辩护的人予以严厉谴责,把韩愈说过“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歌颂君主专制的话,斥之为“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官。”(36)
所以,谭嗣同十分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法国人的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特别欣赏他们行民主而伐专制的坚定态度,他说:“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37)斥君主为大盗,是因为他窃天下为私有;杀君主以快人心,是因为他阻挡兴民权。谭氏不仅发愿拯救本国,而且号召土耳其、阿富汗、波斯、朝鲜等海内所号为病弱之国,“莫若明目张胆,代其革政,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38)以实现其“中外通”的世界大同之仁。谭氏虽然还没有说明民主的起源、内涵和本质,但他批驳了“君权神授”这一封建统治者自我神圣的君统理论,阐明了君主专制的不合理性和民主的合理性,把自古以来的皇帝斥为“独夫民贼”,斥君主专制为“秦政”,鼓舞了中国人反对君主专制的信念,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从君主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化的进程。
自由,是资产阶级视为胜过生命的思想理念,“不自由勿宁死”是对封建奴役和束缚的挑战。根据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人人生而自由,人生来就有人身的权利,即人身自由权。谭嗣同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比附《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一语,发挥微言大义说:
“‘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旨哉言乎!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轸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倡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39)
谭氏把人类获得全部自由定位在消灭国家和大同之世,但在《仁学》中却处处落在实处,无一不针对清末的社会现实生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被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权力。他揭露清朝统治者“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絷其手足,涂塞其耳目,尽驱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40)在这样情况下,统治者对人民可以肆意“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41)把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剥得精光,甚至连衣饰发型都没有自由,清政府发布“严薙发之令”,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对不肯屈服的“山林幽贞之士”,统治者也“必胁之出仕,不出仕则诛”(42),连避地遁世的自由也没有。至于清军所到之处,更是滥杀无辜,谭氏认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不过略举一二,实则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所以谭嗣同主张志士仁人要学习为挣脱封建束缚而战的陈涉、杨玄感等人;赞赏日本武士挟剑叱咤风云的“任侠”气概。他站在争自由的立场上,斥责湘军而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湘军之役不仅破坏了东南数省的元气,而且阻挡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他发出对“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43)的叹息,号召中国人学习陈涉、杨玄感、洪秀全、杨秀清为摆脱封建束缚,为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而战!他理直气壮地说,这里不存在“叛逆”的问题:“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44)谭氏揭开了统治者压迫人民自由的虚伪性,而昭示了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真理性,诚如卢梭所言,当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时有反抗压迫的自由:“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45)谭氏虽不若卢梭论自由直截了当,但他用摆事实的方法,也颇有说明力。
追求言论思想自由和婚姻自由是人类高层境界的自由。斯宾诺莎认为,每个人应当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46)谭嗣同十分痛恨清朝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禁锢言论思想自由的高压政策,甚至发生了甲午战败这样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也不准许人民议论,结果造成“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的局面。至于文字之狱更是清朝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自由的酷政,有清一代,文字之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查禁书目凡数千百种,连前数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例,文网可谓至密,文字之祸可谓烈极。谭嗣同对文字狱的控拆,就是对著书立说言论思想自由的呼唤,他在南学会和时务学堂慷慨激昂的演说,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体现。
谭嗣同非常同情妇女,猛烈谴责封建纲常对妇女的压迫与束缚,痛诋宋儒“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47)他认为男女婚姻自由,是“男女内外通”的为仁之道,反对强迫漠不相关的人结为夫妇,欣赏“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的婚姻自主,谭嗣同一生极尊重妇女的感情,为妇女争取婚姻自由而奔走呼号。
自由发展工商业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经济张力,在《仁学》中谭嗣同对自由发展工商业充满反传统的思考。他认为古人惜时之义,由于机器之学出而光大,因为制出高速的轮船和铁道,一日可兼十数日之程,则一年可办十数年之事,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诚不虚言。他觉识象中国这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应该改变“主静尚俭”的观念,力主开源而慎言节流,给人民以开矿、耕田、建厂的自由,“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有田焉,建学兴机器以耕之”,“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大富办大厂,中富办分厂,这样“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不惟无所用俭也,亦无所用其施济;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48)谭嗣同看到了自由竞争机制促进了工商业积累增厚的远景。同时,他意识到发展本国工商业还必须参加国际的交换与竞争,这就表现为仁的“中外通”之义,他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49)商品交换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谭嗣同认为一个国家“绝其通商,匪惟理不可也,势亦不行。”(50)他力主中国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尤其要重视开矿和扩大对外贸易,显然受到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这样,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庶彼仁我,而我亦有以仁彼。能仁人,斯财均,而己亦不困矣。”(51)谭嗣同的仁商观具有激进的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但是当时中国主权丧失,生产落后,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在华特权非法不正当竞争,仍然“以商灭人之国”的手段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是勿庸置疑的。
平等一词在《仁学》中使用频率很高,《仁学界说》一节就出现17次,仅次于仁。谭氏认为,平等生万化,“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52)盖以当时之中国为世界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从皇帝到平民,等级森严,所谓皇帝“口含天宪”、“刑不上大夫”,完全违背了天赋人以平等权力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公例。所以谭氏在《仁学》中宣称“仁以通为第一义,”(53)通有四种,“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意在打破各种隔阂和限制,消除各种不平等现象,实现人类的平等。要达到“人我通”的无差别的境界,他认为必须“断意识,除我相”,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便可以“异同泯”、“平等出”,达到“仁矣夫!”(54)换言之,不平等是相对的,平等才是绝对的,人们思维的精进和道德的完善,都是为了推进这个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平等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要求,也是客观世界自然运动的规律。
为了揭露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争取实现平等的理想,他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部位“三纲五常”,并勇敢地发出“冲决网罗”的呐喊。谭嗣同用新的观念说明封建“名教”是统治者桎梏人民的工具,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事实上这个“名忽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55)名教既不是先天就有的,也决非永远象“冠履之不可倒置。”(56)他揭露封建统治者发明“三纲五常”,目的是使“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如果大家都用“仁”作为行动准则,对于统治者就“于箝制之术不便”了。他指出,在“天”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父和子也不例外:“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57)他对“夫为妻纲”抨击最为猛烈,激烈地谴责封建纲常对妇女的压迫束缚,以及重男轻女、女子缠足等恶习,甚至造成溺杀女婴的酷行陋俗。《仁学》列举各种事实控拆了许多妇女被封建纲常伦理虐杀的惨状,表明谭嗣同对于当时妇女悲惨命运的无限同情。他在撰写《仁学》期间,曾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发起“戒缠足会”,接着又发起设立“湖南不缠足会”,提倡解除强迫妇女缠足的恶习,并且随地创立女学塾,让女子学习文化。谭嗣同为中国妇女解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谭氏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采取批判态度,而独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因为朋友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自由”、“平等”和不失人的“自主之权”的尊严,故“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他认为朋友不独贵于四伦,而且是四伦之圭臬,如果以朋友之道贯通四伦,则四伦可废,无论孔教、耶教和佛教都是一个道理,例如“其在孔教,臣哉邻哉,与国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妇者,嗣为兄弟,可合可离,故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至兄弟之为友于,更无论矣。”(58)而且朋友是形成群体和社会集体的基础,也是仁的一种深层结构。他说:“自孔、耶以来,先儒牧师所以为教,所以为学,莫不倡学会,联大群,动辄合数千万人以为朋友。益匪是即不有教,不有学,亦即不有国,不有人。凡吾所谓仁,要不能不恃乎此。”(59)
关于博爱即泛爱一切人,谭嗣同在《仁学自叙》中开宗明义即表明了赞赏墨家“兼爱”而吐弃其“尚俭非乐”的主张,因为墨既称举“兼爱”之旨,则必人我如一,若专以尚俭非乐苦人,“自足与其兼爱相消,犹天元代数之以正负相消,无所于爱焉。”(60)谭氏虽然承绪了韩愈《原道》中“博爱之谓仁”的学说,但把仁扩充到天地万物之间,并利用新名词“以太”赋予仁以普遍意义的解释,认为孔子之“仁”,墨子之“兼爱”,佛祖之“慈悲”,耶稣之“爱人如己”,格致家之“爱力、吸力”,都是精微至大无所不通的“以太”的结晶。
谭氏认为,博爱是一种与生具来的天性。正如卢梭引用诗人犹维纳尔的诗说:“自然既把眼泪赋与人类,就表示出他曾赐与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61)人即由七十三种原质共同构建,通过“以太”的作用粘砌而成,所以人与人之组合排列虽有不同,有男女之别,而无亲疏之分,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吸引的爱力。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大自然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吸力,这个吸力造成了社会与自然的均衡状态,如果吸力偏于某一方面而不兼及其他,则均势被打破,这个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系统就因失衡而消亡。他主张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必须用爱来维系,他说:“夫吸力即爱力之异名也。善用爱者,所以贵兼爱矣。”(62)因此,他在《仁学界说》中提出仁之为道,通有四种:即“中外通”,指出近代中国落后了,应学习西方实行变革,走向远近若一的大同之世;“上下通”、“男女内外通”,指上下相亲,男女相爱,则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通则利,不能则不利;“人我通”,是运用《金刚经》“无人相,无我相”,意欲破除人我彼此的分别,走入爱的浑一世界。谭氏在“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前提下,运用万能的“通”打破人间各种阻隔,追求的是无限的博爱。所以谭氏盛赞美国解放黑奴之举为“震古铄今之仁政。”(63)他深信人类共通的博爱观,可以使全世界融合为一和谐的群体。
谭嗣同在《仁学》中讲仁的不生不灭,破生死界,破对待,破亲疏分别,提倡兼爱,意在扫除人间的壁障和矛盾,造成博爱一统的世界。他的生死观、矛盾观、自然观、伦理观,虽然不免有相对论的涂饰,但也透出一股朴素辩证法和进化论的锐气。他认为,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新陈代谢的世界。谭氏追求的是无差别的博爱,所以激赏“兼爱”一语,认为是“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64)而“礼”生分别亲疏,阻碍了博爱的延伸,“可以至于大不仁”。只有全新,才通全仁,只有全仁,才达博爱。谭嗣同指认孔教处于据乱之世,耶教处于升平之世,佛教处于大同之世,这一判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他幻想说:“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箝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65)这时,佛祖就可把芸芸众生普度入极乐的博爱世界,则仁就升华到最高最美的境界。虽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谭嗣同在《仁学》中都宣扬了佛教的空幻,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幻想来看到他们追求博爱、平等、自由的真实思想。”(66)台湾学者黄克武博士也认为:“谭氏的思想虽有宗教特质,却是较近于科学主义的。”(67)
总之,谭嗣同糅合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和佛教、耶教的教义,再混合当时科学家的以太说,创造出他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融合中西的新仁学,我们既可以看到他深受康有为新仁学理论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他对康有为的超越。在五光十色的杂博之学外衣掩盖下,谭氏运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的网罗,冲决民族压迫的网罗,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用科学来反对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开早期《新青年》提出科学与民主口号之先声。谭嗣同在《仁学》中表现出的冲决封建网罗的泛仁论精神,不特为戊戌维新进行了哲学诠译,而且推进了儒学自身的近代化,既有历史的识力,又有时代的波力,对近代中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愧为新仁学的集大成者。
注释:
① 康有为:《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8页。
②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③ 康有为:《南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④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页。
⑤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⑥ 康有为:《不忍杂志序》,《不忍》杂志第一册,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2月发行。
⑦ 康有为:《蒙藏哀词上》,《不忍》杂志第一册,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2月发行,发俄人侵略内外蒙古之阴谋,而言至痛:“夫俄自西伯利铁路成窥蒙久矣。吾国人有万里边而慢藏不备,于是召俄人三十六款之事;吾国人不环顾外势而内讧,于是有库藏独立、呼伦贝尔继之之事;吾国人不乘夏时长驱袭库伦密擒诸叛以绝俄藉,于是有《俄蒙协约》之事。至今乃始举国愤张,奔走旁皇,待命于俄强,呜呼迟矣。今《俄库密约》十七条布露,其名与实,皆包括蒙古而言,盖明明吞内外蒙古新疆之地,令人惊痛,吾读之手颤泪承睫,我其发出狂矣!”
⑧ 康有为:《蒙藏哀词下》,《不忍》杂志第二册,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3月发行,发英人侵略西藏之强横,其言至哀:“顷闻江孜、察木多驻兵数千,拉萨驻兵二千,日进不已。今英报助之,英政府持之,非复昔者一使之言矣。而达赖既与库伦联盟拒我,又将遣使游欧,浸假而约章渐交于列强,浸假而英兵弥满于藏境。吾于藏也,使臣骨断,诸将血埋,匹马只轮不返,英又阻我,道路不通,曾几何时,全藏几无吾华人之影矣!”
⑨ 康有为:《蒙藏哀词上》,《不忍》杂志第一册,上海广智书局1913年2月发行。
⑩ 汤志均:《试论康有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页。
(1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六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5页。
(12)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9页。
(1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六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4页。
(14)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7页。
(15)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7页。
(16)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9页。
(17)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91页。
(18)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19) 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412页。
(20) 康有为:《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21)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页。
(22) 康有为:《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23) 康有为:《礼运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9页。
(24) 康有为:《孟子微》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页。
(2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2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18页。
(27) 陈荣捷:《康有为论仁》,上海图书馆藏、康保延编撰《康南海先生史迹汇编》,第29页。
(28) 谭嗣同:《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2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22页。
(30)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31)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338页。
(32)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9页。
(33)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谭嗣同辈当时并声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然严复《辟韩》是用《民约论》观点阐述君主起源、君民关系的,发表于1895年,谭氏1896年至1897年著《仁学》时,应看到过严复文章。所以,谭氏未详知卢梭其人,但受《民约论》之影响似为无疑。
(34)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35)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36)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
(37)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2-343页。
(38)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9页。
(39)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7页。
(40)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
(41)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1页。
(42)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0页。
(43)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5页。
(44)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4页。
(45)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46)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1页。
(47)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9页。
(48)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
(49)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页。
(50)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51)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8页。
(52) 谭嗣同:《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53) 谭嗣同:《仁学界说》,《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页。
(54)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5页。
(55)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
(56)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见《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上海东方书局1935年印行,第50页。
(57)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58)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0-351页。
(59)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0页。
(60)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61)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
(62)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页。
(63) 谭嗣同:《仁学》卷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页。
(64)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65) 谭嗣同:《仁学》卷一,《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5页。
(66) 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页。
(67)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62页。
标签:谭嗣同论文; 康有为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仁学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大同书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学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