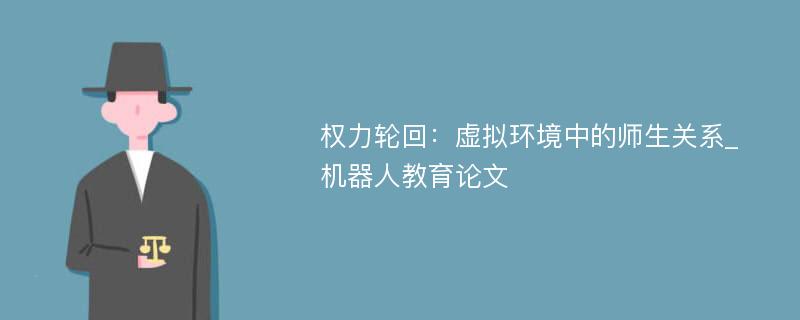
权力的轮回——虚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生关系论文,权力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创造出了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虚拟”的社会环境,“在虚拟环境下人类的社会生活将如何变化”因此成为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勿庸置疑,教育活动在虚拟环境下也将可能出现一些新景象与新问题。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尚未成熟,对于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构想必将带有一定的推测性,因此,本文选择了电影《黑客帝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鉴电影对未来社会的幻想性描述作为研究的基本模型。之所以选择电影《黑客帝国》是因为该电影是对未来虚拟环境的一个典型性描述,该电影的播出曾引起学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虚拟与现实”问题的大讨论。电影所描述的未来景象虽不是真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未来的问题做出猜想与反思,科学幻想历来就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动力(注:将电影、文学等艺术作品作为教育学研究的资源,已有学者从方法论上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参阅〔加〕马克斯·范梅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宋广文,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
电影《黑客帝国》(原名The Matrix)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22世纪时,人类已丧失了对地球的统治权,地球被机器人(也即电脑)所控制。机器人用电脑程序虚拟出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影片中将这个虚拟的世界即称作“Matrix”。人类生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不知真相,而人类的真实肉体却被机器人用来为机器提供能量,也即人类的肉体沦为了机器的电池,完全被机器所操控,彻底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而仅有一小部分人类摆脱了机器人的控制获得了身体的自由,他们在地底深处建立了一个“真实”的生活世界(相对于机器人建立的虚拟世界而言),那是一个称为Zion(锡安)的城市,这些摆脱了机器人控制的小部分人类一直试图拯救那些被机器人所控制的大多数人类。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相互斗争持续了很久,最后以人类与机器人和平共处告终。
电影所描述的未来社会中,因为机器人的介入,社会结构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是由人所构成,人是社会行动的主体,因此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想象都源自于人自身的变化。教育活动的主体也同样是人,主要表现为“教师”与“学生”这两大主要角色类型,没有教师与学生也就没有教育,没有了教育也便不会再有教师与学生。因此,未来教育的变化首先会体现在这两大教育角色上,虚拟环境下教育的转变将首先表现为教师与学生这两大教育主体之间的角色关系变化上。
一、虚拟环境下师生关系的转变
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两大尖端技术:一项为人工智能技术,另一项为虚拟现实技术,而两种技术的发展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二者相结合最终在创造着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新世界。电影《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未来世界的场景正是由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所构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趋势就是机器的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在电影中机器最终获得了和人同等的智慧并进一步取代人控制人类世界,而机器人用以控制人类的手段就是虚拟环境。美国当代著名发明家雷·库兹韦尔曾大胆预言:“在21世纪结束之前,人类将不再是地球上最有智慧或最有能力的生命实体。事实上,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这最后一句话是否符合真实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在此,我们看到这两个世纪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如何定义人类将是下个世纪基本的政治与哲学问题。”[1](P2)这一预言无疑揭露了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之后的一个可能性后果:即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实现计算机对人的替代,这种替代将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既然机器的智慧可以与人同等,那么机器也就可以替代人的许多社会角色,承担人的许多工作,在教育中自然也不例外。电影中机器可以取代人类的领导层,那么教育中机器也将同样可能取代教师。在当下的教育活动中,计算机已经开始大量参与教学,成为教师教学的得力助手,可以说计算机在当下的环境中已经成为半个教师,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对教师的整体替代也就并非不可能。
在电影中,未来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冲突,这正是机器对人的整体性替代的结果,事实上,机器获得人的同等智能之后也便获得了同等的社会身份,可以说机器在此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试想如果机器介入教学成为教师的替代品,那么学生要面对的将不再是作为人的教师,而是机器教师,也就是说,师生关系将因此由传统的“人—人”互动模式转变为“人—机”互动模式。当然,电影所描述的那个机器人统治的世界只是一个想象的结果,真实的社会中机器能否真的获得完整的社会身份从而与人共处还难以定论。但是,信息技术同时又在创造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下的网络环境已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这样的虚拟环境中,人所面对的也并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实体。如同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的那句名言一样:“在网络中,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在虚拟环境下,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虚拟环境下人所面对的都是机器,因为人所真正面对的只是一个机器模拟出来的虚幻环境而已。所以,机器即使不会替代教师,也会成为师生交往互动中的一个中介,在虚拟的环境中,师生都要通过机器去认识对方,向对方传递信息。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教师或学生所面对的都已不再是人本身,而是机器,因此,虚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也必然表现为“人—机”关系。
二、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对抗
无论是传统的“人—人”关系,还是虚拟环境下的“人—机”关系,其根本还都体现于“教师”与“学生”这两大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那么,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关系表现为什么样的特征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从电影中发现一个类似的隐喻。
电影的主题其实是讲了一个对抗和斗争的故事,对抗的双方主体是人和机器。在电影中斗争以一个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双方都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分别是机器人的代表——史密斯与人类的“英雄”——尼欧,他们分别代表了“虚拟”与“真实”两个不同的世界。影片中将史密斯描述成本领强大无人能敌,因此,为了与他抗衡,尼欧被推崇为“救世主”,他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超能力:能够在空中飞行、阻挡子弹,会使各种武功,只有他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电影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救世主情结”,这样一个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古老人类传统在科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却同样出现,正说明了这一情结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存在的普遍性。或许人类需要从救世主身上获得安全感,救世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救世主提供给世人一种信念,一种可以依靠信赖的意识。在电影里战斗的人类正是凭借对“尼欧就是救世主”的确信而最终取得胜利的,所以,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救世主本人,而是他人对于救世主的诚信。
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有一个群体性的心理意识作支撑,“诚信”即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诚信”是社会交往过程中确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精神纽带。在世界各类宗教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旨趣就是“心诚则灵”,这即是对于宗教教义的一种“诚信”,诚信在此成为宗教活动的一种组织性力量,人们凭借诚信的力量把信仰宗教的个人组织起来。而我们稍作联想就可发现,事实上在人类任何需要统合性的社会活动中,“诚信”都是一个普遍使用的组织手段,统合性越强的活动对诚信的需求就越大。在教育活动中,诚信的力量同样十分重要,首先体现为对“知识”的诚信,并进一步发展为对于“知识”的传播者——教师的诚信。对于教师的诚信也使得教师的身份带有了一种近似于“救世主”的宗教崇拜色彩。
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角色扮演一直有一种“救世主”的象征。教师既是知识之神又是人格之神,因此能够救助无知无识的学生。而教育活动本身更被神化为社会的救世主,“教育救国”成为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影片最后的结局是以尼欧的自我牺牲换来胜利,也即救世主只能救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他的伟大不在于超能力而在于自我牺牲。同样,尼欧的牺牲精神也在教师这一救世主身上有所体现。中国的文化中历来有把教师喻为“蜡烛”的传统,所谓“牺牲自己,照亮别人”,教师的牺牲既被夸大又被圣化,这是一种奇异的现象。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而言,与其他职业具有同等性,并不比其他职业贡献更多的东西。但教师和教育被奉为救世主是因为真实的社会需要这种幻觉,这里隐含了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和要求,即教师必须有能力来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区别于广大受教育对象的特殊的人。教师角色需要这种特殊化的提升来敛聚“诚信”的精神力量。而对于“诚信”的极度需求恰是由教育活动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对教育活动的理解与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维度,但笔者在此仍旧赞同教育社会学的先驱人物——涂尔干的看法,涂尔干将教育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尽管后人对于教育的认识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也只是探讨的角度和方法有所差异,其根本仍旧没有离开涂尔干的这一经典性定义:“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2](P309)。事实上,涂尔干对于教育活动乃至于整个社会活动的看法都根源于一组对立性的关系的存在: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涂尔干看来,个体的人与群体性的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性,因此,代表群体的社会相对于个人而言就具有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教育活动就是一种强制性行为。“教育儿童的现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一个不断强迫的过程。儿童视听言动的方式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而是通过教育的强迫力使然。”[3](P7)这种强制性会对个人形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有压迫就必定有可能形成对压迫的反抗,因此,在压迫与被压迫的双方会构成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只是这种压迫性力量因个人无意识的内化接受过程而常常显得不为人知,难以察觉,但这并不能否认压迫的存在。“一种压迫在反抗时表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未反抗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存在着。因此,我们有时受了外界的强制却还以为是自我的原因。逆来顺受,或许感觉不到强制的压迫,然而那种压迫力却总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人们生活在空气中,并不觉得空气的重量,但空气的重量仍然总是存在一样。”[3](P6)而教育活动也同样在过于日常化的过程中隐匿了其中存在的压迫性力量。既然教育是成人社会对于未成年个体的一种强制性影响,在教育活动中就必然有一种压迫与反压迫的对抗性关系存在,而压迫与反压迫的主体双方也必然落到了这种对抗力量的主要施动对象——教师与学生身上。因此,我们说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抗。在教育活动中隐含的救世主情结促成了这种对抗性关系的形成。
电影中另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机器人史密斯的形象十分的“拟人化”,也就是说,这个机器很像一个真正的人,他有着完整而独立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他也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这其实也是一种象征,机器与人之间的冲突归根结蒂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史密斯与尼欧可以看作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人类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是一个必然存在。从广义的角度,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涂尔干所认为的社会事实外在于个人但却对个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作用,是默认了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它们不能同时满足时则必定会构成一定的冲突,为了保证社会的利益而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去剥夺个人的利益。因此师生的对抗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体现。而从狭义的角度,就教育活动自身而言,教师与学生仅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两个不同群体,他们是存在利益差别的两类人,因此,他们之间也和其他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一样会存在某种矛盾和冲突。尽管理想化的教育理论一直在试图创造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各种教育实践也都试图去让两者步调一致,但两者之间的这种身份与地位的差异却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强制力之所以特别表现在教育方面,是由于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个人培养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从历史上看更不乏这样的例子,人类就是用这种方式不断地再创造出来的。这种强制力存在于社会中,通过父母、教师来铸造社会的新成员,而他们则是社会与儿童之间的中间人,是社会强制儿童的代表者。”[3](P7)由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强制与反强制),一定的冲突与对抗关系就是必然,师生之间这种不同的角色要求决定了师生关系的本质就是对抗。救世主的出现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力量需要救世主的出现,只有救世主才能有能力与之相对抗。可以说是对抗的立场造就了救世主的身份。同样,也正是对抗的立场造就了教师与学生。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对抗”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仅用来对差异性关系进行一种客观性的描述。对抗并不一定就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对抗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和谐共处,如同电影中机器与人最终的和平共生一样,但这并不能否认对抗的存在本质。只要存在着教师与学生就必然存在着双方之间的对抗关系。
三、虚拟环境下师生关系的新表现:权力的轮回
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抗,这种对抗是一种永恒存在。在真实世界中,师生间的对抗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而在虚拟环境中,师生间的对抗将转化为人与机器的对抗。那么人与机器间的对抗与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又可能有何不同呢?
首先应看到机器与人的角色差异性。媒体研究的先驱人物麦克鲁汉提出的“媒体是人的延伸”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机器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电影中的机器人看起来都具有人的一切特征,这也说明机器实质是对人的一种模仿与复制。最初是人创造了机器,而人对机器的一切设计与想象无不建立在对人自身的了解基础上,人是机器的最初来源。电影中有一个大胆想象是机器人把人当成电池用来为机器提供运行的能量,这其实也是对于“人创造机器”的一种暗示和象征。没有了人,机器无从诞生,但人类一旦创造出了机器又将越来越依赖机器,摆脱不了机器的控制。可以想象,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离不开计算机,从停电所引起大慌乱上就可以看出没有机器的辅助,人类社会的很多系统都将趋于瘫痪。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和机器本质是一体的,是互为因果相互共存的。人面对机器时实质是在面对自我,人所面对的机器是人的自我在数字世界中的投影。电影中,电脑人史密斯曾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不属于哺乳动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会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无限侵占地球的资源,所以他们认为人与病毒是同类,是地球的癌症。这在电影里代表了机器对于人的看法,但实质上是人借助于机器之口说出了对于自身的认识。这同样也是一种象征,也就是人借助于机器认识了自己反思了自己。人的世界和机器的世界实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它们本质是一个共同世界的“颠倒的两面”[4]而已。
人区别于机器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人具有感情,当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的智能已越来越接近人类,但对人类感情的模拟则始终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难题,也就是说机器能够拥有人类的智能,却不能拥有人类的感情。而人的行为是由理性与感性的力量共同支配的,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无法彻底脱离感情的控制而达到纯粹的理性化程度。因此,由于感情性因素的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常常变得十分复杂,难以用科学化的语言加以精确表述。人与人之间或亲密、或敌视、或合作、或斗争的种种不同关系常常仅仅是出于感情的一种冲动。相比而言,机器的表现则完全受逻辑严密的程序指令所控制,机器的一切行动都可还原为科学化的语言。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于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具有更多的模糊性与不可预知性。由于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存在,“人—人”关系容易出现极端性,而“人—机”关系则是一种相对更温和的关系。譬如机器不会觉得厌烦,不会发脾气,但人与人之间因为情绪忍耐力的丧失而导致的激烈冲突却十分普遍。因此,虚拟环境下的师生间的对抗将可能更趋缓和平稳。
电影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在虚拟世界中,尼欧看见一个孩子能够用意念使金属汤勺自动变软弯曲,孩子告诉他其中的奥秘是要意识到汤勺其实并不存在,改变汤勺其实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必须改变自己。这是在暗示这样一个道理:改变现实的方法其实就是要改变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即改变自己的意识。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转变:通常人改变周围的世界是直接把力量作用于外部对象,而不会作用于自己。改变的过程就是在对周围的世界行使权力,在实施改变的行动中,权力是指向外部,指向他者的。而电影中让汤勺弯曲的方法却改变了这种权力的流动方向,把权力反过来指向了自身。这种权力流向的转变就是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的一个差别,也是人与机器交往和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差别。在通常的教师与学生的交往过程中,师生间的对抗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抗,权力都是由自己指向对方的,要么由教师指向学生,要么由学生指向教师。而当虚拟环境中师生关系转变为“人—机”关系时,人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格实体,而是一个虚拟的角色模型。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作用力承载对象,因此在对抗的过程中权力不是表现为对对方的直接作用,而将反过来指向自我。所以,虚拟环境下的师生间的对抗表现为一种轮回式的权力流动关系。控制对方将首先意味着控制自己,控制对方的力量也将使自己被控制。
在电影中,尼欧最终战胜电脑人的秘诀在于战胜自己的意识。所以,与其说是他改变了周围的世界,不如说他改变了自己。而电脑人用以操纵人类的方法其实归根结蒂在于人类自身的意识之中,电脑人让人对虚拟世界信以为真,就可以用程序设计出的虚拟世界轻易地控制人类的生活,也就是说,控制人类的方法在于控制人类的意识,而不需要任何真实的物质手段。这是一种更高效且更经济的控制手段,通过机器来管理教育活动也将有可能更高效更经济。在虚拟世界中人失去了与真实生命的碰撞,既失去了敌人也失去了朋友,所以在虚拟环境下人只能自己与自己相处。因此,维持这样的虚拟世界的稳定就只能要求人自己管理自己,权力由自己流向自己,这也就意味着人必须达到高度的自律。自律是一种最精密也最无形的控制。师生通过虚拟环境进行较量,权力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权力的使用也更具隐蔽性,因此,对抗表面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体现出来,但实质可能力量更密集。权力在轮回的流动中相互交结,将会使对抗的双方缔结成一种更牢固的对抗关系。
结语
电影中还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电脑人为了有效的管理人类曾对虚拟世界的设计工作进行过多次实验。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彻底无痛苦的世界,但却导致了人类在其中大量的死亡;而最终设计成功的是一个有痛苦的混乱世界,这个世界终于使人类沉醉其中不能自拔,被人类自己视为“文明的颠峰”。在这里,我们看到电影试图把痛苦视为人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动力。事实上,痛苦在这里的作用恰恰是在制造一种对抗的关系。与其说痛苦是生命力的源泉,不如说对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力量。在虚拟世界中,人无法与他人真正对抗,但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对抗性的力量存在,于是人只能构造自己对自己的对抗,痛苦就是一种构造自我对抗的力量。所以,电影里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类需要痛苦来制造对抗,需要对抗来维持那个虚拟世界的发展。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弗洛伊德将人类的生命原动力归结为力比多。前者论述的是作为群体的人的状态,而后者描述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状态。这两大思想都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文明发展,而这两大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实质也即揭示出了对抗的本质。阶级斗争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抗;而力比多制造的是个体的自我对抗,因此,无论是人类群体还是个体的进步,对抗力量都是一种根本性的推动力量。如马尔库塞所言:“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自由只有作为解放才是可能的。而解放随统治而来,同时又导致对统治的重新肯定。”[5](P139)人为了获得自由就必须去对抗统治,而对抗统治之后所带来的解放其实最终又在进一步强化统治,这就是一种权力的轮回运动,人类社会就是在自由与统治的对抗中不断前进的。所以,没有对抗的世界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对抗的师生关系也同样是乏味沉闷的。任何有经验的教师都会体会到:如果在师生的交往中学生仅仅成为教师的应声虫,彻底顺应教师的意愿,这将使教育活动失去活力。对抗体现了两种相反的力量关系,这其实也正应和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师生关系之道也在于这种对抗力量上。
当然,要说明的是在师生关系中对抗不是敌对,教师与学生并不是敌人,敌对是一种消极的对立关系,而师生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关系。如同福柯所说的,权力同样具有生产性,对抗双方之间的权力流动并不必然就是破坏性的。在涂尔干看来,虽然社会优越于个体而且强制性地制约着个体,但这种强制并非以物理性暴力而是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即通过文化的方式内化到个人意识之中。涂尔干将这种通过心理内化所实现的社会对个人的强制看作是道德的。同样的是,师生之间的对抗也正是这种“道德的”强制表现形式之一,它同样是积极的,必须维护的。
在电影中,最初的“Matrix”与“Zion”被描述成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代表虚拟,一个代表真实,彼此间有着清晰的界限,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立场,但后来却证明这种对立是一个巨大的谎言。“Matrix”与“Zion”在电影的第二部中已被发现不过是平行操作的两个程序而已,究竟孰真孰假难以辨别。这其实也是揭示了这种对抗关系的复杂性。虚拟环境下的对抗远不像真实世界中那样简单,对抗双方永远存在着纠结颠倒的并行关系。但其实也是对抗把双方联结起来,在这里,对抗的目的不是造成双方的分裂与疏离,而是促成双方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是对抗最终构造了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电影将最后的结局设计成人与机器的和平共处,也正表明了对于和谐共生的一种期待,对抗同样可以促使双方的和谐发展。中国古人一直讲究“阴阳平衡”的和谐宇宙观,阴阳之间本身即是一种对抗性关系,但恰恰是这种对抗性关系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对抗性力量并非一定是消极的力量。所谓“教学相长”正是师生双方互相促动的表现,而如果师生之间言语、行动、思想完全一致没有差异,没有一定的张力,又如何能够构成这种互促的行为呢?虚拟环境下的师生关系会出现一些新变化,尽管对抗的本质不会改变,但对抗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如何把虚拟环境下的师生对抗引向一种和谐共生的积极对抗关系将是未来教育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