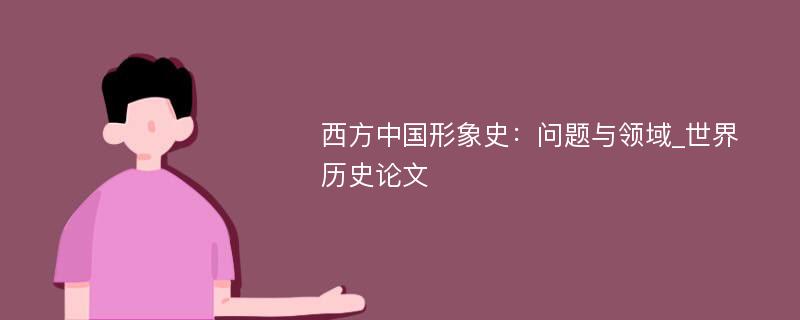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象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 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 问题值得注意: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 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 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 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 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 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 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 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 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 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注:马可· 波罗时代之前,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 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 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 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 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 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 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 ,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 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大中华帝国的神话,从 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 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 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 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 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注:参见《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柏 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 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 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 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 ”,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 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 0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 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 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注: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 (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 、《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 、《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 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 斯记》(1436-1480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 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 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内容,既有记实、也有虚构, 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 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 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 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 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 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 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 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 (注:(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13 7页。)
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 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 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 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 ,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 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 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 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 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 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 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 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 ·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 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 《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今 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 有119种。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也像 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 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大,统治 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 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 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契 丹传奇》,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 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 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 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 述(注:霍尔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述”(representation),他认为“表述”是同 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 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edited by Stuart Hall,London:The Open University,1997,
Chapter I,“The Works of Representation”.),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 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 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蒙 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 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 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 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中华帝国”的 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 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 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 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 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 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华帝国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 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 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 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 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 。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 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 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 定了大中华帝国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 的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 。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 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 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孔子 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 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 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大中华帝国》 ,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 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 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 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 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 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 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 ,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乌托邦将从地理大 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 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 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 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 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 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注:详 见周宁著、编注:《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二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 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 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 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 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 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 待中的大中华帝国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 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 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注: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 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 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世纪 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 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 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 、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 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 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注: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y Adolf
Reichwei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25,P25-26.)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 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 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起初是商人与传教士,后来是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 的哲学家。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 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 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 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 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 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 治之争、政治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 ,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 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 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注:详见周宁著、编注:《世纪中国潮》,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 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 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 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 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 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更多地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它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 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文化策略与逻辑。文本是唯一的依据 ,而作为文本的语境出现的现实,在此也不是指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如中国),而是 构成文本写作的社会语境与话语策略(西方文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 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启蒙运动中中 国形象逐渐转变,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 贸易与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可以这样说,真正使中国形象改变颜色的,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 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到英国完 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 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扩张中与中国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 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二、 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赛义德在对 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 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 的话语模式”。(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 1999年版,第8页。)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 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 密关联。
首先是西方现代扩张史上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 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 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 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 的西北角,直到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 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 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 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 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18 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 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 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 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年前后,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 ,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局势直到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 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 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 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年英 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100%降到世纪中的12.5%,茶 价一路下跌,1750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3700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 。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鸦片。他们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 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 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 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 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 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 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 折点。175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 。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 国。世界格局变了,英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 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 ,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 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 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 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 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鸦片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 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 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其次,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 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 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 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 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 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 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 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 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 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注:参见Paradise on Earth:Some Thoughts on European lmages of Non-European Man,by Henri
Baudet,Trans,by Elizabeth Wenthol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 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 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 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 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 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 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 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 。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伊斯兰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 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 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 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 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 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 ,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 动中达到高潮。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中华帝国作为 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 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中华帝国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 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 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中华帝国形象中获得了某 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 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 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中华帝国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 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 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 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 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 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 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 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一、“古 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 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三、西方政治革 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 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 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 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 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 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 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 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 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500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三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 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 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 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注:笔者认为, 西方现代的起点在1250年,而不是1500年。参见拙文:《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 他者》,《粤海风》2003,3。);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 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 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 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注: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 ,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有关现代性的 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人民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 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 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年版。)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 ,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 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 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 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 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 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 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 中华帝国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 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 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 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 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 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 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 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 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 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 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 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 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 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 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 ”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 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 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 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 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既可以 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 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 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 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 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 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注:参见拙文:《停 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10。)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于启蒙运动后期的法国与英国,到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 哲学中获得最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教条与规训意 义的知识,又表现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的停滞,进可以为殖民扩 张提供正义的理由,退可以让西方文明认同自身,引以为戒。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是 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 ,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 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唯一的障碍,如 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 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概念取代进步概念,避免了启蒙思想的温情,进化 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 ,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 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 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劣等民族的呻吟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社 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 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 成意识形态。
犹如进步与自由是启蒙大叙事的一对紧密相关的肯定性概念,停滞与专制也是一对紧 密相关的否定性概念。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 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 社会的中国的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以致于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或西方对华政 策。话语指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特定主题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话语 假设语言与行为,观念与实践都是不可分的,话语不仅决定了意义与意义表现的方式, 还决定了行为的方式,甚至行为本身也是话语。西方的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 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就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 态,福柯认为话语中知识/权力是不可分离的,知识不仅假定“真理”的权力而且使权 力变成真理。一旦你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 ,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如果再将中国形象定位在专制与野蛮上,西方 掠夺性的野蛮战争就获得了“正义”的解释与动机。
我们在三个层次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探讨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七个多世纪 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 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在何时又如何生成的,在什么社会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 、继承的;其次,分析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形象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 以及该体系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与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表现出某种 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成为一种文化程式,又如何控制个别文本表 述的;最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暗含的权力结构,分析它作为知识与想象,是如何 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渗透权力并发挥权力,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 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并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霸权的。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一个 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毒品贸易与战争的罪恶 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某种 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 “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 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 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鸦片帝国》、《第二人 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 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 “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 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 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 ,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 、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 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 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 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 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 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1750年前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 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 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 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 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龙的幻象》,学苑 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 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 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其中 反复出现两种极端类型表现出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及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对西方文化认同 与超越的功能,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宗旨。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这 种话语可能断裂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甚至完全相反,也可能在变化中表现出某 种原型的延续性。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 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 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 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 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注:( 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 9年版,第77-78页。)20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20 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无知、误解 、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注:China
Misperceived: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By Steven W.Mosher,A New Republic Book,1990,上述观点参见该书第1-34页:“Prologue”与“Introduction ”。)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 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 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象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 前景产生怀疑。《被误解的中国》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点在30-70年代间。科林· 麦克拉斯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1999)则写到90年代末,重点在20世纪最后20 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20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 两极间的剧烈摇摆,在20世纪内,它是50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 国形象史上,它是1750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的继续。
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 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 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 ,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 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 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 “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 、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象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国,这个飘浮在 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 ,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马可·波罗游记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英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