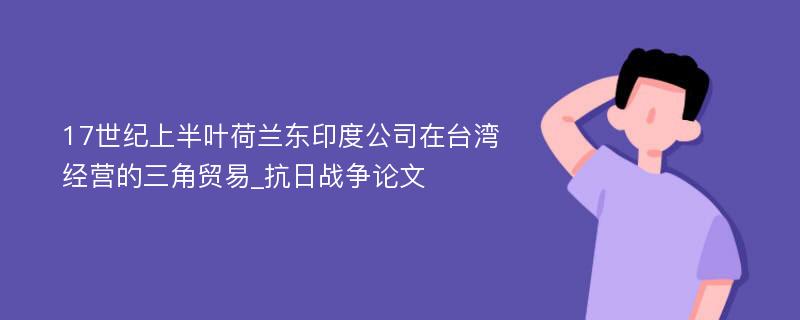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经营的三角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印度公司论文,荷兰论文,世纪论文,贸易论文,在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5—0086—05
17世纪上半叶,东亚的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来的西方殖民者为开拓远东国际贸易市场,在中国东南沿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一改过去丰臣秀吉时代极具侵略性的强硬外交,实行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在中国,正处于明代后期,明朝在平定倭寇的基础上,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商出海贸易,但对日贸易仍属严禁之列。由于形势的改变,原本位于远东海上交通干线之外、鲜为外界所注目的台湾,因其地处大陆和日本之间,足以控制当时世界上利润极其丰厚的中日贸易而日益引起世人的重视。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曾以台湾为基地,从事过对华、对日贸易。然而,由于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占据台湾的时间最长、势力最强、贸易规模也最大,因此,本文主要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商业活动为中心来阐述大陆—台湾—日本的三角贸易。
一、中日商人在台湾的贸易
早在荷兰人到达台湾之前,由于明朝对日实行海禁,而德川幕府又相当重视对华贸易,故台湾成为中日走私贸易据点。对于中日商人在台湾的交易活动,许多外文史料皆有记载,如1623年2月23日, 吧城寄给荷兰董事会的信中就提及:“日本人亦每年来该处(指大员)与中国人贸易。”① 荷驻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Peter Nuyts)在提交给上司的报告中亦指出:“关于日本人,远在我们来此之前的好多年,就秘密与中国人通商,且一向能买下足够的货物。”② 不过,中日间的这种商业活动到1635年幕府禁止国人出国以后就基本停止了。在台湾,中国商人除了与日本人进行贸易之外,还与当地土著民交易,把鹿脯、鹿骨等运回大陆,而把鹿皮销往日本。
二、公司获取中国商品的途径
与其他欧洲人一样,荷兰人很早就垂涎于中、日这两个富庶的东方国家,一心想打开对华、对日贸易。1595年,荷兰国会对一支取道北冰洋前往远东的舰队发出的训令中,要求他们设法到达中国和日本, 并调查日本的政府及其经济状况。 ③ 1609年,公司很顺利地在平户设立了一个商馆,正式确定了与日本的商业关系。但在中国的遭遇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公司刚建立即着眼于对华贸易”④,但当时的明廷只许中商领引出洋贸易,而不许外国人到东南沿海一带经商。荷兰殖民者煞费苦心也无法打开直接对华贸易的大门,便于1624年占领台湾南部,以此作为对华、对日贸易的中继站,经营与大陆和日本的三角贸易。
荷占台以后,千方百计想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国商品,他们很清楚,如果无法得到中国商品,公司在日本的贸易将很难赢利。但当时的明朝尚未公开允许大陆商人前往大员通商, 公司与大陆的生意基本是由一位名叫许心素(荷人称之为Simsou)的厦门大商人以承包方式独揽。德·韦特(de With)任台湾长官期间(1625—1627年),荷人开始以预付资金的方式通过许心素置办中国产品。然吧城并不赞同这种贸易方式,因为这样做使荷方过分依赖许心素,公司被迫以较高的价格购入丝绸,有些商品甚至是以比一般价高出50%的价格购入的,且通过预付方式经营贸易,公司难免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许心素垮台时,尚欠公司19086.5里亚尔,所以自1627年以后,吧城即多次下令不许再向华商预付资金,不许只与许心素之类的中间商做生意。⑤
荷兰人除了通过中间商购取大陆商品外,有时亦在福建地方官员的默许或纵容下,前往漳州湾购物。相对前者而言,荷兰人当然更愿意选择后一种购物方式,因为即使加上必要的贿赂,以后一种方式买到的物品仍比前一种方式便宜。⑥ 特别是郑芝龙被明朝招抚后,荷兰人经常到安海与他进行交易。如1631年上半年,高级商务员特罗德纽斯被派驻漳州湾与郑芝龙贸易。⑦ 每当开往日本或吧城的船期即将来临,而大员的存货不多时,荷兰人就得派几艘船到厦门去,在当局的默许下买进大量的大陆商品。⑧ 但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方面,荷兰人不太舍得施重礼;另一方面,这毕竟不是一种正当的贸易渠道,一些地方官员虽对荷兰人的这种作法视而不见,或亲自参与对荷贸易,但中国人还是忌讳荷兰人到大陆沿海来,因为这为明朝法律所不容。故很多时候荷兰人到大陆的时间都很仓促,只能匆匆抛出资金即撤回大员,造成了所购货物有的质量太差,赢不了利。甚至个别时候中国人只愿意把货物以高出大员1/3的价格卖给荷兰人,而从荷兰人手中购入的货物不但数量有限,且价格比大员低了1/3。”⑨ 荷兰人也渐渐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后来便较少到大陆沿海来采购,而主要倚靠大陆商人将货物运至大员,尤其是1634年明朝增发通行证,允许更多的中国商人到大员贸易,而不许荷兰人复来大陆沿海后,荷兰人就基本不再到大陆来采办货物了。
其实,荷兰人一到大员定居后,便以怀柔的手段极力诱引华商到大员经商。早在首任驻台长官宋克(Martinus Sonck)任职期间(1624—1625年), 就有不少华商相继前来,荷人把布作为礼物送给船上的人,和他们处理好关系,希望藉此促进贸易的顺利发展。⑩ 据《吧城日记》1625年4月6日条载:当时一位叫王桑(Wangsan)的华商建议荷人以较高的价格诱商前往大员,只要保证他们获得25%—40%的利润即可。一旦打开市场,每年可输入10000担丝绸, 根本用不着操心丝绸供货不足等问题。荷兰人采纳了他的建议,抬高收购价格。类似的鼓励措施在荷据台期间多次实施,但仍有不少中商宁可到马尼拉与西班牙人交易,因为中国帆船到马尼拉的航行由来已久,那里的利润又比大员高,且西班牙人因资金充足而基本用白银支付。1626年2月1日到吧城的一位漳州船主告诉荷印当局,将有百余只装载丝绸及其他贵重物品的中国小帆船驶向马尼拉,那里的丝价每担240两,至少比大员高出100两。为了使华船转航大员,荷兰人软硬兼施,一方面提高货物的购入价,另一方面不惜诉诸武力,破坏漳州和马尼拉的往来。由于自1568年起,荷、西即处于80年战争之中,公司的任务之一就是打击西班牙人在远东的势力,因此截阻华船前往马尼拉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11)
荷兰人一到远东后制定的首期计划就是在商业上孤立菲律宾,为了切断马尼拉与中、日的商业联系,他们把船停靠在依戈律(Ilocos)和邦加丝楠(Pangasinan)沿岸,或干脆驶向中国内地,袭击和抢劫了几乎所有奔赴马尼拉的帆船。(12) 1624年荷据台湾后,更是把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视为眼中钉,多次拦截来往马尼拉的华船。纳茨向吧城总督作的前述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因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深信诸位将看到西班牙人自动离开马鲁古群岛,甚至离开马尼拉。尤其是他们此刻已被日本驱逐,如果再被我们夺去中国贸易的话,他们必然忍受不了那么大的费用和负担。”(13) 荷兰人的海盗行径迫使华商不得不转向台湾与荷交易。1629年,纳茨在上述同一报告中声称:“……自从我们定居在这里以及海上有了海盗出没以来,中国船只就很少出海,后来开始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最近几年来,中国同西班牙人的贸易十分萧条。”(14) 即便有冒险到马尼拉的,也只敢载少量船货,如1626年到吕宋的50艘华船仅运去40担生丝,而同时期载到台湾的丝却有900担。(15) 因此,荷兰在大员与漳泉海商的贸易额飞速增长。特别是1634年,福建地方官员取消贸易之禁,允许商人到大员贸易后,从中国到大员的货物运输日益频繁,1638年甚至出现了因中国产品大批运至而造成价格下跌的局面。(16)
三、公司的竞争手段
17世纪上半叶,与荷兰人一起在台经营中日贸易的还有中国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他们都是公司的竞争对手。为减少乃至消除竞争,公司针对不同的对手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相对其他对手而言,中国人是最容易对付的。这主要是因为中日直接贸易为明廷所不容,只有那些走私商们才敢在台湾偷偷与日本人做生意。这些得不到明廷支持和保护的华商面对以国家为后盾的东印度公司,几乎没什么竞争力,所以当公司于1625年起借口华商使用其筑造的码头而向他们征税时,华商不敢有任何异议,尽管他们知道纳税后的利润将大大减少。不仅如此,荷兰人还严禁居日华侨到台湾做生意,同时严惩那些胆敢将鹿皮出售给日本船的中国人。(17)
相比之下,对付日本人可就棘手多了。荷兰人侵台不久,即与日方就大员的贸易权发生过严重争执。日本人强烈反对荷兰人要求他们缴纳10%关税的做法,认为他们比公司的代理人早来此地6年,因此,是他们最先占有该地的。关于这点,荷印总督燕·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于1622年给侵犯澎湖的舰队司令莱尔森(Cornelis Reijersen)的指示中已予承认,当时莱尔森也允许日本人在台自由贸易。(18) 现在的问题是日商的经营规模比公司大得多, 他们很容易就能买尽中国人所提供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有时一年在大员购入的货物价值高达30万两白银。(19) 日本人强有力的竞争,造成了大员商品价格上涨,对荷兰人很不利,吧城担心长此下去,公司在大员的贸易会深受打击,便明确指示宋克以公司的名义在大员拥有并行使最高权力,不必畏惧任何人,也不必向谁认错,并要他告知日本人,如果他们愿意在此贸易,就必须和其他居民一样纳税。我们从前面提到的纳茨报告书中的一段自白就能理解日本人的感受,他写道:“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在该国除了送给皇帝和高级官员一份轻微的礼物外,充分享有贸易自由而不必交纳任何税款,而我们却向该国人抽税,这不是不合理吗?此外,‘Quiprioresttempore,priorestjure(先到的人有优先权)’这条格言,对他们也适用。因为他们远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同当地人通商。照理说,他们有权向我们抽税,而不是我们向他们抽税,可他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的事。因此,如果我们执行诸位阁下的指示,我们结果非离开日本不可。”(20)
荷兰人是决不会离开日本的,因为正如纳茨所指出的那样,同日本贸易,对荷兰人是利润很大且至关重要的,公司在日本的地位不同于其在东印度的其他国家,在那些地方,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即可取得贸易权,而在日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对荷兰人一点也不在意,不怕荷兰人加害于他们,况且他们从荷兰人那里购得的任何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从其他商人手中买到。荷兰人一开始到中国沿海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开展中国贸易,以获取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的货物。(21) 吧城很快就意识到向日本人征税这一做法将产生的严重后果,故吧城总督卡彭蒂尔(Carpentier)曾试图以遣使送礼的办法来防止事态扩大。1627年,他派纳茨出使日本,但纳茨刚愎自用又目中无人,非但没能见着将军以缓解日荷冲突,反而使之愈演愈烈。(22) 1628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滨田弥兵卫”事件,日本为此对公司实行长达5年的贸易制裁,直到1632年,公司将肇事者纳茨引渡给日本, 平户商馆才于1633年重开。(23) 不过,日荷这一扰人的争端最终还是由日本人自己解决了。当时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传教活动造成的影响力使幕府吓坏了,担心基督教将变成西方渗透的工具。1633年,除了九艘幕府特许的“朱印船”外,其他船只都不准航行海外。两年后,幕府严禁日本人出国,那些在国外的日本人被勒令立即回国,违者处以极刑。(24) 这以后,荷日关系融洽多了。
与中国人、日本人的做法不同,饱受荷兰人破坏的西班牙人不甘示弱,于1626年和1629年分别占领了台湾北端的鸡笼、淡水,并建起两座堡垒。此举令纳茨警觉起来,他敦促公司尽快派支远征军去攻破西班牙人的堡垒,并危言耸听地指出,原来是荷兰人能够切断西班牙人的航运,现在正好相反。他预见到西班牙人能够并将赢得台湾原住民与中国内地移民的信任,且可能会挑动他们起来反抗,而以武力制止这一危险的费用足以花光大员商馆的利润。纳茨于1629年就极力主张攻打西班牙人的居住区,但吧城避免了仓促的行动,(25) 因为虽然入侵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也曾积极从事对日贸易,但毕竟规模太小。公司只是变本加厉地截击商船,他们企图阻止福州的中国人到台湾北部与西班牙人做生意;派船到福建沿海巡逻,所有过往船只,只要不是驶往巴达维亚或大员的均有可能遭到截劫。(26) 他们把抢到的物品贩卖到能获取最高利润的地方,而抓到的中国人则送到吧城去当苦力。直到1642年8月,公司才彻底把西班牙人赶出台湾。(27)
四、公司以大员为基地的中日贸易
17世纪上半叶,由荷兰人输入日本的物品有丝绸、瓷器、糖、鹿皮、鲨鱼皮、铅、锌、香料、象牙、来自欧洲的羊毛衣、各种给小孩和家庭主妇的小玩意儿;从日本输出的有金、银、铜、樟脑、漆器、谷物、和服,以及少量的日本瓷器等产品。(28) 其中销往日本的商品以大陆和台湾的货物为最大宗,如1637年7月23日到9月3日间输往日本的船货价值共计2042302.14.9荷盾,其中大员的中国产品和鹿皮就占了近96.6%,为1972404.19.14荷盾。(29) 从日本运出的物品中,绝大部分是白银。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丝绸一样,都是公司在亚洲贸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事实上,公司在以台湾为中转港而从事的大陆—台湾—日本三角贸易中,最常见的经营模式是以日本白银来购买中国丝货。公司从日本运走了巨额的白银,如1626年,仅“奥兰治”(Orangie)号和“恩丘伊钦”(het Wapenvan Enchuijsen)号从日本载出的白银就有297万里亚尔。(30) 大员经营着大规模与日本的商业往来,1638年初,大员所获利润(1948732.15.7荷盾)中有一半以上(1000000荷盾)用于采购日本所需物资。(31) 1641年,公司在日本出售的货物价值居然达到800万荷盾。(32) 这以后由于受中国内地不稳定局面的影响,荷兰人在日本的贸易高峰期已过。尽管如此,1643年,公司仍要求各地向日本提供201.2万荷盾的物品。每年从日本出口的物资规模也不小,如1636年的2、3月间,到达大员的3艘货船共载了价值1077215.16.14荷盾的日本货物。(33)
公司拥有台湾以后,利用自己在大员的优势,致力于发展对日贸易,其利润确实是特别优厚。我们以中日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中国生丝为例,日本人习惯于高价买进生丝,如1624年,日本人以每担260两的价格购入生丝,(34) 而荷兰人在大员丝货短缺时,一般是以每担140两的价格进货,有时为了吸引中国商贩,把采购价提至150两/担。照此计算,则有73.3%—85.7%的收益。据统计,公司每年对日贸易所产生的赢利大约是50万荷盾,大大超过了荷兰与亚洲其他地方的贸易所得。(35)
五、结语
1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台湾变成了中日贸易的一个极具价值的转贩据点。中国人、日本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曾在此从事过中日贸易,但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个时期的台湾基本上控制在荷兰人手中。他们充分利用台湾的有利地位,一方面设法得到中国商品;另一方面又以种种手段对付其他竞争对手,从而大大增加了中日之间的贸易额,(36) 台湾因此成为公司“对华、对日贸易的一个最有价值的商站”。(37)
注释:
① 赖永祥、曹永和译:《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台湾银行,1959年,第2页。
② Co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Taip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72,p.56.
③ Albert Hyma,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Michigan:George Wahr Publishing Co.,1953,p.141.
④ (荷)C.J.A.约尔格著,任荣康译:《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第304页。
⑤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68、93、100页。
⑥ D.W.Davies,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1,p.62.
⑦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113页。
⑧ Formosa under the Dutch,p.52.
⑨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114、159页。
⑩ Formosa under the Dutch,p.36.
(11)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47、58、53页。
(12) 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E.P.Dutton & Co.,INC,1959,352.
(1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p.55.
(14) Ibid.,pp.52—3.
(15) 李金明:《十七世纪初荷兰在澎湖、台湾的贸易》, 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2期,第66页。
(16)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197页。
(1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市政府发行,2000年,第164、183、193、201页。
(18) Formosa under the Dutch,p.36.
(19)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96页。
(20) Formosa under the Dutch,pp.37,56.
(21) Ibid.,pp.56—7,26.
(22)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97页。
(23) 日中村孝志著,吴密察、翁佳音编:《荷据时代台湾史研究》(上卷),稻乡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24)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p.74.
(25) Ibid.,pp.64—5.
(26)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85页。
(27)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p.65.
(28) 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p.159.
(29) 荷包乐史著,庄国土、程绍刚译:《中荷交往史》,路口店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
(30)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61页。
(31) 同上,第88页。
(32) 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p.163.
(33) 《荷兰人在福尔摩莎》,第253、173页。
(34) 《巴达维亚城日志》,转引自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页。
(35) A History of the Dutch in the Far East,p.159.
(36) Ibid.,p.155.
(37)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p.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