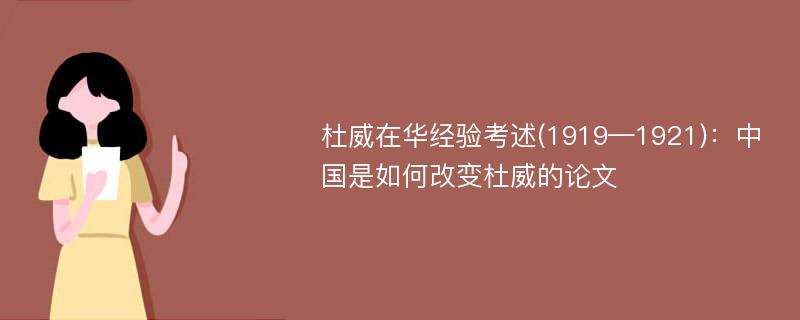
杜威在华经验考述(1919—1921): 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
[美]尚恩·罗尔斯顿(Shane Ralston)
(伍尔夫大学哲学系,英国剑桥 OX12JD)
摘 要 :在19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时他业已到访过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两年两个月——并且书写最多的也是他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本文将聚焦于“中国是如何影响杜威的”这一问题。特别需要指明的是,本文解释了杜威构思经验(提供了一个他称之为“经验形而上学”的名目)的过程,以便弄清杜威是如何体会他自己的访华经验的。
关键词 :实用主义;中国;杜威;经验;文化;美中关系;中国哲学
刚到中国的人在观察和评判各种事情时,通常会犯过于看重当前发生事件的错误。
——杜威《联邦制在中国》(Dewey,1996,p.149)
杜威学会了以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和尊重中国。
——王清思《学习者杜威在中国》(Wang,2005,p.64)
一 、杜威作为国际主义者
美国哲学家杜威最为人称道的或许是他对教育哲学的诸多贡献,尽管他在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1952年去世前后,他被赞誉为“美国的哲学家”(America’s philosopher)和“20世纪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将杜威称作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那一时期他到访了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国。在所有这些地方当中,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达两年两个月,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并且他书写最多的也是在中国的经历。令人遗憾的是,太多的文献都在讨论杜威如何影响中国。
在这篇简短的论文中,我想着重讨论中国是如何改变杜威的。在正式切题之前,有必要阐释杜威是如何构思经验的(描绘一幅他所谓的“经验形而上学”图画),以便领会他是如何构思自己的中国经验的。
二 、杜威论经验
对于杜威而言,经验可以比作拍打着沙滩的层层海浪。许多经验是通过文化、教养、隐喻和旅行来被动地和非认知地被我们“拥有”或“感受”的。这一原初经验为更富有认知性的间接经验的产物所引导。依前项比喻,原初经验的沙滩上散落着贝壳、鹅卵石或者说间接经验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威最终拒斥了美国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而赞成“不插手”或“不干预”的做法。“中国不会从其自身之外获得拯救”,他写道,因为中国“习惯于从容不迫地对待自身的问题:中国既不理解也不可能从西方世界急不可耐的方法中获取任何好处,因为这些方法对中国的智慧民众而言是非常陌生的”(Dewey,1996,p.171)。杜威鼓励美国领导人将中国视为“文化同伴”而非幼稚儿(Dewey,1996,p.175)。因此,杜威努力克服他自身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尝试着在他两年期的驻留中获得更多的对中国文化敏感性的欣赏。
间接经验包含通过理智探究、实验和反思而来的“认识”或“学习”——活跃的海浪将从数学公式到逻辑形式再到心理学原理等一切事物都沉淀在原初经验的海滩上,这些原初经验将在后续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使用。间接经验充满了认知要素,但其目的在于丰富原初经验,而不是成为朝奉自己的神庙。事实上,杜威与伯特兰·罗素的论争表明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是如何构思经验的。罗素将它视为一种可以以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来了解和分析的东西;杜威则认为它是一个首先应当被整体理解的过程。那么,杜威对于中国的经验是什么呢?
同时,杜威看到,中国文化与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历史悠久的对传统的尊重紧密相连。他提到,“惟有依据在自身历史演进中生发出来的制度和观念,中国才能得到理解”(Dewey,1996,p.216)。对杜威来说,制度不仅仅是分立的机构、或是它们所占据的建筑甚至是构成它们的人。相反,制度更像是不定形的文化和习惯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尽管它在中国这样更为传统的社会中变化缓慢。
三 、杜威论中日关系
在来华访问之前,杜威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家长专断式的。然而,至少就一个方面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家长式作风是偶然的,原因在于它为杜威与中国学生建立关系开辟了道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向中国返还了部分赔偿金,其中一个条件是将这笔钱作为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奖学金。杜威在中国的首席阐释者胡适即是这项奖学金的获得者,他最初于1910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胡适后来安排了杜威在中国的驻留访问。
跟孙中山一样,杜威觉察到了中国人民的保守主义和消极态度,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推测。他认为,大部分人居住在人口稠密地区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心理倾向:“毋庸置疑,中国人的许多思维特征是非比寻常的、长期持续的人口密度的产物。”(Dewey,1996,p.53)并且,“互相帮助互不干扰是对拥挤环境的反应”(Dewey,1996,p.53)。他还认为,同样的生活环境可以解释人们为何有保持脸面或保持形象的习惯:“当人们比邻而居彼此之间不可分离时,外表,换言之留给他人的印象就变得与现实生活同等重要了,即便不是更重要的话。”(Dewey,1996,p.58)
与孙中山的这次交往很可能激发了杜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心理的好奇心。1919年6月,杜威在一封通信中向子女坦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从未像在中国那儿学到这么多东西”。
四 、杜威论中美关系
约翰·杜威于1919年5月1日(亦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天前)来到中国。“五四”当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活动,抗议《凡尔赛条约》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以及中国北洋军阀政府软弱的外交反应。
(2)能够将一些似是而非的因素加以区分,并利用关联函数计算方法,在临界阈值上加以界定,避免了因为一些微小区别而产生的判断误区。
五 、杜威论中国文化
绩效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的业绩,也深刻影响着一个单位的发展。绩效考核的目的是激发工作人员的主动性,提高其绩效水平并通过考核使员工的个人目标和单位的整体目标趋于一致。目前我国多数高校并未构建一套完善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常把财务分析指标作为基准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因为该项指标主要凭借价值性指标对财务的具体结果进行评价,因此无法全面、客观反映高校的实际财务情况,难以全面反映经济考评中的非经济指标的重要性。在充分考虑高校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有必要构建一套相对完善的高校财务人员评价体系。
撇开他对这场运动的复杂看法,杜威对中国的印象远比对日本深刻得多。在他访华的第11天( 即1919年5月12日),杜威与孙中山会晤并共进晚餐。在晚餐中,杜威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切,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当杜威在与子女的通信中回忆起这次会谈时,他对这位中国革命家的反应感到惊讶:“中国人的弱点(据孙中山说)归因于他们接受了一位旧时先哲的观点:‘知易行难。’因此,他们不喜欢采取行动,也不认为人们有可能获得一个完美的理论见解,而日本人的长处则是即使身处无知的情况下也会采取行动,并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继续改正前行;中国人因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陷于麻木。”
本文以船舶应用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提出船舶分布式数据网络管理平台,根据智能船舶系统的固有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该平台不仅能弥补传统数据管理平台的缺陷,而且具有全面感知、可靠传递和智能应用的优势,应用于远洋船舶运输管理中,可建立集航运企业各部门和远洋船舶于一体的安全监控平台。此外,船舶分布式数据网络平台可大大提高船岸定时交互数据和协作管理业务的效率,增强远洋船舶物资运输、航行、机务系统和油耗监测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为船舶智能管理业务和应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根据我院急诊科临床本科护生问卷测评表,评价两组临床实习效果,从理论知识和临床护理技能操作两项成绩评价,分值每项各100分,分数越高,表明临床护生的实习效果越好。根据我院设计的护理专业实习生应用护理程序能力考核表,评定两组临床护生的病例分析能力(根据患者病例提出主要和潜在护理问题50分、给予相应护理措施50分),总分值100分,分数越高,表明临床护生的病例分析能力越强。根据我院制定的教学满意度评价表评定教学满意度,分值为100分,分为满意(≥90分)、一般(60~89分)、不满意(≤59分),总满意度=满意/总数×100%。
虽然杜威是一位业余文化人类学者,但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中看出杜威很真诚地由内而外地欣赏中国文化。甚至于在杜威访华期间发表的许多公开演讲中,他也将个人演讲要旨加以改变以适合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场域,而不是推销美国药丸以作为治疗中国弊病的万能药方。
英国人洛克曾说过“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就会成为粗暴,学识就会成为迂腐,机制就会成为逗趣,质朴就会成为粗鲁,温厚就会成为谄媚。”若这种现象发生在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希望的大学生身上,恐怕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而事实却是部分大学生责任感与使命感缺乏、浮躁与迷惘俱在、审美价值观扭曲,这是不容否认的现象。因此,面对当前的大学生审美价值观现状,作为审美教育的影视艺术教育理应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中坚力量,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观。与其他的价值观教育途径相比,影视艺术教育会通过左右大学生的审美价值观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整个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
六 、杜威论中国哲学
同时,杜威出人意料地以开明姿态和谦逊之心来接受道家学说和儒学思想。他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常常被描述为行动和进步的需要,藉此人们可以操纵自然来推动预定目标的灵活实现。老子的学说,尤其是他的“无为”观念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学说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杜威完全可以有各种理由来拒绝老子的学说。然而,几乎如同自相矛盾,杜威却在为它们辩护:“自然造化会适时将人为造作的烦恼和愤怒化为虚无。若给予自大傲慢和雄心勃勃之辈足够的通天绳索 ,他们最终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人为纠缠所捆缚。”(Dewey,1996,p.222)无论如何,坚信时光流逝、顺其自然能够消解疑难情境的道家观点与实用主义的经验性和工具性问题解决路径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杜威也意识到探究方法并非出现在真空中,它们反映了更广泛社群和文化的主导信仰。类似于儒家, 杜威坚信西方所主张的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胜过服膺社群履行义务的观念不过是一种“虚构想象”(Hall & Ames,1999,p.225)。中国古代“仁”的观念对杜威转向共同体理想和共同体验产生了影响。根据王清思(Jessica Ching-Sze Wang)教授的观点,杜威“与中国的接触增进了他对共同体生活基本价值的信念”(Wang,2007,p.106)。如果杜威能够从中国学到走近共同体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他西方人同样也能够。正如杜威所说:“中国的生活哲学包含着一个对人类文化具有非凡价值的贡献,这个贡献正是风风火火、心浮气躁、忙碌不堪和焦虑不安的西方所迫切需要的。”(Dewey,1996,p.223)
七 、结语 :中国如何改变杜威 ?
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之间,中国至少以三种深刻的方式改变了杜威。首先,它向杜威表明:只有通过对过往的深刻了解,才能彻底理解自己的现状。考虑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前瞻性倾向,这或许是一种看似奇怪的非实用主义思维。然而,正如我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约翰·杜威的伟大辩论——重建论》(John Dewey ’s Great Debates —Reconstructed )中主张的,这是弄清杜威专注于历史探究的唯一途径。
其次,中国特别是道家改变了杜威,让他更加关注人类应当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问题。正如我在自己的第二本著作《实用主义环境论》(Pragmatic Environmentalism )中所指出的,我们人类不需要总是主宰或者控制自然。如果我们还希望地球能够长期维持人类种族的生存,我们应当学会在与自然世界的交往中保持克制,保护其生物种群,并保存它为我们提供的资源。与道家的“无为”观念相一致,有时我们只需选择不行动,同样,也不加利用。最后,由于长时间的体验,中国通过增强他对文化情境的敏感性从而改变了杜威。
在我的第三本著作《哲学实用主义与国际关系》(Philosophical 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我考察了实用主义哲学与国际外交实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美国外交官在跟中国外交官互动之前必须先学一件事的话,那就是要明白谈判及协商绝不能仓促进行。同样地,杜威提到:“为了在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充分适应他们对时间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给他们时间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利用好时间。”(Dewey,1996,p.223)在经验形而上学的框架中,杜威在为期两年的访问中对中国的学习收获丰富了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总体印象及对中国未来的希望。杜威的访华经历也在原初经验的海滩上留下了贝壳般的沉积,这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指引美国哲学家的思考。
参考文献
Dewey, J. (1973). Lectures in China : 1919-1920. Edited by Robert W. Clopton, Translated by Tsuin-Chen Ou.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ewey, J. (1996),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The Electronic Edition , Edited by A. Hickm an.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oration.
Hall, D. L., & Ames, R. T. (1999).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 Chicago: Open Court.
Keenan, B. (1977). 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Ralston, S. (2009).The Ebb and Flow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xperience: Kayak Touring and John Dewey’s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Environment ,Space ,Place , 1(1), 189-204.
Ralston, S. (2011). John Dewey ’s Great Debates —Reconstructed . Charlotte: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Ralston, S. (2013a). Pragmatic Environmentalism :Toward a Rhetoric of Eco -Justice . Leicester:Troubadour Publishing.
Ralston, S. (2013b). Philosophical Pragmat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ssays for a Bold New World . Lanham:Lexington Books.
Ryan, A. (1995).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 New York: Norton & Co.
Stroud, S. (2013a). Economic Experience as Art? John Dewey’s Lectures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of Mindless Occupational Labor.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 27 (2), 113-133.
Stroud, S. (2013b). Selling Democracy and the Rhetorical Habits of Synthetic Conflict: John Dewey as Pragmatic Rhetor in China. Rhetoric &Public Affairs , 16(1), 97-132.
Tan, S. H. (2011). How Can a Chinese Democracy be Pragmatic?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 47 (2), 196-225.
Wang, J. C. S. (2005). John Dewey as a Learner in China. Education &Culture , 21(1), 59-73.
Wang, J. C. S. (2007). 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 . Albany: SUNY Press.
Westbrook, R. (1992).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hn Dewey ’s Experience in China (1919 -1921 ):How China Changed Dewey
Shane Ralst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oolf University, Oxford, OX12JD, U.K.)
Abstract : In the early 1920s, to call John Dewey an internationalist would be to state the obvious. He had travelled to Japan, Russia, Mexico, Turkey and China. Of all these places, he stayed in China the longest—two years and two months (May 1919 to July 1921)—and wrote the most about his experiences there. Unfortunately, too much of the literature addresses how Dewey influenced China. What the author focuses on in this article is how China influenced Dewey instead. Specifically, he explains how Dewey conceived experience—offering an account of his so-called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in order to then appreciate how Dewey appreciated his own China experience.
Keywords : pragmatism; China; John Dewey; experience; culture; 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 Chinese philosophy
DOI :10.16382/j.cnki.1000-5560.2019.02.007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冯加渔 译)
(责任编辑 胡 岩 )
标签:实用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杜威论文; 经验论文; 文化论文; 美中关系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伍尔夫大学哲学系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