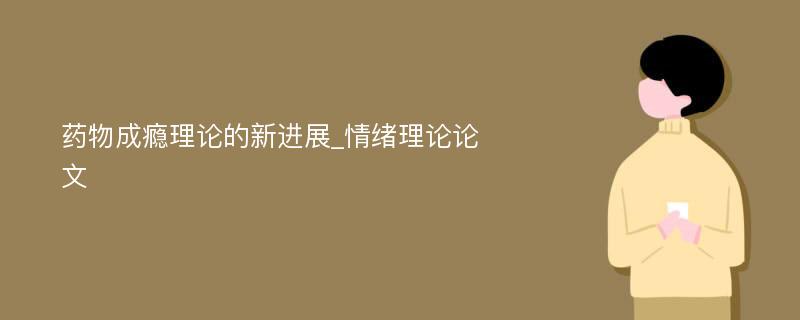
药物成瘾理论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药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06)—03—0264—08
1 引言
药物成瘾(drug addiction)一般被界定为强迫性药物寻求和药物摄入的行为模式,是一个由偶尔用药逐渐过渡到强迫性用药模式的过程[1]。研究者普遍认为成瘾过程伴随着一系列脑机能和心理机能的适应性改变,且该类机能的改变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成瘾者对药物的依赖性,但对药物滥用如何导致这些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何诱发成瘾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2]。近年来,由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在该领域的应用,有研究者借助注意偏向概念对成瘾过程的认知及脑机制作出了新的解释。另有研究者利用心理测量及动物实验技术,对负性生活事件及外部压力在维持药物滥用及诱发复吸行为中的作用进行研究[3,4],提出了以压力或负性情绪因素为核心的理论模型,为药物复吸行为的诱发研究开辟了新思路。本文重点评述药物成瘾的认知加工模型和以压力或负性情绪为核心的相关理论模型及其研究。
2 认知加工模型:从对诱因的神经易感化到对线索的注意偏向
药物成瘾的诱因—易感化模型(the incentive-sensitization model)是Robinson和Berridge基于对大量有关动物成瘾研究成果的整合而提出的[1,5]。根据该模型,长期使用成瘾性药物会改变与伏隔核(the nucleus accumbens,NAcc)相关的脑系统的功能,使其逐渐对药物的作用以及与药物相关的中性刺激变得非常敏感,形成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病理性特性,即神经易感化(neural sensitization)。它使依赖者在心理上内隐性地表征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特性,使其成为突现性诱因,引起其在认知上过分夸大或歪曲该类线索的作用,从而引发病理性用药“欲望”(pathological"wanting"),最终导致其无意识的(内隐的)目标导向的药物寻求行为。这一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依赖者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的脑机制,同时对情绪反应、学习和情境因素在成瘾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是一个具有相当整合程度的理论模型。然而,该模型并未就该“病理性欲望”引导依赖者指向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机制作出明确描述,更未阐明药物及其相关线索如何成为依赖者优先加工的突现性刺激的认知机制[6]。此外,该模型主要以动物实验为依据,缺乏有关人类依赖者的实验支持,对于解释人的成瘾行为是不充分的。
近年来,Franken基于对药物依赖者注意偏向及其神经药理学的研究,通过引入依赖者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优先加工的假设,揭示了诱因—易感化模型中“病理性欲望”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加深了对药物依赖和复吸行为的认知机制的认识[7]。他认为,成瘾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存在显著的注意偏向。该注意偏向是药物相关刺激引发依赖者的渴求感与复吸行为的关键性认知中介,它一方面调节着药物刺激和依赖者对这些刺激的初始反应(渴求感),另一方面调节着依赖者后续的行为反应(如药物寻求和复吸)。在该模型中,注意偏向影响药物成瘾和复吸行为的路径有三种:依赖者将注意自动指向药物线索,并预期到药物线索的可能结果,导致成瘾行为的维持;依赖者将更多的注意资源投放到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自动加工过程中,引发对其的记忆(记忆偏差)以及对药物的期待等外显的思维过程,从而导致依赖者对药物线索的注意难以转移;由于注意资源的有限性,对药物线索的自动化注意“固着”势必影响对竞争性线索的加工。正是由于注意的这一“固着”特性,依赖者很难将注意资源分配到旨在回避药物使用的认知与行为策略上。可见,被放大的对药物相关刺激的注意加工(注意偏向)在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且对药物线索的注意偏向是自动化的过程[7]。
认知加工模型的实验证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大量行为研究证据表明,药物依赖者普遍存在着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8—10],且神经电生理学的研究证据显示,药物线索可增强脑皮层对该类线索的认知加工过程[11—14]。例如,EEG的研究发现,在多药物滥用者身上可观察到对可卡因刺激的α波呈同步化现象[11];香烟刺激使尼古丁依赖者表现出β节律的同步化特征[12];酒精、尼古丁线索可增强药物依赖者认知加工过程中的P300振幅[13,14]。该类结果提示,依赖者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认知加工过程存在注意资源优先分配的特性。其次,认知加工模型也获得心理药理学某些间接证据的支持。以往研究表明多巴胺释放与对心理活性药物奖赏效应的体验有关[15],而近期的研究发现,药物相关刺激同样能引起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能的释放[16]。而且有关注意功能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提示,多巴胺系统是注意系统的生物学基础,对诸如选择性注意[17]和目标探测[18]等注意加工具有调节作用,而激活正常被试或动物体内的多巴胺活动可减弱潜伏抑制(Latent inhibition)能力[19,20]。由于潜伏抑制涉及对无关刺激不予注意的能力[21],研究者推论,多巴胺的激活不仅可引发药物渴求感,而且受渴求感的驱使,依赖者对药物及其相关刺激分配了更多的注意资源,并可实现自动化加工[7]。最后,由于注意偏向和渴求感具有高相关[8],因而有可能拥有共同的神经基础。神经解剖学研究显示,可卡因及其相关线索诱发的渴求感与ACC的激活水平有关[22],而ACC的激活涉及注意功能的发挥[23],且新近的研究表明,药物相关线索可诱发注意脑区的激活,使其成为突现性加工目标[24]。因此有理由认为药物渴求感的诱发和注意加工过程拥有共同的脑区[7]。
以注意偏向为核心概念的认知加工模型的本质在于揭示诱因—易感化模型中“病理性欲望”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以阐明药物成瘾和复吸行为的心理—生理基础。就此而言,该模型是对诱因—易感化模型的深化和发展。然而,该模型在解释诱发药物依赖者优先加工并导致其形成“病理性欲望”的药物相关线索只包括了直接与用药行为形成固定联结的正性刺激,而忽视了其他性质的事件。事实上,在人类依赖者身上,诸如来自人际关系中的不信任、鄙视、被排斥以及失业、贫穷等引起负性情绪的社会—心理事件同样可能诱发其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这些现象提示,诱发药物依赖者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的心理机制可能不仅限于对药物及其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
3 去抑制假设:压力对于诱发药物复吸行为的作用
药物成瘾研究领域对诸如高社会压力、紧张的家庭关系或人际和谐度等负性社会生活事件[25,26] 以及不良人格特质和负性情绪[3,4,27] 等个人心理因素与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关系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研究者普遍认为,上述事件不仅是诱发药物使用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终止戒断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然而,该类研究均基于临床观察和问卷测量的结果,虽对深入的科学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但难以揭示压力导致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的内在机制[28]。
为了探讨上述问题,研究者首先求助于动物实验。Shaham等人利用复发程序(reinstatement procedure)考察了压力对动物恢复药物寻求行为的影响[29]。该程序最初是为考察戒除后的成瘾性动物在面临药物及其相关刺激时的行为反应而设计的实验方法,其基本操纵模式是将药物戒除数周后的动物暴露在药物及其相关环境中,观察其是否表现出恢复药物寻求行为的倾向。后来,Shaham等人将该程序中的药物及其相关刺激改为负性的压力性刺激(如电击),以观察压力对动物恢复药物寻求行为的影响[30,31]。研究发现,对海洛因戒除后1~2周及4~6周的老鼠给予10~15分钟间隙性电击,能有效地恢复其海洛因寻求行为。进一步改变电击的持续时间以及电击的不同部位的研究也获得了一致的结果,且电击所诱发的海洛因寻求反应与起初的海洛因注射具有同样的效果[32]。此外,在操纵戒除期限、电击参数和紧张水平以及药物类型(如可卡因、酒精和尼古丁)条件下也均获得了类似效应[31,33~35]。上述结果说明电击压力诱发恢复药物使用的现象具有普遍性。
Shaham等人以“去抑制”(disinhibitory)概念解释压力诱发复吸的机制问题[28]。他们认为,由于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的功能是当强化物不再起作用时(如撤药后),停止正在进行的行为[36],因此电击压力可通过阻止行为抑制系统的活动而诱发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即急性压力可破坏正常情况下对优势行为抑制性控制的神经过程。因此,压力诱发的行为恢复可视为一种去抑制现象(disinhibition phenomenon)。为检验该假设,Highfield等人检验了其中的两个推论[37]。其一是脑区内侧隔膜(其作用是对行为实施抑制性控制)的灭活能够模拟电击压力诱发复吸的效应;其二是压力可以延缓消退的速度(消退是激活抑制的过程,即强化物不再起作用时,有机体倾向于抑制已形成的反应)。实验结果表明,内侧隔膜的灭活诱发了药物寻求行为的恢复,而内侧隔膜的激活则促使压力诱发恢复倾向的衰竭,且电击压力有助于提高对消退行为的抵抗能力。这些结果支持压力诱发恢复药物寻求行为的“去抑制”假说。然而,该假说缺乏人类依赖者的实验数据,对于人类依赖者的药物复吸行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由于无法将人类被试置于能自由获取药物的高危情境下以观察压力对已戒除的被试重新寻求药物行为的影响[38],迄今针对人类依赖者压力的实验研究十分有限。仅有的几项研究采用模拟情境诱发依赖者的情绪体验,以主观报告的渴求感为测量指标,探讨了压力对药物寻求复发行为的影响。Childress采用催眠术探讨了药物戒除者不同情绪体验与药物渴求感诱发的关系,发现抑郁体验提高了戒除者对阿片类药物的渴求感和对阿片类戒断症状的自我评定分数;焦虑体验只提高了渴求感的自我评定,而愤怒体验只诱发了戒断症状,但欣快体验未见相应的诱发效应[39]。据此,Childress认为,负性情绪状态可能是诱发药物渴求感及其他药物相关反应的条件性刺激。在另一项更严格的实验室研究中,Sinha等人通过模拟压力情境,用两个实验考察了基于压力的负性情绪对诱发可卡因渴求感的影响[40]。实验一要求接受可卡因戒除治疗的被试准备一份面对录像机演讲的材料,并被定义为能引发焦虑情绪的演讲压力任务。演讲结束后,被试完成与其生活和环境有关但与用药行为无关的个人压力想象任务。结果发现,两种压力任务均导致被试原有中性和愉快情绪状态的显著下降,而其畏惧状态显著提高,且个人压力想象任务比演讲压力任务更能有效地诱发对药物的渴求感。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增加了与个人压力想象任务对照的中性想象任务,结果发现,与中性想象任务相比,压力想象任务不仅显著提高了被试对可卡因的渴求感,且其心率、唾液分泌和主观焦虑也有显著提高。该研究的线索诱发范式为进一步探讨人类依赖者的压力诱发药物渴求感的心理机制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手段。
4 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研究者基于快乐主义假设提出了快感—戒除反应理论,以解释药物成瘾过程[41]。根据该理论,依赖者起初的用药行为受药物的快感功能驱动,而药物的重复摄入引起神经系统对该类药物的适应性,并导致其产生对药物的耐受性和依赖性;停止用药会引发依赖者不愉快的戒除症状,故回避该症状便成为其再次用药的基本动机[2]。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观点因受到Robinson和Berridge的强烈质疑[1,5] 而被冷落10余年。最近,Baker等人基于认知与情绪领域的新近理论和研究,特别是基于“热”加工过程的研究,对早期快感—戒除反应理论的合理性做了新的阐述,提出了药物成瘾的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an affective processing model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该模型认为对负性情绪的逃避是维持成瘾行为的优势动机,负性情绪对于诱发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具有关键作用[42]。Baker等人认为,针对快感—戒除反应理论的主要批评——对由戒除症状导致的压力的逃避不能解释成瘾、渴求感和复吸行为[5] ——忽视了药物寻求动机潜在的情绪基础,因而不适当地低估了负强化对药物寻求动机的影响[42]。实际上,尽管使用不同成瘾性药物表现出不同的戒除症状,但对所有成瘾性药物的戒除症状均包含着负性情绪(如焦虑、易怒或悲伤等)这一核心特性。依赖者所以维持用药,主要在于逃避伴随戒除症状产生的负性情绪。因此,负性情绪是构成药物戒除症状的核心成分,依赖者所以维持用药,主要在于逃避伴随着身体症状的负性情绪。
根据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戒除症状在药物使用的早期便会出现,即在药物成瘾过程中,药物成分在体内的吸收、扩散和消除反应会引发一系列信号,以调节体内药物水平。当依赖者觉察到体内药物水平降低时,该内感受线索(interoceptive cues)便会导致戒除症状,同时伴随着诸如焦虑、易怒或悲伤等负性情绪的产生。该过程的重复使依赖者对体内药物水平降低的觉察和对负性情绪的回避动机之间逐渐形成程序化的固定联系。当依赖者中断用药或处于戒除期时,体内药物水平的降低便会成为引发负性情绪的内感受线索,使依赖者对该线索变得高度敏感,成为优先加工和反应的对象,使依赖者将注意集中于觉察威胁性事件及其负性情绪,产生注意偏向和选择性反应,从而使对负性情绪的逃避成为其维持用药或复吸行为的主要动机。由于药物使用是其改善负性情绪的最有效的反应,因此当负性情绪水平出现时,依赖者会反射性地选择用药行为,而其他反应由于不能直接减弱负性情绪而被抑制。这时依赖者的认知控制资源被投放于旨在缓减负性情绪水平的药物寻求行为,使其难以从情绪性应对过程中退出。Baker等人认为,依赖者虽然可能意识到自己觅药的欲望和药物寻求行为,却意识不到诱发觅药欲望及药物寻求行为的动机是在于逃避由药物水平降低所造成的负性情绪[42]。
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的核心在于重新强调,成瘾性药物依赖者维持其药物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其痛苦的情绪体验的观点,从而重新肯定了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对于诱发药物寻求和复吸的作用。它既不同于基于药物相关线索的认知加工理论,也不同于基于压力的去抑制假设。后两者都把诱发药物寻求的线索定义为外部线索,即外感受线索(exteroceptive cues),认为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认知加工偏向或对外部压力的负性情绪反应是诱发药物渴求感的核心因素,而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则认为导致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的负性情绪是依赖者对其体内药物成分下降的自动化觉察的结果,即负性情绪的产生是基于对内感受线索的自动化觉察。该模型主要依据认知与情绪领域的新近理论和研究,特别是基于“热”加工过程的研究,认为基于内感受线索的负性情绪使依赖者将认知控制资源用于选择能有效回避负性情绪的应对策略,从而忽视了对其他信息的加工。这一观点有助于加深负性情绪对诱发药物寻求行为作用的理解。然而,负性情绪的产生不仅基于内感受线索,而且基于外部的压力线索。该模型忽视了外部压力或压力线索导致负性情绪的机制问题,也忽视了已经产生的负性情绪对外部压力线索的加工过程的影响。此外,该模型虽然重新肯定了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对于诱发药物寻求和复吸行为的意义,却始终没能正面回答Robinson和Berridge对快感—戒除反应理论的主要批评,即没能解释经过长期的戒除治疗,其戒除症状及相关负性情绪已经消除的依赖者(可卡因或海洛因依赖者)为何复吸的机制问题。
5 小结
综上所述,认知加工理论试图以药物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加工偏向解释药物成瘾及复吸行为,而去抑制假设和负强化情绪加工理论则试图从对外部压力的回避或对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的回避倾向对成瘾和复吸行为作出说明。随着上述新的成瘾理论模型的发展,目前该领域形成了两种分离的研究取向:其一是以线索诱发药物渴求感为内容,通过认知加工理论解释药物相关线索诱发复吸行为的心理机制;其二是以压力或负性情绪诱发药物渴求感为内容,通过回避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或行为“去抑制”的概念解释依赖者药物滥用或复吸行为的心理机制。其中基于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证据,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而针对外部压力或基于戒除症状的负性情绪模型的研究则多局限于测量学方法,尽管该类模型的部分假设已获得基于少数动物模型和人类被试的实验支持,但尚缺乏系统的科学证据,其理论模型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加强基于人类被试的压力及负性情绪诱发药物滥用及复吸行为的实验探讨,并整合基于药物相关线索的认知加工机制研究和基于压力及负性情绪回避的心理机制研究,建立更具整合性的药物成瘾理论模型,以获得对药物成瘾及复吸行为机制的全面理解。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项目(BBA0300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4BSH023)和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中心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