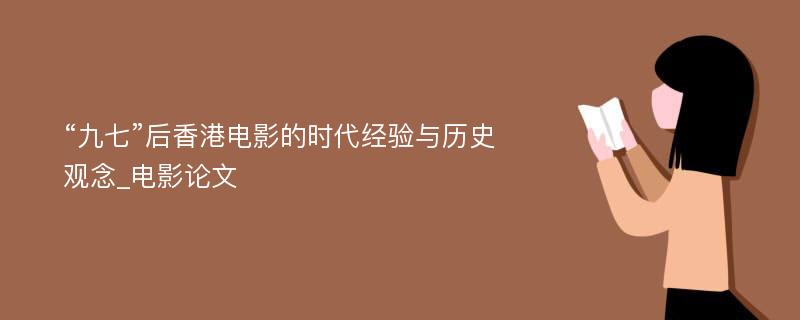
“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电影论文,观念论文,时间论文,历史论文,后九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香港导演冯炳辉“自主创作”了一部29分钟短片《香港公路电影》,并明确表示电影和录像不需要“解释事实”或“表达观点”;但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刊《香港电影面面观96—97》在介绍该片时,仍然意味深长地叙述道:“1997年7月1日,是历史性的时刻。1997年6月30日,也是历史性的时刻。1997年6月31日,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人在逃避未知的九七大限,另一个人默默地等待,然而,两者却可以在网上的Cyber国度里相遇。……”(1) 而在电影节节目策划和编辑王庆锵专为该刊所作的“序言”里,则表达了自己对“Hong Kong”可能就要变成“Xianggang”这一事实的忧虑以及对1984年开始就“没完没了”地被问及“你如何看1997?”这一问题的郁闷。确实,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时间刻度,“九七”之于香港社会和香港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样,1997年7月1日之后亦即“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便成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两地电影界亟待展开的学术话题,并成为深入阐发当下香港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涵的重要途径。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指称的“香港电影”,按一般情况基本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其导演是在香港住满7年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第二,其出品公司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的公司;第三,其影片幕前及幕后工作人员至少有1/3为香港居民。与此同时,为了论述方便,笔者试图选取“后九七”(1997年前后至2007年初)香港影坛中一批较为“用心”或颇能“言志”的作者与文本,从文化批评的层面进行认真地分析和读解。这些作者和文本主要包括:陈可辛、许鞍华、陈果、王家卫、关锦鹏、杜琪峰、林岭东、陈嘉上、陈德森、叶锦鸿、马伟豪、徐克、成龙、尔冬升、刘镇伟、周星驰、袁建滔、刘伟强/麦兆辉等导演或监制的《甜蜜蜜》(1996)、《香港制造》(1997)、《春光乍泄》(1997)、《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两个只能活一个》(1997)、《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暗花》(1998)、《非常突然》(1998)、《野兽刑警》(1998)、《我是谁?》(1998)、《风云雄霸天下》(1998)、《枪火》(1999)、《暗战》(1999)、《紫雨风暴》(1999)、《千言万语》(1999)、《细路祥》(1999)、《目露凶光》(1999)、《半支烟》(1999)、《花样年华》(2000)、《榴莲飘飘》(2000)、《顺流逆流》(2000)、《少林足球》(2001)、《蓝宇》(2001)、《麦兜故事》(2001)、《蜀山传》(2001)、《香港有个荷里活》(2002)、《天下无双》(2002)、《见鬼》(2002)、《三更之回家》(2002)、《无间道》(2002)、《金鸡》(2002)、《忘不了》(2003)、《大只佬》(2003)、《PTU》(2003)、《向左走,向右走》(2003)、《地下铁》(2003)、《无间道2》(2003)、《无间道3终极无间》(2003)、《人民公厕》(2003)、《功夫》(2004)、《三更之饺子》(2004)、《2046》(2004)、《大事件》(2004)、《旺角黑夜》(2004)、《麦兜菠萝油王子》(2004)、《江湖》(2004)、《黑社会》(2005)、《杀破狼》(2005)、《神话》(2005)、《七剑》(2005)、《如果·爱》(2005)、《三岔口》(2005)、《伊莎贝拉》(2005)、《情癫大圣》(2005)、《黑社会2之以和为贵》(2006)、《放·逐》(2006)、《伤城》(2006)、《门徒》(2007)、《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7)等等。总的来看,“后九七”香港电影通过对时间元素的强力设计,执著地表达着记忆与失忆、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展现出历史编年的线性特征与主体时间的差异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正是通过这种浸润着香港情怀的现代性时间悖论,“后九七”香港电影呈现出一种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于一身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特质,并以其根深蒂固的缺失感界定了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
应该说,人类的时间体验与历史感知由文化建构并经由文化而获得,不同的文化对时间有不同的体验,时间则在不同的时空中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意义。(2) 这也是从文化批评层面探察“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所能秉持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西方哲学史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笛卡尔、柏格森与海德格尔等,都在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历史等领域进行过精深的研究与经典的阐发。迄今为止,笛卡尔“真正的精神是记忆和失语症,是绵延的时间”的观点以及柏格森关于“主客体区别与融合的问题是根据时间而不是空间提出的”的论题,都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时间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弗朗索瓦·利奥塔指出,“种族文化在很长时间内曾是各民族贮存信息、组织空间和时间的工具”,“它们创造了被我们称为历史叙事的时间性的特殊结构”,而“历史叙事”可以被当作一种类似“时间过滤器”的“技术装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应该自认为是一种“原因”,也不是一种“结果”,而应将自己看作一种可靠的“转换器”,一种由其技术科学、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及其带来的“新的记忆方式”的“转换器”。(3) 在弗朗索瓦·利奥塔看来,“时间”将应总是被置于将来的“尚未”与过去的“不再”之间,“非人”则为寻找失去的时光而丧失时光。
电影或影像无疑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新的记忆方式”。在《电影2:时间—影像》一书里,通过对小津安二郎与安东尼奥尼等杰出影人作品的具体分析,吉尔·德勒兹强调了“影像”与“时间”的本质联系:“每个影像都是时间,都是在时间所变之物的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的时间。”(4) 至此,存在/时间/影像构成一个颇有意味的等式:银幕上的影音即为时间的展开,也为存在的表征。这样,考察“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与历史观念,便成为研究香港意识及其精神文化的题中之意,反之亦然。
对于大多数普通的香港民众而言,1997年不仅是“前途未卜的大限”和“患难意识的地平线”,(5) 而且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中断其内心深处一以贯之的时间体验和历史观念。也就是说,在一种充满着紧张感与焦虑情绪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随着“九七”的到来,香港社会将会遭遇一段时间的裂缝与历史的虚空,这种独特的精神体验和文化状况,自然也会呈现在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里。
精神与文化的构成跟时间的范式密切相关,现代社会是机械时钟时间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期。正如论者所言,从心理学上来说,把时间划分为均匀的单元,可以满足人们所渴望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当这样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被打断之时,身心的和谐便被干扰,这种对于“时间裂缝”(time-gap)的体验就会令人心神不宁;总之,“时间裂缝在我们对于时间流逝的意识中产生了谜一样的空白。这种时间错觉同样应被视为一种干扰因素,它使得我们难以把握当下”。(6) 对于香港社会与香港电影而言,1997年7月1日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裂缝”,由其带来的社会震荡、心灵创伤与行为偏执,都能通过存在/时间/影像的等式获得理解。
在一篇全面回顾1996年香港电影现象的文章里,李焯桃生动地阐述了“时间”之于香港电影的重要性以及电影中所体现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九七情意结”:“若不计延迟了推出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及《古惑仔》系列的续篇《97古惑仔之战无不胜》,整个古惑片潮流于短短八个月内便发展完毕,压缩程度的确惊人。电影潮流的周期愈来愈短,固然是世界性的现象;但香港独有的九七因素,更使港产片这方面遥遥领先。事实上,随着九七逼近眉睫,港片无论定位或关心的焦点,都愈来愈回归香港本身。在《奇异旅程之真心爱生命》及《嬷嬷帆帆》直写宿命大限参悟人生后,仍有赵崇基的《三个受伤的警察》及梁柏坚的《摄氏32°》,分别借警察片及杀手片的类型,抒发其对九七的悲观绝望情绪。《三个》把剧情背景局限在九六年除夕一天之内,最终爆发悲剧,时限压力的喻意明显不过。……”(7)——在这里,作者不仅点明了时间裂缝(“九七”)迫近之前香港电影或恐慌、或抗拒、或悲观、或绝望的精神症候,而且体会到这种因时间裂缝(“九七”)而引发的“时代错置感”,亦即时间连续性的中断与历史完整性的丧失。
因应《奇异旅程之真心爱生命》、《嬷嬷帆帆》与《摄氏32°》等影片的“宿命”陈述,“后九七”香港电影也步入一个必须直面时间裂缝与历史虚空的“宿命”。这一点,在许多导演创作的影片中都有所体现,尤以陈果导演的一系列与“九七”相关的影片以及许鞍华导演的《千言万语》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2046》等为代表。
从1994年撰写电影剧本《香港制造》开始,陈果就在以特定的方式,自觉地将自己的电影创作与“九七”香港回归中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尽管由他导演或编导的大多是低成本影片,却相当深刻地描绘出“九七”前后香港民众的惶惑心态与梦想历程。正如研究者所言:“陈果是香港导演中惟一一个有意识将‘九七’前后拍成‘过渡期三部曲’的导演。《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和《细路祥》这三部电影坚持以香港作为‘根’的强烈自我意识,极具生活感和感情的撞击力,细述了香港人面对时代变化的不同反应。”(8) 确实,在陈果导演的“过渡期三部曲”以及此后的《榴莲飘飘》、《香港有个荷里活》、《人民公厕》等影片里,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事件及其对香港社会的深刻影响,总是与草根阶层无望、无助或无奈却又细微、琐碎或荒诞的生存状况交织在一起,并衍生出极具反思性的情感张力。线性的历史编年跟各异的主体时间产生巨大的落差,时间裂缝造成的历史虚空,使“后九七”香港电影笼罩着一层令人茫然的乖谬之气。
《去年烟花特别多》是陈果“过渡期三部曲”中与“九七”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密的一部。影片开始,伴以《友谊地久天长》的童声吟唱,是1997年3月31日亦即香港回归中国三个月前Hong Kong Military Service Corps(香港华人英军)正式解散的纪实性画面。接下来,底层者的故事展开。退伍后的HKMSC军人吴家贤、吴家璇等仿佛被社会遗弃,在1997年的香港这座烟花盛放之城里挣扎着求生,并以“半个黑社会的会员”身份跟着老大抢劫银行。正是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与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的仪式过后,满城璀璨的烟花消散。雨中人海里的主人公吴家贤一行,在警察的严密监控和穷追不舍之下,竟抬起右手,向进城的解放军军车庄严地致敬。历史正在以其预期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迈进,曾经为“英军和香港历史”做出贡献的个人却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局。这种时间裂缝和历史虚空,正像黑社会老大面对吴家贤的真情告白,现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是新的”,“连香港也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我和你已经是老婴儿了”;也像影片结束时响起的主题歌:“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冲动,灿烂的烟花也是一场空。”
作为“过渡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细路祥》在《香港制造》和《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香港回归的历史事件与旧区街坊的日常生活令人惊奇地组织在一起,却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风格化境地。影片选取祥仔和阿芬这两个儿童的视点,以他们的心境体味香港回归前半年的人情世态;并以两人的各异身份和不同命运,见证历史巨浪中个人无法辨识的成长路程。就像影片结束之前,瘦小的祥仔骑着高大的脚踏车,飞快地穿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巷弄,疯狂地追赶被警车带走的内地好友阿芬,却非常搞笑地错追到救护车上。警车中面无表情的阿芬与救护车里一脸迷惑的祥仔,在1997年7月1日之前的香港,在结束他们的友谊的同时也结束了他们的童年。可以说,围绕在祥仔和阿芬周遭的一切,是陈果勾勒“九七”氛围和想象香港身份的细腻层次。(9) 影片中一个神采飞扬、令人遐思的段落,是祥仔和阿芬来到海湾,眺望着香港岛的高楼大厦,各自高喊“香港是我们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回归”之日,一种悲喜交集、茫然惶惑而又不知所以的复杂情绪,通过这两个儿童之口,得到了合理而又会心的宣泄。(10)
如果说,《细路祥》里的阿芬从内地偷渡来港,在与香港土生土长的祥仔共享友谊的同时却分担着不同的香港经验,那么,在《榴莲飘飘》与《香港有个荷里活》里,陈果则颇费心机地通过秦海璐和周迅饰演的两个“北姑”及其不同命运,将内地的香港经验与香港的内地观念统合在一起,力图填补时间的裂缝及其造成的历史虚空。然而,颇有意味的是,《榴莲飘飘》中在香港接客三个月后返回东北老家的阿燕,想起香港就像内地女孩阿芬从香港寄来的榴莲,她的香港经验只是旺角的后巷、公寓和茶餐厅;《香港有个荷里活》中以卖腊肉为生的朱家父子,对内地的理解仅限于针对北方女孩东东的肉欲和依恋,东东的出现和消失伴随着香港特区政府的重建计划,随之消失的便是香港历史上的最后一片木屋区。这样看来,两部影片虽然以导演特有的方式呈现出内地的香港经验与香港的内地观念,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内地与香港之间无法理解与沟通的困窘。《榴莲飘飘》里的榴莲,在香港号称“果中之王”,在牡丹江却少有人识,也无人问津;《香港有个荷里活》里的东东,只要出现一下,就把香港木屋区“搞得一塌糊涂”。(11) 这是一种将香港与内地互相表述为“他者”的方式,不仅无法填补“九七”后的时间裂缝,而且不能阐明两地亟须整合的历史认知。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与王家卫的《2046》里。《千言万语》以“忘记”、“革命十年”、“不会忘记”的三段式结构展开叙述,凸显“时间”和“历史”之于创作主体及其影片本身的重要性;而具体的时代背景,则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止于1989年春夏之交。尽管影片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给定一个宿命的悲情结局;而经历过爱情的创痛、政治的无情与港人“自尊的破碎”,女主人公刻意隐瞒病情,为要“忘记过去”期盼着重新生活;男主人公之一甘仔也离开香港踏足深圳,“展开梦想之旅”,(12) 但如此抛开“历史的重担”,除了期许一个更好的“明天”之外,这种游弋于“香港”与“中国”之间的浪漫情怀,确实无助于填补那些时间裂缝造成的不安与不适,更不可能在历史的虚空中标明“坚持到底”的价值和意义。(13) 正像“忘记”与“不会忘记”之间形成的情感错迕,“九七后”的香港电影,正在设法抹平香港与内地之间因“时间”与“历史”的断裂而形成的巨大裂隙。
其实,在香港导演群体中,王家卫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对“时间”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敏感性的电影导演;“时间”甚至就是王家卫电影永远不变的主题。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为分界线,王家卫电影中嘈杂、逼仄而又变形的空间展示以及超常强度的时间设计、终归失败的异域寻根、宿命一般的现状认同、无法遁逝的感情逃避与纳入议程的秩序重整、美丽凄婉的信念坚守等一系列反复隐现的叙事动机,基本对应于香港民众面对“九七”所领受的复杂的心路历程。(14) 值得注意的是,“九七”之前与“九七”以后,王家卫电影里的时间设计也颇有差异。如果说,“九七”之前的王家卫电影,往往是以无法阻止的紧张态势以及精确到分、秒的计算方式突出呈现历史编年的厚度与个体时间的质感,那么,“后九七”王家卫电影亦即《花样年华》、《2046》里的时间,或在近乎凝滞甚至静止的氛围中散发出针对过去岁月的怀旧情调,使观众沉湎于一种远逝的生活、唯美的情感与虚无的体验之中,或在充满神秘、无法把握的机械世界里,营造出2046这个特殊的未来时空,并在1966年与2046年间展开一场有关“找回失去的记忆”的爱情接力。显然,“后九七”王家卫电影里的时间设计,已经颠覆了此前的编年模式。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或者被浓缩在一点,或者被拉长到无限。时间失去应有的向度,历史崩塌。
当时间失去应有的向度,记忆也会失去依据;而当失忆成为追寻的动机,“后九七”香港电影充满了怀旧的无奈。
几十年来,香港电影中也有以“失忆”作为故事情节的转折或人物命运的安排的先例;但只有在“后九七”香港电影里,才会出现如此集中、如此饱含深意的“失忆”主题。仿佛在一时之间,跨不过“九七”这个时间裂隙,银幕上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失去记忆,并对着电影院里心态各异的观众,不无沉痛而又略显滑稽地追问:“我是谁?”甚至把这个既深邃又荒诞的问题叫成自己的名字。
《我是谁?》是成龙的跨国制作。在影片中,成龙饰演的主人公没有过去,也没有来处。他有6本不同国籍的护照,却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个失忆的特别突击队员,在无法进行言语交流的非洲,被土著人叫成了" Who am I? " 诚然,失忆的处境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成龙灵活多变、庄谐并重的演技,并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高的票房收入;但影片中不时出现的“我是谁?”的呼喊或疑虑及其蕴涵的失忆主题,总是以非常醒目甚至过于夸饰的效果呈现在银幕上,直达受众的感官。这样,无论是从类型还是作者的角度来读解《我是谁?》,都不能不对影片中成龙即“我是谁?”的尴尬遭遇和荒诞处境表现出特别的同情。个人的失忆引发集体的焦虑,因失忆而失去名字和身份的“我是谁?”,映照的是“后九七”香港回归中国后失去归宿、茫然无措的集体无意识。颇有意味的是,《我是谁?》上映8年后,成龙在另一部自己主演的影片《神话》中,尽管没有“失忆”,却仍要面对“如果蒙将军战死沙场,那你是谁?”的诘问。满脸疑惑的当代考古学家Jack,此时确实无法把自己跟秦朝的蒙毅大将军分别开来。然而,如果要在“蒙将军”和Jack之间画上等号,成龙饰演的这两个角色,必须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这样,幻境与现实交织,并在最后转换成“神话”叙事。即便是梦,也可以成为记忆,在怀念中品尝命运的无奈与爱的甜蜜。
在一篇论述影片《紫雨风暴》的文章里,针对《我是谁?》和《紫雨风暴》等“后九七”香港动作片的“失忆”主题及“创作新倾向”,纪陶指出:“失去记忆,在戏剧中可比喻成身份强被掠夺,或者被迫清洗,在九十年代港片出现探求身份的现象,明显是与九七主权移交有直接关系,而失忆更可说是港人在后九七的症候群,大家都必须/被迫清洗以往殖民时代的记忆,抛掉以前的价值观及处事方式,要重新学习,重新适应,才能够融入中共的大体系。”(15) 将电影里的“失忆”主题与现实中的“权力”政治进行如此比附,似乎太过直接,但“后九七”香港电影里的“失忆”,确实不再是个人的率性而为或偶然的情节设置,而是与创作主体担心失去以往身份的隐衷联系在一起。这在叶锦鸿编导的《半支烟》中体现得更加明晰。限于篇幅,不再具体阐释。
跟“失忆”的主题相伴而生,“记忆”也是“后九七”香港电影经常表现的主题。尤其是在赵良骏导演的故事片《金鸡》、《金鸡2》以及袁建滔导演的动画片《麦兜故事》、《麦兜菠萝油王子》里,分别通过主人公阿金和麦兜的喋喋不休的自述,以个人的经历参证香港的历史,在怀旧的氛围里复现“九七”症候中香港的电影记忆。根据《金鸡》里阿金的叙述,阿金的色情业务伴随着20年来香港的政治、经济与民生。从经济起飞、中英谈判到北姑入侵、九七回归,从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负资产、破产浪潮再到投身“一楼一凤”自雇行列并与香港市民同唱《狮子山下》;而根据《麦兜故事》里麦兜的叙述,九龙大角咀猪样小朋友麦兜的成长,也经历了出生、上幼稚园、上中学,再到长大最后负家产的过程。这种主动回归线性编年历史的个人叙述,无疑是一种努力克服现代性时间悖论的尝试。通过这种努力,“后九七”香港电影重建了一种完全立足于香港本土的时间向度和历史陈述,在普遍的失忆中找回了记忆。
然而,“后九七”香港电影更为普泛的精神状况是:在记忆与失忆中反复徘徊并为身份的缺失备感焦虑。这也是不少具有“卧底”情节的警匪片尤其是刘伟强、麦兆辉导演的《无间道》、《无间道2》与《无间道3终极无间》在影坛上产生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按影片出品方寰亚电影执行董事庄澄的理解,《无间道》“最大的特点”,是很像中国画的“留白”,并利用许多“暗场”来交代剧情。(16) 可以看出,这种“留白”和“暗场”,确实正与主人公暧昧难辨的身份状况形成颇为精妙的同构;而在主人公刘建明与陈永仁第一次相遇的音响店里,两人坐在一起,听的是同一首《被遗忘的时光》的老歌:“是谁在敲打我窗棂?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这三句歌词,在试听音质的时候被接连着播放了两遍。随后,在大厦的天台,陈永仁的上司训斥已经在三合会卧底近十年的陈永仁:“你忘了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影片结束之前,仍然是在大厦的天台,身份互换的刘建明与陈永仁举枪互指,两人的对白还是有关记忆与身份的话题。直到《无间道3终极无间》的结尾,编导者再一次倒转时空,回到刘建明与陈永仁第一次相遇的音像店里,再一次试听那首《被遗忘的时光》的老歌。表面上看,三集《无间道》讲述的都是紧张曲折、警匪互渗的“卧底”故事,但从其内在意蕴上分析,总能让人联想到“记忆”、“失忆”、“怀旧”、“身份”等香港电影的关键词。
更进一步,包括《无间道》、《无间道2》与《无间道3终极无间》以及在此前后的《两个只能活一个》、《暗花》、《风云雄霸天下》、《枪火》、《暗战》、《蜀山传》、《PTU》、《见鬼》、《大只佬》、《黑社会》、《神话》、《放·逐》、《黑社会2之以和为贵》、《伤城》等影片在内的“后九七”香港电影,除了以强力设计的时间元素执著地表达记忆与失忆的主题外,还在强烈的身份追寻中展现因果与循环的特殊命题,力图在历史与个人的时间悖论里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中在一起,昭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缺失。
《无间道》片名已经宣示出这种因果和循环的宿命。影片片头,即出现几行字:“《涅槃经》第十九卷:八大地狱之最,称为无间地狱,为无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片中的音乐元素,也不时浸润着佛乐的宗教意绪。在此之前,文隽、刘伟强根据马荣成的漫画作品改编导演的《风云之雄霸天下》,即以传达世间的“因果”和“宿命”为旨归。影片中,雄霸的命相军师泥菩萨为从雄霸的手中留下聂风和步惊云的活口,预先把聂风和步惊云的时辰八字给了雄霸,并以“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的批言,预测风、云二人能帮助雄霸一统天下;随后,收了聂风、步惊云为徒弟的雄霸,得到了泥菩萨的另外两句批言:“九霄龙吟惊天变,风云际会浅水游”,遂萌生杀徒意念,没料到错杀了自己的女儿孔慈;而和好后的风、云二人,也分别以父亲遗下的“雪饮狂刀”和“绝世好剑”,跟雄霸展开了生死决战。在这里,泥菩萨的“批言”主宰着人们的言行,令人感觉到“天理”循环、“天意”难违。正如泥菩萨所言:“我只知天理循环,因果报应,冥冥中自有主宰。”按影片编剧文隽的解释,电影跟漫画一样,不仅是“商品”,而且是一种“潮流文化”,(17)《风云雄霸天下》中因果和循环的宿命的主题,以及比漫画本身更加严重的父权至上、红颜祸水的“保守的意识形态”,虽然容易招致批评界的诟病,(18) 但经由电脑生成视觉奇观后的电影作品,在观众中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也是无法阻挡的。
如果说,在刘伟强监制或导演的影片里,总是传达出一种与宗教情感或东方神秘密切相关的有关因果和循环的特殊命题,那么,在杜琪峰监制或导演的影片中,这种充满着怀疑和无奈的因果和循环及其宿命意识,则跟世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哲理联系在一起。谈到影片《大只佬》,杜琪峰表示:“电影本身,就是想鼓励大家做人的道理。《大只佬》同韦家辉一起导演的,最希望讲到的就是因果,有因必有果。‘果’改不了,因为之前种了这个‘果’,要改就要改‘因’。‘因’就是现在,现在改,将来的‘果’就会改变。人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因果因果,佛学更大的就是一世、两世、三世……今世做的事可以做错,但是来世、再来世为了这个‘因’就要做好多好多事来赎罪。如果今天做了一些好的东西,就会得到一些好的结果。简单说,就是‘因’和‘果’。”(19) 而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观时,杜琪峰毫不避讳“宿命”论:“我自己的生存理念都是宿命。很多时候人都会重复犯错,不是重复一次,是不断重复,这就是人生。用在宿命上,人生是可爱的、可笑的、有趣的。”(20) 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因果观和宿命论,杜琪峰创作的一系列黑色电影风格的警匪片,如《两个只能活一个》、《暗花》、《枪火》、《暗战》、《大只佬》、《PTU》、《黑社会》、《放·逐》、《黑社会2之以和为贵》等,往往在一个逼仄的空间和压缩的时间里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最后的结局,或者以其突然的转折令人匪夷所思,或者在无可奈何的宿命中令人唏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后九七”香港民众不愿直面历史编年的逃避心理。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无论表现记忆与失忆,还是阐发因果与循环,“后九七”香港电影的时间体验,都没有跨越“九七”这个巨大的裂缝;也正因为如此,“后九七”香港电影,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将怀旧的无奈与怀疑的宿命集于一身的历史观念与精神特质,并以其根深蒂固的缺失感,界定了香港电影的文化身份。
注释:
(1)《香港电影面面观96—97》,1997年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题特刊,第50页。
(2)[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3)[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50页。
(4)[法]吉尔·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谢强、蔡若明、马月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5)参见[美]丘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唐维敏译,郑树森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6)[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7页。
(7)李焯桃《古惑仔潮流与九七情结》,载《香港电影面面观96—97》,1997年第2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刊,第8—9页。
(8)列孚《90年代香港电影概述》,《当代电影》2002年第2期。
(9)参见王玮《香港电影壹观点》,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04—305页。
(10)本段论述,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534页。
(11)参见张燕《映画:香港制造》中的“与香港著名导演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12)参见宾尼《〈千言万语〉:希望》,载何文龙主编《一九九九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0年版,第98页。
(13)影片中,甘仔说过这样一段话:“上主,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坚持呢?我们是应该坚持到底的!”
(14)本段论述,参见李道新《王家卫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含义》,《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
(15)纪陶《根源所在》,载何文龙主编《一九九九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0年版,第64页。
(16)弥生《庄澄回首〈无间道〉》,香港《电影双周刊》第643期。
(17)文隽《风云——一个十句讲完的古仔》,香港《电影双周刊》第502期。
(18)参见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28页。
(19)(20)吴晶《时代的影像者·影响者——杜琪峰导演访谈录》,《当代电影》2007年第2期。
标签:电影论文; 香港有个荷里活论文; 香港论文; 香港电影论文; 去年烟花特别多论文; 榴莲飘飘论文; 失忆症论文; ptu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犯罪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法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