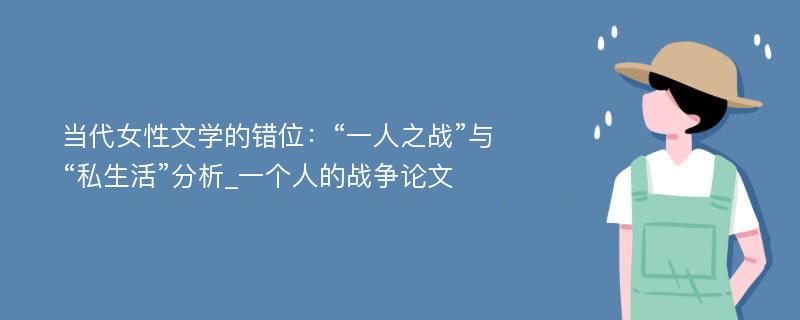
当代女性文学的误置——《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战争论文,私人生活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开始,文学界的“阴盛阳衰”便成了一个经常被人谈论的话题。当政治经济的话题从文学主题的宝座上谦逊地退位以后,似乎男作家们也随之被挤到了文学园地的一隅,最精彩的戏都是由“感情化、神经质”(王蒙语)的女性作家们来上演的。女作家们本身就是一种新型人格的探索者,她们大都置身于男作家的“寻根”的集体意识之外,往往能更直接更细腻地表达极为新奇特异的感触和思想,而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意识保持着有意的拒斥关系。然而,由于她们自身固有的某些缺陷,她们虽能形成一股冲击传统审美趣味的情感和情绪力量,但最终往往很难定位于普遍人性的开拓,无法形成真正有力的个性人格。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所鼓吹的“个人写作”或“私人话语”,其落脚点仍然是“女人写作”和“女人话语”,所表达的主题往往从反传统滑向了反对男性,从树立个人变质为呵护女人。林白和陈染是这一倾向的较典型的代表。
9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所鼓吹的“个人写作”或“私人话语”,其落脚点仍然是“女人写作”和“女人话语”,所表达的主题往往从反传统滑向了反对男性,从树立个人变质为呵护女人
当然,一般来说,90年代女性写作的确对传统男性文化是一种深刻的震动和挑战。但这只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由男性建立起来的政治道德文化传统在显性的男性话语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厚的女性文化的根基。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女性化”的,这从男性文化本身从来无法清除的恋母,寻根的倾向可以看得出来。因此,女性写作揭示出中国文化这一阴盛阳衰的事实,这本身就足以摧毁男性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的自信,成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动。这种举动有些类似于“痞子文学”对实情的揭露;但也正因此而成了一种变相的“寻根”;它不能解决在摧毁了旧东西之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很可能如鲁迅说的“醒来”之后发现“无路可走”。这种寻根如果不能向更高的精神层次探寻,而是沉溺于其中流连忘返,以物质(男女两性的区别)来冒充精神,就会重新堕入传统文化(女性文化)的圈套,散发出陈腐的气息。这大概是某些最“先锋”的女性作家始料不及的。换言之,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让男性读者也从中读到自己的灵魂,而只是满足着男性的某种窥视欲和好奇心,这种作品就无法达到人道主义的层次,而将局限于传统女性特有的狭隘、小气、自恋和报复心理。
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让男性读者也从中读到自己的灵魂,而只是满足着男性的某种窥视欲和好奇心,这种作品就无法达到人道主义的层次,而将局限于传统女性特有的狭隘、小气、自恋和报复心理。
林白和陈染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是个性化色彩较突出的,而且她们自己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达到了故意标榜的程度。林白和陈染只要读上两三句,就知道出自女性(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之手。她们似乎以此而自豪,因为在男性占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大合唱”中,她们自认为是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的一声“强有力的独唱”(见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及附录“另一扇开启的门”)。看她们的小说,我老想起有本杂志上一篇叫作《做女人真好》的文章,里面有句宣言式的话是:“下一辈子还做女人!”作为艺术,我看不出这种情绪能为作品增色多少。至少,女性化决不等于个人化(因为人类有二分之一都是女性)。真正的艺术得从更高处用力。
下面我想根据90年代两部有代表性的纯女性文学作品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来分析一下当代中国人对于个体人格建设所存在的理解上的误区,评价一个当代中国最有思想活力的女作家们在这一误区中的冲撞和摸索。
(一)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开头的题辞颇富哲理:“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一个人的战争》,载《林白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页。 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单从这一题辞来看,这是一连串的悖论,它表达了自我意识内在的自否定和经过自欺而自我深入的结构。应当说,这是一种成人的心态,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人的灵魂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内心焦虑和冲突,通过它一个人达到精神上的成熟。
然而,林白一开始就把这种心态理解成了一种性格上的孤僻。这是一种生就的自我敏感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多米从五、六岁起就有一种自我抚摸的爱好。其实许多敏感的孩子都有这种经历,它属于儿童心理发展上的正常阶段;但是如果从小缺乏大人的关怀(如多米三岁失去了父亲,母亲经常不在家),这种自我关怀就会得到加倍的刺激,以致于发展为某种“受虐狂”。这也许是多米在进入青春期“常常幻想被强奸”(第19页)的心理原因。并且,由于没有亲人的抚摸,多米长期靠自己满足自己,她从小养成了“一种男性气质”,“从不撒娇”,她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受过锻炼的人,千锤百炼,麻木而坚强”(第24页)。“她没有领袖欲,不喜欢群体,对别人视而不见,永远沉浸在内心,独立而坚定,独立到别人无法孤立的程度”(第26页)。但是,一个性格上独特的女孩子是否能成长为一个人格上独立的女人呢?不一定。
多米虽然具有某种“男性气质”,但她内心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甚至“女性崇拜者”(第33页)。她说:“我30岁以前竟没有爱过一个男人”,“我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女人”,“女人的美丽就象天上的气流,高高飘荡,又象寂静的雪野上开放的玫瑰,洁净、高级、无可挽回;而男性的美是什么?我至今还是没发现。在我看来,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美的,我从来就不理解肌肉发达的审美观”(第27页)。她甚至因此而有一种类似于同性恋的倾向。显然,对女性的这种崇拜以及对一般男性的厌恶不是来自性格,而是来自文化。多米的审美观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和众姐妹的审美观,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例如多米也和贾宝玉、林黛玉一样,认为就连男人住过的房间都有“一股浊气”(第165页)。由此看来,她那“不喜欢群体”、 “独立而坚定”的性格在文化的浸润中也成了一种林黛玉式的孤傲。其实,如林黛玉一样,多米何偿“不喜欢群体”,她内心渴望群体的理解,这渴望阻止她真正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在大学里,她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来“帮她投入人群,使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第55页)。
但这种需要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渴望而保存在灵魂深处。多米的心性很高,她深知周围人群中没有能使她投身于其中的对象,即使在大学,她也害怕人际的接触和坦露。“只要离开人群,离开他人,我就有一种放假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感到安静和轻松”(第37页)。然而,这种孤傲是无根的,或者说,它的根恰好是相反的东西:她的坚强来自于她的软弱,她的隐蔽欲来自于她的敞开欲、裸露欲。正因为意识到一旦敞开、裸露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为这种敞开将会是那么彻底和不顾死活),她才那么小心地隐蔽自己。同样,她对同性的拒斥(如对同性恋者南丹的“天敌”式的拒斥)正是源于对同性的美丽的赞叹,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顾影自怜的赞叹。这种赞叹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欣赏,而不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占有和融合,否则就会变成同性相斥。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不恰好说明,多米对女人的美的欣赏以及她的自我欣赏并不真正具有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而恰好背后隐藏着一种异性的(男性的)眼光。的确,她正是用男人的眼光在欣赏自己。正是在男人的眼中,“美丽的女人总是没有孩子的,这是她们的缺陷,又是她们的完美。她们是一种孤零零的美,与别人没有关系”(第129页)。 男人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孩子、与别人“没有关系”的孤零零的美丽女人。
在中国,极其“女性化”的写作从本质上看都是立足于男性的眼光和趣味来进行的。换言之,西方女权主义要摆脱由男性文化所塑造起来的女人身上的“第二性”特征,来强调女性自身的独立不倚;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却恰好是鼓吹和美化这种“第二性”的狂热分子。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中国,极其“女性化”的写作从本质上看都是立足于男性的眼光和趣味来进行的。换言之,西方女权主义要摆脱由男性文化所塑造起来的女人身上的“第二性”特征,来强调女性自身的独立不倚;而中国的女性主义却恰好是鼓吹和美化这种“第二性”的狂热分子。西方女人不要孩子是为了能象男子一样追求社会活动和精神的创造及享乐,中国女人不要孩子通常却是为了男人的趣味、男人的方便。因此,毫不奇怪,多米逃避了南丹的倾慕,却渴望哪怕有男人来强奸,来毫无顾忌地、粗暴地享用她的美,乃至她在轮船上轻易地委身于第一个来和她搭话的男子,她后来总结这件事的起因:“有两样东西更重要:一是我的英雄主义(想冒险,自以为是奇女子,敢于进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软弱无依。”(129 页)而后者是更根本的:“她还没有过服从别人的机会,”“她需要一种服从和压迫。这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一种抛掉意志、把自己变成物的愿望深深藏在这个女孩的体内,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女孩自己却以为是另一些东西:浪漫,了解生活,英雄主义”(第131页)。 我不知道林白在写出这些真知灼见时是否已意识到她自己的矛盾:她渴望被纳入“男性叙事”的语境,而当她不自觉地努力吸引和诱惑男性的眼光时,她自己却以为是在进行“个人化写作”和为女性争取自己的“主体”,在与男性叙事“竭力对抗”(第303页)。林白的细腻、准确的感觉确实没有欺骗她, 她分析多米的心理说:“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但她并不是“不明白”,而是“不由自主”,“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用男人的话来说:“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第135 页)。在他们那里,这是一种赞扬;而在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更不用说女权主义者了)听来,则含有屈辱的成份。多米在理性上有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当有男人对她说“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时,她反驳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但私下里却又承认“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和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第140 页)这表明她从直觉上已承认了自己从骨子里本能地已屈从于男性眼光的事实。所以就有了小说后半部分有关一次“傻瓜爱情”的恋爱故事。
这“另一个世界”就是以朱凉、梅琚为代表的世世代代被社会遗弃了的女人的世界,即怨女幽魂的世界,也就是《红楼梦》中的绛珠仙子“魂归离恨天”的那个世界。
“傻瓜爱情”是一个中国文学史上谈腻了的题目,已经很难有什么思想上的开拓性。当然,林白的细腻真切的感觉仍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上给人一种“老生常谈”的印象。故事的古老模式是:一个与外界隔离、封闭、纯情的女子,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幻想中的如意郎君。有一天,“那个人”来了。“我”一见钟情,为他奉献了一切。但男人负心,始乱终弃。这一场恋爱,终于轰轰烈烈地收了场,多米满足了自己受虐的欲望,她自愿地在男人面前把自己变成了“物”。“我无穷无尽地爱他……其实我跟他做爱从未达到过高潮,从未有过快感,有时甚至还会有一种生理上的难受。但我想他是男的,男的是一定是要的,我应该作出贡献”(第178页)。 这真是多米身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劣根性的一个总暴露!她即使在自暴自弃中,也仍然是那么贤淑,居然把毫无乐趣的的性交当作自己对爱情应尽的责任!难怪她后来发觉“我想我根本没有爱他,我爱的其实是我自己的爱情”(第175页), “一切就象一场幻觉,连做爱都是,因为这是无法证明的,除非留下孩子”(第183 页)。但她为了“男的”已把腹中的孩子做掉了,她一无所有,她的自尊,她的自傲,她的独立和决断,一切都在刹那间崩溃,一个被遗弃的怨女,什么都不是,只留下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她随后就把这躯壳卖给了一个老头子,为自己在京城谋了一个位置。作者在这里声明:“多米她从此就脱胎换骨了”(第190页),就是说,她成了一个幽灵, “无论她是逆着人群还是擦肩而过,他人的行动总是妨碍不了她。她的身上散发着寂静的气息,她的长发飘扬,翻卷着另一个世界的图案,就像她是一个已经逝去的灵魂”(第190页)。 这“另一个世界”就是以朱凉、梅琚为代表的世世代代被社会遗弃了的女人的世界,即怨女幽魂的世界,也就是《红楼梦》中的绛珠仙子“魂归离恨天”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另一个自我对她说:“你才是我虚构的”,“你的血也是虚构的”(第15页)。
《一个人的战争》中所达到的只是一个被物化和虚化了的人对沉重人世的解脱(而不是解放),是一种麻木和无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愁和伤感。一切“生命涌动”和“跳跃飞翔”在个人化写作中最终归于寂静。个体人格凭天生性灵和才情无法确立自身,只能是半途而废。
这正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最后唯一可能的归宿,它证明,多米的所谓“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面“风月宝鉴”,是用来警醒多米,使她大彻大悟,懂得“做一个虚构的孩子是多么幸福,虚构的孩子就是神的孩子”(第106页)这一永恒的谶语的。 当她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第125页)时,正应了空空道人“因空见色, 由色生情,移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故事(见《红楼梦》第一回)。所谓“一个人的战争”到头来成了一个人消灭自我、将一个人融入太虚的战争。林白曾自豪地说:“个人化与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第303页)。其实, 《一个人的战争》中所达到的只是一个被物化和虚化了的人对沉重人世的解脱(而不是解放),是一种麻木和无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愁和伤感,一切“生命涌动”和“跳跃飞翔”在个人化写作中最终归于寂静。个体人格凭天生性灵和才情无法确立自身,只能是半途而废。建立在“记忆”上的想象力为记忆所累,完不成个人的创造性突围,只能回到更原始、更古老的内心记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兼早衰的特点,即不看现实,一味怀旧,什么都归结到童年时代的本心、真心,哪怕这真心早已不存在,也要借助于“想象力”和白日梦将它唤回来,作为一种“境界”、一种解脱和“解放”,其目标是要否定一切“生命涌动”和“跳跃飞翔”的。而个体人格的失落也就是女性的失落,女性成了“虚构的孩子”,一个抽象概念;在现实中她什么也不是,只是男人的一个“物”(尤物);就连她的自我欣赏,也是从男人那里借来的。她是“无”。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化写作”也就成了消解女性的写作。
(二)
陈染的《私人生活》在很多方面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都有相似之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不与群体相容、落落寡合的女性,都从小缺乏父爱,都有过小时候对自己身体特别敏感和关心的早期经验,都有对自己和对同性肉体的欣赏、崇拜及类似同性恋的心理,也都有独自一人出走并把贞操献给自己所不爱的人的举动;最后,她们都由于自己所爱的人离自己而去而变成了行尸走肉:多米自称“虚构的孩子”,倪拗拗则自称为“零女士”;前者“脱胎换骨”成了幽灵,后者进了精神病院。这两位很有个性的作家当然不是约好了才共同创作同一题材的作品,而是表现了中国女性作家某种文化心理上的雷同性和必然性。这正是我所关注的。
与林白相比,陈染似乎更加喜欢作哲学的沉思。她向往某种男性的方式,希望自己“具备理性的、逻辑的、贴近事物本质的能力”,不仅用皮肤、而且“用脑子”写作(《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7年,附录,第26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倪拗拗的“私人生活”比起多米的“一个人的战争”来,更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战争”。她给自己的胳臂和腿分别取名为“不小姐”和“是小姐”。“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第55页),“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这样很热闹。我们不停地交流思想,诉说着随时随地遇到的问题。我总是有很多问题”(第10页)。倪拗拗天生的任性和偏执是她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性格特点,她甚至有时会感到自己体内“有两个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时支配我”,使我丧失行为能力(第109页,又见第37页)。 但要由此来建立一个成年人的坚强人格,仍然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点上,陈染和林白陷入了同样的误区。
不过,倪拗拗对自己的性格似乎没有多米那样抱有自信,勿宁说,她对自己主动地离群独处有种本真的焦虑,称这种状态为“心理方面的残疾”(第72页),“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是我永久的一种残缺”(第59页)。她看出,“收敛或者放弃自己的个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彻底敞开大门,这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存敞开了方便之门;而反过来,就等于为自己的死亡敞开了大门”(第73页);她看出自己的这种“个人化”实际上是一种幽闭症,但她有时又对此感到自豪,因为她后来发现(大约从书上读到)“孤独其实是一种能力”(第48页)。因此从审美的意义上,她对自己的这种独自一个强撑着对抗世界有一种悲壮感。她以希腊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命:
“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消耗殆尽。但是,西西弗斯却在这种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中发现了意义,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动下散发出庞大的动感的美妙,他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象舞蹈一样优美,他沉醉在这种幸福当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了苦难”(第108页)。
她把西西弗斯承担自己苦难的崇高感,读成了从自己苦难命运中寻出美来自我陶醉的自欺妙法;把一种以清醒的意识来抗拒悲惨的命运并由此构成一种战胜命运的形式的生活态度,歪曲成了道、禅式地适应自己的枷锁、不敢直面苦难而是粉饰苦难的驼鸟策略。中国人只有在以某种方式使自己“感觉不到苦难”时,才能维持自己“健康人格”的完整。
这真是倪拗拗以中国人的眼光对伽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精神的绝妙的误读!她把西西弗斯承担自己苦难的崇高感,读成了从自己苦难命运中寻出美来自我陶醉的自欺妙法;把一种以清醒的意识来抗拒悲惨的命运并由此构成一种战胜命运的形式的生活态度,歪曲成了道、禅式地适应自己的枷锁、不敢直面苦难而是粉饰苦难的驼鸟策略。中国人只有在以某种方式使自己“感觉不到苦难”时,才能维持自己“健康人格”的完整,否则就会“和外部世界一同走向崩溃,她自己也会支离破碎”(第225页)。这的确是“人类所有的特性中的一种”特性, 即缺乏人格的儿童、婴儿的特性,但并非倪拗拗“这个个体”特有的(同上),而是中国人普遍共有的。一个儿童或一个长不大的民族不具有承担苦难的人格,而只具有逃避苦难的“人格”。
这种逃避苦难的人格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把苦难化为“美”。这种美特别在女性身上体现为一种哀艳之美、凄绝之美。倪拗拗与禾寡妇之间的那种不寻常的(近乎同性恋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以此为纽带的。禾是满清望族的后裔,祖上与曹雪芹有过交往,如今家道败落,“但是祖上的遗风依然使得她的骨血里透出一股没落的贵族与书香气息”(第47页)。这种氛围是《私人生活》全书的一个基调。禾寡妇就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梅琚和朱凉,也是一个林黛玉。她代表中国传统(男人眼中的)理想的女性;没有孩子,“孤零零地”与别人没有关系;同时又具有美丽的外表和娴静优雅的悲剧气质,柔弱、绝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女人对倪拗拗乘戾的性格有种无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实和宁静,使她的内心混乱和冲突得到中和。不过,这种哀婉的基调只是一个底色,在这底色上应该还有一些花纹,一些隐隐约约的故事。先要“传情入色”,才能“自色悟空”。这“色”,就是性爱。
倪拗拗对性爱的领悟较迟。由于父亲的暴戾,和后来父母的离异,她从小对男人就没有好感。学校班主任T 先生的故意刁难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对男人的恐惧和厌恶。潜意识中,她常常把父亲和T先生搞混, 并“怀着对T和我父亲代表的男人的满腔仇恨”(第108页)饲机报复。可是,当她在的狂热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于这个她一直仇恨的人时,她发现自己受两个互相矛盾的自我所支配,“她更喜欢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人,……她此时的渴望之情比她以往残存的厌恶更加强烈”,“她的肉体和她的内心相互疏离,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个人,一个完全被魔鬼的快乐所支配的肉体”(第133页)至于对父亲的印象, 她后来也在想象中进行了修饰和改观。她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想成自己的父亲兼情人,“我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 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为致命的残缺”(第152页),“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的父亲般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第154页)。 而在她结识大学同学尹楠之后她又迷恋上了这个具有女性气质的漂亮青年(无独有偶,多米的爱恋对象也有“像女人一样白而细腻”的皮肤和“少女一样”的体香,见《一个人的战争》第179页)。由此可见, 倪拗拗的“色谱”是多么的宽广,她其实爱恋着整个男性世界,只要能体现男性的优点的东西,她全想要。但她只是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作为男性主体的“延伸”(器官?),作为男性思考的补充,而“继续思考”。倪拗拗的“恋父情结”并未因早年对男人的恶劣印象而得到遏止,反而促成她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和“残缺”。
这种对男性世界的“恋父”式的爱背后的底色其实是“恋母”,因为对母亲的依恋,即对儿童时代的回归倾向是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层次的东西,
然而,故事的进一步发展显示出,这种对男性世界的“恋父”式的爱背后的底色其实是“恋母”,因为对母亲的依恋,即对儿童时代的回归倾向是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层次的东西,当尹楠一旦永远离开了倪拗拗时,这一点就突然显露出来了。她看出:“那个人也并不是尹楠,那个大鸟一样翱翔的人,原来是我自己!”“地面上真实的我,手握牵线,系放着天空上一模一样的另一个我……”(第204页), 这个我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纯情的关系,线的那一头可以是尹楠,但也可以是禾寡妇、母亲(禾寡妇也是倪拗拗精神上的母亲, 见第136页)或任何一个可以补充自己的“残缺”的对象。“也许,我还需要一个爱人,一个男人或女人,一个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条狗。”“对于我,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一种奢侈”(第8页)。性,性爱只是空空底色上的一种花色。 悟透了性本身的无谓,便可以在任何其他对象(如禾)那里使自己的残缺得到补偿;而当唯一能使她得到补偿的禾和母亲相继去世是,倪拗拗就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残缺,从此成了“零女士”:“我没有了……我消失了……”(第220页)
正如多米在丧失了一切时便“脱胎换骨”了一样,倪拗拗在成为“零女士”时,在被当作精神病人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当我感到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末日的时候,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第231页)。 这个新故事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第237页), 也就是孤独的人,因为“孤独的人是无耻的”;要与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耻感、与群体的轻松和群体的欢娱唱反调。为此陈染写下了一篇庄严的宣言: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第209页)
鲁迅的狂人在一切人脸上看出“吃人”,当他拒不服从公共舆论时他是看出了世俗的虚伪、堕落和自欺;倪拗拗则坚持自欺,不顾公共舆论而认为她母亲(象征传统文化的纯情)没有死,这与鲁迅的“狂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前者抗拒世俗是为了澄清事实,后者也抗拒世俗,却是为了维护梦想,类似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挺住”。
但庄严的宣言底下的事实是,有勇气说“不”的倪拗拗进了精神医院,因为她固执地认为她母亲没有死。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个比较。鲁迅的狂人在一切人脸上看出“吃人”,当他拒不服从公共舆论时他是看出了世俗的虚伪、堕落和自欺;倪拗拗则坚持自欺,不顾公共舆论而认为她母亲(象征传统文化的纯情)没有死,“他们看到的是伪现实”,“我的母亲没有死去,她在和我们大家开玩笑”,她还在和死去了的母亲每天交谈(第211页)。 这与鲁迅的“狂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狂人”揭穿的正是“良心”(仁义道德)的虚假,倪拗拗坚持的却是“世上有真情”的“真实”;“狂人”反抗的是对现实真相的粉饰,倪拗拗反抗的则是现实真相本身;两人都是“孤独的人”,但层次却大不一样:前者抗拒世俗是为了澄清事实,后者也抗拒世俗,却是为了维护梦想,类似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挺住”。
但母亲毕竟已经去世了,正如禾寡妇也已经死去一样真实。这一真实使倪拗拗这个骨子里一直靠自己的纯情关系而寄生在母亲(和禾)的人格上的“风筝”怀疑起自我的真实性来,同时也怀疑起任何“我”和“你”的关系来:“我依然坚持‘我’和‘你’只有在排除一切目的的关系中,才是真正的关系,多元的世界已经抹杀了纯朴的‘你’和‘我’的定位,‘你’与‘我’已失去了生命的导向。”(第221页)。 “排除一切的关系”的“纯朴的”我你关系,如果有的话,决不是两个独立主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直接等同关系,或“我(或你)是你(或我)的影子”的寄生关系。当人去掉自己的假面、敞开自己的内心时,就既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你”,只有“我们”,“我”和“你”都寄生在“我们”中,都借此感到满足、充实,感到互相坦诚无欺。而现在,“我”被“我们”所抛弃,从此“失去了生命的导向”;“我”在假面后面一无所有,既无道德,也无羞耻,更无所谓“良心”。这样要成为一名“世界公民”的庄严宣言一旦落实下来,便成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告白:“我就是要做一个无耻的人!”(令人想起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的确是“世纪末的流行病”!
正如林白自认为“提前进入了老年期”,陈染笔下的倪拗拗也把自己所患的“流行病”称之为“早衰症”,即“已经失去了畅想未来的热情,除了观察,只剩下回忆占据着我的头脑”(第240页)。回忆, 回归,回复到母亲的子宫;自恋和恋母,以自淫和意淫来解决性问题……这一切,是世纪末文学的通病。倪拗拗既不真正甘心做一个“无耻的人”,又不愿意和大家“搂搂抱抱”,于是,她从心底里升起了一种恶作剧的冲动,给她的精神病医生们写了一封调侃味十足的信(第241—244页),表明自己病已痊愈,恢复了常人,颇近鲁迅《狂人日记》中“已早癒,赴某地候补矣”之口气。
但实际上,倪拗拗越发孤独了,她甚至感到自己的房间都太大,而宁可住在浴室里,睡在浴缸中,她布置这个浴缸,就象布置一口美丽的棺材,“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弄不清里边和外边哪一个是梦”(第245页)。她倒底要干什么呢?
她要写作。
但这种写作,由于只限于“回忆和记载个人的历史”,由于在她的历史中的“生气和鲜活的东西太少”(第231页), 就成了一件使她“身心交瘁”的“没有尽头的枯燥的工作”(第232页)。 她的“私人生活”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同她阳台上的植物盆栽一样:是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呢,还是留在花盆里?
当一个“天使”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时,只能说明她其实并不是什么“天使”,而是一个潜在的魔鬼;而只有当一个人承认并时时意识到这一点时,她(陈染喜欢用“她”来泛指一切男人和女人)才开始形成了自己一贯到底的、敢于自己承担责任的独立人格,她的根才真正扎入了“污泥”中,获得了强健的生命活力。
结论也许已经有了,因为陈染说:“生命像草,需要潮湿,使细胞充满水,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第233页)。 “私人生活”固然纯净、高洁、深情、孤傲,但只会使人陷在自己干燥的回忆中,像花盆里的花那样失去生命的养料。尽管“如果你不经常变成小孩子,你就无法进入天堂”(第102页);然而,“通向地狱的道路, 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第5页)。 当一个“天使”“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时,只能说明她其实并不是什么“天使”,而是一个潜在的魔鬼;而只有当一个人承认并时时意识到这一点时,她(陈染喜欢用“她”来泛指一切男人和女人)才开始形成了自己一贯到底的、敢于自己承担责任的独立人格,她的根才真正扎入了“污泥”中,获得了强健的生命活力。因此,真正的私人生活不是孤芳自赏、逃避和害怕环境的生活,而是“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巴斯卡语)的生活,真正的天堂不是“回头看看往昔”和“变成小孩子”就能进入的,而必须努力去寻求和创造。要经历苦难和血污,带着累累伤痕,步履踉跄地去冒险突围,才能逐渐接近。否则,私人生活要么是对生活的取消和放弃(有“私人”而无“生活”,即自杀),要么是将私人化解为“零”的生活(有“生活”而无“私人”,即醉生梦死)。
这就是陈染,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