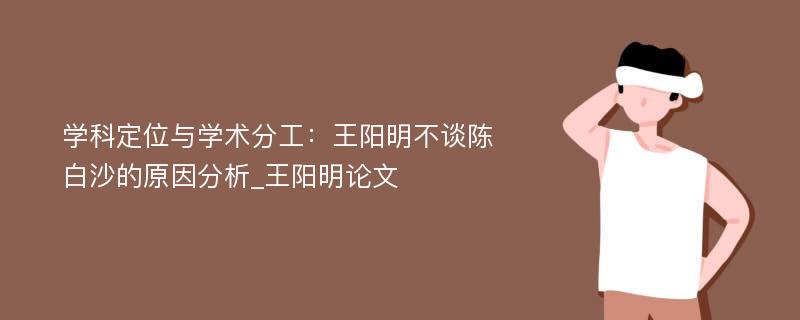
主体面向与学术分野——王阳明不说起陈白沙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探析论文,主体论文,学术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53-06
陈白沙哲学摆脱宋儒繁琐的学风,倡言“自得”的心学,力求简易的“治心”涵养工夫,在明代理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贡献,影响所及,首推王阳明。关于白沙哲学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哲学史上早有结论,如王畿曾指出:“愚谓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①聂豹同样以为:“周程以后,白沙得其精,阳明得其大。”②黄宗羲也持这种观点,他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③在作为正史的《明史·儒林传序》中,虽对陈、王学术持批判态度,但仍然承认:“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④王畿、黄宗羲等人的概括,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定论,即明代心学是以陈白沙为其开端而以王阳明集大成,也就是说,明代心学由白沙开启,由阳明大成,二人一前一后,一“精”一“大”,同属一脉。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陈白沙与王阳明虽同属一脉,但阳明从来不说起白沙,即黄宗羲所言:“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⑤这个问题看似不大,好像还很偶然,但由于此问题涉及到两个重要哲学家的关系,涉及到明代心学的开端和展开的内在机理,所以,此问题实际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姜允明教授(Paul Jiang)说:“罗光、冈田武彦、陈荣捷、王庚武、柳存仁、牟宗三等师辈都曾亲口嘱咐应重视陈王之间关系的研究,陈荣捷还特别提示如果由我撰写一篇文章证明陈王之间并无承传关系,则此明代心学的公案,便可从此盖棺论定,以免枉费未来学者精力。”⑥可见,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一、阳明不说起白沙的已有解释
对于阳明不说起白沙,已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一种解释是,阳明不说白沙,像白沙不说薛瑄一样,其心里自然清楚,但原因我们不能得知。如胡直在书简中就陈述了这样的见解:“夫阳明不语及白沙,亦犹白沙不语及薛敬轩。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辈未臻其地,未可代为之说。”⑦
另一种解释是阳明“狂妄”,根本没有把白沙放入法眼。如顾宪成认为:“阳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数白沙,故平生并无一语及之。至勿忘勿助之辟,乃是平地生波。白沙何尝丢却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从来亦无此等呆议论也。”⑧
当然,绝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阳明与白沙实质上是师承关系,尽管阳明不提白沙之名。据姜允明考证,实质上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白沙之名并非没有出现过,阳明有三次提及白沙的名字。首次提及其友“尝游白沙先生之门”,第二次在诗中提到“白沙诗里莆阳子,仅是相逢逆旅间。”,第三次提到湛母“教其子以显。尝使从白沙之门。”⑨但阳明没有在主要著作中说起白沙。
对阳明与白沙实质上是师承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证据。在阳明《全书》中有一处,被学者们怀疑为,阳明因白沙的思想而引起共鸣。王阳明在断定致知二字是“孔门正法眼藏”的一封书简中指出:“如太阳一出,鬼魅魍魉自无所逃其形矣。尚何疑虑之有?而何异同之足惑乎?所谓此学如立在空中,四面皆无所倚靠,万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来,不容一毫增减。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⑩
“色色信他本来”六字联用,首次在白沙的《与林郡博》书信中,在白沙哲学中,此六字实质表示“自然”和“自得”的内涵,表示万事万物的自然、自由状态,也表明“自得”之后,从内心涌出的对悟道的自觉和自信。而王阳明基于其“致良知”说,用此六字是说明,由于良知的存在,使天地万物的存在得到保证。虽然从二者的学说本身分析,其所指稍有所差异,但也可以说是阳明借用了白沙的说法,二人的字面意思并无不同。
基于以上看法,今学者多认为阳明与白沙实质上是直接继承关系。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著作中根据黄宗羲的理解,即自白沙至阳明的哲学发展脉络,根据阳明言“支离羞作郑康成”与白沙“真儒不是郑康成”的相似表述,认为只有阳明才真正承继了白沙之学,并使之发扬光大,虽然阳明从不说起。姜允明则以王阳明的狱中诗为切入点,说明阳明师承白沙思想是有迹可寻的,并认为自己的研究解答了五百年来的大悬案。他从王阳明如何承受湛甘泉的“云锦裳”而“誓言终不渝”,乃至从后来阳明学中的“知行合一”、“致良知”与“自得之学”中,探寻出白沙与阳明学说内容之相契和一贯之传承,证明王阳明为陈白沙真正之衣钵传人。姜允明认为,从宦的王阳明不便公开提起被攻击为“流禅”的白沙,纯为政治因素,同时为了发扬白沙“自得之学”的精神,亦不必提起。姜认为,一般哲学史上的定论,只承认陈白沙是陆王心学之间的桥梁,但所谓王阳明与湛甘泉“共创圣学”,实际二人同为白沙衣钵传人,如此一来,对陈白沙在宋明心性之学上应重新定位。(11)
与以上看法均不同,熊十力对此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余尝怪阳明平生无一言及白沙。昔人有谓阳明才高,直是目空千古,故于白沙先生不复道及。果如此说,阳明必终其身未脱狂气也。阳明之贤,决不至是。湛甘泉在白沙门下名位最著,阳明与甘泉为至交,而论学则亦与之弗契,足见阳明于白沙必有异处,而终不道及者,正是敬恭老辈,非慢也。其异处安在,余亦欲论之而未暇。”(12)熊十力认为,阳明不语白沙,必是二者学说有异,但不提及白沙,是恭敬长辈,但与湛若水则可以无此禁忌。从整体看,熊十力的这一说法是值得重视的。
以上是关于师承问题的基本观点。当然,由二先生学术是否一致的问题,又自然引申出二先生孰高孰低的问题。对此,王畿虽然主张阳明学源白沙,但白沙承继曾点、邵雍一脉,终是“孔门别派”,与阳明学无法并提:“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从静中养出端倪,犹是康节派头。于先师(阳明)所悟人处,尚隔毫厘。”(13)但也有扬白沙、抑阳明者,如对压抑阳明学倾注热情的唐伯元,为显彰白沙,编集《白沙先生文编》,并加了恰当的注,胡庐山评而断曰:“此书题评,虽扬白沙,其实抑阳明。”(14)
二、“自得之学”的一脉相承
从正统的朱学角度讲,白沙与阳明二人均属于“离经叛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白沙与阳明几无二致。明代以来,对阳明的批评要株连白沙,对白沙的批评也累及阳明,似乎二人形同一人。如清初的儒学家王弘撰说:“大抵阳明之学,真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而其实始于陈白沙,至阳明而盛。白沙元无学,故人惑之者少。阳明事业文章,炫耀一时,故天下靡然从之。”(15)至吕留良,则对二人近乎是恶意谩骂:“夫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16)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仍将陈、王捆于禅学,一视同仁,如程树德认为:“陆、王一派末流如罗念庵、陈白沙辈,几于无语不禅,亦是一病。”(17)
从正统的朱学立场上,将白沙、阳明进行株连式批评均是有道理的。因为白沙、阳明均背离了朱学,使对朱学抱怀疑态度的学人们,相继汇集到他们的周围。从背离的意义上,二人的确可视为同党。因而在朱子学阵营看来,白沙、阳明不仅不是明代思想史的开拓者,而是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颓废,引起了社会体制的瓦解和变动的责任者,所以二人当属“同党”。
二人既然属同党,那为什么王阳明不说起白沙呢?至于说,从宦的王阳明不便公开提起被攻击为“流禅”的白沙,这不符合王阳明的“狂放”的个性。王阳明敢于用性命抗疏,与阉宦为敌,何畏公开承认白沙之影响?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是熊十力的说法,即阳明与白沙“必有异处”,即二人的学术有重大分歧。也就是说,二人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有重大分歧之处。这里似乎产生了矛盾。但从历史和逻辑的线索考察,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存在着一个前后历史发展、个体学术性格上的不同所致。仔细考察白沙与阳明关系的开端和发展过程,实是考察明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
先从其一脉相承之处说起。白沙与阳明并非同一时代的学者,但白沙的“自得之学”依然给阳明极大的启发,这要归因于湛若水与王阳明的交往。由于白沙哲学对湛若水影响至巨,湛是白沙学说的忠实继承者,所以,湛若水完全可视为白沙哲学的代表。白沙与阳明并非同时代,但阳明与湛若水的学术交往可通约为陈、王交往。
阳明在宏治十八年(1505)首次获交湛若水,湛回忆说:“日夕相与论议于京邸,王子于吾言无所不悦。”(18)这里的“王子”是指王阳明。阳明之所以如此欣喜,我们可以分析其原因。正是因结交湛若水,阳明才首度得闻白沙的“自得之学”。陈白沙的“自得之学”是将为学的路径从朱学的外在求理之路,转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的内在路径,其强烈的主体性无疑非常契合陷于“格竹”困境中的王阳明,(19)白沙之学对王阳明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影响。对于这个过程,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中有一基本的说明:“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圣人之道。某幼不学问,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释老,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后兴,晚得友于甘泉子,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之为禅,诚禅也,吾犹未得而见。而况其所志卓尔若此。则如甘泉者,非圣人之徒欤?”(20)这里,阳明毫不隐晦地承认其受惠于甘泉的“自得”,其实这是在承认其受惠于白沙。在阳明“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岌岌乎仆而后兴”之时,白沙的“自得之学”的确好似星星之火,引发了阳明心头的燎原之势。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龙场日夜端居默坐,大悟“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圣人之道。其显性自得之过程,与白沙的求“此心”与“此理”的凑泊吻合的静坐过程极其相似。至此,二人基本是在同一条路径上展开其学术思想的,白沙对阳明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自得之学”强调对主体的肯定和高扬,这是一种“至近”、“道在我”的状态和过程,在白沙是一种费力十年静坐才省悟的结果,但由于有白沙先行的见道经验之借鉴,阳明得道见体的过程要短得多。这是白沙的先行之功对阳明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白沙开启明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白沙与阳明并无二致,完全可以称为一脉相承。
三、分歧与原因
事实上,白沙与阳明的关系是在一条既相同又不同的路径上展开。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均以程朱的“格物致知”之路为外,均以“心”为开启圣途的通道和枢纽。二人的自得之学中,对“心”与“理”的关系具有相同的看法。白沙“心”,是万理完具之心,即“君子一心,万理全备”、“心为主”等,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心即理”或“心外无理”的表述,但实质上包涵了心就是理的看法。(21)在“心”与“理”的关系上,二人是没有差异的。但二人对于如何实现“心即理”却有了重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王、湛对“格物”的理解上。正德十五年(1515),王阳明与湛若水展开“格物”之辩。湛若水主先师之说,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正念头”,同时包含着“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他说:“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即造诣之意,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进,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随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意、身、心一齐俱造,皆一段工夫,更无二事。”(22)“格物云者,体认天理而存之也。”(23)湛将“格物”等同于“随处体认天理”,阳明批评其“是求之以外”,(24)这标志着阳明学与白沙学的分歧开始。黄宗羲站在阳明心学的立场上,对二人的“格物”之辩做了如下总结:“先生(甘泉)与阳明分生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其间为之调人者,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何异?何同?’然先生论格物,条阳明之说四不可,(25)阳明亦言随处体认天理为求之于外。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然天地万物之理,实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若以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之理,求之天地万物以为广大,则先生仍是旧说所拘也。”(26)
黄宗羲从原则上,肯定了阳明学的“致良知”、白沙学的“随处体认天理”二者并无根本矛盾,“良知”即是“天理”,“体认”也就是“致”。当然,黄宗羲主要还是维护了阳明学的观点。但如果对“致良知”、“随处体认天理”仔细体会,二者在细微处,仍然有区别。因为“体认天理”强调“天理”,易理解为轻忽“心”而求之于外,强调“致良知”强调的是“正念头”,易理解为执著于内,二者似乎正是从这一忽之念间产生出绝大的分歧。
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五十岁时,提出“致良知”说,这一年湛若水完成《白沙子古诗教解》,应该说,二人的思想均达到圆融阶段。他们之间书函频繁,私交甚笃。但阳明对白沙学的“随处体认”说批评愈烈。阳明在给邹东郭的信中说:“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夫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27)言辞十分明确,指出白沙学的“随处体认”之说是“捕风捉影”,与圣门的“致良知”之功相差一层,谬之千里。
湛若水应邹东郭之请,有《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之作,(28)阳明读后,大为不满,批评曰:“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功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只要自立门户,外假衙道之名,而内行求胜之实,不顾正学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益悍,党同伐异,覆短争长,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谋,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29)批评言辞极其激烈,出于常情之外。
当然,此批评的关键在于,阳明认为,白沙学的“随处体认”说与其“致良知”说有异,阳明批评白沙学为“自立门户”,其实正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白沙在世之时,已经有人以“自立门户”批评白沙,白沙曾在《复赵提学佥宪》中答复:“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学孔氏者则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所谓“自立门户”者,非此类与?”(30)
这段话是白沙对诋毁他“自立门户,是流于禅学者”所作的回答。在这里,白沙并没有否认,但也没有承认他“自立门户”,他强调的是他实质上是孔子之学。“一者,无欲”的“一”,实是自然的道的“至大”,既然是至大无欲之道,所以,白沙在这里辩解,其无非强调了“一”,这是孔子之学,怎么就成为“自立门户”了呢?
正由于此,黄宗羲提出的“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的问题,有了答案,即:两先生之学虽然相近,但实质不同。白沙学的“随处体认”说被阳明理解为“求之于外”,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甚至被斥为“自立门户”。由于有如此大的成见,阳明在其著作中不说起白沙当可理解。
那么,为什么同为一脉相承的“自得之学”,会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呢?事实上,白沙学的“随处体认”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分歧的根源,并非在于“格物”之辩。问题的实质在于,由于哲学家的主体性差异,或者说,由于不同的关怀面向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二人的学术分野。白沙一生未能通过科举入仕,他一心想报效朝廷却始终得不到仕进的机会,无奈之中选择“退则独善其身”的进路,即通过“静坐”涵养此心,随处体认天理;而阳明却青年入仕,并不以科举为念,其表现为积极进取,追求的是“天地一体”的“良知”。此已决定了二者的不同。其具体表现为:白沙注重心的“虚明静一”,主要追求的是“自然”境界;而阳明虽在仕进与事功方面大展其才,却从不以之为意,其关怀侧重始终定位在如何清学术、正人心上,所以强调“致良知”说。以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白沙、阳明虽同属心学,却自有不同的来路与不同的指向。这是白沙与阳明的根本差异。
由于主体面向的根本差异,也导致了二人学说具有不同的特征。阳明“致良知”说,以“心”内聚为天理本身的直接呈示,将本心“良知”直接等同于天理,其特点是十分简明,如:“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矣。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31)这样,求“理”不必外求,求之于“心”即可,其为学的主体性更为明确,使得为学求理的过程极大地简化和直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阳明学比白沙学更为“简易”。
但阳明之强调“吾心”,极易被理解为“是内而非外”,如湛若水认为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有割裂“理”与“心”的倾向,都有其片面性,都是“支离”,他说:“夫所谓支离者,二之之谓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过犹不及耳。”(32)
事实上,湛若水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阳明学虽简洁明快,但是,在客观上易于造成过分地强调了“吾心之良知”的天理的意义,从而强加给存在世界,从而走向偏失。因为,在将整个世界均置于“吾心”之评判下时,除非对此“心”的底蕴具有极准确的认证和把持,否则,便易流为持心傲物、形检不修的“王学末流”。事实上,王学在阳明之后,实质上陷于纷乱陆离,其弊日显。如王夫之云:“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沈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赴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33)王夫之在这里指出白沙开启了王学的作用,但他着重批评的是王学脱离中道,矫枉过正之弊,而这一弊病并未涉及白沙。
为什么阳明学后来会陷于纷乱陆离之弊,而白沙之学则没有此弊呢?仇兆鳌在《明儒学案》序中有一说明,可以看出陈、王学术及其产生后果之不同,他说:“白沙之学在于收敛近里,一时宗其教者,能淡声华而薄荣利,不失为闇修独行之士。若阳明之门,道广而才高,其流不能无弊。惟道广,则形检不修者,亦得出入于其中,惟才高,则骋其雄辩,足以惊世而惑人。”(3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阳明之学,因为“道广才高”,“形检不修者”得以出入其中,“骋其雄辩”者“惊世惑人”,故流弊日显;而白沙学“收敛近里”,“能淡声华而薄荣利”,培养的多为“闇修独行之士”,造成门限较窄,故流弊亦少。事实上,白沙的门人弟子,多清苦自立,如黄宗羲所言:“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35)但白沙学的这种“清苦自立”、“闇修独行”的特征,也并非没有弊端,如《明史》称“孤行独诣,其传不远”,(36)的确是白沙学派的弊端。
当然,细考白沙学的“随处体认”说,实质上依然是精一之“心”学,其理论实质与阳明“致良知”说的内涵并无绝对冲突,阳明学与白沙学虽表述不同,但大旨无异,属殊途同归。当时王门的学生与湛门的学生也相互出入,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27)
阳明去世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寿命的甘泉,也意识到阳明学与自己殊无二者,赞阳明曰:“予观周孔而降,未有文公先生精神之大者也。”(38)王畿在其友人钱绪山的《行状》中这样叙述道:“时海内主盟道术,惟吾夫子(阳明)与甘泉翁。夫子主良知,甘泉主天理。或问二教同异,君曰:“妆无求二教之同异,求自得焉已矣。言良知则实致其知,言天理则实造其理。所谓自得也,心一也。以其自然之条理而言,谓之天理。良知天理,岂容有二。”(39)王门的聂豹也做如下评说:“王、湛二家之学,各自为宗旨。果能实用其力,各自有得力处,今日天理即良知也,随处体认即致也,顾亦未为甚非。但其实有不同处,亦不可诬也。”(40)可见,王门弟子亦承认二人只是路径不同,其学无异。
属于陈湛学系的许孚远,评论角度与王门虽稍有不同,也对陈、王两家“殊途同归”的意义作了如此论述:“由国初而迄弘正间,人才朴实,风俗淳庞,文章典雅,彬彬称盛,当时学者,稍滞旧闻,不达天德,拘固支离,容或有所不免。故江门、姚江之学,相继而兴,江门以静养为务,姚江以致良知为宗。其要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补偏救弊,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41)
总之,我们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阳明早期在求学造道的过程中,经历了与白沙相似的“不得其方”的困惑,但由于结交了湛若水,领悟到白沙“自得之学”的精要,成就了其学说。这一阶段阳明学与白沙学息息相关,这决定了二人的一脉相承,也决定了白沙学说对明代学术的开创意义。但因主体面向与学术个性的差异,所以,二人虽同属心学路径,但学说面貌最终不同,由此导致阳明不说起白沙。
这一个案其实具有普遍意义。大凡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学术争辩和分歧,如先秦的“古今”、“礼法”之争、“天人”、“名实”之辩,魏晋玄学中的“有”“无”之辩,宋明理学中的朱陆之争、朱陈之争,乃至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理论、经验论之争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往往是哲学家之主体面向的不同,决定了学术的分野。所以,在研究某种哲学思想成因、内涵和特征时,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其主体性,从哲学家主体之独特的经历与感受出发,作出个体式的说明;外在的、宏观的视野仅能解释哲学思想的一般成因,不足以解释其具体的成因,尤其不足以解释其学说之具体的性质与面貌。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个体的人生经历、境遇才是哲学思想学说的直接成因,也是其学说性质与面貌的直接决定者。(42)
注释:
①王畿:《复颜冲宇》,《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道光二年会稽莫晋刻本。
②聂豹:《留别殿学少湖徐公序》,《双江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黄宗羲:《白沙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78页。
④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传》卷二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7222页。
⑤黄宗羲:《白沙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五,第78页。
⑥姜允明:《陈白沙其人其学》,《自序》,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页。
⑦胡直:《论学书》,《江右王门学案七》,《明儒学案》卷二十二,第527页。
⑧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东林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五十八,第1391页。
⑨姜允明:《陈白沙其人其学》,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2页。
⑩王守仁:《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点校本,第185页。
(11)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姜允明:《陈白沙其人其学》,第1-21页。
(12)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13)王畿:《复颜冲宇》,《龙溪集》卷十。
(14)胡直:《困学记》,《江右王门学案七》,《明儒学案》卷二十二,第526页。
(15)王弘撰:《格物》,《山志》卷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页。
(16)吕留良:《答吴晴岩书》,《吕晚村文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丛书》集部第14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8页。
(17)程树德:《论语集释·凡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页。
(18)湛若水:《赠别应元忠吉士叙》,《甘泉文集》卷十七,同治丙寅箿刻本。
(19)关于阳明“格竹”经历,林乐昌教授作了深层阐释:格竹经历对阳明的思想演变并非无意义的“笑谈”,而是一次严肃的精神探索;格竹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并非对朱学的“误解”,而是阳明怀疑乃至扬弃朱学的契机和转折点。(参见林乐昌:《王阳明“格竹”经历的深层阐释》,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53页;刘述先:《论阳明哲学之朱子思想渊源》,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5卷;姜广辉:《阳明哲学的视角》,《哲学研究》1993年第5期。)
(20)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1页。
(21)马振铎:《陈献章的哲学思想》,《论宋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364页。
(22)湛若水:《答阳明》,《甘泉文集》卷七。
(23)湛若水:《论学书》,《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882-883页。
(24)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90页。
(25)湛若水说:“盖兄之格物之说,有不敢信者四。”可简述为:其一,“兄之训格为正,训物为念头之发,则下文诚意之意即念头之发也,正心之正即格也,于文义不亦重复矣乎?”其二,“于上文知止能得为无承,于古本下节以修身说格致为无取。”其三,“兄之格物,训云正念头也,则念头之正否,亦未可据。”其四,“孔子告哀公则曰:‘学、问、思、辨、笃行’,其归于知行并近、同条共贯者也。若如兄之说,徒正念头,则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甘泉集》卷七。)
(26)黄宗羲:《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876页。
(27)王守仁:《寄邹谦之》其一,《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01页。
(28)湛若水:《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甘泉文集》卷十八。
(29)王守仁:《寄邹谦之》其五,《王阳明全集》卷六,第206页。
(30)陈献章:《复赵提学佥宪》,《陈献章集》卷二,第146页。
(31)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5页。
(32)湛若水:《论学书》,《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第882页。
(3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11页。
(34)仇兆鳌:《仇兆鳌序》,《明儒学案》,第5页。
(35)黄宗羲:《白沙学案上》,《明儒学案》卷五,第78页。
(36)张玉书等:《明史·儒林传序》,第7222页。
(37)黄宗羲:《甘泉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第876页。
(38)湛若水:《朱氏修文公事迹叙》,《甘泉集》卷十七。
(39)王畿:《龙溪集》卷二十。
(40)聂豹:《答董明建》,《双江集》卷十一。
(41)许孚远:《答周海门司封谛解》,《敬和堂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公司,1997年版。
(42)参见丁为祥:《明代心学的形成机缘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标签:王阳明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黄宗羲论文; 明儒学案论文; 心学论文; 湛若水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