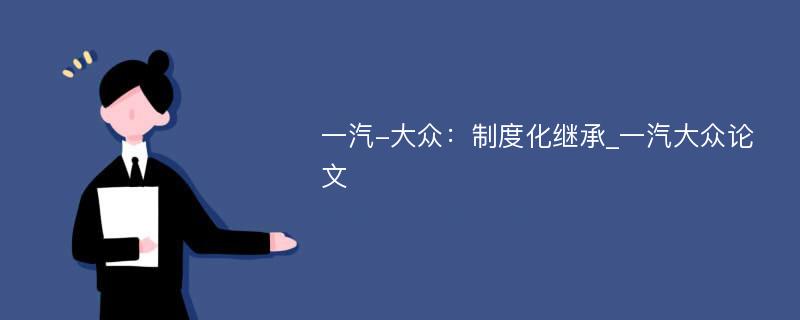
一汽—大众:制度化接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春,寒冷和汽车似乎成了这个城市冬季的标志。
从火车站到一汽-大众公司,一路上高耸的广告牌上要么是波司登等防寒服的广告画,要么是捷达车的巨型照片,像一长串路标,一直把人们引向捷达车的生产地。
在记者眼里,长春空旷的大街上行驶的似乎只有三种车---捷达、奥迪和公共汽车。桑塔纳偶尔驶过,富康车则绝对不见踪影,“这绝对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结果,如果你要探究秘密,只能说是合资的结果,因为长春10年前并不是这样。”一位普通市民如此告诉记者。
总经理的合同
一汽-大众位于长春的西南角,一溜欧式的建筑,在一汽集团的厂区里非常显眼。此前一个月,这里曾发生一场重大变故。
2001年11月7日晚6时30分,在桂林大宇饭店,由中外双方共同出席的一汽-大众董事会宣布了一项4年来最大的决定:中方高层集体换届。此事成为当年4月东风集团高层及神龙富康公司总经理张世端卸任后我国汽车界又一次重大人事变动。
人事变动涉及3人。原总经理陆林奎之职将由一汽集团质保部部长秦焕明接任;原商务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周勇江之职将由原一汽集团北京办事处主任李武接任;原人事副总经理葛凯之职将由一汽动能公司总经理杨道平接任。
在一汽-大众最红火的时候的这次高层大换血曾引起外界种种猜疑,外界曾将此标明为“高层地震”。但是,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厂区,没有任何员工表示出对高层“换血”的诧异。“我们已经习惯了高层换血,因为这是制度。”大门口的一位员工说。
“在一汽-大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总经理助理张银福教授说。据他说,新的领导层在2002年1月1日上任,按照制度,提前一天也不行。而即将卸任的管理层已经出国考察,不在国内。
张银福今年已经57岁,他目睹了一汽-大众从建立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包括领导变迁。“所有领导干部都是要签合同的,合同上标明任期4年,如果需要可以延长。陆林奎总经理已经延长2年,周勇江副总经理已延长1年多。按照制度,到了换届的时候了。在人事方面,最高管理层任期届满就要换。所以,尽管外界认为一汽-大众即将卸任的这一届领导人业绩非常好,但是任期到了,他们必须卸任。这就是合资企业的制度”。张银福很清楚地解释了换届之谜。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则是一汽-大众的中方母公司---一汽集团的战略考虑。整个一汽集团在年富力强的总经理竺延风的领导下也正处于改革中,一汽集团需要一汽-大众的人才,希望一汽-大众成为为一汽集团培养人才的基地。因此,一汽-大众的换届实际上是使经过合资公司“洗礼”的高级管理人员重
新回到一汽集团,推动一汽集团自身的改革。
事实上,在一汽-大众,每一届管理层都没有连任。第一任总经理林敢为干了4年多,第二任总经理陆林奎同样干得出色,但也没有连任。每一次人事变迁的结果,除了引起外界的震动之外,再有就是业绩上升得令人惊讶。“是一汽-大众的管理模式造就了优秀的管理者,换一个管理层,继任者在现有模式下仍会做得很好的。”一汽大众的一位职工如此说。他认为,良好的企业经营模式在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靠企业家个人改造企业,这与现在国内企业经营好坏多数依赖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能力恰恰相反。制度的力量
中国车市寒冷的“冬天”似乎只是在“冻结”二三流厂家,在一汽-大众的宽大厂房里,捷达一辆接一辆下线。“我刚来的时候这里还不大。”一汽-大众公关部部长逯柏林说。逯今年已50岁左右,他所指的脚下这块地原来是一汽集团作为实物投资的厂房,1991年一汽集团与德国大众合资时,这块地拨给了一汽-大众,总占地面积为116万平方米。
逯柏林不停地指着四周,说明各个厂房的用途。他的意思是一汽集团建起这个中国第二大合资轿车厂不容易,从中德谈判成功到厂房建成前后花了4年时间,1995年才竣工。这个时候一汽-大众已经是第5个轿车合资厂,前有上海大众等4家堵截,后有神龙富康追赶,而且,国家给予轿车工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正逐步取消。
“就是这样的环境,一汽-大众仍然在1997年开始翻身,去年捷达、奥迪共卖出去11万多辆。自1997年以来,一汽-大众销售量以每年2万辆的增量增长,2000年增量更为可观,市场占有率在中国轿车市场中为18%。”随后,逯柏林又加重了语气:“这是合资的力量。”
总经理助理张银福教授总结说:“一开始搞合资的时候,一汽-大众就有意识地在组织机构、管理思想上奔着与原来国有企业完全不同的模式来搞,这可能是一汽-大众成功的关键。”
这个管理模式事实上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一开始,很多制度是由德国大众提出来的,但中方人员毕竟是从一汽集团过来的,无法全部接受。最初,每周一次的经管会上,总经理林敢为都会与外方争吵,10年过后,争吵已成过往烟云,德国大众的管理思想多数得到落实。
张银福说:“就拿公司办公室来说,主任就我一个。这其实是沿用德国企业管理的‘一长制’,即一个部门只有一个负责人,不设副手。一汽-大众公司最大的轿车厂总共有4000多人,只有一个厂长、一个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没有副厂长。”
对于中国职业经理人来说,大部分在学习美国企业的管理制度,采用德国式管理方式的并不多。但因为是中德合资企业,一汽-大众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德国企业的烙印。做事认真、有计划性是德国人的特点,于是办事要讲规矩也成为一汽-大众很重要的一种管理模式。
张银福的说法是,“一汽-大众干任何事情都必须按规矩来,不能是领导一句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举了个例子,财务报销只有领导签字并不行。像德国企业一样,一汽-大众实行的是财务预算制度,预算年初定下来后,所有开销必须对号入座,对不上号的不能花,这个制度虽有些麻烦,但一直被一汽-大众沿用。
谁说了算?
一汽-大众的厂区大得记者每次出入都要乘坐车辆,厂区内看不到行人。按照公关部部长逯柏林的说法,假如一个员工老是在厂区的街道上呆着,那多半离被开掉不远了。严格的管理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逯柏林每次开车载着记者出入大门,尽管双方熟识,但他照样下车,主动打开后备箱接受检查。他说:“一汽-大众是制度说了算,而不是个人说了算。”
张银福接受记者采访的这间会议室,正是一汽-大众中德双方领导每周开会的地方。张银福回忆起当初这项制度的实施时仍然津津有味。“一汽-大众中层以下不设副职最初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德方同时提出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一人说了算,而是要集体协商。这样做避免了企业完全决定于一个人手中。”
这一做法打破了国企都习惯老总一人说了算的观念,因此在1991年建立一汽-大众时,按照德方的想法,双方确定了最高组织机构“经管会”,由5个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组成,中方3人,德方2人。同时规定经管会每周开一次总经理办公会。
这其实更揭示了一汽-大众管理层换届并不影响经营的原因。每次无论中方还是德方换届时间都是不同的,中方换届时德方的人还在,将引导中方继任者磨合,反过来也一样。
融合与冲突
德国式的管理和一汽-大众的实际业绩使一汽-大众日益成为一汽集团体制改革的榜样。竺延风就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后,力图在一汽集团也搞业务流程,甚至想搞财务预算制。母公司学习子公司,这一点也让一汽人感到有些意外。
但是,一汽-大众实际上处在一汽集团的环境包围之中,员工大部分来自一汽集团,难免受其影响,而管理制度又多引进德方的管理模式,因此,一汽-大众更多地处于两种经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之中。
张银福教授举了个例子:一汽-大众在技术上实行的是项目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可能是一个部门经理,也可能是一个科长,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业务员。有时候一汽集团开会,一汽-大众只派一个业务员去,因为业务员就是项目负责人,而集团有可能是厂长主持。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的习惯,一汽集团也在感受着合资引起的管理体制的变化。
同时,一汽-大众也未完全摆脱一汽集团的某些影子。从表面上看,在一汽-大众,各级管理层依次称为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用国企的叫法就是科长、处长、总经理。但实际上,记者在一汽-大众听到最多的称呼仍是“工人”、“干部”这些在国企中习惯的称呼。
目前,几乎所有一汽-大众的管理层都是从一汽集团来的,现代化的人事制度还需要摆脱传统的国企制度的影响,而中德文化冲突的烙印还存在。但无论如何,一汽-大众已合资10年,一汽-大众已经在走向国际化管理模式中先走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