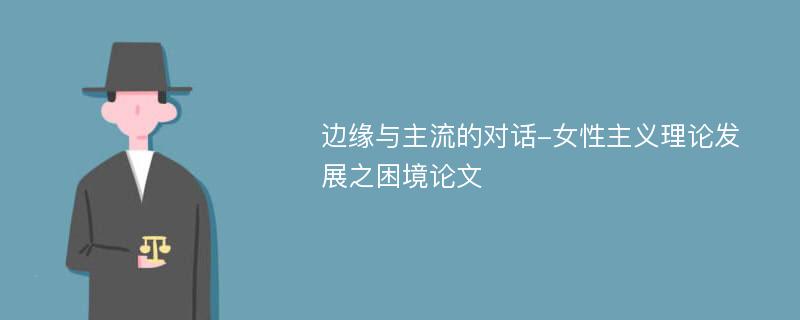
边缘与主流的对话——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之困境
孙子尧,苗 菊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自19世纪以来,女性运动的浪潮广泛波及到社会学、语言文学和翻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深刻的理论思辨。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开始涉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然而,由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二者的结合颇费周折。鉴于女性主义一直徘徊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的边缘处境,女性主义学者多次尝试消除主流学术界对于社会性别视角先入为主的偏见,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往往是在令双方意兴索然的各说各话中不欢而散。追溯女性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旨在分析对话过程中产生的误解和分歧,探索女性主义与主流范式接轨的可能并引发思考,拓展新的研究视域。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视角;国际关系理论;对话与误解
一、引言
对于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尴尬处境,女性主义学者有着切身感受:“如同遇到歌利亚的大卫”①(Zalewski,1993:221),或是徘徊于战场的边缘(Peterson,1992b),或是望洋兴叹(Williams,1993:142)。作为一个“被持续边缘化的分支”(Marchand,1998:200),女性主义就如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她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Tickner,1999)。时至今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女性主义份额仍极其有限(Youngs,2004),影响力也十分微弱(Schmidt,2002)。尽管学术界正逐步接纳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但女性主义方法论却始终未被主流理论所认可(Riffkin-Ronnigan,2013)。数十年间女性主义学者不断尝试融入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但二者的相遇却是“令人尴尬的沉默”和误解(Tickner,1998:205)。
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依据英国学者吉尔·史丁斯(Jill Steans,2003)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主流范式的划定,即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简要回顾这两种范式的理论发展历程,同时也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概述。文章重温了女性主义与主流范式间的经典对话,以揭开女性主义学者心中的疑惑:她们与主流和传统的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彼此的误解。通过解读主流学术界的回应,文章分析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从中扮演的角色,探讨误解和分歧产生的根源,并展望女性主义在未来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接轨的可能。
二、女性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简述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旨在了解战争的起因,避免生灵涂炭的悲剧重演,也就是说,主体(主权国家)的存续和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根本要务。虽然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内部不同范式和方法论之间的竞争持续存在,但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近年来反恐战争的愈演愈烈,现实主义(含结构现实主义,又称为新现实主义)已经牢牢占据了国际政治领域的主导话语地位,被公认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理论(orthodoxy)(Tooze & Murphy,1991;Steans,2003)。另一些学者则坚称,自由主义及其衍生出的新自由主义终将取代悲观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戛然而止,完全超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而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世界经济蓬勃复苏,在这个看似和平的年代,没有大规模迫在眉睫的战争冲突,新自由主义得以顺应时势,迅猛发展(Russett,1993;2013)。但就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而言,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非绝不可调和,二者具有诸多相似的理论假设前提,彼此补益与借鉴,区别仅在于利益的侧重点不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相对利益(relative gain),主要关注国际安全与军事问题,而自由主义更倾向于在政治经济、国际环境和人权等方面建立区域合作机制,以获取绝对利益(absolute gain)。二者皆采用科学实证主义(scientific positivism)的方法论探究世界,寻求客观公允的普世价值 / 逻辑。这一类型的分析方法在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外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亦颇为常见,如和平主义(pacif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等。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安·狄克娜(Ann Tickner)为代表的学者在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third debate)中所倡导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方法论,她们质疑所谓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反对价值中立的理论谬误,采取民族志的分析模式,强调话语建构的历史偶然性、语境特征以及利益负载,后者同时也是批判性研究方法的代表之一(Lapid,1989;Tickner,1997)。
时至今日,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与演变,其统治地位并非无可撼动。随着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批判性理论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纷纷兴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亦应运而生,她们致力于揭露和批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实践中的男性霸权,试图通过言说不同历史与社会背景下的女性事实,打破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的桎梏,为以往性别盲目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新的理论维度;在性别视角的审视之下,女性主义学者提醒人们关注国际政治领域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女性失声和性别歧视问题,以此为前提,方能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家体制和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大多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和探讨知识 / 权力结构表象下的性别机制。具体而言,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由一些列充斥着战争与冲突、对抗与防御、武器与军事策略等的男性话语建构而成。这一代表西方白人男性精英的价值体系维护着一个“扭曲而片面”的世界观,它宣扬男性对权力的掌控与支配,却对女性、老人与儿童等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生存与安全问题视而不见(Youngs,2004:75-87)。
虽然女性主义以性别平等与解放为共同己任,但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女性运动浪潮中,其内部亦滋生出众多理论流派,她们或是建立在不同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基础之上,或是拥有不同的阶级归属和现实诉求,相应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自身特点,不可一概而论(李银河,2005)。例如,早期自由女性主义主张经验研究,用事实数据说话,记录、批评和纠正女性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身份缺失和从属地位。激进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立足于女性立场,抨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父权本质,她们强调知识的情境性(situatedness),主张倾听边缘或亚文化群体的声音,并将女性体验置身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探讨权力关系的压迫机制(胡传荣,2007)。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受历史唯物论、激进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的共同影响,试图冲破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目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忽视,辩证地审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对女性的压迫。批判论女性主义运用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1981;1987)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模式,探索性别身份 / 政治的概念与现实体现并试图通过对历史结构与现有世界秩序的分析和了解,提出可行性的改革方案。后结构女性主义挑战一切关于理性和权威的宏大叙事及其本质主义理论主张,她们关注性别的话语实践、身体操演(performativity)、制度规范和性别意义的不确定性,进而利用多元性别视角和交叉性身份认同瓦解西方二元论传统。后殖民女性主义除了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殖民扩展以外,也针对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诸多质疑,认为她们贬损前殖民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将其形象扭曲或单一化并排逐出女性主义内部的主流话语,实则培育了新型帝国主义霸权(Tickner & Sjoberg,2013)。
在后续的对话中亚当·琼斯(Adam Jones,1996)针对“性别让世界转动” (Gender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的女性主义口号提出了质疑。一方面,琼斯承认了女性主义学者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她们为国际关系研究注入了性别的视角,开拓了女性作为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参与者和研究主体的身份。但琼斯也指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把性别等同于女性或女性权益,容易让人们对性别的理解产生误区。随后琼斯(Jones,1998)转向批评恩罗,认为恩罗对国际关系中性别范畴的定义过于偏激,拒绝考虑男性弱势群体,并排斥男性研究主体。琼斯继而强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是片面的、有选择性的和不完整的,他建议女性主义学者将男性考虑在内并将性别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客观变量来进行探讨(ibid.)。对此女性主义内部一片哗然,指出除去琼斯植根于本质主义传统的性别观念以外,他将性别因素视为国际关系众多变量之一的做法尚有待商榷,因为这很有可能再次将性别置于无人问津的边缘,让人们无法更全面和清晰地看到国际背景下的权力获取、支配与运行法则(Carver,Cohran & Squires,1998)。相比而言,女性主义学者将性别作为核心分析范畴,这有利于提出新的理论假设,获取新的情境知识。传统国际关系学者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便是女性视角,抑或是后结构女性主义提出的女性社会身份认同,皆无法独立于性别关系而存在,与其对应的男性或男性社会身份认同的相关定义与话语建构亦通过女性视角不断展开,从未缺席(ibid.)。以恩罗(Enloe,1990)的理论专著《香蕉、海滩与基地:建立对国际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为例,无论是植物园女工、女性消费者、外交官夫妇、军人的妻子、军营里的妓女,她们的生活体验皆真实地展现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制度作用于性别关系的方方面面。
针对第一类误解,回顾女性主义对性别概念的界定:性别包含了一系列由社会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特征变量,这些变量与传统观念中的本质主义生物两性互为关联,如理性、自由和冒险精神通常被视为男性特征,感性、依赖和软弱则通常被视为女性特征,而前者往往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价值。尽管现实世界中的男女与传统观念所期待的性别特征并不一定吻合,但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区分却持续影响并塑造着人们对于世界和彼此的理解与认识(Carver,2014)。正如德博拉·坦嫩(Deboran Tannen,1991)指出,两性差异比其他的文化差异更为棘手,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诠释和制造着我们的两性不平等关系。虽然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这种人为规定的差异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弊端,但传统国际关系学者却通常将性别视为人际关系研究的范畴而非国际关系所关注的问题。琼·斯科特(Joan Scott,1999)也指出,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内化并加剧了性别歧视与压迫,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合理化,两性关系通常被定义为家庭内务,处于政治的对立面,这也是性别因素被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无视的原因之一。
但面对女性主义理论掀起的批判性反思热潮,主流学界并非不为所动,在为数不多的、试图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学科化的学者中,包括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基欧汉(1989)大致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流派分为了三类:立场论女性主义、后结构女性主义和经验论女性主义并分别定义为好女孩、坏女孩和小女孩。基欧汉对于后结构女性主义(坏女孩)缺乏理论价值以及实质性研究计划的发难首先遭到了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1994)的极力反驳,韦伯认为,他无非是要将女性主义束缚在现有话语体系的安全范围内罢了,因为在基欧汉眼中合理的女性主义仅限那些倾向于采用问题解决模式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流派。例如,立场论女性主义(好女孩)和经验论女性主义(小女孩)践行建立一个相关命题的猜想,将此猜想扩展为符合现有理论的假设,分析该假设的可观察影响,验证这些影响是否与现实世界相符并确保整个过程的透明性与可重复性。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作出回应,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复杂且多元的自身特性,其内部流派亦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诞生,她们之间未必能达成绝对统一的方法论共识,却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反思社会现状,揭露和批判一切所谓理性和中立的知识结构表象,她们深入地剖析两性权力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Pateman,1994)。而后艾米丽·罗森堡(Emily Rosenberg,1997)也补充道,若不假思索地将性别或女性因素加入到现实问题的论述中,并主观臆断性别差异的合理化前提,都只会将理论研究带入死胡同且加剧两性不平等关系。通过在恐怖袭击中出现的女性自杀性人体炸弹以及纵观历史长河中仅有的、极少数的女性政治领袖,抑或在日常生活中女性通常承担了主要的家庭分工,便一概而论地判定女性具有暴力倾向,领导能力欠缺或是比男性更加适合从事家务劳动,诸如此类的草率结论皆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先入为主的性别偏见有关,而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作为学科掌门人(gatekeeper)急于同后结构女性主义划清界限的男性偏执(male paranoia)也是误解产生的源头之一(Weber,1994:337-338)。
三、女性主义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碰撞与分歧
如前文所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张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女性主义则大多运用社会学的、后实证主义的和民族志的分析模式,并将性别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范畴。对此狄克娜(Tickner,1997:613)谈到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结合往往引发三种误解:(1)关于性别定义的误解;(2)关于研究主体的分歧;(3)由于认识论差异而产生的质疑,女性主义是否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范畴。
除以上所提及的,国际关系领域不乏许多其他的女性主义流派,派别之间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但无论如何,正如史丁斯(Steans,2003:435)总结说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1)通过指出国家中心论和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揭露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排她性与偏见;(2)建构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参与者身份;(3)分析性别歧视在日常国际政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体现;(4)赋予女性认识主体(subjects of knowledge)的权力,通过其所处的边缘地位与切身体验,开拓女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维度。
第三类误解与认识论的差异有关。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95)指出,经典现实主义传统的终极目标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客观准确地判断、预测并操控国际局势,最终建立起和平的国际秩序,因此,现实主义理论以逻辑推演的方式深化认识,进而增长理论知识。相比之下女性主义在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孕育成长,她们以民族志式的情境知识为立论基础,同时关注性别话语的建构与操演实践,对于她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流的实证主义逻辑往往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长此以往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与女性主义学者的对话最后往往变成了各说各话,白费口舌。辛西娅·恩罗(Cynthia Enloe,2004:96)曾谈到一个发生在联合国小型武器交易论坛上的典型案例,面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质疑,与会人员的态度几乎一边倒的认为,这里谈论关于战争、生死和武器交易的问题,你们怎能用性别身份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浪费时间。
而最早的期货发源于农产品交易,农民和买粮的商人为防止未来因粮食丰歉而导致粮价涨跌,而预先商定未来的粮价,即通过提前交易锁定价格风险,这就是期货的雏形。此后,市场又发明了标准合约和保证金制度。1848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期货时代的开始。
整个课程的设计是由行业专家对“功能性食品”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选取典型的工作岗位。然后对典型岗位的能力需求进行分析归纳制定相应的课程标准。并依据岗位能力需求设计教学内容。校企共同制订培养计划、教学内容及知识点,确定考核形式,实施“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组织模式。根据不同的教学任务,分别录制相关的微课、Moocs。
第二类误解涉及到主流范式与女性主义的交锋。作为政治学科的类别,国际关系学从创立之初便是自上而下,以国家为中心,旨在维护国家主权、本土安全与宏观经济秩序(胡传荣,1999)。与之相比,女性主义研究本质上属于社会学范畴,其落脚点在于社会人与社会关系,在方法论上体现了自下而上和以人为本的特点,不过女性主义历来呼吁“个人的即是政治的”(Smith,2012),毕竟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全息息相关。对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而言,其研究主体为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的理性、单一制国家,虽然近年来人权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亦被提上日程,但在其他关乎女性与儿童安全的问题上,如国际人口贩卖和性暴力等,主流学术界却并未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更无法像社会团体或非政府组织那样迅速地有所作为(Riffkin-Ronnigan,2013)。而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学者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互助、洲际合作、非国家行为体以及现代公民的自由行动权利;他们大多秉承了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认为现代公民不仅是遍布在社区的普通个体,也是严以律己,积极遵循普世道德标准的理性公民且有能力引导国际关系朝着人类自由生活的方向发展(Linklater,1982)。然而,康德理性主义思想的理论前提及其推崇的道德观念却并不为女性主义所认同,后者批判这一建构在抽象理性话语之上的西方价值观,它将女性彻底排逐在理性范畴之外,实则是白人男性精英的道德典范。总之,不论是以国家为导向的现实主义,还是以理性行为体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这门关乎理性与国家主体的学科似乎从根本上未曾给女性主义提供可以涉足的领域,而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前提等各个方面,女性主义和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皆处于对立或抗衡的状态,女性主义学者建议,若要建立一个重视性别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除非首先扫除传统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Tickner,1997)。
四、边缘与主流对话的延续
虽说女性主义借鉴和发扬了许多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思想,但它自始至终将性别作为核心研究范畴,以揭示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进而尝试重构性别格局乃至消灭性别歧视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隐患。总体而言,依据考克斯(Cox,1987)的理论分类,女性主义作为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分支,与其对应的,是以国际社会现状的合理性为前提,主要任务是针对其运行机制中的功能性缺陷和突发问题进行修缮和引导,并力图维持现有权力关系,巩固现有政治秩序支配地位的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而批判性理论侧重于对历史结构变化过程的反思,关注表象下的内部矛盾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审视现实中存续的常理并针对问题解决理论的预设前提提出质疑,探究理论背后的服务对象与政治诉求,最终提出对现行秩序的可行性替换方案。连考克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批判性理论极其容易被边缘化,因为它不像问题解决理论那样毕恭毕敬地为当权者出谋献策(ibid.)。而实际上女性主义的地位远比考克斯预想的还要低。女性主义学者坚信这个世界是建立在不平等性别制度之上的,她们既不可能对现有的制度作出妥协,更不会与主流认识论握手言和,这也是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对话中面临的最大阻碍。女性主义对后实证观点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它让人们意识到历史进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与其探究所谓既定事实,不如关注权力结构的变化与重建(Peterson,1992a)。因为长久以来“女性的智慧不是被遗忘,就是被更具支配地位的话语所湮没”,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将性别纳入因果关联和量化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众多因素之一,只是为了遮掩女性主义理论所带来的颠覆性力量而已(Tickner,1997:612-620)。
11月10日该两测点所在部位土方仅开挖到基坑深度的中部,且已经停止土方开挖,墙体变形虽然暂时稳定,但是已经产生的变形量过大,主要是施工因素所致。
传统电气设备的控制技术,需要安装相关配套设备以及软件,整个安装过程非常复杂,一方面考验安装人员的技术和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影响着矿山生产的进度。应用PLC控制技术,在安装过程中,只需要根据安装提示进行,过程非常快捷。因为PLC控制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优良性,就能够降低PLC控制技术在运行之中所发生的各种故障,从而尽量降低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便于后期维护和保养。PLC技术无论是在安装上,还是在后期维护上,都具有传统控制技术所不具有的优点和长处。
但与琼斯所见略同的批评不绝于耳:“女性主义似乎变得只关注女性”(Zalewski,2003:291),“表面上看,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内容丰富,呼声颇高,实质上却十分的狭隘”(Carpenter,2002:125)。我们有必要再次回顾一下女性主义的性别定义。斯科特(Scott,1999)指出,“性别”这个术语包含了肉体与自我行为中文化部分的可塑性,以及剩余的无法改变的自然属性的总和。女性主义将女性(或女性社会身份认同)作为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视域下的研究主体,即是意识到男性作为社会资源、经济地位和政治体制受益人的身份直接导致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及其处于权力结构边缘的政治立场。正如特勒尔·卡弗(Terrell Carver,2003:290)谈到国际关系中的男性与男性气质研究(men and masculinity studies)往往是在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框架下,抑或是在对女性主义友好(feminist-friendly)的模式中进行的,性别被打上了女性的烙印,无非是在大多数男性眼中,性别与自己无关,而是女性代名词,为女性所用而已,这种观点无异于再次重申男性标准和菲勒斯中心主义,是真正意义上对女性现实的忽略。
五、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涉足国际关系研究以来,女性主义学者一直将性别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致力于批判和改善长期以来忽略、纵容、助长性别歧视和对女性认识主体实施政治压迫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女性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关系未来的研究方向?女性主义最终能否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接纳?这一切的答案尚待历史和时间的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对女性主义性别视角缺乏关注(Sylvester,1994),尽管存在诸多先入为主的误解,尽管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差异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主流理论话语中显得格格不入,但女性主义学者长久以来积极努力地发起对话,尝试打破僵局并引发理论思辨。
传统国际关系各个理论范式和流派之间的话语权之争不容小觑,女性主义登门入室所引发的猜忌和排斥也就不难理解了。有支持者认为,女性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有的放矢的整合与创新,反对者则嗤之以鼻,“她们是最差劲的读者,其行径与烧杀抢掠的土匪没什么两样,她们把有用的东西抢走,把剩下的东西弄脏砸烂,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Zalewski,2003:293)。女性主义以英美国家为主要根据地,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妇女运动浪潮,亦备受美国或欧洲中心主义的诟病,对于其在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适用性以及理论旅行之后的演变尚有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讨论中。近些年来受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性别与人种、民族、经济、宗教和地缘政治等交叉性社会因素密不可分,为消除普遍主义或简化主义(reductionism)的论调,作者认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务必不断地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将范式内外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不论性别是否转动了世界,女性主义理论亦将一如既往地质疑和颠覆一切被看作理所应当的男性偏执,从社会性别以及知识/权力关系中处于边缘人和她者的视角出发,提醒人们关注那些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注释:
①圣经故事《撒母耳记》里记载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Goliath)勇猛残忍,力大无比,却在与年轻牧羊人大卫(David)的冲突中被石头投中,一举击溃。人们常常用大卫与歌利亚的典故来比喻实力悬殊的竞争,以强调智慧与勇气的重要性。
5.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个基本要求。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基本要求,是对以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科学把握,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Carver, T., M. Cochran & J. Squires. 1998. Gendering Jone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283-298.
[2] Carver, T. 2003. Gender/Feminism/I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 287-302.
[3] Carver, T. 2014.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Research[J].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 113-126.
[4] Cox, R.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J].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126-155.
[5] Cox, R.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6] Carpenter, C. 2002. 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 Contributions of a Nonfeminist Standpoint?[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 153-165.
[7] Enloe, C. 1990.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 Enloe, C. 2004. III ‘Gender’ Is not Enough: the Need for a Feminist Consciousness[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95-97.
[9] Jones, A. 1996. Does ‘Gender’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Feminist Critiqu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 405-429.
[10] Jones, A. 1998. Engendering Debat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 299-303.
[11] Keohane, R. 19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J].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245-253.
[12] Lapid, Y. 1989.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 235-254.
[13] Linklater, A. 1982. 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Macmillan.
[14] Marchand, M. 1998. Different Communities/Different Realities/Different Encounters: A Reply to J. Ann Tickne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199-204.
[15] Morgenthau, H. 1995.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ory[A]. In J.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6] Pateman, C. 1994. The Rights of Man and Early Feminism[J]. Schweizerisches Jahrbuch fur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34): 19-31.
[17] Peterson, V. 1992a. Transgressing Boundaries: Theories of Knowledge,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183-206.
[18] Peterson, V. 1992b. Gendered State: Feminist (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M]. London: Lynne Rienner, Boulder, Colo.
[19] Riffkin-Ronnigan, C. 2013. Theory Talk #54: Ann Tickner on 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Engaging the Mainstream, and (still) Remaining Critical in/of IR[EB/OL]. http://www.theory-talks.org/2013/04/theory-talk-54.html.
[20] Rosenberg, E. 199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 159-160.
[21] Russett, B.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 Russett, B. 2013. Liberalism[A]. In T. Dunne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Scott, J. 1999.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4] Schmidt, B. 2002.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In W.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5] Smith, D. 2012. Poets Beyond the Barricade; Rhetoric, Citizenship, and Dissent After 1960[M]. Portland: Ringgold.
[26] Steans, J. 2003. Engaging from the Margins: Feminist Encounters with the ‘Mainstrea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anl Relations, (3): 428-454.
[27] Sylvester, C. 1994.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Tannen, D. 1991.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M]. London: Virago.
[29] Tickner, J. 1997.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st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ly, (4): 611-632.
[30] Tickner, J. 1998.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 205-210.
[31] Tickner, J. 1999. Why Women Can’t Ru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ccording to Francis Fukuyama[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 3-12.
[32] Tickner, J. & L. Sjoberg. 2013. Feminism[A]. In T. Dunne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Tooze, R. & C. Murphy. 1991. Getting Beyond the ‘Common Sense’ in the IPE Orthodoxy[A]. In R. Tooze et al.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C]. Boulder: Lynne Rienner.
[34] Weber, C. 1994. Good Girls,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 337-349.
[35] Williams, A. 1993.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or Without a Look i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Individual in IR[J]. The Oxfo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142-155.
[36] Youngs, G. 2004.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Or: Why Women and Gender are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e’ Live in[J].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75-87.
[37] Zalewski, M. 1993. Feminist Standpoint Mee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Feminist Version of David and Goliath[J].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2): 221-229.
[38] Zalewski, M. 2003. Women’s Troubles Again in I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 287-302.
[39] 李银河. 2005. 女性主义[M].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40] 胡传荣. 2007.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简析[J]. 国际观察, (1): 9-16.
[41] 胡传荣. 1999. 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J]. 世界经济与政治, (5): 70-75.
Dialogues between Margin and Mainstream: A Feminist Dilemma 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UN Zi-yao & MIAO Ju
Abstract: Feminism has contributed powerfully to sociolog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ny other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trigger profound theoretical speculation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owever, the feminist intervent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1980s was not successful due to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fference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feminism has always been hovering on the margin of the dominant discourse, feminists constantly try to eliminate the prejudice of mainstream academia towards gender perspectives, but the results turn out to be rather disappointing. This paper briefly traces the origin of feminism and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ries to analyse the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vergences in the dialogues to explore the compatibility of feminism and mainstream paradigms, and hopefully to provoke and open up new research horizons.
Key words: feminism; gender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dialogue and misunderstanding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9)2-0133-10
收稿日期:2018-12-04;
修回日期:2019-02-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语术语知识库建设与应用研究”(15ZDB102)
作者简介:孙子尧,博士生,研究方向:性别与国际关系、翻译
苗菊,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应用翻译多学科发展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性别视角论文; 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对话与误解论文;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