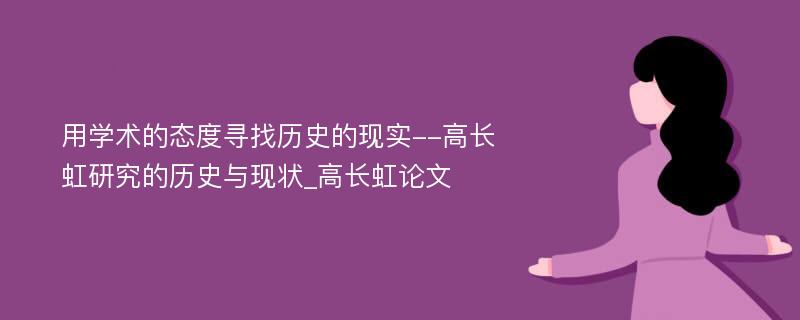
以学术的态度求取历史的真实——高长虹研究的过去与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态度论文,求取论文,学术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 (2000)03—006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曾经力倡狂飙运动的闯将、一个曾与鲁迅并肩战斗共同办刊并被鲁迅称为“奔走最力”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和诗人、“狂飙社”的创始人和旗手——高长虹,在建国后的文学史界却有相当一段时间被冷落和遗忘,历史在此发生了“遮蔽”,而且在一些文学史著中虽偶尔提到高长虹,也只是用三言两语对其人做全面否定,对其创作则完全回避。高长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都曾经是一个被简单化了的反面人物。近年来,高长虹研究开始引入史家视野,历史的“遮蔽”逐步敞开,且研究正在由冷渐热。
一、“高长虹”:“走到学术界”
建国后较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与文学研究,基本把高长虹的文学创作排除在视野之外,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高长虹曾与鲁迅发生过冲突。因而,有的史著介绍早期的文学社团,不得不涉及“狂飙社”时,也都只是简单地对高长虹加以否定。如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和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观点完全一致。认为“高长虹等在上海组织“狂飙社”,倡狂飙运动,以超人自居,攻击鲁迅,宣传尼采思想;但不久即无声息了。”(见王著54页,刘著83页)可见高长虹的主要罪状是“攻击鲁迅”。这样的评价虽极度抽象和概括,却在三言两语间对高长虹做了彻底否定。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这就首先对其作了政治的和阶级的定性,科学地、客观地研究其文学创作自然就是不可能的了。较早对高长虹介绍最详尽也最具权威性的是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 2卷关于《奔月》的一条注释,其中首先称高长虹是“当时一个非常狂妄的青年作家,一个在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并详细介绍了他自1924年认识鲁迅后到与鲁迅冲突的整个过程。对高长虹的评价是“倾向恶劣”、“招摇撞骗”、“卑鄙地诽谤鲁迅”等,其全面否定的态度甚为鲜明。直到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界,高长虹研究实际成了“禁区”, 几乎无人敢于作为个人行为去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直到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鲁迅年谱》,在介绍鲁迅有关高长虹的一些文章和信件时,仍旗帜鲜明地认为高长虹“先是想利用鲁迅抬高自己,后是摘下假面,攻击鲁迅”、“对鲁迅肆意诽谤”等,此外还在多处对高长虹采用非常敌对的话语,如“卑劣行径”、“卑劣手段”、“别有用心”、“暗箭伤人”等。
随着新时期以来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得到全面贯彻,学术研究也越来越走上正轨,高长虹逐步被引入学术视野。《人民日报》1983年9月23 日发表了董大中的一篇短文《勿“以偏概全”》,针对舒展的《为骄傲正名》一文中以高长虹为例谈“骄必败”时说的“高长虹不可一世,一切打倒,鲁迅也不在话下……狂妄了一辈子”等语提出反对意见。起码从两个方面对高长虹进行了大胆地肯定:第一,在现代文学史上,高长虹是起过积极作用的,鲁迅称高长虹是办《莽原》“奔走最力”者,高长虹的“狂飙”宣言,鲁迅曾大段引用,并给予很高评价;第二,高长虹“要做强者,打倒障碍”并不是“打倒一切”,更不反对革命,而且后来又主动投奔延安,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这篇短文可说是公开为高长虹辩解的第一声呼叫,虽然还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的层次,起码具有了学术性态度和追求公正的精神。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也颇具影响力。
1984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发表青苗的《高长虹片断》, 更为明确地指出:“高长虹因为和鲁迅的争吵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但高长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现代文学史上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歪曲的地方很多。”文章认为:“高长虹缺点很多,很突出,但如果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观察他,他也有某些优点。”在此还应特别提到的是陈漱渝以《鲁迅与“狂飙社”》为题发表在1981年第3 期《新文学史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刚刚进入80年代后最全面介绍高长虹史料的一篇文字。文章题目虽如上述,但主要内容是介绍高长虹,包括他所创办的“狂飙社”及其刊物,他的家世及与鲁迅的交往,甚至也介绍了他与许广平通信的情况以及其离开上海后漂泊异国他乡直到1949年去东北的情况等,材料极为翔实,让人最早了解到高长虹较完整的面貌。但仍因其与鲁迅的冲突,被看做“忘恩负义”者。这篇文章也可看做高长虹研究开禁和解冻的第一个信号。
1985年以后,《山西文学》、《晋阳学刊》、《名作欣赏》、《鲁迅研究动态》、《延安文艺研究》、《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中国现代杂文史》等书、报、刊都相继发表关于高长虹的文章,完全突破了高长虹研究的禁区。1989年底,《高长虹文集》三卷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高长虹研究文选》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关于高长虹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热潮。
二、思想倾向与人格评价
刚刚起步的高长虹研究,更多地还是讨论高长虹的思想倾向与人格特征等问题,这当然是还高长虹一个真实面目的很关键的一步。
关于高长虹的总的以及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各家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即认为他“古怪”、“孤僻”、“自负”、喜“独往独来”,甚至显得“狂妄”等。但在关于他的道德品质以及某些具体行为的评价上,又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传统的“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倾向(见高远东《鲁迅研究的传统与当代发展》,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2期),使许多研究者仍然只能从维护鲁迅的立场和好心出发, 坚持把高长虹全盘否定。在高长虹的人格评价上仍延续着前文所引的那些五六十年代的观点;而另一方面,一些曾经和高长虹一起共事或有过接触的革命前辈和老作家等,却发表了许多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戈风、张稼夫、张磐石、胡风、冈夫、张恒寿、青苗、侯唯动、高沐鸿、曾克等。张稼夫认为:“高长虹性情孤僻、愤世嫉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很坚决,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观点”;张磐石说高长虹“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坦率、诚恳、热情,我极喜爱他对旧思想、旧制度、旧社会的反抗精神”;冈夫则说他:“为人直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对待青年热情”;张恒寿还详细回忆了他在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高长虹给予他的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多次帮助,充分肯定了高长虹的基本人格。(以上引文均见《高长虹研究文选》)
关于高长虹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研究者们谈论最多的是他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如何?对高长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认定,最早还应该追溯到鲁迅,而1956年版《鲁迅全集》中《奔月》的那条注释又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后来,有人甚至把高长虹当做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屈的共产党人》(二)中就有这样的话:“当时在太原,无政府主义曾风行一时,其代表人物高长虹等。”甚至认为他们“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进攻。他们大肆宣扬个人的绝对自由,宣传平均主义。”并认为《狂飙》是“一个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刊物”等。这样的观点在其他一些党史资料中也有出现。这样的评价显然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切实际之处,但却一直有人在坚持。另有些研究者则取完全不同的观点,1984年,陶沙便发表《关于〈狂飙〉的质疑与商榷》(《山西党史通讯》第2期),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 不仅从时间上指出上述观点有“人为提前”之处,而且根据许多老同志回忆,《狂飙》“并没有系统的宣传什么无政府主义,也没有打着什么共产主义的招牌”,况且当时无政府主义也不需要共产主义来装门面。张磐石同志则以自己与高长虹的实际接触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认为“说高长虹曾研究和宣传无政府主义,据我所知,这是不确切的”,“最近我们共同回忆了长虹的一生……总结为这样几点:长虹一直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坚韧刻苦,锲而不舍;在政治上他爱国、爱社会主义新事业;为人诚恳、坦率、热情赞助朋友前进……”(见《高长虹研究文选》)董大中似乎对此分析得更为冷静和客观:“在旧中国,许多进步青年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或多或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就高长虹而言,他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说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总觉根据不足。无政府主义是对政府的权威性和私有财产的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一种思潮。高长虹的主导思想与此不同。他要‘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打倒’,所说‘障碍’,都有明确的含义,指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反动势力。”董文中还指出因山西人景梅九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高长虹办《狂飙》曾得到景的支持,这可能是人们把他当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董文中还认为:“称后期的高长虹为革命作家,并不为过,尽管他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不像其他作家那样自觉和严格。”(董文见《文艺报》1990年7月21 日)陈漱渝对高长虹的评价有较普遍的代表性:“高长虹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较早运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进行创作的一位进步作家。”而且“1927年前后,高长虹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论和艺术论的影响下开始了重要的人生转折,最后终于奔向延安、奔向东北解放区。”并“唱出了他的新歌”。(见《高长虹研究文选》第7页)
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高长虹是一个比常人要复杂许多的人物。从他的创作到个人生活,都表现了一种极为复杂而独特的存在,其心理心态比郁达夫、徐志摩等人还要奇妙神秘,是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个体,陈改玲就从其作品入手,破解这个巨大的谜,认为“高长虹是这样一个人:黑夜中的漂泊者、现在行为派以及力的狂放之士。”(《我所理解的高长虹》,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1 月)对于这样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解答。
三、高鲁冲突:是非评价与文化观照
在高长虹研究中,高鲁冲突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这不仅因为高长虹几乎是20年代后期惟一一个敢于向鲁迅“进攻”的青年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曾与鲁迅合作并被鲁迅所器重的干将,尤其是其中还夹杂着与许广平的关系及一些传言。高鲁冲突曾被史家看做鲁迅放弃“进化论”的一个思想的转折点,当然也是高长虹被冷落的根本原因,甚至高的后代也因此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因而,辨明这场冲突的是非,也就是许多研究家们致力要做的。
由于长期的“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基本研究取向,对高鲁冲突之是非的评价当然是绝对一边倒的。直到1995年1月和3月相继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许广平》(张恩和著)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可以爱》(马蹄疾著)等,仍带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甚至前一书简直把高长虹描绘成一个因“醋意大发”、“妒火中烧”而“肆无忌惮地对鲁迅恶语相加”、“为泄私愤而伤害鲁迅和许广平”的小丑。这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高鲁冲突的认识。作为学术性研究,彭定安的《论鲁迅与高长虹》(《晋阳学刊》1986年6 月)最为系统地论证了高长虹“攻击”鲁迅的全过程,结论自然是高长虹一无是处,纯属“狂飙式的‘骚乱’”,鲁迅则由此更显进步和伟大。
那么,对高鲁冲突究竟还有没有做其他解释的可能呢?这一事件的真实状况究竟还有没有事实上的出入呢?以董大中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曾多次撰文,力求摆脱先入之见,更加贴近真实,重现历史真相,这方面的论述和考证最有代表性的是董大中的《论“月亮诗”》(《黄河》1994年2 月)和韩石山的《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山西文学》1993年10月)
董大中《论“月亮诗”》近2万字, 以高长虹的系列诗《给——》第28首(即“月亮诗”)为观照的基点,并以鲁迅的书信、日记等原文为依据,认真考察高鲁冲突的前前后后,包括高长虹与许广平等人交往的始末,从而完全否认“月亮诗”是影射鲁迅与许广平之作。文中首先根据鲁迅致韦素园信的三种分析,认定所谓“月亮诗”是“自比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纯属“传说”和“流言”(此二语均为鲁迅用语),因为这些“传说”至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实“自比”或“他喻”的可靠依据,只有韦素园的“传说”而已。至于人们最敏感的高长虹说他对鲁迅曾做过“生活上”的让步,文中也有详细分析,认为“仅从《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就可以看到,有编《莽原》时每月拿十元八元生活费而形同乞讨,帮助做了一些事反被当做‘多管闲事’等数种。这都应该当做‘生活上’的让步。”那么,高长虹“痛哭流涕”作《给——》的诗究竟是“给”谁的呢?董文又根据高长虹的生活和创作进行分析,认定其“是写给石评梅和别的女士的”。作者还在《文汇读书周报》等刊发表《高长虹的“单相思”》、《这月亮不是那月亮》等文,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论证。而对压稿事件上高长虹的做法,董大中认为是“不能原谅的”,“应当受到谴责”。
韩石山的文章以其作家兼评论家的文笔,对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做了分析,在“思想界权威”问题上,韩石山的文章认为高虹的“不满主要是针对韦素园的”,“即使因此迁怒于被颂扬者,报上开列多人,也不能说是专对着鲁迅一人的。”且很快“也就过去了”。至于“压稿事件”,主要是《莽原》同仁中“山西帮”与“安徽帮”的分歧,高长虹本来是想“恳请鲁迅主持公道”,但鲁迅“不给这个面子”,又作“启事”开高长虹的玩笑,这才“伤了和气”。文中又进一步分析了鲁迅之所以如此的“当时的处境与心境”,这就没有把讨论停留在表面事实的追究上。
另有一些研究者则完全避开关于高鲁冲突之是非的判断,而去深入发掘其中的思想文化意义。阎继经认为:高鲁冲突,本质上不是反鲁迅,而是反“思想权威”;高远东将其概括为“自由与权威的失衡”;钱理群“从高长虹与二周论争中看到的”是“几千年的以长者、尊者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的压力所致”,而且,“事实上,在整个论争过程中,高长虹与周氏兄弟都表现了追求思想自由、个性独立与尊严的高度自觉”,“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一致”;谢泳则借助西方的“代沟”理论,进一步发掘高鲁冲突的思想文化根源,并从中发现了“青年”与“老人”冲突的永恒普遍意义;樊骏从另一个独特的角度,认为高长虹的怪僻和独异,“不能仅仅用他信奉过尼采哲学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上的原因解释,而是生理上的变异和病症”。而且他的“自我”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独立性,也导致了他拒绝新的精神营养,造成终生的悲剧。也许,对高鲁冲突以及高长虹本人的研究,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上着眼,还有着无限开阔的研究前景。(引文均见《高长虹研究文选》)
四、高长虹作品研究:从0起步
高长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十分独异的现象,其特殊的行为本身牵引了研究者的许多注意力,而对其作品的研究却还刚刚处于起步的阶段。近年来,高长虹作品研究已开始走上正轨,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屈毓秀的《高长虹诗文散论》(《晋阳学刊》1986年3 月)可说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高长虹作品论,集中论述了其诗歌和散文。文中认为高长虹的诗是“在黑暗的重重包围中,寻不到光明出路,因而痛苦、彷徨。”诗中常常“感叹宇宙、人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便向梦中寻求,因此,写梦,写梦幻,也成为高长虹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他的“情诗常表现一种变态的恋情,甚至是性的苦闷”;而到了抗战期间,他也“唱起了抗战的歌声”。高长虹的散文,“有革命的呼号、对黑暗势力的抗争、目空一切的自白、孤独生活的哀鸣”,高长虹的散文更是展现了他自己的一个赤裸裸的精神世界。吴福辉的《我读高长虹的小说》(《高长虹研究文选》)首先指出:“最能表明他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作品,恐怕是散文、诗和杂感批评”,而对他的小说的总的评价是:“只要一经接触他那奇僻、激越而思想外溢的文字,就很难忘怀一个刚刚经历‘五四’解放的人磅礴的无所顾忌的气质,和全部复杂的心灵旅程。”高长虹小说“一色是自叙传体”,其中的青年知识者形象“确乎是满身创伤”,而且“人物经常是一个‘飘泊者’”,“他的小说缺乏故事……多的是情绪的空间,思想的质地”。陈改玲的《我所理解的高长虹》则是通过高长虹的做品来观照他的全部内心和精神世界,剖析他的“生命特征”。认为“高长虹是个追求极致生命形态的人,无论是‘黑夜的漂泊者’、‘现在行为派’还是‘力的狂放之士’,都贯串并表现了这种极致。”李文儒从高长虹作品中,重点发现的是他的“超越中国农民文化意识”,认为在高长虹的文论中,“他总是从人类文化、人类情感的角度来发表见解”,“全球意识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所以经常出现在他文论中的基本命题是人、自然、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李文儒还把高长虹与赵树理加以比较,力图解开这同一文化环境(同为山西人)产生的两位差异极大的作家之谜。(《高长虹现象与高长虹之谜》)
董大中的《孤云野鹤之恋》(北岳文艺出版社),是迄今惟一的一部解读高长虹诗歌的专著,此著把高长虹《给——》集中的40首恋爱诗逐一解读,作者精微的解析和准确的阐释使诗中本来处于屏蔽状态或朦胧意境中的那些艺术情景和感情蕴涵,一下子显得豁然开朗。研究者在该著作中非常灵活地使用着一些现代哲学以及文化学眼光,驾御着一些现代主义的批评方法,恰如其分地从原诗作的各个层次与结构中发掘与扩展,既注重了意义的还原,又做了极大的艺术的再创造。对于高长虹能够为更多人接受和了解,起到了桥梁性作用。
研究者们还对高长虹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初步研究。吴福辉指出:“高长虹创造的形象,思想大于性格,无疑是大量融进了作者的面影的。而且,叙述者同作者很难分清。无意中,第三人称的叙事受到限制,作者只会直接地介入,还无从掌握转化和变形的叙述技术。”并论述了高长虹小说的“诗的因素”。陈改玲分析了作者“往往采取尼采式的语录体,或者屈原式的离骚体”,“无节制地使用仅仅是为刺激人的意象”等。董大中的《孤云野鹤之恋》也较多地涉及了高长虹诗的写作技巧,分析也较精到。但是,对高长虹作品的研究毕竟还刚刚起步,高长虹研究中的许多课题还都属空白,尤其是一位较早运用现代技巧与现代手法的作家,人们对其认识和把握还远远不够,高长虹的创作尤其是其艺术技巧方面的研究,亟待有更多的专家去投入和参与。
收稿日期:1999—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