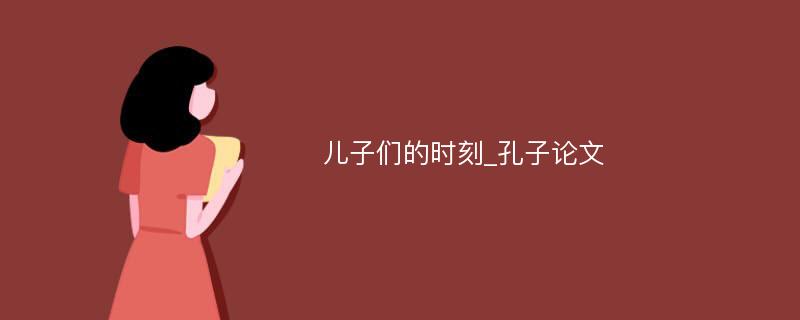
诸子的那些瞬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诸子论文,瞬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轴心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在此书中,他对中国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在这个时代,在地球上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里,人类的文明精神出现了重大突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 这种突破,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人类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宗教开始出现。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超越和突破类型。 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终极关怀的觉醒”?我的理解是: 第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不是零敲碎打,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同时,人类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类和宇宙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认识论出现。 第二,人类开始有了自觉,开始认识自我,认识人我关系——伦理学展开。 第三,人类开始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不仅是一个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世界观觉醒。 第四,人类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开始关注人类的历史,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文化的存在并且有着文化的使命和宿命,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历史观诞生。 其实,在中国,在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过去不到100年,汉武帝时代的一位太史令,一个大学者,一个更大学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对中国的轴心时代作了深刻的总结。他的一篇专题论文《论六家要旨》,总结了轴心时代的六个重要流派的主要思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实,仍然没有囊括尽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比如,兵家,医家……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商鞅、荀子、韩非子……他们鼓吹着这样一些概念: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尚贤、大同、小康…… 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变成了文明的成果积淀下来,这些积淀最后就成了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 司马谈眼中的圣人,不是孔子,而是老子。难怪他的儿子司马迁不仅把老子写成孔子之师,还借孔子之口,称服老子为“龙”。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这样记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以自隐无名为务,这句话有意思。因为,人须已显行迹已有名声,才有隐藏行迹埋没名声这样一层烦恼,否则,历史上漫漫而来又漫漶而去的芸芸众生何其多耶,谁又需要一门专门的学问来泯灭行迹名声。盖老子当是当代大名人,后来孔子不远数百里求教洛邑,也可印证。 作为周朝的档案馆馆长,见周之衰,便黯然离去。离开了周,老子去哪里呢?据说是出关去西域了。出的关据说就是函谷关。 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此时大约在2500多年前,公元前500年左右。既然老子要无名自隐,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著作昭示众生。如果没有此时此地此人,没有这个瞬间,《道德经》一书就没有了。 据说这位关令尹喜也是周之大夫,也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他预先望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经过,便留意观察东来行人,果然迎得老子。尹喜对老子说,你要从人间隐退了。在你远行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吧。 司马迁接着叙道: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去。我们不知他的生,也不知他的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他好像是来自宇宙中某一个星球的高度发达的物种,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东方落脚,然后,又飞升而去。据说,甘肃临洮的“超然台”,就是他的飞升之所。 后来道教的仙人,都是以“飞升”的方式离开这个星球。难道道士们就是一群来自星星的你?老子,他或许还在那个星星上远眺地球。会有一声叹息来自天庭吗?他还记得他留在这个地球上的五千言吗? 它们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智慧渊薮。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动人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身。” 此刻的老子,估计应该在六十岁左右吧,孔子,三十四岁。面对这样一个血气方刚的后生,老子不动声色地点出两个字:藏和愚。 其实,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藏不是没有,不是放弃,是一种含蓄而坚定的保持。“愚”,不是智慧的缺乏,而是智慧的“收藏”,不是智慧的不足,而是智慧的收敛,不是智慧的麻木,而是智慧的蛰伏。 此时的孔子,学问有了,志向有了,眼界胸襟都有了。但是,还缺乏一种东西:弹性的性格。 孔子见老子,是孔子人生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如同滚烫的生铁突然淬火,获得了更多的特质。此后的孔子,阳刚依旧,阔大依旧,但多了一分从容淡定、轻松自在。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歌鼓琴,奏曲未半。 孔子的私学,与弟子切磋琢磨的日常生活,实现了人类生活有可能达到的现实与精神、物理与心灵的圆融。这种圆融,已经超越了物理之真与伦理之善,而达到极致的境界:美。真与善的纯粹之境,就是美。 庄子,毕竟是手眼通天的极致高人,他感受到了孔子生活方式的诗意,他直觉到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人类生活的大美。他用自己的文字,让这个美永恒停留:眼前春水,身后杏花,白云在天,清风在袖,落花依草,弟子围坐——这虚构的一时胜境,从此成为一个民族永恒的灵境,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永在此境,弹琴,歌唱,笑语盈盈。——这其实就是天堂的模样。 ——这是孔子生命的一个瞬间,但是,它成了一个民族的永恒时光:就在这一瞬间,这个民族重新获得了从容与安详,获得了光明与方向。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十五岁的从事“鄙事”以养活自己的少年,何以会立下“志于学”的志向?在他那个阶层的人无论传统还是现实都以出仕从政为人生正途的时代,“志于学”这三个字是何等石破天惊,预示着一个圣人的降临,预示着一个民族的苏醒? 我还常常想一个问题,三十岁的孔子,从社会的最底层已经进入鲁国的上层甚至可以进入太庙,在仕途一派光明的时候,突然放弃这一切,转而创立私学,开启人类教育的新纪元,把文明的星星之火点燃?他领悟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老子走了,孔子来了。 老子因失望而离去,孔子为拯救而到来。 老子是史前史的后记,充满叹息和诅咒。《道德经》作为历史的总结,智慧高超,但冷静到冷酷。孔子是新纪元的序言,充满期待和勉励。《论语》作为新历史的开篇,仁德蔼然,热心到热切。 老子留给我们巨大黝黑的背影,孔子展露给我们宽广明亮的前额。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对于体制来说,老子是身处其中而离开,庄子是身处其外而不入。这两者似同而实异:身处其中而离开者,是出于失望;身处其外而不入者,是出于无望。一个是由有入无,一个是本来即无。盖庄子,较之老子,对体制的道德属性更其绝望,他是避世之士,而老子,其实还只是避人之士——与孔子其实差不多。老子出关,孔子去鲁;老子远去西域而以华夏化胡,孔子欲居九夷而用君子除陋,其实,两人都还是有一番作为之心。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之“出世”,并非印度佛教之“出世”。中国儒道之出世,乃是弃绝体制;印度佛教之出世,乃是跳出轮回。儒道之出世,并非出伦理,只是出体制;不是出人生,恰恰相反,是要一个更好的人生。儒道之出世,不过是拒绝公共生活影响私人生活,不使公共责任影响个人逍遥,不让职事之鞅掌限制个人之自由,更不愿体制之污浊亵渎个人之名节。说到“逍遥”,我们就不能不说庄子了。翻开庄子,第一篇就是《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逍遥游》) 庄子的价值,在于为人类开拓出一个经验之外的世界,并且告诫我们,使我们不自由的,恰恰是我们的经验和知识。 人生最常见的待什么?待知识。待经验。待常识。 但是,庄子偏偏告诉我们,不能依赖知识、经验、常识等等,甚至,你读他的文章,他都暗示你,不要带着成见、经验、知识进来。 试想,带着经验和常识,我们如何能读这样的文字?经验、常识与理性,如何能容忍和接受这样的文字? 庄子的出现,拓展了我们的世界和视界。孔子讲日常伦理,他要我们踏实而真诚地生活。庄子大言,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在教我们超凡绝俗地生活。但庄子最独特的贡献,还是他教会我们如何去死。 庄子《大宗师》有言:“死生,命也。” 我们有这样两个成语,一个叫“视死如归”,一个叫“人生如梦”,这是庄子给我们创造的——庄子说,人只有经过一场大觉才能知道他自身乃是一场大梦。 他岂只是为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他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生死观,让我们含笑面对死亡,让我们在死神面前,保持潇洒的风度和英雄的气概。 它们——一、显示了我们的洞彻人生的智慧;二、体现了我们的笑对死亡的风度。 庄子从更广远的视野,看到了一个人的渺小,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旷世的大哲人。 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人命何等危浅。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里,人生何等渺小。 孔子看到了,一人的生死,牵动着时代和文化。而庄子看到了,一人的生死,无损于宇宙和世界。我们惊觉:此刻的我们,如此执着、孜孜矻矻的我们,我们的形体与角色,是真实的还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的一场梦?当我们醒来,我们大觉之时,会发现我们是什么东西?或者,不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