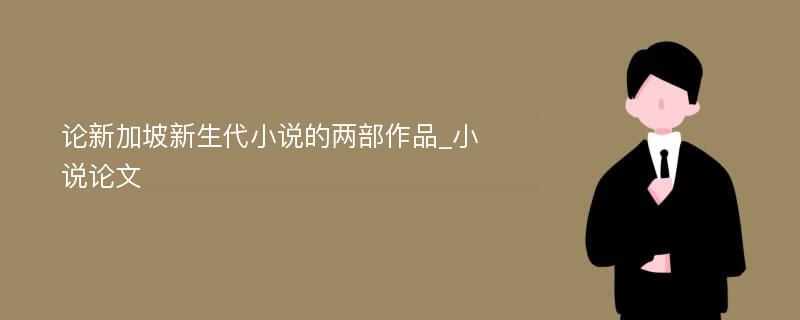
新加坡新生代小说两作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新生代论文,作家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希尼尔小说出发于新加坡乡土而终极于世界性的艺术视野,谢裕民小说对新加坡“城与人”文化主题的新开掘,都反映出其创作多元文学因素的交汇,而尤自觉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新加坡本土文化传统的融合。这些不仅形成了新加坡新生代小说家的特色,也构成了“新加坡小说再出发”的某些内容。
本文所言的新加坡新生代华文作家是指五十、六十年代出生,差不多同新加坡共和国“同步”成长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中许多人作为新加坡的“末代华校生”,承受过语言教育转换过程所造成的精神放逐之痛,更浸润着新加坡自80年代急速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种种变革的思维成果。他们写作的创新意识锐利,在小说文体上尤为活跃。王润华博士曾认为就因为有了这批作家,新加坡的华文小说“才有所突破和创新”,因此称他们的作品代表“新加坡小说的再出发”。[①]
本文就拟通过简析新加坡新生代作家希尼尔、谢裕民的小说创作,来揭示“新加坡小说再出发”的某些内容。
希尼尔小说:出发于新加坡乡土终极于世界性的艺术视野
1957年出生于加冷河畔的希尼尔(原名谢惠平,祖籍广东揭阳),1989年以“一本植根于文化乡土上的诗集”[②]《绑架岁月》引起新加坡文坛的关注。但几乎同时,他的微型小说创作也出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势头。仅1988—1990的三年,他就发表了36篇小说,并获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1992年,他出版了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收作品60篇。之后,他创作锐意不减,又相继发表了《太原王氏后人寻墓札记》、《现象36变》等20余篇小说,其中《认真面具》、《变迁》等以其独特的艺术震撼力被视作新加坡华文小说重要的“新收获”。
希尼尔在回顾他10余年的小说创作经历(他的第1篇小说是1981年9月发表于《南洋商报·文林》的《解雇日》)时说:“在取材上已潜意识地从处理某个特定时空的事物到触及一组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至于手法则从平稳落实转为尖锐荒谬,并带有很大程序的实验色彩。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培育我的乡土上那个特殊的社会。”[②]而当《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出版时,新加坡文坛曾有人感慨万分:“在今日这个西化环境里,本地能有这么一本掷地有声的小书,怎不令热爱自己文化的人士心生喜悦呢?”[③]希尼尔小说创作的意义,就在于他以深沉的人文关怀和大胆的艺术探索显示了在建立融合中国文学传统和新加坡本土文学传统的“双重文学传统”中的新加坡华文小说价值观。
希尼尔深悟新加坡华人在社会急遽都市化中“连根拔起”的遭际所带来的心灵痛苦同急切寻根而不得的精神迷惘,他将这种心灵冲突纠结强化,颇有历史气势地外化为一种“客观投影”,在只尺条幅中酿成一种悲凉厚重的艺术韵味。《南洋SIN氏第四代祖屋出卖草志》通篇以父子对话将历史眷恋同现实“代沟”间的矛盾冲突写得意气酣畅。儿子告诉父亲:“我把屋子给卖了!”,父亲的反应是惊愕:“你们给老家给卖了?”一个把祖屋只是当作能在“炒地产热”中卖个好价钱的“屋子”,一个却视祖屋为魂之所系、根之所在的“老家”,因为那“天下为公”的横匾是孙中山先生亲笔所题,“老祖公当年是同盟会的成员,孙先生几度南来时,就曾在祖屋里与盟友会晤”;后院浮脚楼处的甘蔗园,“救了大伯等一批好汉”,而母亲为保全儿女撒手人世,身后骨灰也撒在了院落里。“这老家累积了我们四代人的回忆与感情,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小说在这里不是将寻根的目光投向遥隔万里的黄河长江,而是引向脚下南洋这片土地、这幢祖屋。作家从乃祖乃夫辈身上寻到的这种生命之根,积淀着新加坡华人魂系“双重家园”的情绪体验和命运思考,有如千丈游丝,一江春水、挥斩不断。《舅公呀呸》描写“华文传统”如何被无知、偏见毁灭。《宝剑生锈》借一把演出《荆轲剌秦王》的宝剑,道出了民族高风亮节的失落,《布拉岗马地》则抒写父亲弥留之际也无法割舍对旧居之地的情感……,这些都是新加坡本土化了的华族情感,使人感到其小说根植于新加坡这片乡土的内涵。
希尼尔的小说从新加坡的乡土出发,其终极视野却是世界性的。他致力于开掘新加坡乡土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层面,具体而微,但关注的目光却始终落在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层面上。《退刀记》、《野宴》、《横田少佐》、《新春抽奖》、《认真面具》、《异质伤口》等小说都涉笔于二次大战日本侵占东南亚时所犯的罪行,而作者不仅将小说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来写,更作为一种人性的记录来描写,他常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观察点的冲突写出了人类忏悔、自责的艰难。《或者龙族》、《捐精》、《生命里难以忍受的重》、《浮城六记》、《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现象36变》等,小说都落笔于80年代新加坡急速进入后现代社会后华人精神的迷惘、抉择的彷徨,由此写出的也是人类共同的困境。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结构的现代都市社会中,生活的急剧变化、纷纭复杂同作家的思维定势经常会发生矛盾,而希尼尔的小说思维却始终敏锐地捕捉住了一个又一个颇有新意的题旨,就在于他的文化心态始终寻求同全人类精神需求的沟通。《横田少佐》(创作于1983年,后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2名)和《认真面具》(创作于1992年,后获华文微型小说国际赛第一奖)中的横田和浩原、其前辈都是日本前期遗将,他们或独身,或随父来新加坡怀古凭吊。两篇小说都在一种历史的沉思中谴责了日本当局对当年侵略行径的掩饰。但比较起来,《认真面目》写得更深沉。小说在述写一位曾从军蹂躏过新加坡土地的日本老人携孙儿浩原“故地”重游,“对曾占领土地的回忆,似乎没有愧疚之意,却仅止于对当年英勇事迹的一种追怀”。小说不仅如《横田少佐》那样:“在回顾历史批判讨伐的同时,更带有智性的分析”[④],而且在剖析老人的心态时,重笔渲染出民俗风情色彩浓郁的种种场景,如老人以朦胧低回的声音讲述“家乡有一座四面卧佛,每当弟子在佛前忏悔后,深夜,佛前总有一张张撕落的面具,随风飘逝”时,那座方圆十里充溢悲情的纪念碑下,冥纸飘落,一老妇人以一种宽怀的姿态侧卧宁夜,以带有此生无法愈合的伤痕的心灵,等待日本军人登陆新加坡后的第50个春祭的到来。这些场景将老人欲忏悔而不能的心境引向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层面,从人类民族性的普遍意义上发出了必须尊重历史、维护正义的呼声。作品没有再如《横田少佐》那样正面着笔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青年在历史认识上的冲突,而是侧面着墨,渲染老人及其孙儿在“认真面具”下无法挣脱的心灵,忧郁注视着对方民族在历史掩饰中尴尬“沉沦”的处境,其开阔的抒写既渗透进乡土的悲凉,也充溢人类的寻求。
王润华先生在为希尔尼小说集作序时,称赞希尔尼“相当创新地在这些小说中试验性地用现代诗的艺术技巧来写作”。这实际上可以构成新加坡华文小说本土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严格意义上的新华文学的新加坡传统,开始建立于7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文学只是其借鉴的一种源流,新华文学更广阔地引进世界各国的文学潮流,在创新中建立自己的传统。希尼尔的近百篇微型小说,正以其文体上的创新锐意参与着新加坡华文传统的构建。
希尔尼在对急速变动中的新加坡社会展开多维度的人生和艺术审视中,拓展小说体式。探索创造了一种现代都市小说体式,这种体式借鉴化用了现代社会中众多的大众传媒,如新闻报道、广告、调查与分析报告、会议档案、抽样调查,乃至请柬、讣告等,让其成为“一组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的浓缩。也许身处高度发达的电脑咨询社会,自己又长期任职于电子部门,希尔尼对一些原先枯燥死板无味的表格、数字有一种特殊的感悟和化用能力。《姻亲关系演变初探——一份新的伦理关系调查与分析报告》以5类伦理关系名称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演变,呈现出现代都市活动对传统伦理关系的离析瓦解。《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以“内部传阅”的会议档案形式,揭示出以同宗同乡联姻的传统华人社团在现代金钱关系面前的消亡,而其荒谬的结果则以戏谑之笔寄托了作者对华人社会的忧虑。《现象36变》以浮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希尼尔常将其笔下的新加坡称为“浮城”,也多少透露出其所感受的“连根被拔起”的精神困境)对居民的群体行为、观念变异等所作的抽样调查,全面揭示出新加坡社会的价值迷失。这些小说,化死板僵化的表格形式为充满谐趣的文学形式,其中纷集的妙思、幽明杂陈的笔调表现出作者想象力的蓬勃和透视力的深邃。他甚至会在《论西汉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及其他》、《报名入学秘诀》这样纯粹抽象思维的题目下写出情趣盎然的生活场景。至于传阅一时的《变迁》更以三则实录的讣告构成了一篇颇具历史震撼力的小说。这三则刘氏三代讣告分别写于1973、1983、1993年。第一则讣告格式用词都是严格规范的华族传统写法,第二则讣告中西文相杂,葬礼也由诵经超度改为基督教式的追思,第三则讣告则是纯然的英语文体了。三则讣告相隔仅20年,实录的形式后面浓缩起所有30岁以上的新加坡华人都曾遭受过的“被连根拔起”的迷惘感、恐惧感和遗弃感。希尼尔小说文体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他对一些普通乃至简单的形式能进行驱遣自如、妙想迭至的组合,并置于东西文化大撞击的背景上,于其中寄托着关注新加坡华人命运的情结,由此提供的智慧世界是开阔明朗的。
希尼尔的小说文体是一种新小说的文体,即如法国新小说派的特征一样,以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写真来表现物的纯客观存在,在纯粹物化的描写中折射出心理真实,传达出某种特殊感受。他之所以选择客观漠然的报表等形式,原因大概也在于此。所以,希尼尔的小说仍是一种写实小说,但把真实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另外一些小说中,他还经常选择某种物件,在冷静的不露声色的描绘中,让这物件一下子呈现出人物特有的感觉、感受、情绪、意识等。例如,《退刀记》写一老妇因为自己的种种幻觉而要退回一把牌子和款式都很流行的小刀,店员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许久,只是发现刀锋上有一排小小横行的字样:“日本制造”。小说于此戛然而止,而这小刀一下子凝聚起全人类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对于侵略者的憎恶。
王润华先生在《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诗歌》一文中谈及“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后现代现象”时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作家“努力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系列企图”,以“希望最终建立一种新传统”。从这样的视野去看待希尼尔的小说,也就不能单纯将其归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事实上,希尼尔在尝试赋予各种已有形式以新的艺术生命,从传统的寓言形式到时下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如1998至1990年间,希尼尔创作了《如何计划一次报复行动》、《园ワ物语》等一系列以动物视点为叙事视角的小说,融入了多视角转换叙事、魔幻现实变形、新闻报道等因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寓言形式。希尼尔在力图不断超越自己,追求着厚重的历史感和精深的艺术境界,如果对他的创作进行同步跟踪研究,也许将会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新加坡新生代创作的希望所在。
谢裕民小说不:对“城与人”文化主题的新开掘
谢裕民比他哥哥希尼尔仅小两岁,但创作格局有异于希尼尔。他18岁时以“依泛伦”的笔名和希尼尔合出诗集《六弦琴之歌》,经历了为赋新词的少年期。之后,他在小说创作上异军突起,3次夺得新加坡小说金狮奖,被称为“新加坡文学从乡土走向一种都市化的新领域”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作家[⑤]。
谢裕民于1989年3月出版了他的第1本小说集《最闷者》,收小说18篇。皆标明为“城市小说,”而杜南发为其作序也以《依泛伦小说和新加坡城市文学》为题。就是说,谢裕民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小说同新加坡这座城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城和人”这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主题在谢裕民笔下有了新的开掘。
《归来去兮》大概是谢裕民第一篇有着“较大题材的架构”的小说,表露了他欲探寻“城市”的文化氛围同人的文化性格之间复杂而又神秘关系的勃勃野心(那时他才20余岁)。小说描写在中国大陆生活了30余年的大哥回到久别的新加坡同父母兄妹重逢,面临“如果一切重来”的人生困惑,但最终又返回了中国大陆,因为“你一旦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你永远是那里的人”。它不同于一般“探亲”小说,思路是对“我”同“大哥”在不同地域中形成的性格差异的点染。小说甚至在哥俩的对话中写到了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等世界各地华人“有明显的差异”的性格。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谢裕民的一个创作视点:他视新加坡为乡土,他要写出新加坡这个“城”中华人性格的演变和再形成。而这才是真正属于新加坡华文文学传统的东西。
谢裕民一次在回答别人采访时说,“有好几本书都以《丑陋的××人》为书名,这××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香港。不见××写成新加坡、太谦虚?不敢?还是……”“人都有丑陋的一面”,“写的人通常‘爱之深、责之切’”。他在《归来去兮》等篇中便自嘲了新加坡人“乘!安分守己,还有,怕输”的性格,而当1994年3月他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世说新语》时,其笔势纵横于新加坡华人的生活面面,针砭世俗,戏谑嘲讽之中已显出某种深刻了。《解放君》开篇的题语:“才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区域性性格”,透露出作者透视“新加坡性格”的历史视角,长期殖民统治的压抑,在新加坡经济急速起飞后以一种历史的反弹力诱发出新加坡华人的种种“劣根性”。《北京唐人街》和《御膳房传人》似乎都是写对“传统”的膜拜,前者中的老板竟然决定在北京建一个“唐人街”,而后者中的“我”于烹调一窍不通,却因被人视为“清朝御膳房主管第五代孙子”而吸引来成批就餐者,后又玩弄“麻将文化餐厅”的新点子……,近于荒诞的情节画出浅薄、盲从的新加坡市民相。在勾勒新加坡的“国民性”时,谢裕民的眼光始终注视着新加坡华人在华洋杂处,急速变动的生活环境中的窘迫不安,探寻形成这种窘迫不安心态的文化根源。《爱拼才会赢》对新加坡华人怕输心理形成的现实压力和历史原因便都有所揭示,这无疑拓展着其透视“新加坡性格”的深度。
谢裕民笔下几乎没有希尼尔小说(如《让我回到老地方》、《布拉岗马地》、《青青厝边》等)中悒悒不乐于都市生活而要返回乡土故居的情结,因此,如果说希尼尔的某些小说还较多拥抱着传统,那么谢裕民的小说则表明着在接受乡土故居的抚慰时又要脱出其束缚,他笔下的人物已经同新加坡这座新兴的都市构成了一种新的关系。《从铜像到狮像》较有历史深度地概括了华人在建设新加坡城过程中的心理历程。从莱佛士铜像所象征的移民开拓精神至鱼尾狮像所意味的现代文明困境,这中间有着道不尽的“迷失”。小说以杂货铺店主黄村南的40年生涯浓缩起新加坡城的历史:日本登陆,和平后的工潮、学潮、新印对抗,新加坡独立,经济起飞。在这中间,黄村南付出得太多,从父亲、弟弟亡于日本飞机的狂轰之下,到17岁的情侣死于50年代的学潮之中,然后母亲、哥哥又殁于60年代可怕的流行病中。当年“热忱、正义、爱国、愤世嫉俗”的他在种种困惑中变得实际。当他原先的情人静恋求他救助仍如当年一样激进的哥哥静萱时,他在心灵矛盾的撞击中终于拒绝了她,他把自己的心牢牢拴在了小小的杂货店上。谢裕民写这篇小说时才23岁,多层时空交织的构思,酣畅而略带凝重的语言,显示出其创作的早慧。但更显示出他创作潜力的是他对于主人公漂流精神历程的把握和开掘。他笔下的人物尽管有着摆脱不尽的迷失,但已不单纯地沉缅于过去,沾恋于乡土,他们务实地把握住了现在,因为他们开始有了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历史。
历史意识的形成,对于力求建立自身传统的海外华文文学来说,无论如何意味着某种成熟。谢裕民的历史视野是在新加坡城的现实变动中探寻新加坡华人性格形成的历史渊源,因而显示出某种冷静。他曾经不无调侃地说:“现在的人做点什么都往历史去考虑,都想把自己写进历史,以致历史成了另一本讽刺时代的小小说”,“许多时候历史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摘一章或半页的过去,使自己站得住脚或令自己获益。是今人与古人互利互惠的一种方式。”[⑥]我相信这种话语中包含着自诫,因为谢裕民的小说让人看到他并非个人化地“玩着”历史。《我们的文学史》被人称为“一篇精彩绝伦的模拟”[⑦],400余字的短小篇幅浓缩起新马华文文学“五十年不变”的历史,浮现出新马文坛使命感、务实精神同保守心态纠结一起的复杂面影。这里,文学史再次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性格史。《孔子之吻》的表层情节是悲叹“五千年文化每年都靠几名可怜的小孩支撑过关”,而作者的深层思考却在五千年文化之根同新加坡社会的“脱节”仍在于新加坡华人的保守心态,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遗嘱》情节后面隐藏着的“为了确定源头”而承受的种种“苦头”,也意在揭示华人社会以家谱体现的历史的脆弱。当外人都羡慕新加坡的治国之道时,谢裕民的小说却透视着其更有历史真实的面影,由此包含的历史预言感无疑具有超越现实的震撼力。
小说形式,技巧的实验,始终是城市文学创作的热点。别人称谢裕民为“江湖气的知识分子”,他也说过“无江湖不卖艺,无卖艺不江湖”[⑧],这反映出谢裕民在寻求新的小说形式、技巧来传达自己的文化感受时,绝不囿于苍白无力的理论。《比赛》这一极短篇便是借世界第一届华文小小说创作大赛第一名作品除五个字的题目《小小说比赛》外,内容一片空白的情节来质疑小小说的定义和形式,表现出谢裕民执意突破小小说这一新文体的规则局限,而不断另辟蹊径的创作姿态。这一方面使谢裕民处于一种自由洒脱的创作心态,甚至是在一种“玩”的心态中孕育蓄积起创新意识和努力;另一方面也使谢裕民的小说文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又无浮躁不定。《世说新语》中的3辑51篇作品,在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了谢裕民探索小说文体的方向:对应于营造新加坡城的文化氛围来寻求文体结构。《世说新语》中每篇作品篇首都有一句孕有张力的话语,同作品正文构成各各相异的对应关系,或戏谑、或启迪,或浓缩、或隐喻,加上配以较为独特的版面设计,使篇首短语成为引导读者去进行某种文化认识的力量,但又只是引导体味,而绝无强制,从而形成一种颇有现代阅读“风味”的作品环境。各篇作品的具体构思则又呈现出谢裕民这样的创作轨迹:“正正经经”地探索某种形式,但一旦成为模式,便又自觉抛弃,探索别样,而整体上的追求似乎有两方面,一是“返朴归真”,一是“越短越过瘾”。谢裕民“写的时候根本不理它属于什么体截”,毫无形式上的霸绊,但却明显合着新加坡城的内在节奏。《心理测验游戏》先在新加坡建国的背景勾勒上,列出10道不乏趣味的文化心理自测题,而读者读到的最后结论却是:“上述10道测验,不管你怎么回答,分数都是:零分。因为当你一开始阅读这么一篇文章时,已经证明你没文化了。”这一结论也许并不会使读者产生受嘲弄之感,反而会刺激某些读者阅读的欲望,因为那10道试题确乎有着实实在在的文化内容,例如问及了对人文地理、环境保护、本土风俗民情,少数民族艺术等态度,所以这“零分”并非测出答卷者的智力和兴趣素质,而隐含着对经济建设中“文化沙漠”现象的焦虑。《量词练习20行》和《论文》也分别在抽象单纯的极短篇框架中,包孕着对现代都市社会中种种文化失落的担忧。这些作品,传统的小说因素几乎淡化到了极点,但却多侧面地呈现出现代都市生活的面影。形式几乎简化到了极限,但内容仍不乏丰富。这种成功,恐怕正来自于作者对于他身处的那座现代都市历史和现实命运的了解和把握。
谢裕民称他的小说为“文字闲聊”,又说“文章贵在体会。不能点,一点就破,破了就成蛇足。”[⑨]其实,谢裕民看似略带玩世不恭的态度中有着认真,而他的创作也有着可辨的理性轨迹,我只是期待着他更大的成熟。
结语
1994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文艺协会联合出版了《新华作家传略》,收入206位华文作家,但其中出生于50年代的,只有27位。有人由此感叹新加坡华文文学有着“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隐忧!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新生代作家无疑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学使命,他们的创作追求直接关系着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转机。
希尼尔,谢裕民的小说创作自然还无法呈现出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全貌,但也确实显露出新生代作家创作出发点的某些层面。他们自觉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新加坡本土文化传统的融合,既适应着商品化的后现代社会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又建立着包容对广大社会阶层人文关怀的艺术视野。他们的创作,已不能单纯归类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而反映出多元文学因素的交汇。他们追随世界文化的潮流,但又自觉不自觉地在某些层面上力图用艺术抵御抗衡、消解分化现代物质社会的压迫。他们生活于双重语言的环境,其语言构形和表现能力都正产生着某些新因素,他们甚至有着强烈的双重乡土观念:新加坡国的现实乡土和华语的精神乡土。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传统有可能建立于他们的努力之中。
注释:
①王润华《门槛上的吸烟者》,载作者论文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1994年10月新加坡版。
②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后记》
③谢清《敲响心中的一面锣——从内容看〈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载《新加坡图书世界》。
④伍木《向历史认罪》,载1994年新加坡版作者论文集《至性的移情》
⑤杜南发《一场浪漫的雨·序〈最闷族〉》,新加坡1989年3月版。
⑥⑦⑧⑨《世说新语附录·江湖气的知识分子》,1994年3月七洋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