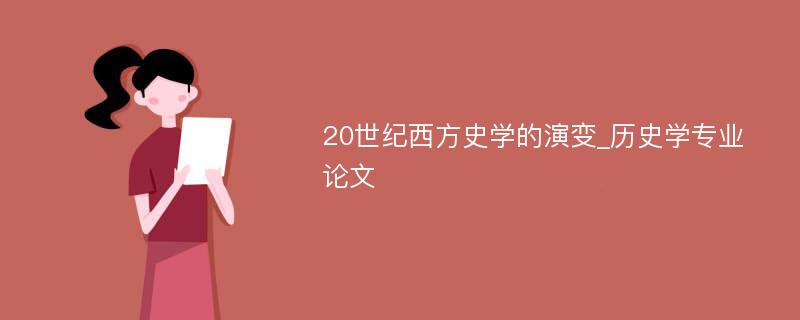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与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历了空前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变化,先后具有三种史学形态,即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的”新史学。这三种史学形态的次第兴起及互相间的争论便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演变的概貌。本文拟对此演变过程及其间三种史学形态的特点略作考察。
一、传统史学
西方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始自19世纪末,此前虽然也出现过杰出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但史学在总体上还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所谓西方传统史学,就是经过长期发展而终于在19世纪末形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西方史学,是西方独立的历史学科的最早形态。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各国为适应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和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的需要,分别建立和加强了档案机构,并将有关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的档案材料向学者们开放,鼓励史学研究。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则为了便于学术交流而纷纷成立历史学协会等学术组织,并创办了学术刊物。至今依然存在的重要史学刊物如法国的《史学评论》便创刊于1876年,英国的《英国史学评论》创刊于1886年,美国的《美国史学评论》创刊于1895年。至于德国,它在史学研究的理论、实践及学术组织等方面则更处于领先地位,早在1859年就创刊了《历史研究》。在大量史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初步规范,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版了两部有关专著,前者是伯因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后者是朗格卢瓦(C.Langlois,1863-1929)和塞诺博斯(C.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研究导论》,它们分别论述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问题。与此同时,在大学里设立了独立的历史系,建立了培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制度,历史学开始有计划地培养训练自己的专业人材,不再像以前那样仅是政客或其他上层人物偶尔为之的副业。至此,西方史学在学术组织、专业人材训练、学术阵地(刊物)和理论方法的规范等方面已臻成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正是如此形成的西方史学的第一个完整形态,即传统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占据了西方史坛的统治地位。
那么传统史学的具体特征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三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就内容而言,传统史学的特征是其严重的狭隘性,即它仅局限于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其代表性刊物《英国史学评论》在创刊号前言中便明确说道:“国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因为国家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通常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①a]这与久远的史学传统恰是一脉相承,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史籍都是记录王朝更迭和帝王将相等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的。尽管其间有些史家史著,如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及其著作突破了这一传统束缚,主张并实践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演变过程纳入历史记述,使历史不仅仅是单纯政治的、上层的,还包括普通人在生产、交换以及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经历,但这仅是历史学科中的涓涓细流,从未在总体上动摇过精英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传统史学内容上述特征之所以形成,直接原因还在于西方的社会与学术背景。欧美列强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历经了接连不断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拿破仑战争、英国的议会改革、意大利的统一、德意志的统一、美国在西半球和太平洋上的扩张及其门罗主义的出笼和演变,以及各国间频繁的摩擦与争斗,等等。在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中,历史学家陷入党争、政争和国际争端,并以历史研究与写作为其政治目的和信仰服务乃是普遍现象。因此,西方政治的需要和史学家响应这种需要所作出的抉择,都导致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学的畅行无阻。
在学术界内部,学术研究的体制也对史学内容起了局限作用。西方多数国家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高等院校,而高校是由按学科划分的各系组成的,每个文科系(即每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都要求在有关人的研究中分得一块特定领地,这使历史学必须同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分割对于人及社会的研究,因此,通过档案资料对以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进行研究便成了史学的中心内容。
20世纪前期,虽然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乃至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已有所发展,虽然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作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学,并给它带来冲击,但它们在总体上仍不足以动摇传统史学的主导地位。直至50年代末期,西方史学的主要权威刊物如《美国史学评论》、《英国史学评论》和法国的《史学评论》仍然充满了对各种政治性历史事件所做的繁琐考证和不厌其详的描述。
传统史学的方法是随着西方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而德意志则是其生长成熟的故乡。
早在19世纪初叶,普鲁士历史学家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便在罗马史研究中发现不少前人的史著有错误,其原因是疏于对原始资料的钻研。因此他主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批判古籍,重视原始的史料证据[①b]。后来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继承发展了尼波尔的精神和方法,他为钻研原始档案资料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而不遗余力地查访德意志及欧洲各地的公私档案馆,搜集、考证资料,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地“据实记事”。兰克不仅写出大量史料翔实可靠的历史著作,而且形成一套考证史料的办法;同时他又在长期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中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于是兰克及其门徒形成了兰克学派,其影响不仅遍及德意志,而且通过外籍学生深入到英国、法国和美国。
兰克的史学方法是西方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由此产生的传统史学也一直奉兰克的方法为圭臬。如传统史学的代表性刊物法国的《史学评论》在其创刊号前言中说道:本刊只接受以“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稿件,作者应采取“严格的科学表达方法,每个论断都须有证据、有史料出处和引语”,同时本刊文章在修辞上“要保持为学者和读者所珍爱的文学性”[②b]。质言之,就是要注意考证史料,力求应用原始资料,在表述上要严谨,杜绝不实的虚饰,同时又讲究语言的艺术性以吸引读者。这些方法论要义自然都是兰克曾经主张和实践过的。
除了上述在搜集选择资料和表述上的主张之外,传统史学在如何认识史料并由此形成对历史的解释这个环节上也有自己明确的主张,那就是依靠“直觉”。凭直觉来理解史料并形成对于前人经历的认识其实是最古老的方法,自有史著以来史家们无不应用这种方法,只是他们多不自觉罢了。传统史学家们不同于前人之处是他们自觉地应用直觉并为此提出了一套说法。最享盛名的德国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便明确指出,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依靠什么理论,而依靠直觉。杰出史学家的“标志”便是善于作“直觉判断”,而这种能力或方法的取得不能靠学校里的学习或训练,只能靠“天赋”、“实践”和“自修”。学校应当传授相关的语言知识和相关时代与地区的法制变迁的知识,这是史学家和历史研究的必要准备,除此之外就全靠史学家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悟性了[①c]。
传统史学在认识论上的一大特征是坚信史学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证与鉴别便可再现历史的真实。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的观点便是典型的例证。他认为,鉴于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因此,“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另一特征是相信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与写作中可以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做到绝对客观。阿克顿在主持编纂《剑桥近代史》时曾要求撰稿者做到绝对的“公正无私”,要求他们笔下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都同样满意”[②c]。
上述传统史学认识论源于19世纪西方由科学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乐观情绪,因此多数史学家在追寻客观历史真实的同时坚信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属于科学。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认为,史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不简单的科学”,因为它所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的演变,而这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历史研究难免会有困难和失败,但我们坚信“对事实真相的真诚探索总会有所回报”。英国著名史学家柏里(John BagnellBurry,1861-1927)则专以“历史科学”为题来发表他作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他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产生希罗多德和历史学之后,到19世纪,人类的自觉意识产生了另一次飞跃,即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不断向上“发展”的过程,这个观念再造了历史学,使它与“客观地研究宇宙事实的各种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③c]。
综上所述,传统史学破天荒头一次建立了一套史学所独有的理论和方法规范,这是不可磨灭的成就。它承认历史真实的客观存在及认为史学属于科学等观点也是十分可贵的。但传统史学在内容上的狭隘,在方法上的自我封闭,以及在认识论上对于客观历史真实的特殊性的欠缺考虑和对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忽视,这些都是它的致命弱点,以致使它很快便遭遇了接连不断的挑战和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交战国之间曾展开激烈的宣传战,各自为自己的战争政策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普遍陷入了沙文主义泥潭,他们互相争吵,为本国政府辩解,甚至使民族国家政治史的研究沦为推动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工具。自视客观、清高的学者们竟成了战争和破坏的支持者与辩护士,这自然给传统史学的社会声誉带来巨大损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各国史学家在战争前后以历史公正为口实展开的互相攻讦充分说明,那种认为史学研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从而让所有人都接受其结论的想法不过是幻想而已。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史学实践证明,史学家掌握的档案资料愈多,研究愈发展,则史学中存疑和争论的问题也愈多,阿克顿所谓的“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不仅没有走近,相反倒似乎越来越遥远。这一切都说明传统史学的认识论是过于乐观了,是不切实际的。
早在一战之前,便出现了批判科学史学的思潮,其代表者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m Dilhey,1833-1911)、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在意大利有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英国有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Trevelyan,1876-1962)和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等。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反对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反对客观主义,认为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完全“排除自我”。有的甚至认为,“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①d]。这种思潮反对19世纪遗留下来的将史学机械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残余,指出历史学家主观因素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及史学研究成果具有相对性,这些都是有道理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述狄尔泰们的思潮在西方史学界流行日甚,从而在理论上给传统史学认识论带来日益严重的冲击。但是必须指出,狄尔泰等人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加以绝对化,妄论自然科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而史学则仅限于“研究个别事实”[②d],甚至否认历史中也有共同因素和因果关系,这些都是错误的,也没有为新史学的主流所接受。
传统史学在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不断遭到挑战。其他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迅速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揭示了人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的物质生活及其再生产(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狭隘的精英政治史的怀疑。德国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836)于1917年发表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于1934年开始出版的12卷《历史研究》,则是在实践上对传统民族国家政治史的重大突破,因为两者都以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为内容,具有很大影响。史学内容的扩大自然要求拓展资料的范围,使得原来档案资料考证的一套方法不敷应用。同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方法的比照,也使传统的直观方法显得十分粗陋,因此产生了借鉴其他学科来革新史学方法的要求。
总之,传统史学在认识论、内容和方法论等方面都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从而逐渐走向衰落。继之兴起的便是新史学。
二、新史学
西方新史学由萌芽到取代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约始自20世纪第2个10年,至60年代方才完成。这半个世纪既是传统史学统治西方史坛的时期,又是它由盛转衰而由新史学逐渐取而代之的时期。
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同是新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西方新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然而,作为一种要求革新的史学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史学在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征。
新史学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的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狭隘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
早在1911年,美国杰出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就在题为《新史学》的著作中针对传统史学的狭隘性指出,国家“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①e]。
1929年,新型史学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创刊,宣告了西方新史学的典型代表年鉴学派的诞生。其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认为,新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②e]。他中肯而尖锐地反对传统政治史肤浅的精英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伟大群众运动”)的真正深刻的原因不在于“大人物”的性格或“外交对抗中的矛盾活动”,而“存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知识因素、宗教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等之中”[③e]。
到年鉴派第二代,其领导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al,1902-1985)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在理论上给传统史学的狭隘肤浅性另一沉重打击。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史学的内容即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仅是“短促的时间”内的事情,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深刻潜在因素;而长时段理论主张史学应当着重考察那些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结构”和“势态”,也就是要考察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时间的历史演变[①f]。这种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对于革新史学内容自然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本身的实践,新史学在研究内容方面大体形成了两个重点。第一,强调研究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人文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生态环境、技术水平的影响、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方式等等。第二,强调研究范围广泛的社会史,如有产财产、权力、地位分配制度的研究,有关家庭、学校、警察等社会教育和控制体制的研究,有关公司、工会等工作机构的研究,有关市政会议、都市政治机构等地方管理体制的研究,有关文化娱乐机构的研究,以及人口的流动、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等都是新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②f]。此外,思想—文化史也是新史学研究的一项内容,但与前两项相比,它不占主要地位。大众文化与心态史研究的真正兴起始于60年代,进入70年代之后才得到大发展,但那是西方史学又一次新转折的内容,因此将在下文讨论。
新史学在内容上的扩展是同它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革新同步进行的,没有新方法和新认识论的协调与促进,史学内容的扩展是不可能的。这里为了表述的方便才将三者拆开,分别加以论述。
新史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是借鉴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这是史学与其他学科双方互动的结果。
传统史学在学术界获得独立地位后,满足于自己的一套考证史料的方法。因此固步自封,毫不关心其他学科的情况。其他多数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也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无暇顾及历史和史学。如人类学只关心它所考察的部落或氏族的现实状况而不考虑其历史渊源,社会学多数只作静止的研究,实验心理学则研究现代人的可观察到的行为和反应。这样,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隔绝乃是必然的。
然而时间和历史对于任何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它们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有时间性和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人类过去的丰富经历也可以用来检验和充实各学科的理论和资料。因此少数学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十分重视历史问题的研究。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奥地利籍的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便十分注意探索历史问题,将本专业知识与史学结合起来。他们所做的跨学科历史研究虽然没有得到同时代学术同仁的足够重视,但毕竟是开拓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影响日渐扩大,到50年代之后,韦伯著作纷纷译成英文出版,受到英美史学界的欢迎;弗洛伊德也被尊为新崛起的心理史学的开山鼻祖。
专业史学家一方,大约从1930年左右也开始认识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从事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史学家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在1928年的著作中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不具备社会学和行为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作出合理的解释”。此外,新史学家还应了解某些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因为“不熟知人类行为的腺质基础就不能够理解和说明人的行动。”[①g]
年鉴学派从其诞生之日始就积极从事跨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创建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后来此第六部在年鉴派第二代首脑布罗代尔领导下进一步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汇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方面人材,开展以史学为带头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正是由于年鉴派对跨学科史学研究做了杰出的组织工作,他们才写出了大量著名的著作,乃至成为西方新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最有影响的群体。
利用电脑和数学方法处理可计量的历史资料从而窥见往昔社会的状况,这自然是史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表现。计量方法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主要是人口史,其次是经济史和新政治史。此外它还应用于范围广泛的社会史。
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计量方法的应用导致了史学著作形式的改变。传统史学是凭借直觉以时间为轴线对往昔政治事件的叙述,是叙述性的事件史;新史学则主要凭借其他学科的理论对往昔社会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计量方法加以分析解答,是分析性的问题史。虽然新史学中不乏叙述性的著作,但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却都是分析性的,且新史学家们有一种成见,似乎那些可以提供新知识的学术研究著作必是分析性的,而叙述性著作则或是课本或是为取得经济效益而写作的通俗性著作。
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幼稚的客观主义,公开承认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无法做到完全超脱和中立,而必然受到某些既有见解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其实历史事实(或证据)并不像传统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会自己出来“说话”,它们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选择才能够同读者见面,得到说话的机会。正如年鉴派的布洛赫所说,任何文献或资料“只有在适当地被询问时,才开口说话”[②g]。而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则将人类以往的经历分成普通“关于过去的事实”和“历史事实”,前者可以是过去发生的任何事,后者则是被历史学家从前者中间选择出来作为其论题资料的事实。历史学家取舍“历史事实”当然不能凭空任意而为,而是凭借某种先入的观念和标准,这就是其主观因素。卡尔认为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大体是:他先有一个“临时性解释”,依照此解释对材料做出“临时性选择”,让这两者交互作用,从中加以调整,以使事实的选择愈来愈客观,使解释愈来愈真实。因此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①h]
新史学家们反对传统史学天真僵化的客观主义,承认并重视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实际上是看到了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相对性,这是新史学比传统史学更为成熟的表现。然而他们在此过程中对于历史发展具有不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问题却缄口不谈。比如卡尔虽然并不笼统地否认历史中的客观性,但认为它“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能是相互关系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历史事实”既然是经过历史学家选择的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②h]。这固然有正确的一面,因为这种经过选择的历史事实必然反映史学家的判断标准等主观因素,其客观性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卡尔却忽略了历史事实还有其本身固有的客观性,尽管它不易被人捕捉到,其存在仍然不可否定,因为前人的行为(历史事实)是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只有大体符合其固有本质时,我们才能说他是大体正确或客观的;否则他就是歪曲了历史。新史学家们由于回避历史事实本身固有的客观性,便为唯心主义的史学相对主义的侵入留下了缺口。
新史学由于在认识论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扬弃,因而不再追求什么“终极的”或“完善的”历史学。但新史学的主流却与其史学前辈一样相信史学是一种科学。不过,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史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改造了人们科学观念之后的科学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布洛赫说:“一个学科,尽管不强调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不变的重复法则,仍可宣称具有科学的尊荣。”[③h]他所指的享有科学尊荣的学科自然就是以年鉴派为典型的新史学。
前述的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相当系统地批评了将史学排斥在科学之外的种种谬论,最后总结道:我不认为“使历史学家跟地质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就一定比使地质学家跟物理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要深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虽然“在他们的假定和方法的细节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在“寻求”对于事物的“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历史学家,正如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个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一种动物”[①i]。
就总体而论,新史学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辅以计算机和数学为手段,将人类的过去与现实及未来相联系,对历史做深层次的有时是结构性的考察,这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公认的社会科学学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新史学自认为是科学应是无可非议的。
综上所述,新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面革新了史学面貌,将西方史学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新史学在以下四个方面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第一,它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扩大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第二,摆脱了精英史观的束缚,将焦点移向平民百姓,重视研究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历史经历;第三,打破传统民族国家史的局限,扩大空间视野,对人类各种不同文化做跨越国家界线的历史考察,或在一国之内探究某个问题的历史发展;第四,由于史学新内容的需要和跨学科方法提供的可能,史料来源也空前扩大了,除了传统历史档案之外,教堂关于婚丧洗礼的记录、绘画艺术品和家具等其他人造物,以及各种口述和调查材料等等都列入了史料范围。同时,计量史学家还以电脑和数量分析的方法开辟了对于某些传统档案资料的新应用。由于新史学如此全面地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它便提高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为作为人类以往经历的历史本来就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并非如传统史学所设想的那样简单狭隘。
其次,新史学提高了史学阐释的精确性。一方面,计量方法以明确的数量化概念代替了某些传统的文字描述,消除了后者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史学界由于对某些常用概念(如“封建主义”、“中产阶级”、“官僚政治”等等)理解的不同曾发生过一些无谓的争论,新史学则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帮助解决了这些名词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从而解决或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也提高了阐释的准确性[②i]。
再次,新史学大大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刻化。其主要表现是注意挖掘不为前人注意的“潜在的”历史因素。传统史学关注的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这些事件均有历史文献记载,其历史性一般为其参与者和同时代人所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显在的”历史事件或因素。但另有一类历史因素则不同,其历史性不为其同时代人所意识,也没有历史文献对其加以记载,这就是“潜在的”历史因素。比如历史上的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组成结构、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等等,任何国家在统计制度建立之前的漫长时代里对这些情况都不作记载,人们也不认识它们的历史意义。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人口总数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估量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其他如人口的构成等情况也兼有直接和间接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有时人口数量的变动还可能直接造成某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和趋势[①j]。除历史人口状况之外,还有土地、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儿童、妇女、家庭的状况等等,都属于潜在的历史因素,而新史学对这些潜在因素都做了一些有成效的研究。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史学自然也有消极方面,正是它的缺陷与不足才使一部分新史学家转向另一种更新的史学形态。
三、“新的”新史学
西方新史学在60年代取得大发展,70年代达到巅峰。但就在其70年代鼎盛时期,新史学内部又发生了一个新变化,即“叙述的复兴”,或“新的老史学”(a new old history)的复兴,也有人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新史学”(the new new history)。最早指出这一新变化的是于1979年发表那篇著名文章《叙述的复兴》的劳伦斯·斯通教授,此人是英国著名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的编委之一,同时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斯通指出的这一史学新变化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得到确认。而在确认这一史学新变化的人中间竟有法国年鉴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他于1985年临终前不久指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新史学”,而年鉴派第三代著名人物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所从事的则是“新的新史学”[②j]。最近,原籍德国的美国教授伊格尔斯(Georg G.lggers)在德国发表的德文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也接过斯通的话题,并重点讨论了这一史学新变化的内容[③j]。从这些不同国籍、经历各异的杰出史学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叙述的复兴”这一现象乃是西方各国史学最近20多年来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我们不妨将此史学新形态暂时统一称为“新的”新史学,或简称为“新新史学”,以别于原来的新史学。
在斯通评论所谓“叙述的复兴”之前,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便于1978年具体指出了新史学内部发生的某些新变化。他说:“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史、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却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同样,……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和表象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①k]这里勒高夫虽未指明新新史学的出现,但他所谈到的新史学的变化实际上恰是新新史学的某些特征。下面不妨顺此线索以新史学为对照来系统概括一下新的新史学各方面的特征。
如前所述,新史学的重点内容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发展,实际上主要的就是社会的结构与演变进程。但新的新史学却将重点转向人自身,探索一定环境下的某个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心态、感受和生活状况,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比如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干酪与蛆虫》(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雷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便描述了在16世纪的意大利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一个农村磨坊主的宇宙观及其文化背景。而年鉴派著名学者勒鲁瓦·拉杜里的《蒙太荣》(Montaillou,巴黎1975年)则考察了14世纪早期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小村庄的情况,生动地再现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乃至衣食住行的各方面状况。因此如将新史学与新的新史学的内容加以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偏重于经济史、社会史,而后者则偏重于思想(心态)—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则重点研究在一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身的主观状态;前者在考察规模上大体上是宏观的,后者则主要是微观的,被伊格尔斯称为“微观史”、“日常生活史”[②k]。新的新史学内容特点之形成大体上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新史学对经济史、社会史的偏重导致了不满,因此使一部分新史学家转向新的研究热点,即思想(心态)—文化史。在此转变中,以年鉴学派最有代表性。
1972年以前,在年鉴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居统治地位时期,年鉴派的主导观念是将历史分为三个层次,即首先是经济—人口因素;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势态;最后才是精神、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此三层次的重要性依次递减,前面的层次是决定后面层次的基础。因此,他们着重对前两个层次开展所谓“长时段”研究,而对第三个层次则比较轻视。其结果是,有的年鉴派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大陆自14世纪至18世纪的历史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无变动的历史”,因为据说这500年间欧洲社会完全禁锢在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经济—人口”状态中。然而恰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其他许多属于文化、科学、宗教、军事等方面的新现象,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现象仅因为属于年鉴派划分的第三个层次而遭到忽视[①l]。还有另一件惊人的事实,《年鉴》杂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长时期中竟未刊载过任何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章[②l],原因自然是法国大革命属于第三层次的政治。这是明显的偏颇。只因为年鉴派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受到赞许和欢迎,其偏颇在一段时间之内才得以掩盖,没有明显暴露。但几十年过去了,短处终究要被发现并遭到日益严厉的批评。于是作为一种纠正,心态史研究的热潮兴起了。虽然心态史最早始自年鉴派的创立者费弗尔和布洛赫,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直到60—70年代,心态史方才真正成为研究的热点。而法文的“心态”(mentalite)一词含义广泛而模糊,似可涵盖具有新新史学特征的全部内容,因此心态史学的兴起也就标志着一部分年鉴派史学家转向了新新史学。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国家内的一部分新史学家也由于大体相同的原因而将研究重点从历史中的客观环境转向了人们的主观世界。
其次,史学家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点的重要原因。
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处在核毁灭的阴影笼罩下,加上生态灾难的威胁和贫困化对相当多人类同胞的煎熬,这些不幸的事实使得西方知识界产生了疑虑,一部分人不禁怀疑现代科技和文明究竟是福还是祸?是给人类带来了解放还是压迫?人类文明是否真的会不断进步并给人类带来日益增多的满足?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是肯定的。而正是这种对于科学和文明进步的乐观信念为西方史学(包括新史学和传统史学)提供了主线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派史学家都共同相信,人类有一种不断走向进步的统一的历史。然而,对于科学与进步的怀疑打破了人类具有统一的历史的观念,怀疑派认为:“历史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不是直线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不但是存在有大批同样充满价值的文化,而且就在这些文化内部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围绕着它归纳出一种统一的表述。”结果是,“代替了一种历史的是,现在有了许多的历史。”[③l]这种观点除了否定西方中心论并承认人类各种文化具有同等历史价值之外,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中则否认以往史学所确认的各种“中心”、主线或框架,而主张为那些以前被排斥在历史之外的“小人物”、“没有登上权势之坛”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立传,写他们的经历、生活和思想体验[④l]。比如作为同男性相对存在的女性的历史在以前的史学中就毫无地位,无论经济史、社会史,还是任何阶级史,都不包含独立的女性史,它只有在上述新观点的指导下才能发展。于是产生了与原来相对说来属于宏观规模的新史学不同的,以从前在历史上没有地位的普通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即新的新史学。
此外,60年代末期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出现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失败以后,很多知识分子情绪低沉,于70年代丧失了以政治行动来改造社会的信心,因此不再关心社会问题,而将兴趣转向私人性质的问题。史学家将这种情绪带入史学研究,便冷淡以往的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而将视线转向人们的心态、情感、价值观等主观状况[①m]。这种情况也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征的一个原因。
新新史学在方法论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它虽然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不像新史学那样依靠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而主要是同人类学和心理学相联系;它放弃了新史学所倚重的计量方法,而主要依靠直观的分析判断来处理资料和进行解释;在表现形式上,它放弃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而回归到叙述。
史学与哪种其他学科相靠近相结合,既决定于研究内容,同时又施影响于内容的选择。前文引录勒高夫的著作指出,人类学“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为史学“优先的对话者”,这正是70年代以来的事实。史学与人类学的紧密结合既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征的原因,同时又为研究其新内容提供了方法。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的所谓“厚描述”的方法,即深入细致地描述事件,分析其文化意义,从而揭示全部社会系统和价值观念的方法,对于微观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在前面提到过的卡洛·金兹伯格和勒鲁瓦·拉杜里等人的著作中都可发现其影响的痕迹。至于新新史学对于无意识心态和性等问题的探索和描述,则不管作者们承认与否,都反映出弗洛伊德学说和其他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新新史学对计量方法的抛弃,一方面是其内容决定的,其内容或者无法计量或者缺乏计量资料;另一方面也与计量方法本身的弱点有关。60年代,在英、法、美等国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计量研究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但往往越是大规模的研究,其组织与实施中的问题也越多。比如资料是否准确完备,众多助手在处理原始资料过程中是否遵循统一的方法,所采用的计量公式与方法合适与否,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因此计量研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在计量研究投入最大、收获最多的人口史领域,其多数深层次的问题也未解决,如欧洲人口为什么在1640至1740年间停止增长?其后人口开始增长的原因是出生率的提高还是死亡率的下降?在城市史研究方面,人口流动趋势仍没有弄清。甚至17和18世纪是英国社会还是法国社会更为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答案[②m]。
勒鲁瓦·拉杜里于60年代末曾断言:“今后史学家为了生存必须能够编制电脑程序”,“不是计量的史学无权称为科学”[①n]。这个断言的荒谬性很快被实践所揭穿。而拉杜里本人仅在数年之后便背弃了自己的断言,他于1975年出版的法国心态史名著《蒙太荣》与计量方法毫不相干,而采取了直观的方法,以大量适宜的材料详尽描述了那个小山村的人文景观。面对计量方法暴露出来的局限性,说过大话的拉杜里尚且可以抛开它,那些未曾公开推崇此法的微观史学家们自然更不必对它表示什么偏爱。这样,摆脱了计量分析,也不依靠任何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模式,新新史学唯一的选择便是以直观理解的方法来处理资料,从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并以叙述的形式表现出来。
新新史学之所以放弃计量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而回归到直观和叙述,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分析性著作很难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某些分析性学术专著的印数甚至在1000册以下,除了少数同行专家和图书馆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要改变这一情况,争取一般读者的垂青,自然就必须改变研究方法,回复到史学曾长期应用过的叙述上来。不过这并不意味向传统史学的复归。新新史学虽然与传统史学一样都采取了叙述的形式,但它却有不同于后者的特点:它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主要描述的是社会下层的各种群体和个人,而不是社会上层;它由于内容的关系几乎无法应用传统史料,而必须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比如经常利用法庭记录,从证人证词中窥探往昔社会及其下层人民的状况;它在叙述的同时,常常也进行分析;它描述一个人一件事不只是为其本身的缘故,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反映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情况[②n]。因此我们说,新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史学形态。
叙述复兴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某些史学家经过几十年的跨学科研究之后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到失望,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抽象的概念没有能力毫无遗漏和毫无歪曲地去理解和传达人类生存的质量方面”[③n]。这不只是史学家单方面的抱怨。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情绪,学者们近年来甚至有一种危机感,认为社会学陷入了“褊狭、琐屑、理想主义”等危机,经济学尚处于“原始”状态,而整个社会科学要阐明“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则还有“光年”的距离要走,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在质量上是有问题的[④n]。正是这种悲观气氛弥漫着叙述复兴的学术背景。
新新史学由怀疑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转而以直观方法选取某种微观的内容(一个人物、一个村庄或一件事等等)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借以反映某种文化或社会的历史情况,这自然不是根据某种假设然后通过证明来得出结论的科学活动,而属于同科学相对的人文性质。因此,微观史学尽管没有完全割断同社会科学的联系(如借鉴人类学),但它确实疏远了科学,不再像新史学的主流那样自称为科学。这便是新新史学认识论的唯一特点,除此之外它与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暂时还看不出其他原则区别。
新新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形态,从发轫至今不过二十几年时间,有的问题尚很难定论。但从上述情况看,它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对新史学的片面性起了一些修正和平衡作用,这明显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它突破了后者的局限,着力于挖掘人们由传统积淀形成的无意识心态,此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以往人们的精神心态状况是重要的历史侧面,是史学的必要课题,而且揭示人的无意识心态的存在和活动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心态史研究使我们看到,文化传统(不管是有文字的还是无文字的)给人们打下的心灵烙印(即无意识心态)是多么深刻而持久,它竟可以不随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不仅要了解彼时彼地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且还要研究那里人们的传统心态,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是影响人们所思所为的社会存在。揭示这个道理是心态史学的一个贡献。
在新新史学的消极方面,似可指出两点。第一,微观史学家们主张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民主化史学”[①o],这固然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往往片面地强调自己所研究的内容的重要性,妇女史学家强调妇女史,同性恋史学家强调同性恋史,他们不仅互不相让互不协调,甚至还为了各搞一套而否定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具有统一的历史。这便走上了极端,否定了对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必要和可能,加剧了早已有之的史学碎化现象。所谓史学的碎化,最早乃由新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所肇始。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做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更加接近于它们所应用的社会科学学科,而在这些史学研究之间倒失去了共同性,它们取得的成果也很难综合到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法合拢的支离破碎的状态。如果说新史学由于不自觉导致了史学的碎化,那么新的新史学则是自觉的,它认为碎化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正常的,因此它为史学碎化现象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一个民族既然成其为同一个民族为什么不能有统一的历史?人类既然同为人类而存在为什么不能有统一的历史?恐怕关键的问题是在打破精英史观之后以什么样的中心和主线来重构历史,这是新新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未解决的问题。
第二,新新史学在强调研究思想文化史的问题上也有偏激现象,乃致有人认为,研究某种社会运动之兴起或其他某些政治或社会的一致行动,主要应当考虑“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不是“阶级”或其他社会经济等因素[①p]。这就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否定了经济等物质条件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当然是错误的。
从事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写作的多是新史学家中的佼佼者,比如勒鲁瓦·拉杜里既写出了微观史学的名著《蒙太荣》,又推崇过计量的科学史学,是兼而涉足新史学和新的新史学的典型代表。因此现在这两种史学形态在研究人员的队伍组成上并无分明的营垒或界线,而是互相交错混杂在一起的。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如前述的斯通和布罗代尔)已确认了新新史学的出现,也有的人(如前述的勒高夫)虽然指出了某些新新史学的特征,但只将其作为新史学的延续和发展,而不看作是一种史学新形态的出现。这并不奇怪,因为新的新史学毕竟刚刚才从新史学中分化出来,还缺乏完全独立的自我意识,更未来得及培养起自己独立的队伍。本文之所以区分出新的新史学和新史学这样两种史学形态,并不是根据其研究者的自我认定,而是根据两者在上述各个方面的实质差别。
目前,新的新史学正在发展,同时属于新史学的计量史学著作和各种社会史著作也在不断涌现,因此这两者处于共生并存而又不分伯仲的状态。而早被新史学排挤出史坛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近年来新史学缺陷的暴露和“叙述的复兴”,它还颇为活跃。因此目前西方史坛恰成三足鼎立之势,任何一方都无法压倒另外两方。美国著名史学家彼得·诺维克于1988年写道:历史学科作为具有“共同目的、共同标准和共同宗旨”的学者们的共同体已经“不复存在”,这里没有任何正统或权威的约束,人们可以“为所欲为”[②p]。此言虽然写在评论美国史学的专著中,但也完全适用于当今的西方史学整体。
注释:
①a弗里茨·斯特恩选编《各种各样的历史学》Fritz Stern,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兰登出版社1973年版,第175页。
①b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②b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第173页。
①c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第192—195页。
②c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第248—249页。
③c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第189—190、210—223页。
①d斯特恩:《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第20—21、25页。
②d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9页。
①e鲁滨逊(原译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页。
②e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55页。
③e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页。
①f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承中译,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第103—120页。
②f劳伦斯·斯通:《过去与现在》Lawrence Stone,The Past & the Present,劳特利奇—凯根·保尔公司1981年版,第21—22页。
①g巴恩斯:《论新史学》,载鲁滨逊《新史学》,第202—204页。
②g布洛赫(原译布洛克):《史家的技艺》,周婉窈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0年版,第65页。
①h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8页;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华世出版社(台北)1985年版,第60—61页。
②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30—136页。
③h布洛赫:《史家的技艺》,第25页。
①i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8—92页。
②i斯通:《过去与现在》,第16—17页。
①j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Bernard Bailyn,The Challengeof Modern Historiography,载《美国史学评论》第87卷第1期(1982年2月),第9—10页。
②j参见伊格纳西奥·奥拉巴里《“新的”新史学》lgnacio Olabarri,New New History,载《史学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34卷,1995年第1期,第11页。
③j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王燕生译,何兆武校,连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4期,1996年第1—2期。
①k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②k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四),《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1、152页。
①l斯通:《过去与现在》,第79页。
②l参见希梅尔法布《关于新史学的思考》Gertrude Himmelfarb,Some Reflections on the New History,载《美国史学评论》94卷第3期(1989年6月),第663页;菲雷:《历史研讨》Francois Furet,In the Workshopof Histo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③l、④l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四),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2页。
①m参见斯通《过去与现在》,第86页。
②m斯通:《过去与现在》,第32—40、82—85页。
①n转引自希梅尔法布《关于新史学的思考》,载《美国史学评论》94卷第3期(1989年6月),第661页。
②n斯通:《过去与现在》,第91页。
③n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四),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第156页。
④n弗雷德·温斯坦:《心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危机》Fred Weinstein,Psycho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载《历史与理论》第34卷,1995年第4期,第301—302页。
①o琼·沃利奇·斯科特:《史学处于危机中吗?》Joan Wallach Scott,History in Crisis?The Others'Side of the Story,载《美国史学评论》94卷第3期(1989年6月),第691页。
①p弗雷德·温斯坦:《心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危机》,载《历史与理论》第34卷,1995年第4期,第308—309页;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续四),第154—155页。
②p彼得·诺维克:《宏伟之梦》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8页。
标签:历史学专业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新史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认识论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