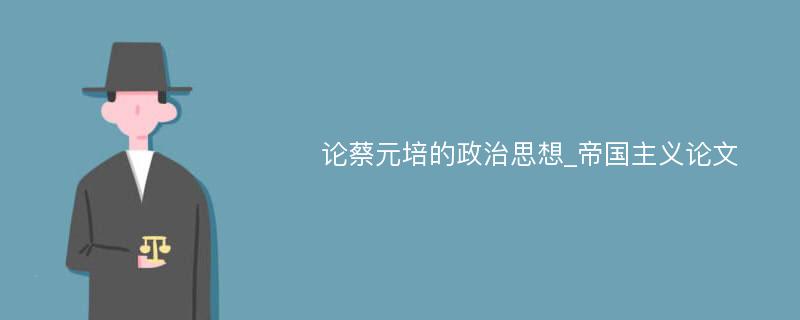
蔡元培政治思想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蔡元培始终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在新风若炽,大故迭起的世纪之初,他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对当时的世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以及蓬勃兴起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提出过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政治观点。分析研究蔡元培的政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透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愿望与政治主张,从而能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发展脉搏。
一、从爱国主义到国际和平主义
蔡元培生长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炮声把他从“学而优则仕”的梦中惊醒。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刚刚跨入翰林院的蔡元培与其他忧国之士联名上书清政府,力主抵抗,反对议和。指出:“道路传闻以为有赔款割地之举,朘生民有限之脂膏,蹙祖宗世传之唬殆业,度圣明在上, 必不肯出此下策,以偷安一时。”〔1〕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却被不幸而言中, 这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1900年,英、美、德等八个帝国主义联合入侵中国,强迫清廷在1901年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仅仅三年之隔,俄日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又在中国领土上开火。蔡元培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侵略战争带给中华民族的耻辱与苦难,他渴盼中国能迅速强大起来,早日收回主权,以免遭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蹂躏。在忧愤交加的心情之下,他于1904年写下了《新年梦》这篇政治小说。文中写道:“各国的海陆军,即然被中国击败,把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统统消灭了。兼且从前占去的地方,也统统收回来了。”〔2〕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对祖国的热爱使蔡元培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爱国并非他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唯一发端。他更从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反对强权、反对侵略,主张建立一个各国平等、和平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他在《新年梦》一文中建议:“请设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判断员与军人皆按各国户口派定。国中除警察外,不得别设军备,两国有龃龉的事,番由裁判所公断。有不从的,就用世界军打他,国中民人与政府不合的事,亦可到裁判所控诉。……既定了约,就立刻照办起来,从此各国竟没有了战争,民间渐渐儿康乐起来,……。”〔3〕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在种族歧视、经济掠夺、阶级争斗、贫富分化等社会现象普遍存在的事实面前,蔡元培幻想设立“一万国公法裁判所”,以公平合理解决一切武力争端,进而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确实是一种异想天开,但从中流露了他渴望灭绝军国主义的正义情感和共建和平世界的美好愿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硝烟四起,生灵涂炭的世界惨剧,蔡元培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愈加深重,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此次德军破坏中立,蹂躏人道主义,任其果获全胜,其祸真甚于洪水。今此祸虽似可免,而成局何时可定,竟难逆睹。……然以现状论,则文化进步之阻力,固彰彰矣。”〔4〕1918年, 当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蔡元培欢欣鼓舞。他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认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昭示了黑暗强权论的消灭、光明互助论的发展,阴谋派的消灭、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的消灭、大同主义的发展。迷信种族,高唱“德意志超过一切”,几十年来恃阴谋、武力而不恃正义的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了,而白人、黄人、黑人团结一致,义务、权利平等的协约国胜利了,蔡元培深信这是世界大同发展的机会,他总结指出:“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5〕蔡元培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迅速扩大,蔡元培毅然投身于抗日运动之中。1933年5月, 他在上海青年会“国耻讲演会”上大声疾呼对日本的研究。他痛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恶,抨击日本政府现行各种侵略政策,特别从武力、经济、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作了有力的揭露,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复杂性深刻性,告诫国人决不可用简单而浮浅的方法来对付。1939年12月,蔡元培为著名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歌》作词,“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6〕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及蔡元培本人认识的偏差,蔡元培未能真正彻底认清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把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发生的混战,看成是英、美、法代表正义对非正义德国的宣战,在很大程度上被现象所蒙蔽。不仅如此,蔡元培的思想言论,还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他忽视人类社会的矛盾根源,呼吁以“公理”战胜强权,用“公法”解决一切国际、国内争端,促成并维护世界和平,当然是毫无结果的。但是,蔡元培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他从爱国主义出发,进而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鼓舞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团结奋斗,共建和平的历史职责,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功不可没的。
二、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
蔡元培是一位从旧式书斋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尤其推崇儒家的“民本”思想。他把“民本”思想与源于西方的民权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古代“民为贵……君为轻”的学说,“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1902年,他编成《文变》一书,收录反映民本思想的的著作,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严复的《辟韩》等,作序说明:“寻其义而知世界风会之所趋,玩其文而知有曲折如间变万方之效用。”〔7〕他对“民本”思想进行现实改造, 把它提到“民意为最大”的高度,并为这一宗旨付出毕生的精力。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自此深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8〕弃官归里之后,他撰写《上皇帝书》一文, 文中表示:“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总办也。”同时指斥清廷中误国害民的当权者,“不知有公司(指国家)也,知有家业而已;并不知有家业也,知一身之娱乐而已。于是乾没不已而勒索焉,笼络不已而渔猎焉。”〔9〕此时, 他已明显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的思想,从原有的儒家民本思想的的基础上迈出了一大步。
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谋求中国大多数人的自由、平等与幸福,蔡元培全力以赴加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1902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1904年,他组织发起“光复会”,并任会长;翌年,又参加“中国同盟会”, 任上海负责人; 1911年,他加入辛亥革命行列,终于把封建专制的清王朝送进坟墓。在参与革命活动过程中,蔡元培始终是基于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特权与专制统治,而去除夷夏之争的先进分子。他认为满人入关以后,经几百年与汉人的杂居,早已与汉人同化。因此,“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10〕同时,他指出当时中国民众的“仇满”情绪以及革命者的反清斗争,皆为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是民权与反民权的斗争,而并非种族之争。“其因之动力在政略上者,其果之反动亦必在政略上,故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事也。”〔11〕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序上抑制了当时一些激进革命者的种族偏见。
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国在昙花一现之后,又是黑暗漫长的北洋军阀统治。蔡元培仍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他把他们比作猛兽,同时把当时的新思潮比作洪水,他号呼疏导洪水,驯伏猛兽,建设太平的新中国。他深信20世纪是民权的时代,是“多数压制少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因此,这个时代“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东亚社会。”〔12〕言辞犀锐,尽现其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厌恶之情、灭绝之志。
教育是蔡元培毕生的事业,教育界自然成为他反封建主义的主要战场。1912年,他身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职,其间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彻底否定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同时,他还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教改措施,向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发起挑战。1917年1月,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议和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教学体制到行政组织,以至师生的社团活动等方面,都进行全面的改革,把北大改造成为一个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与教育内容的新式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准备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蔡元培在教育界的反封建斗争实践无疑是他反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必然反映。
蔡元培一生历经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三个时代,自始至终致力于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他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同样,他也无情地抨击蒋介石政府的新专制主义。他痛陈封建专制的罪恶:“独夫横暴,学途湮塞,……文网密布,横方有禁……。虽有超群拔萃、才智雄强之士,亦噤若寒蝉,罔越畔岸……。”〔13〕热情呼唤民主自由之潮勇往迈进,以冲决藩篱。
与其坚定的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蔡元培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不同于其他旧式文人,在意识到中国无力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抗衡之后,他一改旧日所学,转而留心西学,以寻求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出路。他第一次出国游学,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学者,这使他更能清醒地筛选、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身入西洋而不被其所惑。法兰西共和国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成为各国追求的创建民主政体的有力武器。蔡元培对之十分赞赏。他明确表示:“昔法国之大革命,争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14〕并称赞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得“道德的要旨。”〔15〕他认为“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好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而法兰西共和国堪称楷模。1918年6 月,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受邀至北大讲演,蔡元培致词欢迎,他说:“吾人为集思广益起益,对于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以国体相同,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为欢迎,……而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法兰西,更绝对的欢迎。”〔16〕
1922年4月,蔡元培联合一批著名学者、教授, 公开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而作为中国现行政治改革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建设“好政府”的目标:“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 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17〕无论是“好政府”的目标,还是政治改革的原则,都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随着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而变本加厉,广大革命志士深受其害。蔡元培终于认清他曾拥护、支持的号称“革命”的蒋介石政权,根本不是他所热切盼望的法兰西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毅然加入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阵营。他与宋庆龄等进步人士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从事保障民权活动的同时,积极参与营救受国民党统治者追捕、迫害的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如邓演达、廖承志、李少石、陈赓、牛兰夫妇等。1933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青年会上作题为《保障民权》的演讲, 公开责问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宪政时期,人民要行使四种政权。若训政时期,尚不能得到最最初步的自由,则何以为行使四权的训练?此其一。为宪政的预备,重在地方自治,人民若生命尚无保障,一切不得自由,则何以厉行自治?此其二。……“现际空前困难,大家都说要全国总动员,始可渡过难关。……若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尚不许充分运用,则所谓集思广益者何在?此其一。且各种事业,均感人才缺乏,若有为之才,偶因言论稍涉偏激,或辗转联带的嫌疑,而辄加逮捕,甚思处死,则益将感为事择人之困难,而无术以救国,此其二。”〔18〕同年5月, 蔡元培又在《民治评论》期刊上发表《民治起点》一文,对他的民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文中表示:“民有、民治、民享,是共和国的真相,而以民治为骨干。”〔19〕因为人民若不能自治其国,则政府即有“日蹙百里”的现象,人民亦无可奈何,何所谓民有?又使政府凭“朕即国家”的蛮力,苛征暴敛,使人民有救死不赡之苦,而无乐其乐,利其利之感,何所谓民享?他大胆指责蒋介石专制独裁政府对孙中山创建的民主共和政体的残踏:“我们这些孙先生之徒,担负了训政的名义,已经数年了,而要求指出一个完全自治之县,竟指不出来。这真是愧对孙先生的一端。”〔20〕
蔡元培处身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时期,他走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之囿,从民族革命起步而最终成为笃信民权,追求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为构建其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他同当时的封建主义、军阀势力以及各种独裁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正如周恩来所说:“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21〕胡绳在其《争民主的战士永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对蔡元培作了极高的评价:“他之所以是一个革命者,就因为他的一生贯彻着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他以‘无所不包’的民主作风,扶助着进步的文化运动;他以‘有所不为’的操守,对抗着一切反民主的势力;他以学者的胸襟而成为民主斗争中的一个战士。”〔22〕
三、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兼容并蓄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20世纪初期,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而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对内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走欧美各国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经之路。然而,世界资本主义此时已弊病丛生,欧美各国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爆发的世界大战,一次又一次向中国的革命者表明欧美式的共和国并非救国良方,这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既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老路,又想避免其本身各种缺陷的愿望。蔡元培正是带着这种愿望,以浓厚的兴趣关注并研究当时国内外盛行的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希图另辟蹊径通向理想中的民主政治。
蔡元培认为中国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学说,记载在《论语》、《孟子》、《礼运》等典籍中的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便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国也有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周礼》、《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古代中国的农业政策,“遂人辨其野之土,土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周礼》),都是类同于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则源于资本与劳工的对立,“如挽近因贫富之不平,而启劳动家与资本家之纠纷。盖因少数资本家之役使大多数劳动家,以增其产业,而劳动家乃转不免于冻馁,其不平也实甚,于是有社会主义之发现。”〔23〕可见,蔡元培对社会主义渊源的认识虽停留在表层,但仍有一些可贵的见地。
蔡元培对当时中国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作过探索,如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互助论”,甚至还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等。他尤其赏识“共产主义互助论”,不仅多次撰文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有关著作,还曾以此作为观察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社会矛盾问题的指导思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内外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发表对战争性质及战后发展的见解,蔡元培明确表示:“欧战的‘最后胜利’,就在协约国。协约国所采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义。”〔24〕他甚至认为克氏的互助论应用于国际政治就是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远不能凌弱的。”〔25〕今后只要人人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世界“自然不愁不进化了。”〔26〕此外,蔡元培还希望用克氏的互助自由联合的方式来创建一个没有贫富悬殊、权利平等,人人读书工作的新社会。为此,他不但大力支持资助北大校内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实社”,还亲自撰文竭力倡议工学互助。他说:“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重大问题也可以解决,要是与全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全世界最重大的问题也统统解决了。”〔27〕总之,蔡元培设想以互相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使其具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公则。”〔28〕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流派中,马克思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日渐深广并占据主流地位。蔡元培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均持敬意,他曾在《缘起》一文中表示:“在此短短之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史科学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认。”〔29〕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蔡元培受到了鼓舞,他不但喊出了“劳工神圣”、“唯劳动者最有将来”的口号,而且公开提出“以俄为师”、“俄国革命为吾人之前驱。”〔30〕同时表示“相信由此以后,世界上必发生极大变化。”〔31〕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他积极热情地支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及青年学生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喀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以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社团组织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都与当时蔡元培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分不开。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大胆冲破国民党政府“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禁令,在1933年3月,与陶行知、陈望道等人联合, 领衔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公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
诚然,蔡元培始终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立场上来兼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他欣赏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进行研究,但他从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的全部用心,是为了汲取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积极因素来填补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缺陷。这使他终究不能摆脱旧民主主义的局限,终究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拯民的道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暴力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主张和平的政治改良。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德治”、“教化”极为欣赏,深信“道德”可以超越、调解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间的冲突。他曾在《社会改良会宣言》中呼吁:“盖所谓共和国民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不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陷,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忘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 ”〔32〕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 其用意正是通过道德培养而形成共和思想的要素。由此可见,蔡元培最终没有真正理解、接受社会主义学说,而只停留在“互助论”式的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同样,他也未能改变和平改良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这使他的种种政治主张及美好的政治理想,无不流失于空想。然而,瑕不掩瑜,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杰出代表,蔡元培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论,以及其追求民主共和,追求绝大多数人幸福的政治理想,都将永存史册。
收稿日期:1995-10-31
注释:
〔1〕《密请连英德以御倭人摺》, 《蔡元培政治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页。
〔2〕〔3〕《新年梦》、《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3页。
〔4〕《致蒋维乔函》,《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第2集第343页。
〔5〕《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政治论著》第175—177 页。
〔6〕《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 《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90页。
〔7〕《文变》,《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63页。
〔8〕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 《教育杂志》第三年第10期。
〔9〕《上皇帝书》,《蔡元培政治论著》第12页。
〔10〕〔11〕〔12〕《释“仇满”》,《蔡元培政治论著》第29页。
〔13〕《〈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61页。
〔14〕《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37页。
〔15〕《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16〕《欢迎柏卜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78—179 页。
〔17〕《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政治论著》第220页。
〔18〕《保障民权》,《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13页。
〔19〕〔20〕《民治起点》,《蔡元培政治论著》第426页。
〔21〕《新中华报》(延安)1940年4月19日
〔22〕《〈新华日报〉专论》(重庆),1945年1月11日。
〔23〕〔29〕《缘起》,《申报》1933年3月13日。
〔24〕〔25〕〔26〕《大战与哲学》,《蔡元培全集》第3卷, 第201—205页。
〔27〕《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0页。
〔28〕《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74页。
〔30〕〔31〕《民国日报》,1922年8月23日。1922年11月20日。
〔32〕《社会主义改良会宣言》,《蔡元培政治论著》第68页。
标签:帝国主义论文; 蔡元培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互助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