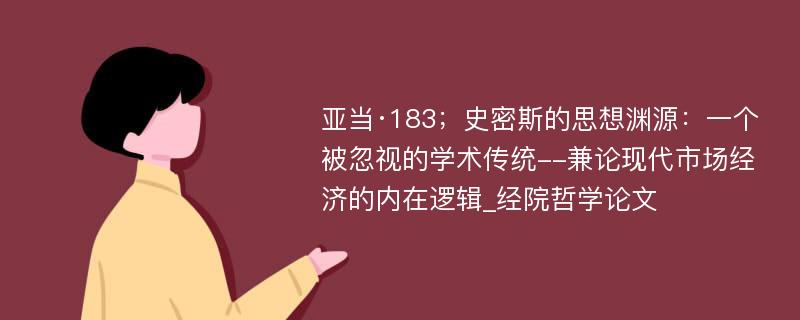
亚当#183;斯密的思想渊源:一种被忽略的学术传统——兼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当论文,渊源论文,逻辑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在《国富论》(1776年)中,斯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构建了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体系,被人们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恩格斯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马恩全集》第1卷第601页)。数百年来,不断有人发出“重回亚当·斯密”的感慨。迄今,斯密经济思想仍对许多经济学家产生影响,仍为我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探讨现实社会经济热点、辩论政府有关政策措施等提供启发。
任何具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系,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既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浓郁的时代气息,又有着对“主流”思想和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富有批判精神,但同时亦具有“三大来源”①。斯密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亦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他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早期教学和晚期写作),对“主流学术”有着很好的把握和理解,其学术思想是对当时“主流学术”的自然继承和系统发展,当然亦有了质的提高——至少就经济学而言,“历史在这里转弯”!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术界对斯密学术思想及经济理论的研究,数百年来汗牛充栋,但对斯密同“主流学术”的关系普遍采取了忽略的态度,而是直接把他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商人、官员或幕僚并列起来。这似乎给人留下如下印象:在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凭空跳出来一个亚当·斯密,从法学教授、道德哲学教授,一跃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提出了一套经济理论并把重商主义痛斥一番后,斯密重新脱离经济学,同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诗人、地质学家等笑谈社会人生,任凭经济学界天翻地覆,再也不予理睬(至少其遗稿委托给了地质学家和化学家管理,而非我们希望的经济学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后世关于斯密的诸多争论、不理解,同这种忽略有很大的关系。人们不禁难以理解,为何斯密的经济理论从法学来,为何斯密能从道德哲学转到经济学再转回到道德哲学,甚至还闹出了所谓“斯密问题”的学术笑话。当然,如果这种忽略的不良后果仅限于学术领域,那么还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不论是罗马帝国兴盛时代,还是华夏汉唐时期,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模型的岁月里,经济照样发展、国家依然富强);不过,如果这种忽略影响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解,那么学术问题或会演变为真实世界的缺憾。果真如此,学术界罪莫大焉!事实上,当前我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热点争论,同这种忽略有一定的关系。
二、学术背景述略:从经院哲学到亚当·斯密
整个中世纪,不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学术研究,“经院哲学”均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可谓那个时代的“主流学术”。尤其是13世纪西方世界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论”(上帝造物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平等主义”(人与人之间)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感觉经验”和“生物学方法”等相结合,形成了高度综合的、长期居支配地位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经院哲学体系;尤其经过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提炼、古罗马西塞罗(前106—前43)发展和“上帝认可”(基督教)后的自然法,在阿奎那那里已经“变得空前的一贯、清晰与有力”(登特列夫,2008第35页),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欧洲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西方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被阿拉伯人阻断,激发了西方世界开拓新航线的热情,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勃兴,新航线的发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欧洲步入“大航海时代”和“重商主义时代”;另一方面,东罗马学者带着大量古希腊罗马文献涌入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不仅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为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其中前者对现实社会经济等世俗世界的影响更多些,后者对学术界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更大些。
“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催生了重商主义政策主张和政府干预措施,并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并没有立即引起“主流学术界”的重视,所谓重商主义者基本以商人、政府官员或官员幕僚为主。不过,上述事件所引起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却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后,宗教改革迅即变为燎原之势,新教学者和传统天主教学者的论战成为当时学术界的辩论焦点。为了振兴传统经院哲学,天主教会召开了特兰托宗教会议,对外反对新教、对内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此为契机,传统的多米尼克会和新兴的耶稣会开始了以西班牙为基地的托马斯主义复兴运动,并诞生了经院哲学最后一位大哲学家——“独一无二的博士”弗兰西斯·苏亚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
毫无疑问,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对于欧洲社会摆脱“黑暗时代”、构造同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相适应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代表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过,由于在阿奎那兼顾“理性”与“信仰”的经院哲学中,新教主张“因信称义”,以“信仰”替代“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术探讨和学术创新。同时,尽管“反宗教改革”代表了时代的反动,但在苏亚雷斯等晚期经院哲学家那里,由于兼顾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信仰、权利与义务,开启了学术创新之门,并成为学术批判、继承与发展的重要线路;其中,对前者的相对重视(个人、理性等),催生了法国启蒙运动及其自由民主理念,对后者的相对重视(社会性、义务等),孕育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推动了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苏格兰哲学智慧和英格兰实业精神),并最终诞生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可以说,不论是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民主理念,还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哲学”,都是自然法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抛却宗教外衣,并在经院哲学的综合(尤其是阿奎那综合和苏亚雷斯综合)中,日渐趋向其中的“人类本性”和人类“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苏亚雷斯、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发挥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于这条学术继承路线,学术界素来关注不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社会对苏亚雷斯相对重视,但英语文献很少有人提及。法哲学领域相对重视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但不仅语焉不详,且充满争议。至于经济学界,尽管有个别学者提及上述学术传承脉络,但往往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例如,Bittermann(1940)曾提到,“有充分证据显示,不论是在《道德情操论》还是在《国富论》中,斯密的诸多思想、例证和表达方式,都深受西塞罗、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哈奇逊的影响”②;他提及的学者都是自然法(欧洲大陆)和道德哲学(苏格兰)的重要代表人物,但这些文字几乎已是笔者所能查到的最具体说法。
中文文献亦是如此,以这些学者最有影响的著述为例:1648年左右,耶稣会传教士(明清传教士多属耶稣会,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卫匡国(M.Martini,1614-1661年),曾将苏亚雷斯的《论法律》译成中文,可惜没有出版,使得迄今仍无中文版的苏亚雷斯著作;《战争与和平法》是1625年出版的法学名著,但迟至2005年才有中文版;普芬道夫的《论义务》和哈奇逊的《道德哲学体系》均是2010年才有中译本。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自然法哲学,上述中译本的出版就是一个反映。确实,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应该较法国启蒙运动更为重要,因为近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多地从前者而非后者那里汲取营养。如果将现代社会比作“大厦”,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的是大厦基座,法国启蒙运动则是大厦门前高高飘扬的旗帜,后者固然光鲜夺目,但前者似乎更为必不可少。
基于上述考虑,下文拟以“自然法”和“道德哲学”传统为线索,探讨“苏亚雷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卡迈克尔—哈奇逊—斯密”之间的传承关系和学术发展脉络。然而,由于有关探讨涉及诸多领域大量富有争议的论题,不仅会冲淡主题,且为篇幅所不许。故本文拟采用高度简化的方式,以“窥斑见豹”,在“主流学术”的诸多领域中仅选取同斯密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③,在该领域中仅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在代表人物中仅选择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著作④;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拟以“学术脉络”的梳理作为重点,而尽量不陷入有关理论细节。
三、自然法传统:从苏亚雷斯到普芬道夫
苏亚雷斯当了一辈子大学教授,被人们视为阿奎那之后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拉丁文版选集达28卷之巨,且几乎卷卷逾千页,其最具影响力的《形而上学辩》(Disputationes Metaphysicae,1597)和《论法律》(1612)仅正文就分别达2000页和1200页。著述篇幅之恢弘、行文“学究式”的纠结,再加上“自然法”形而上、“泛道德化”之研究主题,兼经院哲学日薄西山,均限制了苏亚雷斯学术思想在后世的广泛传播⑤,但对当时的学术界却不存在参阅的困难,因为拉丁文正是当时的学术语言(如同英文是目前经济学语言一样)。从表面上看,苏亚雷斯的作品几乎是纯神学著述,且其所在的耶稣会亦因准军事编制、严格的组织纪律、近乎秘密组织的清规戒律,难以吸引现代人的眼球(其教育、传教和学术成就或许同其献身精神有关)。不过,在这种不太合理的外表下,苏亚雷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阿奎那式“综合”,不仅重塑了传统经院哲学体系,而且赋予了时代气息。尽管苏亚雷斯探讨的主题限于神学领域,但他在论述有关问题时,总是会认真辨析各种观点,并对流行观点做诸多修正和发挥,因而其思想体系容纳了很多近现代概念和观点,令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学术界可以不断挖掘的“宝库”。
尤其是在自然法和国际法领域,苏亚雷斯不仅重新复兴了自然法哲学,更被视为“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重要先驱(故有人称之为“国际法祖父”)。关于格劳秀斯和苏亚雷斯的关系,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格劳秀斯继承了苏亚雷斯的许多思想,尤其是《捕获法》(De Jure Praedae)手稿的发现,为人们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国富论》早期草稿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1604年底、1605年初,格劳秀斯写作了《捕获法》手稿,但一直下落不明,直至1864年才被发现,并于1868年正式出版。虽然在写作时间上,该手稿(1604年)要早于苏亚雷斯的《论法律》(1612),但它显然不是一次完成的(虽然都是格劳秀斯手迹),而是后来新加了一张稿纸(纸型略小,字母小而密),其内容几乎就是苏亚雷斯《论法律》第二卷第19章和20章的摘要。由此可知,格劳秀斯知道苏亚雷斯,并参考了苏亚雷斯关于“万民法”(Jus Gentium)的论述。至于格劳秀斯为何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没有提及苏亚雷斯,这或许同格劳秀斯当时的处境有关。
格劳秀斯1621年4月逃至法国后,在路易十三的资助下从事《战争与和平法》的写作。在《论法律》中,苏亚雷斯在探讨立法权和各类政府理论时,尽管打着上帝的旗号、尽管旁征博引,却仍然表示出了“主权在民”思想,并把它作为第一条推论⑥。不仅如此,尽管苏亚雷斯主张一个稳定的政府,但同时亦认为:若当权者“陷入专制”,一个社会(Community)剥夺其统治权就是正当的(Suárez,1612/1944,第387页)。在路易十三看来,这无疑是句句刺耳。或许正是虑及路易十三的感受,寄人篱下的格劳秀斯才没有在著述中明确提及苏亚雷斯的影响。
至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卡迈克尔、哈奇逊和斯密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争议相对少些,故仅做简要阐述。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问世后,迅速风靡欧洲,瑞典国王阿多夫(Adolphus)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更是把它与《圣经》一起放在枕下,不时阅读。普芬道夫同瑞典王室的关系则是有目共睹的:其最主要的自然法哲学著作《自然法和国家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1672)就是献给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一世的;不仅如此,这部著作也正是在他接受查尔斯十一世邀请出任隆德大学法学院自然法和国际法教授期间写成的。不过,《自然法和国家法》洋洋洒洒八卷本,篇幅甚大;1673年,普芬道夫出版了该书的摘要版,即两卷本的《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简称《论义务》)。1718年,格拉斯哥大学首任道德哲学教授卡迈克尔将《论义务》译成英文,并附加广泛注释和评论后正式出版(1718初版,1724再版),将普芬道夫的《论义务》和自然法传统引入苏格兰学术界。卡迈克尔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哈奇逊的老师,而哈奇逊又是亚当·斯密的老师;不仅如此,他们还先后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任期分别为1694-1729,1729-1746,1752-1764)⑦。正是这师徒三人,不仅实现了“自然法哲学”向“道德哲学”的转变,而且最终形成了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第一个经济理论体系。
四、从自然法到道德哲学:经济理论的演变
自然法貌似“形而上”和“泛道德化”,但却有着合理的内核和良好的理论创新可能性。事实上,只要将“假设条件”或逻辑前提稍作调整,传统的经院哲学体系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学术思想。事实亦是如此。苏亚雷斯的《论法律》完全是神学作品,但他的“学究式”研究,为直接从“人性”探讨自然法提供了学术空间,如“自然法可以独立于上帝”等。格劳秀斯(1625)试图建立的是一套独立于神学的“世俗”法律体系,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明显的“神学压力”:经常引经据典,以表明其理论相容性。而到了普芬道夫(1673)那里,则基本上同神学无关了,尽管他“并不拒绝向某一疏远的上帝观念聊表敬意”(登特列夫,2008第59页)。这样,同政治领域中神权和君权分离,宗教回归精神世界一样,“主流”学术界也实现了宗教和世俗的分离(普芬道夫可能是一个标志)。
从苏亚雷斯到普芬道夫,“主流学术”基本实现了从神学到世俗生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彻底:假设前提、研究方法均完成了转变,但研究主题中仍包含了部分传统内容,斯密则完成了彻底的转变。例如,普芬道夫的《论义务》分析了三种义务:对自己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和“对上帝的义务”;卡迈克尔的研究主题基本重复了普芬道夫,哈奇逊的《道德哲学体系》亦保留了“对上帝的责任”的探讨(参见第一篇第九、十章);而到了斯密那里,则几乎看不到上帝的影子。以斯密的主要著作为例:《法学演讲》中的法律,分为公法、私法和家庭关系法;《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哲学,分为“对别人利益”的关心所产生的美德(第一、二卷)和“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所产生的美德(第三、四卷);《国富论》中的富国裕民,更是同上帝丝毫不沾边。
尽管存在这些不同,但上述学者的学术研究却有着下述共同之处:(1)研究方法是学术性的,讲求系统性、准确性和内在逻辑性。(2)研究主题和核心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却有着类似的研究心态和行文风格,冷静、理性、温和、循循善诱。(3)有着大量共同的词汇,如人性、理性、社会性(群居性)、义务(责任)、权利、正义、美德等。(4)对不同问题的探讨运用大致近似的论证思路: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全”(生命和维持生命的手段)或“关心自己”,但人要同其他人打交道(社会性或群居性);人是有着“理性”能力的高级生物,凭此能力可以兼顾“自己”和“他人”;最后,基于人性并符合理性的东西是正义的,是美德。
在论证过程中,或许“学究式”研究的特点,他们往往是综合的、温和的和不偏激的,如兼顾个人和社会(群居性)、理性与信仰(神启)、义务与权利、过程与结果等。这些特点,不仅易于进一步学术探讨,而且同新教学者、法国启蒙运动多数成员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新教重视信仰却相对忽视人们的理性(能力),法国启蒙运动学者过于强调个人和权利,不太关注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及其相应的义务等。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人利益或“自保原则”在上述学术传统中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生命高于一切”,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则认为生命之上可以有更高的东西,可谓思想界对自然法哲学的过度发挥,如卢梭曾明确指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谁要依靠别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必要时就应当也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当君主对他说:‘为了国家的缘故,需要你去效死’,他就应该去效死”(同上,第46页)。但苏亚雷斯至斯密的这一学术传统却存在很大不同。以经济学中相对重要的“财产”为例,它们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手段,维护财产安全是人们的重要权利;然而,一旦同“生命”有关,“财产”马上就变成第二位的东西:“如果为危急情势所迫,任何人都可以从他人那里拿走对于维持其生命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格劳秀斯,1625/2005,第129页)⑨;当然,其前提是“危急情势”并危及生命,“一旦危急情势不复存在”(同上,第131页),则个人的财产权利重新得以恢复。本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略费笔墨,是因为国内学术界相对重视新教和法国启蒙运动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同时强调“黑暗时代”经院哲学的落后与腐朽,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西方社会的学术演变过程。其实,任何学说都有两面性,需辩证看待。
回到经济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同样蕴含在上述“主流”学术传统中,其思路大致如下:(1)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却不得不过社会性(或群居性)生活,不得不同其他人打交道;(2)幸运的是,人类有理性能力,可以“由己及人”,洞察他人的想法,进而进行平等自愿互利的交换;(3)交换需要公平公正,需要契约,而契约的基础是“价值”,从而需要价值理论;(4)真实世界的交换,受供求影响,价格有时会围绕价值波动,从而需要价格理论和供求理论;(5)为便于交换,需要“货币”,涉及“利息”……尽管形式有异,但从阿奎那到斯密,这种逻辑思路基本类似,这也是“价值论”最初出现在“契约”部分的原因之一。
不妨具体分析之。因资料所限,我们没有发现苏亚雷斯对于经济问题的系统阐述,但不少地方仍可看到上述思路的痕迹。以《论法律》第二篇第19章为例,苏亚雷斯指出,伊西多尔(Isidore,560-636)在《词源》⑩中提及的诸多例子,如“货币的使用”、“买与卖的私人契约”等,均是在自然法的条目下讨论的(Suárez,1612/1944,第350页)。苏亚雷斯还提到,“第三个要素是同没有敌意的人们签署商业契约的自由,这种自由源于万民法。……按照万民法建立的商业往来应该是自由的,若无合理原因禁止此类交往,就是违反这种法律制度。”(同上,第347页)在这些论述中,自然法、契约、商业、货币等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中,上述论证思路变得比较明显。在该书第二篇第12章“论契约”部分,格劳秀斯考察了“涉及别人利益”的交换行为。他不仅区别了“以货易货”、货币之间的“兑换”和“用钱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三种契约(自动约定或明示契约),提到了借贷、雇佣、股份、垄断、货币、风险等经济概念,而且分析了契约所具有的“平等”、“自由”、充分信息披露等属性。正是在这一部分,格劳秀斯指出,“物品的通常价格顾及商人为获得该物品所付出的劳力和花费,而市场上经常发生的价格突变往往取决于购买者的多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和可售商品的丰贫。”(Grotius,1625/2005,第203~204页)。寥寥数语,价值论、市场供求、货币理论等,均有所涉及。尽管格劳秀斯的论述并不系统,但“别人利益—契约—价值—价格”论证思路,基本符合上文的总结。
普芬道夫的《论义务》也是如此,但较格劳秀斯有了很大的扩展和完善,第一卷第14章“论价值”几乎就是标准的经济学教材。普芬道夫不仅将“论价值”单列一章,且处理方式同前述思路也是一致的,这可以从其章节顺序看出来:在论述完“对上帝的义务”(第四章)和“对自己的义务”(第五章)后,普芬道夫开始探讨对别人的义务,并在论述完契约后,在“所有权”之后、“合同”和“契约债务”之前,探讨了“价值理论”;显然,普芬道夫同样是把价值论等经济理论,作为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约(交换)的基础。卡迈克尔的处理方式同普芬道夫类似,但进一步简化,重新将“价值论”放在“契约与准契约”一章(第11章)中,并特别总结到:价值取决于“稀缺性和获得的困难”(Carmichael,1724/2002,第106页)。哈奇逊基本上是集普芬道夫和卡迈克尔之所长,但做了极大的拓展;就篇章安排而言,所有权、契约、价值等部分几乎完全沿用了普芬道夫的做法,同时充分吸纳了卡迈克尔的有关评注。同普芬道夫“论价值”相对应的一章,哈奇逊将标题改为“商业活动中商品的价值以及货币的性质”(第二篇第12章),并对需求、价值、度量标准、金银价格等做了更为全面的讨论,现代社会所熟知的经济理论已是呼之欲出。
五、斯密学术思想:继承、发展与突破
从斯密主要著述看,斯密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论证思路、行文风格等,基本完全延续了上述自然法(道德哲学)传统,但有很大的改进和重要的突破。如果把斯密放在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斯密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解。事实上,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现代社会经济秩序构建时期,其经济理论亦旨在对市场经济体系做出相对完整的描述。
1.研究方法。正如登特列夫(2008)指出的:“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不同于经院哲学的地方,并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方法。”(第58页)尽管格劳秀斯8岁时就创作了拉丁文诗歌,但对数学却情有独钟,“在格劳秀斯的学说中,法律问题和数学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在自然法学说后来的发展中,这种用数学方法阐述法律问题的倾向甚至更为明显。”(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格劳秀斯经常提到数学,1604年写作的《捕获法》序言部分,就以9项法则推出13项法律,而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关于“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的“数学应用”,更成为近代人文学科得以摆脱传统经院哲学桎梏的有力武器。其实,尽管自然法貌似“形而上”和泛道德化,但由于它重视人的本性(假设前提)、强调理性的作用(论证工具),故它实际上同数学方法是兼容的。从苏亚雷斯的著述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概念辨析、提出命题、得到推论;格劳秀斯明确提到了数学方法,而普芬道夫则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普芬道夫与斯宾诺莎、洛克同岁(生于1632年),他和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同是数学大师魏格尔的得意门生;同格劳秀斯相比,普芬道夫的数学水平要高得多。1656年,普芬道夫结识了数学家、哲学家、耶稣会成员笛卡尔,也许对他写作《普通法理学精义两卷》(Elementorum Jurisprudentiae Universalis Libri Duo,1660)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1675)类似(该书在形式上几乎就是数学专著,完全由假设、命题、证明等组成),《普通法理学精义两卷》基本由定义、公理(源于理性)和Observations(源于经验)组成。在其更具学术影响力的八卷本《自然法和国家法》和作为该书摘要版的两卷本《论义务》中,普芬道夫放弃了数学形式,但论证思路明显留有几何学痕迹。
哈奇逊和斯密是苏格兰人,而苏格兰学者大多具有浓郁的经验心理主义和情感主义特征,他们重视历史(多数学者有史学著作,但不同于德法史学,而是强调个人和心理,所谓“推测的历史”或理论历史),强调个人的心理和情感。同苏亚雷斯、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相比,这些苏格兰晚辈继承的东西很多,但同时亦融入了上述苏格兰学术传统。哈奇逊的著作,不少地方似乎是心理学著作,斯密著述中亦大量体现出了心理学分析。如斯密认为,“一个体系就是一部想象的机器,发明它是为了在想象中把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不同活动和结果连接起来”(《天文学史》,格拉斯哥版“斯密全集”第三卷第66页);“哲学可视为一门致力于想象的艺术”(同上,第46页)。显然,在进行“想象的艺术”的研究时,欧洲大陆前辈提供的方法并不足够。心理、经验、归纳、推理等,在斯密那里是相互兼顾、相得益彰的。简言之,就研究方法而言,斯密兼顾了自然法的欧洲大陆传统和苏格兰学术传统,是一种借鉴、综合与提高。
2.研究主题。从名称上看,欧洲大陆的自然法哲学(从经院哲学到普芬道夫)和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似乎存在很大不同,“自然”和“道德”似乎完全是不搭边的两个词。不过,借助于上述“研究方法”辨析,我们可以大致推出如下结论:二者形异而神同,几乎就是一回事!不论是自然法还是道德哲学,其假设前提(逻辑起点)都是一致的,即人类本性(自我保全、关心自己)。不过,在从自己推导到他人时(人类的群居性或社会性),传统自然法更多地借助于人类具有的“理性”能力,而苏格兰道德哲学(以斯密为例)则另外添加了一种人类所具有的“同情”能力(或“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能力”)。“理性”是人类具有的能力,“同情”也是人类具有的能力,它们都是道德中性的概念(在斯密那里,“同情”是一个心理学而非伦理学词汇),这也是欧洲大陆的“数学”或“演绎”方法变为苏格兰学者经验心理主义方法的内在逻辑。当然,自然法和道德哲学的结论也是一样的:符合人类本性(前提)和人类能力(“理性”或“同情”,论证方法)的东西,是正义的。简言之,自然法和道德哲学的起点和终点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论证过程略有不同而已,即在“理性”能力中加入“同情”能力以体现苏格兰学术界的经验心理主义特征。
正因如此,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同“苏亚雷斯—普芬道夫”学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研究主题也是大致吻合的。不妨以哈奇逊和普芬道夫为例(在本文选择的代表作中,只有这二人的著作是相对完整的体系,苏亚雷斯、格劳秀斯和斯密的著述仅是完整体系的一部分)。正如上文提及,普芬道夫的经济理论(第一卷第14章“论价值”)在契约和所有权之后,但二者之间还插入了“语言”(第10章)和“起誓”(第11章)两部分。在《道德哲学体系》中,哈奇逊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做法,即论述完契约后,分别阐述了“语言”和“誓约”问题,然后转向经济理论和“合同”问题。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斯密的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开始,如《塞谬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1755年)、《论语言的形成与语言的特征》(1761年)等。
3.斯密思想体系:基本思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上述“自然法和道德哲学”学术传统,大致勾勒出斯密学术思想的基本思路。分析的起点是人类本性和“自保原则”。斯密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道德情操论》,第101~102页)因此,“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同上,第103页)也就是说,利己人性(关心自己)是逻辑起点,生命(首要原则)和生命的手段(财产)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保障对象。这同“主流”学术传统完全一致。
同自然法和道德哲学传统一样,分析完“个人”后就要研究“社会性”(群居性)。斯密同样认为,“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环境。”(《道德情操论》,第105页)然而,“主要关心自己”的人,如何才能过一种社会性生活呢?自然法哲学借助于人类具有的“理性”能力,斯密则引入了“同情心”。斯密认为,尽管每个人生来主要关心自己,但幸好人类还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想象”(《道德情操论》,第5页)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怜悯或同情。借助于这种能力,每个人就能够设身处地,综合考量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并采取适宜的行为;而适宜的行为,就是美德。
以上是斯密学术思想的基本框架,不论是法律、政治还是经济问题,斯密基本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其法律和政治著作始终没有完成,我们无法了解其论证细节(《法学演讲》过于简略),《法学演讲》的法律学之“绪论”提到了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但“契约”则是欠缺的,相信应是其构思但未完成著作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斯密已出版的作品而言,其法律政治部分明显不如其学术前辈完整(尤其是“契约”、“所有权”和“合同”等)。道德哲学的原理部分,斯密有继承和提高(欧洲前辈过于重视理性,哈奇逊过于重视情感,斯密则很好地兼顾之),更有大的改变。在其学术前辈的论述过程中,“个人”(自己)和“社会”(他人)分得不是很清,且往往先讨论个人再分析社会,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则明确将“他人”(第一、二卷)放在前面,“自己”(第三、四卷)放在后面,这或许是仅仅看完该书前两卷的读者,误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分别基于“利他”和“利己”并存在所谓“斯密问题”的原因。
4.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同学术前辈相比,斯密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国富论》对经济理论的阐述,不仅完全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且不再局限于自然法或道德哲学的框架之内,而且自成体系,对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同时,由于已经具有坚实的道德哲学(或自然法)基础,已经借助于《道德情操论》对人类行为有了全面的把握,因而可以直接探讨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斯密的经济理论仍然具有下述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斯密经济理论同他的道德哲学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其二,斯密论述经济问题的思路和行文风格,同前文提及的自然法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三,尽管斯密的经济理论独立成篇,但仍然留有不少传统体系的特征,尤其是他的分工交易理论。
具体而言,同“主流”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是,每个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但他要同别人打交道,故而需要同他人进行平等互利的交换(或许是自然法哲学的“理性”能力,或许是斯密所说的“设身处地”的“同情”,斯密在《国富论》中称其为“互相交易”的倾向)。人类交换的倾向引起了分工,而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对分工交换的进一步分析中,斯密依次探讨了货币问题(便于交换)、价值理论(度量交换比例)、供求理论(交换机制)、分配理论(反馈机制)等,由此构成了《国富论》第一篇的基本内容。除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人数(就业)对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而就业增加同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有关,此为《国富论》第二篇主要内容。按照苏格兰学者的惯例,斯密接着研究了经济史(第三篇)和经济思想史(第四篇),最后探讨了政策问题(主要是财政问题)。以上就是《国富论》的大致思路和主要内容。
分工交换理论上承道德哲学(或自然法),下接价值论等后世熟悉的经济理论,是斯密经济理论的一大特色。并且,它也是斯密非常看重的内容。不论是《法学演讲》、《〈国富论〉早期草稿》还是《国富论》,分工交换理论均占据重要位置;其中,《早期草稿》中只有“分工交换”部分给出了详细内容(超过一半篇幅),其他理论仅仅给出了提纲。遗憾的是,在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学者再提及“分工交换”理论:古典经济学直接从“价值论”入手,新古典经济学更是直接从“价格”和市场供求着手。这或许同上文提及的西方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关:分工交换,作为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无需再费口舌。但对于我们则有所不同:分工交换理论看似简单,但蕴含了自然法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如果无视这些“基本功”,专注于西方成熟社会的数理模型,则不仅仅是学术的懒惰,而且容易沦为“畸形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的帮凶。我们将在后文的启发与思考部分做进一步探讨。
六、启发、思考与借鉴
正如前文所示,斯密的学术思想是对经院哲学“主流”(尤其是“自然法”及其苏格兰变体“道德哲学”)的继承和自然发展。为了便于理解和简化分析,下面拟以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这种学术传统、但被后世经济学界忽视的斯密“分工交换理论”为例,结合“主流”学术传统的若干特征,对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1.脉络回顾:学术界为何忽略这一学术传统。自然法哲学经过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的阐述、阿奎那的综合和系统化,在苏亚雷斯、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那里逐渐从经院哲学转变为近现代学术思想,并在现代社会秩序形成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被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作为思想利器(不过,其论证思路过于简略,有关思想有些发挥过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法律政治、伦理道德等趋于完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走向实证主义。尤其是19世纪之后的法学界,逐渐抛弃了自然法传统,认为难以检验、不可证伪和“泛道德化倾向”的自然法,会以“道德污染法律”。然而,二战时期的实证法学面临巨大挑战:流亡英国的法国政府和纳粹占领下的伪政府,谁颁布的法律具有效力?纳粹政府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是否合法?是否正义?是否值得遵守?如此等等。经过如此人类浩劫后,战后法学界开始了反思,自然法重新获得了一些学者的重视。
就经济学而言,重商主义时代的经济理论并不是“主流”学术界的关注对象,重商主义(以商人和政府官员为主体)本身亦谈不上系统的思想体系和完整的经济理论,有关著述更多的是充斥市面或“献礼”之类的小册子。斯密实现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融合,但其学术思想体系更多地同上述“主流”学术传统、而非重商主义有关。在《国富论》中,尽管斯密几乎用了整整一篇(第四篇)分析重商主义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主张,但他最多将重商主义作为批判的“靶子”,重商主义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和系统经济理论并没有太多内在的逻辑关系。
事实上,斯密之前的“主流学术”和现实经济基本不搭边,但这种学术与实务“两张皮”所造成的问题却越来越多。经济学巨著《国富论》,更多的是斯密面对这种窘境,忙里偷闲,给财经界人士补补课而已。当然,经济理论只是斯密学术思想中的“毛”,其“皮”则在《道德情操论》和他念念不忘的关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的未完成作品中(参见《道德情操论》,“告读者”),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应对斯密学术思想作更完整的理解。
斯密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学术”坚定地走向了实证主义道路,全身心地致力于探究市场机制的内在运行机制(古典、新古典等)、市场失灵与恢复市场活力的手段(如凯恩斯主义)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既没有必要(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其市场经济的法律政治制度、社会伦理道德等基础已相对完善,制度、习俗等已大致实现了相应变革)又没有兴趣(热点难点问题已由市场经济构建转变为市场经济运行)梳理斯密的思想渊源(对经济学而言,斯密本来就是外来者“插足”,虽然涉足较深、较广)。因此,西方经济学界(尤其是英语世界)对这种学术传统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对于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我们来说,有些基础性的工作不能完全忽略,无视市场经济的上述基础而直接“拿来”成熟经济体的理论模型“套用”中国经济,无疑是学术上的一种偷懒行为。
2.理论思考: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同任何经济制度一样,市场经济制度同样包含人类的各种行为,而经济行为则是众多行为中的一种,并成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按照苏亚雷斯至斯密的学术传统,人的本性是“关心自己”和“自我保全”,但同时也同其他人打交道。经济行为也是如此,按照斯密的分工交换理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不可能全部由自己生产),“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国富论》,第13页)。不过,“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同上),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其对生命维持手段(财产、商品与服务等)的需要,不能主要依赖于别人的恩惠或施舍,而“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同上,第14页)。
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人们平等自愿互利的市场交换。现代社会同样存在救济、施舍和赠与等,但只有平等自愿的市场交换才是市场经济中占支配性地位的经济行为;不仅如此,由于斯密把“交换”视为人类的天性,故这种经济行为是正当的、是正义的;正因为是正当和正义的,有关契约应该得到尊重和履行。当然,相对于“生命”,财产、交换、契约等“生命的手段”仅享有“次级优先权”。在发生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形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行为才可凌驾于“市场交换”行为之上。
按照苏亚雷斯至斯密的学术传统,“生命”处于第一位,生命的手段(健康、名誉和财产等)处于第二位,其他社会性规范、文化习俗、政策法规等处于第三位。目前,我国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争论,乃至对食品安全、医疗、教育、保障房、“富二代”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的争议,多同人们对“优先次序”的不同认识有关。
另外,斯密的分工理论还有一个重要但学术界关注不多的问题,此即《国富论》第一卷与第五卷的矛盾:一方面,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增进;另一方面,分工会使人们“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国富论》第,339页),因为它会侵蚀自然法哲学高度重视的“社会性”和“群居性”,而每个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理性”能力或“设身处地”能力,不仅是塑造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同样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蒲鲁东、萨伊和西斯蒙第等均有所提及(但多限于经济学框架之内的分析)。笔者认为,结合自然法或道德哲学传统,深入研究该问题,远较纠缠于“利己”与“利他”更为重要。
简言之,按照苏亚雷斯至斯密的学术传统(自然法和道德哲学)以及斯密的分工交换理论,完整的市场经济应该具有下述特征:(1)“关心自己”是正当的;(2)“理性”或“设身处地”的能力,使人们可以同其他人交往,发生包括市场交换等经济行为在内的各种行为;(3)市场交换必须是自愿平等互利的;(4)市场交换或其他行为需要“契约”,契约应该是自由平等互惠的,并应该得到遵守;(5)生命具有首要优先权、生命的手段拥有次级优先权;(6)政治法律、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应该遵循上述原则,如此才是正当的,才是正义和美德。
3.现实启发:我们能否借鉴?任何学术思想或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社会经济的抽象和简化,均基于现实、但高于现实,均有某种启发的意义、但没有“照葫芦画瓢”的价值。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有长期的实践和成功的经验;既有西方经济理论和发达经济体成熟经验的参考,又有传统习俗的影响。目前,可谓处于关键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需要一个过程,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可能“水土不服”,传统习俗仍然发挥着顽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学术传统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启发或借鉴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客观地讲,脱胎于经院哲学并留有相当印痕的上述学术传统,就其内容而言是过时的,曾一度被西方学术界所抛却。不过,不仅其发展脉络能够给我们以启发,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相对严谨、相对完整的思考,尤其是运用的方法和基本思路,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确实,任何社会都会面临“个人”和“社会”问题,该学术传统从个人的本性(人性)出发,借助于“理性”、“信仰”或“设身处地”,为社会性或群居性生活方式提供基准,并以之推导出法律政治制度、市场交易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等,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在学术上留有创新空间,在现实中易于形成普遍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它兼顾个人与社会(相对强调“社会”)、义务与权利(义务略优先),强调人与人之间自由自愿平等互利的关系,重视生命与生命手段的先后次序,有助于“打造”现代市场经济的“同质”主体(西方经济学中“代表性消费者”或“代表性厂商”等诸多概念正是以此为基础)。
市场经济需要这种“共识”(普罗大众、市场交易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等)。个人感觉,当前中国出现的诸多问题,均与这种共识的欠缺有关。比如,同一种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不同人倾向于采用不同的“标准”,社会热点的网络争论更是折射出判断标准的天壤之别,二奶、小三居然能够博得同情,地沟油、毒奶粉能够问世于人间,贪污腐败者能够安身立命,折射出“共识”的缺乏、“标准”的混乱和“社会性约束”(11)的严重不足;我们需要理解和宽容,但不能没有底线,尤其是那些严重侵蚀“人类社会性生存”的各类行为。按照前文提及的学术传统,只有在生命遭受危险的紧急情形时,人们才能违背平等自愿互利原则;二奶、小三、贪腐者、有毒食品生产者在自身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侵害他人利益,不仅是法律法规所不允许的,更为整个社会舆论所不容。正如普芬道夫(1673/2010)所强调的,“最基本的自然法是:每一个人都应尽其所能地培养和保存社会性”(第83页),而“社会性”需要普遍的“义务”,“义务常被看做是权利的镣铐,它约束我们必须为某种行为。也就是说,义务给我们的自由之马安上了马勒子”(同上,第73页)。
对于这种缺乏“共识”、“标准”混乱和“社会性约束”不足等现象,上述学术传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系严密性和逻辑一致性。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诸多共识同这种学术传统有关。问题是,中国具有五千年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基础、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传统能否应用于中国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华夏文明中,“儒墨道法玄”博大精深,儒佛融合并形式化后长期占据“主流学术”地位,同西方“主流学术”存在极大的不同;马克思不仅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排在“封建”之前,而且是在“古代”之前,显示出东西方社会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管怎么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半封闭式生活生产方式造成了“人格化”交易行为:广大乡村的自我治理、乡里乡亲相互帮忙代替市场化交易、亲情血脉优于契约化交易和普适性法律等,同“古罗马的世界主义”和“基督教面向每个人的感召”观念存在巨大差别。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救济型社会中,这种观念习俗、伦理道德及其衍生的法律政治制度等,尚不存在多大问题。一旦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即以“契约化的”、标准的、每时每刻发生的“交易行为”为主导的经济体系,不同群体拥有不同“标准”的文化传统,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凝聚各方面力量、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经济成就。不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已经触及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共识”已不足以面对有关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亦难以完全满足系统性制度建设需求。医疗、教育、住房、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均要求一种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共识”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上文提及的学术传统,虽然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存在差异,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学术借鉴:经济学是否讲“道德”?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一度掀起了“经济学是否讲道德”的争论,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是手段,不能以手段取代目的,经济学家不能对贪污腐败、道德沦丧视而不见;反对者认为,术业有专攻,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客观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好本职工作,不能越俎代庖,否则很容易“好心做坏事”。双方观点看似各有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争论双方似乎没有认真界定什么是“道德”,有关争论倾向于流于表象,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按照阿奎那以来的自然法传统,人类本性是关心自己,但人类拥有的理性能力(或设身处地“想象”的能力)使得人们可以过一种社会性生活。因此,凡是同“人性”和“理性”一致的行为,都是正义的,都是美德。例如,腐败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维持生命的手段(财产),但若理性地或站在别人角度想一想,人人腐败必然同样会伤害自己的利益(不救无钱病人、有毒食品等亦是如此),因而有关行为是违反“理性”的、是不正当的;况且,腐败、不救无钱病人、生产有毒食品等,在杜绝此类行为并不会危及自身生命的情况下,并不享有优先权。在上述学术传统中,“道德”与否源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义务与权利的对称,并不是纯粹外在的或形而上的东西。
自然法并不是现实的法律,它并没有强制力,但它提供了一种标准或“底线”。相对于法学,自古以来经济学皆滞后一步。当自然法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时候,经济学只有几个简单的概念;当法学坚定地走向实证主义的时候,约翰·穆勒还未曾忘记对经济学做“社会哲学”的反思,马克思更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武器;二战后法学界的自然法重新复兴,西方主流经济学却仍在实证主义道路上昂首阔步。不过,在环境生态问题上、在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中、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华尔街责任的争论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这种影子,但远不成体系,亦未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
经济学家应否讲道德?关键看什么样的道德。至少对于尊重生命的“道德”,经济学家还是可以讲的,不能把数理模型(经济理论)和计量模型(检验方法)之外的一切探讨均视为“不务正业”。同时,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或“共识”,现代市场经济还是存在一定“底线”的。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这些标准或底线未必可以直接借鉴自然法或道德哲学成果,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界的责任,也是每个人的义务(12),以共同寻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助于“社会性”生活的基本原则、“共识”或“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注释:
①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中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41~42页。
②H.J.Bittermann(1940),"Adam Smith's Empiricism and the Law of Na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4):487~520;48(5):703~734,转载于J.C.Wood(ed.)(1984),Adam Smith: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Croom & Helm,pp.190~235,引文参见第191页。
③例如,Viner(1927)曾对斯密的学术渊源做出过如下总结:“通过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罗马的自然法深深影响了斯密的思想。文艺复兴对个体的强调,沙甫茨伯利、洛克、休谟和哈奇逊的自然主义哲学,苏格兰哲学家乐观的一神论,孟德斯鸠的经验主义,都对斯密有着更为直接、有力的影响。”,参见:J.Viner(1927),"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5(2):198~232,转载于J.C.Wood(ed.)(1984),Adam Smith: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Croom & Helm,pp.143~167,引文参见第144页。
④有关代表著作分别选取苏亚雷斯的《论法律》(De Legibus ac Deo Legislatore,1612)、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1625)、普芬道夫的《论义务》(De of Ficio Hominis et Civis Juxta Legem Naturalem Libri Duo,1673)、卡迈克尔的《〈论义务〉评注》(Supplement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Two Books of the Distinguished Samuel Pufendorf's On the Duty of Man and Citizen,1718,1724)和哈奇逊去世后出版的《道德哲学体系》(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1755)。正如后文分析,这些著述在学科领域、论述主题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学术传承性。
⑤以本文参考的Suárez(1612/1944)为例,该英文节译本的编辑曾指出该书不好译(故而也不好懂)的三大原因:(1)当时的法哲学和神学,充满了形而上的探讨和诸多抽象概念,本已难读。苏亚雷斯学究气十足,务求准确的辨析、严谨的定义和详尽的阐述,让人们更为纠结;(2)苏亚雷斯的著述,只能研读、不能浏览。他善用描述性笔法,别人的观点、自己的观点均做详细阐述,若仅作大致浏览,很容易把别人的观点混同为苏亚雷斯的观点;(3)苏亚雷斯的拉丁文水平没得说,但他不仅用一些“之乎者也”之类的学究词汇,而且经常把西班牙语里的含义用在拉丁文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及的《论法律》即参考该书(没找到其他英文版),书中还包括《为天主教辩护》(Defensio Fidei Catholicae et Apostolicae:Adversus Anglicanae Sectae Errores,1613)和《神学三德论》(De Triplici Virtute Theologica,Fide,Spe,et Charitate,1621)。不过,后两部著作选译得不多,参见Suárez(1612/1944)第647~865页。
⑥“第一个推论如下:尽管我们讨论的权力在绝对意义上是自然法的后果,但它作为权力和政府的一种具体应用,却取决于人们的选择。”(Suárez 1612/1944,p.382)
⑦严格地讲,尽管卡迈克尔1694年从圣安德鲁斯大学转往格拉斯哥大学之后,其工作性质一直就没有变过,但最初还不能称为道德哲学教授。1727年大学改革(主要是苏格兰“四校”)后,格拉斯哥大学才首次设立道德哲学教授职位(“道德哲学”之谓,同自然法特别是普芬道夫《论义务》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故“名副其实”的道德哲学教授,卡迈克尔实际上只有两年而已。至于斯密,他最初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由于哈奇逊继任者托马斯·克雷吉身体不好,他于1751年开始帮克雷吉代课;1751年底克雷吉去世后,斯密在新学期开始时(1752年4月22日)正式受聘为道德哲学教授。1764年初(寒假期间),斯密带巴克勒公爵赴法游学,到达巴黎后(2月13日)才正式辞去道德哲学教授职位,此后就是衣食无忧、但不以稿费为目的的“自由撰稿人”了。
⑧对人的“社会性”(或群居性)存在方式的重视,以及对由此衍生的“义务”的强调,是自然法哲学的一贯传统。如阿奎那(2010)指出,“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第44页)
⑨这是经院哲学和自然法的一贯传统,如阿奎那(2010)亦曾指出,“如果存在着迫切而明显的需要,因而对于必要的食粮有着显然迫不及待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的危险,而又没有其他办法满足他的需要,——那么,他就可以公开地或者用偷窃的办法从另一个人的财产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严格地说来,这也不算是欺骗或盗窃。”(第143页)
⑩西班牙大学者伊西多尔的《词源》(Etymologiae,共20卷),号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前流行于整个欧洲,200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该书英文全译本,苏亚雷斯提及的部分参见第5卷第6条(第117页)“什么是自然法”(Quid Sit Ius Naturale)。
(11)这种社会性约束(如二奶、腐败者会为社会唾弃,很难融入别人的生活圈子)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丝毫不逊色于经济处罚、法律制裁。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1890)中曾指出:“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于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要不了多久,他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转引自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页。
(12)不能认为这种设想是纯粹的“理论冥想”或难以短期实现的“学术幻觉”。以驾车者为例,早期通常并非普通百姓,其“义务”意识并非太强;随着中国进入汽车消费时代,自然法哲学强调的“义务”或“社会性”,在“有车族”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学法规、考驾照的过程几乎就是培养“义务”意识的过程,“有车族”或能成为“市民社会”的突破口(“醉驾入刑”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性“义务”观)。假如官员、学者、市民均拥有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务观”,那么目前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就相对好解决。现代市场经济,并不仅仅由法国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权利”构成,自然法传统和苏格兰道德哲学所强调的“本性”、“社会性”和“义务”(包括个人义务、政府义务等)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市场经济就是畸形的、不完整的市场经济。
标签:经院哲学论文; 自然法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战争与和平法论文; 亚当·斯密论文; 经济学论文; 法律论文; 道德哲学论文; 格劳秀斯论文; 数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