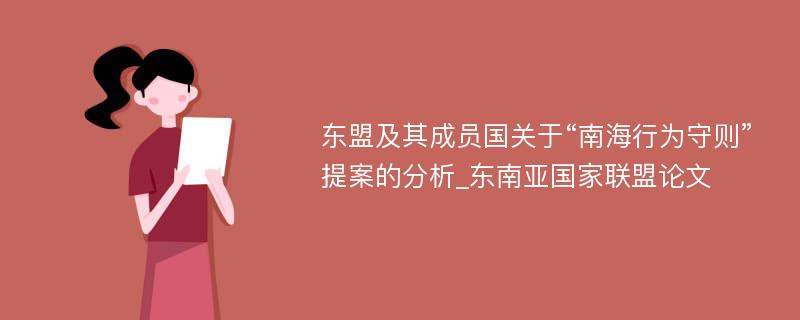
东盟及其成员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之议案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南海论文,成员国论文,议案论文,行为准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7-0086-17 一、引言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宣言》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政治文件,在各国围绕南中国海问题之解决所进行的努力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①但是,《宣言》在性质定位、对象选择以及具体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严格来讲算不上是真正的国际法律文件,法律拘束力的缺失令其在国际法上体现不出预期的影响和效果,②因而《宣言》第10条明确指出,有关各方重申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简称《准则》)将进一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同意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朝最终达成该目标而努力。如今,随着南海争端愈演愈烈,尽快制定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准则》的呼声也日渐高涨。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达成落实《宣言》的指导方针,承诺迈向最终制定《准则》。此后东盟及其成员国更是加快了筹划和制定《准则》的脚步:2012年7月9日,第45届东盟外长会议一致通过了旨在作为未来与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的基础的“核心要素(key elements)”,但会议未就关于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作为弥补,外长们于2012年7月20日发布了东盟对南海“六点原则(six-point principles)”的声明;③在同年9月举行的第6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印度尼西亚向参会的东盟各国传阅了一份《南海行为准则》“零号草案(Zero Draft)”,希望以某种“中立”的身份来推动制定《准则》的谈判,并获得了其他成员国的支持。而在2014年5月10日举行的东盟首脑峰会上,与会各国外长更是前所未有地在共同声明中表达了对南海局势的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平解决争议,尽早完成《准则》的制定。 由此可见,通过制定有拘束力的国际法律文件来解决南海争端,恐怕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论中国政府对于这种进路持何种立场,也不论中方自己所提议案内容将会如何,都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认真分析和解析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有关提案,以便在日后的南海争夺“法律战”中不落后于人或者授人以柄,而更加有的放矢、游刃有余地参与有关国际谈判。为此,本文将致力于从国际法的角度梳理东盟的“核心要素”和印尼的“零号草案”,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法律上的对策建议。 二、东盟“核心要素”与中国的应对 东盟并未从官方层面正式公布其“核心要素”,根据其曾经发布的“六点原则”以及后继发布的相关声明,并对照有关的非官方资料,④大致可以将其“核心要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简称《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各种规定和平解决冲突的国际法原则。这一方面的“核心要素”显然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表示有关各方倡导尊重以《宪章》和《公约》为主要规范的国际法,对此中国显然不会提出异议。 第二,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设立管理和管制相关国家在南海行动的机构,并为避免军事冲突建立合作及争端管理机制。该方面的“核心要素”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解决南海争端的对策,即通过设立某种区域性国际组织来管理有关国家的行为,并要求建立某种争端解决机制。显而易见,这一“核心要素”一旦落实,就将根本改变目前南海争端的博弈态势。因为目前在南海并不存在一个区域协调和管理机构,有关的争端大多是通过当事国彼此之间来交涉,东盟有时候会被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但东盟本身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南海争端交流机制,更不用说对争端起到某种“管理”作用。如果贯彻该“核心要素”的话,那么以后所有的南海争端都将受到该机构所设争端管理机制的管理,当事国的代表在机构内部可以沟通和博弈,但是对于该机构通过正当的表决机制所决定采取的争端管理措施,则应当予以配合。从“核心要素”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争端“管理”是旨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或者通过政治协商为法律解决创造条件,而不是要从法律上将当事国之间的权利义务确定下来;该机构只管各国的行为,不管岛礁主权归属与海洋权益的确定。从有利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促进合作与交流的角度上来讲,这一区域性国际机构的设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可以考虑在充分保障自身主权以及机构内部表决权的基础上,⑤与东盟就落实该“核心要素”进行沟通和谈判。 第三,保障航行自由。其实这在以前一直都不是一个问题,只是最近由于南海问题升温,美国等国才提出中国可能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从未提出过任何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主张。中国一贯认为自己对南海的权利不影响外国船舶和飞机按照国际法通过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飞行自由和安全,在中方看来,这一自由甚至应当不受南海争议的干扰和影响。⑥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水域所主张的权利,均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甚至滥用《公约》相关规定的结果,以分割控制南海水域、遏制中国海权并尽可能多地夺取南海资源专为己用为最终目的,而这些主张都是对久已存在的世界各国在南海自由航行权的侵犯。因为按照这些国家的逻辑,一旦占据岛礁,就要以该岛礁为基点划基线,基线内部是内海,基线外部则依次是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这就意味着有相当的南海海域不能自由航行或者仅能“无害通过”,而更多的南海海域则必须在遵守沿海国规章的条件下航行;或者是把自己占据的岛礁看成一个整体并将其间的水域划为自己的“群岛水域”——这就意味着南海水域的很大部分将由这些国家分割控制,而不能再供世界各国自由航行或者仅能提供与“无害通过权”程度相同的“群岛海道通过权”。⑦由于中方仅仅依据国际习惯主张对南海“九段线”内的水域拥有非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而非依据《公约》主张对该水域拥有某种排他性的主权权利,故而两相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也更加有利于保障南海的航行自由。因此,中方对于该方面“核心要素”不仅不必提出异议,而且要阐明上述观点,要求有关国家不再从事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单边行为。 第四,协议的实施情况将由双方(中国与东盟)监督。该方面“核心要素”提出以中国为一方、东盟为另一方来监督协议的实施,这实际上就是要让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谈判对象与合作伙伴,也就是采取某种特定的双边路径来解决争端。这种做法原本就是《宣言》所避免采用的,⑧但时至今日,马克·瓦伦西亚(Mark J.Valencia)等西方学者力促东盟统一步调迫使中方让步,⑨东盟成员国也越来越倾向于“抱团”与中国谈判,故而若要达成《准则》,恐怕不得不考虑其可能性。更何况,这种进路对于中方也是有利有弊的:弊端在于谈判对手“抱团”后实力得以增强,但好处在于,“抱团”至少有助于阻止单个东盟成员国采取一些不理智的、只会导致南海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单边行动,⑩达成和平解决协议并得到有效实施的可能性将增大、谈判效率也将提高。因此,对于这方面的“核心要素”中方可以适时考虑接受,变多边进路为双边进路,以促成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的达成。当然,中方还是应当首先主张采取“各个击破”的双边进路或者多边进路,在确有必要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再退而求其次,与东盟进行“双边”谈判并签署《准则》;而且中国即使同意由一对一分别谈判或者多边谈判转向与“抱团”后的东盟谈判,也只能与东盟声索国谈判,非声索国不能以任何方式参加。此外,依据2008年生效的《东盟宪章》,东盟的职能是促进成员国在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并强化涉及东盟共同利益事宜的磋商机制,不具备任何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其决议的实施依靠各成员国的自觉;因此原则上来讲,东盟不能代替成员国行使谈判、缔约和划界的职能,东盟所签署的法律文件对其成员国没有拘束力,如果真的“抱团”与中方谈判并签署《准则》的话,那么东盟成员国内部需要达成一项授权协议。 第五,根据不同情况,将基于国际法诉诸冲突调停机构。这一方面“核心要素”提出将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机构。尽管其并没有明确使用“司法机构”一词,但主张“基于国际法”提交“调停”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应该不仅仅具有“调停”的功能,因为调停争端本身并不需要基于国际法来进行,只要争端当事方达成不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协议即可。由此可见,前文提到的东盟第二方面的“核心要素”里面建议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不具备司法性的“初步”争端“管理”机制,其职权应该是在《准则》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处理一些争端的程序或者实体事务,对于《准则》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可以想见对于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争端议题各国很难达成一致并将其写入《准则》)或者《准则》虽然有规定但是争端的发展态势已经超出有关规定所能解决的范围的情况,还是需要一个最终的司法解决途径。从道理上讲,确定一个最终解决争端的司法途径来解决各项南海纷争并无不可,无论是某个专门设立的司法机构,还是既有的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常设仲裁法院等都可以承担此任务。但是,基于《公约》有关海洋权益划分的规定如此含糊不清、(11)中方对于在《公约》层面运用国际司法机构毫无经验、中方因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南海争端故而在法律准备上相对不充分等原因,此方面的“核心要素”对于中方就显得极具挑战性。更何况,中方主张的南海“历史性权利”虽然先于《公约》并且依据国际习惯得以成立,但毕竟从未体现在任何国际条约规范之中,与后来《公约》的规定如何衔接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2)故而在法庭争讼的过程中举证、质证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容易受到作为争端当事方的东盟成员国的挑战和质疑。然而,历史性权利又是中方对南海所提全部主张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不能确认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有效性,中方在南海的多数主张就无法站住脚,司法机构的裁判对中方肯定不会有利。基于此,中方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该“核心要素”,可以出于稳妥的考虑而对此予以拒绝,但也可以在东盟各国表现出足够诚意、对中方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承诺予以尊重的前提下,就此与东盟各国达成妥协。此外,出于国际政治现实的考虑,若在《准则》框架下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则该机构应当与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常设仲裁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一样,不拥有强制执行自身裁决的权力,此项权力仅能由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享有和行使。 第六,中国和东盟以外的国家也可以签署行为准则的议定书。该方面“核心要素”旨在将其他国家也拉入《准则》的法律体系之中,而这个“其他国家”,实质上主要就是指美国。在如今的南海争端中,美国一直是东盟及其成员的支持者,在背后为有关国家提供支持并出谋划策,使得其敢于与中国对抗;美国甚至不时亲自出马,指责中国“妨碍”了南海航行自由。(13)2011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安保协议,并提出要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显然是为了进一步遏制中国、“重返亚太”。而那些东盟成员国虽然在历史和现实上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种种冲突,但是在联合遏制中国这一点上意见一致,所以乐于拉美国来制衡中国,这就是此项“核心要素”出炉的本意。显而易见,这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是一种纯粹从本国利益出发的政治考量,对此中方必须坚决地反对。如果一项《准则》的出台,最终是为了让美国“合法地”干预南海事务,那么这是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而且从条约法的角度来讲,条约的相对效力、即“条约对第三国无损益”乃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准则》只要没有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侵害既存的南海航行自由,与第三国就没有任何关系。《准则》当事方依约处理南海事务,其他国家依据《公约》和国际习惯自由航行,两相各行其是即可,强行拉入第三方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更何况,从缔约程序上讲,如果以中国为一方、东盟为另一方缔结《准则》,那么《准则》本质上就是一项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双边条约,加入双边条约是非常罕见的;(14)若是让美国作为第三方来加入此项双边条约,则不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令人匪夷所思,即便真要这样做,也必须经缔约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东盟提出此项“核心要素”的意思,一方面,东盟在与中国进行《准则》谈判、缔结和实施的时候,就要抱团成“一方”以增强博弈力量,从而形成“中国-东盟”的“双边”态势;另一方面,东盟在《准则》制定之后,又想将其解释成开放性的“多边”条约,以便让美国等第三方能够加入,这显然是前后矛盾、毫无法律逻辑可言的。而即便真的将《准则》算做多边条约,其也属于区域性的、封闭性的条约,并非能够开放给任意其他国家、尤其是无论所辖领土还是海洋均与南海不沾边的国家加入。因此,中方在《准则》的谈判过程中,应当指出该方面“核心要素”在法律逻辑上的荒谬之处,并主张在《准则》中写明其他国际法主体不得加入的条款。 综上,关于尊重国际法和保障航行自由的“核心要素”,中方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可以反过来据此要求东盟及其成员国遵守国际法、不妨碍南海航行自由;关于设立行动监管机构、建立合作及争端管理机制,并由东盟各国“抱团”与中方谈判的“核心要素”,中方可以适时而有条件地接受;关于设立专门司法机构的“核心要素”,只有在东盟各国承诺尊重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前提下才能接受;而对于旨在将第三方拉入《准则》体系中的“核心要素”,中方必须坚决反对。 三、印尼“零号草案”的特点和内容 尽管近一段时期以来东南亚学者非常热衷于《准则》研究并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15)也不乏周边其他国家的学者以个人身份提出《准则》“示范草案”,(16)但并未引发普遍关注。而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和东盟内最大的经济体,其政府提出的正式命名为《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零号草案”,显然更加具有代表性与号召力,故而其出台伊始就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更因其与东盟历来对南海的主张一脉相承,故而随后各东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以此文件为基础与中国展开谈判。(17) “零号草案”在立场上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印尼不是南海岛礁的主权声索者,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解决南海争端,扮演着“诚实可靠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和调停者角色。(18)虽然印尼的这种“中立”地位只是相对而言,(19)但较之纠结于南海岛礁主权争端之中的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来讲,印尼确实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对中方来讲,若准备就制定《准则》进行对话,那么在印尼“零号草案”的基础上与东盟各国展开讨论,也不失为一个相对较好的选择。 (一)序言部分 “零号草案”在序言中做了如下表述:认识到对南海主权和管辖权争端的一项全面而持续的解决将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强调为了在达致分歧和争端得到持久解决的同时维持南海作为一个和平、稳定、友好与合作的区域地位之目标,而进一步在南海促成一个和平、友好、和谐的环境的必要性;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并且依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来处理分歧而不诉诸武力或者武力威胁;回顾各国依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承担的保护南海环境特质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义务;重视东盟以及中国领导人所做出的构建一项《南海行为准则》以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承诺。(20) 将上述内容与《宣言》的序言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零号草案”从序言开始就显示出为南海争端构建法律依据的倾向。虽然《宣言》第4条也曾提及“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然而《宣言》在序言中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下诸如“和平”、“稳定”、“创造条件”之类的套话,加之第4条只不过重复了原本就应当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国际法渊源,故而并未从法律依据上面给予南海争端解决更大的帮助。如今“零号草案”将其位置提升到序言中,一方面彰显了其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更具体的法律表述的出现腾出了空间,因为既然序言中提出了依据国际法的大方向和基本原则,那么在具体条文中给出进一步的规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有的学者认为,“零号草案”序言这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表述是专门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是基于“历史性权利”而非《公约》。(21)言下之意就是,双方基于某种妥协和需要而选择了较之《公约》更为宽泛的法律,或者这是由于中国坚持这样做的结果。笔者认为这样理解是不妥的。因为南海争端乃是国际公法上的岛屿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而非国际私法上的民商事权益争端,国际公法争端所适用的法律是既定的,不存在当事国通过“意思自治”(22)选择法律的问题;诚然,当事国在谈判或者争讼过程可以选择放弃某些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这绝不意味着其能够选择法律本身,否则的话,被视为国际法渊源权威表述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就得加上诸如“当事国选择适用的法律”的规定了。而实际上,第38条第1款所提及的仅仅只是依据国际法,根本不存在当事国选择法律的余地;即便其第2款表示法院可以在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适用“公允及善良”原则判案,也往往只是意味着国际法院若得到当事国授权,则可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判案(这种情况迄今从未出现),绝不是指当事国有权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尤其是排除某些本应适用的法律。基于此,凡是与南海争端有关的国际法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都适用于南海争端,所谓“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都体现在这些国际法渊源之中,不存在主动选择某些国际法渊源而舍弃另一些国际法渊源来构成这些“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问题。《公约》虽然是当今海洋法上的主要渊源,但毕竟只是有关国际条约中的一种,《联合国宪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其他国际条约显然也适用于南海争端,而且《公约》也是对国际习惯的一种编纂,这就意味着《公约》规则本身既是条约法又是习惯法,适用《公约》本身也就意味着适用国际习惯。(23)至于《公约》没有编纂的有关国际习惯,只要未被《公约》所否定或更改,则仍然是适用的——显然,“历史性权利”就属于这种情况,其在《公约》出现之前就已经依据国际习惯而成立且未被《公约》所否定或修改。由此可见,认为南海争端应当仅仅适用《公约》或者当事国有权利指定《公约》作为唯一适用的法律,显然是将国际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张冠李戴之后的结果,是不能够成立的;南海争端适用包括《公约》在内的一切有关国际法规则,乃是其应有之义,而并非为了专门照顾中国的某种利益。(24) (二)主干部分 “零号草案”第1-9条构成其主干部分,对于南海争端及其解决做了一些实质性的规定。 第1条列举了《准则》的指导原则,包括《宪章》、《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从“零号草案”所列的指导原则来看,基本上是跟中国的主张一致的。因为中国是《宪章》、《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宣言》的成员国,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基于国际习惯而非国际条约,所以有必要在此强调国际习惯的指导作用。尽管草案中也留了一个“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尾巴,但是若在此不明确提及国际习惯,则以后有可能被解释为该条所指“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包括国际习惯。 第2条明确了《准则》是一个具有规则导向的、涵盖一整套管理各方行为程序的法律架构,其致力于增强互信、避免冲突、处理和解决争端。第2条的规则导向,中方可以赞同。显然,南海问题若要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获得解决,就只能在尊重和依据国际法律规则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缔结协议。如果不承认规则导向,就意味着当事国只能主要依靠国际政治、军事博弈(24)来处理南海争端,如此一来,对峙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区和平与稳定也将难以实现。尽管博弈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中方单较之东盟及其成员国似乎在综合实力上占有相对优势,然而南海争端涉及当事国众多、形势错综复杂、关系盘根错节,加上美国正有借此机会“重返亚太”之意,故而对于意欲“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纯粹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手段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法律依据研究到位、相关证据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中方可以先尽量运用国际法规则,阐明自身对南海的合法主张并据此在南海实施更广泛、更深入的实际控制,进而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法律战”,在保障本国基本海洋权益的前提下,促进有关争端的和平解决。 第3条阐述了当事国的“基本保证(basic undertaking)”。该条款复述了《宣言》中已提及过的构建信任与信心的承诺、航行与飞越自由、以和平方式解决主权和管辖权争端而非诉诸武力或者武力威胁等保证。然后又加上了三项关键承诺:(1)尊重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2)尊重《准则》以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3)鼓励其他国家尊重《准则》。对于复述《宣言》内容的“基本保证”,中方应予以赞同,但是对于新加上的三项“关键承诺”则要区别对待——无论是尊重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还是尊重《准则》以及相关行动,问题都不大;但是鼓励其他国家尊重《准则》,可能隐含着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南海事务的因素,必须慎重考虑。对此最为稳妥的方法,还是坚持主张“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原则,不在作为封闭性条约的《准则》正文中提及第三方,而将涉及第三方的问题留给《公约》等普遍性的多边条约或者国际习惯来调整。 第4条指明了《准则》的适用范围,其应当适用于南海相关当事方所未能解决的海洋边界区域。但这种表述是非常不清楚的,因为这不仅需要明确什么叫“未能解决争端”,而且需要明确什么叫“海洋边界”。事实上,很多国家在实际控制岛礁及其附近水域额的情况下根本拒绝承认存在海洋争端;而同一块南海水域可能分别被不同的国家主张为内水、领海、群岛水域、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或者历史水域,如此复杂的情况用“海洋边界”这个词是难以对号入座的。因此,还不如明确规定《准则》适用于整个地理意义上的南海,但是不妨碍有关当事国相互之间依据业已达成的国际协议来处理部分南海水域范围内的海洋争端,当然前提是不违反国际法和《准则》且不侵害其他当事国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南海范围内,原则上《准则》都适用;若有特定协议则依协议;若某争端涉及多个当事国而仅仅其中部分国家达成协议,则仅在协议国之间适用协议而在协议国与非协议国之间适用《准则》。 第5条是涉及南海领土主权主张的除外声明,其明确表示《准则》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解释为对任何当事方在南海领土(或岛屿)方面立场或者主张的损益,并重申了依据公认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第5条将主权争端排除在《准则》的体制之外,意欲避开异常复杂和棘手的南海主权争端,(26)是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有利于争端各国绕开敏感争议而在其他领域展开合作,(27)也符合中方历来所主张的“搁置争议”。从这个角度来讲,中方应当予以赞同。但需要指出的是,南海问题的真正解决离不开岛礁主权争议的平息。现在为了促进《准则》的谈判与达成,可以选择暂时搁置主权问题;但若当事各国意欲进一步将《准则》打造为处理南海争端的主要法律文件,则需要在《准则》体制中保留对于岛礁主权争端的关注以及在日后对其加以调整的可能性。 第6条规范了《准则》的实施问题,这其中又涵盖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促进信任”,为此当事国应当避免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军事警戒或者其他挑衅行为;避免在岛屿和地面占据或建造新的设施——无论其当前是否被占领;避免向当前无人居住的岛屿或者其他地面部分移民;避免采取危害航行自由和/或污染环境的措施。另一个部分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国际协定,如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1973年《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等。我们需要对第6条的各个部分做出具体分析。第一部分提出要避免在南海进行军事行动、避免占领岛礁和建造设施、避免危害航行自由和/或污染环境。显然,对于最后一项各国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前两项却是极具争议的。如今周边各国纷纷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若要让其放弃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行动,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东南亚各国真的表态同意此项规定,其诚意也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不能不考虑到在《准则》之外,还有美国、日本等国的海军力量,南海不会由于此项规定而成为非军事区域。对于具备海洋大国潜力的中国,其海军也正在做出突破“岛链”(28)封锁的尝试,而南海则是必经之路。可见“零号草案”想要避免南海军事行动的说法是根本不现实的,如果改为避免军事冲突,则还算具有一定合理性,也具备现实的可接受度。而占领南海岛礁并建造设施,乃是近年来南海争端当事方的普遍行为,若要有关方面放弃这种行为,除非全部争端都得到解决,否则在现阶段是绝对不可行的,故而该项规定应被删去。至于第二部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其主要适用于船舶尤其是军舰的操作者而非国家及其决策者,故而应当被剔除出《准则》而另行议定。(29) 第7条是“监督和报告机制”,规定《准则》应当通过某种东盟和中国一致同意的机制来得到监督,以审查该行为准则的实施和报告。这种程序机制有助于《准则》的充分讨论与实施,中方原则上应当同意。但在具体操作上,中方应当主张明确该机制的监督审查职能,并将其与《准则》所要设立的争端管理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该机制的设立是为了便于日常监管,而不是为了解决争端。明确其职能有助于防止个别当事国滥用该机制来纠缠中方,从而妨碍整个《准则》的落实。 第8条是争端解决机制,建议首先运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若争端无法在东盟框架内解决,则当事方应运用包括但不限于《公约》的国际法所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是,建立一个由各缔约国部长级代表组成的高级委员会来受理已经出现的争端;高级委员会主要采取政治手段解决争端,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但这一切都以争端当事方同意为前提条件。(30)鉴于中国早在2003年就加入该条约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加之高级委员会的运作模式与中方历来的主张并无二致,故而优先采用此种方式是可行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包括但不限于《公约》”的其他争端解决机制,这种说法有可能成为类似于菲律宾对中国强行启动《公约》仲裁程序行为的借口,因此中方可以考虑主张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准则》的唯一机制,或者提出在采用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时候以当事国同意为前提或者不得违背当事国业已依据有关国际法做出的相关管辖权声明。 第9条倡导建立一种以所有相关当事方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审议机制,每五年由成员国的部长级代表们进行一次审议。这显然是借鉴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旨在促进《准则》在成员国之间的良好实施。但是这里面涉及一些敏感而复杂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审议什么?如何审议?审议结果有何效力?显然,这里所审议的绝非《准则》本身,因为《准则》的修订在附则中有专门规定,如此一来,审议的对象就只能是《准则》的适用情况,换言之,就是成员国的海洋政策是否符合《准则》的要求。尽管这跟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缔约方贸易政策为审议对象是一个道理,然而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后果就是审议结果将具有类似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效力,(31)即,审议结果本身没有拘束力,但是其对于成员国海洋政策是否符合《准则》的表述具有某种权威性,能够用来论证成员国海洋政策的合法与非法性,并间接影响政治谈判以及司法裁决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审议(即表决机制)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草案第9条采取了所有相关当事方协商一致的表决机制,显然是比较容易被各方所接受的。但问题在于,基于协商一致的特点,(32)其往往并不适合表决涉及国家公法权益的具体事项,而仅仅适用于非重大的、经济性的、程序性的或者较为原则性的事项。在牵涉自身海洋权益的时候,让南海争端各方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审议有关各方的国家海洋政策,显然很不现实。尤其是要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协商一致不投票的特点,来刻意掩盖其他当事国的反对意见。鉴于南海争端的重要性,中方可以主张采用全体一致的表决方式来审议《准则》成员国的海洋政策,尽管这种表决机制通过议案的难度较大,但是这跟中方倡导主要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南海争端的进路是一致的,而且议案一旦通过其执行力也比较有保障。 (三)附则部分以及未尽事宜 “零号草案”的剩余部分属于附则,主要规定了一些程序性的、事务性的事项,这些事项对于任何有拘束力的条约来讲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具体包括:《准则》禁止保留,《准则》的生效问题,《准则》的修订问题,《准则》的适用期限为无限期,鼓励其他国家尊重《准则》,由东盟秘书长将《准则》向联合国秘书长登记等。 由于上述规定基本上是程序性的,不涉及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故而中方对于其中大多数皆可同意。但是对于《准则》的适用期限则需要再斟酌考虑。因为《准则》毕竟是南海争端现阶段难以解决的产物,其最大作用就是作为《公约》的辅助,暂时缓解争端并为其最终解决争取时间和机会。因此至少从目前看来,无限期适用《准则》并非最佳选择,也不符合南海争端最终定纷止争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可以主张采取类似于《宣言》的做法,对于适用期限不做明确规定。如果以后各当事国一致同意将《准则》进一步发展为调整南海关系的主要法律文件,再确定适用期限不迟。 有学者指出,“零号草案”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条款,包括:(1)《准则》的缔约方范围;(2)共同开发无损争端各方立场;(3)承诺仅为和平目的使用南海水域;(4)承诺采取特定的信任构建措施,诸如对话、预先通报军事行动、主动交换情报等;(5)促进具备实用性的临时安排;(6)承诺不采取任何有损于最终协议达成的单边行为;(7)再次确认《准则》的法律拘束力。(33)笔者也认为,“零号草案”确实存在某些未尽事宜,但是如果有关事宜已经在《公约》、《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文件中表述过,那么《准则》也可以不再列出,而上述“遗漏”条款中的第三点至第六点建议均属于此类情况。至于第二点建议中的共同开发无损争端立场问题,这原本就是各国公认的国际习惯;加之《准则》本身并不专门调整共同开发问题且“零号草案”第5条已经有了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无损争端立场声明,故而也无须特别加入草案之中。而第七点建议主张再次强调《准则》的法律拘束力,则有啰唆重复之嫌。唯有要求明确《准则》缔约方范围的第一点建议值得考虑,即,《准则》究竟是应当以东盟作为一方、中国作为另一方,还是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中国皆为独立的一方?这实际上就又回到了此前讨论过的采取双边进路还是多边进路的问题。联系到上面对东盟相关“核心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东盟的态度是倾向于“中国-东盟”双边进路,而对中国来讲,在与每个当事国均进行双边谈判并“各个击破”的理想进路几无可能的情况下,显然多边进路更值得考虑;何况从客观上讲,绝大多数南海争端都因牵涉两个以上当事方而具有多边性质,只有西沙群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勉强算做双边争端。(34)不过就如今的形势来看,东盟“抱团”与中国谈判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若一概拒绝的话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故而中方也可以考虑妥协。另一个问题是,缔约方范围能否包括除了东盟成员国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联系东盟相关“核心要素”,其确实有拉其他国家干涉南海争端的倾向,而这显然是中方无法接受的,必须坚决拒绝。因此,若要明确《准则》的缔约方范围,那么中方应当坚持主张《准则》是非开放性的区域性条约、缔约范围仅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问题;至于以何种方式缔约,中方虽然应力争采取多边进路,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做出让步。 四、结论 从不具有正式法律文件性质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发展到具有真正法律拘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乃是大势所趋。中国有必要因势利导,积极地参与这一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达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的目的。除了提出自己关于《准则》制定的议案之外,中国还需要专门研究东盟的“核心要素”和印尼的“零号草案”,具体分析其中条文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未来的谈判中明确自身立场,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主张,具体要把握以下内容:哪些议题属于共识,哪些议题属于分歧;有关分歧所产生的动因是什么,是否存在某些特殊的背景;哪些分歧是必须坚持立场不动摇的,哪些分歧是可以妥协的;对某些分歧做出妥协的条件是什么,等等。 总的来说,东盟“核心要素”除了某种将第三方拉入《准则》体系的倾向明显是针对中国且不符合国际法逻辑之外,其他内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接受性。对此,中方要利用现有的与东盟交流的平台,阐明《准则》对第三方无损益的原则,促使东盟放弃上述不合理的倾向。更何况,“核心要素”本身就是基于谈判的需要而提出的,绝非一成不变,这一点从东盟及其成员国并未从官方层面正式公布“核心要素”上就不难看出来。也就是说,东盟自己也在斟酌“核心要素”的最终内容,并且在未来与中方就制定《准则》展开正式磋商之时,也会对不同的“核心要素”采取不同的谈判策略。在中方始终表明可以完全接受或者有条件接收其他“核心要素”,但坚决反对上述将第三方拉入《准则》体系的“核心要素”的情况下,谈判各方同意将此项要素排除在外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唯有如此,制定《准则》的谈判才能进行下去。 至于印尼的“零号草案”,因其基本思路是建立在“核心要素”之上的,故而中方对其的应对思路理当与对“核心要素”的应对思路保持基本一致。“零号草案”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可接受性,谈判各方可以就此讨价还价以求达成妥协。中方所必须反对的“零号草案”内容与“核心要素”中的一样,乃是让第三方染指《准则》以及南海事务,只不过这在“核心要素”里面是一种原则性的倾向,而在“零号草案”中则演变成一种具体的关于缔约范围的规范。因此,中方必须坚持《准则》的缔约范围仅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至于此前各方关注较多的以何种方式缔约(“中国-东盟各声索国”双边进路、“中国-东盟”双边进路、“所有声索国”多边进路)的问题,尽管谈判各方对于不同的方式有着不同的接纳程度和优先顺序,但为了促成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可以进一步加以探讨。 截稿:2014年5月 注释: ①周洋:《略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困境与应对》,载《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第28页。 ②尽管中方在《宣言》的谈判和签订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并对《宣言》促进中方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寄予厚望,但之后的现实却是令人遗憾的,《宣言》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在《宣言》中所释放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回应。“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的各方承诺基本上是一纸空文,而有关各方在《宣言》签订之后的所作所为,更是与上述承诺大相径庭。参见罗国强:《多边路径在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及其构建》,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第96页。 ③Michael Lipiu,"Cambodia Says ASEAN Ministers Agree to 'Key Elements' of Sea Code," Voice of America,July 9,2012; Michael del Callar,"DFA Chief:ASEAN Agrees on Key Elements for Code of Conduct in West PHL Sea," GMA News,July 11,2012; ASEAN Annual Report 2012-2013,Jakarta:ASEAN Sectetariat,June 2013,pp.27-28. ④ASEAN,"Statement of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on ASEAN's Six-Point Principl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uly 20,2012,http://asean2012.mfa.gov.kh/? page=detail&article=312&lg=en,登录时间:2014年6月16日;ASEAN,"ASEAN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EAN Statement & Communiques,May 10,2014,http://www.asean.org/news/asean-statement-communiques/item/asean-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the-current-developments-in-the-south-china-sea,登录时间:2014年6月16日;Carlyle A.Thayer,"ASEAN's Code of Conduct(Unofficial)," Thayer Consultancy Background Brief,July 11,2012,http://zh.scribd.com/doc/101698395/Thayer-ASEAN-s-Code-of-Conduct-Unofficial,登录时间:2014年6月16日。 ⑤显然,国家加入国际机构是出于主权国自愿,而不是要损害主权,如果要成立某种南海管理机构,那么笔者认为,至少中国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以及“九段线”水域的历史性权利是不能损害的;同时,如果该机构采用一国一票的多数表决制,那么就容易形成中国为少数的一方、东盟为多数的另一方的不利局面,因此该机构的表决机制必须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东盟由诸多小国组成的特殊性,采取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加权表决制”,赋予中国更大的表决权。 ⑥2011年7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出席第18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指出,南海争议与南海航行自由是不同范畴的两个问题。作为国际航道,南海的航行是自由的,航道是安全的,区内外国家都是受益者。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对亚洲及周边国家尤为重要。中方与有关方一道,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南海航行自由现在不会、将来也不应被允许受到阻碍。参见《杨洁篪接受中外媒体联合采访:智慧解决南海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7/26/c_121719994_2.htm。登录时间:2014年5月20日。 ⑦比如,南海东南端的马六甲海峡历来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国际航道,自由航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为借着海洋法发展之机捞取利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曾经于1971年11月发表联合声明,声称马六甲海峡不是国际航道,但将允许“无害通过”。上述行径因遭到多数国家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⑧《宣言》的磋商是以中国为一方、以东盟为另一方进行的,其签署也是由这两方在2002年金边东盟首脑会上完成的,这导致有的学者据此推断中国倾向于“中国-东盟”的双边进路。参见Rodolfo Severino,"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Pacific Forum CSIS,August 17,2012,p.1。但也有学者指出,中方所主张的是与有关当事方进行双边谈判,并反对在《公约》框架下以多边方式解决,而且现在中方也开始与东盟成员国进行多边的沟通。参见Sanae Suzuki,"Conflict among ASEAN Member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DEJETRO,September 2012,p.2; Shin-Ming Kao,Nathaniel Sifford Pearre and Jeremy Firestone,"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Analysis of Existing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43,No.3,2012,p.284。笔者认为,《宣言》的签署是由中方代表和每个东盟国家的代表共同完成的,而且《宣言》在开头就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盟各成员国政府……谨发表如下宣言……”因此,不能认为《宣言》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双边文件,更不能认为中国希望以“中国-东盟”的双边进路解决南海争端。中方主张的双边进路是分别与其他当事国进行双边谈判,中方并非一概反对多边进路,而是反对在《公约》框架下进行多边谈判(因为《公约》不能为历史性权利提供法律依据)。 ⑨Mark J.Valencia,"The South China Sea:Back to Future?" Global Asia,July 15,2011,p.6. ⑩比如,菲律宾于2013年1月就与中国的争端单方面申请国际仲裁,越南于2014年5月在西沙海域干扰中方石油钻井平台作业并纵容国内民众举行反华游行(之后游行演变为骚乱)。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上述强硬立场是短视的,并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区域紧张和不稳定;如果接受合作,各方可能都是“赢家”,然而目前的方式只能产生“输家”。参见Sam Bateman,"New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Whose Sovereignty over Paracels?" RSIS Commentaries,No.088,2014,p.2。 (11)《公约》只是在第15条沿用了《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12条第1款,并在第74条和第83条规定,海岸相向或者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但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这两条规定缺乏具体性、未提及任何划界方法,且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公平解决”意思极为模糊,故而对解决具体问题毫无用处。参见Yoshifumi Tanaka,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Oxford:Hart Publishing,2006,p.47。 (12)有学者指出,中国早在《公约》制定前半个世纪就正式公布了南海U型线(“九段线”),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性权利是不可抹杀的。东盟国家无法真正依据国际法驳倒中国的主张,但同时《公约》也不能被用来支持中方主张。由此就需要解答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公约》是否是解释“九段线”的唯一国际法规则?第二,在包含国际习惯在内的普遍国际法上是否存在支持“九段线”的规则?第三,《公约》所确立的海洋权利能否推翻其制定之前业已存在的权利?参见Zou Keyuan,"China's U-Shaped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visited,"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43,No.1,2012,pp.28-29。 (13)参见《美官员:美日关注南海航行自由欲在东亚峰会展开探讨》,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9/2019739.html,登录时间:2014年5月20日。 (14)李浩培:《条约法概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390页。 (15)任远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问题研究:现状与走向》,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43页。 (16)比如,印度学者拉德罕曾于2012年5月12日提出一项名为《促进南海和平稳定与互信及确保和谐的行为准则》的“示范草案”。参见Dr S.D.Pradhan,"South China Sea:A Model Code of Conduct," May 12,2012,http://www.globalindiafoundation.org/SOUTH%20CHINA.pdf,登录时间:2014年5月20日。 (17)印尼“零号草案”对《宣言》、东盟“核心要素”及其六点原则颇为倚重。参见Carlyle A.Thayer,"South China Sea in Regional Politics:Indonesia's Efforts to Forge ASEAN Unity on a Code of Conduct," Paper for 3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on Managing Tens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CSIS,Washington,D.C.,June 5-6,2013,pp.2-6。 (18)常书:《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演变》,载《国际资料信息》,2011年第10期,第26页。 (19)印尼未对南沙岛礁提出主权要求,但由于其北部所属的纳土纳群岛(Natuna Islands)毗邻“九段线”西南端,其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东北端与中国“九段线”内“历史性水域”在西南端有部分重叠,加之印尼对于中国“九段线”及其相关权利一直持有异议,故而两国仍然存在海洋划界争端。参见Ian James Storey,"Indonesia's China Policy in the New Order and Beyond:Problems and Prospect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1,2000,pp.157-158。此外,印尼在该地区曾经与马来西亚和越南存在争端,但已经分别于1969年和2003年达成了大陆架划界协定。 (20)Marl J.Valencia,"Navigating Differences:What the '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and Doesn't Sat)," Global Asia,Vol.8,No.1,2013,pp.72-78. (21)Marl J.Valencia,"Navigating Differences:What the '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and Doesn't Sat)," pp.72-78. (22)“意思自治”是国际私法上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理论,是指合同当事人具有选择合同关系准据法的特殊权利,合同由合同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 (23)伊恩·布朗利就曾断言,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法律概念并存于习惯法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创设的法律制度之中。参见伊恩·布朗利著,曾令良等译:《国际公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24)有国外学者对此攻击道,尽管历史性因素应当被考虑,但中国无法证明自己迄今为止在一个确定的区域内持续有效地行使了权力并且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故而其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不符合国际法上的标准。参见Florian Dupuy and Pierre-Marie Dupuy,"A Legal Analysis of China's Historic Rights Clai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7,No.1,2013,p.141。然而,正如现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高之国在列举“厄立特里亚-也门仲裁案”以及“大陆架案”的相关裁决后所指出的,历史性权利是受到国际司法机构的承认与尊重的,南海争端的解决应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尊重历史既对南海区域人民的生活至关重要,又是全面解决南海僵局的现实需要。参见Zhiguo Gao and Bing Bing Jia,"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History,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7,No.1,2013,pp.121-122。 (25)博弈的基本形式包括零和博弈(谁是懦夫)和变数博弈(囚徒困境),博弈论被频繁地应用于外交决策、军备竞争、合作与冲突、战争与和平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26)正如有观察人士所指出的,南海争端中的领土主权问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法律、技术和地质因素,构成冷战后该区域的最大安全问题,也是东亚的主要冲突爆发点之一。参见Lalita Boonpriwan,"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Evolution,Conflict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ICIRD,2012,p.1。 (27)有学者指出,目前在南海业已实施的区域合作存在于海洋环保和海洋科学研究领域,可能实施的区域合作存在于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领域,而在主权争议方面则不存在合作。参见ShihMing Kao,Nathaniel Sifford Pearre and Jeremy Firestone,"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Analysis of Existing Practices and Prospects," pp.288-291。 (28)所谓“岛链”,是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特定概念,它既有地理上的含义,又有政治军事上的内容,其用途是围堵亚洲大陆,对亚洲大陆各国特别是中国形成威慑之势。“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第二岛链”北起日本列岛,经小笠原群岛、硫黄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延至哈马黑拉马等岛群。 (29)Marl J.Valencia,"Navigating Differences:What the '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and Doesn't Sat)," pp.72-78. (30)《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15条规定,在通过直接谈判无法达成解决的情况下,高级理事会将负责处理争端或局势。它将建议有关争端各方通过斡旋、调停、调查或调解等适当的方式解决争端。高级理事会将参与斡旋,或根据有关争端各方达成的协议,参加调解、调查或调停理事会工作。在必要的时候,高级理事会将提出防止争端或局势恶化的适当措施。第16条规定,除非征得有关争端各方的同意,否则前面一条不适用于解决争端。参见《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3-08/12/content_5318793.htm,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31)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国际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尽管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在国际层面上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得到有关国家的普遍接受和广泛采纳。参见Tim Hillier,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London: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1999,p.240。 (32)协商一致,是指成员国之间通过广泛的协商,不须经过投票,对某些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做法。协商一致程序避免了硬性投票表决可能带来的弊病,维护了国家间主权平等和民主协商决策等原则,表现出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灵活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其仅仅意味着没有异议而不一定是所有有关方面都真心同意;其允许有关各方对决议提出保留或做出有利自己的解释;其尚未形成一套固定的广泛适用的具体规则。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页。 (33)Marl J.Valencia,"Navigating Differences:What the 'Zero Draft'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Says(and Doesn't Sat)," pp.72-78. (34)Rodolfo Severino,"A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p.1.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南海九段线论文; 南海争端论文; 日本南海论文; 南海局势论文; 东盟外长会议论文; 南海美国论文; 南海军事论文; 准则论文; 国际法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