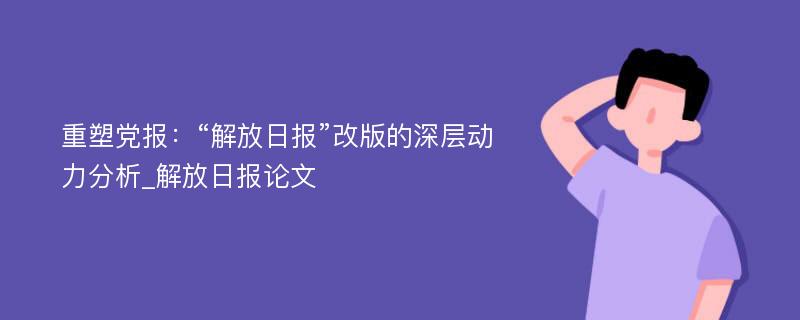
重塑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深层动力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日报论文,党报论文,探析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09)04-0105-07
编辑记者是一个报社的活的要素,报社每一次任务的执行,政策的落实都是从他们开始的。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这些人经历了怎样的思想认识过程,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怎样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他们改进业务有何作用,他们的心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都是需要分析的。本文从改版本身对当时报社的记者,即改版运动最直接的参与者自身认知的转变,深入探讨记者内心对改版工作的认知过程,并揭示转变背后的动因。
整风运动与报纸改版
由于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了解《解放日报》改版的缘由,必须厘清整风运动的背景。关于这个问题,陆定一在《在延安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里已经讲的非常清楚。《解放日报》的改版和整风运动是一体的。陆定一说,“解放日报的改版,是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风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那时候军权已经不在王明集团手中,但是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中,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有大权”。从陆定一的分析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整风运动必须将这些“还有大权”的“重要成员”整肃干净。也就是自1931年王明来到苏区后,曾经拥护过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① 及其思想,到这时是要彻底清算了。
当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党内还担任重要职务的,除王明外,还有张闻天,博古和何凯丰等。②1940年5月,王明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上发表题目为《向毛泽东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毛泽东压倒王明路线,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而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彻底失败。③ 张闻天也在这期间交出了大权,“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在第一次“九月会议”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以为我好好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④1942年1月26日,他外出考察一年多。曾经力挺过博古的何凯丰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虽是这样在1941年的9月到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也作了检讨。而博古自遵义会议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延安的时候,已经降为《解放日报》的社长了。博古的检讨是在1942年的3月31日。但王明和博古在当时延安的青年和干部中间还是很有影响的,被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18∶1的男女比例中,很多女青年的择偶标准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思想”。因此整风运动就是要彻底清除他们的错误思想,降低他们个人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
这时的博古就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所以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的改版分不开,也是有这层关系的。
报纸的领导、编辑、记者
解放日报的领导层
改版前《解放日报》的编辑记者领导层主要有博古,杨松,余光生,这三个人都有海外工作的背景,其中博古和杨松是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在批判王明路线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身份和经历(特别是博古)都被认为曾是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
从各自的经历中,博古是上海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到苏联学习4年,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团中央书记,⑤ 并在1931年9月到1935年间担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41年5月为《解放日报》总编辑。虽然博古从来没有利用《解放日报》反对过毛泽东,“在博古控制下,报纸既对国民党政府的攻击比较节制,也对统一战线并不格外坚持。同样,也避免促进毛泽东发动的土地革命和其他运动”。⑥ 博古是中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虽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自遵义会议后不断上升,但“博古的任命显示出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并没有丧失殆尽,也许他的任命有潜在的意图,即非公开的制衡毛泽东的权利”。⑦ 因此说这份报纸受到了莫斯科的影响并不为过——版面和标题,内容的选择等。每天一期的社论关注国际问题,国际和国内的消息在二版上的地位是同样的。当扩版为四版后,第一版基本为欧洲战场的消息,一些国内消息和社论;二版为欧洲战争新闻,三版为国内新闻,四版上半部为边区新闻,专栏在下半部分。
那博古自己对整风运动和针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是怎么看的呢?从一些细节上看,他对这次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运动,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应该说准备不足,因此在丁玲因为小说《在医院中时》受到批评,要做深刻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说,“不必,等等看”;后来《三八节有感》而再受批评时,博古还走到她身边陪她坐着,并问“怎么样”,令丁玲在回忆中深受感动。⑧ 但博古自己的思想压力还是有的,“毛主席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初期他感到压力很多,表现很沉闷,不愿意向我们暴露思想情况”。⑨ 经过大家的帮助和自己的思想斗争,3月31日改版前的大会上,继张闻天、王明、凯丰后,博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杨松的经历比博古要简单得多,自1927年(20岁)开始就到苏联学习,到1935年(28岁)回国,38年到延安工作,41年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病逝。但杨松也是和王明有联系的,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时,杨松是作为陪同人员。因此,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让杨松任报纸的总编辑,他似乎感觉到工作的难度,对昔日的同事张仲实说,“我对于外国的事情,还可谈几句。对于本国情形,的确一点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对党实在没什么用处”。⑩ 因此他十分勤恳,在报纸创办一个月内,写了29篇社论。
余光生为美国铁路运输和公路建设硕士,在美国从事共产主义事业,1939年底回延安,任张闻天的秘书,《解放日报》创刊后,为报社国际版主编,杨松病重期间任代总编辑,后任总编辑和社长。在同事杨永直的眼中,他是一个“为人活泼,身上颇有点‘稚气’”的领导。到陆定一到报社主持工作后,他就不再担任主编职务了。
普通的工作人员
一般的编辑记者主要有几个来源:原来《新中华报》的工作人员——其中有编辑、记者,也有校对,发行,印刷等后勤人员,其中一半以上还是从事印刷、发行、校对和排字工作的;原来新华社通讯科及其所属人员并入了报社采访通讯科(简称采通科),以及文协、青委、鲁艺、马列学院等单位的人员。这些人员中,有过专业新闻训练的相当少,他们“多数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虽然抗日救国的大方向、大目标是一致的,但每人的头脑里也都程度不同地有那么一点自己的小天地、小算盘;有人在国统区做过新闻工作,对新闻业务比较熟练,可是新闻观点却同党中央机关报的要求有距离;有人刚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爱好文艺,想当名作家,分到报社,不安心工作;还有人来自边区政府或部队等实际工作部门,总觉得‘洋领导’,‘洋学生’看不起‘土包子’”(11) 等等,新闻素养比较差、思想观念差距也比较大。
杨永直,第二版编辑,因为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过两年,在报纸创办前被胡乔木同志指名到青委办的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讲“新闻学”,杨说,在上海“我主要的精力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没有多少时间专门学习新闻课程。胡乔木同志鼓励我,他说我毕竟是科班出身,这在边区还很难找。我们党要培养新闻工作人才,就要学会写新闻,写通讯,写政论,办报纸,办通讯社,这都很重要”。(12) 虽然他并没有说自己讲的是什么内容,但一定不是改版后确立的党的新闻理论和政策。所以说当时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党的高层领导——非王明集团成员,对如何办党报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思路,不然不会将一个大学中学习过“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学生放在干部培训班上当老师。这些人基本没有或少有编辑大型党报的经验,因此对待如何办好这份报纸的问题上,苏联的《真理报》和中国的《大公报》成为学习的榜样,更何况,博古和杨松对苏联的《真理报》还是相当熟悉的。
总之,改版前党报的工作人员中,领导者是在苏联工作或学习过的,甚至政治上犯过错误的人;基层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多少办报经验和专业知识,大家都是在学习中办报。这样的身份预示着在马上到来的整风改版中,其思想和业务都将经历巨大的变化。
改版前对报纸的认识
政治上认可,但业务上急需提高
因为《解放日报》的创办就是为了“统一全党的舆论。那时正值皖南事变以后,各根据地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的同志按个人的理解和意志发表意见,有的言论违反了党的政策和中央指示精神,例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对马日事变的估计,等等。在此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改进新华社的工作,一切党的政策,都通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同时,党中央还发出了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纠正那种无政府状态。《解放日报》一开始就在贯彻党的政策,统一全党思想上,起了积极作用”。(13)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为报纸的发刊词上可以找到例证,发刊词对“团结”和“一个战争”的强调,是当时党的政策的核心。(14) 黄旦教授研究认为,党报在这个时期的作为是符合党的要求的,“所有都合乎程序按照党报的要求进行,无论是其组织隶属关系还是内容,没有一点跨越‘雷池’之迹象,也未见丝毫异议,直到1942年2月”。(15)
自报纸创办到改版前,报社内部经常开编委会会议,编辑部会议和副刊版、国际报道等专项会议,对报纸思想业务进行批评总结。从试版当天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出,当时党报的工作者对报纸的自我评价是,“优点是政治上强,材料丰富,消息正确。缺点是有错字,标题不清,排版不正”。(16) 评价显示了除政治方向上外,党在创办大型日报上物质基础和经验都相当缺乏,其看到的缺点仅仅是报纸出版中最基础的问题,党报力量相对薄弱,这一自我评价基本上延续到1942年的2月。
从1941年5月16日创办到改版前的二十多次编委会会议上,党报工作者对报纸自身评价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内的社论和消息少。这个问题在5月28日的报纸开办后的第一次编委会上就提出了,以后在9月9日,1942年1月13日的编辑部全体会议上被再次提出,“国内栏消息来源困难,内容不充实”;“大家对国内消息注意不够,国内社论亦少”等。这个问题的出现和当时报社人员不足,专业水平低,以及边区通讯条件简陋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当时采通科在条件艰苦的季节,有时一天要写5,6条新闻才能补足边区版的版面,“由于报社的编采人员无人参加西北局的会议,又没有基层通讯员,地方党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很难知道,所以,很难写出受群众欢迎的好新闻”。(17) 博古甚至说,“报纸能坚持每天出版就是最大的成绩”。虽然做过多次人员上的调整,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第二,博古的国际路线对报纸的影响产生了作用——他指出当时宣传的重点是苏德战争。(18) 但报纸改版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后,这个一开始被认为是新闻业务上的不足,就变成了思想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成了报纸党性不足最重要的证据。
其次,对国际时事和党的政策了解甚少,要加强政治和政策的学习。报纸出了13期后,报纸再次开会,博古提出要多研究当时国际形势,杨松就此提出每周开一次时事研究会的决定。在以后的类似会议上,博古曾就苏德战争,国际局势,中国局势等问题发表看法,同时提出关于国际问题的社论和专论首先“政治上不犯错误”,其次要注意翻译上的统一与准确,要中国化,提高社论质量,“力戒夸夸其谈”等。从这些评价和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编辑记者注意更多的是业务领域的问题,比如如何翻译,如何立论,如何加强社论的战斗性等,并没有认为下苦功夫提高的国际问题报道是党报战斗性不足的表现,是运动中所要整顿的对象。恰恰相反,认为组织更多的国际问题通讯,把国际电讯翻译好,是从政治上到业务上的明智之举。这其实可以理解,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关系到整个二战的胜败,和中国的抗战事业紧密联系的,很多人对战争的前途表示担忧,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及时报道和评论这一大事同样重要。因此加大对这个战场的报道是符合党的抗日政策的。
第三,党报的工作人员当时认为自己最不足的是业务不精,而不是党性不纯。如编排技术上需要改进;标题下工夫不够;译电科和编辑部之间联系不密切,有时使译文的字句被编辑部改错;自采稿件质量差,报道内容不新;本市通讯员和外勤记者在某些方面有冲突,互相抢消息;版面缺图,不够活泼;编排不够雅致,头小尾大等等。这些批评意见比较容易理解,属于可以修正的业务层面。另外,从历次编委会上,我们可以看出,业务的讨论地位比较突出,显示出博古、杨松对提高党报从业者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重视。
报社政治方面的问题开始提出
1941年9月9日(决定王明彻底失败的“9月会议”期间),在报社内部会议上,博古根据4个月来报纸的情况,第一次指出,“办报在政治上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但了解情况不够,掌握政策不紧”,“没有把我们的报纸变成战斗的报纸,报道的东西分析性、指导性差,很少反映党的政策,对读者具体帮助少”(19) 等属于政治层面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宣布报纸作为党的斗争工具是不合格的,报纸需要改革,即扩版。虽然有这样的意见,但在惯性的作用下,报纸工作依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20) 也许博古的注意力放在了自身的政治生命上,没有深入的理解报纸在反映党的政策方面到底该如何突破;也许是因为报纸依靠自身的力量达不到党所要求的效果(当时还不是全党办报),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这次扩版从后来看是在原来的老路上越走越远了。也就是说:由2版到4版,一二版为欧洲版,三版远东,四版上半版为边区,下半版为副刊;而且总编辑杨松直接负责一二版。从这个安排上,看出报纸的领导层还是没能体会到中央对报纸的希望和企盼,继续着原来的“错误”。问题归问题,做法是做法,为什么博古还把报纸做成这个《真理报》在边区的翻版,很难说他是政治上的故意,只能说并没有现成的改革路子可供模仿,以往的排版惯性,如所有的关于中共领导人的报道,均放在第三版,(21) 因此虽然从内容上如何加强报纸对共产党的报道,从版面编排形式上依然没有突破。
尽管报纸内部的人员对报纸的不足有各种批评,但来自政治上的压力还是由博古等领导同志在顶着,而普通的记者和编辑感受到的还局限在新闻专业领域方面,属于业务范畴内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提高党报工作人员的业务还是很有帮助的。
业内人士的评价
《解放日报》虽然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整风开始后对报纸的关于党性不强,主观主义、党八股等指控,但它在党内的地位毋庸置疑,这份报纸对当时各根据地的新闻宣传起了榜样的作用。陈克寒回忆说,虽然他那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对《解放日报》的情况不太清楚,但“那是我们学习的报纸,在根据地的影响很大”。(22) 当时在《边区群众报》作主编的胡绩伟也说,“在《解放日报》改版时,我认真学习了改版的有关文件,……但是对改版前的《解放日报》,我并没有看出它的缺点,还以为中央级的大报就应当是那种格调。在学习了《解放日报》改版文件以后,看到改版后《解放日报》的报纸面目大变化,才算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党报作为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道理。”(23) 从以上的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大部分党报从业者,包括中央边区和地方上的编辑,都认为《解放日报》的样子就应该是那样的,其被认知和认可的程度是很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报社人员黎辛和吴文焘回忆,当时博古不仅经常把重要社论交毛泽东审阅,而且他和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贯彻始终”,(24) 而胡乔木更直接说,“解放日报一直是毛主席管的,改版前也是他管的”。(25) 因此针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意见并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严重。陈克寒更是说,“《解放日报》一开始就在贯彻党的政策、统一全党思想上,起了积极作用。……《解放日报》在总的宣传方针上是正确的,在党的新闻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新闻业务和新闻理论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发展”。(26) 因此,报纸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和认知程度是比较高的。
谁改变了党报工作者的思想和业务
当党关于整风运动的明确指示以及对《解放日报》必须整顿的各种言论出台后,从报纸的业务上看,缺乏经验的报社记者编辑,甚至包括博古等领导者都没能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党所期待的“完全的党报”,这个让人无法揣摩的词汇以及各种缺乏实践指导的指示精神一时之间让党报工作者的思想和业务处于无法突破的尴尬境地。不过一些细节使他们开始找到党报改革的突破口。
毛泽东的直接干预
虽然毛泽东从《解放日报》创办开始就对报纸进行管理,但并不意味着报纸出现错误,要由毛泽东来担任,恰恰相反,如果这个报纸出现了“不完全党报”这样的问题,是报社的工作人员没有体会中央的意图,要自己完全承担责任。事实如此,1942年初,来自中央的批评意见以及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批评意见开始在报社内部传达,引起大家的不安。毛泽东第一次专门针对《解放日报》的批评性意见是1942年1月24日,其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决议同意,即“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论、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需坚决废除党八股。并决定由中央各部委(中央同志在内)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广播新闻消息一件,写社论或专论一篇。”(27) 当时毛泽东已经掌管中央,因此他对报纸的不满对报社的触动相当大。两天后(26日),博古要求报社编辑记者们“从明天起搞自己的新闻,各版都出去跑跑,听取反映和意见。通讯科要报道党的消息”。(28) 30日,博古再次决定将党的消息交给三版专门登载,以示对党的消息的重视;紧接着,一系列的改革行动开始出现,2月13日,决定减少国际消息,从每版抽出一人组成评论部,但版面仍维持现状。应该说,博古自己以为减少国际消息的登载以让位于党的消息,同时将国际问题的评论减少,加强国内问题和党的政策的宣传能让中央满意,因此发表了社论《展开宣传工作上的新阵容》来强调这个问题。20日,编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报纸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这个意见为报纸工作者减轻了很多思想上的压力。3月3日,报纸决定出版“党的生活”专栏,加强对党的宣传。正在这时,3月9日,13日,报纸的“文艺”栏连发两篇被毛泽东批评的文章,一个是《三八节有感》,一个是《野百合花》。这两个到目前为止还颇有争论的案子,使报纸自1942年初就已经开始的改版成绩化为乌有。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被目前确认为改版的序幕。3月31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解放日报》改版前的座谈会,延安各负责部门同志和作家70多人的出席,说明毛泽东提出的要“全党办报”是要切实落实了。
博古的几次检讨
除了1942年3月31日博古在改版前的全体大会上对毛泽东、党内各部门及作家的检讨外,7月31日博古在报社的内部会议上公开表示,“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的东西”,(29) 彻底转变了自己的办报实践。9月5日,陆定一传达毛泽东说,报纸“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时,博古和余光生再次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博古的几次检讨,在报社内部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博古还是工作认真,丝毫没有犯了错误之后的消极情绪和抵触情绪,对同志们的安慰和鼓励很大。田方回忆说,“我们根本看不出博古同志像某些同志犯错误后那种精神不振的忧郁状态,而是精神振奋地带领我们改正错误,开创工作的新局面”;(30) 陈坦也说,“博古同志逐渐解除了顾虑,愿意与我们交心,节假日还经常一块打扑克,对他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后来党中央召开了‘七大’,博古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的心情更好了,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我们编委会内部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了”。(31)
改版后,博古和中央派来的新主编陆定一一起管理报纸,表面上博古还是社长,陆定一为总编辑,但实际上陆定一已经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虽然很多回忆文章刻意强调二者之间的亲密合作,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两个人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最后在社论问题上爆发出来。博古对自己新闻本位思想的最后一点坚持表现在一天一篇社论上,这被认为是对《真理报》的效忠,也是对《大公报》的模仿。自8月21日陆定一正式接替杨松作主编后,博古还是要求他每天写一篇社论。陆定一对此坚持不下来,到12月份,矛盾无法协调,闹到毛泽东那里,最后毛泽东支持了陆定一的意见。陆定一自己说,“我对博古说:第一,我不做杨松;第二,我的社论十年以后还要经得起审查,不能像大公报的社论只管二十四小时。他对我也没办法,没有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调和路线。”(32) 从口气上看,地位略低一点的陆定一并没有对博古全面服从,而毛泽东的支持更使陆定一的意见和思想被大家重视。
莫艾的报道计划
社论的问题因为有各机关领导同志同时负责,似乎压力比较轻;但关于“大后方通讯少”的问题,是比较难克服的。正在这时,4月18日的编委会上,莫艾提出了自己的采访计划,“找一个斯达汉诺夫的典型来动员春耕”。(33) 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成为拯救《解放日报》新闻报道的突破口。4月30日从吴满有开始,中国的劳动英雄就开始不断在报纸上出现。
对吴满有报道的意义超过了报道本身,在缺乏“党新闻”的特殊时期,能用这些既生动,又贴近现实,并有政治意义的报道充实报纸的版面,在业务上意义重大。以后像吴满有这样的劳动模范成为报道的主体,在1943年上半年出现的各种劳模有600多名以上。(34) 莫艾的报道计划,从业务上拯救了《解放日报》,也从政治上提升了《解放日报》对党的事业的贡献。因为这些劳模的宣传对当时经济水平低下,急需经济支持的边区政府提供了非常成功的促进生产的宣传功效。
在一系列的成功报道和令毛泽东满意的宣传之后,9月15日,毛泽东写信给凯丰,说,报纸有望成为完全的党报。有了这些思想和业务上的铺垫,在一系列关于党和党报文章的作用下,1943年7月,记者们开始了报社内的整风。刘白羽回忆说,自己写了7遍悔改书,最后连小时候欺负保姆小姑娘,揪她小辫子的细节都挖掘出来,思想上真的作了彻底的改变。也许正是这样的思想上的洗礼才使的报社编辑记者彻底从一种思想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说的“在延安岁月,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取得了双重功绩,既抵制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紧身衣,也塑造了新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确,报纸的改版彻底使报纸摆脱了“先国际,后国内”,“一天一篇社论”,亦步亦趋紧跟苏联《真理报》等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等的错误,但由此形成的国际新闻不能上党报头版头条,拒用国外通讯社稿件,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宣传为主的报道模式,一直成为新的“教条主义”被继承到现在。
[收稿日期]2009-03-23
注释:
① 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
② 凯丰(何克全)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从莫斯科回国的,他随之进入中央苏区,接替顾作霖为“少共中央局”的书记。
③ 1941年,受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镇压的米夫的影响,王明被共产国际怀疑,因此共产国际不再支持王明。2007年11月17日,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纪念延安整风运动暨《解放日报》改版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杨奎松教授的发言。
④ 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
⑤ 1930年底,米夫(苏联中山大学校长,作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代表)来华。米夫此次的任务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前台,控制中共中央的权力,以保证“百分之百”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实现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王明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是团中央总书记,这一届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就是后来被称为王明集团的主要成员,博古在王明秘密赴苏就任共产国际代表后,成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这就是王明左倾路线和宗派主义的最初来源。
⑥ The Last Battle:Mao and the Internationalists' Fight for the Liberation Daily Patricia Stranahan The China Quarterly,No.123.(Sep.,1990),pp.521-537.
⑦ The Last Battle:Mao and the Internationalists' Fight for the Liberation Daily Patricia Stranahan The China Quarterly,No.123.(Sep.,1990),pp.523。
⑧ 见《秦邦宪乘飞机遇难 丁玲作〈我们永远在一起〉》,中华新闻网,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70827/14302206.html
⑨ 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9页;“我们”是指陈坦、陆定一和余光生等编委会人员。
⑩ 张仲实《悼杨松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7日。
(11) 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12) 杨永直《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日子》,《解放日报》2004年10月28日,新华网转载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4-04/28/content_1444564.htm
(13)(22)(26) 王敬《陈克寒同志谈延安〈解放日报〉》,《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19、118、119页。
(14) 发刊词中说,“本报治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摩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
(15) 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再审视》,“纪念延安整风运动暨《解放日报》改版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上海。
(16) 这是对1941年5月15日试版的评价。见王凤超,岳颂东的《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26辑,第126页。
(17) 田方《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新闻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61页。
(18) 虽然从很多材料上看,都说博古当时是代表党内的国际主义派,即王明路线的重要代表,但并没有材料支持报纸上国际性报道占主导地位是他借此对抗毛泽东的主观故意行为。本论文的这一观点和Particia Stranahan一致。
(19) 见王凤超,岳颂东的《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33页。其实在1941年7月10日召开的编委会上对6月20日社论《评德土友好协定》有错误,但也是从业务的角度上讲的,并没有上升到1942年4月1日《致读者》里说的“对苏德战争前夜德土协定的估计上有主观主义”。
(20) 这是在1942年1月30日的编委会所提意见。
(21) 而这是符合当时党的政策的。
(23) 胡绩伟 《胡绩伟自述》(29)http://56cun.myanyp.cn/5/articles/070504064912671.aspx?z=456226&m=858000
(24) 黎辛《博古,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黎辛、朱鸿召《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哀》,(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年,237页。
(25)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27)(28)(29)王凤超、岳颂东《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39、140、160页。
(30) 田方《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回忆在陕北的采访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月,第23辑,61页。
(31) 陈坦《回忆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1月,第22辑,第19、20页。
(32) 陆定一《陆定一谈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总第8辑,7页。社论不一定每天有,这个原则是1942年12月7日的编委会上提出的,同时提出要写时评的主张和建议,并在当天的社论位置刊出了第一篇时评《日寇海军消耗于所罗门》。
(33) 王凤超、岳颂东《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26辑,147页。斯达哈诺夫是顿巴斯煤矿区的年轻汽钻掘煤手,苏联“二五”期间全国劳动模范,他在1935年8月30日夜间,用6小时挖了102吨煤,超过定额13倍。苏联在“二五”计划期间,全国掀起了称作“斯达哈诺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人们纷纷学习他的榜样,生产革新手接连打破劳动纪录的浪潮席卷了全国。
(3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67页。后来有人批评众多报道中有“假劳模”,“假英雄”现象出现。
标签:解放日报论文; 王明论文; 延安整风运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真理报论文; 毛泽东论文; 陆定一论文; 整风运动论文; 博古论文; 杨松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