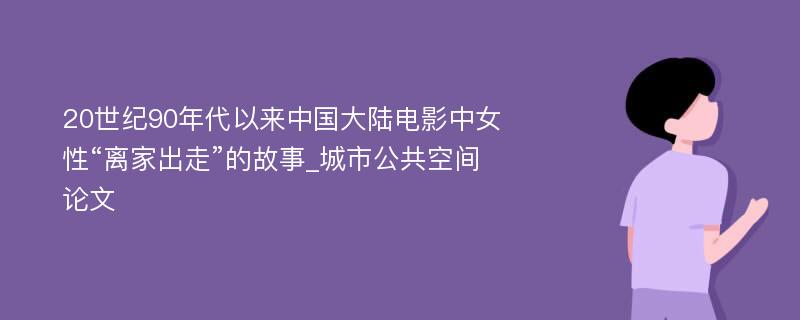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电影中的女性“出走”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故事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告别家庭空间的历史
从父系社会确立,家庭父权出现的那一刻起,女性由于生理、经济等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便走向家庭,并囿于家庭。自从弗吉尼亚·伍尔夫要求一个“自己的房间”以来,女人要求有属于自己空间的声音就不断涌现,于是对家庭的反叛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这种建立在对家庭反叛基础上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女性在传统父权制文化和历史的遮蔽下对自身解放道路展开的一场有力的现代性探索。
在旧中国,女性的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她们的人生舞台在家庭。到了1930、1940年代,也只有极少数女性参与社会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社会生产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得到着力塑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婚恋自主,把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爱情和婚姻的主要基础;勤俭持家,一切听党的话。影片《李双双》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了传统的家庭空间,表现出她爱家爱丈夫爱孩子的基本性格特点,但发展生产、恋爱、看戏等日常生活细节中,李双双善良、热情、倔强、泼辣、坚持原则等性格特点决定了正是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造就并支持着李双双在家庭中的突出地位,从而说明“家庭”的作用只是日常生活的加油站。女性的勤俭持家,是为了使家庭成员能保持较健康的身体和较稳定的情绪,以轻松的心情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
1980年代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塑造的女性的解放含义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农村妇女来说都不再重要,相反,这个时候的典型年轻女性将端庄、贞节的少女形象、少妇形象融合在一起,成为传统和乡村生活的符号象征。典型表现是谢晋电影中温良、执着、坚韧的女人们,和谢晋影片努力用家庭用母性抚平个体男性在公共空间中的伤痛的情节剧范例。①纯真少女的形象从《黄土地》中的启蒙仪式开始,常常处在外来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萌动着离开父权制家庭的勇气。外来者往往是先进意识形态的男性代表,如《黄土地》中的顾青、《哦!香雪》里的“小北京”等;或者是代表现代新女性形象的知识分子,如《青春祭》、《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里年轻的女大学生。而更多其他新时期电影,如陆小雅的《热恋》和《红衣少女》、鲍芝芳的《金色的指甲》、王君正的《女人·TAXI·女人》和《独身女人》、董克娜的《女性世界》等,自觉地将一种性格外向、有胆识、举止优雅、崇尚消费主义、性感和性解放、大踏步走向公共领域的年轻女性形象塑造出来,并将她们从城市家庭的妻子、母亲、女儿、女友等角色中解放出来,送往公共领域的传统的女性工作岗位,如秘书、护士、图书管理员、接待员等。同时,这些女性形象也走向了在传统家庭视域中的少女,并用潜移默化的力量鼓励她们走出家门,增加她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对文明的渴望。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传统家庭中出走,成为了农村年轻一代的主题。在这一庞大的迁移潮流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当然,一部分女性继续在农村生活和劳作,如《香魂女》(1992)中的扮演着母亲、情人、妻子三重角色的香二嫂,带领大家种菜致富的新媳妇喜莲(《喜莲》)(1996)。其余的农村女性则选择在喧嚣中,一批批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很快,这种变化在彭小莲的《女人的故事》(1987)中卓见成效。主人公小风与另外两个农村姑娘来到城里做买卖,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与熏陶下,她们发现和认识了自身的独立性。在经济上,她们获得了自主,在精神上,她们也追求到人格的完整。
自古离开家乡四处奔波的人,几乎都是男人。女性印象则与私人空间紧密相连,女人一生最大的移动很可能就是出嫁。对女人来说,婚姻标志着一个基本的断裂:离开出生的家庭、自主性的丧失、来自亲戚朋友支持的丧失以及在几乎一无所知的婆家的权威下担当起新的繁重责任。经典的女性转移话语,往往将离开父权制的家庭转化为进入夫权制的家庭。夫权家庭是父性之家的转换性表现。家庭对于女性来说已然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她姓他的姓,属于他的宗教、阶级、他的生活圈子、随着他的工作而迁徙。在家庭中女性由子一辈的女儿身份衍变为妻子的角色,由父/子(女)的血亲关系变为男/女的爱欲关系,父亲之家被转换成他人之家。到了1990年代,在一些农村,留在城市已经成为年轻女性在离开父权制家庭和进入夫权制家庭之间的空隙中期待的一个通过仪式。这里,流动女性对父权家庭的否定和对他人之家的否定,都是一种公开直接的行为,即使不能将之称为一种运动,那么,无论如何它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浮出水面提供了契机。从1990年以特区打工妹为主角的《特区打工妹》,到1994年周晓文导演的《二嫫》、1996年的《紧急救助》,再到1998年的《玻璃是透明的》、2002年的《惊蛰》、《西施眼》、2004年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以及以后的《今年夏天》、《红颜》等等,以从家庭出走的流动的女性或从乡村流动到城镇的女性为主角的影片,越来越丰富。
迁移流动打破了农村女性单一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使她们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她们积累着对城市生活的正面与负面感受和经验,并融进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建构。但女性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艰难与困惑,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变得日益严峻。一方面她们为争取解放的、现代的年轻都市女性的主体位置而奋斗,渴望像她们一样拥有金钱、性、权利、快乐和自由。另一方面,她们更容易堕落为各色三陪女、傍大款的小蜜和街道经验中的妓女。
二、商品化“私有”空间中的“新人形象”
1990年代以来的城乡流动,加上乡村和城镇郊区工业化的巨大增长,在某些方面模糊了城乡之间的区分。然而在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增加,这种区分甚至变得更加尖锐。对于来到城市里的乡村女性来说,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对这些女性的肯定性的价值判断,对理想的价值形象的构建,并使之成为观察和评价现实生活的标准,也成为后来者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目标。这种正面意义上所设定的人的价值形象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人形象”,打工妹也需要自己的“新人形象”,电影在这一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进城不久,这些灵慧、勤劳的姑娘经过锻炼,很快成为城乡文化结合的一代新人。她们走出乡村田野时,带着一身土气和力气,当她们归来时,不仅带回了资金、信息、技术、市场,还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和家乡人所不具备的开拓市场经济的本领”。②《女人的故事》(1987)里三个农村女人毅然出门挣钱,尽管她们在公共汽车上遭人嘲笑,但最终她们在经济和精神的各个层面都重新认识了自己。《安居》(1997)里的农村姑娘珊妹,是儿子为晚年的阿喜婆请来的小时工,她陪伴着处于城市的空间焦虑和情感焦虑的阿喜婆回乡扫墓,进入山村,找到山坡上的榕树,陶醉在故土人情之中,在土语民谣的抚慰里,在珊妹质朴的感情中,阿喜婆终于找到了诗意的栖居。《特区打工妹》(1990)是第一部明确以打工妹为主角的电影作品,建构了女主角田杏子的自我价值实现过程,其历程类似于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中的女主角赵小云,从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也塑造了春花这样在现代化中的堕落者和牺牲品;其后还有主旋律影片《爱情傻瓜》(1993)中的陕北女青年、《我正年轻》(1996)里的环卫工人等等。当然,在《玻璃是透明的》(1998)中的“王小姐”、“小丫”等从过上好日子,有着与上海人一样正规的户口这样不高的起点出发,最终达到自己和城市人一样具有“崇高”的生活欲望,并占领这个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杨亚洲电影《美丽的大脚》(2002)、《泥鳅也是鱼》(2005)等在深刻性、复杂性上都达到了更高的高度。而王全安《惊蛰》(2003)中的关二妹则将这一形象上升到了令人震撼的高度。
保姆、家政人员、服务员、流水线上的女工角色是这些作品中常见的形象。相对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她们所对应的空间:工厂、车间、“家”、雇主的寓所、集体宿舍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空间是商品化的“私有”空间。所谓“私有”说明了空间属于私人领域及空间的属他性,而流动女性并不占有这个空间,她们与这一空间的关系是商品化的,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在这一空间中存在下去。家政服务所处的空间显然是最典型的“私人领域”——家庭,但这个私人领域是属他的,对于流动主体而言是商品化的。她在其中的劳动表现决定了她的价值。有时她被要求得更多,除了单纯的劳动,还需要有高尚的品德,质朴的情感和足以感动他人的人格魅力。一方面,流动女性通过劳动与服务在此空间立足,另一方面,作为交换,她们被这一空间文明化和现代化。
《泥鳅也是鱼》里的泥鳅在社会变迁中,卖了家里的地和房子,比任何人都坚决地离弃了乡村生活来到了城里。她如此信赖这个新的环境。在她工作和生活的三个重要空间里,真正属于城市的只有她做保姆的雇主家。她的临时住所或者是民工聚集的更像是村庄的简易集体宿舍,或者是火车道旁待拆的简易平房,而工作空间或者集中在如同一个混乱村庄的人头攒动的建筑工地,或者上面才是城市车来攘往的大街小巷的地下管道,在性质上基本与城市无关。在雇主家,一个中产阶级女性集中了城市的所有符号:高傲、情感冷漠、苛刻、只会用金钱说话、在理解什么是快乐时显得幼稚可笑,与泥鳅卑微的爱情相比,她的情感世界一片空白;与共患难的男泥鳅相比,她对待丈夫的感情更加冷淡。影片对女泥鳅几乎在任何私有空间都会遇到性侵害进行了重复表现:在包工头男泥鳅说了算的车皮上;在弥漫着男性欲望的大殿里;在病入膏肓应该已经丧失了性能力却突然春心焕发的雇主谢老的家里;在讨要工钱时被应该已经阅女无数的建筑老板欺负……这表达了女性流动与私有空间之间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时空中移动,乃是移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转移了时空位置,身体本身也改变了”。在流动女性没有得到“自己的房间”之前,她面临的将一直是商品化的私有空间,这一空间与性联系在一起,时刻成为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被逐渐典型化为城市的威胁。这也是其实并不性感或者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泥鳅,来到城市以后要勒紧裤腰带的原因了。但是女泥鳅的正面价值或者说新人形象的设计使得她每次遇到这种侵害都会义正词严,这些场景重复出现而又重复失败,提高了女泥鳅对于流动女性如何对待爱情的认识高度,同时也完成了人的尊严和女性尊严的提升。
商品化的“私有”空间给流动女性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在这里她们有时受到保护,有时又遇到侵害,但最终她们都得以成就。在这样的空间中,她们被描述成不是威胁国家与都市社会的罪犯,也不是与城里人相比“落后的”下等人,而是城里人需要仿效的发展与自我发展的新人“英雄”。她们率先大胆地走出封闭的乡村田野,在陌生的都市生活中受到文明的洗礼并增长才干,从而唤醒了田埂上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引导他们进入城市的大课堂,接受市场经济的磨炼和培训。她们为家乡带来的重大效益在于:她们给家乡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并为家乡锻炼出一批敢于搏击市场风云的生力军。她们的行动同样也给家乡一个重要的启示,外部世界天宽地阔,走出狭窄的田野就能改变一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要依靠自己去创业、去奋斗。
三、私密化“公共”空间中的“妓女形象”
主流意识形态对从家庭中出走、进入城市的流动女性的“新人形象”的塑造,不能掩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即原本最纯洁无知的乡村少女在城市里的堕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在带来社会繁荣和经济飞跃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平衡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调节时,人们就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条件去片面争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当这一现象具体到农村女性时,相较于乡村而言,城市的文化特征对于体力绝对信赖的摆脱,在相当程度上给女性提供了同男性平等的契机。智力的炫耀颠覆了体力的垄断,暴力不再轻易构成对女性的威胁。当夏娃们开始告别乡村时,她们不再逃离自己的伊甸园,而是要去寻找自己的伊甸园。也许就是在这一刻,性别之间的长久较量终于爆发了。在男性的乡村那里,诚实和劳作构成了全部生活简单而又本真的逻辑;但在女性的城市那里,计谋与享乐使生活的逻辑变得复杂且浮华。除了工作局限于保姆、清洁工、服务员等低收入范围内的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选择了用身体在这次迁移中转变命运。于是,一些女性为摆脱贫困将婚姻当成交易,或为满足虚荣心甘做富人的“二奶”,或为改善物质生活放弃尊严从事色情服务等。
在第六代的作品中,出卖身体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得到了较多的表现。《苏州河》(1997)里的美美、《小武》(1997)里的梅梅、《扁担姑娘》(1997)里的阮红、《安阳婴儿》(2001)里的婴儿母亲冯艳丽、《哭泣的女人》(2002)里的王桂香、《租妻》(2006)里的王莉、《邮差》(1995)里小豆跟踪的卖淫女、《盲井》(2003)中的小城妓女等等。乡村少女成为妓女,这是女性“出走”故事中一个突出的悖论。1990年代以来表现底层悲悯和底层力量的影片中,妓女身份被作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资源充分甚至过度加以利用,尽显“现实非法性”的特征和“女性被剥削”的秘密。从空间角度来讲,《苏州河》里的妓女美美在酒吧里做“美人鱼”表演的水族箱,成为女性在流动空间中一个代表性的象征——公共空间的私密处。她的白皮肤和黄头发符合了全球化的想象,她每天在巨大的水族箱里浸泡着,展示着,尽显了人成为商品的利弊。
公共空间,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室外雕塑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容所涉及的一个术语,一般指市内的公园绿地、广场街头等场所。但是对于文化研究和文艺批评而言,公共空间还涉及其他形式的公共场所,如餐厅酒吧、体育场馆、影剧院、店铺、街道等场所。公共空间的隐秘场所,③是指对公众开放的空间的隐秘之处,它既是隐秘的也是公众的,常人不便或不能涉猎,但这一场所又向公众开放。
娼妓文化与城市想象之间的联系在1930年代通过街道经验展开,在1990年代的又一个轮回里,随着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消费型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公共空间的私密处展开。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大量的类似歌舞厅、旅馆、美发厅、酒吧等各种娱乐场所以及这些公共空间中的隐秘角落。在这里,流动女性体现了城市的诱惑、不稳定、匿名及晦暗不明。这些特征将女性的面孔、身体与都市的灯火交错并置,而城市黑暗一面的转喻往往对应于一种特定空间:公共空间的“私密”之处,以表现她们的弱势地位和不安全感。在公共空间的“私密”处,女性极易受到身体和性暴力以及其他形式恶习的伤害。这些场所中性服务往往与其他服务一起被出卖和消费。《盲井》中的小城妓女虽然不是影片的主角,却是影片中真正的无名者。其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一个肮脏的小旅馆里当嫖客的场景,在视觉上的冲击力几乎到了女性观影者可以接受的极限。唐与宋嫖娼的场景隐喻着性、身体的快乐,对唐与宋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不能够享受多样文化生活的底层而言,嫖娼几乎是发泄欲望的唯一手段和得到快乐的通道。在这一表现得如此真实的场景里,两个妓女的身体和尊严被挤压到了最底层,她们和在鱼缸里的美美以及许多无名者一起成了纯粹展示和消费的对象。
周蕾曾经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对下层人的表述与色情写作共享着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同样信赖于对他者的某种客观化和镜式反映……如果色情作品的兴奋点可以描述为类似于‘越下流越好’的话,那么对下层人的表述的兴奋点或许可以描述为类似于‘被社会剥夺得越彻底越好’。两种兴奋类型都信赖于对象所缺之物——就是她的强烈需求(或者我们应该说她的堕落),以及她邀请读者主动填充这一需求的过程。”④可以说,下层人身份和被色情化的可能性叠加在一起,使得年轻的农村女性而不是男性成为对一个都市媒体大众来说更吸引人的纯粹消费对象。
一旦来到城市,外来女性很快便意识到她们作为外地人标志的那些东西,尤其是服装、发型、语言和行为举止。她们努力地试图抹去这些标志,如学说普通话、剪掉头发、购置时尚用品等。她们以为这样便会显得城市化。虽然首饰、衣服、发型等与财富无关,但却可以作为外在形象改变的一种道具,传达了农村进城女性对这些装扮物的欲望和踏足公众场合的欲望,实际上这并不能带来流动农村女性身份的实质性改变。这正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流动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传统女性在家庭中的生活可以总结为“一个屋子的故事”,许多人在这个屋子里住过,祖母、母亲、女儿,她们的生活方式是由各种实物以及如何看待、摆放这些实物所决定的,她们的生活方式是由祖父、父亲、兄弟如何看待、摆放这些实物的方式所决定的,由此女性成为空间的产物,那么,在今天,对于这些从传统家庭中出走,需要重新塑造边界世界的流动女性来说,情况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得更糟。女泥鳅和美美的故事代表了流动女性无论在商品化的私有空间,还是在公共空间的一个个私密的封闭式的小包间里,上演的依然是愈演愈烈的与性有关的故事。离开家庭的牢笼,面对新的流动情景,出走的女性依然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屋子,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女性再一次顺从地接受了被物化的地位。
《我的美丽乡愁》(2002)中那个离开餐馆后的胖妞对着城市上空大声喊:“我要回来!我要买房!我要买车!我要找一个帅哥结婚。”一方面面临着城乡差距,一方面面临着性别差距,在大多数的文本中,对性别差距的弥补被凸现,其表现方式就是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和妥协,从而改变身份以弥补城乡间的差距。这一凸现性别的方式,实现着一种对阶级话语的转移,或者说把阶层的流动具象化为性别场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的阶级想象。她们按照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行事,利用外流的时机扩展自身,有的也摧毁自身。她们充分运用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则,并寻求改变这些规则,使这些规则对她们有利。永恒的“农民精神”死去了,同时灭亡的还有建立在谷物混作基础上的家族制和家长制以及女性永恒的地母形象。
注释:
①母亲的情节剧范例:母亲拒绝随同中产阶级的丈夫去往某地,而选择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她的女性气质表现得越来越过度。
②[澳]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米雅·当娜凡(Mia Donovan)的启示,加拿大当代年轻女摄影艺术家米雅·当娜凡曾在蒙特利尔举办影展“玉体横陈”,展示她对公共空间隐秘处的探索。参展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蒙特利尔的影视脱星、夜总会的脱衣舞女之类的“性工作者”。
④Chow Rey,Love Me Master,Love me Son:A Cultural Other Pornographically Constructed in Time.(周蕾:《爱我,主人,爱我,儿子:在不定时间内色情建构的一种文化另类》)in Boundaries in China,ed John Hay,243-256.London:Reaktion Books。
标签:城市公共空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