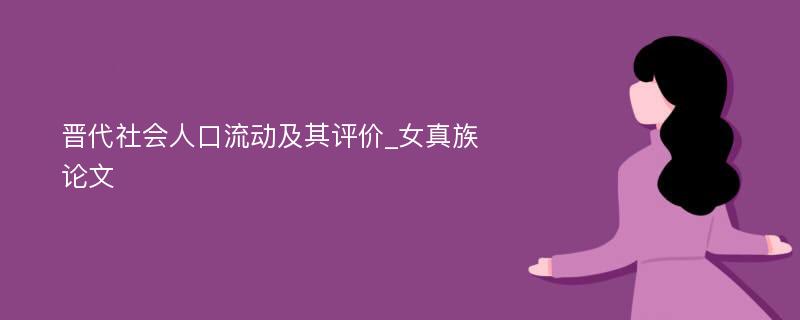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评价论文,金朝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6-0045-05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女真族向中原迁徙、汉族向金源故地徒徙,以及契丹族向各地的迁徙。金朝的社会人口流动主要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而且贯穿金朝历史的过程,对金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女真族向南迁徙
源于黑水靺鞨的女真族的向南迁徙,在辽朝就已经发生了。辽朝灭亡渤海移徙渤海遗民南下,黑水靺鞨随之南徙,女真之号出现于此时,成为臣属于辽朝的部族之一。辽朝时称女真族之在南者“熟女真”,入辽朝籍,在北者称“生女真”,不入辽朝籍,后来建立金朝的即是生女真中的完颜部。
辽朝末年的生女真分为若干部,各部的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其间的经济联系也不是很密切。所以,各部生女真的迁徙也只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至金朝建立前夕,随着女真部落联盟的发展壮大,诸部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但是,女真族人口走出故有的聚居地,形成颇具规模的流民潮,还是金朝建立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对辽、宋战争的发展,疆域不断扩大,为女真族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天辅五年(1121年),金太祖“以境土既拓,而旧部多瘠卤,将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视其地。昱等苴其土以进,言可种植,遂摘诸猛安谋克中民户万余,使宗人婆卢火统之,屯种于泰州。婆卢火旧居阿注浒水,至是迁焉。其居宁江州者,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仍赐婆卢火耕牛五十。”(《金史·食货志一》)。从以上记载中可知,这次移民是由金朝官府组织实施的,是为了满足猛安谋克户对土地的需求而进行的;迁徙的民户两部分相加至少有11000余户,规模是十分可观的;在下令婆卢火屯种泰州以前,就有女真族民户已经来到宁江州从事垦植。
太宗时期,金朝已经确立了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又扶持伪齐刘豫傀儡政权代其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为了巩固在中原广大地区的统治秩序,金朝把大批女真族民户迁入中原,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悉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六》)。“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建炎以年系年要录》卷六八)。由此可见,金朝这次移民的规模是空前的,几乎把金源地区的女真族民户全部迁走。
至金朝罢废伪齐政权,推翻挞懒主持与南宋达成的和议,重新夺回河南,并以强大的军事压力逼迫南宋订立了“绍兴和议”,与南宋隔淮河南北对峙,实现了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直接编译统治。在这种形势下,金朝除了加强对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外,还面临着因长期战乱而带来的社会残破、经济凋蔽的严峻现实。于是,熙宗时继续大规模迁徙女真族民户进行黄河南北地区,并由此发展为猛安谋克屯田军制度。“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大金国志》卷十二)。关于南迁猛安谋克户的安置所在和人数,据《大金国志》中《屯田》条所记:“今屯田之处,大名府、山东、河北、关西诸路皆有之,约一百三十余千户,每千户止一四百人。”根据这组数字计算,应为5万人左右,与上述记载相差不多。但是,与“比屋连村,屯结而起”的移民情形相比,五六万之数似乎又太微不足道,很可能这两次的移民数字都是某一时期的记录,并不能全面反映移民的数量。即使如此,南迁猛安谋克户安置屯田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海陵帝即位后下令大规模营建燕京宫室,改称中都,天德五年(1153年)迁都于此,确立了金朝政治中心的地位。海陵帝的迁都,带动了金源故地女真族人口向中原地区的又一次颇具规模的迁徙。世宗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的与宰臣谈话中说:“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向焉近,并徙元南。”(《金史·世宗纪下》)世宗的话虽然对海陵帝不无批判之意,但亦可以从中看出这次迁徙的人口数量是很大的,以致于世宗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上京之行中,下令从速频、胡里改两路迁徙了猛安30谋克女真族民户充实上京。
以上是金朝前期女真族人口向中原迁徙的大致情况,至金朝末年,由于无法抵御北方兴起的强大的蒙古的军事压迫,导致了女真族人口的再次向南迁徙。贞祐年(1214年),宣宗在接受苛刻的谈判条件换取蒙古自中都城下撤军后,又慑于蒙古军威,下令迁都南京,由此引发了全军在黄河以北的连连溃败。“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加以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金史·抹燃尽忠传》)“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金史·胥鼎传》)这里所指的显然是当时黄河以北的整体社会破坏情况,猛安谋克户亦包括在其中。据宣宗时的大臣高汝砺估计,因河北战败流入河南地区以来是女真族人口流动最大规模的一次,但这一流动却是在金朝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发生的,与前期有组织有目的迁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前后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女真族人口如同江河波涛一般涌入中原,使女真族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上都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有条件接受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的熏陶,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大大加快了女真族走向文明进步的步伐。同时,也对金朝统治下的民族关系格局以及金朝事关处理这种关系的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从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来说,金朝建立以前,生女真虽然已具有比较久远的农耕经济的传统,但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上,这主要是由于劳动人手的匮乏和生产技术的落后,使金源地区土地资源开发和利用难以很快发展起来,所以在生女真的经济生活中呈现了农耕、渔猎、畜牧、采集诸业并举的局面。金朝建立以后,女真族的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农业不仅为衣食所系,而且事关金朝的征服战争胜负和统治秩序能否巩固的大问题,统治阶级无论是对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开发,还是对新占领地区因战乱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越来越给予关注和重视。通过女真族人民辛勤开发,以及移徙以北来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金源地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学习和接受了汉族农民的农耕传统和生产技术。就整体情况而言,至熙宗时期,农业已经成为女真族经济生活中的最主要部分,渔猎、畜牧、采集诸业则退居次要的补充地位。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能够如同女真族这样在短时间里迅速彻底的把经济生活的基础转置于农耕经济之上是不多见的。
由于有以上的前提,女真族及其统治者在学习、借鉴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和经验以及汉族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是十分迅速、彻底。在女真族的“汉化”即封建化进程中,章宗是一个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史称章宗时期“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之规”(《金史·章宗纪四》)。金朝国家的上层建筑主要方面的封建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至此,金朝统治下女真族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使女真族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上都真正具有了中国统治民族的资格。女真族的这一历史飞跃,如果没有向中原迁徙的机遇和所置身的全新社会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上是女真族向中原迁徙给女真族的发展与进步、给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这是主要的,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女真族是以征服战争的胜利者和统治民族的姿态进入中原的,其统治者碰到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好以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尖锐问题。因此,如同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的政权一样,金朝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女真族在金朝社会中始终处在特殊的地位上,皇室、各级贵族、文武官僚等构成金朝的统治阶级中的主要部分,这是勿庸置疑的。而一般的猛安谋克户即女真族平民虽然从形式上与上述统治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他们又是金朝着力扶持保护的社会阶层。比较汉族农民,猛安谋克户虽然承担着沉重的兵役,而他们的赋税负担却相对要轻得多,而且他们屯种的土地是由国家无偿拨给的,这些用于分配的“官田”又往往是剥夺汉族农民的私有土地而来。因此,由以上问题而引起的民族矛盾经常见诸文献记载,是金朝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金朝统治的衰弱也与此不无关系。
二、汉族人口向金源地区流动
在对辽、北宋的战争中,金军所到之处,都把掳掠人口当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对辽朝东京道所属州县作战时,为减轻进攻阻力,大力招降纳叛,对各族实行怀柔安抚政策,对占领区的各族人口就地安置,把他们编制在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组织中。当金军进至长城以南汉族聚居区时,金朝的掠夺人口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把大批汉族人口强制迁徙到“内地”,以缓解金源故地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人手缺乏之间的矛盾。
天辅六年(1122年)以后,金军应北宋之请,不战而下燕京,又在派遣大军追求天祚帝时控制了河东大部分地区。“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以实之。又命耶律佛顶以兵护送诸降人于浑河路,以皇弟昂监之,命从便以居。”(《金史·食货志一》)金朝统治者所看重的是汉族人口所具有各业生产技术,拥有这些人口就可以为他们创造源源而来的财富。因此,在金朝初年,掳掠和安置汉族人口与其军事进攻并重,太祖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军中将领切实解决好掠获人口的安置问题,以防止发生新的逃亡。天辅七年(1123年),太祖下诏:“郡县今皆抚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释其罪,更宜招谕之。前后起迁民户,去乡未久,岂无怀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金史·太祖纪》)由于当时仍处于战争环境下,太祖的诏令能否不打折扣得到全部落实,是值得怀疑的,但起码说明金朝统治者对汉族人口的迁徙、安置是十分重视的。
天辅七年(1123年)四月,金朝与北宋在处理有关燕京所属州县的交涉中,金朝把从辽朝手中攻取的燕京及其属下的檀、顺、景、蓟四州交还北宋;北宋向金朝转交原来给辽朝的岁币50万匹两和每年送交金朝100万贯燕京代税钱。双方围绕归还俘户的交涉中出现分歧,金朝坚持在此前投降北宋的辽军将领郭药师及其统领的常胜军8000余户(原来是辽东人,按金宋“海上之盟”的约定,辽东属于金军作战范围)应作为辽东俘户归还金朝。而北宋则以郭药师在金朝攻占燕京以前就投降了北宋,且已经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官职,拒绝了金朝的要求。当时北宋与金朝谈判交涉此事的官员向朝廷建议:“若以燕人代之,则不惟常胜军得为我军,又复得燕民田产,自可供养,不烦国家应办钱粮,此一举而两得之。”北宋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金朝也接受了这个解决方案。于是,金朝在撤出燕京之际,“根据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以上家业者,得三万余户,尽数起发,合境不胜残扰,独涿、易二州之民安业者,良以先归大宋也”(《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金史·太祖纪》中对这次强制移民也有所记载:“命习右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强、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这些安土重迁的汉族民户先是向金军统师完颜宗翰游说,请求收回迁徙成命而未。当迁徙的队伍行至金朝南京平州时,部分人策动了辽朝降金的大臣、当时任南京留守的张觉以兴辽为号召起兵反金。张觉在受到金朝重兵进攻时势穷转而投降北宋,金朝据理指责北宋违背盟约,北宋不得已杀张觉,送其首级于金朝,并由此引发了金宋战争。
太宗即位后,在对北宋战争的同时,继续把大批汉族人口迁徙到金朝内地。天会四年(1126年)闰十一月,全军攻占北宋都城开封,次年四月,金军撤离开封时,被带走的北宋徽、钦二帝皇室、外戚、官员、伎艺、工匠、娼优,各类人等10余万人,成为金朝向金源地区迁徙汉族人口最多的一次。
至天会六年(1128年),金朝把南宋的军事力压迫至黄河以南,在黄河以北的统治日趋稳固,在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的主持下,迁徙洛阳、襄阳、颍昌、汝、郑、均、房、唐、邓、陈、蔡等府州民户进入河北地区。这次迁徙人口的数量虽然已无从详考,但从移民所波及的地区之广,其数量当不会很少。
金朝对汉族民户的强制迁徙是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金军铁蹄所至,庐舍焚毁,田园抛荒,百姓背井流亡。迁徙途中饱受颠沛之苦,即使随徽、钦二帝北行的皇室、后妃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普通百姓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初,男女北迁者,以五百人为队,虏以数十骑驱之,如驱羊豕。京师人不能徙走远涉,稍不前,即敲杀,遗骸蔽野。”(《三朝北盟会编》卷九)而迁入金源地区的各阶层汉族人,包括帝王子孙、官门仕族中的多数人沦为官私奴婢,以供驱役。
尽管如此,大批汉族人口迁入金源地区,为女真族加快走向封建化提供了外在动力,对促进金源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巨大作用。首先表现在汉族人口的到来,传播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增加了经济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大大提高了金源地区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例,从今东北各地出土的金朝种类繁多的铁制农具,可见比较辽朝已有明显进步,在形制上与中原的农具非常接近。可以这样说:汉族人口的迁入,带来了我国古代东北农耕经济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次是数量众多的汉族士人的迁入,承担了传播汉族封建文明的重要角色,使女真族原来的闭塞、愚昧的落后状态大大改观。以金上京会宁府为例,“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时节序,皆一中国侔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在金朝初年的文人群体中,虽然仍以汉、契丹、渤海各族人为主,女真族尚未出现出类拔萃的文人学士,但也确实有一批根植于女真族民族传统土壤,在仰慕和学习汉族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大热情的优秀代表人物。如熙宗完颜亶自幼年起,其养父宗干即为他延请汉族学者韩昉为师,“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茗香,弈棋象战,徒失女真之本态耳”,“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六)汉文化的熏陶为完颜亶即位以后模仿中原政权进行金朝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契丹族人口的流动
辽朝灭亡前后,契丹族人口并未因辽朝统治的互解而发生大规模的流动,除有很少部分契丹人追随耶律大石辗转西迁外,绝大多数人仍留居原地。这也与金朝在反辽战争中为减轻进军作战的阻力,集中力量打击以天祚帝为首的辽朝统治集团,对契丹贵族、官员和一般族众实行招降安抚政策有密切关系。收国二年(1116年)正月,太祖在反辽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下诏:“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勒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金史·太祖纪》)金朝的招降安抚政策对于孤立天祚帝,动摇辽朝的腐朽统治,壮大反辽战争的声势起了巨大作用。
契丹族人口在金朝的第一次大规模流动是因耶律余睹的降而复叛引起的。耶律余睹是辽朝皇室近亲,辽末的重要将领之一,因被附马萧奉先诬陷无法自明而投降金朝。耶律余睹虽然被任以都监之职,为方面之帅,但是金朝并不真正信任他。而耶律余睹则自以为助金灭辽有功,对于久不提升官职“意不自安”。天会十年(1132年)九月,耶律余睹奉命率军进攻漠北的耶律大石。当耶律余睹驻军曷董城时丢失金牌,越发引起金朝的怀疑,把他的妻子家人扣为人质。耶律余睹遂策划起兵叛金,谋泄,父子以游猎为名出奔,被鞑靼人杀死。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仅耶律余睹的部属,当时云中、河东、河北及燕京等地的契丹族官员全部被杀,金军前线最高指挥机构元帅府下令各地“诸将分捕余睹余党,仍令诸路尽杀契丹,诸路大乱,月余方止。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夏国,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大金国志》卷七)甚至西路军统帅宗翰掠天祚帝元妃所置次室萧氏也被元室在搜捕耶律余睹党翼中杀死;在辽、宋、金三大势力角逐中先是降宋继而降金的辽军将领郭药师本非契丹人,也在这一事件中受到株连,被逮下元帅府狱,获释后,完颜宗翰以“财可聚众”为名剥夺了他的全部家产。经此浩劫,辽朝时迁入长城一线以南的契丹族人口所余无几。
契丹族人口在金朝的第二次大规模流动是在世宗时发生的,是出于对契丹族的监视防范而进行的强制迁徙。世宗在平定了窝斡领导的北方契丹族大起义后,为加强对契丹族的控制,罢免追随窝斡“作乱”的契丹猛安谋克,把所辖户口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大定十七年(1177年),金朝派监察御史完颜觌右巡边,随行的契丹押剌妥剌、招得、雅鲁、斡列阿等四人乘机逃奔耶律大石。世宗缘此对契丹族采取了进一步的控制措施,即对契丹族实行距离迁徙,把曾经参加窝斡起义的契丹族众由西北路迁至上京路的济州、利州各地,“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嫁,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金史·唐括安礼传》)世宗对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员下诏说:“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真人相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计也。”仍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使讨灭。”(《金史·唐括安礼传》)说明世宗企图用民族同化的办法泯灭契丹族的“反侧之心”,而在貌似温情的背后却隐藏着森然的杀机,即这种民族同化是以武力的镇压为后盾的。
金朝契丹族人口较具规模的第三次流动发生在章宗时期。金朝继承了辽朝的群牧养马制度和部族分番戍边制度,诸群牧主要是由契丹族牧民组成。金朝的东北、西北、西南路招讨司下各辖有数量不等的乱军,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契丹族,他们与各部族军共同承担着分番戍边的任务。契丹族牧民在群牧生产受到的剥削、歧视,以及戍边乱军所处的恶劣自然环境,都促进了他们对金朝的仇恨情绪不断滋长,终于在蒙古高原诸部兴起南下的背景下爆发出来,多次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承安元年(1196年)的特满群牧德寿和隋锁领导的起义,有众数十万,建元身圣,附近的诸乱军也起而响应,震撼了金朝的腐朽统治,金朝为防止群牧的起义牧民与诸乱军联合作战,把诸乱军迁徙至中都附近以便就近监视,然后分兵各个击破,镇压了这次起义。金朝末年,在蒙古支持下活动于辽西、辽东的耶律留歌政权,其属下的数十万众中的大部分就是这一带的契丹族牧民和乱军组成的。
金朝对女真族以外的各民族实行压迫歧视政策是其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族在金朝除了遭受经济盘剥,还要经常受到屠杀、强制迁徙和充满血腥暴力的民族同化。虽然终金一代契丹族以各种方式顽强表现自我存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但是,作为曾经在中国北方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契丹族,金朝以后影响日微,虽然至蒙古汗国时时期仍不乏有耶律楚材那样的卓越人物,但是作为曾经创造过彪炳史册的英雄业绩的契丹族已成为历史陈迹。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很少有专章记录契丹族的活动和事迹,就是这一史实的客观反映。中国本土的契丹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女真、汉、蒙古等民族中,成为这些民族中的一部分。
契丹族的历史发展和最终结局,是中华民族演化的重要阶段和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之一,符合民族发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契丹族尽管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不存在了,但却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的历史内涵。
[收稿日期1999-06-20]
标签:女真族论文; 契丹论文; 金朝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族人口论文; 三朝北盟会编论文; 大金国志论文; 耶律余睹论文; 金史论文; 宋朝论文; 中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