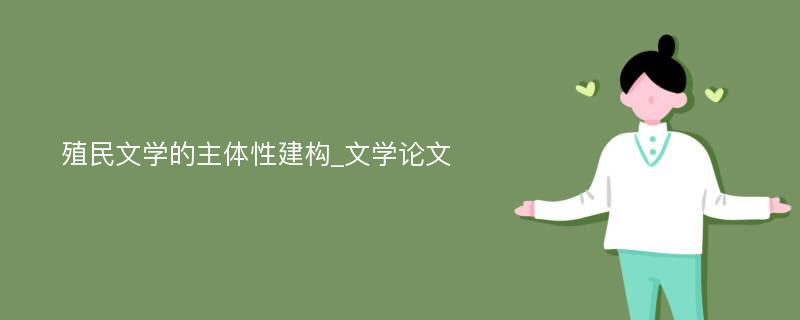
殖民(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agency”和“subjectivity”两个概念的汉译同是“主体性”,但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之间没有区别。英语中的“agency”代表一种“能动”或“能力”,主要指个人或群体自由、自主、自动地发起行为或发表言说的能力,①英国诺丁汉肯特大学考斯·维恩教授简洁地称之为“我能”(the‘I can’)。②英语中的“subjectivity”则表示一般主体(subject)的建构过程和方式统一体的存在,维恩简洁地称其为“我”(the‘I’)。③据此,“subjectivity”可以说是“我能”之“我”。本文使用的“主体性”概念即指此意。至于殖民文学和殖民主义文学的概念,艾勒克·博埃默已做出专述:“殖民文学(colonial literature)……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看法和经验的文字,那些主要由宗主国作家,但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欧洲人后裔以及当地人在殖民时期所写的文字。……我以为这种殖民文学既应该包括不列颠本土写成的文学,也应该包括在殖民时期帝国的其他地区的文学。这种宗主国的文字……在形成并强化不列颠是主宰世界的强国这一观念方面,它们是参与其中的……”④“殖民主义文学……是由欧洲殖民者为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它含有一种帝国主义的眼光……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⑤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殖民文学”主要是西方宗主国(虽然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当地)作家写的文字,这些文字参与强化西方宗主国是主宰世界的强国的观念,而所谓“强化西方宗主国是主宰世界强国的观念”的过程即是凸现西方主体性的过程;二、如果说“殖民文学”参与建构西方主体性,那么“殖民主义文学”(colonialist literature)就是“殖民文学”参与的建构西方主体性的行为本身。博埃默的这两个定义可谓是对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揭示的西方小说与帝国主义间共谋关系的肯定和释义。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中强调:“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⑥同样,博埃默也认为:“帝国主义思想在想象文字中无所不在的影响,展示这种文字对于帝国所给予的隐而不见的支持……这一时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作家,不管怎么说已成为帝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争议也好,对帝国的仇恨也好,他们都是与之(帝国——笔者注)声息相通的。”⑦可见,无论是博埃默定义的殖民文学、殖民主义文学,还是赛义德阐述的东方主义文学,都是在帝国形成过程中与帝国融为了一体。文学与帝国的融合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探索文学建构主体性的空间。本文将在这个空间里集中讨论殖民(主义)文学建构西方主体性的本质性过程。
在后殖民理论奠基之作《东方主义》中,赛义德鞭辟入里地论述了包括埃斯库罗斯、但丁、歌德、雨果、夏多布里昂、福楼拜、司各特、拜伦、迪斯累里、康拉德、吉卜林、福斯特等在内的著名西方作家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西方殖民者——如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克罗默、本杰明·迪斯累里、约翰·穆勒、约翰·亨利·纽曼、托马斯·拜宾顿·麦考利⑧等——你呼我应、共同谋造东方和东方人的。我们注意到,赛义德论及的迪斯累里、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人既是作家又是政治家,⑨他们的双重身份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笔下的作品与帝国之间水乳一体的关系。而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则阐述了西方作家是如何潜心构建或刻意表现西方自我主体的:“如康拉德很强烈地认识到的那样,维系帝国的存在取决于‘建立帝国’这样一个概念;”⑩“康拉德想要我们看到,克尔茨伟大的掠夺冒险、马洛逆流而上的旅途以及故事叙述本身,有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非洲、或在非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控制力量与意志。”(11)赛义德在此探讨的不再是马洛耳闻目睹的刚果河及其沿岸土著人,而是马洛、克尔茨等人表现出来的西方帝国的力量和意志。但是,赛义德的两部著作实际上都表明,殖民(主义)文学是西方主体的一个构成部分。
殖民(主义)文学建构“我”的主体性的过程可以说根源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12)的思想传统,因为东方主义文学(殖民、殖民主义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13)具有笛卡儿的“我思”之逻辑先在性。但殖民(主义)文学建构主体性“我”的过程又不完全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过程,因为埃斯库罗斯、但丁、康拉德、吉卜林等西方作家的思维并没有像笛卡儿那样封闭于“我思”自我意识之内,而是将“我思”延伸至“我思”之对象。笛卡儿在其第三沉思开始时说:“现在,我将闭目掩耳,脱离一切感知。”(14)与笛卡儿这种普遍怀疑主义的封闭式“我思”不同,东方主义作家不仅“在思维”,而且还在追询“思维什么”。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作家思维的对象是东方和东方人: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以胜利者和强者的口吻表述的落败的、绝望的波斯国王薛西斯;但丁在《地狱篇》中陈述的江湖骗子穆罕默德;歌德在《东西诗集》、拜伦在《异教徒》、雨果在《东方人》中表述的使人获得解脱、充满创造机会的东方;司各特的小说《护身符》中被肯尼斯爵士说成是蒙昧、邪恶的魔鬼的后代萨拉辛人;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描写的堕落淫荡的埃及名妓库楚克·韩妮媚;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英国姑娘阿黛拉的眼里被怀疑为侮辱女性的印度医生阿齐兹;勃朗特的《简·爱》里简·爱看到的野兽般的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笛福在《鲁滨孙飘流记》中描写的来岛上举行人肉宴的野蛮人;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描写的非洲刚果河沿岸食人肉的野蛮人等等。但是,这里作为东方主义作家思维对象而呈现出来的东方和东方人,并不是东方主义者耳闻目睹的东方的自然或自然的东方,而是赛义德所说的由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方。(15)西方殖民(主义)作家笔下的东方和东方人并未摆脱认识论的统摄而到达本体论所追问的终极的东方(人)本体。本体论追求的超越认识能力和意识显现而自然存在的终极本体或外在的经验实体,遭到笛卡儿的怀疑和埃德蒙特·胡塞尔的悬置。
胡塞尔在悬置外在经验实体和自然存在本体的同时,强调意识的基本结构乃其“意向性”。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性”克服了笛卡儿孤立的怀疑主义“我思”形式,指出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个对象,意识不能没有对象,没有对象的意识是没有意义的意识。胡塞尔说:“认识体验具有一种意向,这属于认识体验的本质,它们意指某物,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尽管对象不属于认识体验,但与对象发生的关系却属于认识体验。”(16)胡塞尔在此所言的意识之对象有别于其存而不论的超越意识能力而自然存在的本体或经验实体,因为意识指向的对象并没有超越意识本身。所以,欧洲人凭空创造的东方和东方人,如西方作家笔下的薛西斯、穆罕默德、萨拉辛人、韩妮媚、伯莎、非洲刚果河等,都是西方意识指向的未超越意识本身的、属于认识体验而非感性经验的对象,或者说,是胡塞尔强调的先验构造的结果。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点是,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构造后者的过程。他认为“事物不是思维行为,但却在这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在它们之中成为被给予性;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自身为何物。”(17)据此,东方和东方人是在被西方思维的过程中被西方构造或建构的;或者说,西方在思维东方并在这一思维过程中建构东方。
在《东方主义》中,贝尔福和克罗默关心的并不是实际存在于北非的那个埃及,而是他们想像的那个埃及。同理,西方殖民 (主义)文学描写的东方也不是实际存在的东方,而是其创造建构的东方。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东方主义或殖民(主义)作家并不是为了建构东方(人)而建构东方(人),而是为了建构西方自我主体而建构东方(人);换句话说,是为了建构西方“我们”而建构东方“他们”。东方主义者在其思维、想像和言说东方(人)的过程中把自己(西方人、宗主国、殖民者、白人等)看作是“我们”,而把其思维的对象 (东方人、臣属国、被殖民者、黑人等)看作是“他们”或“他者”,这就是加·查·斯皮瓦克所说的“他者化”(othering)过程。(18)赛义德也认为,他者化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文明、先进、高贵的”西方主体——“我”或“我们”;这一建构过程的本质是,“一群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此指西方)的人会为自己设立许多边界,将其划分为自己生活的土地和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紧密相邻的土地以及更遥远的土地——他们称其为‘野蛮人的土地’(此指东方)。换言之,将自己熟悉的地方(此指西方)称为‘我们的’(ours)、将‘我们的’地方之外不熟悉的地方(此指东方)称为‘他们的’ (theirs),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做法所进行的地域区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19)其实,赛义德此处所说的“我们的”与“他们的”区分并不完全是任意的,而是特意的;其意不是要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而是要把“我们”从“他们”当中突显出来。西方人在划分“我们”与“他们”的过程中称“东方”为“野蛮人的土地”;“野蛮人”这个称谓已超出划分行为而构成创造行为,其目的是要说明“我们”西方人是“文明人”。西方人就是这样巧妙地建构西方主体“我们”。彼德·查尔兹说得对,“东方从来就是作为西方现成的对立物而存在的。”(20)西方人从“野蛮的他们”中区分、辨认出“文明的我们”的行为从本质上看与拉康所说的“镜子阶段”的婴儿从镜子里辨认出“我”的行为共通一致。在拉康看来,婴儿只是到了“镜子阶段”才开始能够辨认出镜子里反映的“我”,同时产生“自我意识”。(21)这种从镜中辨认“我”的行为可谓建构“我”的行为。在此过程中,镜子仅是一个象征物,婴儿根据镜中的映像来确定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又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言,“在他者注视我时,我认识到我的存在。”(22)萨特此处关注的是“我”的主体,但“我”须在“他者”的注视下把握“我”的“被注视的存在”。同理,西方人通过“野蛮的他们”确定“文明的我们”;东方主义作家通过建构落败的薛西斯、骗子穆罕默德、邪恶的萨拉辛人、淫荡的韩妮媚、兽性的伯莎、野蛮的星期五等东方他者来证明胜利、诚信、正善、贞洁、人性、文明的西方“我”的主体。
但是,作为东方主义作家建构和思维对象的东方人,并不是被动存在的没有主体认知能力的客体,而是另一个具有思维意识能力的主体存在,所以,这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主体的思维、意识、作用、统摄、整合的过程。在此,我们应当突破唯我论和一元主体论,深入到多元主体间互动关系中窥测西方主体性的建构过程。胡塞尔坚持一元主体的自明性原则,同时又试图建构多元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这种两难困境使其只能在同一先验主体之内的多个世俗自我之间建立主体间性理论。所以,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不足以解释西方在其东方主义话语中建构西方主体性的复杂现象。保罗·利科说:“孤独的‘我’是不存在的。”(23)在后殖民话语中,西方主体性“我”总与另一个主体“他”或“他者”同时共在。如同婴儿在镜子阶段从镜中辨认出“我”一样,西方主体从东方“他者”注视自己的目光中确定“自我”,双方相互对视的目光反映出两者主体间关系。范农在法国的遭遇便是最好的例证:当时一个白人小孩用手指着范农让妈妈看,并大声喊道:“看呀!妈妈,黑鬼。”紧接着,小孩又大声喊起来:“妈妈,看见了吧,黑鬼!我害怕!”(24)面对白人小孩的注视和喊叫,范农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带着满脸苦笑凝视那个白人小孩。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牙买加克里奥耳人伯莎的面容是简·爱噩梦醒后在黑暗中从镜子里看到的:“那是张没有血色的脸——那是张野蛮的脸。我但愿能忘掉那双红眼睛的转动和那张脸上可怕的又黑又肿的样子!”(25)简·爱从黑暗的镜中看到的秉性粗野、相貌丑陋、心态畸形的东方“他者”映像本身凸现出简爱或罗切斯特举止文明、相貌堂堂、充满智慧的西方主体形象。
另一方面,“内格罗土德”(négritude)作家群,(26)乔治·兰明、匈沃、里斯等一批来自原殖民地的作家又力图通过逆写、重写或改写西方作家笔下的“他者”来建构东方自我主体性。内格罗土德作家艾米·西赛尔在加勒比版的《暴风雨》(Une Tempéte)中带着“奴隶创造历史”的信念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凯列班改写成一个其主动性和重要性都强于普洛斯彼罗的造反者。乔治·兰明在《被放逐的愉快》中消除了普洛斯彼罗、爱丽儿和凯列班之间的等级关系,凯列班不再是莎剧《暴风雨》中那个远离文明、野蛮畸形的生物,而变成一个带有明显异国语言和文化的西印度人。J.M.科埃齐在《敌人》中把笛福笔下的星期五改写成一个能够通过书写圆圈来主动表达他被囚禁之意的角色。笛福在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歌《鲁滨孙的小岛》、诗歌集《鲁滨孙的日志》以及剧本《哑剧》中则成了当代加勒比生活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物。吉恩·里斯在《辽阔的马尾藻海》中颠倒勃朗特《简·爱》的视角,重写被关闭在阁楼里不能说话的模糊黑影伯莎,给她注入生命的活力,使其复活、开口说话,并改其名为安托伊尼特。里斯本人在1958年4月 9日写给赛尔马·瓦斯·戴艾斯的信中说:“我反复读过《简爱》……我肯定要建构[安托伊尼特]这样一个人物……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里的那个克里奥耳人是一个台下的边缘人物……在我看来……她必须是台上的正中人物。”(27)台下边缘的伯莎转变为台上中心的安托伊尼特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他者”对“我”的逆写,是“他者”主体性的自我建构。此类逆写还有很多,如康拉德《黑暗之心》中的“刚果河”在匈沃的《界河》、萨里赫的《向北迁徙的季节》、威尔逊·哈利斯的《孔雀的宫殿》、奈保尔的《河湾》等后殖民文学文本中被改写为“霍尼亚河”、“尼罗河”等不同的河流等等。总而言之,东方“他者”,如同拉康描述的六月婴儿能从中辨出“我”的镜子,东方“他者”在殖民(主义)文学中被用作西方主体“我”的反射体,但这些所谓的“他者”随后又被东方殖民地作家重写、改写或逆写,成为他们力图建构的东方主体性的直接体现者。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作家或东方主义作家建构西方主体性的过程乃M.H.艾布拉姆斯所论述的体现艺术家与作品、世界之间关系的表现主义和实用主义(28)方法论的实际运用。殖民(主义)文学既不是东方主义作家对柏拉图“理式”世界的摹仿,也不是对现实东方的亚里斯多德式摹仿,而是对东方世界的建构、想像、创造,以此表现西方主体性。东方主义暗示有一个先于殖民(主义)文学而独自存在、现被悬置起来的非恒定的现实东方世界。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先于表象符号存在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或是“无”(nothing)的存在。据此,殖民(主义)文学对现实东方的摹仿只能是对“无”的摹仿,而“无”的摹仿只能是“无”中生有,所以说,殖民(主义)文学不是对东方世界的模仿,而是对其的创造。这种对东方世界“无”中生有的创造来自艾布拉姆斯论及的作家主体性的表现。但东方主义作家主体性的表现形式有别于诗歌表现诗人情感的形式。威廉·华兹华斯在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说出的那句名言“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29)表明了诗人情感的流向和主体序位,即诗人情感流露,而不是诗人流露情感,因为华兹华斯强调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情感的人为流露。与此不同,西方主体性“我”是东方主义作家人为创造东方他者来建构的。
诗人的情感是诗人主体性的存在形式之一。在一般情况下,诗人的主观意志主使诗人的情感,使诗人无须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摹仿世界。但一旦诗人或其他作家的主观意志演变为尼采所言的权力意志,诗人情感流露的过程就变成其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同时表现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化。据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的论述,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是贵族道德价值体系和奴隶道德价值体系相互斗争的结果。由于受权力意志的驱使,西方贵族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自己觉得“好”的贵族价值体系。如尼采所言:“对于‘好’的判断并非来自那些表现出‘好’的人!而所谓的‘好人’自身——即贵族、权门、上层、睿智——其实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好人的行为的人们——即为第一流的人物;他们因此断定他们是‘好人’,与一切低下、弱智、普通、卑贱的事物形成对照。”(30)尼采又强调说:“如我所言,这种表现高贵和地位身份的人为因素 (pathos of nobility and distance),即,高层统治者们在与低下人们所形成的反差关系中所体味到的持久的、强势的、根本的总体感觉才是‘好’与‘坏’之间对立关系的起源。”(31)可见,所谓“好”的西方贵族是西方贵族自己感觉的结果。尼采所说的“感觉”过程不同于华兹华斯所说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过程,前者是在权力意志驱动下发生的有目的的感觉过程,后者则是一个本能或自然的过程。保罗·吉尔伯特将民族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唯意志论两类:前者指按一个民族真实面目反映该民族的文学,后者则指某个民族国家按其政治意图或民族意志选择的文学。(32)吉尔伯特认为,民族文学或者是“事实”(fact),或者是“建构行为”(construct)。(33)殖民(主义)文学显然属于后者,如同西方贵族建构贵族道德价值体系和唯意志论民族文学建构某个民族一样建构西方主体性。
从实用主义诗论的角度看,诗都是有目的的。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一辩》中说:“诗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娱情悦性。”(34)锡德尼所说的“教”与“乐”是古已有之的诗歌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而在于文学的目的不能扭曲或破坏文学对世界的摹仿。一旦作家带着某种目的 (教育、娱乐或其他)摹仿世界,他就不能按世界本来面目摹仿世界,而只能按其目的模仿世界。结果,摹仿本身遭到扭曲或破坏,被模仿的世界被消解,摹仿的意图 (目的)也遭受质疑。西方殖民(主义)文学是西方对东方的创造、建构、想像和表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些文字,为西方读者提供了娱乐和教育,但它们通过创造一个野蛮、落后、边缘、臣属的东方“他者”来建构一个文明、先进、中心、宗主的西方“我(们)”,无疑也显示了其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褊狭——“我”思“他”,故“我”在。
注释:
①可参见Bill Ashcroft,C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8-9。
②③Couze Venn,Occidentalism: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London:Sage,2000,pp.226-227,pp.86-87.
④⑤⑦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3、25-26页。
⑥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前言第2页。赛义德关于西方小说与帝国主义之间共谋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阅其《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第一、二章 (第1-270页);同时可参见“爱德华·赛义德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专题讨论会”,载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3-312页。
⑧贝尔福当时是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1902 -1905)和外交大臣;克罗默当时是英国军官和外交家,曾任英国驻埃及代表和特命全权总领事,著有两卷本的《现代埃及》(Modern Egypt,1908)和《古典与现代帝国主义》(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1910);迪斯累里是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其领导的政府极力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并发动过侵略阿富汗、南非的战争,同时迪斯累里又是一位作家,写过小说和一些政论作品;穆勒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纽曼是英国宗教领袖;麦考利是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印度总督府最高委员会任职,其后又担任过英国陆军大臣等要职。
⑨夏多布里昂既是浪漫主义作家,又是政治外交家;拉马丁既是浪漫派诗人,又是政治活动家。
⑩(11)爱德华·W·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29页。
(12)René Descartes,A Discourse on Method: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trans.John Veitch,London:Everyman,1994,pp.25-26.
(13)(15)(19)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1、67-68页。
(14)René Descartes,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with Selections from the Objections and Replies,trans.John Cotting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4.
(16)(17)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8、61页。
(18)斯皮瓦克关于“他者化”的详细论述可参见:G.Spivak,"The Rani of Simur," in Francis Barker et al ed.,Europe and Its Others Vol.I Proceedings of the Essex Conference o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Colchester:University of Essex,1985; G.Spivak,In Other Worlds: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Methuen,1987; G.Spivak,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Sarah Harasym ed.,New York:Routledge,1990; G.Spivak,"Identity and Alerity:an Interview" (with Nikos Papastergiadis),in Arena 97:65-76.
(20)Peter Childs ed.,Post-Colonial The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A Reader,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p.6.
(21)Jacques Lacan,"The Mirror Stage," in Identity:A Reader,Paul du Gay,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eds.,London:Sage,2000,pp.44-45.
(22)Jean-Paul 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trans.Hazel E.Barnes,London:Routledge,1969,p.222.
(23)Paul Ricoeur,Oneself as Another,trans.Kathleen Blame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18.
(24)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trans.Charles Lam Markmann,London:Pluto Press,1986,pp.111-112.
(25)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26)“内格罗土德”是艾米·西赛尔(Aimé Césaire)杜撰的术语,主要指一批居住于法国巴黎、讲法语的黑人知识分子[如列泊尔德·塞达·桑戈尔(Leopold Sédar Senghor)、毕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范农、西赛尔等]的写作行为及其意图。“内格罗土德”在我国又被译为“黑人文化自豪感”,这表明内格罗土德的主旨是要在西方宗主国主动传播非洲黑人引以为豪的文化,展示非洲黑人独特的品格,建立非洲黑人的主体性。
(27)Jean Rhys,Letters,1931-1966,Francis Wyndham and Diana Melly eds.,Harmondsworth:Penguin,1985,p.156.
(28)M.H.Abrams,"Orientation of Critical Theories," in David Lodge ed.,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72,pp.1-26.
(29)威廉·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曹葆华译,见王春元、钱中文主编《英国作家论文学》,汪培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31页。
(30)(31)Friedrich Nietzs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trans.Douglas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2,p.13.
(32)(33)Paul Gilbert,"The Idea of a National Literature," in John Horton and Andrea T.Baumeister eds.,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p.199,p.200.
(34)Sir Philip Sidney,"An Apology for Poetry," in G.Gregory Smith ed.,Elizabethan Critical Essay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04,p.158.见杨荫隆《西方文论家手册》,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第83页。
标签:文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简·爱论文; 暴风雨论文; 他者论文; 胡塞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