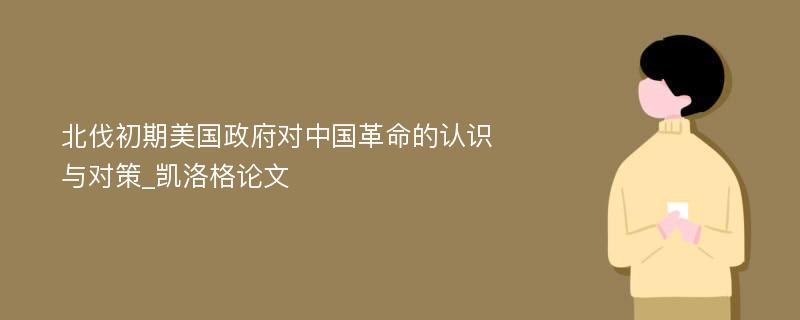
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认知论文,对策论文,中国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中,20年代一向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比较起来,对北伐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还算稍多,但学术界对此似尚无一个广泛接受的共识。本文拟从当时当事人的认识与关注点去考察分析问题,希望能在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方面作一些史实的探讨与重建,或可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稍进一层。
一、几个背景因素
过去有些研究似倾向于从后来国共两党成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的角度来反观历史,所以较少注意美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其实,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时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并不为许多人所了解,也未曾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综观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关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争斗,只是在武汉与南昌的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而当时报刊上最著名的“赤党”,实际上是活跃在台面上的徐谦与邓演达,对真正的中共反而了解不多也注意不足。中国人不过如此,遑论对中国情形的了解终究要差一步的外国人了。故本文虽然侧重于美国与南方的关系,仍注意将其放在南北对峙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
就国际环境而言,过去对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首先,列强的合作政策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远东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因而也就低估了这段时期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其次,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并不包括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完全独立的中国政策,实际上形成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有力挑战。而国民党恰利用了这一缺陷,先后从这两国获得主要的军事援助。
实际上,“华盛顿体系”的列强合作精神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伐前夕召开的修订治外法权会议。关于这次会议,日、英两国基本上没有严肃对待,只有美国还比较认真。美国向会议提交了482项涉及美国在华权益的案例,而英国只提出了很少的案例,日本则根本没有提交任何具体案例。这很能说明各国的态度。会议的决议报告基本是据美国的材料由美国人在实地调查之前就已写成,一向对外交条款斤斤计较的英、日外交官并未提出多少修改意见〔1〕。这一切都说明列强间的合作大致已名存实亡。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北伐时的中国局势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尤其以变化的突然与急剧著称。在这样的情形下,任何外国除了大的原则外,实不可能有多么具体的政策,尤其不可能有预先制定的政策。北伐初起时,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北政治力量,都未曾预见到后来急速的军事进展,在华外国人也同样如此。列强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幻莫测的局势,只有不断调整其原有的政策原则,故北伐时主要列强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局势一样,是以多变为特征的。
就美国而言,另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北伐期间美国驻北京使馆与华盛顿的国务院之间长期存在意见分歧。从1925年到任开始,对于从五卅事件到1926年11月的《中比条约》废除等几乎每一件较大的事件,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与国务院都不断发生政策争执。一再受挫后,他曾于1926年底致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明确表示缺乏相互了解,要求回国面商,但他刚走到日本就因中国局势日见紧张而被召回任所。到1927年初,随着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Nelson T.Johnson)晋升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而项白克(Stanley K.Hornbeck)出任远东司司长,马慕瑞与国务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他曾明确反对项白克的任命。马慕瑞在1927年2月12日写了封15页的长信给代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举出七个国务院拆他的台、使他出丑的例子,认为国务院对中国政策的指导是“犹豫不决和易变的”,是“放弃、消极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政策〔2〕。直到马慕瑞离任,他和国务院几乎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同时,驻华使馆与各领馆间也常出现不同意见,美国各级外交人员的意见不一致的情形是明显的。造成美国各级意见不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对南方新兴的国民党内派系及国共两党关系(包括合作与斗争)的了解可以说从未达到准确的程度。实际上,美国人接触较多的是国民党中那些能说英语的领导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是孙中山的亲戚和幕僚(如孙科、宋家成员和陈友仁),他们大部分较年轻,也因能说英语,故与握有相当实权的鲍罗廷关系密切,在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前基本偏左。美国外交官员对南方的好感多得之于这些人,而其提出的偏向南方的政策也常常是有意无意针对这一势力。
反之,多数美国人对蒋介石个人的观感一直不好。对多数中外观察家来说,蒋本人正是联俄的主要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由于蒋介石自1925年以来在国民党内争中不断变换立场,忽左忽右,马慕瑞对他的观感从来就不好,认为他太不可靠。关于美国外交官对蒋介石的认知,过去的研究基本忽视,故有必要作简短的史料考释。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并未受到美国驻华外交和情报官员的太多注意。正因为准备不足,美国驻华官员对在该事件中崛起的蒋认识相当模糊,缺乏定见。实际上,蒋在那次事件中的许多行为的确具有突发特征,他自己的日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故即使是熟悉蒋的中国人,对他在那段时间变化多端的所作所为也不甚了了〔3〕。
在中山舰事件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对蒋介石的观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4〕。到6月,精琦士终于有了初步的结论,即蒋就是“广州的政府”,他不会容忍“不管来自温和派还是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可以看出,蒋本人并非精琦士眼中的“温和派”。精琦士认为,蒋与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的暂时联盟不过是为了得到军火和资金。但他也在那次报告中明确指出,蒋本人正是以“排外而特别是反美”而著称的〔5〕。
蒋介石自1925年以来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收回主权的激进主张颇令美国担心。1926年春,美国《国民》杂志记者根内特(Lewis S.Gannett)在广州采访蒋介石,蒋以各种问题了解了根内特的观点后,得出根内特尚属“真诚”的结论。然后蒋介石宣称也要告诉根内特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真话:“中国有思想的人恨美国更甚于根日本”,因为美国人是两面派,虽然甘言笑脸,却和日本人行动一致。由于蒋介石至少认为他自己是中国有思想的人,则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却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6〕。
蒋介石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激进外交主张并非特例,北伐时期中国南北双方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都明显偏于激进而不是温和。对这段时期中外关系的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革命性”发展对中外关系的直接间接影响。国民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1926年告诉美国人:美国关于条约修订的政策是采“渐进”的取向,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却从根本上是“革命”性的,因而也就要求一种 “革命性的,亦即根本的解决”。那种一步一步地调整的“渐进”取向实与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违背〔7〕。
政治的“革命性”发展也引发整个思想界舆论界的“革命”倾向。“革命外交”就是革命时代的一个典型产物。何谓“革命外交”?说到底,就是不按或至少不完全按既存外交规则行事。曾在欧洲长期受教的周鲠生在北伐期间发表《革命的外交》一文,提出“革命外交的第一要义”便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即“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而第二要义则是“利用民众势力”。具体言之,就是不但不能“怕事”,而且要能够“生事”,以“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为外交的“要诀”。一言以蔽之:“革命的外交,决不能是绅士式的”;相反、“流氓的方法,实在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政府最有效的外交方法”〔8〕。周氏学的是国际法,并以此名家,竟全然置其学者身份于不顾,公然号召不遵行国际规则、惯例及条约,而其文章又发表在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所办的《现代评论》(一般均认为此刊物“温和”而不“革命”)上,最能体现世风的激进。
在实际操作层面,北伐时期南北政府主持外交的陈友仁与顾维钧都受过西方训练,尤其懂得怎样利用西方的“道理”来对付列强,最使列强头痛。1926年11月6日,经过长期无结果的谈判,在代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主持推动下,北京政府宣布废除已到期的《中国比利时条约》〔9〕。这是自有中外不平等条约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主动废除与外国签订的条约。顾氏在主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在其他中外谈判中持强硬立场),实表明北方在外交实践的“革命”性方面,丝毫不比南方逊色。
在北京废除中比条约两个星期后,蒋介石在南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北伐开始后蒋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对北京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他并宣布:“国民政府以前的中国任何政府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定,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承认。”蒋介石进而指出:“这是一场革命,不能取渐进方法。”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革命才算完成,国民党决心立即废除各种条约特权,而不考虑通过谈判修订条约的方式〔10〕。
正如马慕瑞观察到的: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中,有“两种对立的主义在进行斗争”,特别是在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上,“一方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而另一方主张取革命的方式”(evolutionary or revolutionary)〔11〕。马慕瑞所说的“中国人”,是包括南北双方的。顾维钧的行为和蒋介石的言论都直接印证了马慕瑞的观察。就南方而言,此时蒋介石尚无与列强发生直接交涉的经历,但他的言论表明他本人正是站在主张采取“革命方式”那一边的。自南昌与武汉的对峙开始到1927年春的南京事件,蒋的反帝言论如果不比武汉方面更厉害,也至少不弱于武汉方面。
蒋的前述讲话给西方人以强烈的印象。在华英文报纸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在1926年11月29日的社论中警告说:蒋的坦率讲话揭示了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是“决不妥协的”。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在1926年11月23日的社论中就把蒋介石列为中国的激进人物之一(英文的radicals在当时是有特定指谓的)。《纽约时报》记者亚朋德(Hallett Abend)后来回忆说:“1926年时的蒋介石是以从内心里讨厌所有外国人而著称的”〔12〕。总的说来,不论蒋介石在中国的内争中有何表现,他在对外态度方面与当时激进的世风并无两样。但对美国在华外交官来说,北伐初期的蒋介石与整个国民革命运动都基本还是个未知数。
二、在列强竞争中美国向南方的逐渐倾斜
正是因为美国使领官员对蒋介石和中山舰事件后新崛起的广州当权官员了解不足,马慕瑞才于1926年6月派遣驻华使馆的第二把手梅尔(Ferdinand Mayer)到南方考察,以掌握第一手材料,从而可针 对那里“惊人的事态发展”提出制定相关政策的推荐性意见〔13〕。梅尔征求了美国驻广州、香港、汕头等地领事的意见,并与所到之处的国民党官员进行了较广泛的接触。他关于此行的报告长达60页,最主要的建议是对南方政府采取更现实和更灵活的政策。同时,梅尔提出一种双向的新举措:美国一方面在维护条约的神圣性方面对南方采取强硬立场,但同时又取消对现存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取悦于南方,因为国民党方面肯定会认为这将削弱北方的力量〔14〕。
美国驻华公使支持取消对北洋政府承认的建议。尽管马慕瑞支持这一举措是出于“北京政权缺乏国际责任感”的认知,他也认为,美国不能“承认一个不被中国人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政权的虚假存在”。同时,美国也承担不起“站在与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相违背的立场”这一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马慕瑞敦促国务院“顺应”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建议美国应带头与英、日一起不承认北京政府。但他怀疑日本与英国是否会支持这样的政策,如果他们不支持,则美国应独立地采取此项行动〔15〕。
这是一向坚持与其他列强取合作态度的马慕瑞首次提出美国在中国采取独立行动。而且这一建议得到相关官员的广泛支持。美国出席关税和法权会议的首席代表史注恩(SilasStrawn)支持取消对北洋政府的承认。同时,马慕瑞的建议也得到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的首肯〔16〕。美国驻北京使馆、大多数领事馆和远东司的意见取得一致,在整个北伐期间都非常少见,这就是其中的一次。
但是一向愿意美国保持独立姿态的国务卿凯洛格这次却驳回了这一提议。他从更广阔的中国观念来看待这一举措,认为这是介入中国内政,而由美国来告诉中国人他们没有一个值得外国承认的政府也是不明智的,两者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凯洛格坚持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且,取消对北京政府的承认意味着退出(已停开但理论上仍未结束的)关税法权会议,这显然会触怒美国国内那些支持条约修订的势力集团,从而给执政的共和党带来麻烦。美国不能承担使关税会议破产之责,故即使北京政府不能履行其条约义务,美国也不带头干这种事〔17〕。
与此同时,北京美使馆对北伐的迅速进展密切关注。1926年7月,在梅尔刚回到北京不久,马慕瑞已在计划他本人对南方的访问。从9月中到11月初,马慕瑞访问了南方,其中包括到马尼拉进行短暂停留,但访问的重点是9月下旬的广州之行。这是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位外国公使进入广州,而美国在20年代中国的地位又非同一般外国,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象征。马慕瑞与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接触最多的是能说英语的陈友仁和宋子文。从他们那里,马慕瑞得到“极为坚强的印象,即国民党的确愿意对列强采取温和的态度”。他完全确信“广州当局感觉到他们需要与列强维持友好关系”。马慕瑞与随行的使馆秘书裴克(Willys Peck)都注意到国民党领导人“愿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而不是单方面宣布废约”〔18〕。
但是,这样的乐观见解与后来的事态发展并不完全一致。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特别是中比条约的废除和蒋介石的相关讲话都表明南北双方的主政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显然仍偏于激进而不是温和。在中国南北双方的外交都颇具“革命性”的情形下,马慕瑞仍希望能努力将双方持“理性态度”的力量结合起来,以便美国可与之交涉。在1926年11月,他试探性地向国务院建议:列强应设法说服国民党人及中国其他政治力量将其对内部事务的分歧暂时撇开,而任命一个代表团与列强就关税问题谈判出一个“中国各政治势力都能批准的”协定。在此基础上,由于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竞争的政府,马慕瑞审慎地试图将国务院原来准备与“任何能代表中国的政府”谈判的主张转移到更灵活的与“任何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代表团”谈判的立场上来〔19〕。
此时美国国务院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国内压力,要求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在华传教土及其在国内的本部是这一压力的主要推动力。传教士很可能是最有势力的在华美国社群:在资金上,美国在中国的教会资产“大于所有其他美国在华的产业”;在人数上,在华从事传教事业的人员也“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行业”。而且,正如后来的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所说,这些传教士的观念通过其书信和报告“递达生活在美国大地上几乎任何角落的大量人士”。到1926年下半年,传教士的影响力由于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拉(William Borah)的坚强支持而空前提高,而美国企业界也有诸如拉门德(Thomas W.Lamont)和美亚协会(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代理书记诺顿(Henry K.Norton)等有力人物和机构,与传教士一样主张调整对华政策〔20〕。
所有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就形成一股极大的压力,致使国会很快就作出了反应。1927年1月,美众院外委会主席波特(Stephen G.Porter)提出尽快放弃治外法权的提案,明确要求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独立于其他列强的行动,尽快与“能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政府所委任的全权代表”进行修约谈判。许多传教组织出席听证会支持。提案在众院以262∶4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后虽被搁置在参院.仍给柯立芝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21〕。而且,美国国务院在此期间更受到强烈的外部压力,即列强修改对华政策所造成的挑战。
随着北伐的开始和不断进展,主要列强间早已是竞争多于合作。1926年底到1927年初,英、日两国都较大幅度地修改了其对华政策,特别是修正了对新兴的南方势力的态度。受国民革命反帝运动影响最大的英国,早在1926年11月13日就决定取消对北京政府的法律承认(de jure recognition),而对武汉政府则予以事实承认(de facto recogni-tion)。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抵达中国后首先到武汉将此信息送达国民政府。到11月 底,英国外交部已确定了后来致送列强的对华政策备忘录,英国政府宣布改变其对华政策,不再坚持中国先建立稳定政府然后才谈判修改条约的主张,意在支持南方政府。但这一备忘录直到12月18日才向北京公使团公布,其目的就是要给列强一个措手不及,显示英国政策的独立性。正如英国人自己指出的:此举正是要“让全世界都知悉这一政策是我们的,而并不是反动的不列颠不情愿地被开明的(liberal)美国和日本拖着脚步走。”〔22〕
的确,在中国树立一个“开明的形象”正是当时主要列强竞争目的之所在。1927年1月18日,日本政府也宣布改变其政策,特别是向南方的政策倾斜。〔23〕英日声明对美国外交冲击很大,凯洛格显然不甘落在英国人后面。当时正在纽约的凯洛格是看了《纽约时报》。才得知英国声明的,他对英国人封锁消息的做法极为恼怒,认为“英国人此事的做法太不公平”,并当即指示詹森起草了一份给马慕瑞的训令。训令指出:这次“英国有意要表现得比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列强更开明”,为摧毁这一形象,国务院要马慕瑞立刻宣布,美国赞同“无保留地实施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关税附加税”。三天以后,凯洛格仍余怒未息,还在指责英国“为与美国竞争[在华]影响而不异自我贱售”〔24〕。
为了与英国人竞争,凯洛格已在考虑是否要在此时带头宣布美国愿意在废约方面“主动与中国人配合”。不到一个星期他已给马慕瑞发去一份针对英国备忘录的声明草稿。但马慕瑞反对在此时对中国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他虽然对英国备忘录感到恼火,但仍希望维持列强的合作。同时,马慕瑞坦率地指出,凯洛格的草稿与他本人对中国政策的认知存在着“根本的歧异”;他显然看出了国务卿的情绪 ,并向他提出警告:美国如果“显露出试图比英国人出价更高的形象,是很危险的”〔25〕。而这正是凯洛格意之所在。
最后,还是詹森提出,美国不如干脆不理睬英国的备忘录,而抢在国会就波特提案采取进一步行动前面直接发布一项政策声明。凯洛格于1927年1月24日将声明要点发往驻北京使馆征求意见,但两天后又不等使馆提出意见就发送出正文,指令使馆于次日正式对外公布。可见其急切的心态,同时也说明华盛顿仍未充分重视驻北京使馆的意见。在凯洛格的声明中,美国表示愿意或者与列强一起,或者单独,与中国的任何政府或能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进一步谈判整个条约修订问题。国务院显然采纳了马慕瑞前此提出的灵活观念,并将其扩大到针对所有条约权利的谈判。这一扩大的立场成为此后两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指导性原则,虽然马慕瑞本人对这一扩大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抵制〔26〕。
美国声明与英、日两国政策调整的一个明显不同即在于,英、日两国都明确表达了在南北之间更倾向于南方的立场,美国在这方面则并无明确表白,只是暗示性地说道:“美国政府欢迎中国人民在改组其政府系统方面的每一进展”。这样,华盛顿的政策取向是一方面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层面的谈判,一方面又试图对等对待竞争中的南北政府〔27〕。在此期间中美双方都曾进行过多次努力,试图将南北双方结合起来解决修约问题,但这些努力均未获得实质性的进展〔28〕。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声明中有一句话明显是影射英国而言:“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租界,也从未对中国表现出任何帝国主义式的态度。”当时英国在九江的租界刚被国民政府藉群众运动的力量收回,而运动中有针对性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许多人来说都还记忆犹新。故声明这句话正是试图复制(reproduce)历史记忆的典范。声明同时指出:“本政府愿意本着最开明的精神与中国交涉”。“最开明”(most liberal)一语尤其道出英美竞争的消息。马慕瑞在十年后心境已较平静时,仍认为英美当时的确是争着向中国人讨好〔29〕。
但是,英美讨好中国的举动都不甚成功。英国政策声明发表后的数周内武汉政府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个行动最能体现英国政策调适的悲剧后果。对美国人来说,虽然凯洛格认为他的声明是迈出了“激进的一步”,中国方面的官方反应却是冷淡甚而是负面的。在武汉方面,陈友仁对美国声明未置评论,而宋子文后来甚至说他根本不知道有此声明。比美国新闻界还晚两小时才得到声明副本的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不得不尴尬地对美国新闻界承认他对此事毫不知悉。但他私下告诉已回到远东司的裴克,凯洛格的声明措词“含混”,甚至“不如英国的备忘录那么开明”〔30〕。
不过,主要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在与苏俄竞争对华影响方面却有不可忽视的潜在推动作用。首先,它显然减弱了提倡反帝的苏联外交的影响。假如帝国主义列强真的能够通过谈判吐出不平等条约带来的权益,许多中国人当然可以不必诉诸“革命”的方式。正如胡适和蒋介石都说过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想减弱苏俄在华影响的方式只有一个,即学习苏俄放弃条约特权的榜样〔31〕。换言之,只要列强真能表现出它们不像苏俄宣传所指出的那么“帝国主义”,苏俄的宣传自然不会那么有效。
更重要的是,列强,特别是英、日两国的新政策表明,它们并不像北伐军方面曾经设想的那样全力支持北京政府。对许多国民党人来说,“世界革命”或苏俄援助的象征意义正在于可以抵御他们想像的列强对其北方“走狗”的支持(包括可能的军事支援)。随着北伐军占领地域的扩大,苏俄的援助早已是象征意义越来越大于物质意义,一旦列强对北方的潜在支持不复存在或不像以前所设想的那么坚固,则苏俄援助的意义即随之而降。对国民党或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与苏俄决裂的可能性已逐渐成为一项具有可行性的现实选择〔32〕。
从1926年下半年起,美国国务院就越来越多地接收到关于国民革命运动的内部分歧情况的报告。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以南昌为中心的总司令部与在武汉的党政中心的矛盾日渐明显。到1927年2、3月间,《纽约时报》已在不断报道这类消息;而国务院收到的相关报告也日渐增多,其中确有一些主张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中的“温和分子”或“保守派”的建议。但这样的观点最高只到总领事一级,主要动机是与苏俄竞争在中国的影响;而谁是“温和分子”或“保守派”,却从未被清楚地界定和确认,特别是此时似尚未见将蒋介石列为“温和派”的文件。实际上,1927年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全会议,对美国人来说提示了国民党内部竞争的暂时平息,因为蒋介石公开表示了对党忠诚〔33〕。
1927年2月,詹森获悉英国人有意向武汉政府派驻高级代表,而俄国也在准备正式承认武汉政府并派驻外交代表。同时,中国驻欧洲的使节集体转而效忠于国民政府,国务院了解到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看来中外观察家都已确认北伐将在当年夏天就以国民党的胜利而结束,而此时美国国内要求在对华政策上采取具体行动的压力有增无减。在此情形下,国务院开始明确地向南方倾斜。詹森于3月14日建议,美国应派一个以官方观察员及驻华公使马慕瑞个人代表身份的高级外交官进驻武汉,其具体的人选就是驻华使馆的第二把手梅尔。詹森明确指出,此举有可能得到武汉方面更大的重视,且既能“讨好国民政府”,又能向他们、特别是“美国国内那些急于要同中国(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保持友好关系的人们”表明,我们正诚恳地尽最大努力与中国各方面保持接触。凯洛格批准了这一政策调适,但马慕瑞坚决反对,他指责国务院试图介入中国的内争,有意在南北之争中偏袒南方〔34〕。
值得注意的是,派代表驻武汉的决定是在国务院已获得许多关于国民党内争、特别是武汉与南昌对立的消息后作出的。这清楚表明美国政府直到此时并无在国民党内争中支持或扶助蒋介石一派的意愿。詹森的话表明,国务院此举不乏与列强竞争在华影响及取悦国民党人的动机,但主要仍是对美国国内的压力作出反应。凯洛格虽然没有坚持派高级代表驻武汉的指示,但这一举措提示着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灵活”态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不是不久即发生的南京事件大大缓和了国内的压力,国务院仍不得不对中国革命的进展作出类似的具体因应。
三、南京事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第二天南京城发生北洋溃军和北伐军袭击外国人及其机构(包括领馆)的事件,英美两国军舰向南京开炮,国民政府和列强间最严重的冲突爆发了。在如何解决南京事件的问题上,马慕瑞再次与国务院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事件一发生,马慕瑞即要求与列强合作封锁中国港口,当即遭到凯洛格否定。马慕瑞又坚持要求以军事准备为后盾,与英、日联合提出强硬的最后通牒。凯洛格仍不同意。由于美国的反对,列强未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而是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总部递交内容一致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处有关指挥官、国民军总司令(蒋)道歉、赔偿损失、保障外国人的安全等。4月14日,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分别复照各国,同意赔偿除北洋军和英美炮轰以外的损失,并指出避免此类事件的办法是取消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方面未作任何答复〔35〕。
列强显然不满意陈友仁的答复,合谋进一步以最后通牒施压。马慕瑞也继续强调与列强一致采取强硬措施,但凯洛格同意詹森暂缓处置南京事件的建议,认为等待一段时间以观南方各势力的发展是明智的。凯洛格告诫马慕瑞说:“外国人可以夺占中国领土或在贸易中用武力维护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慕瑞反对凯洛格的态度,指责国务院想走中间道路,实等于挖他的墙脚。凯洛格对马慕瑞的愤怒加以抚慰,但并不改变态度。由于凯洛格坚持不合作而持观望态度,列强未能在南京事件上进一步联合施压〔36〕。
马慕瑞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如果美国不与英、日合作,则将使它们重新靠拢,结果是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将二者分开的政策失败。但问题是英国在1926年末改变其对华政策时也并未事先知照美国,自然没有理由埋怨美国不与它一致。而日本在处理南京事件上显然持相对克制的态度。正如柯立芝总统所说:不同的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利益〔37〕。对马慕瑞来说,采取独立的政策意味着美国放弃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领导地位;而对凯洛格来说,“领导地位既存在于强制行动中,也存在于克制行为中”。换言之,美国采取独立的克制行动,恰可以表现其在列强对华政策中的领导地位。马慕瑞对国务院拒绝采纳他的意见非常沮丧,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他们或者撤我的职或者逼我辞职的时候即将来临。”〔38〕
随着北伐军挥师北上,沪宁地区的局势渐渐和缓下来。而南京事件的的爆发使美国国内在1927年春达到高潮的对中国的同情舆论和参众两院对行政方面的压力都大大缓和〔39〕。许多传教士在修订对华条约方面的态度显然不那么急切,有些人更转而反对修约。这样,在南京事件后,压力大减的国务院几个月来首次能够基本在外交的技术层面比较冷静地考虑其对华政策,此后直到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国务院基本实行了一种相对稳健的一面观望一面准备行动的政策。
观望意味着相对的消极,美国的观望政策最明显的表征即在于,1927年4月的四一二事变及其后的清党不仅未引起美国政策什么改变,反而促成了美国观望政策的确立,助理国务卿詹森注意到蒋介石4月12日的政变,鉴于宁汉之间分裂已经明显,詹森认为对南京事件可暂缓处理,以观国民党内部斗争的结果〔40〕。
实际上,甚至四一二事变后的清党也未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蒋介石一派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在某些方面甚而有所恶化。20年代中国南北双方都面临一个军人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问题。在1927年春的清党开始以后,宋子文曾亲口告诉访问上海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M.O.Hudson):“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这很能代表与“武人”保持距离的一些国民党文职官员的观念。赫氏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41〕。陈友仁后来表示,清党后的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并无两样〔42〕。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早在1926年就报告了广州国民政府内文武势力的竞争,他自己显然倾向于文人一边。这不仅因为与“文人更容易打交道”,而且更因为他们“非常希望培植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并正在努力将两国关系维持在比较和谐的层面”。当然,精琦士也注意到,这些文职国民党人想取悦美国的举动是要把美国从其主要敌手英国方面争取过来〔43〕。实际上,国务院在获悉许多关于国民党内争的信息后,仍发出向武汉政权派驻代表的指示,部分也因为武汉与南昌的争夺正具有文武势力竞争的意味。
美国记者根内特与宋子文的观点相近,他对清党以前和以后的蒋介石的看法迥然相反。在清党以前,他认为蒋有理想,有军事能力,但怀疑蒋能否与人很好地合作,尤其是担心他能否接受文人领导而不是谋求建立个人权威。在清党之后,根内特在为《国民》杂志写的社论(1927年5月4日)中,却正式攻击了蒋。他说,在华外国势力总是要寻找一个中国“强人”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强人”都证明不过是稻草人。西方曾选择了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作为其支持的“强人”,现在又试图选择蒋介石了。蒋固然与北洋的“胡子”军阀不同,但他背叛了他本应忠于的文职政府,且正欲建立一个独治的政府,与北方张作霖政府正复相类。蒋以残忍冷酷的方式对待其以前的文职盟友工会(这一点根内特有误解,上海的工会也有一定的武装),这已超过了(中国)所有以前向往个人权威的统治者。根内特强调:蒋迫害工会的行为不能以“镇压共产主义”来解释,“对一个自称是孙中山那样民主的民族主义的继承者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纪录”〔44〕。这样的社论出自著名的《国民》杂志,美国人对清党的印象决不会好。
如果说根内特和《国民》杂志有自由主义倾向或稍偏左的话,明显反共的美国记者索克思(GeorgeE.Sokolsky),在这个问题上与宋子文的见解一致。索克思根本认为“清党”是“白色恐怖”;他虽然反共,但同时认为蒋在国民革命运动内争中的取胜意味着军人的胜利。从1927年5月起,索克思开始撰文攻击“宁波帮”,到7月更点名攻击蒋为“宁波拿破仑”。索克思觉得,一个由蒋统治的中国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区别。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在军人统治之下,由国民党中亲西方人物所推动的西式现代化进程会因而夭折〔45〕。
索克思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与宋子文和马慕瑞私交甚笃,被认为是当时最了解国民党内幕的外国人。他的见解随时都在向美国使领馆输送。他所担心的最后一点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共同心态。他们当然都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也观察到,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实际上有助于国民党中亲西方成分把中国引向一个接近西方的“现代化”未来,而武汉政权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西化的一个政府。同样,美国政府希望看到一个统一(但未必是强大)的中国,国民革命的分裂和军人作用的增强使得中国有可能出现类似前些年的军阀混战局面,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外交官员对中国前途持悲观态度〔46〕。
在国务院,以前曾是对华积极政策的主要推动者的詹森,其态度就明显比以前消极,他与马慕瑞见解一致的时候开始增多,但凯洛格仍希望有所行动。宁汉的分立使得许多观察家原以为即将结束的北伐又显得前景不明,国务院对南方局势感觉不乐观的一个重要例证是,美国再次开始努力促成一个南北双方的代表团来进行修约谈判。这一举措虽然又没有成功,但凯洛格的确指令詹森和马慕瑞做好修约谈判的所有技术性准备工作。正是由于准备充分,美国才得以在北伐结束后迅速与南京政府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成为主要列强中第一个承认新的中国政府的国家〔47〕。
总的说来,清党之后,除日本人明确决定在国民党的内争中支持蒋外,其他主要列强的外交官更多是感到困惑,因为蒋介石忽左忽右,此前改变其政治立场己有数次。英国公使蓝普森的话也许代表了大部分西方外交人员的共同观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48〕马慕瑞和蓝普森仍然觉得蒋既不可靠也不可信。尤其是马慕瑞,他一度对宁汉分裂基本不予注意,竟然在报告中“全然不提国民党的内争”,连国务院都对这一点感到“有些奇怪”。至少就对外态度方面,马慕瑞没有理由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49〕。
的确,从清党到蒋介石在1927年秋的下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温和”的态度;特别是相对武汉政权而言,南京事件后武汉正实行鲍罗廷提出的外交“战略撤退”,故蒋介石比以前稍温和的反帝腔调与武汉方而同样的降调适成正比。蒋的真正“温和”要到1928年1月他复出后,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全大会的宣言称:“吾国革命之努力,唯一之根本目的,在于民族平等与国家的独立 ,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为达此根本目的之具体的方案……吾国民须知一切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惟有以实际之建设为真正手段者,乃得实践之效果……生聚教训,为独立自强之始基。独立自强,为平等地位之根本。”〔50〕换言之,为达平等的根本目的,重点不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而在自身的建设上。 这正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逐渐在走上攘外必先安内道路的先声。
但是,蒋要面临的外交局势并不轻松。国民党已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英国在华南的势力,在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后,南京又以苏俄外交人员参与暴动为由正式断绝了与苏俄的外交关系。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扩大,苏俄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局限于满洲北部。而蒋在继续北伐的路线上很快将与日本遭遇。鲍罗廷为国民党设计的分化帝国主义的方针与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有相通之处,但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要有两个以上的“夷狄”活跃于中国。这样,在列强均无意轻易放弃其在华权益的大背景下,而美国对华态度又趋消极之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态度未明但素以强硬著称的日本(日本政府对蒋的支持主要针对国民党的内争,在南北关系方面则尚未明确)。结果,正是日本的进一步入侵使南京政府认识到美国在华的重要作用,最终导致中美关系的转折〔51〕。
注释:
〔1〕参见Wesley R.Fishel,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2,p.112;Strawn to Kellogg,May 12,1926,theJohn V.A.MacMurray Papers,the Seeley C.Mudd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
〔2〕MacMurray to Kellogg,Dec.30,1926,MacMurray to Grew,Feb.12,1927,MacMurrayPapers.
〔3〕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1936年版,第617-658页。
〔4〕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25,1926,U.S.Department of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然摇摆不定。
〔5〕Jenkins to MacMurrar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
〔6〕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uey,L(May 1926),pp.181-182.
〔7〕陈的观点见U.S.Department 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hereafter as FRUS),1926,1,851—852。
〔8〕周鲠生:《革命的外交》,收在同名论文集,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1页。周氏后来在中美解决南京事件的协定签订后,认为这是“外交失败”,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军事前进而外交落后”,从而提出“党化外交”的主张,其激进尤可见一斑。参见《今后的外交》,《革命的外交》,第74-84页。
〔9〕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5-360页;MacMurray to Kellogg,Nov.9,1926,FRUS,1926,1,991-995
〔10〕蒋与合众社记者施瓦茨(Bruno Schwartz)会见的内容见于Hankow Herald,Nov.23,1926,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Lockhart)的报告中附有此剪报,Lockhartto Kellogg,Dec.4,1926,SDF 893.00/7993; 并参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910页。
〔11〕MacMurray to Kellogg,Nov.19,1926,FRUS,1926,1,999.
〔12〕Hal1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
〔13〕MacMurray to Kellogg,May20,23,1926,Kellogg to MacMurray,May21,26,1926,FRUS,1926,l,706——709.
〔14〕Mayer's report of mission to South China,July 6,1926,SDF 893.00/7713.
〔15〕MacMurray to Kellogg,Aug.14,1926(两函),FRUS,1926,1,671—681.
〔16〕Strawn to Kellogg,Sept.16,1926,SDF 500.A4e/652 1/2; Johnson's memo for Kellogg,Aug.20,1926,SDF 893.01/228.
〔17〕kellogg to MacMurray ,Aug.24,1926,FRUS,1926,1,682.
〔18〕MacMurray to Kellogg,June 16,1926,SDF 893.00/7532; MacMurray toAdmiral Williams,July 30,1926,MacMurray Papers; Mayer to Kellogg,Oct.3,1926,FRUS,1926,1,868-869;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Peck and Sir Victor Wellesley ,Dec.9,1926,SDF 893.00/7981; China WeeklyReview ,Vol.38 (Sept.25,1926)p.9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92页。
〔19〕Mayer to Kellogg,Oct.3,1926,the State Department to the BritishEmbassy,Oct.5,1926,Macmurray to Kellogg,Nov.20,1926,FRUS,1926,Ⅰ,868-869,855,855-858.
〔20〕Warnshuis to Strawn ,Dec.16,1926,SDF 893.00/8058; William L.Neumann,“Ambiguity and Ambivalence in Ideas of National Interest in Asia”,in Alexander Deconde ,ed .,Isolation and Security,Durham ,D.C.:1957,pp.135-138,史汀生的话引在p.137; 关于波拉与诺顿,参见Dorothy Borg,American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Macmillan,1947,pp.189-190,245-246;关于拉门德,参见Johnson to Kellogg,Jan.12,1927,SDF 711.93/113。
〔21〕波特提案全文见FRUS,1927,Ⅱ,341-343。
〔22〕MacMurray to Atherton,Nov.30,1926,MacMurray Papers;MacMurray to Kellogg,Dec.2,4,1926,FRUS,1926,1.902-906,Dee.11,14,1926,SDF 893.00/7930,/7940: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Wellesley and Peck,Dee.9,1926,SDF893.00/7981;Atherton to Kellogg,Jan.17,1927,SDF 893.00/8140;详细的讨论参见EdmundS.K.Fung,The Diplomacy of Impcrial Retreat: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81-99;Richard Stremski,The Shaping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Taibei:Soochow Univerny,1980.chapters 7 and 8.引文在p.103。
〔23〕参见Mac Weagh to Kellogg,Jan.17,Feb.18,1927,SDF 793.91/1611,893.00/8392;Akira T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65,pp.110-114.
〔24〕Johnson to Grew,Dec.20,1926,Grew to MacMurray,Dec.20,1926,Kellogg toMacMurray,Dec.23,1926,SDF 893.512/7358,/472,/479,/484.
〔25〕MacMurray to Kellogg,Dec.28,1926,Jan.2,1927,Kellogg to MacMurray,Jan.5,1927,SDF 893.512/492,/501;Kellogg to MacMurray,Dec.29,1926,FRUS,1926,1,930-934.
〔26〕Johnson to Kellogg,Jan.19,1927,the Nelson T.Johnson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Kellog to Mayer,Jan.24,1927,Mayer to Kellogg,Mar.26,1927,SDF 711 .93/115A,/115B,/116.声明全文见FRUS,1927,Ⅱ,350一353。
〔27〕Schurman to kelloggg,Dec.22,1926,Mayer to Kellogg,Jan.25,1927,SDF 893.01/249,893.00/8132;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ellog and Sze,FRUS,1927,Ⅱ,52-55.
〔28〕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宽,拟另文详细探讨。
〔29〕马慕瑞后来的评论见其1935年为国务院写的著名备忘录“Development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published with the title How thePeace Was Lost,ed.with introduction by Arthur Waldron (Stanford,Calif.,1992),pp.91-92。
〔30〕Kellogg to Mayer,Jan.24,1927,SDF 711.93/115A; 当马慕瑞在1928年7月告诉宋子文说美国政府早在18个月前就已许诺与中国谈判关税自主时,宋回答说:“不可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回事。”(这当然也可能是宋故作姿态,但不排除是事实)见Abend,My Life in China,p.94; 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ze and Peck,Jan,27,1927,SDF 711.93/124。
〔31〕《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6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
〔32〕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论证,关于蒋介石和顾维钧的相关观念,参见文砥(文公直)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册,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119、163页;《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7—398页。
〔33〕杨天石主编(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二编第五卷的第二章第一节对这段时期的国民党内争有详细而持平的论述;美国人的认知见Anderson to Johnson,Dec.29,1926,memo by George Sokolsky,Jan.1,1927,Johnson Papers;Artherton to Kellogg,Jan.17,1927,Gauss to Kellogg,Feb.5,1927,Cole to Johnson,Feb.1,1927,Warnshuis to Johnson,Feb,5,1927,Jenkins to MacMurray,Feb.16,1927,Lockhartto MacMurray,Feb,8,18,1927,SDF 893,00/8140,/8336,/8218,/8219,/8502,/8459,/8568;New York Times,Feb.8,1927,p.4,Mar.1.1927,P.1,Mar.4,1927,p.4。
〔34〕Warnshuis to Johnson,Feb.5,1927,MacMurray to Kellogg,Feb.15,1927,SDF893.00/8219./8251:Johnson to Strawn,Mar.21,1927,Johnson Papers; Johnson to Kellogg,Mar,14,1927,Kellogg to MacMurray,Mar.18,1927,Macmurray to Kellogg,Mar.22.1927,Kellogg to MacMurray,Mar.21,1927,SDF 893.00/8408,/8408A,/8420,/8428。
〔35〕关于南京事件的详细来往函件见FRUS, 1927,Ⅱ,146-236;国民政府方面的部分文件见于《革命文献》第14辑,第14、2378-2401页,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5-130有扼要而持平的讨论;并参见伯纳德·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第6章,重庆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的史料证明这是一个预谋的行动。在1927年3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表示袭击外国人的是“暴徒”而不是“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柯立芝的讲话载1927年3月3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转引自科尔《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第111页。
〔36〕本段与以下三段的讨沦参见MacMurray to Kellogg,Mar.28,29,Apr.1,23,1927,Kellogg to MacMurray,Apr.25,1927,FRUS,1927,Ⅱ,151,168,173-174,209-210 ,210-211; MacMurray to kellogg,Apr.2,1927,SDF 893.00/8528。
〔37〕关于日本的反应,参见Iriye,After Imperialism,pp.128-133; 柯立芝的话转引自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aese Revolution,p.320。
〔38〕MacMurray to his mother,Apr.24,1927,MacMurray Papers.
〔39〕远东司长项白克承认,南京事件使美国舆论和国会对国务院的压力大减,见Hornbeck to MacMurray,July3,1928,the Stanley K.Hornbck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40〕Memo by Johnson,July 1,1927,Johnson Papers.
〔41〕胡适:《追念吴稚晖先生》,《自由中国》第10卷第1号(1954年1月1日),第5-6页。胡适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1927年与胡适同船从日本到上海的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谈话与此基本相符。参见斯特朗《千千万万的中国人》China’s Millions,the Revo-lutionary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收入《斯特朗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30一31页。
〔42〕1927年9月17日《晨报》,第2版。
〔43〕%Jenkins to Lockhart,Oct.1,1926,cited in Warren W.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 and Disunity: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1925-1938”,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1972,pp.61-62.
〔44〕根内特曾将其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结集成书,由《国民》杂志社出版,即LewisS.Gannett,Young China,rev.ed.,New York:The Nation lnc.,1927。关于蒋介石参见pp.27-31,55。
〔45〕George E.Sokolsky,Tim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32,p.341;关于索克思对蒋的攻击,参见Warren Cohen,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9一14l。到蒋与宋美龄结婚后,索克思又改变了对蒋的评价。
〔46〕参见lriye,After Imperialism,pp.149-150。
〔47〕Johnson to Momroe,May 16,1927,memo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ohnsonand Dr.Hume,Aug.16,1927,Johnson Papers;参见lriye,After Imperialism,pp.150-151;Tozer,"Response to Nationalism",pp.172-177。
〔48〕蓝普森的话转引自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oolution of the 1920s,Hanover:Middlebury College Press,1991,p.258。
〔49〕Peck to Macmurray,Apr.16,1927,Macmurray Papers.
〔50〕《革命文献》第69辑,第189页。
〔51〕关于济南事件后的变化,参见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标签:凯洛格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武汉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人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