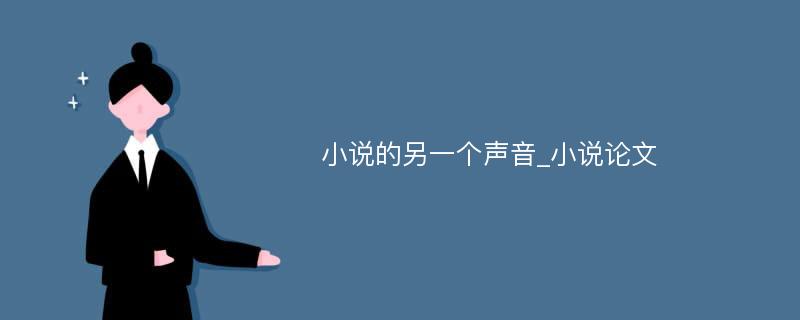
小说的另一种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冯小说无论在其现实性上还是在其艺术想象性上的最重要之处有两个,一是雅俗共赏,二是避开了性与暴力的描写。这些故意模仿小说用很奇特的方式来表现很平常的事情,用很普通的故事来收到很隐喻的效果,形成李冯雅俗共赏的后现代先锋特点。李冯的小说具有一种流畅性和简明性,但这不是说他的作品简单、肤浅,而是说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故事性,以致这些故事本身已把形式和意义融合在一起。他的历史小说普遍运用了故意模仿或戏谑模仿的方式,但隐藏在这种方式后面的却是对于生活发现的透彻性,对于现代生活加以古典性比喻和讽刺的可能。他的古典人物和历史人物在当代生活所面临的困境,对当代生活衰败和混乱给出一种独特的形式和意义,也把一种古典精神的现代锋芒包含在这种复杂而和谐的体系中,以追求一种精神的伊甸园,来解释现代人设想自己处于与古典情境完全相反的处境。故意模仿的核心是戏谑讽喻,轻淡、沉静的嘲讽在这里占了主要地位,这些小说把互不相像的古典人物和他们的现代气质联在一起,依靠古典人物自身的矛盾性和人物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既组织了故事的冲突,也反映了现实的冲突。利用故意模仿的任意性和自由性,李冯组织、控制、容纳了不同情绪和情境于同一故事中。
李冯小说在其现实性上表达了种种普通的生存问题和情感。
1.古典精神的怀恋。古典神和英雄,都表现了古典式的生存态度和道德价值。这种生存精神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武松式英雄特质或牛郎式情感特质,而是用某种精神向度代表着完整的人格追求,这种理想人格包含了人类理想主义的现实化内容。古典作品中的世界,作为一种背景来抬高理想主义,降低现代人的个人主义,嘲讽我们自己。古代人注重精神生存,他们崇拜理想主义、道德价值、人格生存和英雄主义,现代人注重具体琐事,谨小慎微,古典精神已经弱化。
《牛郎》写了传说中的星社——牛郎和织女在世纪末的中国遭遇贬损和平庸化的故事,这种对天神的想象化不幸在现代人间被戏谑化、普通化、悲剧化、平淡化地加以实现:织女因牛郎的经济实力不够而觉得他情感不够成熟,和他离婚。
《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这个对《水浒》的戏仿故事,借古典人物盛装现代情绪,故意毁损宋江和武松这样一直被人们颂扬的形象,破坏他们的古典英雄气质,借对古典英雄主义的戏谑和反讽,表达英雄主义在现代失落的遗憾和怅惘,借古典英雄的颓变,表达现代常人的平庸和委琐。
《另一种声音》中孙行者取经历程非常简单平庸,一路的无聊使孙行者非常厌倦,以至他回到水帘洞便一睡再睡。沉睡苏醒后在世界上的游荡表明对过去的精神追恋。孙行者的游荡与《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在都柏林的游荡相似,斯蒂芬在寻找一个精神之父,孙行者在寻找一个精神之根。古希腊精神和孙行者取经精神的伟大,衬托了斯蒂芬的渺小,而现代精神对孙行者的浸淫,也使他的古典精神日益弱化。
2.欲望的虚幻。把人们的现代问题用古典故事包装,可能很适合人们的眼下口味。《16世纪的卖油郎》中卖油郎所面临的三个问题集中地代表了李冯戏仿小说中现代人面临的困境和疑惑:其一,赚钱的欲望。赚钱的疯狂欲望和美依赖金钱去获得形成一种反讽效果:美只剩下了虚假的外表,美已被金钱的欲望所损害。其二,控制的欲望。卖油郎曾经试图反抗,但这种反抗毫无意义。有趣的是,这种对卖油郎的压力,既包括他的怂恿者父亲,也包括他的诱引者花魁,既是对象化的,又是动力化的,这使卖油郎无处可逃。其三,性的欲望。卖油郎力图对性欲和爱情加以区分,力图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性实现,而这与周围的人对他的要求相互抵触。用花魁的十两银子身份和卖油郎的穷困来描写20世纪未部分中国人的感情失值时,在痛心金钱主宰人性和情感的普遍书写中别有新意。
由于欲望的追逐,古典织女早已蜕变为现代女郎,古典的织女精神早已在现代社会中衰落。使用世纪末用语、世纪末观念的牛郎和织女,不得不重新看待他们的关系,他们的浪漫关系已失去生存的古典土壤,他们只不过构成了一场普通的世纪末婚变。这个现实中普遍发生,又被小说普遍叙说的分居故事,因古典韵味和现代风情的融合而别致起来。人间已失去古典爱情的神性,而《牛郎》则可能在呼唤这种神性。
《另一种声音》中,孙行者的儿孙们都将他忘却了。相反,猪八戒的子孙们却异常活跃地繁衍着,并且发扬光大了猪八戒的享乐精神,沉醉于现代享乐主义。猪八戒的子孙们有不少是猪八戒乱伦的结果,这隐含着现代享乐主义的失控,成为现代生活的讽喻写照,以此怀恋纯朴的人性和英雄主义。
《墙》对于现代欲望的实现有一种困惑的、批判性的中国式哲学解释;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欲望的疯狂实现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反倒有可能是一场彻底的虚幻。
3.真实的怀疑。被当代生存问题层层包裹的人,已经失去了真实性,既无法辨别自己与周围事物关系的真实性,又无法看到外在世界的真实。对于自己和世界存在真实性的怀疑,是对生存价值和意义的破坏,当存在显得可疑时,价值和意义自然有了虚假性。李冯的小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对人们颓废生活和价值实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按照李冯所采取的故事文本形式,故事表现了虚假性对整个现代生活的威胁。李冯在这些作品中所流露的忧虑和恐惧,表明当代生活中已经隐藏着这种商业化怪物。
当代人不可靠的真实性,被强制施行了戏仿的武松真实中。对武松作为英雄的真实性的拆损,实际上是对当代人真实性的怀疑。故事文本中将老虎和打老虎置放于武松的梦幻中,故意将真实和梦幻混淆不清。武松醉梦中怀疑自己的梦是真实的,酒醒后却又对自己打虎真实表示怀疑,老虎和打老虎对武松都不可靠,武松甚至对自己的真实存在也表示了怀疑:他只是个被放置在打老虎传说中的人物,他被人们传说得那么久,以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同样,《牛郎》中的牛郎和曼倩也无法追求到一种真实。牛郎送给曼倩的大礼盒被层层拆去,却始终拆不尽。礼盒中究竟装了什么,牛郎和曼倩都不知道,它是个现代社会的幻影,人们已经劝告牛郎不必知道里面是什么。
《墙》将《崂山道士》中弟子的贪欲和无知颠倒为有知和求真,弟子带着对道的真实存在的疑惑而上山求道。一个古典的不真诚求道的故事,演化成求道不真、真道不可求的故事,演化成既追求真实又厌倦平庸的真实的故事。
4.现实的限制。不论对于精神完整和理想人格的追求,还是对欲望的实现,或是对真实的怀疑,在现代社会都受到限制,在限制中不得不被迫选择是现代人的命运,他们始终陷于一种悖反的困境中。
《我作为英雄武松生活的片断》寓意深长的是,尽管武松对自己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仍不得不成为人们传说中的英雄,人生价值的真实性并没有远离那些控制他、装扮他的事物。《墙》中的限制性规则既是墙又是道,两者的纠缠表现出现代生存限制的重叠交错和极端悖反的复杂情状。墙作为道的一种复杂而具体的暗示,审视了终极存在与具体现实的悖反现象和矛盾关系,仿佛墙是某种不解之谜的一部分。
在《牛郎》中同样产生这样的问题:神性的爱情要求不受到任何世俗限制,但无可限制的神性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爱情和真实不得不在现实的泥淖中实现。《16世纪的卖油郎》、《我作为英雄武松生活的片断》都面临着存在的困境或迷宫。
但李冯的故意模仿小说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表达了现实性意义,不如说在于对小说艺术自身的探讨和小说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些小说标志出他对文本之间、叙述与阅读、小说与现实、虚构与存在、虚构与真实等种种关系的独特理解和处理,并呈现出表现这些关系的具体文本特征和故事风格:
(1)反悖。李冯小说的叙述策略之一,是采取了中国世纪末文学很少见的反悖手法。这些历史故事文本和人物主要依靠对原有故事文本和人物的反悖而生成。反悖是违反现实逻辑和故事文本身逻辑的叙述手法,由于李冯小说反悖形式的故事结局彻底地出乎人们的阅读意料,它们在探求现实方面就具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
在李冯的戏仿小说里,宋江以小人面目出现,武大不忠厚老实,潘金莲也不漂亮淫荡,武松失去英雄气质,牛郎和织女被降低为凡人,卖油郎演变为谋财害命者,孙行者被描写成随波逐流、任时间摆布的玩偶……所有的人物都脱离了故事逻辑和现实逻辑。《水浒》那样轰轰烈烈的历史场景、《西游记》那样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牛郎和织女以及卖油郎和花魁的不渝爱情,都被故事的反悖生成淡淡瓦解,但历史事件、人类情感、理想主义却被用反悖方式加以表达,用拆解它们的方式重新建立它们,用逃离它们的方式重新进入它们。
牛郎和织女的主动离婚、织女的嫌贫爱富、牛郎的漂泊和流落,这些违反原有故事情节和情感的描写,形成一种现实化的效果,借以隐喻现代婚姻的可能失败。
《庐隐之死》采取连续反悖手法,造成一种对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爱情进行评说的奇特效果,将石评梅和高君宇两个人的世界扩展为人间爱情世界,反过来又点化了他俩爱情的深沉和伟大。
《中国故事》以反悖手法描写了利玛窦在中国经历的奇异性:想同化中国的利玛窦反被中国所同化,中国这块土地将一切愿望都化普通为神奇。
(2)叙述失踪。李冯的戏仿故事文本常设置一个悖反古典故事文本叙事效果的圈套,这个圈套主要由叙述失踪或叙述中断造成。
当读者正沿着李冯铺设的情节大道顺畅前行时,突然发现这条大路中断了,李冯诡秘地拐入了一片交错的小径,使你失去了原先叙事的踪影,展现在眼前的景色虽然新鲜,却令你大惑不解:叙述评论、事实报道、剪贴的片断、不连贯的情节、抒情和议论……它们常常令你猝不及防地出现,使你茫然失措。《我作为英雄武松生活的片断》中,武松的事故中突然出现美国科学家的原始婚姻研究报告、《墙》中由墙引伸出现代墙饰和家具、《另一种声音》中对吴承恩墓的考古调查和鉴定,以及各个故事文本中任意出现的报告、杂志、影视等都打断了故事情节的逻辑发展,由古典故事文本的情节世界突然进入20世纪末的现实世界,虚构的堕落现实和历史的突然消失,将古典情怀遭到败坏、古典精神被迫陨落的情境强调出来。现代人的庸碌、渺小与正在谈论的真正历史和古典人物相隔十分遥远,这反而格外强调了对古典理想主义和完整人格的怀恋。
既然叙述中断成为故事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故事文本结构本身便免不了具有片断性。这些故事文本内部的联系,不依从现实逻辑,也不遵循戏仿文本自身的故事规则,而依循它的前文本故事构成连续性。《我作为英雄武松生活的片断》中,武松正在打虎却突然没了结果而进入阳谷县,至于老虎打得怎样并不知道。武松在阳谷县和兄嫂同住也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就来到了发配途中,他为什么变成了被解送的犯人同样不知道。这个小说的标题已标明这是一些片断描写。片断相连或者叙述失踪的部分,要由读者来补充,而读者的补充要依据武松故事的前文本《水浒》来实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为超级读者写的后现代故事文本,它要求读者具备足够的文学阅读知识,片断间的叙述失踪或缺失部分,不可能由戏仿文本的叙述补充,也不可能由读者的任意想象来补充,而要由前文本的内容和读者的阅读理解双重因素来完成。由于李冯的戏仿文本都是中国古典通俗故事,便将这样一种高级化文本巧妙地转化为人人都能读懂的故事文本,使每个故事文本的读者都变成超级读者。
(3)多重叙述声音。李冯的戏仿小说不仅是对故事的叙述,也是对文本的叙述,不仅是对现实的虚构,也是对虚构的虚构。李冯小说的叙述者同时担负起几套话语的角色,小说在几个叙述声音或几套叙述话语之间不停变幻:虚构性话语、纪实性话语、叙事性话语、评论性话语。不同的话语往往来自好几个叙事声音,这些声音在故事文本中相互重叠交叉,众语喧哗。《庐隐之死》中的庐隐朦胧飘渺地在我们之间行走,幽幽地穿行于老舍的北京、真正的历史、对她的评传、对她的虚构故事、她自己的生存、石评梅的友谊和其他几个历史人物之间,仿佛不是这个文本在讲她的故事,而是她主动来到了故事中间,在控制着故事的那种表面混乱,出没于我们和各种有关她的材料之间,以至她能穿越时间和作品,看到叙述者在叙述。
《中国故事》同样由不同的叙述声音和话语构成,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东方与西方、知识与情感被一种利玛窦的神秘体验编织在一起,有关利玛窦的叙述只有一个粗略的故事框架,其中并没有具体的故事和情节,却不断剖析着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与文化。《16世纪的卖油郎》、《我作为英雄武松生活的片断》、《牛郎》等,基本上都以一个故事声音为叙述主干,在这主干上横插入各个破坏这个故事叙述的话语,阻隔、间断、分解故事,正是这种对一个主要故事声音的破坏,引诱读者参与故事的想象。
故意模仿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核心战略,其重要之处是发展了塞万提斯的思想,从一种虚构进入另一种虚构,打破虚构的界限,扩大小说对于世界的包含。从根本上讲,李冯对虚构的虚构是对原有虚构的破坏,也是对自身虚构的破坏:它用原有的虚构破坏了新建虚构。武松、卖油郎、牛郎的传统故事和庐隐、石评梅、利玛窦的真实存在,无疑与李冯的戏仿故事形成对比,历史事实和古典故事使这些戏仿故事遭到怀疑,但它们的意义正是在它们遭到怀疑时才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