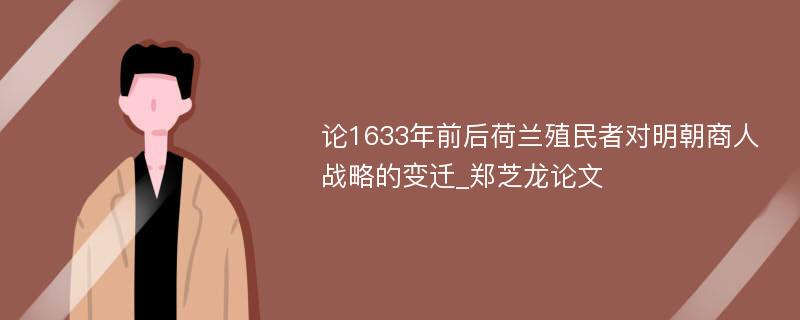
试论1633年前后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商论文,明朝论文,殖民者论文,荷兰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5)06-0048-09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在南部大员港(今台南)一带设立据点收购中国商品,从事对日转口贸易。此后荷方为了掌握台湾海峡贸易的主导权,对明朝海商施展了各种策略,企图利用对方实现以武力胁迫明朝开放贸易的目标。1633年金门料罗湾海战后,荷方调整策略,转而依靠明朝海商充当明荷交涉的桥梁,由此与后者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直到明朝灭亡,在双方合作的背后,矛盾与冲突依然存在,甚至呈现出激化的趋势。如何看待这一时期荷方对待明朝海商的策略及其发展演变,学术界此前已涉及过这个问题。①本文试图就此再作细化分析整理,并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商榷。 一、1633年前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的策略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大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取代葡人与西人以中国货物对日本贸易,从而在日本换取大批银两”。②但由于明朝福建当局一直不允许其船只在大陆沿海停留贸易,所以荷方主要只能在大员向明朝海商收购中国商品。为了发展大员的贸易,东印度公司“下令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例如在大员提高收购价格等,可望吸引中国商人把丝绸运往大员”。③但当局为了保持对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的控制,只对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许心素等少数“官商”发放贸易许可,其他人要想前往大员贸易十分困难。如一名叫六官(Lacquan)的明朝海商便向荷方抱怨称:“他因为公司工作而在中国遭遇极大的困难与痛苦,为此必须花大笔钱财打通关节才能恢复自由。已经跑到这个官员不找他麻烦了,就会又有另外一个官员开始要来办他。弄得他不敢去大员见我们。”④这使荷方难以获得足够的货源,严重影响了大员贸易的发展。 为了摆脱福建当局和许心素的控制,荷方迫切希望得到在大陆沿海自由贸易的权利,认为只有“(使荷兰人)获得上述许可(指派船去漳州河通商的许可),那时公司才能取得真正的利益,享受到期待已久的全面通商交易”。⑤相比台湾,大陆的中国商品充足且廉价。荷方在大员收购的生丝,价格高达每担140两左右,而如果私下派船去漳州河(今福建九龙江)收购生丝,价格仅为每担115两到125两,“司令官认为,若中国准许人们公开贸易,我们甚至可以100两一担的价格收购”。⑥所以,荷方如果能在大陆沿海自由贸易,便能掌握充足廉价的货源,从而夺回贸易主导权。为了迫使福建当局同意其要求,荷方决定在明朝海商中寻求协助,而他们选中的对象便是武装海商。 武装海商是明末中国海商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与一般海商的区别在于拥有强大的武装作为后盾。不少人在从事贸易之外,还兼事海盗活动,具有“亦商亦盗”的性质,甚至敢于同明朝当局对抗,争夺海洋的控制权。而当时的台湾海峡便活跃着郑芝龙、李魁奇、刘香等多股武装海商势力,被福建当局视为心头大患,这也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注意。荷兰台湾长官纳茨便曾向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荷方总部报告称:“我可以奉告您阁下,(当中国人不肯通商交易,而我们要逼他们交易时)公司从这些海盗可以获得多大的益处和帮助。我认为,我们应该网罗他们,支援他们。因为他们连这种(海盗的)力量都无法抵挡,怎能敌得过我们和那些人(海盗)合起来的力量?”⑦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些武装海商的支持,对荷方胁迫福建当局开放自由贸易自然大有裨益。 因此1633年之前,荷兰殖民者一直将武装海商势力视为交往的重点对象,试图将对方拉入自己的阵营,共同对抗福建当局。如1625年郑芝龙势力兴起后,便得到了荷方的大力支持。在1625年10月29日及1626年3月4日的荷方信函中,均提到郑芝龙(荷方文献中称之为一官)的船队“是悬挂亲王旗(princevlaggen)和旒旛旗(wimpels),以公司或荷兰人的名义去(抢劫)的”。⑧“公司按照跟他(一官)约定的办法,取得该船(打劫到的东西)的半数”。⑨纳茨认为,“继续供应他,支持他,使他强壮起来,直到我们取得军门、都督与海道等人承诺的效果,是一件好的事情,至少可以跟他合作到我们要取得完全自由贸易的事情更加清楚和确实起来的时候”。⑩ 1628年郑芝龙接受福建当局的招抚后,其同伙李魁奇率众叛离,盘踞厦门、漳州等地沿海,与郑芝龙相对抗。1629年,荷兰新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便亲自前往漳州河,向李魁奇送去象牙等礼品,(11)希望以此“使他在各方面更热心帮助我们”,从而“让所有商人自由无阻地来跟我们通商交易”。(12)1633年,为了迫使福建当局屈服,荷方决定“对中国发起一场严酷的战争……以获得所希望的自由的中国贸易”,(13)随后便向刘香、李国助等与郑芝龙及福建当局敌对的武装海商势力发出邀请,称“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们并力攻打中国,可以自由来我们这里,如果他们载有商品,我们为要感谢他们,将予全部收购并予付款。而且,我们将允许他们自由通航大员、巴达维亚,以及所有我们有城堡的地方……只要他们能继续使我们自由交易,就能得到我们永远合作的保证”。(14)可见1633年前东印度公司对待明朝海商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对武装海商势力的利用上,将其视为胁迫福建当局开放自由贸易的工具。 不过,荷方的策略并未取得其预想中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这些明朝武装海商势力均是实力雄厚的海上豪强,个个野心勃勃,希望成为台湾海峡贸易的主导者,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充当东印度公司的棋子。如1629年李魁奇控制厦门等地沿海期间,许多海商都不敢运货前往大员,因为“没有他(李魁奇)的许可而带来卖给我们(指荷方),会受到严厉处罚,如果去申请许可,必须付他很多税,多到无利可图”。(15)为了保持对贸易的控制,李魁奇不顾荷兰殖民者一再示好,坚持拒绝开放贸易,称“除非他也有利可图”。(16)荷方恼怒之下,转而与李魁奇的死敌郑芝龙联手。1630年2月,在荷兰舰队的协助下,郑芝龙最终消灭了李魁奇。而作为交换,后者承诺将允许荷方“永远享受”在大陆沿海自由贸易的权利。(17) 但荷方很快发现,郑芝龙和李魁奇、许心素一样,都企图将贸易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希望荷方在大陆沿海自由贸易。如1631年3月15日,郑芝龙便同东印度公司交涉,要求其船只不要继续在厦门停留,称当局将给商人发放前往大员的通行证,而荷方必须“按照几乎他们要求的价格收购他们的货物,连那些不好的有破损的货物也都要跟好的货物一起收购,不然就不来和公司交易了”。(18)发放通行证的权力也完全属于郑芝龙,他“不准任何没有他的许可的商人航往大员……除非他们事先同意,愿意支付生丝5%,布、糖、瓷器及其他粗货7%给他”。(19)无论是郑芝龙还是李魁奇,还是其他武装海商,虽然和福建当局立场不尽相同,但在对待明荷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只希望将荷方留在台湾加以控制,而不会允许其前往大陆沿海自由贸易:“从各种情况已可清楚看出,我们(指荷方)在中国是如何被看待了,他们希望我们离开,远过于希望我们来。”(20) 第二,明朝武装海商对荷兰殖民者的消极合作态度,也与后者的策略有着极大的关系。以郑芝龙为例,如李德霞所说:“荷兰人之所以乐于帮助郑氏集团,是因为他们想借助郑芝龙的力量打开对明朝直接贸易的大门。对于他们来说,郑芝龙只不过是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已,一旦与自己的利益相左,便可随时更换抛弃,不足为惜。”(21)所以当1627年9月福建当局以“事成之后将永久准许其臣民自由到大员和巴城贸易”(22)为条件,请求荷方出兵剿灭郑芝龙时,后者便欣然应允。 1628年郑芝龙受抚后,荷郑双方重新合作。但如前所述,1629年李魁奇兴起后,荷方便与其积极接触。后因交涉未果,才转而与郑芝龙讨论联合对李魁奇作战,要求对方事成之后对其开放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他们又背信弃义地将作战计划泄露给李魁奇,告诉他“如果还愿意表现他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朋友,在两三天内丰丰富富准备好各种商品,并履行他说了好几次的诺言,则我们不但无意使他毁灭,相反地还要用我们的士兵和船只全力帮他”。(23) 林仁川在《评荷兰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中,称荷方这是“为了击败这些海商集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采取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24)不过这一归纳似乎只部分反映了问题的实质。如前文所述,“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目标,只在于要获得自由开放的贸易”,(25)而不是要击败消灭明朝武装海商,相反为了获得自由贸易,他们一直视后者为拉拢的对象。只是由于殖民者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荷方往往采用多头下注的方式,往返周旋于各股武装海商势力之间,谁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便支持谁,“希望公司能够借以得到一个最可靠,最固定的人为公司效劳”。(26) 但对明朝武装海商来说,荷兰殖民者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事作风显然不可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如1633年荷方联络刘香等人时,对方的态度便十分迟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怎么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怀疑这是荷方与郑芝龙合谋消灭他们的诡计。(27)虽然最终刘香同意了联合事宜,但后来明荷双方在金门料罗湾展开决战时,刘香的船只“见势不妙,弃蒲特曼斯长官于不顾,夺路相逃,这就是蒲特曼斯长官率领的船队陷入困境的原因”。(28)正因为上述种种因素,1633年前,尽管荷方多次试图笼络明朝武装海商势力,但成效并不明显,而其获取自由贸易的目标也始终未能实现。 二、1633年后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的调整 1633年10月22日,荷兰舰队在金门料罗湾惨败于郑芝龙率领的明军水师,其以武力夺取自由贸易的迷梦被粉碎。巴达维亚总督布劳沃尔被迫承认:“我们去年发动的战争足以表明,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大员长官和评议会已深深意识到这点。”(29)与此同时,荷方在处理与明朝武装海商的关系时也陷入了十分矛盾的境地。虽然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利用刘香等人的企图,但为了修复与郑芝龙及福建当局的关系,荷方又不敢“为刘香提供任何帮助和支援,也不能与他签订任何协议和条约”,(30)这自然触怒了刘香。1634年4月8日,刘香派兵进攻大员,虽未成功,但双方关系因此完全破裂,这也宣告了荷方利用明朝武装海商策略的彻底失败。 在失败面前,荷方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待明朝海商的策略。明末活动于台湾海峡的中国海商,并不只有武装海商这一种类型。更多的商人经营海洋贸易,依靠的不是强大的武装,而是“中国丝、瓷、糖等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通晓荷兰语及个人的经商技巧和公关的能力”。(31)相比武装海商,这些普通商人实际上更加适合成为荷方的合作对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拓展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虽然徐晓望认为:“对福建商人来说,到台湾贸易其实是对日本和东南亚贸易的一种比较浪费的形式,有同样的货物,不如直接销往马尼拉或是日本。”(32)但由于倭寇问题等历史原因,明朝中央长期严禁对日贸易,这让商人从大陆直接运货前往日本困难重重。于是与福建仅一海之隔、当局控制力又相对薄弱的台湾,便成为明朝海商眼中合适的贸易中转站,“因为此地的位置比任何其他地方对他们都更好,航行时间短,而且对于暴风和海盗的攻击,航来此地也比去其他地方都更安全”。(33)正因为在贸易上的重要价值,所以早在1624年荷方侵占台湾大员之前,当地已是中日走私贸易的重要场所,“每年有日本商贾乘帆船而至,在当地购买大量鹿皮,特别是与中国的海上冒险商做大宗丝绸生意,这些冒险商从泉州、南京及中国北部沿海各地运出大批生丝和绸缎”。(34)在大陆与日本直接贸易渠道尚未贯通的情况下,台湾至少已是这些明朝商人最佳选择之一,绝谈不上“浪费”二字。因此他们与荷方一样,反对福建当局对两岸贸易的种种限制,渴望自由前往大员贸易。而1633年后,随着料罗湾海战的失败,荷方也逐渐退而求其次,不再坚持要求前往大陆沿海自由贸易,转而专心争取让明朝方面“准许我们在大员享受自由贸易,并能运来各种所需商品”,(35)这也让双方的利益更加趋向一致,从而奠定了彼此合作的基础。 而且,普通海商并没有争夺贸易主导权的实力和野心。他们十分乐意依附实力更为强大的荷方,为其获取自由贸易提供协助。一名明朝海商便曾直截了当地对荷方表示,只要让他们能赚一点点,荷方便不致缺货了。(36)所以对荷方而言,这些没有武装的普通商人更加容易驾驭。 最后,虽然普通商人没有武装海商那么强大的军力,但他们大都长期经营两岸贸易,有着与福建当局周旋交涉的丰富经验,懂得如何运用赠礼、游说等各种手段抓住官员的心理,这种特性使其正适合充当明荷关系的黏合剂。所以1633年后,荷兰殖民者逐渐加强与普通海商的合作。1633年12月,荷方决定委托大员的著名商人Hambuan前往大陆修复与明朝方面的关系,“要跟中国铺出和平自由的贸易之路”。(37) 在执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Hambuan等海商充分显示了精湛的公关手腕。一方面,他们代表荷兰殖民者大肆馈赠礼品,对明朝官员宣传荷方之前剿灭李魁奇等“功绩”,以改变其对荷兰人的印象。当Hambuan成功打探到福建当局对荷方船只不去大陆沿海这点十分执著,同时又正因战争损失而困扰的心态之后,便趁机建议对方应尽快开放商船运货前往大员。(38)这样既能稳住荷方,让其不致重新开战,又能避免荷方派船前往大陆沿海贸易,这自然让当局难以拒绝。另一方面,Hambuan也尽心向荷方传授取悦当局的方法技巧,应该“按照中国的习俗,用请求的口吻写得文雅,礼貌一点,不然,他们还会对我们生气,不跟我们和平来往”。(39)同时他还转述郑芝龙的话,称“用战争是捞不到好处的”,让荷兰殖民者放弃增兵再战的打算,并建议荷方扣留刘香在大员的船只。(40)这些都对交涉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1634年,明朝当局最终决定给前往大员的商船发放官方通行证,“使所有的商人都能自由地用上述戎克船(于缴付国税之后)来大员跟荷兰人交易,就如同跟前往所有其他地方交易那样”。(41)荷方多年来自由贸易的心愿,终于倚仗明朝海商的协助而得以部分实现。 三、1633年后荷兰殖民者与明朝海商的合作 1633年后,荷兰殖民者调整了其对华政策,放弃了联合明朝武装海商胁迫当局开放大陆沿海自由贸易的策略,转而加强与普通海商之间的合作,利用后者向明朝福建当局疏通交涉,最终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在台湾大员自由贸易的权利。徐晓望认为,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本质上是明朝海商对荷方做出了妥协: 荷兰人对台湾海峡的入侵,使他们获得了一半的台湾海峡控制权,并在不断的骚扰战争中,迫使中方承认荷兰人占据台湾的现实,同意与其贸易。对福建商人来讲,他们为了不再受到更深的损害,被迫将原有利润中的一部分分给荷兰人,以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42) 这一观点并非没有根据,大员自由贸易的开放,确实可以看成是明朝方面的妥协,但这一妥协却并非出自明朝的广大普通海商。相反,他们同样是此次妥协的获益者。由于荷兰殖民者此后不再派船前往大陆沿海,只能坐守大员,依赖明朝海商运货上门,从而导致两岸贸易主导权此后依然牢牢掌握在后者手中。关于这点,张彩霞、林仁川等前辈学者已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述。(43) 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另一方面:对明朝普通海商来说,自由前往大员贸易是其一直以来的强烈愿望,在此问题上,对其利益损害最大的并不是荷兰殖民者,而是对贸易进行限制的福建当局,以及企图独占贸易的郑芝龙等武装海商势力。因此明朝方面此次的妥协,实质上也是后两者对广大海商做出的妥协。海商得以光明正大地冲破明朝当局的阻挠,从两岸贸易中分一杯羹。“因为现在允许前往大员通商的戎克船要缴纳国税(以前都只是偷偷地去交易的,未缴纳国税),因此将来即使官吏要阻止或禁止这种通商,也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必须每年呈缴收到的税金”。(44)不少民间海商如Hambuan、Jocho、Jocksim等人此后终于能够合法地经营两岸贸易,而且由于他们与荷兰殖民者的合作关系,荷方也愿意为其提供优惠:“只要运来好的,不掺杂的布料和丝,我们将乐意多付一点价钱给每一个人,并承诺将来会这么做。”(45)尽管福建当局颁发的通行证数量有限,且每三个月就需更换一次,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商人们的贸易热情。仅在1655年3月便有四艘商船满载生丝、瓷器等货物到达大员,总价值达12万里尔。荷方对此自然欢欣鼓舞,称“在这以前,公司未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中国收购到这么多的货物……使公司终于得大尝她屡次竭尽全力以赴的所期待的中国贸易的果实。”(46) 荷兰殖民者还利用这些海商充当交涉中间人,以加强与福建当局的关系。如1637年1月,Hambuan受荷方之托前往大陆,“去向大官们和所有商人们更加保证公司的富裕和对中国贸易的真诚”。(47)在大陆期间,Hambuan得知当局将派官员Limbing前往大员调查贸易状况,立刻将这一消息提前通报荷方,并建议“要按照他的身份接待他,好好款待他,让他做一切他要做的事,因为这对公司只会产生更好的结果,更确保贸易的进展”。(48)荷方盛情款待Limbing的到访。让其回去后“向中国的大官们转达公司的好意”。(49)1639年2月,荷方又付给Hambuan“价值1719.2.0荷盾的布匹,也赠送商人Jocho和Jocksim分别为232.12.0和101.10.0荷盾”,委托他们代表荷方向明朝官员赠礼。(50) 而在这些交涉对象中,海商最为重视的当然是身兼福建当局官员与武装海商领袖双重身份,对贸易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郑芝龙。尽管普通海商与郑芝龙之间在两岸贸易上存在着竞争关系,Hambuan等人也不时抱怨“一官的亲信排挤他,跟他抢生意”,(51)但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贸易权利,海商们也只能接受贸易主导权为郑芝龙所掌握的现状,并不惜血本与其保持关系,担当在郑荷之间牵线搭桥的角色。如1639年2月Hambuan带着荷方礼物到达大陆后,第一个拜访的便是郑芝龙,“向他阁下详细报告关于公司贸易的所有情形”。(52)他甚至将礼物又增加了一半,并亲自安排船只为郑芝龙护送某位官吏回乡,传说“这一趟花掉了他在此地赚一年的钱”,(53)可见其对郑芝龙的重视程度。 海商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Hambuan等人“一再去跟贸易所依赖的大官们打交道,极力说明贸易的好处”,福建当局对两岸贸易的态度逐渐趋向积极。海商“一旦缴纳皇帝的关税,中国地方官员和其他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有意刁难他们,他们甚至被允许公开销售从大员运回中国的货物”。(54)地方官员之间甚至还出现了争夺商税征收权的现象,“每一个都要征收运来此地的货物税,或至少要向他们各缴纳一半;泉州的海道说,因为通行证是他们发行的,而漳州的海道则说因为那些戎克船大部分在他们那里出入港的”。(55)为了平衡地方利益,当局也乐于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1634年9月,“漳州与泉州的海道及其他几个大官……要在上述三张通行证之外,再允许发放两张通行证给我们的人,以便从漳州的人及泉州的人平分征收国家的税,并使更多货物运来给我们(指荷方)”。(56)1635年3月,“在几个商人的请求下”,当局又决定给前往大员的商船加发六到八张新的通行证,并下调税额。(57)Hambuan称:“他们已经显然乐于继续贸易,不会改变,无可怀疑地,贸易将进展成功”。(58)而在不挑战其贸易主导权的前提下,郑芝龙也乐于接受海商们提供的好处,让其参与到两岸贸易当中,乃至通过海商与荷兰殖民者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如1634年两岸贸易开放后,不少商人即便没有申请到通行证,也可以搭乘郑芝龙的船只前往大员贸易,而且这样“在中国就不必缴纳应缴的税金”。(59)1639年,郑芝龙还委托Hambuan联络荷方,“让一官每年以他自己的账目,用公司的船只载运价值200,000荷盾的货物去日本,相对地,一官将供应公司要运往日本、祖国和东印度地区贸易所需要的,直到价值100到120吨黄金的货物”。(60)这种局面的形成,对两岸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上可见,1633年后,明朝海商在改善明荷关系,拓展两岸贸易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两岸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而荷方也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根据李德霞的计算,荷兰在大员的生丝转口贸易,收益率可高达73.3%到85.7%。(61) 四、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的局限 1633年后荷兰殖民者对明朝海商策略的调整,确实使其与后者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也存在着根本上的局限性,让双方的合作关系难以长期维持。 荷兰殖民者在亚洲的根本战略目标,是排除西班牙、葡萄牙等竞争对手,独占中国、日本的贸易,树立荷兰的殖民商业霸权,这是由殖民者的本性所决定的。和这一目标相比,与明朝海商的关系只能摆在次要位置。因此荷方为了维持其在台湾的贸易,对明朝海商采取了以合作为主的策略,但在台湾以外的地区,特别是被荷兰殖民者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东南亚地区,其对待明朝海商的策略却十分蛮横霸道,一旦后者在这些地区的活动侵犯到了荷方的贸易利益,便会遭到他们不遗余力的打击,这点从未发生过改变。荷方对明朝海商所实施的此种打击破坏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针对前往西班牙、葡萄牙等荷方竞争对手控制地区贸易的中国商船的劫掠,其主要目的在于破坏竞争对手的贸易,以打击削弱对方。西班牙控制下的马尼拉、鸡笼(今基隆),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均受到荷兰舰队的海上封锁,如有中国商船从事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便会成为荷方的劫掠对象。 二为针对与荷方从事相同贸易,彼此间有商业竞争关系的中国商船的劫掠,其主要目的在于排除中国海商的竞争,以维护荷方的利益。荷兰殖民者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视为其贸易势力范围,不容中国海商染指。“没有我们(指荷方)的许可驶往北大年、渤泥、占碑、旧港、万丹、亚帕拉、交唐、比马(Bima)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帆船”,都将遭到他们的拦截。(62) 荷兰殖民者试图通过这种海盗策略限制明朝海商的贸易,将其驱赶至大员和巴达维亚等荷方控制下的地区。虽然1633年料罗湾海战失败后,荷方已不敢再派船前往大陆沿海骚扰,但对远航东南亚地区的明朝商船的袭击依然从未停止,就连那些与荷方有着合作关系的海商也不能幸免,这便是荷方策略最大的局限性。1636年,明朝海商Bendiocq名下的一艘商船前往占碑(今苏门答腊)贸易,与荷兰船只遭遇。尽管其属下船员一直向荷方强调Bendiocq“在各方面帮助荷兰人,从来不遗余力”,但对方依然毫不留情地将船货洗劫一空,令Bendiocq愤怒不已,写信向荷方控诉,(63)然而对方根本不为所动。1638年,巴达维亚总督范·迪门宣称:“我们坚持决定拦截占碑和旧港等地的船只,断绝中国人前往这些港口的航路从而逼迫他们前来我处。”他甚至还得意地表示:“在占碑附近拦截Bindiock(64)的帆船(有人因此而忧虑重重)造成怎样的结果?没有人再提及这件事情。”(65) 荷兰殖民者如此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马尼拉白银市场不景气和澳门对日本贸易中止的情况下”,只要坐拥大员这块贸易宝地,就算在其他地方再怎么胡作非为,明朝海商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66)但这种想法成立的前提,是明朝海商能在大员赚到足够的利润。17世纪30年代末期,这一点开始成为了疑问。随着大员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荷方有限的购买力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明朝海商的贸易需求。 早在1637年,荷方便已接到大员方面的报告,称“贸易繁盛致使资金短缺,我们的人急切盼望着日本的救援,但迟迟未能得到”,(67)这导致他们常常无法按时向明朝海商支付货款。巴达维亚总部警告称:“这种局势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不然一切将如烟消云散。”(68)1639年后,由于缺乏现金,荷兰殖民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吸引明朝海商而为其提供各种优惠,反而一再提高商品的收购标准,这大大影响了对方的贸易利润。1639年11月4日Hambuan在写给荷兰台湾长官的信函中称: 阁下只要新的和好的货物(将以好的价格支付),其他货物不要。商人们都不同意地说,去年他们只获得2.5%的利益,那是很少的,而现在则还不到2%,他们都来找我理论说,我是个说谎者,用谎言欺骗他们,因为我对他们说过,那里存有足够的现款……这事到处传扬,也传进官员一官的耳朵里了,他对此非常震怒。(69) 因此,既然明朝海商在大员已逐渐无利可图,同时在其他地区的贸易利益又一再受到荷方海盗策略的侵害,1640年后,前往大员的明朝商船数量开始明显下降,“其真正原因在乎公司在台窝湾(大员)无现银,而无现金时,狡猾之中国人不愿携带货品前来台窝湾”。(70)除此之外,商人们此时已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贸易航路。到了17世纪40年代,“虽然明廷没有解禁对日贸易,但在郑芝龙的操作下,开通了厦门、安海到长崎的直接贸易,对日贸易进入半合法状态”。(71)这对大员作为中日贸易中转站的地位是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海商自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大员贸易,而是直接将商品销往日本,与荷方公开竞争。仅1643年,“中国人今年运至长崎的丝和极有用处的丝织物,价值f.4,500,000多”,(72)其数量之巨大令荷兰殖民者根本无力竞争。荷方哀叹道:“今年将只有中国人在日本贸易,而我们,照他们的做法看来,将只有失望而已。”(73) 于是荷方的殖民强盗本性再次显现。巴达维亚总督范·迪门咬牙切齿地表示:“如果公司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把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74)1643年6月4日,荷方召集大员的明朝海商,宣称将派遣舰队巡航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航道,“要他们知道,铭记在心,回中国以后还要广为宣传,叫大家及时停止航行,以免将来遭受损失”。(75)明朝海商拒不屈服,警告称“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商人不会放弃前往日本贸易”,如果荷方“捕捉了官吏一官的戎克船,他会完全断绝大员的贸易”。(76)日本当局也坚决反对荷方的这一行为,甚至试图强迫荷方“书面签字以性命担保不损坏任何来往于日本的中国帆船”。(77)虽然荷兰殖民者拒绝了日方的要求,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搁置了这一计划,表示“我们不会阻拦北部地区甚至来自漳州和广州两省的中国人率小型帆船前往日本(正如在我们到达那个国家出现之前葡萄牙人的做法)”。(78)但另一方面,为“使公司沉重的负担因此而得以稍获补偿”,(79)荷方对在东南亚各地贸易的明朝商船的拦截却变本加厉。1644年5月,一艘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遭到荷兰船队袭击,多达120名中国人惨遭杀害,另有240人被掠走。(80)1645年,荷兰殖民者又洗劫了两艘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夺走的货物价值高达f.277,629,125。荷方恬不知耻地声称,这种做法“缓解了贸易的不景气”。(81) 因此,17世纪40年代以后,荷兰殖民者对待明朝海商的策略逐步由合作走向对抗,从本质上说,这是明朝海商要求自由发展海外贸易与荷兰殖民者企图垄断对华贸易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明朝海商来说,荷方占据台湾对明朝海外贸易的破坏作用已经明显超过正面影响,只有将这帮殖民侵略者驱逐出台湾,彻底解除其对中国的海上经济、军事威胁,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明朝海商的利益,然而明朝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了。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明朝灭亡,随后清军入关南下。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郑芝龙垮台,东南中国海商势力再次陷入混乱。因此明朝海商的这一愿望,直到近二十年后,才由中国海商的新领袖郑成功代为实现。 注释: ①林仁川《评荷兰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将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争夺战中使用过的各种政治、军事手段进行了分类归纳,但对其总体方针策略的演变过程缺乏分析;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李德霞《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文对此问题也有涉及,但各方观点不尽一致,且尚有论述未尽未及之处。 ②③⑥(13)(22)(28)(29)(30)(34)(35)(54)(62)(65)(66)(67)(68)(72)(74)(77)(78)(81)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2000年,第12页,第65页,第77页,第126页,第78页,第143页,第147页,第148页,第28页,第158页,第158页,第203页,第203页,第221页,第188页,第193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51页,第259页,第271页。 ④⑧⑨江树生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书信集(一)》,台南:台湾历史博物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0年,第266页,第240页,第266页。 ⑤⑦⑩江树生译注:《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书信集(二)》,台南:台湾历史博物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0年,第20页,第4-5页,第81页。 (11)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29年12月13日,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年,第8页。 (12)(1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29年12月20日,第9页。 (14)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3年7月27日,第109页。 (1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0年1月3日,第11页。 (1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0年2月13日,第18页。 (1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1年3月15日,第41-42页。 (1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3年9月15日,第123页。 (2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2年1月11日,第66页。 (21)李德霞:《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0年2月1、2、3日,第14页。 (24)参见林仁川:《评荷兰在台湾海峡的商战策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3月22日,第151页。 (2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29年12月24、25、26日,第10页。 (2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3年8月28、29日,第118页。 (31)参见杨国祯:《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2)(42)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3)(36)(45)(5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5年3月7日,第199页。 (3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3年12月30日,第141页。 (38)(39)参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3月7日,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年,第148-149页。 (40)参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2月3日、3月7日,第145、149页。 (41)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10月21日,第185页。 (43)参见张彩霞、林仁川:《中国海商:17世纪台海贸易的主导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4)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12月31日,第195页。 (4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5年3月19日,第200页。 (47)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7年1月4日,第280页。 (4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7年3月4日,第296页。 (4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7年3月29日,第305页。 (5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9年2月16日至3月12日阙漏,第424页。 (51)(5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10月21日,第186页。 (52)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9年3月24日,第427页。 (5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9年3月27日,第429页。 (5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10月4日,第184页。 (5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4年9月19日,第181-182页。 (58)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7年5月22日,第316页。 (6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从1639年12月10日到1640年1月28日的补充资料,第467页。 (61)参见李德霞:《17世纪上半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经营的三角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6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6年11月12日,第270页。 (64)Bindiock即Bendiocq,参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索引,第17页。 (6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1639年11月11日,第460页。 (70)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译:《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二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第322页。 (71)杨国桢:《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73)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二册,1643年8月26日,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189页。 (75)(76)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二册,1643年6月4日,第148页。 (79)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二册,1643年5月24日,第142页。 (8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二册,1644年5月26日,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