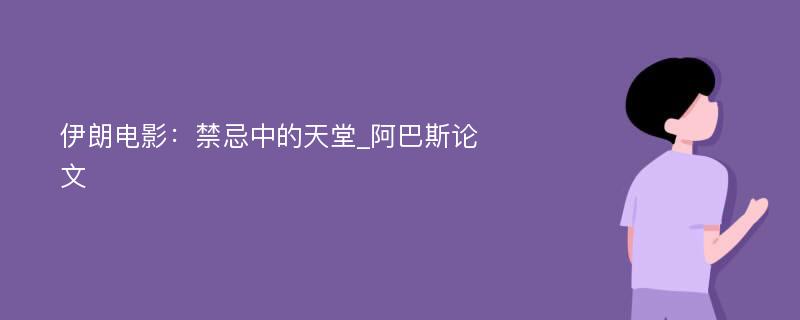
伊朗电影:禁忌中的天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禁忌论文,天堂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恋人上了公共汽车,一个在车厢前部,一个在车厢尾部,男青年手捧鲜花,隔着 一段距离,定定地看着自己的女友。它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久违的词句:男女授受不 亲。这就是伊朗,一个充满禁忌的国家。即使是一个小姑娘,她也必须裹着长长的头巾 ,到妇女区的车门口上车。这是伊朗电影《谁带我回家》提供的一组画面。正像我们借 助好莱坞大片完成我们对美国社会的想象一样,我们通过伊朗低成本影片建立起对伊朗 社会的想象。电影的文化传输功能,将它的民族国家的价值立场毫无隐藏地呈现了出来 。
这些影像中的人群看上去没有太多的愁苦,至少他们表现出的是这样。身在禁忌之中 却感受不到禁忌,他们的心灵锁住了天堂。
人的感受有多么重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哪一种方式对人 来说更适用?自由是一个无法阐述清楚的题目,弗罗姆用逃避自由这个概念来为生命的 荒诞和无常寻求开脱,但同时这一切又必须以人首先获得了自由为前提。人永远都摆脱 不了困境,然而总有一些顽强的人群却在地上寻找到天堂。天堂无处不在,天堂是属于 自我的“一种美好体验”。
困境中的美好
第一次接触的伊朗电影是由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1994年执导的影片《橄榄树下的情 人》,它后来还有一个译名,叫《穿越橄榄树林》,似乎更准确一些,这样说是因为这 个名字不仅富于动感,而且它还忠实地反映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穿越橄榄树林这个高 潮段落。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称他们是一对情人很不合适,他们正处于男孩子追求女孩 子的阶段,女孩子自始至终很少说话,不知是羞涩,还是拒绝,但仅仅表现这一过程就 已经很美好了,何必过分地关注结果呢?
故事发生的背景极具反差性,这个地方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的洗劫,一个电影摄制 组来到这里,拍摄人们震后的状态。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以群众演员的身份参加了剧组的 工作,女孩子还从家里抱来了一个花盆作为道具。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剧中扮演一对新婚 夫妻,丈夫要出门,在门口的台阶上翻来覆去地重复穿靴子的动作,因为男孩子的心思 放在女孩子的身上,他利用拍摄的空隙向女孩子发起求爱的攻势,所以同一场戏拍得总 是达不到理想。从男孩子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我们了解到震前小伙子已经和姑娘的奶奶 谈过了,姑娘的奶奶同意小伙子向自己的孙女求婚,尽管奶奶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但小 伙子记住了奶奶的承诺。
导演阿巴斯在这部影片里运用了不断重复的艺术手法,将小伙子穿靴子这一戏中戏的 反复的拍摄过程纳入影片的结构,像波浪的舞蹈,呈现出独特的电影韵律。这十年我们 习惯了好莱坞电影制作快速切换所带来的眼花缭乱和狂轰乱炸效果,对与其相反的美学 探索倒充满新奇之感。亚洲人出身的电影导演普遍倾向于在一种慢节奏中捕捉审美的韵 味。代表东方世界最先在国际影坛引起巨大轰动的中国台湾本土电影大师侯孝贤在这方 面不仅登峰造极,而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美学立场,在电影界,侯孝贤的名字等同 于长镜头这一电影概念本身。与伊朗导演阿巴斯在这部影片表现出的趣味很相似,侯孝 贤在《好男好女》中表现台湾热血青年奔赴大陆参加抗日武装——接受审查的那个叙事 段落,几乎是一个全面的纪实过程。在低调的光影下,空间里回荡着单调而重复的一问 一答声,当它处于运动状态下的近距离的表现时,我们的确要忍受它的冗长,但当它最 后化解于渐起的抒情的弦乐气氛时,一段凝重的往事,被时光之手推向了远处,它因此 成为了极具力量核心的华美乐章。近几年堪称国际影坛新锐的法籍电影导演陈英雄承袭 了这一美学趣味,他在《青木瓜之味》一片中将镜头不断地给予附着在青木瓜枝叶上的 露珠和露珠的运动,让它们在时间上获得一段持续的停留,以显示时间的韵律和节拍。
在我看到《樱桃的滋味》这部影片的同时,传来了阿巴斯导演的影片《樱桃的滋味》 在嘎纳电影节上与日本今村昌平导演的影片《鳗鱼》并列荣获金棕榈大奖的消息。这是 伊朗电影首次在国际影坛上获得领衔的地位。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在世的时候给予阿巴 斯极高的评价,他用印度电影大师雷伊来和阿巴斯比较,他承认雷伊去世的时候,他很 伤心,但是他接着表示看到阿巴斯的影片后,他认定“上帝派这个人来是为了接替雷伊 的”。《樱桃的滋味》与《穿越橄榄树林》一样,它表现的也是一种困境,只不过这一 次它把镜头对准奢侈的有闲阶层人士,一个城市里的中年人开着车四处游荡,他想雇人 了结他的生命。一个雨夜,他躺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等待死神的降临,可是第二天的 早晨他被士兵们的报数声惊醒。在这里,阿巴斯选择了一个开放的结尾,中年人爬出土 坑出现在拍摄的现场,一下子扫尽了沉闷和压抑。阿巴斯总是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影踪 ,他不甘心现实的沦落。
如果让我在这两部影片之间进行比较,我还是心仪《穿越橄榄树林》这部影片。我喜 欢它的至纯至善,它所表现的人们在困境下的一种沉静之美,巨大的灾难没有动摇人们 对实现生活美好愿望的努力,没有影响人们继续去谈情说爱。正像影片中那个女孩子怀 里抱着的盆花一样,生命总是顽强地散发着热情。
需要注意的是,伊朗影片中所反映出的伊朗人民对文化的崇尚之心,让我们对他们的 内在民族精神充满敬意。在《穿越橄榄树林》中,男孩子真挚地向女孩子表白,正是因 为我没有文化,所以我才要追求你,我不想让我的下一代没有文化。同样的理念,还反 映在萨迷拉导演的影片《黑板》里,影片一开始,从山路的拐角处出现了一群背着黑板 的男人,他们的身份是教人识字的老师,在一个岔道口,两个男老师分手,一个进了村 ,一个上了山。一个与偷运私货的孩子同行,教他们识字,以换取一块干粮;一个加入 了逃难的人群,跟一位带小孩的妇女草草组成了动荡的家庭,用黑板抵挡呼啸的流弹。 画外不时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枪声。但是,老师的黑板追逐着这些漂泊的人群,提示着 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的存在。
《黑板》荣获第53届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年仅20岁的女导演萨迷拉·马克马巴夫 闯入了人们的视线。
萨米拉依靠电影世家的优势先行一步进入影坛,1998年18岁的她执导了《苹果姐妹》 一片,探讨了伊朗文化对女性的特殊规范。一对小姐妹尝试着要走出小屋,展露对外面 世界的好奇心,而老父亲固执地认为,女孩像花朵,放在太阳底下会枯萎。萨迷拉初出 茅庐就显示出对此类敏感题材的迷恋和特殊的驾驭才能。
一方是困境,一方是人们心头执著绽放的梦的花朵,它开得美丽而灼人。
即使是一桩显而易见的悲情故事,伊朗电影也完全杜绝伤感主义的滥觞。
由阿巴斯担任编剧的第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让风带着我飞》,讲述的是一 个男孩子补玻璃的故事。和许多的伊朗影片一样,这部电影也设置了一个事件的障碍与 前提,就是这个男孩子必须在天黑之前把教室的玻璃补好,否则明天无法继续上学。故 事的叙述过程很细碎,包括玻璃的尺寸有些拿不准,途中男孩子抱着大玻璃几次临近险 情,让我们为他提心吊胆。终于把玻璃弄回了教室,玻璃的大小幸好合乎尺寸,可是他 得需要一个帮手,这时学校里已经没有人了,正在孩子绝望之时,一个校工骑着摩托进 了校园,风雨中校工没有听见孩子的呼唤声。如果此时校工多逗留一会儿,下面也就没 戏可看了。校工骑着摩托很快离去,带走了男孩子最后一点希望。男孩子只好背水一战 ,用两个小钉子简单把玻璃固定好,转身到教室门外去拿锤子。我们共同担心的事情还 是发生了,在教室的门被打开的一瞬间,男孩子听到身后传来玻璃粉碎的声音,一切都 停止了,世界变得一动不动。时间陪着男孩子的心情停顿了下来,这时,影片出现了一 组空镜,空寂的教室走廊里几个日常不被注意的角落。
假如影片在这时候结束,它会让我们的心情沉落到底,当然电影没有这方面的义务, 一定要为观者一天的生活情绪负责,但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还是获得了一个启示,影片结 尾的调子是可以昂扬起来的,只要它贯穿着真实的理想。更主要的是我们面前的这名男 孩子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记住了卖玻璃的老头的话,如果有什么不合适,他可 以在晚上七点前找到他。男孩子重返来路,这时画面是一个大远景,天际一抹晚霞制造 出温暖的色调,山路上男孩子遇上了他骑摩托的好朋友,好朋友带着男孩子驶向他要去 的方向。这个结尾强化了我们对生活的信仰,这样的主旋律让人接受起来顺理成章,同 时我们也获得了一次愉快的观影经验。
简单中的曲折
《小鞋子》、《白汽球》、《谁带我回家》等一批伊朗儿童电影在国际影坛胜出,聪 明的伊朗电影人沿着成功的线路,乘势而上,连连出手,将伊朗儿童电影终于打造成伊 朗电影的一个黄金品牌。提起伊朗电影,人们的眼前就会浮动出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蹦 跳的身影。
孩子是伊朗电影人偏好的选择,他们是纯洁、自由和葱茏诗意的化身,是幸福生活的 隐喻,他们是从特殊角度曲折表述的文化宣言,是意义的代码,是诠释伊朗国家意识形 态的一个生动注脚。谁看到这些天真质朴的面孔,不会认为这是人间天堂里最新鲜的花 瓣?它们从艰辛的生活土壤里脱颖而出,显示出生命持久的张力。由伊朗儿童电影搭建 起来的这个精致而独特的价值体系,足以跟庞大而虚张的美国好莱坞爱国主义和英雄主 义抗衡,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孩子这一祖国花朵所起到的文化大使的作用,孩子是 积极人生的写照,无论怎样艰辛悲伤的内容,只要孩子们出现了,就好似一粒烛光照亮 了整个黑暗的隧洞,而它所带来的希望资源是无可限量的。
马基德·马基迪是这一希望资源的打造者和贩卖者,这位伊朗第三代电影导演中出类 拔萃的人物,开创了伊朗儿童电影的纪元。《小鞋子》又名《天堂的孩子》,是马基德 ·马基迪的导演代表作,它围绕一双跑鞋讲述了一对兄妹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 单的故事,但这个简单的故事却一波三折。在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我首先看到的是它的 一个小故事梗概,我把它剪了下来,并推荐给朋友,我只要讲述第一个情节段落,你就 会发现从故事结构上看,它拥有一个多么出色的文学脚本。哥哥去鞋铺取妹妹修理的鞋 子,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把妹妹的鞋子弄丢了。兄妹俩只好轮流换穿哥哥的大鞋子上学, 妹妹下学后飞快地跑到约好的地点,把鞋子交给哥哥,每天如此。这是一段非常漂亮的 开头,一个完全电影化的表现,我们可以假设一幅幅兄妹俩奔跑的画面,这样的展开有 时间的容量,这样的镜头富于动感。可是再精彩的开头持续时间太长,同样让人无法容 忍,它必须寻找变化的切口。妹妹穿在脚上的鞋子很大,怕引起同学们的注意,所以她 经常低着头,并格外注意别人的鞋子,她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现她原来的鞋子穿在别的同 学脚上,兄妹俩跟踪这名同学来到她的家门口,兄妹发现这名同学的父亲以捡破烂为生 ,也正应了那句话——没想到你比我还穷。原来的鞋子不想要了,这时峰回路转,父亲 表示要到大城市打短工用赚来的钱为妹妹买一双新鞋。如此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结局也 算是皆大欢喜,父亲带哥哥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富人居住的街道上,贫穷却有希望在身, 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煽情段落,拥有相似生活经历的人会有一番酸酸的感动。情节发展 至此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父亲在城里骑车摔伤了腿,赚钱买鞋的愿望成了泡影。这样 结束这个故事还有点太早,必须重新挑起一个新的线头,引进新的情节因素。这个新的 线头和情节因素是学校要举办运动会,其中长跑比赛的第二名将获得一双新跑鞋。这对 兄妹俩无疑是一个振奋的消息,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要知道哥哥天天为了赶时间而 练习飞跑,这个从前的行为成了当下行为的铺垫。哥哥在赛跑的过程中瞄准了那双新跑 鞋,所以他在队伍中有意排在第二位。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人人都想争先,哥哥想保 持第二名目标的打算受到了威胁,哥哥顾不了那么许多,奋力向前猛冲。这对兄妹俩是 一个关键时刻,鞋子和希望都在前面,观众也一定屏住了呼吸,整个故事进入了高潮。 这是一组放慢的镜头,并伴以犹如鼓点般的放大的心跳声,画面上哥哥的每个动作在缓 慢的时间段落中得到了特殊的强调,显示了非同一般的雷霆万钧之力。可是,哥哥努力 过了头,最后获得了长跑的冠军。在场的人都向他表示祝贺,可哥哥自己却非常沮丧, 因为他失去了那双新鞋。伊朗儿童着实可爱,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他们比赛的目的如 此单纯,只是为了一双跑鞋。影片最后是一个充满灵性的结尾,哥哥把跑肿了的双脚泡 在养满金鱼的水池里,希望能让疼痛减轻些。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这部片子还有第三 个译名,叫《金鱼与运动鞋》,我觉得金鱼在整个情节中占的内容虽不多,但它却是一 个具有抚慰意味的感性化的意象,足以抚平哥哥因失去一双运动鞋而带来的忧伤。
越是简单的故事越需要埋伏许多机巧,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很多情节复杂的故事被 导演处理得很平淡,是因为创作者忽视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外在的眼花缭乱的喧嚣将他 的思维裹挟而去,使他忘记了寻找人物行为的心理依据,一个可能很有看头的复杂的影 片因此变得极其琐碎平淡。马基德·马基迪为这个简单的故事设计了一个曲折的情节链 条,通过丢鞋——找鞋——买鞋——争鞋等几个情节阶段,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变成了厚 重的充满诗意和人文关怀的文本。
《白气球》是与观众进行的一次智力的对弈。妹妹要买一缸金鱼,妈妈给了妹妹50元 的大钞。妹妹没有马上去买金鱼,如果妹妹买成金鱼,这个故事就不成立了。妹妹拿着 钱去看街头的卖艺表演,卖艺人收了在场的许多人的钱,包括这位小妹妹手里的大钞。 观众第一个反应是,小妹妹被卖艺人骗了!观众这时候直为小妹妹干着急,可是表演结 束后,卖艺人把大钞还给了妹妹,原来妹妹遇到的是一个好人。接下来,妹妹的大钞又 掉进了一个店铺门前的下水道。妹妹急得叫来了哥哥。一个路过的士兵主动提出帮忙, 并对小妹妹说他有一个妹妹跟她长得一模一样。观众的心又一次悬起,这名士兵是不是 一个坏人?士兵后来走了,一个卖白气球的人在竹竿上面粘了一块口香糖,把50元大钞 粘出了下水道。士兵这时又出现在画面里,他在站牌下等待着班车的到来。故事中出现 的都是好人,他们对小妹妹手里的大钞没有恶意的企图。这是一首轻声讲述的人间的赞 美诗,它不及《小鞋子》那样紧凑,但还是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心理,制造了一点点悬 念。
纪实中的虚构
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以虚构作为支点,尽管它表面上伪造了一副真实的假相。
在观看伊朗影片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混淆了想象与真实的界限,把它们当作 真实的读本。伊朗的导演们似乎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他们把真实视为最高的创作准则, 在创作过程中他们自觉地把权利让渡给事物发展的自然流程。
伊朗导演通过长镜头的应用、虚拟的片场、人为的穿帮等一些看似粗糙的制作途径, 向观众传达着某种真实的讯号。
长镜头的运用——
长镜头维护着事件在时间进程中的完整性,它是最贴近真实的电影语言,体现着现代 电影的叙事原则。在《穿越橄榄树林》一片中,有两段长镜头的突出运用。一处是剧中 的摄制组乘车向震后的灾区行驶,镜头对准汽车的前方的山路,随车速一起运动。镜头 在拍摄之前没有预先的设计,它和导演一样对未知的时空充满探索的欲望;一处是影片 的结尾,摄影机的机位设置在山顶,长时间地拍摄男孩子追求女孩子的过程。女孩子一 路下山,踏上了田野的一条小路,拐进了田野的深处。背对着镜头站在山顶上的男孩子 醒悟过来,他开始尾随女孩子的踪迹,下山,拐进了田野,我们看到镜头的深处两个小 圆点重合在一起,一会儿重又分开,一个小圆点开始沿着来路返回。两个年轻人之间发 生了什么事情?镜头说:它不知道,这样反而强调了某种真实。它节制地把自己限定在 一个固定的位置,它只看见两个年轻人变成了两个小圆点,它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它 掌握的就是这些局部的真实。
虚拟的片场——
拍摄现场进入了影片,犹如写出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的小说家马 原提示读者他正在当下写作一样,都是在骗取观众和读者的信任,越是告诉你这是假的 ,你就越是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些创作者把大家绕进了逻辑的怪圈。
在《樱桃的滋味》的结尾,扮演主人公巴蒂先生的演员出现在导演阿巴斯的身边,剧 组的工作人员在周围紧张地忙碌,这个场景从根本上瓦解了这个故事的真实,使它成为 作家电影的写作文本。
人为的穿帮——
穿帮是电影的行话,它是指电影在拍摄中不经意暴露出的破绽。这本来是电影拍摄与 制作中的一大禁忌,却被《谁带我回家》的导演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片。《谁带我回家 》叙述的是一个小姑娘放学后独自回家的故事。小姑娘在乘车的时候,突然摘掉手腕上 的纱布和头上的纱巾,面向镜头发起脾气来,她说她不想带着这些东西演了,并赌气地 跑下车,要自己回家。镜头一时失去了稳定,现场的灯光以及服装道具全部暴露在镜头 前。这时导演来了一个将计就计,跟踪实拍小演员独自回家的过程。其实,我们千万别 被突然出现的这一变故蒙蔽了,这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又一叙述圈套,原来的叙述方式本 来就是封闭和虚拟的,索性不如戳穿它、牺牲它换来一个真实的认可。观众是否注意到 ,小姑娘独自回家这个故事内核一点都没有改变,交换的只是另一种叙述方式。
实际上,这不过是更大的一场虚构。
伊朗电影以它的简单、真实和纯洁之美,构建了一幅天堂的图画,它里面的人物在困 境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追逐着希望的光辉,让我们从中找回到一种罕见的情感。我们 必须承认,在这个处处弥漫矫情的年代,伊朗电影使人类真善美的神话重新复活了一次 。
